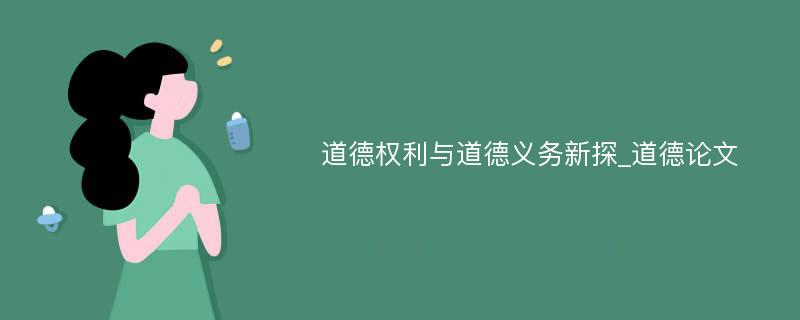
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问题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新论论文,义务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利定义必须包括资格、要求、权力、利益、自由五大要素。道德权利是构成人格的基本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的不相对应意味着人类生活理想状态的破坏。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既说明道德不以道德权利以外的利益为动机,也说明道德价值的崇高不为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分离、不为非道德的对待所动。
The definition of Right must include with five factors asfollows:ENTITLEMENT,CLAIM,INTERIST,POWER, LIBERTY, Themoral right is the most radical right which means why humanto be human,so it constitutes the radical priscriptive ofpersonality,The moral right identities with the moral duty,the non-corresponding between them means the violation to the ideal state of human life.The non-rihgt motivility of moral duty not only illustrates that morality does not hold the interests as motives except the moral right, but also illustrates that the of lofty the moral value does not effect by the devorce of the moral duty and the moral right,either the non-moral treatment.
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伦理学问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是不少,各种见解异采纷呈,但有许多问题尚未厘清,某些基本概念的含义及其使用颇为混乱,为此,深入探讨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问题仍甚为必要。
一、权利和道德权利
在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中,没有相当于现代权利概念的词。权利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以后的事情。随着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权利概念得到广泛的运用。《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和《法兰西人权宣言》(1789)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性贡献。自此以后,权利观念得到广泛的运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国际性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言》,它充分地说明权利观念在当代成为共同的人类意识。
权利一词具有广泛的哲学内涵。在现代汉语中,权利可直接分解为“权力”和“利益”两个方面,因其兼具“权力”和“利益”的内涵。但是,无论是权力还是利益,都不能单独地阐明权利观念的完整内涵。在一般意义上,权利往往被理解为不受干涉的资格。这种理解切中权利概念的内涵,但还不就是权利概念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起码不是作为哲学范畴的权利概念所必具的全部意义。既然权利是一种拥有利益的资格并拥有实现这种资格的权力,它就必然表现为一种实现自身利益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权在道义上是不可剥夺的。只有作为要求,权利的利益内容才会具体化。
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权利范畴不能仅仅从某一方面去把握, 而应从不同角度去把握。 权利起码包括以下五个要素:资格(ENTITLEMENT)、要求(CLAIM)、利益(INTERIST)、权力(POWER) 、自由(LIBERTY)。对权利进行考察, 可以以这五个要素的任何一个为原点,以其他要素为内容,进行综合把握。就资格要素而言,权利表示享有、拥有、实施、完成、要求某种或某利益的资格。资格是权利观念的核心要素,权利的实质、要旨是资格,享有权利意味着拥有资格。资格表现了权利作为人在社会关系中具有某种人格规定的内涵。就要求要素而言,权利表示因资格的享有而对在社会关系中负有义务的一方拥有要求权。要求权是权利的特征,因它赋予权利特殊的意义,使权利和一般利益区别开来。就利益要素而言,权利表示在社会关系中应当享有的利益。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构成权利的实质。利益要素是权利范畴的基础。权利作为利益,其实质是一种非竞争意义上的优势,即一种使自身得利而又不因此使其他任何人受损的利益。拥有权利,意味着权利所有者因赋者资格而要求或得到某种预想的利益。就权力概念而言,权利表示主体行使利益的一种力量、能力、优势。权利概念的权力意蕴既表现为道义力量(即权威),也表现为现实的经济、政治、法律力量。前者是基本的、无形的,后者是具体的、可见的。二者相互支持。就自由要素而言,权利表示因资格的享有而具有的不可侵犯性或不要干涉性。自由是权利的本质属性,对权利的侵犯或干涉意味着对社会关系的否定。在道义上可以侵犯和干涉的不是权利。这五个要素是相互渗透的,每一个对权利定义都是不可缺少的。可以以其中任何一个为原点,综合其他要素把握权利概念。若以资格为原点,则可以把权利定义为:在社会关系中,主体因法律、道德、传统的赋予而拥有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可干涉的享有、实施、索求和要求某种利益的资格或名份。
道德权利和权利是什么关系?道德权利是否存在?对道德权利概念是否存在这一点持否定态度者大有人在,比如,边沁把道德权利的观念形容为站在“高跷上的胡言乱语”。然而,承认道德权利概念的有效性者还是居多数。在我看来,道德权利不但存在,而且还是最一般、最基本的人类权利。道德权利概念不过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这种基本事实的反映。权利和义务概念一道,以应当的形式使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构成性制度中固定下来。义务表示利益关系的予的一面,权利表示利益关系的取的一面。有了义务和权利的规定,人类的利益关系就是具体的,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就是包含应当、正当的理想追求的活力的关系。所以,有了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就意味着个体在社会关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拥有特定的名份,具有了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皆体现了人格的道德要求的必然性和绝对性。可以说,权利和义务组成了道德人格的首要要素,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一样,乃人之为人之所在。由此看来,道德权利乃是基本的、普遍的权利,是权利概念的最一般的内容。这一点从权利概念的基本义即可看出。权利这个词和义务一样,最基本的含义都是应当、正当。权利和正当在大部分西文中都是同一个词(臂如英文RIGHT,德文RECHT,法文DROIT),权利从正当含义发展而来。中文的“权”即衡量、 度量的意思。以“权”的衡量来限制“利”,即是经过一定标准衡量过的正当利益。可以说,道德权利构成权利概念的最普遍的内涵或要素。事实上,正如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主要是施行方式上的区分一样,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主要是要求方式上的区分。在行为形式上,尽管二者可能各自有其独特的形式,但大多数是可以重合的。因此,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经常表现出一致性。从客观性而言,二者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利益关系出现差别的结果;从主观性而言,二者都是对规则所认可或保障的要求的范围的自觉意识。所以,道德权利从施行方式上说是为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由特殊的道德调控方式所维系的权利,从要求方式上说是索要相应义务的权利。
二、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关系
权利总是和义务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英文DUTY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DUE,即欠债应还之意。欠债应还,债主有索债的权利, 欠债者有还债的义务。因此,DUE还含有权利的意思。DUTY则又与权利RIGHT相对应。虽然追索义务所由派生的权利,或者追索与义务相应的权利,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在债务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总是被视为应当的。因此,权利和义务作为主体和主体之间同一关系中的两种相对的要求,有本质性的对应联系。
义务和权利的对应关系在理论上是个很明显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则是个具体地解决利益关系和利益差别的问题。在没有私有财产和利益差别之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分离的倾向,二者浑沌一体:对社会承担某种义务亦即行使自己的权利;行使某种权利亦即自己应尽的义务。在利益差别和矛盾的当代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和不一致则是一种现实。因此,权利和义务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改造问题。理论的探讨总是以理想性预测在客观上为实际的社会改造开辟道路。
社会生活的现实利益差别和矛盾的存在,决定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不可能是绝对对应的,只有表现为一种弱相关性。在理论上,权利的语言和义务的语言可以互换,一个人的权利迫使他人承担避免干预或提供某种利益的义务,而一切义务同样赋予了他人以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就不那么简单了。权利的主体所面对的承担义务的客体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比如,某甲借了某乙的钱,乙有索债的权利,甲有还债的义务,在这时客体是确定的。而象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这些一般的人权,其对象则不确定。也许可以说国家或某个集团是承担义务的客体,但国家或集团这个客体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承担多少义务,这往往是个不确定的问题。企业首脑有扩大企业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并不能直接课予他人以义务。同理,义务主体所面对的权利客体可能确定,也可能不确定。比如劳动义务,除了能确定自己是权利的客体外,其他权利客体则不容易确定。履行行善的义务,尤其不易确定权利客体,不能说谁对独立的个体具有要求履行仁慈义务的权利。因此,权利和义务从社会整体上说是应当相等的,然而在具体的生活领域仅仅表现为一种大体的对应。
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对应关系上的弱相关性,既有现实的根源,也有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关系自身的特殊性。
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对应关系是以应然的形式要求的,并非如政治法律意义上之权利和义务要求强制性的对应关系。就作为人格之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言,道德权利即为道德义务,道德义务即为道德权利,二者直接同一,自然是绝对对应的,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道德义务的对应性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相对应的必有之义。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从总体上说是相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的,二者方向相反。道德义务表现客体对主体的要求的客观社会关系,道德权利表现主体对客体的要求的客观社会关系。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位置可以随着主体和客体的位置的改变而互换。对于彼主体而言,此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于他是获得道德权利,此主体获得道德权利于他是履行道德义务,反之亦然。当然,履行道德义务并不一定赋他人予道德权利,获得道德权利也不一定课他人道德义务,但不同的主体之间总体上的道德义务的对应性是应该存在的。中国古代以对应形态表现出来的道德义务,如“五伦”、“十义”等,就是以道德义务的对应性确保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相对应的形式。其特点在于,强调人伦关系中某一方的道德义务的履行不以对方的道德义务为前提条件和强调人伦关系中双方道德义务的对等性的统一。在主体身上,道德权利意识是对与之相应的道德义务的深刻反思,亦即高度责任感化了的道德义务意识。就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整体的权利和义务而言,二者在实际的个体的行为中往往是分离的。对于道德人格而言,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无不对应,正如无人能强索道德义务一样,无人能强夺道德权利,二者本性是自由的。对于社会而言,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对应不仅是道德意义上的对应,而且必须是道德义务和超道德权利之外的政治权利、法律权利、经济权利的对应。对于个体而言,道德义务和社会的政治权利、法律权利、经济权利之间并无本质联系,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或然的、偶合的。所以,社会正面须以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具体的内心信念等特殊道德手段对道德权利加以维护,并且在这些特殊道德手段之后更加以硬性的强有力的政治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维护。否则,社会关系就将混乱,社会结构就将解体。
相应地,公民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应有以下关系:其一,平等性。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也负有平等的道德义务,此点须得到法律的强调和保障。任何人不得只享有权利而不负有义务,也不可能只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其二,互为前提。任何人要享有道德权利必须履行道德义务。反过来,每个履行道德义务的公民都享有相应的道德权利。每个公民既是道德权利的主体也是道德义务的主体,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在相互对待中存在。其三,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彼此结合。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合二而一。比如劳动和受教育既是每一公民的基本道德权利,也是每一公民的基本道德义务。第四,相辅相成。道德权利的保障促进道德义务的履行,道德义务的履行确保道德权利的享有。比如,履行尊重他人人格的义务,相应地会得到被尊重的道德权利,反之,公民得到人格尊严的尊重,相应地也促进其履行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的义务。
就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而言,二者何者为先?有人主张义务以权利为基础,认为在使某人尊重义务的正当方式是服务于另一个人的权利所依赖的利益的基础上,权利先于义务。比如,父亲有保证孩子衣食和受教育权利的义务。有人则主张权利以义务为基础,认为如果某甲不具有帮助某乙的义务,那么尽管甲应该帮助乙,乙也没有要求甲帮助的权利。相反,如果甲具有帮助乙的义务,那么甲就没有不帮助乙的权利,而乙则具有要求甲帮助的权利了。因此,具体的要求权利以义务为基础,具体的放弃要求权利则以不具有义务为基础。例如:印第安人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教育,无人能强迫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事实上,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只是人类利益关系的反映,无论是权利以义务为基础也好,义务以权利为基础也罢,二者都以人类的利益关系为基础。这是确切无疑的。在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决定权利和义务不平衡的情况下,强调权利的获得以义务为基础可能有反映社会的平等要求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权利的要求和义务的奉献不应仅仅以自身为目的,而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差别和矛盾。就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本身关系而言,一般来说,每一特定的道德权利在个体身上总是以道德义务为基础的。不完全义务作为供人们选择的行为,不赋予某个特定对象具体的权利,完全义务则赋予他人享有相关的权利。后者是赋予他人权利的公正义务,前者则是基于仁爱原则的义务。道德权利的实现以道德义务的履行为必要条件。反过来,道德权利的获得则客观上又促进道德义务的履行。在此意义上,道德义务是第一位的,道德权利是第二位的,道德义务是道德权利的核心。以义务为基础的权利对于期待他人以及要求保障我们的权利都具有重大作用。
三、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
如果说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不可执于一偏的,那么也可以说,行为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不以报偿为前提。换言之,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获得个人报偿,而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此即谓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
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不以个人报偿为先决条件,决不是意味着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是分离的、对抗的,只讲道德义务不讲道德权利,更不是否认道德权利的存在。相反,强调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不以权利为动机,是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在此,不为动机之权利是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权利在内的整体权利。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性与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是一致的。强调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性,就应该强调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而不是相反。如果说,坚持政治法律义务和政治法律权利的统一,其目的就在于使人们既要要求合法的正当权利又履行应尽的义务,反对只索求权利不尽义务的话,那么可以说,坚持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使人们以履行义务作为享受权利的前提,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以服务于社会国家利益为动机,而不是以个人的报偿的获得为动机。
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并不等同于康德的形式主义的“为义务而义务”。道德义务作为行为动机性特性在不同的伦理学中有不同的理解。康德强调道德义务动机的非功利性质,主要是针对个人的任性的贪欲。就此而论,舍其形式主义不论,为义务而义务是有合理性的。康德的缺陷在于,他对偏好的反对只停留于对道德的普遍性、意志自律性的形式主义的强调,没有进一步把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没有从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的统一关系中去把握道德义务的具体内容。所以,道德义务不以获得个人报偿为动机,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为义务而义务”,但不是康德的形式主义的“为义务而义务”,而是代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利益的现实道德要求。履行道德义务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动机或意图,但这种目的、动机或意图不是纯粹的个人私利、个人的权利,而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利益。
坚持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非但不是排斥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相反,只有坚持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首先,带着个人私利的目的或意图去履行的不是道德义务,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他之所以要尽道德义务总是不以获得道德权利为前提的。带着个人私利的目的和意图去履行的义务根本不是道德义务,自然也就谈不上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恰恰相反,其实质乃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背离,即无德者得福。换言之,只有在一个履行了道德义务的有德者身上,才谈得上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性问题。在此意义上,道德义务不以权利为动机,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统一的前提条件。其次,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不以权利为动机,不以报偿为条件,并不等于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之后得不到相应的道德权利,相反,道德义务的履行是获得道德权利的前提。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合理,就在于它是否给履行道德义务的主体赋予相应的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既是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结果的固有属性,也是道德义务的另一方面的要求。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与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统一性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不以权利为前提,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有德者的褒奖和对缺德者的鞭挞又赋之予以道德权利;一方面,主体履行道德义务不以道德权利为动机,另一方面,他人、社会反过来对主体履行的不以权利为前提的道德义务又赋予主体履行道德义务的结果以道德权利;一方面,个人履行道德义务的目的乃在于造福社会、他人,另一方面,社会又通过特定的形式,以一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的权利表彰履行道德义务的个人,从而使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相对应,并激励道德义务的履行。可见,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相对应的前提。综上所述,如果说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是真理,那么可以说,道德义务不以权利或报偿的获得为动机是更高层次上的真理。
就道德义务的履行和社会舆论的褒奖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言,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一个为善不颂、作恶不责,甚至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的社会,决不是公正理想的社会。因此,加强道德舆论的作用,改善社会道德风气,是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的应有之义,也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相对应的应有之义。舆论的完善的社会道德评价和内心信念的成熟的自我道德评价是道德义务行为的“催化剂”,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相一致的公正合理社会的主观条件。社会着意对道德义务的履行者进行表彰,这是激励道德义务的履行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的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相统一的方式之一。
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的原因之一在于,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方向不同。从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的关系角度来说,道德义务可说是在行为主体自知其特殊意志和普遍意志相关的前提下,由普遍意志指向特殊意志,特殊意志作为普遍意志要求自身履行与他人相关的行为。在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的关系中,道德义务强调的是特殊意志。与此相反,道德权利则是行为主体在自知普遍意志与自身的特殊意志相关的前提下,由特殊意志指向普遍意志,普遍意志作为特殊意志要求他人履行与自己相关的行为。在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的关系中,道德权利强调的是普遍意志。因此,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指向不同、本身就包含有二者不相对应的可能性。只有当二者都消遁于善的道德价值之中,在善的道德价值中得到“蒸发”,实现特殊意志和普遍意志的统一,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才会绝对对应。而这一点只有在建基于理想的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形态中才可能实现。到那时,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不再单独存在,因为它们都作为善本身而消遁了。
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和道德义务的自觉自愿地履行的特点是相互联系的。道德义务不仅仅是他人、社会对主体自身的行为要求,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主体自身对自己的要求。道德义务的自律性表现在道德义务使自身成为行为动机。出于主体自我的要求而非外部强迫而履行的义务才能作为主体的行为动机。这是因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利益要求关系中,主体满足客体的利益要求的确证是在行为之后,在义务行为履行之前是无法满足客体的利益要求的。义务作为社会对个人行为的要求,社会总是从义务行为的履行后果来看待自己的权利是否得到满足。在这里,义务总是因外在强迫而履行的义务,总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权利的手段,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义务作为行为动机,不如说是权利成为行为动机。而在主体对自身的利益要求之中,主体满足自身的利益要求是在行为之前,即准备,打算履行义务本身就是满足自身利益要求的确证。义务作为主体对自身的要求,这个要求从行为的动机、意向上就可以表现出来。换言之,前者的利益要求是在义务行为之后才得到验证的,而后者的利益要求则是在义务行为之前就已开始了。
综上所述,道德权利是构成人格的基本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的不相对应意味着人类生活理想状态的破坏。道德义务的非权利动机性,既说明道德不以道德权利以外的利益为动机,也说明道德价值的崇高不为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分离、不为非道德的对待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