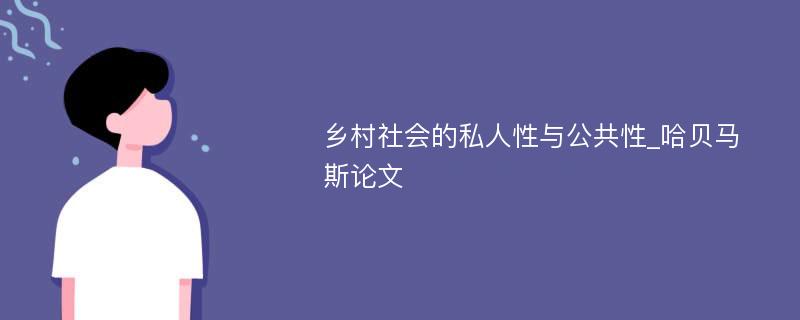
村社社会的私人性与代表的公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人论文,代表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国家与社会之间未形成领域上的分界,首先是因为国家社稷属于帝王一人,是一个“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濒,莫非王臣”:上至京城百姓,下至乡野村夫,一家一户都在君主的治下,都是皇帝的子民。一家得王权,便得到天下,一人成帝王,便得到天下臣民。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国王们的权力就受到教会和社会的制约。中国却始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尽管经过若干分裂时期,皇帝的权力从未受到过宗教或社会方面的制约。至高无上的君权对于帝王来说是一种真实的观念,虽然从政治治理来说,君主的统治要长治久安,就要“置民之产”,不可擅取民产,也要防止官吏擅敛民财。但是,从人们(民众和君王)共有的意识上看,既然天下是一家之私,在大私之下,普通民众只要自家的私产尚可得到维护,便不会去问自己的私人权利在这经济权利之外,还能在其他社会领域占有多大空间。
这种“家天下”之私却是同村社社会这个基础相互适合的。村社社会是一个私人性的社会。这种私人性,是各个孤立的、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私人的共同特性。这些私人之间的联系仅限于由于历史的血缘关系而聚居在一起,以及由于这种比邻而居的生活而产生的那些日常交往。他们照应着自家的田产和耕作,一家一户成为了一私产的继承和维护的单元,除开这个私的领域之外,其他的领域都几乎不存在。这种私人,用哈贝马斯的语言来说,是古典意义上的而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私人(哈贝马斯,1999,第33页)。这种前现代意义上的私人是其活动处于个人和家庭的切身所需的个人。他们个人及其社会联系受着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束缚,他们的劳动是较为纯粹意义上的私人劳动,这种劳动同其他社会成员极少发生契约性的分工合作,他们的经济是较为纯粹的自然经济,他们生产的所有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是自给自足,通常只有很少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在这个由一个个缺乏有机联系的私人的世界,将各个私人之私看做由一个大“私”来笼罩的观念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帝王被看做一个最大的私家也是合情入理的。私人之私所及领域的范围,是他的占有物——田产、房屋、牲畜与耕具、收获物等等。各个私人的占有物的总和,加上属于家族组织有限的族产,构成物质形态的村落。在村落之外,与其他村落交错的自然边界以外的世界,并不被看做一个无主的世界,而是被看做一个属于更大的私人的世界。这个最大的私家,不仅由于拥有了所有不属于一个个私人的资源,而且由于使它获得了这个资源的强大权力,而获得了对各个私人的统治权力。任何一家之私,如果获得了强权并将天下夺了去,就都要将那天下变成一家的天下。历史上,即令一个王朝的苛政被视为恶得不得了,因而被农民起义推翻而立起一个新的帝王,新的王朝也还是会走到那条老路上去,因为这天下又成为了他的一家之私,尽管开国的帝王常常会较多记取前朝苛政失国的教训,但这种教训的吸取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二
然而,帝王们的家天下却冠上“公”的名义。这个“公”,本义为区别于各个私人的私产和私事的财产、制度与事务,所以具有某种公共性之意义。然而帝王之“公”不是来自各个私人的,而是来自他一家对天下未属私人的事物和国家治权的独占。帝王的服饰、印玺、朝仪、举止、习惯乃至自我称谓和修辞方式,这一整套显示其尊贵的、独一无二的身份的“繁文缛节”,不仅被他的朝臣们,也被他的臣民,看做是表明他的权力的“公共性”的(哈贝马斯,1999,第7页)。
哈贝马斯在阐述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与领主权力的性质时使用的“代表的公共性”概念,对于分析中国帝王权力的本质性质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在欧洲中世纪的领主权力中,哈贝马斯指出,所有权与治理权是未分离的;所有权与(治理权的)公共性是一个意思,公共性意味着领主占有;特殊性和豁免性是领主所有制的真正核心,也是其“公共性”的核心(哈贝马斯,1999,第5-6页)。所有这些基本性质,在中国的帝王权力上都以更为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对江山社稷的所有权同治理权是不可分离的,获得了江山社稷的意思也就是有权治理它。据有了天下,使天下成为一家之私,同对天下臣民进行治理的公共性是一回事,因为这治理是面对所有人的;皇帝及其家室的私家利益同国家官僚机构的利益是未明确分离的,尽管皇后通常被限制不干预宫廷政事,因此皇帝并不在意说它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而在受治理的臣民方面,统治的权力无论是一家之私的还是被看做“公共”的,其实际效用都是一样的,因为这种统治都意味着自己的无权力。皇权的真正核心是对国家的独占权和司法的豁免权:皇帝作为主人是发布法律者,是在法律之外的。尽管一些朝代也有关于天子犯法当自刑自身的陈文,但是作为法律颁布者这种自刑仅具有象征的意义。
哈贝马斯将这种公共性称为“代表的公共性”,一个含义即是,它是间接的公共性,而不是真实的公共性。譬如,如果我说,“我来代表你”,这意思就是,我不是你,但是我来代替你来做某某事,或说某某事。所以代表就间接了一层:我来代表你,但是这里发生了我是否能够完全地代表你或他(她)的问题。在政治生活当中,间接性是免不了的,因为人们不可能随时都聚在一起来讨论和做决定。如果国家的权力是民众的,君主是民众委托来代表国家的,那么他就是人民的间接的代表。而如果他本身就是国家,这国家的权力就只是他的而不是民众的,他所代表的就是其所有权、特权,而不是民众(哈贝马斯,1999,第7页)的权益。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君主降格为国家主权这个为全体公民享有的权力的代表,将治权交还全体公民所委托的政府。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国家的权力则向来不是民众的。中国的帝王,连同他的服饰、仪仗、语言、称谓等等,在民众面前构成一种代表和象征,在表面上他代表和象征国家,在深层含义上,他代表和象征的是他是“天子”——据有国家和天下的特权者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公”的概念仅仅是对帝王作为这样一种地位的象征和代表的间接的表达。
使这种色彩得到极大强化的是一种不但为统治者,而且为所有的人共同持有的一种关于普遍秩序的观念:这种秩序是由“天”的运行确定的,帝王这个可以私有天下的人是“天”之子,“天”将这个使“天下”专属于他的特权赋予了他。这个观念是汉代前后的知识分子,带着对这种无形的巨大权力的敬畏,演绎形成的。这种观念也自然地被村落中人们接受下来,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对一种令他们感到卑微的莫名力量的惶恐。帝王诚然乐于以这样的普遍观念做自己的“天子”地位的辩护,因而他的号令也借天之名被命名为“奉天承运”的“诰命”。然而,这个观念所含有的、在他背后的那个神秘力量其实也同样令他惶恐。
三
“公”的观念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它最早是作为“私”的对立面而形成的。《尔雅》将“公”训为非私。随着历史的发展,“公”的观念发生了复杂的含义。它的正面意义原本是指原始氏族制度的公有资源、利益以及有关的制度和事务。在远古的观念中,凡未明确划定属于一个私人所有的无主资源,便属于“公”,即属于共同体集体共有的资源,这两者之间是未加区别的(注:William T.Rowe.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J].Modern China,1990.(3): 317.罗厄(Rowe)在那里引述的是日本学者Mizoguchi Yuzo的观点。)。这就是《礼记》所说的“天下为公”。在远古时代,许多自然资源都被视为这类“公”产。以后发生的变化在于,由于这类资源逐步地变得有限,它们逐步地被视为属于一个个村落共同体,因而具有了排他性。这类资源与利益随着历史的流逝而越来越稀少,常常是一些属于村落里的共有的水源、湖泊、山林、水井等等。
尔后,在中国绵延积久的帝制传统中,“公”的观念获得了指称未加明确区别的帝王之私和“朝廷”、“国家”、“官家”的意义,成为了帝王、国家、朝廷的象征。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对这种象征的公共性具有深刻的需要。君主即国家,他的私人事务仅仅是经他的努力才得以同朝廷政务分开,即使这样也仍然难得逃过大臣和宫廷侍从们的耳目。国家在吏治层面上即是官家,它们的这种含义在人们的观念中一经形成,便由于政治与制度的现实而成为“公”的观念的主要和基本的含义。官吏们处理的文书称为“公文”,在朝廷和衙门做事称为“办公”,处理政务称为“秉公办事”。
“公”的观念尔后又产生了第三种指称意义,它被用来指从各个私人那里通过募集、捐赠而获得,或者从国家税赋分拨下来专属于一个由私人构成的共同体整体,而不再属于各个私人的那部分资源和利益,以及同这种利益和资源有关的事务和活动。同样重要的是,这部分资源和利益以及相关的事务、制度和活动也不再被看做属于国家的。
“公”的观念的第一层含义只是在古典文献中还具有实质意义。它的后两层意义是它的主要的含义,而这两层含义时常是含糊的。它究竟是指何者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辨分清楚。许多语汇,例如“公事”、“公务”、“公差”、“公用”、“公费”等等常常可以含有这两种含义中的任何一种。说话人通常无需特别地表明,因为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两种含义的区别是明确的。一个朝廷官吏对属下说他是“秉公办事”,他说的“公”通常指朝廷或国家。一个地方民间人士说他近来“公事繁忙”,他所说的“公事”则通常是指他所服务的地方组织的公共事务。言说者有时也会感到一种将两者区分开来的特别的需要。例如,就如巴斯替德注意到的,清末刘坤一在回忆录中就曾明确区分了他对“国”的责任和对“公”的责任(注:M.Bastid,"Official Conceptions of Imperial Authori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Stuart Schram(ed.)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87.158,178.)。不过通常说来,“公”的两种含义之间的差别不像“公”与“私”之间的区别那样明显,后一种区别影响着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定式。
四
费孝通先生尝言,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村居民的最大的毛病是“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种毛病的最好写照(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诚然,这句话并不是说,没有任何人会帮助另一家打扫门前雪,但是它描述的中国人的“自顾自”的习性是真实的。人们的确已经习惯于对自家之外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所以,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共用的院子必定满院荒草(费孝通,1998,第24页)。而且,倘若某个人置自家门前雪于不顾,或是在扫完自家门前雪之后又去扫别人家的门前雪,还可能被指责为多管闲事,甚至被诬有巴结献媚或窥探他人隐秘之意。这种习性终于使得中国人看周围与自家无关的人们的事情有如观看西洋景一样,他们会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无论那个或那些人处于多么紧迫的情境中而需要得到帮助。
这种“私”的毛病当然还不仅仅在于“自顾自”,而且在于凡不是自家也不是其他某个邻人私家的东西,便被看作是“公家的”,便觉得是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费孝通,1998,第24页),每个人都急欲要取回自己的一份,并试图在他人不注意或无力抵抗的时候,把别人的那一份占为已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2册,第16页)“公家的”一词的最清楚的意思就是不属于自家,但是捞得了一份便算得到了一点便宜之物。清朝末年的一位西方传教士曾经记述了这样的场面:
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干完活才能通过。农夫砍树,他会把树横倒在路上,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把树砍倒、搬开为止……杀猪的、理发的、肩挑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融为一体。更有甚者,女人把被褥拿出来,晒在街上,因为他们的院子远不如街上来得宽敞(注: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95-96.)。
无论属于祖传的公产、皇家的王土,还是众人合作兴建的水井或其他设施,都是“公家的”,因为不属于自家。凡“公家的”便是捞一点便宜算一点,没捞得就是倒霉的。所以,人们争相以从“公家的”东西里面捞便宜,仿佛是一场有趣的竞赛游戏。
自上古时代之后,中国人经验中的“公”就或者是对圣人所描述的远古共有制度的依稀回忆,或者是身边的在人们口头上和文献上广为传播的帝王的“公”,或者村落里面少数可怜的公共设施,例如水井、道路、桥梁、水渠等等,或者——也是更普遍的情形——是所有这些的总和。祖传的公产已渐渐丧失殆尽,少数公共设施则常常是官府拨出一定资金并由保甲摊派各家徭役而建成的。这些设施在村民们看来与其说属于所有的人共有的,不如说是属于官府的。“王土”本是皇家私产,仅仅因为它不是人们自家的,便也被称作“公家的”。这三种“公家的”事物的观念之中,皇家权力与私产借助皇权通过官吏的统治,无异是被视为“公”的事务中最重要和基本的东西。普天之下皆“王土”,凡不属于一私家的事物,便都算是皇家的“公”产了。最多是,天高皇帝远,皇家既然未能委派官吏管辖此地,我开垦而用之,也是为这“公”家增添的财富并减少了一户饥民。
五
是什么使得中国人形成这种“私”的毛病的呢?这是梁启超、梁漱溟那一两代知识分子绞尽脑汁想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梁启超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自视为奴隶和盗贼,而国人自视为盗贼,乃是因为帝王以天下为自己一家之私,使臣民成为奴隶和盗贼(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册,第58页)。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其实并不比西方人更自私,中国人表现得不顾及公益,是某种制度使然,西方的制度使西方人公与私结合,积久而成自然(注:梁漱溟.中国文化的要义[A].梁漱溟集[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395.)。
梁启超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尽管还不是最终的原因:帝王之“公”的内里其实是一个“私”,一个笼罩着各个私人的“私”的“大私”。由于它的“公”不真,于义理和逻辑上不通,它如何培育得出基层社会中的“公”的倾向?作为真实的公共性的“公”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作为生活规则的公共性,和作为公共善(产品、服务、财产、设施、场所等等)的公共性。规则的公共性只有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基于各个私人的同意,才具有合理性。帝王颁布的规则和法律,并不因它们是来自一个地位至尊者便具有了此种公共性,它们的公共性只能合理地来自将接受其约束的各个私人以某种形式表达的同意。公益的公共性只有当它是来自各个私人的自愿贡献才具有真实性,所以同样要基于同意。过去时代皇帝的赈灾与国家财政拨出的扶持基层公益工程的资金虽然都出自百姓的税赋,但由于税赋的征收未经过任何同意,且它们在此之后便成为了皇家的私产,所以这种赈济的物资和扶助公益的资金总是具有皇家慈善事业的性质,而失去了本有的公共性。国家的生活没有这样一种透彻合理的公共性原则,社会的生活中也就不会发生真实的公共性的关切。
梁漱溟接近于谈到了中国人这种“私”与“公”隔绝的制度上的原因,但是他未得深入进去。这种制度所以未曾形成,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中,国家与社会未分化为两个彼此区别和制约的领域,再进一层,则是因为在村社社会这个僵固的社会结构中,村社社会的范围就是公共生活的范围,公共生活极度不发育。村社社会使人们以家族聚居,以乡土为纽带,日常交往局限在村落的范围,日常生活的问题一向通过家族的血缘群体的系统来解决,这使得公共生活关系始终未得脱离家族的纽带而形成,使得公共生活的机构(某种中立仲裁、调节机构和掌握公共资源的分配的机构,等等)也从未摆脱家族村落的日常交往网络而形成。孤立的、缺乏相互交往的有机联系的前现代的私人是非自律的。私人自律是契约的交往关系的产物。这种契约的交往关系是可以通过法律来调节的公共性的交往关系。无论是商业的(通过市场的)和非商业性的契约交往关系,都假定了当事人同对方在法律确定的关系上(每一方算作一个人)的平等地位。这种关系,一般说来,只有借助人们对于陌生人同自己的某种平等地位的观念才能形成。
在村社社会状态下,由于公共交往关系难以形成,在各个私人之间无法结成重要的同每个私人相关的公共事务,私人因此也没有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主体性的经验。家庭仅仅是人们共同地生产生活必需品和新一代成员的共同体,它产生着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感情,但是不能成为培育私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自律精神的私人领域。所以,在私人的空间中始终未能分离出一个处理私人社会的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这个在私人社会中处理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如果是开放的、人们能够平等自由地来参与讨论的,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如同哈贝马斯所理解的,既可以对国家可能的过度控制进行抵制,也能够对私人领域的狭隘性进行批判。由于这样一个领域始终没有在中国基层社会中产生出来,当然也没有以制度的积累性方式发展起来,在基层社会,这种公共性关切就不可能在私人社会当中产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