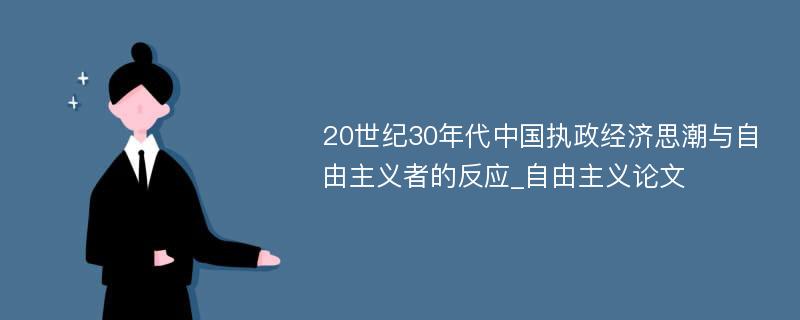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中国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者的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自由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6)02-0027-05
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发展危机,不得不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出路,出现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对“九一八”事变后苦苦探索救国根本之计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专制主义和统制经济“世界潮流”似乎意味着大势所趋。1933年以后,在中国学术界,既出现了“民主与专制”的大争论,也出现了“统制经济”和“现代化问题”大讨论。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等人关注于政治与文化问题,而忽略经济问题,除了介入“民主与专制”和“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争论,对“统制经济思潮”则持一种低姿态的怀疑态度,并未以经济自由主义立论、坚决地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局限性,是引人深思的。
一、朝野上下的统制经济思潮兴起
翻开1933年以后的报刊,就会发现有很多热烈谈论“统制经济”的文章。正如时人所论:
“近年来‘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等名词,在国内刊物上,成了很时髦的题目。”[1]“现在一般的知识界正在兴高采烈地提倡什么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等。”[2]
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的大势所趋的世界思潮:
“‘经济统制’‘计划经济’现在已变成了时代的标语,世界议论的洪水了。英国及美国的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与International Economic Plan ning,法国之Economic Dirgee,德国之Plan nwritschaft,皆鼎沸于论坛,酿成一般经济学教授不在讲坛上纵谈‘统制经济’就不足以显其本色的样子。”[3]“现在经济思潮的争论,是经济统制化呼声趣高的时候,这种呼声是激于经济恐慌的波涛中,成了现在经济界争论的焦点。”“这几年,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各国与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恐慌,拯拔这末日的恶运……最普遍有力的(手段)就是所谓‘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4]
当时的知识界拒斥自由市场经济,主张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确蔚然成思潮。1933年发行的《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征文中(26篇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化应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都非常少,绝大多数人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如大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形式,即主张混合方式的,约有9篇”[5](p.357)。笔者统计,明确主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仅有 1篇,占3.8%。这充分说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已成为当时思潮,而自由市场经济备受冷落。
概观当时学术刊物上的有关文章,统制经济思潮大体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左翼认同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反对资本主义。如克己在1933年5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的《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指出,统制经济广义而言,分苏联“依共同意志总辖的经济”,“以营利经济为基本的,依国家权力的发动”的资本主义统制经济。前者是成功的,后者如意、英、德、美统制经济是变态的,“想克服资本主义机构内存在的本质的破绽,无异是一个梦想”。他认为统制经济发展的原因:(1)世界大战战时“统制经济”经验。(2)产业合理化运动的升华。(3)政治无力所引起的反抗运动。(4)世界经济的恐慌。(5)苏俄五年计划的成功。(6)集团经济思想的发生。[3]
叶作舟将“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当作一回事。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其采用“计划经济”的直接原因:其一,以利润为本位的资本主义,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和阶级斗争激化。其二,欧洲资本主义大战不得不采用“高度统制的计划经济”。其三,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各国萧条,“不得不有全盘的统制计划”。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会议”的无力,无法解决物价、金融、失业问题,因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消极的,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6]
第二种,认同法西斯统制经济的观点。如白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刊物《前途》发表《统制经济的两大代表形态:苏维埃计划经济和法西斯计划经济》,认为:“近年来尖锐深刻的普遍的经济恐慌中,对于无计划的自由主义经济,早已觉得失望”而怨声载道了,统制经济的呼声,成了现在的普遍要求。在两种统制经济形式中,法西斯统制经济与苏维埃计划经济有本质区别。苏联计划经济由中央集权强制推行,排斥赢利竞争,从纯理论出发,反对国民生活和历史传统。而法西斯经济,却是以个人的意志与事业家的精神来支配的一种现实经济制度,求阶级调和,尽量利用既存制度,使其有效的制度。意大利法西斯就是从意大利民族精神中产生出来。因而是中国应该仿效的。
第三种观点,对“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进行客观的研究,以之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或现代化模式。
如郑独步认为,统制经济就是以协调国民生活、发展国家经济为目的,对于国家经济行为总体加以合理统制,而扫除经济行为之矛盾冲突,因此,“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是)正相反的”。而现在是“以国家斗争为单位的时代,则经济行为不能不以国家的特殊意志加以适当的统制”,发达国家用统制经济提高国力以胁迫各国,而落后国家则以统制经济“整理发掘本国国富,期与各国并驾齐驱”,以“防御经济侵略”。中国由于“未能适应今日社会环境的需要,以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促进经济社会的向上与统制经济的迈进,故已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7]。因此中国必须采用统制经济以挽救民族危机。
张素民认为,“统制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是“有节制的资本主义”[8]。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与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这与亚当·斯密之自由放任政策完全相反。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绝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再退一步讲,即令吾国私人资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国现代化的可能,然而我们若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切恶果;我们又何苦重走别人已经走错过的道路呢?
罗敦伟是在蒋介石政府的从政书生。1933年他在《中国经济》《汗血周刊》《现代学生》《国闻周报》《首都新民报》《申报月刊》《银行周报》《复兴月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统制经济,并于1934年 5月出版十万字的《中国统制经济论》专著,是一位统制经济理论专家。
他在《中国统制经济论》一书中认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新的产物”,“在经济的组织上及生产过程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新制度、划时代的新制度”。“所谓统制经济即是与自由经济的对立”,“无论生产及消费之任何部门之自由,都应该服从中央意志,由中央统制机关,指挥统制”。“我个人的意见,以为经济统制与计划经济形式上是完全相同的”[9]。中国统制经济的目的:其一,“完成国民的自足主义,在计划之上满足社会的需要”,“求得国际借贷的平衡”。其二,“摧毁封建势力,完成中国产业革命”。其三,“用自己的建设来打倒帝国主义”。其四,“求得社会经济的向上”“平衡”,“永远消除对立的社会关系。准备大同的物质条件”。针对有人认为这样岂不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混同,罗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尽可埋头在事实上做去,不必争论这些不必争论的问题”,以掩饰他对“计划经济”的模仿。他认为统制经济是“当前中国唯一出路”,并从各个角度论述其必然性:大体上说,中国社会是变质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是封建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由于帝国主义的垄断,中国资本主义决无自由发展的可能。社会主义道路则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实行统制经济,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世界危机的机会,以国际的力量,集中人力财力并借用外国财力与技术完成巨大建设。中国文化的散漫和民族资本的弱小既说明统制经济的必要,又可减少实行的阻力。作者为推行统制经济提供了一个详尽的蓝图:应先设立“经济参谋部”,可定为“统制经济最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专家、技术人员、行政院长和各部部长、次长。其组织系统为中央、地方两种。其任务:研究问题,制定建设程序,指导各省市建设,实行经济独裁等,它直属中央政治会议。具体措施:“提倡国营企业,也不致压迫民营事业”,“小规模企业由私人经营,大规模企业由国家经营”。“国营企业加特尔化”,“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后盾,以民生主义为目标”[9]。统制经济重点是重工业,轻工业由人民经营,利用外资和技术。对农业、商业、棉纺、钢铁等实行统制。其中“土地的统制”,是“复兴农村经济的基本问题”。
罗敦伟由于是国民政府的智囊团的技术官僚,因而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方案,许多内容为国民党政府采用。他在《中国统制经济论》中声称:“中国近来统制经济论调,忽然抬头。宋子文氏发表谈话,认为统制经济为世界共同趋势,中国非实行统制经济不可。汪精卫先生也曾经在中央纪念周上报告过,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论坛上也渐渐注意到‘统制经济’上来了。”[9](pp.119~122)
这说明“统制经济思潮”是由国民党政府高官提倡而又有知识分子呼应的思想与实践。罗敦伟本人不单纯是在野知识分子,他在《序》中说:
“1932年初到实业部以后不久,即主持中国经济年鉴的统纂事务。……因此,我同各项经济资料接触机会特别多,观察和分析的结果,觉得我国除非展开统制经济政策以外,绝对没有建设的可能,自然对于统制经济的研究更感兴趣,所以1932年底,即开始作这书写作准备。”
陈公博在《四年从政录》自述道,1931年他即倡统制经济,认为:“第一,中国商业团体本来不大健全,自经济衰落影响中国,无论任何事业,皆希望国家予以助力。第二,中国实业所希望于国家保护者多……一切实业,无不与政治为缘。第三,中国为农业社会,组织力本来微弱不堪,若与外国的资本对抗,除失败以外,无其他路径。”[10](pp.124~125)
陈氏1932年1月5日接任实业部长,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提出四年实业计划。1933年宋子文自美归来,已知棉业危机的严重,首先和陈公博讨论棉业统制问题,10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成立的机构是棉业统制委员会,冠以“统制”二字[10](pp.46~47)。
因此,统制经济思潮,是“九一八事变”尤其是 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当时朝野寻求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救国方案。这种自上而下权威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必然。
二、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怀疑统制经济思潮,搁置经济自由主义
胡适等理想型自由主义者,其思想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即政治文化理念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却不是经济自由主义,因此很难对当时的统制经济思潮提出有力的批判,遑论从理论上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了。
胡适早在1927年就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以后的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露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组织不能真正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的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家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大势力的分子。十年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服最有势力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这是社会化的新宗教新道德。”[11](pp.8~9)
但是,胡适赞扬的“社会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我是主张‘那些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想有资产阶级存在。二是避免‘阶级斗争’的倾向,逐渐享受自由,享受社会的方法。这方法我想叫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 ism)。共产党的朋友说,‘自由的社会主义是政治哲学’。”[12](P.43)
胡适认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因此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也就缺乏维护资本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内涵,也就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反对统制经济思潮。而且,其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不喜欢追逐形形色色的思潮,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因而自觉地同各种打着“主义”旗号的思潮保持一种隔离。比如对于 1933年《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胡适撰文《建国问题引论》,对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几十年的革新工作,无论是缓和的改良运动,或是急进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太偏重主义,而忽略了用主义来帮助解决问题。……‘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这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短时期就能解决的。这件建国的工作是一件巨大、极困难、极复杂的工作。在这件大工作的工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参考采抉的作用。”[13]
既然对一切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他自然对介入当时时髦的“统制经济”思潮不热心。但忽略经济自由主义,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参照系和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来看,是一种缺陷。正如李大钊所说,主义与问题是辩证统一的,主义既是一种价值立场,也是解决大问题的一种思路。胡适以实验主义态度放过了“统制经济思潮”,也搁置了经济自由主义,对此他几十年以后有所反省。
同样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丁文江则从民族主义近代化和实用理性立场,主张“新独裁主义”,把“新独裁主义”作为“统制经济”先决条件。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实行统制经济条件》,认为:首先政治统一是建设前提,“政权一天不统一,统制经济是一天不可行的。中国是一个整个的经济单位;要使得富源利用合理化,生活程序现代化。“第二个必须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三个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现代化”。其中第一、第二个条件正是他“新独裁主义”的主张。他在文章最后说:“许多人眼看国家危亡,急不暇择,以为用统制经济的政策,可以促进政治的统一,缩小外国的势力,改良行政系统。我认为这不但是舍本逐末,反果为因,而且是病急乱投医”[13]。显示其对政治统一之“新独裁主义”的重视和对统制经济的怀疑。
在同期“独立评论”中,前溪撰文《统制经济问题》认为,“统制经济者,各个国家,各在其国某种经济主义之下,平时或临时,为某种目的,作(做)成一种整个有系统之经济之计划,在某种经济制度中,而以国家统治之权力施行之。”但“某种主义”,“某种目的”,“国家的权力”,“某种组织”,在中国均是“一个X”,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于统制经济是否可行于今日中国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前提的,这前提便是请求拿具体计划先给我看”。这也是从实用主义立场提出怀疑,并未进行明确批判。
宋士英在同期《独立评论》上撰文《山西省的统制经济》,从国家统一的立场,批评山西统制经济的分裂。他对统制经济只是发了一番牢骚:“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是列强的殖民地,就是思想上学术上,也同样是人家的殖民地,因此不论什么事,总要窃取外人的名词理论,来作例证,来作号召。”
前溪与宋士英二人是否是自由主义者还乏材料证明。
蒋廷黻在1933年至抗战前未对“统制经济”发表过论文,而是作为从政书生,鼓吹“新专制主义”。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声称,他与胡适区别不在自由主义理念,而在于二人对政治与经济何者优先轻重缓急的理解不同。胡适注重政治与思想,几乎忽略了经济问题,而他注重经济问题[14](p.142)。他对胡适的评价是中肯的。然而他鼓吹“新专制主义”,难道是经济问题?当然蒋氏本人在1941年明确地发表文章,不赞同“统制经济”,而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他在1941年《新经济半月刊》撰文《从无为而治到统制经济》,认为统制经济是资本高度发达与工业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原因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所说,是资本主义发展自然形成统制;一是国家主义所说的国防需要;第三是战争需要。他认为中国本是无为而治政治和自然经济,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和工业,故而没有实现统制经济的条件。他说:“孙中山先生虽热心民生主义,他反对破坏,反对阶级斗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工业和资本根据不存。我们的问题不在破坏现状,而在建设将来……时代的认识,这是大政治家之所以成为大政治家之最重要条件……我以为当今要图不在统制,而在扶助自由经济……这对历史的现阶段去找出路,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15]
但他在文中仍主张国家政权的作用,因此他并非完全是经济自由主义者。
1932年11月1日,蒋介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蒋介石的亲信钱昌照拟定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名单:“军事方面有陈仪、洪中、杨继曾;外交方面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教育文化方面有胡适、杨振声、张其昀;财政经济方面有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杨端六、刘大钧;原料及制造方面有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交通方面有万国鼎、沈字瀚、赵联芳等,一共有四五十人。”[16](p.107)从此许多人才被网络到国民政府中,成为其智囊团。一些活跃于二十年代具有政治抗议特征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成为体制内具有极端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对粮食、资源、交通、金融、财政等实行统制。翁文灏任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成立经济部,翁文灏任经济部长。在翁文灏领导下,大后方国民党的国家资本得到发展,保证了国民党抗战的物质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形成毛泽东所说的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17](p.1149)的现代化模式。我认为,国民党这种以“统制经济”为旗号的“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没有如苏联计划经济那样,取消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国家资本垄断下的市场导向的权威主义与市场主义结合的现代化模式,不是人们所一般认为的官僚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尽管不乏自由市场要素,但国家政权的权威主义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起着某种压抑的反面作用,是一种不规范的扭曲的市场经济。
因而胡适在50年代演讲《从到奴役之路说起》,总结历史经验,对自由知识分子为国民政府以“统制经济“为旗号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之推波助澜的历史作了反省和忏悔:
“中国士大夫阶级,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大势所趋。……在政府里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把持了中国的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多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以上)许多中国士大夫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18](pp.170~172)
然后胡适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不过是勤俭持家。这样胡适改正了几十年前漠视“经济自由主义”的错误。这是对三十年代“统制经济思潮”的迟到的反省与批评。自由主义尽管内涵丰富,但总起来说有基本的内涵,它是一个包含哲学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的每一方面,对于面对现代性挑战的中国社会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简介]张连国(1962-),山东莱州市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比较政治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5-11-28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