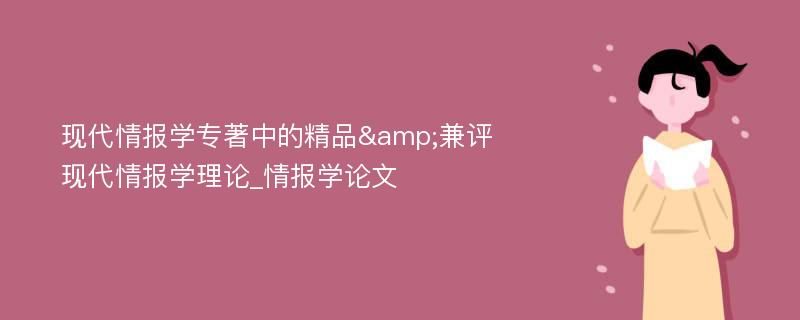
现代情报学专著中的精品——简评《现代情报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简评论文,专著论文,情报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6年岁末有幸较早地拜读严怡民教授和他的博士生们合著的《现代情报学理论》一书,不胜欣喜。酣畅之中颇有些感慨。情报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几与现代社会同龄。溯其源流,本与图书馆学一脉相承,欧美同行称为“图书馆与情报学”。循其发展,则情报与信息(信息论亦产生于二战时期)始终维系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概念之争持久未息,终至形成90年代我国将“情报”改为“信息”之举。严教授等的专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客观地说,90年代之前的情报学(至少在中国)只是科技情报学,在整体上并未上升到一般情报学的理论层次。90年代初的“情报”改“信息”风潮及其后持续至今的概念之争触发了情报学领域的“大学科”意识。本书作者提出“大情报”观就是颇有代表性之一例,他们试图通过科技情报学的外延扩展解决上述概念之争。大情报观的“核心是要求情报服务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密切结合,面向经济,面向市场,面向社会,改善服务方式和管理,增强服务功能,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情报需求”[1]。与此相关,情报学也将成为“全方位地研究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的情报及其活动圭律蹬科学”[1],我们姑且称之为“大情报学”。大情报观与大情报学正是《现代情报学理论》的理论精髓。
根据大情报学的思路,《现代情报学理论》充分拓展了情报学的理论空间,其论述范围涉及情报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扩充后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用户情报行为研究、信息交流理论及其量化研究、信息产业结构及发展战略、社会经济信息化、信息系统以及情报政策与法规等等。可以说,这样的体系结构基本上是一种宏观结构,它始于用户情报需求及其行为的研究,重点是信息交流理论和信息系统理论的阐述与研究,最后终于社会信息化以及宏观的信息产业和情报政策的研究,由微而著,井然有序,深合情报活动之规律,兼且融合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可谓集情报与信息之大成。
大情报学的另一必然发展趋势是从科技情报学拓宽到一般情报学。如果我们深析和比较90年代之前的情报学理论专著或教材,则可发现其体系结构主要是由情报学方法、科技文献交流过程、现代情报技术的应用和情报系统管理四大板块组成的,其核心是科技文献的处理与检索。反观《现代情报学理论》,科技文献交流仅存在于半个页码的空间里而成为信息交流的一种模式;作为新的理论核心的“信息交流”还包括通信的数学模型、传播学模型、社会学模型、管理学模型、情报学模型等多种模式,而所有新的模式较之“科技文献交流模式”都具有一般理论的通用性价值。更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探讨是关于情报信息交流的定量研究,信息交流中时间、空间的对数变换,学科(行业)的对数变换,信息衰减与增殖原理和信息传递的保真原理与冗余原理等等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量化推导,凭添了大情报学的理论魅力。从多侧面、多层次、多维的角度分析,此书也确有许多独到之处。
总之,这是一本情报学概论性专著,但它超逸出传统的路数,打破了程式化的表现方式,以得心应手地融汇多学科的广博理论知识和实用技术方法的功力,以新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的科学语言,对情报学做出了精湛、深邃的诠释。
大情报观和大情报学是信息时代情报学理论的升华,不仅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更具有显而易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还应指出,此书作者队伍的“豪华阵容”也保证了该书以集体的努力达到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国际水平。第一作者在情报学界已功成名就,年岁已近70嵩寿,但仍不断进取,积极发展和提高情报学,实在难能可贵。可以说,这是心中涌动着使命感、责任感,秉持着科学良知,沤心沥血写出的一本学术精品专著。
当然,与所有事物一样,该书也不可能尽善至美。例如,“情报”与“信息”时而并列平行,时而互相包容(更多的时候是情报包容信息),似可商榷。信息交流“栈”理论等也需再推敲。对于大情报学和与第一作者在同一情报学博士点的另一位博士生导师胡昌平教授倡导的“信息管理科学”[2]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现实论题论述得不够。还有,我们认为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以最浅显、明确的语句科学地、通俗地说明就足可以了,不必追求玄奥与华丽,因为著述的目的是使人便于理解和接受,因为归根结底科学的道理本来就是简单的。
综观全书,《现代情报学理论》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情报学专著中的精品。
标签:情报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