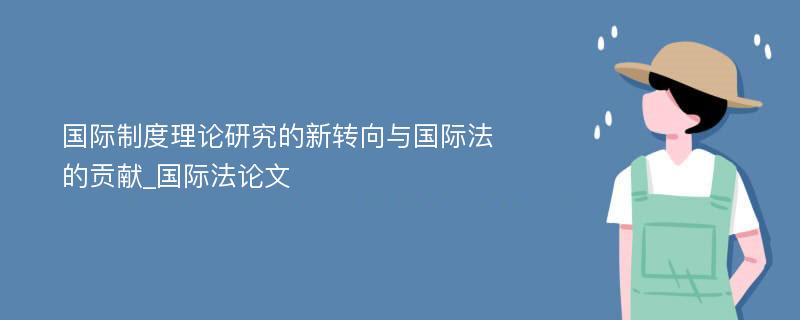
国际制度理论研究新转向与国际法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法学论文,贡献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学自学科诞生起,一直通过从相关学科中汲取理论、观念和方法而不断得以发展。其中,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具有相互交叉的研究志趣和研究议程。虽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个学科之间彼此隔绝、平行发展,不过,这种彼此间“相互忽视”的情况在冷战行将结束之时得以改观,学界有意识地利用两个学科的知识和理念,提高了解释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合作研究已经“步入舞台的中心”。①可以说,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
不过,当前的跨学科研究也存在着显著不足,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跨学科合作出现了不对等的状况。大部分双方合作研究的著述都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解释国际法现象,很少关注国际法学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可能贡献,双方对话出现了不对等的情况。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简·克莱伯斯(Jan Klabbers)认为,国际法学者致力于取悦国际关系学,尤其是现实主义,因为只有现实主义运用国际法的语言来阐述其自身的世界观,国际法才能够具有吸引力。比如,国际法的约束力依赖于国家自身的考量。②基于“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无法超越政治”的认知,国际法学者常常被要求严肃对待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学者常常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因素无法全面掌握国际法的理念、观点与方法。
其次,跨学科合作中存在明显的学科偏见。国际关系学对国际法的学科偏见导致了跨学科分析上的不足,部分国际法学者籍此质疑或反对跨学科合作。由于跨学科合作更多地借鉴了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问题,因而,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之间交流的不对称引发了严重的跨学科紧张关系。③这种紧张关系表现为不少国际法学者害怕国际关系学对法学的“入侵”,由于国际关系学者理解并运用的法学知识迥异于多数国际法学者所持的立场,因而国际法学者对合作持反对态度。有学者指出:“跨学科的学者总是且不可避免地产生屈服。跨学科的学者往往将某一学科的词汇、方法、理论与特质运用到另一学科之中。总之,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中弥漫着权力的气息,权力往往向国际关系学科倾斜。”④
最后,跨学科合作面临认识论的挑战。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认识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对知识概念的界定、知识的来源及知识的种类。⑤同时,更多地主张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强调对国际事务的观察和检验。而国际法学界在认识论问题上具有多样性,既有对国际法的规范、实践进行价值评判,也有分析国际法的社会背景,还有部分学者对法规进行实证分析。不过,多数国际法学者忽视实证主义的作用,仅从法律权威出发,将法律作为权威的来源,明确把国际法研究内化为对法律来源的研究,因而国际法更多地表现为对条约文本与实践的描述。比如,英国比较法委员会主席、肯特大学教授杰弗里·塞缪尔(Geoffrey Samuel)认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相比,宣言式的、形式主义的或明文的法律方法内在地决定法律宣言的有效性。⑥因而,从专业上说,国际法是一门很强的学科,而从学理上看,国际法又是一门相对较弱的学科。⑦
当然,上述跨学科合作的挑战并非说明跨学科合作在根源上就有缺陷,而是说国际法学者不要被跨学科合作的塞壬女妖歌声所迷惑,跨学科合作有可能导致对国际法的误解与误用。就其本质而言,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的跨学科合作之所以吸引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科占据了“同样的概念空间”,而是因为作为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同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即探寻相似的问题并使用类似的方法论。⑧如今,很少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法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微不足道。比如,很多学者认为国际法在深化国家间合作过程中发挥了持续的作用。国际法学者也反复强调法学虽然是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但从来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封闭学科。因而,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能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西方国际制度理论出现了新的研究转向,这种转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制度的组织转向,即从国际制度研究转向国际组织研究;二是国际制度的治理转向,即从国际制度研究转向制度治理或全球治理研究。这两个学术转向是国际制度理论形成20多年以来最为重要的变化,这既为国际制度理论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给国际制度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
如果说国际制度理论的产生受到了经济学的显著影响,那么,国际制度理论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了国际法学的持续智力支持。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⑨在国际制度理论的新近转向中,国际法学可以提供相应的知识工具,国际法学为国际关系研究开启了新的、有用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议程。国际法既对国际关系学者理解国际合作的原因与结果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重新阐述国际关系的手段。⑩可以说,国际制度理论的新近转向为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的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可能机会。
当前,我国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跨学科合作逐步发展。从国际法学的阵营看,刘志云、徐崇利与王彦志等都积极倡导跨学科合作。(11)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王逸舟、王铁军、朱锋、张胜军等学者也积极倡导跨学科合作,尽管这种合作的具体成果较之国际法学阵营要少。(12)国际制度理论的新近转向则为我国的跨学科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本文将首先论述国际制度理论新近的两次转向,即组织转向与治理转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关联研究视角出发,尝试运用国际法的相关理论、观点与方法来分析制度理论的转向及其潜在影响,阐述国际法学在制度理论转向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显示,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跨学科合作有助于提高国际制度理论研究过程的可控性与准确性,增强制度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推动跨学科合作领域的进一步扩展,进而提升认知世界事务、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能力。
一、国际制度理论研究中新的转向
国际制度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通常而言,国际制度理论建立在国际机制概念基础之上。不过,国际制度理论的直接缘起则可以追溯到1972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13)可以说,国际制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14)国际制度理论自形成始,所面临的第一个急迫的理论命题是制度是否有效。可以说,国际制度理论研究议程是从有效性研究开始,期间经历了遵约与履行、理性设计、非正式制度、委托—代理研究、国际授权,直至最新的国际制度密度与复杂性研究。纵观40年的研究历程,国际制度理论具有丰富的研究内涵,对世界事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跨学科合作方面,1989年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跨学科合作的主要关注点,双方跨学科的合作集中研究国际法律制度、进程及结果。(15)就国际立法而言,国际机制理论与博弈理论模型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影响,并被整合进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研究文献之中,尤其表现在对弹性条款、争端解决设计、软法硬法的选择,以及制度复杂性的论述之中。在制度进程研究方面,遵约打下了国际制度与国际法共同的印记,包括了早期的执行学派、后来的工具主义学派与规范学派的观点;履行研究也同样如此,建立在条约基础之上的履行为国际协议如何在国家层面得到执行提供了一条途径。制度结果的研究主要关注国际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超越制度本身的更广泛结果。不过,国际制度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及将国家偏好设置成外生给定的立场,具有局限性。
在国际关系理论内在发展与世界政治现实外在挑战的双重压力下,近年来,国际制度理论出现了新的研究转向。一方面,为了寻求解决自身理论面临的内在冲突,国际制度理论转向了国际组织研究;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国际制度理论同时也出现了治理转向。
(一)国际制度理论的组织转向
国际制度理论的发展有一条内在主线,即从早期的具体国际组织研究到国际制度研究,直至新近出现的回归国际组织研究。如果说早期的国际组织研究与后来的制度研究烙下了《国际组织》杂志深刻印记的话,那么,新近出现的组织转向的标志是两份新杂志的创立:《国际组织评论》(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与《国际组织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udies)。尤其是于2010年创刊的《国际组织研究杂志》,致力于为国际组织研究者提供一个讨论国际组织的进程、功能与活动,并对组织治理进行比较、讨论和分析的学术平台。(16)
应该说,国际制度概念替代国际组织概念是国际关系研究者汲取早期国际组织研究相关教训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组织研究主要关注国际组织形成的条件、构成国际组织的法律基础,以及国际组织的内部因素。具有方向标指向的《国际组织》杂志在这一阶段一直重点讨论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正式官方国际组织。比如,对联合国投票权的分析及受美国政治学影响的对联合国系统内部政治的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术界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由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Haas)、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K.Jacobson)等人开创的国际组织政策制定自主性特征及其影响研究。(17)不过,早期的国际组织研究也涉及对国际政治体系特征,以及国际组织发挥功效的运行机制方面的内容,因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文本主义。比如,英尼斯·克劳德(Inis Claude)出版的《铸剑为犁:国际组织的问题和进程》,撕去了有关“道德和信念”的标签,以鲜明的现实主义视角,对国际组织的性质与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该书出版后多次再版,至今仍是国际组织研究的必读之书。(18)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早期的国际组织研究被国际机制研究逐步取代。一个明显标志是在国际机制研究逐步兴盛之时,哈罗德·雅各布森等人对国际组织内部关注的研究反而没有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原本具有内在联系的国际组织研究与国际机制研究,作为对立物被明确区分。国际组织研究被国际制度研究所取代,原因在于理论构建需求与现实政治发展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组织研究缺少具有统领性的、可操作的概念框架。尽管早期的制度研究提出了组织透明度、正当性等观点,却没有办法将其统一在一个概念框架之中。莉萨·马丁(Lisa L.Martin)与贝思·西蒙斯(Beth A.Simmons)认为,由于没有一种概念框架可以把这些有价值的想法结合起来,也没有一种系统的比较研究来整理出其规律性,(19)造成了国际组织研究相对凌乱、静态的状况。戴维·埃利斯(David Ellis)从组织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鉴于国际组织在组织理论开放系统框架下的运作,为国际制度取代国际组织成为首要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经验教训;(20)二是20世纪70年代起的国际政治现实导致了国际机制及更广泛的国际制度研究的兴起。这一时期,美国霸权衰退使得人们一方面开始质疑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垄断地位,并注意到跨国界非政府或次政府层面交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担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机制的护持问题。(21)直至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学派仍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出于学派论战的考虑,学术界集中关注国际组织的分配与合作功能,国际制度这一称谓最终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取代了国际组织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主导概念之一。
不过,国际制度理论的研究议程也具有明显的狭隘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更多地关注国际制度的结构影响,而对其关注并没有办法解决国际制度的遵守与成员国的承诺问题。为此,罗伯特·基欧汉试图借鉴国际法学的相关知识研究国际制度的遵守问题,即美国政府在何种条件下遵守而不是违背国际承诺。(22)然而,这一研究纲领遭遇了挑战,由他亲自主持、他的学生共同参与的“美国的国际法遵守”研究计划项目最终还是失败了,这对他本人学术研究产生不小的影响。(23)不过,他的学生、美国哈佛大学贝斯·西蒙斯在国际法遵守研究上做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她通过自利与声誉的关联分析,论证了国际法对国家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努力最终促使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开始重新关注具体的制度安排,即具有部分权威与自主性的国际组织研究。
国际制度研究的组织转向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浮出水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组织在解决军事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肯尼思·阿博特(Kenneth W.Abbott)等人提出了国际组织不同于国际制度的两个特征:一是中心化,即管理集体行动的稳固的组织结构和行政机构;二是独立性,即在给定领域自治行动的权威和中立。(24)国际组织具有自身的领导机构、工作人员与预算,具有动员内部资源的功能。因而,在现代官僚主义的理性—立法权威看来,国际组织具备了等级特征、非人格性及专家特征。国际组织一方面具有理性—立法权威,另一方面通过自身行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道义权威。在国际机制分析大行其道之时,由于对国际官僚机构运行缺乏兴趣,国际组织动员内部资源和制度的经验传承(institutional memory)方式很少被学术界关注,往往被误认为是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控制较少所致。(25)
当前,学术界有三种定义国际组织的概念:作为正式组织的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机制的国际组织,以及作为国际机构、秩序和原则的国际组织。(26)这三个概念分别对应早期的国际组织研究、国际制度研究及新近转向的国际组织研究。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焦点在于国际组织的设计与运行,以及国际组织的自主性与权威。应该说,这两项具体研究议程都与国际制度遵守、承诺命题联系在一起。正是对国家遵约的关注,重新引发了学界对正式国际组织的兴趣,以期解决与国家承诺相关的问题。国际组织设计研究继承并发展了制度理性设计专辑中有关制度特征、设计变量以便解决合作难题所进行的探讨。当前,这一研究最富有成果的方面是探索设计各种具有弹性的机制,比如,保护条款、退出条款、期限条款及保留条款。因而,这些设计条款能够有效地应对国际制度遵守问题。
国际组织的自主性来源于成员国的授权,被授权的国际组织参与协议的履行、修订和监督,具有解决争端和履行遵约的权力,这些行为对签约国产生了重要影响。(27)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克(David A.Lake)等人认为,授权国际行为体一定的自主性,有助于提升这些行为体的可信度、“锁定”受认可的政策、克服集体政策制定方面的不足。(28)当然,自主性与权威也会受到约束与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权力政治的存在、频繁的非正式管控措施,及强国选择场所的可能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组织的自治与权威。(29)成员国同样也可以对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倾向施加重要影响。一国可以利用投票权、任命组织内部工作人员、撤销资金赞助及介入常规政治活动,影响国际组织。(30)
国际组织研究的回归,反映了制度理论的重新定位。随着国际协议及具体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人们更多地关注实际的合作制度如何运作,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国际关系学界对合作问题的争论没有明确结论,近年来却出现了研究国际协议的价值及其功能的回归。(31)有学者感叹道:“研究国际组织的政治科学家近年来开始重回对正式国际组织的研究,尽管这次回归具有明显的理论意图。”(32)扎根于坚实理论基础之上的组织转向丰富了既有的制度有效性、制度设计、遵约与履行等领域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正式国际组织的相关文献不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关注协议的履行,对关键制度的遵守,这些构成了现今国际组织研究的领域。(33)与此同时,组织转向也揭开了与其密切相关的国际制度理论的另一转向即治理转向。
(二)国际制度理论的治理转向
当前,西方国际制度理论出现了另外一种研究转向即治理转向。从世界政治的背景看,治理转向的出现建立在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科林·海(Colin Hay)以复合相互依赖为基础,认为相互依赖包括社会领域的相互依赖(domain interdependence)与空间领域的相互依赖(spatial interdependence),前者包含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相互依赖,后者则是指空间范围和分析层次上的相互依赖。(34)由于全球治理关注在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政策制定与履行,因而,全球相互依赖导致了寻求新的全球治理方式。一套有效的全球治理制度由于其传递全球正义的能力,越来越成为人们期盼的目标。(35)当前,尽管国际机制的概念仍在使用,自由制度主义的关注点已经从作为国际制度特定形式的国际机制的建立和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转移到全球治理。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如火如荼,自由制度主义者更频繁地使用全球治理的概念,尽管事实上这两个概念都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36)
国际制度研究朝着治理方向的转变具有客观的必然。一方面,国际制度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随着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成立,全球治理的呼声和浪潮席卷了国际关系理论界,这既是对世界政治领域新事实的敏锐发现,也是国际制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国际制度成为世界事务治理的供给者,在全球治理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国际制度有效性已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全球治理的要素包括全球治理的价值、机制、主体、客体及结果,其中,全球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的关键要素。全球治理机制实质上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而采取的由多元行为体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机制。全球治理机制反映出全球治理与国际制度间的紧密关联,即全球治理是通过国际制度安排作为途径和中间环节来实现的治理结构。如果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确实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全球治理便很难落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奥兰·扬(Oran R.Young)认为,个体机制的运行已经产生重要结果,换句话说,制度的影响已经越过特定问题领域,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37)总之,国际制度作为治理的结构框架,构成了全球治理的核心。
另一方面,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多元化的政治主体、包罗万象的政治议题,而其中尤为紧迫的是日益增加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应对模式,这就是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也认为全球化需要有效的治理,这将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以及跨国网络而非世界政府的形式得以实现。但是,即便民族国家将许多当前的功能保留下来,一个逐步增加的、实现局部全球化世界的有效治理需要更广泛的制度。如果不希望全球化停滞不前或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促进合作及解决冲突的治理安排是必需的。(38)不过,从金融领域到生态领域,复杂的全球进程把世界上各团体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使全球层面的治理能力处于压力之下。(39)随着全球治理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发挥国际制度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制度理论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方面。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国际制度理论出现了治理转向。
当前,治理转向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长期以来,主流制度理论即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理性的单一行为体。自20世纪90年代始,全球化的加速进展与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跨国公司及个体精英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作用的发挥,直接挑战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既有观点。全球治理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过程,在实践中,各种治理模式并非界限分明,往往交汇融合、互相补充。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众多行为体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需求的相互信任关系,并由此出发,在相互依赖的全球政治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全球事务。这说明全球治理的真正实现仅仅依靠单一行为体的作用是不够的,需要依靠各种行为体的通力合作。多元多层合作治理被认为是全球治理在运作中最为现实且最具普遍意义的治理模式,就是明显的例证。当然,除了对国际组织等跨国行为体的关注外,当前,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也越来越重视诸如国内机制类型、国内利益集团,以及“遵约选民”(compliance constituencies)、政党竞争等因素。(40)
治理转向的出现,使得学术界能够更好地关注并探讨全球治理机制可能的负面因素,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治理机构的合法性缺失。一般而言,合法性包括五个方面:透明度(transparency)、责任度(liability)、可控性(controllability)、责任性(responsibility)及响应性(responsiveness),其中最重要的是责任性与响应性。(41)全球治理中存在众多组织,这些组织在不同的领域运作,其中一些主要由成员国构成,而另一些可能包括了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基于治理机构与主权国家间的多维关系,合法性问题的分析显得更加复杂。应该说,治理转向关注国际机构合法性,就在于合法性关系到多边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合法性缺乏将导致国际制度与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性下降,这是制度主义全球治理理论分析的显著优点。在此领域,罗伯特·基欧汉与同事合作还首次建立了制度合法性适当的分类标准,推动了全球治理机制研究和实践的渐进性发展。(42)
(三)组织转向与治理转向的关系
国际制度理论的新近变化对制度理论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制度理论的组织转向汲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组织研究的经验,在已有丰富理论的指导下,当前国际组织的实践为制度理论的自身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就治理转向而言,国际制度理论把握住了未来发展趋势,着眼于解决日益增加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治理需求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国际制度理论将沦为狭隘的研究项目,仅能提供专家应对国际层面特定问题的需求。(43)在自身理论建构与世界政治现实的双重挑战下,国际制度理论需要关注制度所造成的广泛结果,尤其需要在制度输出、结果及其影响这一因果链中,审慎考察国家在问题解决、行为改变与目标获得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国际制度理论的组织转向与治理转向紧密关联。组织转向与治理转向都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对相关规则、条约与文本的关注。国际组织的研究常常与条约紧密相关,国际组织如果要实现自身的宗旨,履行相应职责,就离不开协商、谈判与缔结条约等国际行为。有关全球治理的研究最终所关注的是相关规则如何出台、如何制定和完善的,关注这些规则是如何帮助制定集体行动的目标,以及这些规则是如何控制国际、跨国及国内行为体的各类活动的。(44)
同时,组织转向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研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与全球倡议网络都提供了全球治理机制设计与有效运行的途径。全球治理常常由于其合法性与透明度的不足而饱受批评,比如,在美国韦尔斯利大学教授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看来,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形式上不民主、道德上存有缺陷”的批评,“低效,而又不能实现资源从富国向穷国的转移”。简言之,就是治理不佳,理解也不透。(45)国际制度理论把研究重心重新聚焦于国际组织有助于深入分析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与公正性命题,弥补合法性方面的不足。总体而言,国际制度的治理转向与组织转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协调、相互补充,从而提高了国际制度理论在观察、解释世界事务方面的能力。
从发展角度看,国际制度的治理转向还有一层超越组织转向的涵义。影响国际制度理论的治理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术界近年来对正式国际组织研究的关注,限制了全球治理的形式选择和可能的治理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日益受到挑战,除国家之外的其他行为体越来越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研究者需要关注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全球市民社会及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除了关注正式的制度安排外,还需要把握联合声明、临时安排、行政性协议、口头承诺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二、国际法学对国际制度理论研究转向的贡献
国际法源远流长,自古罗马的万民法开始,国际法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主要的古老学科之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雪莉·斯科特(Shirley V.Scott)从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跨学科合作的角度界定了国际法的概念,国际法是治理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组织、个人及其他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之间关系的规则、原则和概念。(46)这表明在国际制度的组织转向与治理转向过程中,国际法学可以提供分析上的新视角,并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埃米莉·M.哈夫纳—伯顿(Emilie M.Hafner-Burton)等人在最近的一篇权威性评论文章中指出,国际关系学者从跨学科合作获得的收益可能为国际法学者特别感兴趣。(47)由于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方面是忽视了国际法的丰富概念与方法,马克·波拉克(Mark A.Pollack)与杰弗里·多诺普(Jeffrey L.Dunoff)提出了一份新的跨学科合作的“计划书”,呼吁国际关系学者认真对待国际法的思想,不要将其当作颅相学(phrenology),即认为人的心理与特质能够根据头颅形状确定的伪科学。国际法应该成为像经济学和心理学那样的与国际关系学紧密相关的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国际合作的原因与结果。(48)当前,国际制度理论的转向为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之间相对等的跨学科对话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国际法学与新近的组织转向
国际组织是国际法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由于国际组织是具有相对独立法律人格的一种国家间机构,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界对国际组织及其法律制度给予持续关注。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际组织由国家基于明确的条约建立,国家是其成员国,具有独立法人特征,能作为区别于其成员国的自治的法律行为体。(49)国际组织能够减少协商的交易费用,建立议题联系,增加成员间的互动,并为免费搭便车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因而能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分歧和争端。美国学者安德鲁·古兹曼(Andrew Guzman)认为,国际组织为国际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催化作用。(50)不过,国际组织一旦建立,其运作与最初的预期未必匹配,国际组织的影响可能损害而非帮助国家的利益。(51)这就是“弗兰肯斯坦问题”(Frankenstein Problem)。(52)国家希望通过创建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新实体,然而新实体却具有自身的生命力,不能被成员国完全控制。由于国际组织具有推动和改变国际法的作用,因而,国际组织的自主性成为国际法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具有共同的研究议程,国际组织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这可以从国际组织的概念、构成要素及核心特征等方面明显体现出来。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伊恩·赫德(Ian Hurd)认为,从国际法学的角度看,国际组织是依据条约的法律义务而建立的,而国际关系学者则将国际组织视为制度化的社会进程。(53)作为具有国际行为特征的组织,国际组织包含了三个构成要素:国际组织依据国际协议建立;国际组织至少有一个机构,使之与各成员区分开来;国际组织建立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国际组织的核心特征则包括了成员身份,权利与义务,组织架构,法律基础与权力,政策制定与监督履行机制。(54)总之,双方关注了包括国际组织的法律义务和国际组织的历史、结构、程序等众多方面。正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前任主席、英国学者伊恩·布朗利(Ian Brownlie)指出的那样,对国际组织和各种各样组织机构的全面研究是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55)国际组织研究已经成为连接双方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纽带。
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在国际组织研究上的“彼此发现”提供了双方跨学科合作的新契机。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对合法性与权威的共同关注,拉开了双方在此领域彼此合作的序幕。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都对合法性与权威非常关注,但却没有能够透彻地予以分析。国际关系学者对权力的论述非常多,但是缺少对权威的分析。(56)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权威需要得到认同,权威是国际组织合法性权力的一种特定类型。在此方面,国际组织提供了双方分析合法性与权威的共同平台。国际组织或国际法是否具有权威取决于自身的结构或内容,因而,社会背景构成了一种权威和影响。在国际法学者看来,合法性构成了一种社会背景,把分析视角转移至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社会背景及其结构与内容,有助于理解国际法的遵守并缓解国际法面临的各种压力。(57)
当前,共同的研究议程存在三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它们分别是绩效研究、组织设计与授权研究,国际法学在这些领域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研究启示。首先,制度有效性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基石、全球治理理论关注的核心,也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当前,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超越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的新视角,着手研究国际组织绩效。(58)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国际法学通过对遵约的论述为制度与组织有效性的评估标准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其次,就组织设计而言,国际组织的设计关系到国际组织的运转与发展方向。国际法学通过把弹性条款、保留条款、退出条款等补充进制度设计中,改善了设计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了组织运作的风险;最后,授权即国家将权威授予一个国际行为体,产生了国际组织的自主性与权威,而国际法学可以明晰授权对国际合作的意义与影响,并控制授权可能带来的损失。这些都是双方在组织转向中合作研究的具体表现,也体现了国际法学在组织转向中的可能作用空间。
国际法学界也对国际组织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选择,即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对国际组织的研究方法彼此相互补充。伊恩·赫德总结了国际组织研究的三种方法:契约主义、机制理论及建构主义,并认为它们均建立在国际关系学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契约主义将国际组织视为论坛场所,机制理论把国际组织视为行为体视角,而建构主义则将国际组织视为来源视角。不过,今后研究应该更关注国际组织做了什么,而不是国际组织说了什么或应该做什么。这促使他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国际法学,试图通过国际法学的知识体系分析国际组织的行为。(59)伊恩·赫德的研究表明,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三种方法从本体论上看是互相补充的。国际组织既是采取行动的行为体,也是其他行为体讨论争辩的场所,还是国家等相关行为体改进并提升自身政治议程的渠道。可以说,这一研究既是国际制度理论回归国际组织研究的重要尝试,有助于制度理论摆脱功能需求理论的束缚,同时也显示出了国际法学对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意义。
就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的选择而言,受国际关系学实证主义研究的启示,国际法学者也试图通过定量方法研究国际组织。当前,国际法学领域出现了数据搜集与数据库建设的持续努力,丰富了国际组织研究。其中,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芭芭拉·凯里迈诺斯(Barbara Koremenos)主持的“欧洲大陆国际法理论”项目便是一种多问题领域的制度设计定量分析数据库。这一项目从超过1550卷内容庞杂的联合国条约库中挑选了约300个国际协议,涵盖了经济、环境、人权及安全等四个领域,具体包括合作命题的履行问题、分配问题、不确定种类、承诺问题,以及有关外部性、症结和协调问题,并提供了具体的定义和案例。其理论根据在于合作问题是制度设计背后的驱动力,对于协议的比较需要理解试图解决的基本合作问题。编码员据此设计了超过500个有关制度设计的问题,不同的编码员通过将合作问题与制度设计联系起来,对理论进行检测。(60)该数据库为跨问题领域的国际法系统比较创造了条件,避免了制度设计理论可能出现的泛泛而谈。正如芭芭拉·凯里迈诺斯指出的那样,该项目深化了我们思考国际协议的视角,以及国际法对国家未来行为重要性的认识,这一数据库所发挥的桥梁作用对于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及法律与经济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61)
总之,国际组织是国际关系学产生早期的重要研究领域。如今,在历经组织研究、机制与制度研究后,它又重新构成了国际制度理论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制度理论研究的这次组织转向产生了丰富的研究话题,为国际法学的参与合作创造了机会。
(二)国际法学与新近的治理转向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使得全球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也形成了世纪之交国际制度理论的一次重要转向即治理转向。同时,治理转向也显示了国际制度理论未来发展的总体背景。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国际法学可以提供具有价值的理念与研究方法上的支持。10多年来,国际法领域出现了四个新的概念框架:互动国际法(interactional international law)、全球行政法(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国际宪政主义(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全球法律多元主义(global legal pluralism)。这四个国际法的具体研究方向为国际制度的治理转向研究及全球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
长期以来,不少国际关系学者对当代国际法理论持有一种错误和过时的看法,即国际法是一成不变的。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国际法学表现了过分的形式主义,由于过分关注法律规则的语言及忽视世界事务运作的实践而备受诟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国际法理论集中于证实、分析和批评法律文本与宣言。由于国际法是规定各主权国家间关系的习惯和条约规则的总体,因而,持续关注宪法、法令、司法见解及其他法律文本成为自拉萨·奥本海(Lassa Oppenheim)以降国际法学的核心。不过,当前的法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关注法律文本与条约本身。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秉承现实主义理念的国际法学者就认为国际法条文无法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际法学界出现的“政策定向说”和“国际法律过程说”都将国际法视为一种决策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否认国际法的规则性。(62)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法学界出现了门类多样的研究方法,比如批判法、女性主义、法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法领域新的理论分支不断涌现,其中互动国际法、全球行政法、国际宪政主义、全球法律多元主义等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些都进一步丰富并深化了面向新世纪的国际法研究,同时也为国际制度的治理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昭示了国际法学的学理贡献。
首先,互动国际法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芬·托普(Stephen J.Toope)等人提出,互动国际法不是一套条约、初生的司法体,也不是发展中的履行机制,而是一种实践共同体。(63)互动国际法的作用有三方面:其一,打破了法律的命令语式,减少了由制裁手段支撑的主权权威,这为国际法在国际层面发挥作用提供了新启示,即国际法规范在缺少核心权威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出现;其二,把国际法当作根植于社会理解力上的实践,国际法是具体化了的制度、一套编撰的规范,由国家立法并予以公开的权威解释。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都可以参与互动之中;其三,有助于解释法律义务的作用及其如何产生的。当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彼此互动履行实践时,便形成了对法律的忠诚,而这种忠诚就是法律的正当性所在。总之,互动国际法认为,共识、法律标准及法律实践对于形成明确的法律义务与法律规范,以及重视法律的承诺感至关重要。否则,法律价值就会受到削弱或被破坏。(6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克里斯琴·雷乌斯-斯米特(Christian Reus-Smit)指出,从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中形成的国际法的互动理论,将朗·富勒(Lon Fuller)的法理学研究方法移植到国际层面,并结合了国际关系学中的建构主义理论。(65)互动国际法关注被纳入互动进程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的组织转向在研究对象上保持了一致。同时,互动国际法也关注国际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组织、其他的认知共同体及精英个体,并认为这些行为体参与其中的互动框架,承认了国际社会存在的差异性,因而互动国际法理论同样也可以运用到全球治理研究之中。
其次,全球行政法的概念来源于国际行政法。国际行政法这一概念,最早可见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法学说中,主要指国际组织在处理劳动争议和其他内部事项中形成的规则、程序和机制。(66)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使得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法律制度发生了深刻革命,全球行政法取代国际行政法的趋势日益明显。全球行政法包括那些促进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全球行政机构问责性,特别是确保其达到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合法性方面的充分标准,以及对其形成的规则和决定提供有效审查的机制、原则、惯例和支持性的社会认同。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Benedict Kingsbury)等人认为,全球行政机构包括正式的政府间规制机构、非正式的政府间规制网络和协调安排、与某个国际政府间机制合作的国内规制机构、公私混合型规制机构和一些行使特别重要的公共性跨国治理职能的私人性质规制机构。(67)全球行政法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及不同层面的全球制度提供一种变化多端的全球行政空间,这一空间包括了国际制度、跨国网络及国内行政体,超越了传统的公私及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划分。(68)
全球行政法的首要功能是控制公共权力,要求法治得到遵守,并规定国际组织内部的相关行为。(69)其中,全球层面法治的意义就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具有稳固的一般性原则,以及诉诸法院以期解决争端的正式权利。(70)全球行政法的突出表现是法官统治,即全球司法统治授权法官拥有权威与法治能力。多伦多大学资深公法和政治学教授拉恩·赫希尔(Ran Hirschl)将法官统治的现象称为司法治理,意指司法审判的法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机构。他同时认为,司法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治理模式的最新发展,这一观点实际上拓展了治理转向的研究视野。
当前,全球行政法还处于形成之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具有司法管辖权的国际性法院,比如,国际刑事法院、欧洲人权法院、联合国海洋法法庭等。全球行政法的勃兴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主要功能就在于创建全球民主所必需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框架超越了一国政府内部的机构,通过倡导全球层面的民主、参与、透明与责任性理念,因而在由私人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层面的特定领域也同样发挥了作用。就全球行政法的发展而言,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如何调动并发挥公民社会在全球法律层面的作用,或许通过民主协商,全球行政法有助于推动并规范全球治理的深入开展。
再次,国际宪政主义或广义上的全球宪政主义主张运用宪法原则提升国际法律秩序的公平与有效性,致力于创立公正的全球秩序。(71)事实上,宪政主义研究的出现可以被认为是让那些在全球治理中没有结构化,以及自发秩序变得更加理性并具有可证伪性。(72)当前,全球宪政主义研究出现了功能宪政主义(functional constitutionalism),关注那些能够推动或限制国际法运作的规则,这一功能主义方法尤其体现在国际人权制度和司法管辖审议领域。此外,国际宪政主义研究还强调跨国政治领域的合法性,着手建立由宪法占支配地位的全球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建立世界政府,倡导世界宪法,是不少学者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世界政府模式是全球治理诸种理念的表现之一,世界政府体现了可能实现的政治实体的世界主义理念,前提条件是现有国家要削弱和放弃某些权力。在世界政府中,国际法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尽管世界政府模式是参照民族国家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具有等级特征的权威体系,存在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是,国际宪政主义的提出是国际法积极调整自身适应全球治理的体现,也是从国际法治迈向世界政府的重要标志,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是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这一方法体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国际法领域的运用。法律多元主义与法律中心主义相对应,其理论构建在法律全球化的基础之上,全球法将主要从社会外缘发展起来,而不是从民族国家和国际体制的政治中心发展起来。(73)法律多元是指既包括官方法也包括非官方法,官方法是正式的、国家层面的成文法,非官方法是非正式的、民间层面的习惯法。当然,法律国家中心主义并不完全排斥全球法律多元主义,它可能承认全球法律的多层次性。出于对国际关系学者只关注国家间互动单一模式的不满,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观念。国际层面的多元主义关注法律秩序的若干特定方面:法律制度进程的参与者、法律的来源、法律实体间互动的数量。(74)也就是说,全球法律多元主义不只是提供游戏规则,而是包括游戏的参与者在内,都构成了游戏本身。因而,全球法律多元主义准确地把握了全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多元治理主体的现状。
国际法学在治理转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同样是对合法化与合法性的关注。合法性是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国际法学的介入提升了国际关系学对此问题的认识程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教授肯尼思·阿博特等人在新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合法化是指“政治的一种明显形式,由现有的实体法所形成和限制”。他们试图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性主义视角与国际法的规范视角相结合,考察合法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基于利益的国际机制在理性主义中表现明显,而规范渠道则在国际法和建构主义中更为突出,而合法化就是实证因素与规范因素互动的产物,即利益与价值互动的产物。(75)这表明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国际法的规范性。实际上,在跨学科合作中,合法性研究是国际法学可以做出更多贡献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互动国际法、全球行政法等法律概念中汲取有益养分。
比如,互动国际法为如何判断国际法的合法性提供了观察方法。在互动国际法中,明确的法律正当性不仅能形成对专门规则的一致性看法,也有助于维护法律规则自身的权威。通过法律规则的建构与维持,国际法的合法性得以形塑。如果没有一致的共识,那么法律规则与规范很难形成,合法性当然也就无法谈起。建设互动国际法也就是通过形成共识来创建国际组织与全球合法性,可以通过社会互动和社会学习的进程来考察共识的出现与演进。(76)一旦共识形成,共识就会成为形塑行为体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行为体对利益形成的认知及如何设置优先议题方面的基础。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这一共识就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合法性的明显例子。
总之,全球治理要求各国公民能够成为行为得体的全球公民,这为跨学科合作提供了契机。(77)在此方面,国际法可以培养全球公民意识和全球共同体意识,使公民们学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包容多样性和差别的同时,积极维护和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此,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注意到国际法学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那种认为国际法是固化的偏见,既无法从理论上推动国际制度研究的深入,也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现实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双方在理论上形成持续的互动,并有效运用于具体问题领域。应该说,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的关联研究已经成为跨学科合作的重要例证。虽然国际关系学一般把国际法认定为由国家制定的基于条约的实体规则,不过,国际法学者对法律的研究存在不同的途径和理论分支,很多方法能够补充和弥补国际关系学的盲点。国际制度理论就是双方跨学科合作、推动研究深入开展的重要平台。
国际制度理论目前主要关注国际协议的设计、授权国际组织权威、国际司法独立的状况与程度、驱使国家遵约的因素、制度扩散引发的制度密度增加等方面。当然,国际法学者同样也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具体而言,国际法学关注国家与国际行为体的功能联系,以及制度成员、组织设计与政策制定程序的细节。(78)双方研究议题的重合迅速推动了跨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因而,国际法学为国际制度的组织转向与治理转向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价值。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国际法学为国际关系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有用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议程。国际法学既对国际关系学者理解国际合作的原因与结果提出了批评姿态,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重新阐述国际关系学的手段。(79)
我国的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跨学科合作如今已经摆脱了严重对立的状况,开始走上跨学科合作的道路。不过,与西方学者在跨学科探索上所取得的成绩相比,我国国际关系学科与国际法学科的“联姻”面临着种种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国际法学者的“一厢情愿”,而非彼此默契配合、“情投意合”的产物。当前,国际制度理论的组织转向与治理转向为国际关系研究者在跨学科合作中发挥更大作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然,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用各自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多样化的解读,常常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跨学科研究概莫能外。
作者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Oona Anne Hathaway and Harold Hongju Koh,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New York:Foundation Press,2005,p.2.
②Jan Klabbers,"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International Law or The Forgotten Politic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1—2,2005,p.41.
③Jeffrey L.Dunoff and Mark A.Pollack,"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roduc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in Jeffrey L.Dunoff and Mark A.Pollack,ed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State of the Ar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1.
④Jan Klabbers,"The Bridge Crack'd:A Critical Look at 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1,2009,p.120.
⑤Colin Wight,"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2,p.35.
⑥Geoffrey Samuel,"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he Authority Paradigm:Should Law Be Taken Seriously by Scientis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Vol.36,No.4,2009,pp.432—433.
⑦J.M.Balkin,"Interdisciplinarity as Colonization,"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Vol.53,No.3,1996,pp.949—970.
⑧Jan Klabbers,"The Bridge Crack'd:A Critical Look at 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 p.124.
⑨路甬祥:《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年第1期,第58页。
⑩Jeffrey L.Dunoff and Mark A.Pollack,"What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April 9,2012,p.37,http://ssrn.com/abstract=2037299,2013-03-17.
(11)刘志云:《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学的互动:从概念辨析到跨学科合作》,《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第54—59页;徐崇利:《构建国际法之法理学: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之学科交叉》,《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25页;王彦志:《什么是国际法学的贡献:通过跨学科合作打开国际制度的黑箱》,《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13—128页。2011年,由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的创刊就是国际法学界更大范围努力的明显例子。参见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1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王逸舟:《重塑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关系:面向以人为本、社会为基的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6—12页;王铁军:《世界政治的法律化:国际制度主义理论的新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40—46页。此外,《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还发表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合作研究的专题,分别刊登了王逸舟、朱锋、张胜军三位国际关系学者的文章。
(13)纪念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学术贡献的论文集具体分析了这一观点,参见Helen V.Milner and Andrew Moravcsik,eds.,Power,Interdependence,an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4)不过,2012年,罗伯特·基欧汉发表文章,回顾了制度自由主义(Institutional Liberalism)30年来的研究历程。他认为,国际制度理论应该来源于约翰·鲁杰(John Ruggie)1982年的学术贡献,即当年发表的《国际机制、交易与变迁:战后经济秩序中的嵌入式自由主义》一文。相关论述分别参见Robert O.Keohane,"Twenty Years of Institu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26,No.2,2012,p.125; 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79—415.
(15)Emilie Marie Hafner-Burton,et al.,"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Law:The State of the Field," Working Paper Series,August 23,2011,pp.69—71,http://papers.ssrn.com/so13/papers.cfm? abstract_id=1764082,2013-03-19.
(16)Kirsten Haack and John Mathias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udies:A New Frontier for Scholarship,"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udies,Vol.1,No.1,2010,p.6.
(17)Ernst B.Haas,Beyond the Nation 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Robert Cox and Harold K.Jacobson,eds.,The Anatomy of Influence: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18)Inis L.Claude,Jr.,Swords into Plowshares:The Problems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56.
(19)[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20)David Ellis,"The Organization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ory," The Journal of l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udies,Vol.1,No.1,2010,p.16.
(21)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0页。
(22)Robert O.Keohane,"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Politics within a Framework of Law," The ASIL Proceedings,Vol.86,1992,pp.176—177.
(23)相关情况介绍参见Robert O.Keohane,"Introduction: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Robert O.Keohane,ed.,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New York:Routledge,2002,p.9.
(24)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2,No.1,1998,p.8.
(25)Bob Reinalda,Routledg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Routledge,2009.p.9.
(26)Alexander Thompson and Duncan Snida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stitutions and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in Boudewijn Bouckaert and Gerrit De Geest,eds.,Encyclopedia of Law and Economics,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
(27)Barbara Koremenos,"When,What,and Why do States Choose to Delegate,"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Vol.71.No.1.2008,p.164.
(28)David A.Lake and Mathew D.Mccubbins,"The Logic of Delega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Darren G.Hawkins et al.,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43.
(29)Randall W.Stone,Controlling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2.
(30)Andrew Guzman,"Doctor Frankenstei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king Paper,2011,p.17,http://works.bepress.com/andrew_guzman/58,2013-03-19.
(31)Barbara Koremenos,"The Contin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Working Paper,2009,p.4,http://sun4.mzes.uni-mannheim.de/publications/wp/wp-128.pdf,2013-03-20.
(32)Alexander Thompson and Duncan Snida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stitutions and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326.
(33)Ibid.,p.316.
(34)Colin Hay,"Introduction:Political Science in an Age of Acknowledged Interdependence," in Colin Hay,ed.,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an Interdependent Worl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12.
(35)Ibid.,p.22.
(36)Thomas Diez,et al.,Key Concep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11,p.120.
(37)Oran R.Young,"Regime Theory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Governance," in Al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eds.,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Coherence,Con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89—90.
(38)Robert O.Keohane,"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1,2001,p.1.
(39)[英]戴维·赫尔德、凯文·扬:《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2页。
(40)Joseph M.Grieco,et al.,"When Preferences and Commitments Collide:The Effect of Relative Partisan Shifts on International Treaty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3,No.2,2009,pp.341—355.
(41)J.GS Koppell,World Rule:Accountability,Legitimacy,and the Design of Global Govern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33.
(42)Ruth W.Grant and Robert O.Keohane,"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1,2005,pp.29—43.
(43)Oran R.Young,"Regime Theory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Governance,"p.102.
(44)[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第三版修订增补本)》,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页。
(45)Craig Murphy,"Global Governance:Poorly Done and Poorly Understoo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6,No.4,2000,p.789.
(46)Shirley V.Scott,International Law in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0,p.1
(47)Emilie Marie Hafner-Burton,David G.Victor,and Yonatan Lupu,"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Law:The State of the Field."
(48)Jeffrey L.Dunoff and Mark A.Pollack,"What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Law?" pp.2—4.
(49)Ian Hurd,"Choice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udies,Vol.2,No.2,2011,p.8.
(50)Andrew Guzman,"Doctor Frankenstein's International Orgnizations," pp.24—25.
(51)[美]何塞·E.阿尔瓦雷斯:《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蔡从燕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51页。
(52)《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于1818年创作的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博士力图创造出有生命的人。通过无数次的实验,他创造了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物,而这一怪物脱离了造物主的控制,并杀死了无辜者。弗兰肯斯坦这一原型在国际关系中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对照,为分析国际组织的自主性提供了新颖和有说服力的视角。参见Andrew Guzman,"Doctor Frankenstein's International Orgnizations."
(53)Ian Hurd,"Choice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9.
(54)Ines Dombrowsky,Conflict,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An Economic Analysis,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7,pp.77—78.
(55)[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01页。
(56)国际关系学界对权力问题最新一次大规模关注是2010年10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退回基本部分:当代世界的权力”研讨会。相关情况参见http://www.princeton.edu/pcglobal/conferences/basics/。
(57)Martha Finnemore,"New Directions,New Collabor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omas J.Biersteker et al.,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Routledge,2007,p.274.
(58)《国际组织评论》杂志曾于2010年发表了国际组织绩效的专栏,总体介绍参见Tamar Gutner and Alexander Thompson,eds.,"Special Issue on the Politics of IO Performance,"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5,No.3,2010.
(59)Ian Hur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olitics,Law,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60)Barbara Koremenos,"The Contin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pp.1—2.
(61)Ibid.,pp.22—23.
(62)徐崇利:《决策理论与国际法学说:美国“政策定向”和“国际法律过程”学派之述评》,载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1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63)Jutta Brunnée and Stephen J.Toope,Legitimacy and Leg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An Interactional Accou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7.
(64)Ibid.,pp.52—55.
(65)Christian Reus-Smit,"Obligation through Practice," International Theory,Vol.3,No.2,June 2011,p.339.
(66)林泰、赵学清:《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99页。
(67)[美]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尼科·克里希、理查德·B.斯图尔德:《全球行政法的产生(上)》,《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5期,第118页。
(68)Benedict Kingsbury,"The Concept of 'Law' 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0,No.1,2009,pp.23—57.
(69)Carol Harlow,"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The Quest for Principles and Valu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No.1,2006,p.191.
(70)Ibid.,p.195.
(71)Anne Peters,"The Merits of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Vol.16,No.2,2009,pp.397—411.
(72)Jeffrey L.Dunoff and Joel P.Trachtma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ization," in Jeffrey L.Dunoff and Joel P.Trachtman,eds.,Ruling the World? Co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Law,and Global Gover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3—36.
(73)[德]贡特尔·托依布纳:《“全球的布科维纳”:世界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清华法治论衡》2008年第10辑,第241—279页。近年来,包括国际法学在内的法学界跨学科合作不断扩大。2009年创立与发行的《国际政治、法律和哲学杂志》(International Theory: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aw and Philosophy),将国际法学、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纳入了跨学科合作的范畴。无独有偶,在中国,创办于2000年的《清华法治论衡》以整合法学理论、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前沿研究为目标,倡导发现与创建适合中国自身的法律与社会理论,在中西古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法学的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张力中寻找平衡与超越。
(74)Paul Schiff Berman,"The New Legal Pluralism,"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Vol.5,2009,pp.225—242.
(75)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Law,Legalization and Politics:An Agenda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L/IR Scholars," Working Paper,2012,p.2,http://papers.ssrn.com/so13/papers.cfm? abstract_id=2088556,2013-03-20.
(76)Jutta Brunnée and Stephen J.Toope,Legitimacy and Leg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An Interactional Account,pp.56—65.
(77)Jan Klabbers,"The Bridge Crack'd:A Critical Look at 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 p.124.
(78)Jeffrey L.Dunoff and Mark A.Pollack,"What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Law?" pp.21—22.
(79)Ibid.,p.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