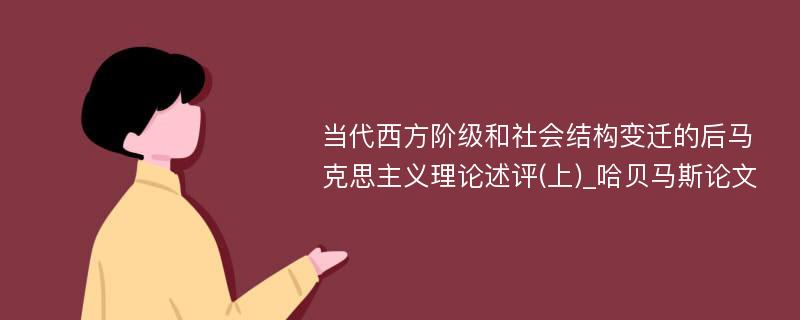
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阶级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56
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引发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危机”,此后,一股“后马克思主义”(注:所谓“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国际上一般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之后,流行于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广义上,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以来西方和东欧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都被纳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以最狭义而言,“后马克思主义”特指直接以这一称谓冠名的英国的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思潮在英、法、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流行开来。与70年代末以前的、以人本主义为主流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不同,也与同时期的、以后现代主义为取向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相区别,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一种哲学思潮,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活跃于20世纪后30年的后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对西方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作出了各种理论界说。
从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线索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是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所关注的不仅是卢卡奇等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重视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也不只是70年代末以前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所重视的工人阶级异化和新中间阶级的形成等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以新技术革命发生后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为理论聚焦点,围绕以白领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新中间阶级研究和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研究,形成了去阶级化的多元社会结构理论。本文主要对英、法、德、美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进行梳理并作出评介。
一、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从后阿尔都塞主义出发,以“话语理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加深了7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政治在西方的“危机”。以米利班德(R.Miliband)的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为起点,以辛迪斯(B.Hindess)、赫斯特(P.Q.Hirst)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和琼斯(G.S.Jones)的阶级话语建构理论为中介,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拉克劳(E.Laclau)和墨菲(C.Mouffe)通过他们在70年代末所主张的后阿尔都塞主义、新葛兰西主义的(工人)阶级“链接原则”和霸权理论,最终走向了去阶级化的多元主义的社会话语认同和激进民主政治。
20世纪70年代后期,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认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通过教育、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渠道,把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传导给大众,使工人阶级和大众认同他们的统治,从而取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和统治的合法化。教育、文化、宗教、工会、媒体等都已成为意识形态机器,巩固了统治阶级获得的社会认同,淡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
米利班德在70年代后期致力于揭露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他站在新葛兰西主义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具有思想文化职能,它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并向公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对资本有利的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任何其他生产方式都不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好。(注:Miliband,Ralph,1977,Marxism and Politic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同时,米利班德强调国家的政治职能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的阶级性和暴力垄断者身份。虽然近代福利国家制度缓和了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是镇压仍是国家最明显的职能。国家一方面直接参与阶级冲突,另一方面通过法律为冲突规定各种条件。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长期的宪政传统,但是一旦社会发生严重冲突,国家的镇压职能马上就会施展出来。(注:Miliband,Ralph,1977,Marxism and Politic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米利班德批判那些主张西方社会没有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多元民主”论等资产阶级思潮,指出其实质是否定“国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制度,它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中特殊的掌权阶级”。(注:米利班德,1997,《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商务印书馆,第7页。)此外,米利班德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变化的动态研究,认为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下通过改良主义获得国家权力。但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从各个方面扩大民主,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米利班德的改良主义理论尚未告别阶级政治,体现了左翼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
与要求阶级民主政治的米利班德不同,70年代中期,辛迪斯和赫斯特已经从相信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的“后1968年”(注:所谓“后1968年”是指以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的1968年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之后的年代。)激进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消极的改良主义者。他们“解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科学范畴,彻底抛弃他们先前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政治,开始接纳以西方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与此同时,他们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分析的解释建立在“再现”(representation)的概念之上,用“形式上的”、“逻辑性的”纯理论方式解构阶级分析。他们认为,马克思从《雾月十八》起,就预设了“被再现的”(the represented)的阶级、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以及“再现方式”(the means of representation),即“相对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将“再现方式”简化为“被再现的”,其后果是导致了阶级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这一“保守的阶级简化论和本质论”。(注:参见Hirst,P.Q.,1977,Economic Classes and Politics,in Hunt,A.(ed.),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9,On Law and Ideology,London:Macmillan:Hindess,B.,1987,Politics and Class Analysis,Oxford:Blackwell。)他们甚至反对“欧洲共产主义”对葛兰西的“非简化的”(non-reductionist)阶级分析的重新发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7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扬弃阶级分析,走向西方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
琼斯则是在其80年代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史的研究中开始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体论。他不仅批判马克思,而且批判汤普森,认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及所有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通病是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二元论,不能解释1847年以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革命性。他认为,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建构在“非指涉性的”(non-referential)阶级话语中的“阶级”,才是对“阶级”的关键把握。在7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以后,他提出应从独特的语言和政治性格,而不是阶级本体论出发来解释宪章运动。宪章主义话语才是理解宪章运动的要害,而这一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将罪恶和悲惨诉诸一个政治原因”,(注:Jones,G.Stedman,1983,Languages of Cla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05.)其抗争焦点已经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是权力。因此,琼斯强调宪章主义的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体论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根本不相容,要求放弃阶级本体论,把“阶级”变成一种话语建构。一些研究者明确指出,琼斯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注:陈宜中,“从历史唯物论到后马克思主义: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评析”,载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8年版,第50页。)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危机、英国新右派崛起和社会主义政治衰落的表现。琼斯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指责工人阶级政治在英国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保守主义甚至特殊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话语不再具有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效能。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放弃狭隘的阶级政治观,创新一种新的政治话语以联合多元的进步力量”。(注:参见Jones,G.Stedman,1983,Languages of Cla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5。)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则告别了后阿尔都塞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以话语多元论解构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多元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受“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拉克劳和墨菲先是接受了新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论,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的成功依赖于工人阶级对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霸权。但是,拉克劳指责普兰查斯(N.Poulantzas)将中间阶层理论化为中间阶级正走向一种“阶级简化论”,他认为中间阶层的政治特色不是阶级属性,而在于其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大众民主”成分。他还将所有的“非(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都纳入“大众民主”的范畴。在70年代中后期,他们分外强调“非阶级”和“大众民主”的重要性,认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于将所有“大众民主”的因素(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系统地整合进它的阶级话语中。(注:Laclau,E.,1977,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ew Left Books.)在这一阶段,他们仍强调意识形态霸权必然是阶级霸权,因为经济“最终”决定阶级政治的必然性。(注:参见Mouffe,C.,1979,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in Mouffe,C.(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他们仍把对没有阶级属性的中间阶层及其大众民主意识形态的争夺视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
到70年代末,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存在不应以具体的“阶级话语”,而应以抽象的“链接原则”(anticulating principle)来理解。(注:参见Laclau,E.,1977,Politics and Idel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ew Left Books,Ch.4;Mouffe,C.,1979,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in Mouffe,C.(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Laclau,E.,1977,Ch.2。)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链接原则”本身不是话语存在,但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链接各种潜在的反体制力量以创造工人阶级的霸权。拉克劳和墨菲的“链接原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危机的深度,他们实际上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非阶级和大众民主因素已经压倒了工人阶级话语,社会主义话语不再具有链接大众民主因素的霸权功能。到了80年代,拉克劳和墨菲正式放弃了(工人)阶级霸权论,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所确认的工人阶级的特殊政治角色,转而主张一种在话语中不断建构与解构的、没有固定本质的社会认同(indentities)。他们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扬弃特殊的政治主体,认为新社会运动意味着所有固定的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因此它不应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替代物。他们把阶级和社会主义斗争看做是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的一环,要求左派放弃阶级政治,并以链接不同的民主政治为首要目标。为了兼顾彼此独立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自主性,他们将政治认同简化为社会认同,以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取代了阶级政治,并以“认同政治”解构了一切左派霸权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在表面上仍然表示:“每一个激进民主方案必然包括社会主义取向,也就是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注:Laclan and Mouffe,1985,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London:Verso,p.192.)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非阶级化的“后社会主义”理论中已经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因素,只有对右派霸权现实的强调和对左派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推崇。他们的观点十分明确,即“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带来民主,而革命的主体也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新社会运动的广泛民主力量。因此,西方不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的革命是“激进的民主革命”。也就是说,英国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修正了社会主义的传统定义。在拉克劳和墨菲眼中,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政治的代名词,而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去阶级化的、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认同政治和激进民主政治的代名词。
二、德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德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应对后现代主义过程中的理论转向。在这一转向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阶级和社会结构演变理论已经从1968年以前的,从高科技高消费条件下分析工人阶级的异化问题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异化问题而形成的“工人阶级融合论”,转向了70年代以后的公共领域民主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后人、哈贝马斯的学生克劳斯·奥菲(C.Offe)则专门研究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扩大对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尽管德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坚持理性主义传统,反对后现代主义解构理性,破坏民主社会的地基,但是其社会理论深受“后学”时尚影响,明显扩展到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新问题域,它对多元主义激进民主的倡导也与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取向和目标相契合,表现出“去马克思化”的趋势。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一致认为,保证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维持利润率不下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职能,而福利国家、代议制民主制度已成为国家实现这一职能的重要制度保证。福利国家有效地协调了资本与劳工的关系,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奥菲指出,福利制度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化的支持系统,其功能在于维持资本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队伍。福利计划的制度化改变了战前的工业阶级斗争的模式,并且带来了“更加经济主义的、以分配为中心的、日益制度化的阶级冲突”。(注:Offe,C.,1984,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Mass:MIT Press,p.193.)他认为,福利国家通过对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作出让步,消除了它们进行斗争的动力。工人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因为充足的利润率和投资水平保证了支持用于福利项目的经济剩余的产生。而资本家也接受了基本工资要求和福利国家开支,因为后者确保了一个健康顺服的工人阶级的存在。同时,奥菲接过福柯后现代国家理论的话题,进一步分析了福利国家所体现的强制性,他着重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复杂化,国家对各种偏离规范的行为也越发敏感,因此从身体到心理对个人的控制越发严密。从反对吸烟酗酒到交通安全教育,国家发展出一整套行为控制制度,过去被视为纯属个人的私事也成了国家关心的问题。(注:Offe,C.,1984,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Mass:MIT Press,p.193.)奥菲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引发的危机的反应。他关于国家功能扩张及其实质的论述显然打着后现代主义的烙印。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模糊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因此,所谓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是过时的、不正确的理论思维方式。哈贝马斯批判性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项基本假定”,(注:哈贝马斯,1989,《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重庆出版社,第134页。)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划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和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成为基础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在后工业社会,许多以往被马克思看做是上层建筑的国家、交往等因素不但不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相反对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影响。“进化优势将从经济领域转到教育和科学系统”。(注:哈贝马斯,1989,《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重庆出版社,第148页。)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形成的基础不仅要到一般商品生产过程中去寻找,而且要到“上层建筑”中去寻找;晚期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中,“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成了一个人”。(注:哈贝马斯,“何谓今日之危机?论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转引自《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第56页。)哈贝马斯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和冲突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已经缓和;冲突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冲突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文化冲突。“更确切地说,新的冲突是在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领域中形成的”。(注:哈贝马斯,1994,《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重庆出版社,第500页。)哈贝马斯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不承认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其他结构的决定作用,从而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经济结构和历史地位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用基于差异的文化冲突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
在上述去阶级化分析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以合理的交往行动取代劳动在传统的社会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性”取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民主的“协商政治”取代了基于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从而实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重建”。交往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性协议,要得到一致性协议就需要借助话语进行主体之间的对话,而只有通过对话或协商,才能获得立足于主体间性的真理,实现共识,推进法律和民主建设。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在道德领域,还是在法律和政治领域,都需要贯彻协商原则,于是就产生了协商伦理学和协商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哈氏以交往理性为支柱来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认为公共领域不是“国家机器”或“经济领域”,而是民主社会的“参与”,是一种“话语领域”(discursive field)。因此,市民社会概念应被解释为思考共同事务和共同利益的话语互动,它体现了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出发,把公共领域当作权力斗争的领域,倡导基于对话的“参与民主”,从而为90年代西方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中心的激进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从批判理论走向建构理论的一个转折。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霸权的批判走向对更多元的民主社会的建构,应视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一个发展。在里根、撒切尔主政后资本主义出现发展高潮,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传统的左翼批判理论频频失灵的历史大背景下,哈贝马斯标榜超越左右意识形态的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理论为西方参与式民主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打造了理论基础,因而很自然地在西方学界和西方社会流行开来。这一理论在当代条件下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哈贝马斯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民主、话语互动等多元文化形式的权力抗争取代了劳动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以差异认同为特点的激进民主政治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以争取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民主社会的目标取代了无产阶级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建立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思想,错误地对马克思基于劳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这一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冲突理论进行了全面“重建”,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损毁。
三、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在1968年运动和前苏联东欧剧变这两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下形成的,其发展高峰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的90年代。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两大事件后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社会主义未来美好社会的目标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探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解说。
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乔治·拉比卡(G.Labica)在90年代仍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政治。拉比卡认为,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这一主要矛盾,使得红色战胜了白色的、玫瑰色的和黑色的东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实际斗争,是建立“多数人的政权”。(注:拉比卡,1991,“共产主义是未来”,载《共产主义评论》,第11期。)他认为,由于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销蚀和淡化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化方面发展革命概念,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世界化”来解决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注:参见周穗明、李其庆,1992,“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第18期。)
法国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塞尔(Andre Tosel)强调对马克思的“实践”理论、韦伯的西方社会结构理论和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的继承,特别是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主将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试图用“生产/行动理论”取代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去分析当代社会运作过程中复杂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大规模文化消费的新时代,其“生产/行动理论”通过批判和“重建”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决定论”,适应和体现了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托塞尔“解构”马克思的基于劳动和生产的实践理论,把实践从“历史宏观”框架降低到个体行动的“中观/微观”结构;反对像马克思那样把生产当作一般的社会实践,主张将生产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并将话语的表达和沟通作为“生产/行动”过程的活的中介。托塞尔认为:当代生产和个人行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将其重心从生产行动转向非生产行动,不管这些行动是政治的、伦理的,还是美学的……”。(注:Tosel,A.,1996,Vers Une theorie neo-marxienne de I'action,in Marx Actuel ,No.19:Philosophie et Politique,Paris:P.U.F.,p.136.)由此,托塞尔以其“生产/行动”,否定基于马克思宏观经济社会分析的“大型主体”——阶级、政党和民族国家,转而重点分析被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个人”及其行动动机、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冲突被弱化为非阶级、非政治的、弥漫于各个社会层面的广泛的、多样的权力抗争或文化霸权的争夺。
处于法国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边缘的左翼激进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则从托塞尔对马克思原有实践概念的“解构”和“重建”,走向取代实践概念的“象征性实践”理论。布迪厄认为,人的象征性实践由“行动者”和“社会”两个固有因素构成,是在人的象征性实践中建构起来和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他从象征性实践出发,创建了一种反思性的象征形式权力社会学,将权力问题置于象征性结构的社会空间和权力场域中去,具体地探讨权力运作的象征性模式。他明确提出,要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中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逻辑,必须与马克思的本质论的社会理论彻底决裂。他指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认为其主要错误在于“为一个真正的实际问题提供了一个错误的理论解决方案,例如肯定了阶级的实际存在这样的问题”。(注:Bourdieu,P.,1994,Raisons Pratiques,Paris:Seuil,p.53.)在布迪厄眼中,社会空间只是一种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的象征性双重结构。社会科学应当构建的不是阶级,而是其内部可以分割成阶级差别的社会空间,而这样的阶级只存在于纸面上。他把社会空间描述成一个个象征性的权力斗争的场域,特别重视由各种资本转化而成的象征性资本,专题批判垄断了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权力的当代社会名牌高等大学。他认为,社会空间中各个场域的权力斗争网络并不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所主张的那样,可简单地归结为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物质关系和人的关系。在高度科技化和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中,名牌大学体系是各个重要社会场域的特权阶层的不断再生产的重要基地,社会各个重要场域的特权分配,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些名牌大学系统中象征性资本累积和传递的情况。(注:Bourdieu,P.,1989,La Noblesse D' Etat,Paris:Minuit,p.406.)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场域的权力斗争及其再分配结果,都与名牌大学系统中象征性权力的分配和斗争紧密相关。由此,布迪厄揭示了象征性权力的特殊结构和运作逻辑。布迪厄理论的长处是重视马克思当时没有触及过的文化再生产中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容纳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抗争的分析,发展了新葛兰西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从而扩展了当代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空间。但是,他以权力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区别和差异分析取代阶级分析,以“象征性实践”和“象征性结构”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结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分析,因而难以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
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自创了一种“元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现代性”的“元结构”解释了当代阶级与政党政治,试图用现代批判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改造”。他主张用韦伯的“现代性”理论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用契约主义、组织性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理论。比岱认为,个人及其契约地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和动因,这种交换和契约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是新的统治关系的基质。契约关系在实现的同时总是遭到破坏,走向反面,如自由平等的市场在现实中造成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因此,在分析市场和阶级关系时应当区分资本主义交换的“法律形式”和阶级剥削的“实际关系”。他说明,契约自由基础上的市场和组织是现代社会理性合作的两种基本模式因素,也构成了两大阶级因素。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完全在财产权,即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它还通过“组织”的文化或社会形式进行。市场和组织在现代阶级结构中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因此,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阶级结构的理论,质疑建立在阶级结构基础上的政党制度观及其划分左右的传统标准,认为马克思对阶级结构的分析忽略了对“组织性”及其实质的分析。现代社会的两党作为“组织”形式、作为“能力”极,都通过与其他极的社会力量建立积极的关系来控制对方,两党之间的区别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老生常谈。现代受剥削的大众只有打破轮流执政的两党所固有的勾结,通过市场和组织的双重进程,才能在结构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替代。社会主义因而是以消除这些因素,建立无阶级,即平等民主的社会为目标的群众斗争。(注:参见雅克·比岱,2003,“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和政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见《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高静宇译。)比岱的阶级理论比较重视阶级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的形成,努力揭露西方政党政治的阶级本质,没有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权力斗争。但是,他的阶级结构理论以个人契约地位的微观分析取代生产方式的宏观分析,弱化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对于阶级形成的决定作用;他的“组织性”分析过度突出文化性,落入了后马克思主义去阶级政治的思想窠臼,其理想也没有超出欧洲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研究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雇佣劳动阶级问题。让·罗金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是雇佣劳动的异质化。今天的雇佣劳动阶级已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雇佣劳动阶级,古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占1/3左右,而服务工人,即教育、文化、医疗保健、通信等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则占2/3左右,此外还有经理雇佣劳动者等。新经济创造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工人的新型雇佣劳动者。(注:参见李其庆,2002,“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载《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第5页。)保尔·博卡拉认为,信息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深刻影响,它改变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为未来社会准备了要素。信息和知识与劳动者,特别是智力劳动者难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权力被相对削弱。(注:参见李其庆,2002,“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载《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第3页。)弗朗赛特·拉扎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在总体上并没有多少改变。它的一端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另一端是广大雇佣劳动者;前者只是少数人,而后者的队伍则日益扩大。她认为新中间阶层不是一种阶级概念,其地位也极不稳定。广大雇佣劳动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注:参见李其庆,2002,“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载《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第5页。)米歇尔·阿格利埃塔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福特主义增长方式正向金融资产增长方式转变,这一转变在微观层次上的反映是体现资本社会化趋势的股权分散化,促使企业到市场去寻求风险资本,从而获得发展动力。但是,他反对所谓工人持股制形成了“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他认为,雇佣劳动者的金融资产无论从职能还是数量上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在当代,银行信贷是资本主义生产实现的条件,而工人无法用自己的金融资产获得信贷来从事经营性生产这一事实决定了其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股权分散化与金融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同时进行的。雇佣劳动者的家庭金融资产不能脱离垄断资本而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佣劳动者对资本的间接从属由于工人持股而加深了。(注:参见李其庆,2002,“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载《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第4~6页。)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eani)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浪潮下,西方企业的雇员股东制的加速发展并没有真正改变劳资关系,这种意义上的所有权的扩散并不具有变革资本主义的性质,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只是个骗局。他对西方雇员股东制的三种形式——企业储蓄计划、养老基金和期权股份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就企业储蓄计划而言,由于股权过于分散,雇员无法赢得任何权力,公司权力仍然掌握在企业领导者手中;在养老基金的管理中雇员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他们无法控制投资,养老基金代表着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期权股份的主要持有者是企业领导者、雇员资产阶级。因此,伴随着人民资本主义的是劳动服从资本,资本把它的逻辑和特有的限制强加给劳动。雇员股东制是破坏性的,它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而金融崩溃对小股持有者的冲击最为剧烈。(注:安德烈阿尼,2001,“人民资本主义是骗局”,载法国《乌托邦批判》杂志,第2期;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9期,第4~6页。)
法国的另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分析了工人持股制对阶级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股民的投资参加资本循环,特别是国际资本循环,从而产生了“食利雇佣劳动者”,这的确给阶级关系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应该承认这些投资的收入(股息和红利)是发达国家形成广义“工人贵族”的经济基础之一(尽管工人所得到的投资收入很少)。(注:参见李其庆,2002,“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载《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第5页。)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出现了新的统治和剥削方式。产业结构调整中部分产业的转移,移民劳动力的竞争和临时工用工制度的推行,社会福利和保险的减少,使发达国家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趋于恶化,而工会力量的削弱又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注:参见李其庆,2002,“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载《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第5页。)
长期从事工人阶级问题研究的奥利维耶·施瓦茨指出,随着法国传统产业的衰落,最近15年或20年来,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正在衰落。尽管工人阶级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30年来不断下降,但仍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整体。服务业中被称做“雇员”的职工也属于“工人”阶层。施瓦茨反对60年代马勒提出的将白领工程技术人员纳入工人阶级的“新工人阶级”理论,认为今天法国工人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而且繁重的工作、不稳定的职业、工资微薄且增长缓慢这些特点还出现在第三产业的许多职业中。同时,施瓦茨也指出了造成工人真正衰落的两个因素:一是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新一代工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缺乏以往工人阶级的明确的同一性和身份认同感。工人和非工人、社会下层和全社会之间的社会界限虽然没有消失,但在今天已十分模糊;二是由于20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不稳定就业增多、去社会化现象日益严重,左翼政党认为各种更加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不是来自工人,而是来自那些无法再进入劳工界的人们,这些人的社会目标越来越远离有工作的、境况以乎不错的工人阶级,而日益转向关注被排斥者、郊区、年轻人、移民和种族主义及其社会运动。(注:奥利维耶·施瓦茨,“工人阶级变成了什么?”,原载于法国《人道报》,2001年5月2日记者专访。)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分析工人阶级政治衰落的原因时认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受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不是西方工人阶级,而是失业人群和外来移民等“下层社会”和边缘人群。
总体而言,法国后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一样,在70年代到90年代都经历了从后阿尔都塞主义到新葛兰西主义的思想历程。由于法国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故乡,因此,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演变理论显然与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有别,更具有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充分彰显了其理论方法论的多元化的特征,也更具有左翼激进批判色彩。
(待续)
标签:哈贝马斯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