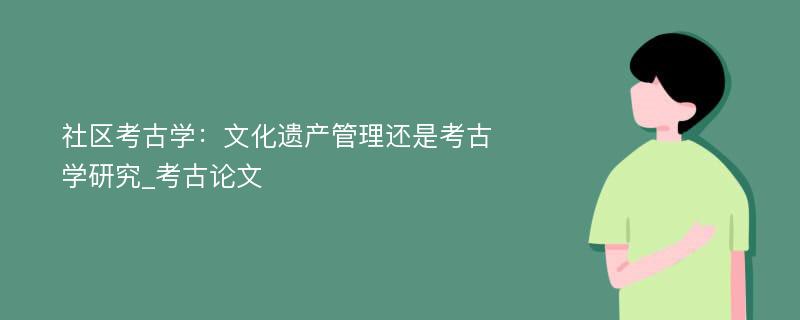
社区考古学:文化遗产管理还是考古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文化遗产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51 文献标识码:A
社区考古学(Community Archaeology)尚处在形成过程之中,无论是研究主题、策略还是作业程式,甚至定义和学科定位都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然而,被广泛征引的社区考古学范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由此可见,社区考古学实践由来已久。但是,直到21世纪初,考古学学术期刊才出现对社区考古学的专辑讨论,而在此前数年,有的职业考古学家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在社区考古学上的价值,或者刻意回避使用“社区考古学”这一术语[1]。《世界考古学》杂志于2002年推出“社区考古学”专号,藉此呼吁考古学职业群体更多地关注和投入社区考古学研究,同时希冀在世界范围内总结社区考古学实践经验,但是却揭示出社区考古学的显著的草创性、不平衡性和多元性[2]。事实上,尽管社区考古学涉及的内容是每个考古学调查和发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很少被职业考古学家以整体性观念对待,其学术关联性也未得认可,大多数学者将社区考古学视为文化遗产管理(heritage management),甚至在很长时间内,社区考古学被视为考古学实践中的“非学术”细枝末节。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成功的社区考古学个案说明,社区考古学在文化遗产管理和考古学研究上具有等同的价值。作为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的一个活跃的分支,社区考古学与作为新博物馆运动的生态博物馆密切相关,有助于廓清围绕生态博物馆的种种混淆观念,解决新博物馆运动在中国面临的实践问题[3];而在考古学研究上,社区考古学与多元的、反思的考古学视角联系在一起,是情境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的一种表现形式,将揭示和弥补传统考古学研究的疏漏和误表[4]。鉴于当前的中国考古学中普遍缺失社区考古学意识,本文拟对社区考古学的源流、概念、特征、作业方式以及在遗产管理和考古学研究上的价值予以初步讨论。
一 社区考古学的源流和定义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学者试图厘定标志社区考古学出现或者成熟的关键活动或者事件。但是,从年代关系上看,美国华盛顿州的奥泽特(Ozette)考古项目是年代较早的社区考古学范例,多被征引为社区考古学成熟的标志之一。奥泽特是地处华盛顿州西北海岸尼亚湾的马卡印第安人保留区中的一个小渔村。当地具有社区考古学倾向的发掘活动得益于一个特定条件,即考古活动从一开始就直接受命于印第安人自治机构,因此,职业考古学家的学术活动和马卡人的自我认知的构建休戚相关。奥泽特项目以常规的合同考古学方式开始。1966年,华盛顿州立大学接受委托,发掘了当地史前时代晚期到历史时代早期的捕鲸村落。但是,发掘结束之后不久,当地又发现大量因埋藏于沼泽环境而保存完好的有机材质遗存。因此,当地自治机构决定再度延请华盛顿州立大学前来发掘,并且提出考古活动不应止步于发掘资料的公布,而需要与马卡人的文化认知结合起来,并且延续到马卡人的社区建设之中。发掘自1970年开始,持续到1981年,揭示出从距今800年到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在北美考古学上,奥泽特遗址以丰富的有机物遗存著称;对于马卡人而言,这个遗址全面再现了已不见于文字记载的本土历史记忆。因此,职业考古学家们也相应调整了发掘和整理策略,至少在展示奥泽特有机物遗存上更多地征引了本地的口述史和民族志材料,出土资料整理完成后,在学术性发掘报告之外,职业考古学家们还编辑了三卷本《奥泽特考古项目研究报告》,供非职业考古学家和社会教育机构参考和引用[5]。奥泽特文化的展示策略也根据社区教育的要求相应调整,并促使当地最终建立了马卡印第安研究中心。与马卡印第安人的合作态度导致奥泽特考古项目明显地不同于同时期乃至更为晚近的单向度的考古项目。
虽然目前尚未形成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社区考古学的定义,但是,不同的实践至少在诸多要点上已经取得共识。社区考古学不是以研究主题或者工作环境命名的考古学类型,而是指特定的考古学运作方式,具体而言,社区考古学就是指考古学和社区之间的关系。社区考古学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取向,因此并不是泛指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以权力让渡问题为核心。社区考古学的倡导者相信,本地社区的功能不应该局限在授予职业考古学家调查和发掘的权力,提供调查数据,提供劳力,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等方面,而是可以有效地参与到从研究设计到遗物和遗迹的保存方式等全部环节。因此,社区考古学的目标是尽可能让本地社区参与甚至控制从调查到阐释的考古学实践,社区考古学就是让本土社会获得考古学“权力”的工作方式。
社区考古学中的“社区”指什么?社区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文化概念。界定“社区”就是界定与考古学家分享考古学发现和阐释权力的实体。作为地理概念的社区既可能指考古调查和发掘直接涉及的土地所有人或者邻里街区,也可能指拥有行政或者管理权力的社区组织,这种社区的居民出于对地域文化传统的兴趣会关注考古学项目;此外,还存在作为文化概念的社区,尤其是历史上的居民发生迁移之后,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继嗣群(descendant group)基于对族群文化传统的兴趣构成了文化概念的社区。众多个案中,两种类型的社区是重合的,但是也不乏地理与文化相分离的社区。埃及的罗马时代港口城市库塞尔(Quseir)的发掘项目中,本地社区在族属上与罗马时代的埃及居民无关,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发掘出土的港口遗存作为本地文化形象的热情[6]。而纽约非裔美国人墓地发掘项目(ABG)地处华尔街闹市区,曾经居住在当地的非裔社区已经迁离出去,但是基于对族群文化的关怀,众多分布在纽约上城区乃至周邻各州的非裔继嗣群组织使该墓地的发掘从一次普通的合同考古转变为社区考古学的经典个案,也造就了纽约第一个专门纪念殖民时代的非裔美国人的国家公园[7]。无论是基于地缘关系还是血缘关系的本土社区都将考古学研究对象视为本地的文化认知的组成部分。
有学者提出:全球各地的社区考古学的发展呈现为不平等态势,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社区考古学实践最活跃、成功案例最多、反响最强烈,而欧洲和亚洲的考古学对社区考古学反应平淡,也缺乏足够多的经典案例[8]。社区考古学的全球不平衡性的确存在,但是上述判断可能并不准确,而且,这揭示出社区考古学的多元特征,在不同的考古学传统中,社区考古学的具体内容可能有所不同,其多元性是不同社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诉求等历史特定性原因造成的。北美大陆地区和大洋洲地区的社区考古学仅仅只是社区考古学的特定类型,这些地区成功的社区考古学个案常常和曾经深受殖民主义伤害的土著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土著居民权益保护法案是确保此类社区考古学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在美国是1934年颁布的《印第安人重组法案》,在加拿大则是1951年颁布的《印第安人法案》。一方面由于权力收归地方自治组织,另一方面由于职业考古学家的赎罪意识,田野调查和发掘特别考虑了此前被剥夺和贬抑的土著文化表达权力。这种关怀与既往的考古学对土著声音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后殖民主义学术的表现形式之一。正由于这个特征,导致有的学者质疑社区考古学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还是仅见于特定的考古学传统之中。本地没有出现过殖民主义考古学的欧洲和曾经出现殖民主义考古学、但是目前以国族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考古学为主流的亚洲,都缺乏类似的社区考古学个案。其实,这只是颇具迷惑性的假象。在欧洲同样存在以本土社区的权利为诉求的社区考古学,只是并不包含土著和外来族群之争的概念。传统考古学采取自上而下的观察视角,并无社区组织的地位,而且,由于传统的民族主义考古学以“国家史”为诉求,其主要关注点常常集中在涉及国家起源的史前晚段和历史早期,相对忽视延续历史较短的“社区史”或者社区记忆,这促成了通过强调自身街区的独特文化遗产表达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的邻里考古学(Neighborhood Archaeology)的出现。这应该是社区考古学的另一种主要形式,而法国最早的生态博物馆、中欧和东欧的文化公园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户外博物馆,都是这类社区考古学的变体。不过,不管哪种类型的社区考古学,在亚洲都缺乏足够的范例,因此,虽然社区考古学存在全球分布的不平衡性,但是分布状况却与此前的分析不同。同时,这也揭示不同地区的社区考古学的生成都极具历史特色和地域特色,同时受到考古学范式转型的影响。
二 社区考古学实践原则
虽然社区考古学是极具实践性的领域,但是目前也没有社区考古学工作步骤的固定模式,事实上,因为考古学的地域特征非常显著,所以很难总结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工作规程。不过,目前全球的社区考古学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足以作为参考。其中,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在埃及库塞尔的社区考古学项目总结了社区考古学的七种策略。
库塞尔港口在埃及历史上被称为Myos Hormos,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确认为公元前3世纪的重要港口,是托勒密时代和罗马时代通过红海与东方地区交换奢侈品的主要港口之一,一直沿用到公元3世纪。在漫长的沉寂之后,库赛尔于13世纪成为朝圣路径上的中转站,因与印度和阿拉伯的主要贸易港口而重新繁盛起来,直到16世纪早期彻底荒废。目前,库赛尔是埃及红海沿岸的主要潜水区。
南安普顿大学在库塞尔的社区考古学项目是更大规模的库赛尔考古学综合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库赛尔考古发掘起始于1999年,目前仍在进行之中[9]。英国在埃及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起始于19世纪晚期的埃及探险协会(Egyptian Expedition Society),虽然在埃及考古学自盗掘向科学考古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无疑属于典型的殖民主义考古学。过去的埃及考古学活动基本与本土居民无关,因此,如同在北美考古学所见到的一样,库塞尔的公共考古学项目是重新赋予土著居民以文化关联性的努力。但是,埃及考古学中的社区考古学又有其特色,即埃及的现代居民和历史居民并不具有血缘关联,库塞尔发掘的对象与现代埃及居民仅仅共享地域价值。因此,库赛尔项目成为基于地缘关系的后殖民主义考古学类型的社区考古学的样本。
库赛尔项目以为社区考古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为目标,提出了七种主要策略,试图覆盖社区考古学的所有主要侧面,包括沟通与合作、就业与培训、公共展示、访问和口述史、教育资源、多媒体档案和由社区主导的商业开发。如果加以总结归纳,我们即可发现,社区考古学就是以权力让渡为核心,主要涉及发掘权、阐释权、教育权和商业开发权。
发掘权是社区考古学的基础。本地社区不仅仅是考古调查和发掘授权机构,而且应该成为考古学活动的主导力量,社区考古学不仅倡导在发掘设计阶段就要充分考虑本地社区的意见,而且应该培训本地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可持续性发展力量。库赛尔项目中的“沟通与合作”、“就业与培训”与“访问和口述史”即涉及这个方面。传统考古学项目常常以职业考古学家的设计起始,本地社群仅在一定的阶段才被引入进来。但是正如戴瑞所指出的:“如果本地社区不参与问题的形成过程,那么他们对答案也会兴趣寡然”[10]。基于这个认识,库赛尔项目强化与当地遗产保护协会的合作,学习用日常生活语言写作报告,并且在展示的过程中,职业考古学者至少不再单方面决定展览的内容和方式。库赛尔发掘者也将对当地居民的访问视为田野考古学的必要准备阶段,事实上库赛尔的一个中世纪码头就是通过口述史访问勘定的。如果将考古发掘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本地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话,公共考古学项目就需要考虑为当地社区提供就业和培训的机会。库赛尔项目着力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为当地社区提供考古学、遗产保护和博物馆陈列方面的普及知识;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提供获取正规学位教育的机会,使库赛尔社区也有自身的职业考古工作人员,即使在库赛尔项目结束之后,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不至于中止。
阐释权和教育权的让渡可以确保考古发现最大程度地服务于本地社区。在库赛尔项目的“公开展示”中,职业学者不再将自我定位为“知识传播者”,而是帮助当地社区更好地理解自身文化遗产的“辅助者”,因此,他们在展示作为罗马殖民点的库赛尔港口的遗物时,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社区对于19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的观念。而“访问与口述史”环节也能帮助职业学者判断怎样才能更好地陈列发掘收获,更好地回答本地社区关心的历史问题。在“教育资源”上,库赛尔项目认为考古发掘应该服务于公共教育和学校教育,因此,在发掘过程中多次设计了面向当地中小学生的考古现场参观和临时展览。基于库赛尔发掘报告,发掘者还和当地教育中心联合编辑用于乡土教育的童书,发掘过程中专门为教育目的而保留的音像资料最终汇编成为社区居民皆可接触的“多媒体档案库”。
在商业开发权上,社区考古学主张在坚持不滥用文化遗产的原则基础之上,将商业开放的主导权完全归还给本地社区。库赛尔港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直到罗马时代才形成,因此基本与法老时代的埃及无关。但是,在库赛尔项目之前,当地旅游市场仍不得不兜售法老胸像和金字塔的复制品等与本地历史无关的纪念品,而在考古发掘之后,职业考古学家帮助设计了体现罗马时代港口城市特征的视觉形象,但是,其开发权完全归属于本地社区。
由库赛尔公共考古学个案可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社区考古学都是传统考古学的拓展。它将发掘前的准备过程以及发掘后的展示、教育和利用过程都纳入到考古学的范畴,使考古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教育机制。在自调查到发掘的传统考古学范畴内,公共考古学也不应该被看成是与职业考古学平行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而是通过双向交流、多元视角的融入,实现了传统的考古学作业的深化。
三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区考古学:重新定义新博物馆运动
20世纪70年代初期,深受殖民地独立运动、土著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六八学潮”的影响,同时也基于对传统博物馆与社会隔阂的不满,巴黎的博物馆学者发动了新博物馆运动[11]。这场运动通过将博物馆重新定义为公共机制的一部分,厘定“生态博物馆”和“整体博物馆”等术语改变了博物馆的运作方式,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文化遗产策略。基于在法国南部出现的最早的成功范例,这场博物馆运动也被冠以生态博物馆运动之名。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生态博物馆运动波及中国,最初见诸贵州、广西和云南,目前几乎遍布各地。与数量剧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生态博物馆普遍面临发展瓶颈。以最早创办、研究资料最为丰富的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可以清晰地显示中国的新博物馆运动的阻遏实际来自于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误解和误用[12]。从表象上看,中国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从梭嘎生态博物馆实践总结出来的“六枝原则”就出自解决这一冲突的初衷,但是,实践证明:这组矛盾是人为地将文化和经济捆绑在一起造成的,即将以保护文化遗产为主要诉求的生态博物馆当成促进经济开发的手段。“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主张最终都以损害文化谋求经济利益。虽然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挫折并不仅见于中国,但是我们有必要重新明辨若干概念,而社区考古学观念将有助于这一过程。
首先,生态博物馆运动仅仅是新博物馆运动的名称之一,与之竞争的其它术语显示,新博物馆运动和社区考古学是相辅相成、理念相通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研究文献基本采用“生态博物馆”一词,这个术语来自法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建立的克鲁索生态博物馆(Le Creusot Montceau),虽然这一术语广为采纳,但是在其它地方,新博物馆运动可能以其它名义出现,如拉美一带被称为整体博物馆或者文化公园,在美国就可能被称为邻里博物馆,在欧洲可能称为社区博物馆和户外博物馆等。新博物馆运动的内核是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揭示出传统的高高在上的、作为精英意识的表现的传统博物馆的不足,而将博物馆视为表达底层、土著、非主流族裔和人群的声音的公共机制,这与社区考古学的诉求同出一辙。从诸多定名上看,新博物馆运动和社区考古学甚至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不同描述方式。两个概念的对照,可能能揭示出两者在不同社会的运用过程中,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如何扭曲了词汇的表达。
将生态博物馆还原到新博物馆运动,并和社区考古学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反思生态博物馆的“生态”观念。对过去十余年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的观察揭示,中国博物馆在理解生态上出现了偏差,将生态取向狭隘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将生态博物馆实践锁定在尚未受到城市化进程显著影响,带有明显的前工业时代经济和文化残留,相对偏僻,自然环境保持相对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为少数民族族群。固然既往成功的生态博物馆项目不少是建立在少数族裔,历史上曾经被忽视的族群之中,但是,生态博物馆并不是必然和环境保护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生态博物馆也不是少数民族或者边远地区的专利,不仅在主体民族中存在,某些工业时代遗迹也可以成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础。因此,在中国,汉族的主要民系之一客家可以按照生态博物馆思路建立生态博物馆,曾经生活在东南、华南乃至东南亚海岸和河流入海口的疍家也可以建立生态博物馆,甚至今天见诸中心都会城市的城中村也可建成作为工业时代记忆的生态博物馆[13]。如果生态不指自然生态,那么其真实含义是什么?根据生态博物馆的运作,以及戴瓦兰对新博物馆运动兴起的阐释,生态更可能指社会生态,即对之前被忽视、被歪曲、被贬抑的族群的重新正名,同时提倡社会文化的多元表达。而社会生态就是通过本土居民表达对自身文化的关注,并且得到认可表现出来的。
社区考古学视角帮助新博物馆运动更准确和清晰地确定了其主体观念和特征。因此,在新博物馆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同样是权力让渡问题或者权力回归问题,即将决定本地社区记忆的问题的权力归还给本地社区,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不能理所当然地充当代言人;其次,从社区考古学的角度理解,新博物馆运动仅仅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设计和策略,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态博物馆能够健康地维持下去的关键要素。因此,文化保护并不必然和经济发展关联在一起,困扰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伪命题。
四 考古学研究上的社区考古学:走向情境考古学
职业考古学在很长时间刻意与社区考古学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主要是因为众多学者认为:社区考古学是遗产保护策略,而不属于考古学研究。但是,近期多个案例表明,公共考古学同样有助于深化职业学者的考古学研究。
社区考古学对考古学研究的最直接、最显著的改变是多元观念的采纳,这将揭示传统考古学研究中习而不察的预设视角。福克纳尔(N.Faulkner)曾经系统地分析了精英考古学和草根考古学之分,藉以唤起对长期以来被湮没的考古学社会属性问题的关注[14]。这种视角并不仅见于考古学,相反,是广泛存在于历史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多元化观念波及到考古学的结果。传统考古学被福克纳尔界定为“自上而下”的精英考古学,这个预设视角不仅决定了观察方法,也决定了考古学观察范畴。这种视角的形成既和考古学的学科特质有关,也和考古学研究的情境有关。近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将历史上大多数人群的物质文化遗存作为研究范畴,与关注孤立器物的古物学划清界限,形成了考古学更擅长整体性描述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学科优势。这个倾向经过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的文化—历史学派考古学的进一步强化,无论是柴尔德的《史前多瑙河流域》和《欧洲文明的曙光》,还是基德的《西南考古学研究概论》,都确立了考古学中的大尺度观察角度和自上而下的类型区分体系;另一方面,和其他萌蘖于启蒙运动的近现代学科一样,考古学先天性地和中产阶级知识阶层捆绑在一起,20世纪以来的学科职业化过程强化了考古学的男性中心论和白人中心论等预设偏见[15],双重原因都诱使传统考古学采取了单向的精英视角。考古学资料存在的社区基本被研究者忽视了。因此,包括社区考古学在内,被福克纳尔称为“自下而上”的草根考古学就是通过其他视角,揭示之前不被关注或者被误读的材料,形成考古学阐释上的不同声音。在既往学术史上,遭到忽视的群体包括草根社区、女性群体、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和非优势年龄集团,这也导致几乎与社区考古学同期崛起的还有女性考古学、土著考古学、老年考古学等学科分支。所有这些分支都可被包含在伊恩·霍德倡导的情境考古学之中。情境考古学的情境不仅仅指考古学的物质遗存应该在自身的文化整体中予以理解,而且强调阐释者的能动性,即阐释者自身的社会归属也会影响考古学阐释。因此,考古学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相互沟通、斗争和妥协的公共机制。毫无疑问,社区考古学就是情境考古学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与研究对象的本土社区和继嗣群集团的沟通获取对考古学文化的全新洞见。
小湍流(Little Rapids)研究项目就是考古学研究上的社区考古学的最佳范例。这是最近30年来最成功的考古学研究项目之一,曾被视为女性考古学的标志性研究,但是这一地位却始料不及地掩盖了它在社区考古学上同样重要的奠基价值。小湍流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瓦普顿达科他人保护区内,19世纪40年代曾被瓦普顿达科他人当作夏季营地。作为最早倡导女性考古学的学者,珍妮·斯佩克特尔(Janet Spector)在此进行了长达20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希冀以此建立女性考古学。斯佩克特尔对女性考古学的认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现作为研究对象的女性。女性主义考古学家对传统考古学最初的反抗表现在关注女性形象在考古学资料中的表现。斯佩克特尔注意到19世纪中期形成的文献片面关注了男性,但又同时提出达科他妇女包揽一切生计活动的“勤勉”形象造成的悖论现象,因此提出在考古学分析中采纳“性别分工”框架,即考虑社会分工如何表现,男女的不同社会空间是什么,怎样形成不同性别的器物组合。在这个思路下,她在小湍流遗址最初的三季发掘收获中界定出属于女性的器物组合[16]。但是,斯佩克特尔意识到前期的“科学”分析仍然存在偏见,即基于西方学术群体的分类系统的“社会分工”既没有考虑作为土著居民的达科他人,也没有考虑女性,“社会分工理论框架滋生了隔绝的、一般性的和死气沉沉的描述”[17]。1986年起始的小湍流发掘中,斯佩克特尔改变了研究策略,构成了她的女性考古学第二阶段。她从罗雅尔·哈斯里克对苏人的描述中发现同一个印第安人社会中男女价值观的差异[18]。同时,她将一位与19世纪中期的达科他领袖有血缘关系的本土历史学者纳入到研究团队之中。这是兼具女性主义考古学和社区考古学意味的转型。传统考古学的社会分工理论因为采纳功能主义取向,掩盖了众多看似平常的“实用器物”实际拥有的重要文化价值。斯佩克特尔因此重新研究了早在1980年就已经出土的一件角质锥把,此前被忽视的锥把上的刻镂图案实际上是妇女才干和成就的记录系统,以此为基础,她写就了《锥子的故事》,成为女性主义考古学和社区考古学的划时代作品[19]。
斯佩克特尔自女性表现向女性视角的转变得益于本土居民带来的本土知识,而在此之前,本土居民的知识创造权是被剥夺或者否定的。与斯佩克特尔的角质锥把的研究相映成趣的是,这类锥子广泛见于印第安人文化遗址之中,但是在其他的研究中仅仅被视为“家用缝补工具”,而且铁质锥尖的意义远远超过骨角质锥把,因为“货物清单显示这是印第安社区输入的重要商品”[20]。由此可见,社区考古学通过确认本土社区的知识生产权,采纳自下而上的视角,可以有效地复原此前被曲解的考古学文化。
综上所述,社区考古学既是文化遗产管理策略,也是考古学研究取向。通过权力让渡,将考古学转变成为公共机制,社区考古学改变了文化遗产的阐释方式,同时也改变了职业考古学研究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尽管有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精英考古学和自下而上的草根考古学之分,但是相对于职业考古学,社区考古学并不是与之平行的草根考古学,相反,它实际上是职业考古学的深化和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