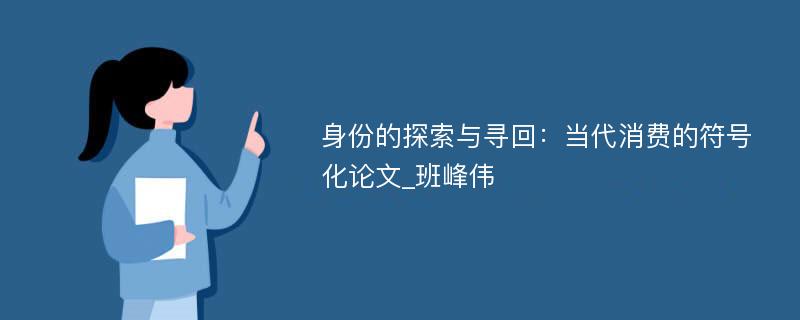
摘要:消费作为交换的方式满足人类的差异性需求,在现代社会,需求对象的主体已由物转为符号,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是自我的身份认同缺失,个人迫切追求能够获得身份认同的方式,复杂的焦虑感促使他们选择消费符号,来获得认同感。焦虑原始聚集于劳动的压迫下,进而转移到消费中,并在残缺的社会关系中以及互联网和广告的错误引导下逐渐加深。符号消费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控制人类的异己力量。
关键词:符号消费;身份认同;焦虑
【中图分类号】G91 【文献标识码】A
消费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基本现象,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科技的迅猛发展满足了人类绝大部分的物质需求,这时需求的对象逐步在发生转向,由于受到现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加速了消费社会的形成,尤其是符号消费风气的盛行。在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人类正面临着重新确立自我身份及社会地位的过程,符号消费是实现此过程的新方式和新选择。
一、从物质消费到符号消费
以物为消费的直接对象,满足人类的真实需求。当物成为消费的间接对象,物背后的符号成为消费追求的意义,这种消费被称为符号消费。符号消费追求溢出价值,其中既有对融入组群体的追求,也有对分圈的差异性追求。
(一)消费异化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中,生产是中心,交换、分配和消费是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消 费只是生产的产物”。[1]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根植于生产,从属于生产,生产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马克思认为物品之所以可以消费,不仅是其具有交换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具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人类的现实需求。
进入二十世纪,消费异化初露端倪,基础消费基本得到满足,可供消费的物品越来越多,逐步迎来了消费社会,基于马克思对消费的批判精神,西方众多学者开始对消费异化进行关注。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明显有闲”、“明显消费的炫耀性消费现象”,对当时西方国家的新贵阶层进行了批判。[2]弗洛姆则认为,在资本主义中的人们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找到自我。可见,消费异化时代的来临,一切文化消费品都被复制,以满足消费者的“异化需求”。
(二)符号消费
在社会学视野中,消费具有三个层次,一是纯粹物的消费,即对物品使用价值的消费,是满足人们的功能性、尤其是生存性需要的消费;二是对物品价值的消费,这种消费是满足基本功能需要以外的社会需要,例如通过有一定含金量的消费昭示身份和地位;三是对物品符号价值的消费,即对商品的文化内涵、个性、品位的消费,这种消费是社会需要和文化象征性的综合体现。[3]我们认为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消费同样列入符号消费的范畴。
符号消费是消费异化的当代表现形式,符号消费是指人们消费的不再是使用价值,是溢出价值,是消费广告宣传所创造的符号意义。被消费的东西成为符号,成为幻觉,人们依靠这些符号和幻觉而生,符号消费成为一种消费文化。“在消费意识形态中,重要的不是消费者,也不是消费品,而是消费的幻想和作为消费艺术的消费。”[4]
腾讯旗下企鹅智库发布了2019年手机品牌的用户画像,把每个品牌的使用人群进行划分。从其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苹果手机的消费群体与所在城市级别关联不大,无论是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及以下的城市,都对苹果手机有近似的消费欲望;从年龄分布来看,67.9%的苹果手消费者年龄段在20-39岁之间;以学历水平为划分依据,大学专科以下学历的消费者比例占到了70.7%;最后根据月收入划分,收入在1001-8000元之间的中低收入者更加偏爱苹果手机。综合数据来看,较低收入及学历的青壮年较其他人群更加偏爱苹果手机。如果说苹果产品在乔布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是科技性,那在在库克的时代,苹果产品的核心理念在向着奢侈品方向发展,更加注重对商品溢出价值的攫取。较低学历和较低收入人群在无形身份的获取上更急切,由于自己在某一层面处于社会水平的中下段,需要在另外的圈子中获得新身份、新认同。他们通过购买苹果手机,获取商品的溢出价值,进入“苹果圈”,也就是消费者们自称的“果粉”,在这个圈子中找到一群审美价值以及价值取向等多种元素相近的人,获得无形身份,找到归属感。苹果公司迎合了这部分消费者的符号诉求,成功地向奢侈品方向转型,成为第一个市值破万亿的公司。
二、身份的探索:符号消费时代的身份认同及其焦虑
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认为符号消费有两个基本的功能:桥梁和栅栏,[5]它们将人们联系到一起,或将人们彼此分开,人们通过各种符号消费来建构自己和识别他人,认同是划分群体的符号边界,是建立群体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符号消费的实质是消费者为获得身份认同而进行的社会关系的二次建构。
(一)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 identity) 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意指单独的个体对自己的本质、信仰以及一生趋向相对一致和比较完满的意识。借用到社会学,身份认同则包含族群认同和个体自我认同,前者是对群体的共同认知,以巩固群体身份、增强对群体的归属感;后者则是对“自我”的正确认知,以增强与“他者”的区别意识。[6]
符号消费中的身份认同,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占有和满足,而是同劳动过程一样是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在消费社会时代,商品的符号正越来越成为个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消费成为工具,通过消费传递信息,人们彼此解读附加在消费背后的信息,从而建立起社会关系,并进行进一步的互动。这种解读和进一步行为选择的反复玄幻构成了消费者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认同。符号消费首先是一种将消费者区分为不同社会身份的区分机制。布迪厄认为,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群体通过不同的消费模式进行区分,因此在消费领域中存在一种“地位性商品”。[7]社会上层人士依据自己的偏好斥资购买球队、俱乐部,中下阶层通过对某一球队或俱乐部的支持展示自己的认同,在这种圈子中获得无形身份。身份认同大到国家内部的认同凝聚,小到个人的自我认同区别他人的强烈意愿。NBA球队文化是以城市为基础的认同凝聚,拥有自己球队的城市形成球队文化圈,追随球队文化的个人融入到一起,分享自己对球队的情感,身旁的陌生人成为彼此的密友。这种身份认同与符号消费并行,球队队服、门票以及各种体现球队文化的周边产品是一个球迷必不可少的装备,比赛前夕往往城市中的体育用品店会被球迷清扫一空。据ESPN统计,2019年NBA球队多伦多猛龙队夺德总冠军后球队市值暴涨11亿美元,这不包括售出球队文化产品2亿多美元的收入。
(二)身份认同焦虑的内容
在劳动及交往中构建的社会关系缺失以及固有的阶层差异性导致了身份认同焦虑,结果集中体现在个人迫切地想要融入新的社会关系,获得身份认同。缓解焦虑最简单的途径便是消费符号,消费者凭借符号消费展示自我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和审美品位等,实际上借符号消费之名来炫耀物质占有之实。例如,通过购买高价电子产品、流行的奢侈品服饰,或进行大众娱乐方式追求一种“符号化”和“象征性”的意义世界。焦虑是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假冒奢侈品无法消除的温床,莆田庞大的假鞋体系、伪造奢侈品全球购订单都是消费者迫切追求认同的后果。不同阶层之间逐渐拉大的购买力差距,使得中低阶层拉近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是通过简单地符号消费可以轻松实现那么容易,去购买“欺骗性”的符号价值让消费者再一次看到获得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在计算出生活必须的成本外,焦虑的消费者将剩下的部分全部用来购买能让自己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的物品的溢出价值。互联网模式下的各种借贷方式便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为了获得身份认同的人以借贷或分期等各种消费形式,透支未来的购买力,焦虑已成为绑架消费者的强大力量。
(三)身份认同焦虑的原因
焦虑直接来源于认同感的缺失,以劳动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是认同充分表达的基础。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生产着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方面。从生产自然关系而言,劳动作为手段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能量完成交换过程,它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基础。社会关系的生产同样是以劳动为基础,以分工、交换为手段,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人类分工合作,在分工和交换中与彼此建立起不同的社会关系,获得身份认同。焦虑的产生及加深源于机器破坏了通过劳动建立起来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个人的身份认同在社会中无法表达。
工具和机器作为器官的延伸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大减轻劳动压力,释放劳动活力,但技术内在的逻辑性很快扭转了这一局面,科技的进步要求更高效的产出,劳动者由于不持有生产资料因此被排挤到社会底层,他们只得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须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十分精彩的总结过这个过程:在简单的劳动合作中,个人的劳动技能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工厂的生产则使得这些劳动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完全推翻了个人劳动的属性。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因为被迫掌握一些高度专门化的操作技能,从而被扭曲了人性,成为了残废。人作为机器的发明者不再是机器的统治者,反而成为机器的补充品。进行工厂劳动以及高强度作业的人群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他们以青壮年为代表,对新鲜事物接受速度快,这部分人在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生活需求层次和消费实践等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8]消费超前,入不敷出是这一群体的最大特点,因此产生的回归现实的幻灭感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打击。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9]他们白天参与高强度的劳动,闲暇的时间就陷入迷茫之中,是对“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拷问,期望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彰显自我存在感,期望融入城市,融入社会。
焦虑的进一步加深是在互联网全方位进入到生活之后,之前人类消费活动受限于时空的分割,聚集在同一社区的人类通过分工、交换以及消费达到相互认同实现,而跨越时空的认同不太可能实现,以社区为基础形成的圈子范围较小,个体之间的各种差异性不明显,且社会关系较为简单。互联网的出现打破这种时空的限制,不同地区的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形成新的虚拟社区和部落,分享彼此的消费符号、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圈通过互联网扩展到世界各地,同时广告构建的符号消费理念更加深入人类的意识之中,通过互联网着力宣传金钱文化、时尚文化,曝光明星、富人的奢侈生活,与普通个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根据虚假同感偏差理论:理想状态会因为个人偏好而变“高估”,个人会因为喜欢的演员、明星或网红,对其生活做放大式美好的想象,理想生活状态与现实生活状态之间的鸿沟好像永远不可能实现,这时填补距离的各种方式开始层出不穷,但二者之间的间隔似乎总是偏向无穷。聚焦在公众视野下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普通大众,甚至被争相效仿。明星就餐后的餐馆生意异常火爆,甚至还会带动其他明星前往;“LV”通过与国内某一线男星签约达到精准广告的目标;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符号价值成为消费追求的唯一目的,焦虑也在逐步加深。
三、身份的寻回:认同焦虑的化解
身份认同基础上焦虑的产生及其加深,是其根源性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劳动中的主体性丧失是焦虑产生的根源;当代错乱的社会关系推动焦虑的发展;互联网及广告等媒介的误导进一步加深个体的焦虑。因此需要通过工匠精神、变革社会关系以及规范广告行业来逐步消除大众的焦虑感。
(一)在劳动中恢复个人的主体性
劳动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和方法,在劳动中发挥能动性,确立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大机器时代的来临加强了劳动压迫,产生焦虑感,这种压迫并非是要求更大的劳动力投入,而是对人性的压抑。应当使劳动者从单一的劳动中获得精神享受、生命价值、劳动意义,新时代,应以工匠精神指导生产劳动,引导劳动者将所有的情感、意志、思想、目的、创造性等投入劳动过程,在非功利性的创造性劳动中实现物我两忘、道技合一。[10]应引导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和创造精神,以消解劳动目的与劳动过程、劳动主体与劳动对象、劳动内容与劳动形式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劳动中获得精神超越和思想的解放。
(二)通过重建合理的社会关系消除认同焦虑
变革单向性劳动的模块化作业,构建个体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重视公民教育,提升个体素质,增强价值认同。目前政府机关、用人单位、培训学校和基层社区等还未将公民教育渗透到各个阶层,各级各类应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引导和教育他们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基础,逐步适应当代社会的生活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和职能规范,培养合格的社会角色,融入社会。财政可实行宏观措施与微观措施双轨制,缩小不同阶层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缓解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情绪。在健康的文化、生活以及工作中构建个体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通过非消费性手段定位自我价值的方向,营造合理高效的新型社会关系。当个人能够在日常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后,就不再需要通过畸形的消费来获得自我的“救赎”。
(三)要有效抵制互联网及其广告的诱导
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广告诱导大众进行过度符号消费,传输一种不消费就无法得到认同的错误观念理念,进一步加深本不富裕的人们的身份认同焦虑。通过代言人以及品牌效应等多种方式诱导消费者去消费符号,从而起到积累资本,剥削劳动者的效果。作为具有思辨性、否定性的人类主体,应当洞察到虚假消费的背后是无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并不能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符号是较高社会阶层对中低社会阶层的文化统治手段,所以作为劳动者应当通过构建自己合理的社会关系,获得身份认同,不应该将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投入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符号中去。同样,大众传媒应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遵守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的政策性和方向性,坚决杜绝报道宣扬虚假和错误的消费文化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7页.
[2]张佳, 王道勇.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演进及启示[J]. 科学社会主义, 2018, 186(06):139-143
[3]孙凤. 关于消费“升级”与“降级”的几点认识[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2):13-19.
[4]仰海峰. 列斐伏尔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J]. 现代哲学, 2003(1):57-64.
[5]Douglas, M. & Isherwood, B.,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6]刘伟.身份认同:《论语》中的祭祀认知问题[J]. 孔子研究, 2019(2):78-52.
[7]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5-168.
[8]滕驰. 符号消费向度下新生代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身份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15-21.
[9]韩少功.第二级危机“酷”的文化现代之一[J].读书,1998(2):57-70.
[10]郭亮亮. 工匠精神:超越异化劳动的劳动解放[J].人民论坛, 2019(3):82-83.
论文作者:班峰伟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1月4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1/1
标签:符号论文; 身份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焦虑论文; 社会论文; 互联网论文; 自己的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1月49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