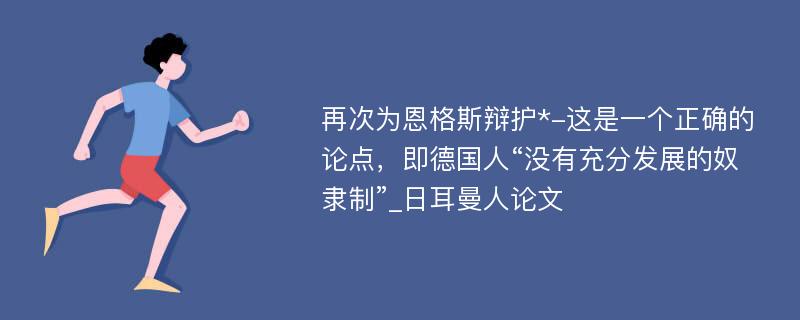
再为恩格斯辩*——德意志人“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是一个正确的论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德意志论文,是一个论文,奴隶制论文,论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庆钧同志在他的论文《日耳曼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吗?》中说:恩格斯:“认为日耳曼人占领罗马帝国以前,由于他们的野蛮状态,还没有达到两种奴隶制的任何一种,这是由于恩格斯受了摩尔根的影响,并且接受了摩尔根对人类史前史的分期”,“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他认为:“不能以所谓高级野蛮社会的框界来规定当时日耳曼社会的性质”〔1〕。虽然胡庆钧同志说“这是首先应该归咎于摩尔根的”, 但也批评了不是“首先”的恩格斯。我认为,恩格斯没有受摩尔根的影响,也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他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因此,再为恩格斯辩解。
一
先来分析胡庆钧同志征引并作了改译的塔西佗著《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两节记载。
第24节:“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一本正经地从事赌博,就是在头脑清醒时也是如此,并且对输赢冒险极了,甚至在赌本输光的时候,把自己的人身自由作孤注之一掷。输家情愿去做奴隶,即使他比对方年轻力壮,也顺从地被缚前往赢家。这种行为表明他们对这种坏习惯的顽梗不化,而他们自己却把这说成是守信义。但赢家也觉得靠赌博赚来奴隶是不光彩的事,所以对于这样的奴隶总是转卖出去的”。转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胡庆钧同志已经提到:“当时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商品交易中,出口货物的大宗除畜产品外就是奴隶”。塔西佗记载的“在赌本输光的时候,把自己的人身自由作孤注之一掷”,就是在向罗马出口大量奴隶的情况下发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证明购买奴隶的罗马社会是奴隶社会,不能证明出口奴隶的日耳曼社会是奴隶社会。胡庆钧同志说:“至于赢家要把赌博赚来的奴隶转卖,主要还不是作者所说的不光彩。因为既然被缚前来,就必须防止走熟路跑掉,转卖的目的主要是割断与家族亲朋的联系,从此孤身一人,这是任何奴隶社会稳住这类奴隶的起码要求。”应该指出,胡庆钧同志的上述解释是不切实际的。赌博的目的是为了赢钱,在赢得了输家的“人身自由”之后,自然要转卖出去,以实现赌博的目的——钱,这才是赢家“转卖的目的”。塔西佗说:“他们天性纯朴”〔2〕。所以在输了“自己的人身自由”之后,“情愿去做奴隶”,“顺从地被缚前往赢家”,他们“把这说成是守信义”。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在本土,是不会“走熟路跑掉”的。所谓“防止走熟路跑掉”,“转卖的的目的主要是割断与家族亲朋的联系”,“稳住这类奴隶的起码要求”等等,只不过是胡庆钧同志从“奴隶社会”概念出发的一种想当然罢了,不是“赢家”的目的,“赢家”是不会考虑那么多的。
胡庆钧同志还说,在塔西佗的另一著作《阿古利可拉传》第28节中曾谈到:有一支从日耳曼尼亚征集而被送往不列颠的乌昔鄙人的军队,在乘船逃跑时被当作海盗先后为斯维比人和弗累昔夷人所捕获,其中有些人被卖为奴隶。可是,后来又怎么样呢?胡庆钧同志没有提,塔西佗接着说:“后来又转卖到莱因河南岸罗马帝国境内”〔3〕。可见, 上述情况也只能证明购买奴隶的罗马社会是奴隶社会,不能证明出口奴隶的日耳曼社会是奴隶社会。
胡庆钧同志还提到“《日耳曼尼亚志》第8 节曾谈到妇女的被奴役最为令人痛心”。这是因为这些部落非常尊敬妇女。但这也不能证明日耳曼社会是奴隶社会,因为,上面已经提到,当时日耳曼人向罗马出口奴隶,其中当然包括部落战争中掠获的俘虏,并且如胡庆钧同志所说的,“这类奴隶当然有男有女”。所以,胡庆钧同志提到的这个情况,也只能证明购买奴隶的罗马社会是奴隶社会,不能证明出口奴隶的日耳曼社会是奴隶社会。
关于第24节,胡庆钧同志最后说:“他们就是古代社会的古典奴隶或者物化奴隶”。可是,如上所述,他们已被转卖到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古典奴隶或者物化奴隶”,所以,不能用他们来论证日耳曼社会是奴隶社会。
恩格斯说:“事实上,除开家畜以外,奴隶是为了和罗马取得贸易平衡而能够大量从日耳曼尼亚输出的唯一商品,单单意大利就在城市里和大地产上使用着大量的奴隶人口,而这些奴隶人口自身是繁殖得很少的……必须向野蛮人购买奴隶。难道日耳曼人不能以贩卖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吗?按照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人早就在出卖奴隶了。(《日耳曼尼亚志》第24节),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也象弗里西安人那样,在金钱不足时就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作为奴隶向罗马人交纳贡赋……他们也大规模地参加了向意大利贩卖奴隶的贸易,而这种奴隶贸易,当时被认为是体面的事业,甚至,是光荣的事业。”〔4 〕恩格斯在1884年提出德意志人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以前,早就读过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但是,“难道日耳曼人不能以贩卖者的身分出现在市场上吗?”,难道他们贩卖奴隶就证明他们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吗?
再谈第25节:“他们不按我们的习俗使用其他奴隶,那就是分别派以家内的各种职责,这些奴隶全部与主人分居并有自己的家庭。象对待隶农一样,主人只是从奴隶那里索取谷物或牲畜或衣服,奴隶的从属关系至此为止;其他的家务由主人的妻子和儿女来承担。笞打、带镣、或课以重役来强制奴隶的现象是不多见的。主人通常也杀死奴隶,但并不是由于执行严格的纪律,而是由于一时的暴怒,就像杀死一个敌人似的,这样做不会受到处罚。
被释奴隶的地位不比奴隶高多少,他们在主人家里没有什么地位,在社会生活方面更毫无权利,只是受国王统治的部落里,情况就不同了,那儿被释奴隶的地位,往往可以升得比自由民和贵族还要高;至于其余部落里被释奴隶地位之低下,却正是他们自由的标志。”
塔西佗称日耳曼尼亚被剥削的劳动者为“奴隶”,但同时又说“像对待隶农一样”,只是索取谷物或牲畜或衣服,从属关系至此为止。这就需要科学地进行分析,究竟是一种什么生产关系?胡庆钧同志说,“从属关系至此为止,是指主人并不叫他们到家里来从事家务劳动”。应该指出,这个解释不符合塔西佗的原意。塔西佗说只是索取谷物或牲畜或衣服,从属关系至此为止,是说在此以外不存在其他从属关系,包括人身占有关系。如果劳动者的人身被占有,会“不叫他们到家里来从事家务劳动”吗?所以,塔西佗的这句话说明,在日耳曼尼亚的剥削者和劳动者之间不存在人身占有关系。胡庆钧同志又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人对这类奴隶比较缓和,却往往由于一时暴怒而把他们像敌人一样杀死,并且不会受到追究。这就充分证明他们仍是被主人直接占有并对之操有生杀大权的奴隶。”胡庆钧同志的这个论证也是不科学的,且不说在罗马帝国法律曾规定不能杀死奴隶,即就日耳曼人来说,当时处于“野蛮状态”,难道对农奴就不能“由于一时的暴怒”、“像杀死一个敌人似的”杀死,这样做“会受到处罚”吗?塔西佗提到的这种现象,只是表明,在日耳曼尼亚,被剥削的劳动者的生命还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并不能证明被杀者的身份。
从生产关系上来说,奴隶是一无所有的,完全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所以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劳动者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下的定义〔5〕。 日耳曼人中被剥削的劳动者有房屋、有家庭、拥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经济上是独立的。剥削者对他们像对待隶农一样,只是索取谷物或牲畜或衣服,这种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下的定义来判断,显然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而是封建制生产关系。恩格斯也读过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他曾提到塔西佗“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6〕,就是根据第25 节的记载。但恩格斯并没有像胡庆钧同志那样说这是“奴隶占有制等级结构”,因为,“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胡庆钧同志说,塔西佗的记载中“并没有涉及索取多少与在他们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可见这种剥削并无必需遵守的限度”,以此来论证生产关系的奴隶制性质。可是,塔西佗的记载中“没有涉及”或者说塔西佗的“拉丁原文无定量之义”,不等于没有这个事实。如果像胡庆钧同志所说的那样,“并无必需遵守的限度”,那还“像对待隶农一样”吗?“像对待隶农一样”,就说明剥削者的索取是有限度的。塔西佗的作品,流传下来的版本很多,各有不同的地方〔7〕,哈吞译为“一定数量”;T·韦德曼译为“确定数量”,不会没有根据。即以胡庆钧同志作了改译的“索取谷物或牲畜或衣服”的译文中也可以看出,索取的品种是受限制的,其中的两个“或”字表明,三者中只能索取一种,不能同时都要。索取的品种都受限制,索取的数量会没有“限度”吗?胡庆钧同志想通过剥削“限度”的否认来否定生产关系的封建制性质,是不能成立的。
古希腊人也曾把斯巴达的赫罗泰(Helots)看成是奴隶的两种类型中的一种,但恩格斯认为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是就生产关系来说的。塔西佗说日耳曼尼亚被剥削的劳动者是“奴隶”,但马克思说:“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9〕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也是就生产关系来说的。 生产关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不能引用古希腊、罗马人的一些观念和称谓来推断其性质的。
塔西佗称日耳曼尼亚被剥削的劳动者为“奴隶”,但是,“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10〕对此,胡庆钧同志不是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是从公式出发,改译为“这些奴隶全都与主人分居并有自己的家庭”。在他看来,“奴隶”而“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当然是“分居奴隶”了。应该指出,在塔西佗的拉丁原文中并没有“分居”这个词,他说的是“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不是“分居”。事实上,不是胡庆钧同志所说的什么“分居奴隶”,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孤独生活”的“农奴”。所以,“不恰当的”,不是“哈吞本译为佃农并释成农奴”,而是胡庆钧同志改译为“分居奴隶”。
拙作《为恩格斯辩》一文已经指出,所谓“授产奴隶”,是古罗马奴隶制生产关系解体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异化现象,从生产关系上来说,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封建制,或者说,农奴制。并且,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化现象,不是释放奴隶的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如胡庆钧同志所说的:“物化奴隶经由授产奴隶到被释奴隶是一连串的发展过程。就正常情况来说,只有授产奴隶才有条件备款赌身,如不允许奴隶授产分居,就堵住了正常渠道上升为被释奴隶的发展道路。”恩格斯说:“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11〕。“授产奴隶”不是释放奴隶必须经过的道路。奴隶之被释,在古罗马,是由于商品经济崩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奴隶已“多余而成了累赘”,因此,“被释放的奴隶的数目日益增加”〔12〕。至于“授产奴隶”,则是上述情况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异化现象,胡庆钧同志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一种类型,来论证奴隶社会,是不科学的。何况,在日耳曼尼亚,还不存在这种所谓“授产奴隶”。
至于奴隶获释后的地位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奴隶获释,就解除了人身占有关系,就不是奴隶了,所以,严格的说,不应再称为“奴隶”。关于这个问题,这里只简单的说一下:在日耳曼尼亚农村,不存在所谓“分居奴隶”,因此,也就无所谓“被释奴隶”。只是在国王统治的部落里,奴隶获释后的地位往往可以升得比贵族还高,这是因为他们原来是国王的一些“家庭奴隶”,所以能接近国王,受到宠幸。这种现象,在封建统治下也是存在的,不能作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立论依据。
所以,胡庆钧同志把塔西佗著《日耳曼尼亚志》第24、25节说成是“有关日耳曼人奴隶占有制等级结构的集中描写”,是不正确的。因为,所谓“古典奴隶或者物化奴隶”,已经出口到罗马帝国去了;所谓“分居奴隶”,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些“孤独生活”的“农奴”,而所谓“被释奴隶”,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属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范畴。所谓“日耳曼人奴隶占有制等级结构”,只是胡庆钧同志的一种描写。在他的笔下,日耳曼尼亚的劳动者不仅是“奴隶”,而且是“来自外族或外部落”、“刚与主人分居”并且“全部与主人分居”的“授产奴隶”。所以,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第25节中所说的“家庭”一词中所含有的“家神之义”,也被胡庆钧同志所否定,因为,他说,对这种“授产奴隶”来说,“不能认为已可供奉自己的家神”。其实,塔西佗所说的“家庭”一词中含有“家神之义”,正是胡庆钧同志所说的“忠实记录”,如果说“家神之义”与上述“授产奴隶”不能相容,那么,胡庆钧同志应该以塔西佗的“忠实记录”来否定他的一连串的公式主义推断,而不应从公式主义的推断出发来否定塔西佗的“忠实记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胡庆钧同志对塔西佗的一些记载并没有科学地进行分析,而只是从奴隶制公式出发,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来描绘他所谓的“三个被统治阶级”和“日耳曼人奴隶占有制等级结构”。所以,虽然胡庆钧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都读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论断。
二
在日耳曼人是否经过奴隶社会这个问题上,胡庆钧同志的观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然而,他想把他的观点说成是恩格斯的“原来的观点”。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就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阐述了三种所有制形式。其中,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这里发展了‘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不仅‘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并且‘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他们在这里使用‘仍然’两字,表明第一种所有制的奴隶制已成为整个生产的基础。至于第三种所有制形式,他们称之为‘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书中还指出:‘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又说:‘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的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十分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阐述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就是他们所说的古代世界处在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阶段,他们既然用日耳曼人占领罗马帝国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可见他们所说的古代世界即第一种与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既包括日耳曼社会,也包括罗马社会”。
可是,胡庆钧同志所说的这一些,只是他的一些曲解或误解,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1.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第二种所有制形式”的论述中说:“……相反地,在意大利,由于地产日益集中……由于耕地变为牧场……自由民几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隶也在不断地死亡,而不得不经常代之以新的奴隶。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介于自由民与平民之间的平民,从来没有超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总之,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和占领地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13〕很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意大利在自由民几乎完全消失,奴隶不断死亡,不得不经常代之以新的奴隶的情况下,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并不是就第一种所有制形式而言的。所谓“他们在这里使用‘仍然’两字,表明第一种所有制的奴隶制已成为整个生产的基础”,只是胡庆钧同志的一种曲解或误解,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2.马克思、恩格斯说:“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 )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14〕这说明,“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指“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提到:“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表现为战争或交易)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只是”指“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的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说“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发展了‘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成为整个生产的基础”。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操作有关的。”〔15〕胡庆钧同志说“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发展了‘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成为整个生产的基础”,所以,“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处在奴隶占有制社会发展阶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种曲解。
3.不仅“第一种所有制形式”不属于“奴隶占有制的社会的发展阶段”,就是“第二种所有制形式”,也不完全“处在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说:“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16〕其中,“古代公社所有制”就不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阶段”。恩格斯说:“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17〕“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18〕。以上论述说明:“古代公社所有制”阶段不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阶段”。胡庆钧同志笼统地说“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处在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阶段”,将“古代公社所有制”阶段也包括到“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去,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的。由于上述错误,胡庆钧同志将存在着“公社所有制”的日耳曼社会——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第26节中说:“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包括到“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不正确的。
4.马克思、恩格斯说:“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征服民族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民族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还只是以它的联合和现存的共同体形式为基础。其次,占领的性质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19〕。以上论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用日耳曼人占领罗马帝国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相反地,他们对上述“通常”的“说明”是持批评态度的。胡庆钧同志说:“他们既然用日耳曼人占领罗马帝国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可见他们所说的古代世界即第一种与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既包括日耳曼社会,也包括罗马社会。”应该指出,胡庆钧同志的这后一个见解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古代世界”,是指希腊、罗马,既不是指“第一种与第二种所有制形式”,也不包括日耳曼尼亚。胡庆钧同志把日耳曼尼亚也包括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古代世界”之内,以此来论证日耳曼社会“处在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发展阶段”,是不正确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而只不过是胡庆钧同志的一种误解或曲解。
5.恩格斯所说的“家庭奴隶制”,是根据奴隶劳动的性质来进行分类,相对于“劳动奴隶制”来说的。这种分类本身就说明“家庭奴隶制”和“劳动奴隶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奴隶制度。恩格斯说:“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成为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入家庭(例如内宅的女奴),〔20〕这说明,东方的家庭奴隶不是直接生产者。胡庆钧同志引用恩格斯所说的上述“家庭奴隶制”来论证“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时期“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已成为整个生产的基础”,也是不正确的。既云“隐蔽”,就说明没有成为整个生产的基础。
胡庆钧同志所谓的恩格斯的“原来的观点”,只不过是他的一些误解和曲解,只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21〕,然后把塞进去的东西说成是恩格斯的“原来的观点”。
其实,按照胡庆钧同志的见解,“改变了原来的观点”的,就不止恩格斯,还有马克思。 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 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而马克思早在1857年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所以,胡庆钧同志批评的,实际上不只是恩格斯,还有马克思。可是,马克思“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又受了谁的影响呢?胡庆钧同志所谓的恩格斯的“原来的观点”,只不过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些曲解。是他的观点,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三
马克思说:“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恩格斯说(德意志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是不是因为“受了摩尔根的影响”呢?
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22〕恩格斯说:“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23〕。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说明,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商品经济,需要高度发展的手工业和农业水平。日耳曼人达到了上述经济发展水平吗?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因此说他们处于“野蛮状态”,“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是从经济上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的一个科学的论断。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论断,怎么能说是因为“受了摩尔根的影响”呢?
恩格斯说“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这是因为,公社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即或出现奴隶制,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尼亚还存在着土地公有的公社,并且,恩格斯说:“马尔克制度,直到中世纪末,依然是日耳曼民族几乎全部生活的基础”〔24〕。恩格斯因此认为日耳曼民族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难道又能说是因为“受了摩尔根影响”吗?
关于“日耳曼人占领罗马帝国以前”的“日耳曼社会的性质”,恩格斯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的地位”〔25〕显然,这是一种阶级社会的隶属形式,这种隶属形式,不是奴隶制,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农奴耕作”。这充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日耳曼人占领罗马帝国以前,日耳曼社会已经存在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已经是阶级社会,并没有“受了摩尔根的影响”,“以所谓高级野蛮社会的框界规定当时日耳曼社会的性质”,难道“农奴耕作”这种“传统的生产”,这种“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的隶属形式,属于“高级野蛮社会的框界”吗?
恩格斯说:“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日耳曼人从凯撒到塔西佗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佗到民族大迁徒(公元400 年左右)以前,他们的进步更要快得多。”〔26〕这说明,恩格斯认为,日耳曼人在占领罗马帝国以前,早已进入文明时代,并没有受摩尔根的影响,“以所谓高级野蛮社会的框界规定当时日耳曼社会的性质”。
需要指出,史前史分期和社会发展规律是两个问题。凯撒——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社会不是高级野蛮社会,而是阶级社会,不等于就是奴隶社会。考古学证明,人类进入铜器、青铜器时代时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也不等于就是进入奴隶社会。拙作《为马克思辩》〔27〕一文已经指出,在世界古代,就根本不存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这回事情。早在四十年代,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说:“斯拉夫人也象其他欧洲民族一样,由氏族制度直接进步到封建制度,中间并未经过奴隶制。”〔28〕恩格斯说德意志人“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完全正确。“摩尔根的分期是可以改变的”,但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事实上,恩格斯并没有“以所谓高级野蛮社会的框界来规定当时日耳曼社会的性质”,倒是胡庆钧同志在以所谓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的公式来规定当时日耳曼社会的性质——“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
四
综上所述,恩格斯既没有受摩尔根的影响,也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他说德意志人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胡庆钧同志不加分析地引用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某些记载以及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的曲解来反对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
胡庆钧同志最后说:“时至今日,如果有人仍然把日耳曼人越过奴隶社会阶段直接跨进封建社会视为历史科学的基石,并以此到处推广,实际上企图把奴隶社会视为特例或例外,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应该指出,胡庆钧同志感到“不可理解”,是因为他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对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所作的结论——“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只有正确理解这一结论,才能理解为什么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一种局部的特殊现象,为什么日耳曼民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
现在,人们都已承认,日耳曼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阶段,恩格斯关于德意志人“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论断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胡庆钧同志反对恩格斯的上述论断,说日耳曼人曾经过奴隶社会阶段,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前一篇拙作:《为恩格斯辩》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资料中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3年第3期转载。
注释:
〔1〕胡庆钧:《日耳曼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吗?》, 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以下,凡引自此文的,不再注释。
〔2〕、〔3〕马雍译:塔西佗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6、31页。
〔4〕、〔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4、522页。
〔5〕请参阅拙作《为恩格斯辩》,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 年第1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58页。
〔7〕、〔10〕马雍译:塔西佗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67页。
〔8〕、〔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6、17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8页。
〔12〕、〔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0、1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页。
〔14〕、〔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0页。
〔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5、19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2、8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6页。
〔2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37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5、17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39页。
〔27〕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28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苏联上古中古史》, 中华书局1951年版,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