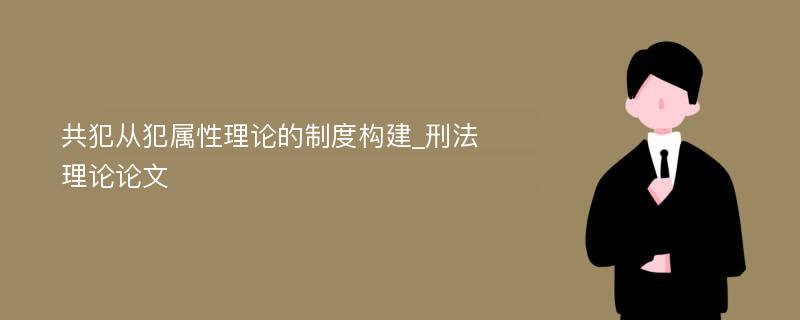
共犯从属性理论的体系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从属性论文,共犯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犯从属性理论是关于正犯和共犯关系的理论,解决的是狭义共犯的成立条件和处罚范围问题。如今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占据重要地位,堪称共犯论的基本原理之一,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通常来说,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和限制正犯概念能够与共犯从属性说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和单一正犯概念倾向于否定共犯的从属性。奥地利学者Kienapfel提出,在统一正犯体系中,在解释论上将直接正犯人和其他参与人同等看待,各共动者只对固有的不法和责任进行答责(自立答责性、独立可罚性原则)。由此,从属性原理没有产生的余地。①意大利刑法学家帕多瓦尼指出,以共犯的行为类型作为基础(即将共犯分为教唆犯、帮助犯、共同正犯)的刑法制度(主要是德国的刑法制度),也包括1889年意大利刑法典所采用的共犯制度,是共犯从属性说赖以产生并发展的前提。②他从该国现行刑法规定出发,不赞同共犯从属性。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可以解释为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因为刑法根据行为类型差异对参与人作了区分,即明确规定了作为狭义共犯的教唆犯,刑法规定包含了正犯和帮助犯的内容;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参与人的犯罪性存在差异而非等价;并且,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和正犯概念在我国刑法学中具有学理基础,它们在我国刑法立法史和学说史中也实际存在过。③基于此,我国刑法学应倡导和研究共犯从属性理论。本文在厘清共犯从属性之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建构共犯从属性理论的体系框架。
一、共犯从属性的不同解读
关于共犯从属性应作何理解,德、日等国家(地区)刑法学界提出了诸种见解。在日本大致可分为三大阵营:团藤重光主张并得到大塚仁、大谷实支持的观点,认为共犯从属性包括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两个方面的内容;平野龙一主张并得到西田典之、山口厚支持的观点,主张共犯从属性包括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他学者提出但表述或内容各异的观点,较有影响的是山中敬一,他认为共犯从属性包括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罪名从属性和可罚从属性四个方面的内容等。以下详述之:①团藤重光提出的从属性分类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共犯从属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有无从属性、从属性的程度这两个问题。具体而言,共犯独立性说和共犯从属性说之间的对立,属于有无共犯从属性的问题;以共犯的从属性为前提,研究其程度问题时,则主要是夸张从属性说、极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最小从属性说之间的对立。④团藤的见解得到了大塚仁、大谷实等权威学者的认可,即共犯从属性可以分为从属性的有无(实行从属性)和从属性的程度(要素从属性)。⑤②平野龙一批判团藤观点是将本应属于复线条的共犯从属性问题简单地用单线条来整理,容易引发歧义。他认为,将共犯从属性分为三种是妥当的,即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这些分别属于不同理论层次的相互独立的问题,即有无从属性、从属性的程度、犯罪共同还是行为共同。实行从属性是有关作为共犯的成立要件,正犯的实行行为是否必要的问题;要素从属性是正犯的行为中,要求具备什么样的要素的问题;罪名从属性是共犯是否必须和正犯罪名相同的问题。具体而言,“实行从属性是正犯现实地实施实行行为,是否共犯成立要件的问题,换言之,共犯尽管实施了教唆行为,但正犯没有实行犯罪时,能否作为教唆未遂处罚。即使正犯没有实行行为,对教唆者也可以作为教唆未遂处罚的观点叫做共犯独立性说,相反的观点叫做共犯从属性说。要素从属性是指作为共犯概念上的前提的正犯行为,是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就行了(最小从属性说),还是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为必要而且仅此就够了(限制从属性说),再或要求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极端从属性说)的问题。正犯之刑的加重减轻事由对共犯影响的问题(认为有影响的见解称为夸张从属性说),也处在上述问题的延长线上。罪名从属性是指共犯是应当与正犯的罪名相同(罪名从属性说),还是说共犯与正犯的罪名不同也可以(罪名独立性说)。该对立也称为犯罪共同说(承认罪名从属性)和行为共同说(承认罪名独立性)”。⑥在弟子西田典之、山口厚等知名学者的大力倡导之下,平野的观点被相当多学者接受。团藤把共犯从属性划分为从属性的有无、从属性的程度,与平野观点具有重合性,这是两说的共性部分,差异在于对罪名从属性的理解上。③山中敬一及其他学者的零散各异的观点,都没有发展到为多数知名学者拥戴的局面,为整理对比的权宜之计,本文笼统地将其归为第三阵营。山中敬一认为,共犯从属性的概念在如下四种意义上使用:实行从属性等于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实行,罪名从属性等于共犯的罪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可罚从属性等于共犯的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的犯罪,要素从属性等于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或违法性或责任。在实行从属性意义上,共犯独立性是指处罚共犯不必待正犯着手实行,共犯如果实施了行为则处罚就成为可能(实行独立性)。与此相反,共犯从属性是指只有在正犯实施了实行行为后才可能处罚共犯(实行从属性),这是通常意义上的共犯从属性和独立性问题。在罪名从属性意义上,存在着狭义共犯的罪名是否从属于正犯罪名的罪名从属性和罪名独立性见解的对立,罪名从属性和罪名独立性问题实际上与共同正犯上的犯罪从属性和行为从属性问题具有共同性质。在可罚从属性意义上,存在着共犯从正犯获得可罚性根据(可罚从属性)与共犯固有处罚根据(可罚独立性)的对立,表现为主张共犯的可罚性是从正犯那里借受来的共犯借用犯说与坚持共犯具有独立于正犯可罚性的固有处罚根据的共犯固有犯说的对立。但是现在没有人采纳共犯借用犯说。于是,可罚从属性问题表现为,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与正犯完全独立(纯粹惹起说)与讨论共犯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不法乃至责任的形式的两者对立。要素从属性的概念相当于平野龙一博士的见解。⑦此外,还有其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从属性概念。齐藤金作认为,从来共犯的从属性被认为有两种意义:一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即教唆犯或从犯为了成立犯罪,至少要正犯着手于犯罪的实行;二是处罚上的从属性,即为了教唆犯或从犯被处罚必须要正犯被处罚,正犯被处罚就意味着教唆犯或从犯亦被处罚。⑧不难看出,齐藤金作所谓成立上的从属性,实际上就是前述的实行从属性。植田重正鉴于共犯从属性及其相对的共犯独立性概念处于未被归纳而错综复杂地、多重意义地被使用的状态,便以Birkmeyer的共犯论为基础,在对其共犯从属性立场加以检讨后,将从属性和独立性的意义分别理解为“实行从属性和独立性”、“犯罪从属性和独立性”以及“可罚从属性和独立性”,并将此运用于“共犯的实行性”问题(即何时为狭义共犯的着手实行时点)、“共犯的共犯性”问题(即包含共同正犯在内的广义共犯是根据何者共同而被视为共犯的问题)以及“共犯的可罚性”问题(即共犯的处罚根据)。换句话说,将共犯行为和正犯行为加以分离,独立地来看,共犯行为如同预备行为,仅属于对结果设定从属性(附属性)的条件而已,不属于实行的范围之内,共犯成立须从属于正犯的实行,这称为“实行性意义的从属性”或简称“实行从属性”;共犯成立范围从属于正犯的犯罪,即共犯成立仅在与正犯成立犯罪的同一限度内有可能性,这称为“犯罪性意义的从属性”或简称为“犯罪从属性”;共犯的可罚性是由共犯者所加功的犯罪借用而来,因此当正犯不具可罚性时,就不存在可罚的共犯,这称为“可罚性意义的从属性”或简称“可罚从属性”。⑨大野平吉认为,共犯从属性包含不同层次的两种问题,分为“实行性意义中的从属性”和“犯罪性意义中的从属性”,大体上对应于“从属性的有无”和“从属性的程度”。前者是指狭义的共犯即教唆犯和从犯为了成立犯罪,要求正犯行为现实地实施,至少着手犯罪的实行。后者指共犯为了成立犯罪,从属于正犯,从正犯那里获取犯罪性为必要(共犯借用犯说),因此,教唆犯和从犯为了成立犯罪,要求正犯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一犯罪成立要件的何种程度,便成为问题。大野认为,植田重正的可罚从属性概念的“借用可罚性”思想,被包含在“犯罪性意义中的从属性”或简称“犯罪从属性”之中了,因此,可罚从属性概念的内容可以考虑被犯罪从属性的概念所解消和包摄。⑩
德国学者Welzel将共犯从属性分为从属性的“内的范围”和“外的范围”,前者指的是要素从属性,后者指的是实行从属性。(11)Maurach区分了“量的从属性”和“质的从属性”,(12)Kienapfel认为,量的从属性,即参与的可罚性是否从属于他人实行了所干之事这种实行从属性;质的从属性,即正犯行为需要在何种程度上具备犯罪要件这种从属性程度的问题。(13)可见,这些观点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概括出六种从属性概念,即概念上的从属性、实行上的从属性、犯罪上的从属性、处罚上的从属性、可罚上的从属性以及要素上的从属性。(14)陈子平曾认为,共犯从属性和独立性的意义应以“实行从属性和独立性”(从属性的有无)和“要素从属性”(从属性的程度)加以理解。罪名从属性问题通常都作为共同正犯的本质问题,即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以及犯罪支配说的对立问题加以检讨。然而共同正犯在本质上属于正犯,而不是如日本通说认为的它也带有共犯性质,因此,共犯从属性的意义无须讨论罪名从属性问题。另外,可罚从属性问题虽与共犯从属性问题相关联,然其应属于共犯更上层、最根源的共犯处罚根据问题,宜放在要素从属性议题上加以检讨,而不作为共犯从属性意义的议题之一。(15)但是,其著2008年增修版《刑法总论》却作如下的表述,即共犯的从属性可分为三种类型: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罪名从属性。与前不同的是承认罪名从属性的概念,即共犯所成立的罪名是否必须与正犯的罪名相同始可的问题,探究共犯应与正犯的罪名相同(罪名从属性说)或者罪名不同亦可(罪名独立性说)。(16)见解前后不一致,使得其立场不甚明了。郑逸哲认为,在个人责任主义下,任何行为人都是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前提就是其独立适用构成要件而产生独立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共犯独立性和从属性并非构成要件之争,是共犯罪名独立性和罪名从属性之争。(17)
二、共犯从属性的概念辨析
围绕共犯从属性这一范畴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应包括哪几个方面的内容(领域之争),各方面内容应怎样准确地归纳(概念之争)。对此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离不开共犯和正犯的相互关系这个大前提,离不开从属性或独立性这个问题点,同时要考虑概念的逻辑性、价值性。下面从各种从属性概念的辨析入手,探索共犯从属性的应有含义。
(一)实行从属性与要素从属性
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共犯从属性包括了实行从属性(从属性的有无)和要素从属性(从属性的程度)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这两者可以说是共犯从属性理论的核心内容。只是,对于实行从属性的外延,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体现在共同正犯之间是否具有实行从属性?日本学者野村稔将实行从属性适用于广义共犯还是狭义共犯的问题,称为从属性的范围。他认为,实行的从属性适用于所有的广义上的共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共同正犯为了实现各自的犯罪意思,至少要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这意味着,在自己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以外,还把他人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违法行为,去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因此,如果在自己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以外,对于他人违法行为的结果也要承担责任的话,现实上就必须是该他人实施了违法行为。这样,要对于他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该他人现实地实施了违法行为是必要的,于是,共同正犯之间也具有相互的从属性。(18)持共同正犯从属性见解的还有团藤重光、植松正等。(19)
我们认为,野村稔关于共同正犯具有从属性的论证方法是不妥当的。他本身并不承认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那么就实行共同正犯来说,是指二人以上出于共同实行犯罪的意思而共同实施实行行为的共犯形式。参与人的违法行为当然是必要的,这是该共犯形式的成立条件,也是逻辑上的必然要求。但是,行为人以其他实行正犯的存在为必要,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求其他实行正犯着手实行,自己才能成立犯罪。事实上,即使对方没有实施,自己已经着手实行的,就已经达到了可罚的未遂程度,如果该罪名在日本刑法中规定了未遂亦罚,那么就可以成立犯罪和对其处罚。就此而言,实行共同正犯根本不存在从属性的问题。认为实行共同正犯具有从属性的观点,是对从属性概念过于随意的理解,而没有紧扣实行从属性的特点内涵。针对共同正犯具有从属性的观点,大塚仁提出过如下质疑:它只是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的问题,还是被认为是共同正犯一般的要件呢?对此,其趣旨不明确。而且,在共同正犯中,共同者相互利用各人的行为、互相补充以实现某犯罪的关系,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是,绝不能看出是从属关系。所谓从属,是对主要者的服从,但是与教唆犯、从犯相对于正犯的关系不同,尽管在共同正犯中共同者之间的行为事实上可能存在优劣,然而,从法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等和平等的,它们一体化“都是正犯”。认为其具有与教唆犯和从犯同样的从属性,是不妥当的。(20)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也从正犯的实行分担角度否定了从属性,“在属于正犯的共同正犯中,每一个正犯的部分行为,彼此互为补充,共同协力而完成犯罪,虽然他们彼此之间亦存在相当程度的依赖关系,但是每一个正犯均依照共同的行为决意内容,而各有其角色功能上的分工,故与属于共犯的教唆犯与帮助犯系依附从属于正犯的主行为的情况有所不同”。(21)这些见解明确否认了一般的共同正犯中的从属性。
事实上,在日本刑法学界,主张共同正犯具有从属性的学者,更多的是以共谋共同正犯为视角。为共谋共同正犯提供共同意思主体说之理论依据的草野豹一郎持该主张,他说,“历来,人们所称的加担犯即教唆犯、从犯依正犯的成立而成立的共犯从属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进而言之,就依通谋而成立的共同正犯而言,也必须承认这种从属性的意义。我把这一从属性称之为成立上的从属性”。(22)传承乃师立场的齐藤金作也认为,在所谓共谋共同正犯的场合,单纯的共谋者从属于实行担当者的实行行为,以此讨论了共同正犯的从属性。(23)我国学者黎宏教授认同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认为“在没有实行行为就不成立共谋共同正犯的意义上,共谋共同正犯也仍从属于实行行为。这就是共谋共同正犯的从属性”。(24)我们认为,即使是共谋共同正犯,也不能承认从属性。在共谋共同正犯的场合,存在共谋者和实行者两种参与人。实行者肯定不从属于共谋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对于共谋者,没有实行,只有实行者才能直接、现实地侵害法益,从这一点来看,共谋者似乎具有了从属性。然而这样的判断,忽视了共谋者本身的正犯性,因而是不妥当的。由于共谋共同正犯中的共谋者被评价为“正犯”,他实施了哪怕是共谋的行为,也因具有正犯性,对于法益侵害存在危险,从而具备了未遂处罚的可能性。既然共谋者本身存在成立犯罪和可罚的基础,不依赖于实行者的实行,又谈何“从属性”呢?如果非要说存在从属性的场合,那就只是从属于实行者构成犯罪既遂,但这已不是“实行从属性”的本来含义。
对于共同正犯和狭义共犯都具有“共犯从属性”的见解,确实在有些时候,共同正犯会面临类似的探讨。比如,在正犯行为合法的场合,是否仍然成立教唆和帮助是个问题,同样的,在其他共同者的行为合法的场合,是否仍成立共同正犯也可能成为问题。但是,如果将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通过“从属性”观点加以处理,在论理上会产生矛盾。比如,在共同者A的行为因违法性阻却而合法,B的行为违法的场合,是从属于A的合法行为,从而双方都不成立共同正犯,还是从属于B的违法行为,从而都成立共同正犯,这在论理上是无法确定的。这体现了在共同正犯中难以设想“从属性”这一观念,共同正犯不存在“从属”于其他共同者行为这样的关系。(25)
否定共同正犯的从属性,更深层的理由在于,正犯和共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根本不同。共同正犯和狭义共犯作为广义的共犯,虽然具有共同的处罚根据,即行为和法益侵害之间的因果性,但具体的因果过程存在差异,共同正犯是法益侵害的共同惹起类型,教唆犯和帮助犯是间接惹起类型。以此为指导,去理解它们的成立条件,就产生了重要的不同,以简单的比喻或图式来说,共同正犯等于因果性+共同性,教唆或帮助等于因果性+从属性。(26)共同正犯基于在犯罪实行中的作用方式和重要程度,应该被评价为“一次责任”。尽管它也有共犯性的一些特征,即在本身并未满足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时,也会受到处罚(比如,两人经过意思疏通开枪射杀他人,只有一人的子弹命中致被害人死亡,另一人虽然未打中被害人,并未满足杀人既遂的单独正犯构成要件,也要作为共同正犯承担杀人既遂的罪责),在这一点上与狭义共犯具有相通的地方,也属于刑罚的扩张形态。但这不能否定其正犯性的本质属性,“共同正犯”概念的核心应落在“正犯”上,“共同”所体现的共犯性一面只具有补充的意义,即共同正犯属于正犯,但并非“本来的正犯形态”,而是“扩张的正犯形态”。德国权威刑法学者Hans-Heinrich Jescheck、Thomas Weigend指出,“不是从属性归责的原则,而是在共同犯罪决意范围内实施的所有犯罪行为的直接的彼此归责,适用于共同正犯……这不是说,共同正犯共同参与了他人的正犯行为,而是共同正犯的所有行为在法律上将被同等对待,并将之归责于每一个共同正犯”。(27)Johannes Wessels也说到,“由于共同正犯的不法性在于其自身,不是根据他人的行为来推论;因此,对共同正犯不适用在属于教唆和帮助的情况中关键性的从属原则,而是适用对所有的以有意识的和所意愿的共同作用所做出的行为贡献予以直接的相互归责(unmittelbare wechselseitige Zurechnung)的基本原则”。(28)共同正犯不同于单独正犯之处在于,不要求每个正犯都完整地实施基本构成要件行为的全部,而是可以与其他正犯相互利用、相互补充来协力完成。但是,共同正犯中任何一员都可以通过自身行为直接地侵害或威胁法益,而不是必须从属于其他正犯,这是狭义共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共犯从属性仅指“狭义共犯”的从属性,即教唆犯和帮助犯从属于正犯,共同正犯的从属性难以被承认。
(二)罪名从属性
根据前述平野龙一的见解,罪名从属性是指共犯是否必须触犯与正犯相同的罪名。犯罪共同说是罪名从属性说,而行为共同说则是罪名独立性说。他进而认为,犯罪共同说与极端从属性说乃至夸张从属性说相结合,行为共同说与限制从属性说乃至最小从属性说相结合。同样,川端博指出,“直到现在,极端从属性说、夸张从属性说与限制从属性说、最小从属性说的对立,以及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对立,仅被作为完全不同的问题而被处理。但是,两者本来就是相同的问题。倘自从属性的观点来看,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对立,是所谓的‘罪名从属性’的问题。罪名从属性是指共犯是否有必要时常与正犯或其他共犯依相同的罪名、罚条进行处断的问题。关于罪名从属性的问题,犯罪共同说认为共犯是共同实行完全相同的犯罪,因此理解为共犯的罪名必须与正犯相同。与此相对,行为共同说认为不需要犯罪共同,犯罪的‘行为’共同即为已足,因此不同的罪名之间也成立共犯关系就被认可”。(29)上述观点表明了罪名从属性概念指涉的问题,以及罪名从属性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对立的关联。然而,共犯是否存在罪名从属性?能否说“犯罪共同说=罪名从属性”、“行为共同说=罪名独立性”,或者“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之争=罪名从属性”的问题?下面逐次辨析:
首先,关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对立的范围,是只针对共同正犯的本质,还是广义的共犯也涉及,理论上存在严重分歧。很多学者持前一种观点(木村龟二、福田平、香川达夫等),比如,木村龟二认为,“广义共犯只意味着由二人以上参加而成立,正确地说,共同正犯是正犯的一种形态,与狭义共犯具有本质差异。因此,认为它们存在相同的本质是不合理的。在教唆犯、帮助犯(从犯)这种狭义共犯的场合,共犯与被教唆者、被帮助者即正犯的关系,从共犯从属性说的见地来看,前者从属于后者;从共犯独立性说的见地来看,则各自处于相互独立的关系,故两者完全不存在共同关系,因而也没有余地说两者存在什么共同的问题。但共同正犯是两个以上的正犯共同实行犯罪,故存在二人以上有什么共同的问题,该问题就所有的共同正犯而言都是共通的、本质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问题,作为广义共犯的本质问题来考虑,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注意,其只是共同正犯的固有问题”。(30)我国台湾地区有多位学者以共同正犯的本质是正犯、正犯和共犯有实质差异为据,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视为共同正犯本质上的固有问题。(31)但是,赞同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少。曾根威彦指出,现在一般认为,关于共同正犯本质的讨论,不仅是共同正犯的问题,也是广义共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共通的问题。(32)山中敬一认为,“包括共同正犯在内的广义共犯,关于与其他参与者共同参与‘什么’的问题,存在两个基本学说即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事实共同说)的对立”。(33)川端博认为:“以前,关于‘共同正犯’,仅在是犯罪共同还是行为共同上被讨论。但是,它应该被作为‘共犯’的全体的问题而被考察。”(34)内藤谦认为,“虽然此对立确实是以共同正犯为讨论的核心,但应理解为有关广义共犯整体的问题。理由在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是有关共犯为何就他人行为所引发的结果要被追究罪责的问题,亦即与包含教唆犯、从犯等共犯整体的处罚根据有关联的问题,乃有关所谓‘共犯的共犯性’(共犯本质)的对立”。(35)龟井源太郎认为,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争论,是“有关复数的共同者之间的共动在同一构成要件内(或者至少在构成要件的重合范围内),可以承认共动的犯罪吗”的问题,不是作为共同正犯的固有问题。(36)常举的例子是,教唆他人盗窃(或伤害),但正犯实际实施的是抢劫(或杀人),那么,教唆者是承担教唆盗窃(或伤害)的责任还是教唆抢劫(或杀人)的责任,这与在共同正犯本质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有关。所以,共同正犯本质问题讨论的射程也及于狭义的共犯,应该作为共犯从属性的内容。如今,日本通说和我国台湾地区多数说认为,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是广义共犯的本质问题,而非仅限于共同正犯。(37)在我国,赞同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都有,比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在刑法理论上,关于共犯的本质的范围存在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共犯的本质只是共同正犯的问题;有人指出,广义的共犯中也存在着是采取犯罪共同说与还是采取行为共同说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共犯的本质基本上是共同正犯的问题”。(38)而明确持后一种立场的学者不在少数,(39)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然而,各方均缺乏具体论证。
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最初来自法国刑法学者对广义共犯本质的探讨,争论的问题是共犯究竟要求什么是共同的,换言之,二人以上的行为在哪些方面共同才成立共犯。该问题在日本由牧野英一提出来,他在“犯罪共同说=客观说”、“行为共同说=主观说”的思考形式下,主张必须坚持“行为共同说=主观说”。(40)两说对立的产生和发展,存在学说史的演变过程。日本学者龟井源太郎经过整理归纳为:完全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又分为强硬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和温和的(或柔软的)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又分为强硬的行为共同说和温和的行为共同说。例如,甲、乙分别以杀人和伤害的故意,共同向丙开枪射击,丙中一弹死亡。①按照完全犯罪共同说,因为一人出于杀人的故意,一人出于伤害的故意,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属于不同的构成要件,故甲、乙不构成共同犯罪,在不能查明谁的行为导致丙死亡时,甲、乙各自单独承担杀人未遂、伤害未遂的责任;②按照强硬的部分犯罪共同说,甲、乙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同正犯,但由于乙只有伤害的故意,乙仅在伤害罪的刑罚范围内处罚;③按照温和的部分犯罪共同说,由于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在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内存在构成要件的重合,因此,甲、乙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共同正犯,由于甲具有杀人的故意,另单独承担故意杀人罪的责任;按照强硬的行为共同说和温和的行为共同说,尽管二人的故意内容不同,但双方具有共同的行为,故分别成立杀人罪的共同正犯和故意伤害罪的共同正犯。在上述的各种处理情形中,强硬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导致定罪和科刑相分离而广受指责;④强硬的行为共同说认为只要是前构成要件的自然行为的共同,就可以成立共同正犯,该说为早期新派学者主张,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征表,这有违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因此强硬的行为共同说现在不再有支持者;⑤温和的行为共同说又被称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强调在构成要件的框架内肯定行为的共同,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称的行为共同说,它受到了客观主义学者的支持,比如平野龙一、前田雅英、山口厚等。温和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称的部分犯罪共同说。总结来说,现在关于共同正犯本质之争,基本上是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41)即温和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与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的对立。从所处历史时期和代表性学者来看,在日本,持完全犯罪共同说(或严格犯罪共同说)和完全行为共同说(或以主观主义为基础的行为共同说)立场的,大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早期学者,前者比如泉二新熊、大场茂马、胜本勘三郎、小野清一郎、泷川幸辰等,后者比如牧野英一、宫本英修等。犯罪共同说首先由泷川幸辰等立足于客观主义刑法理论而提出,现在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是立足于构成要件论而主张部分犯罪共同说,如团藤重光、福田平、大塚仁、大谷实等。该说不再强调共犯是数人实施所预计到的“特定的犯罪即一个故意犯”,而主张在同罪质的构成要件相互重合的范围内认定成立共犯。比如,大塚仁就认为,以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础理解共犯时,应该根据犯罪共同说,即二人以上者共同实行某特定犯罪时,就成立该犯罪的共同正犯。不过,即使二人以上者共同实行的是不同的犯罪,当犯罪具有同质的、互相重合的性质时,在其重合的限度内也应该解释为成立共同正犯。(42)该说目前在日本仍居通说地位。其二是立足于共同意思主体说,主要由草野豹一郎主张,中坚力量为早稻田大学齐藤金作门下和中央大学下村康正门下的学者。由于其所强调的意思结合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故意犯”,主张“一个主体一个犯罪”,因而结论与完全犯罪共同说并无不同。现在也只有共同意思主体说严格坚持犯罪共同说。(43)持构成要件行为共同说(或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的行为共同说)的学者有佐伯千仞、平野龙一、内藤谦、金泽文雄、川端博、前田雅英等,(44)该说在日本逐渐成为有力说。
从以上的学术考察可见,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在于,共犯因“犯罪”还是“行为”而共同。作为两说如今主要立场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和构成要件行为共同说,分别立足于“构成要件被评价为具有实质重合性的犯罪”与“构成要件行为”,来探讨共犯因何而共同。这就说明了两说的对立,应该是关于共同正犯本质问题的争论。因为,根据限制正犯理论,狭义共犯是基于刑法分则构成要件和总则共犯规定相结合的修正构成要件形式,教唆和帮助行为本身并非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那么,狭义共犯和正犯之间也就不可能像共同正犯那样,存在实质重合性犯罪或构成要件行为的共同的问题。在狭义共犯加功于正犯的场合,其意图教唆或帮助正犯去实施的行为,正是正犯本身实施的行为,由于只存在正犯的构成要件行为,因而便无从共同。只能说狭义正犯“意图”正犯实施的行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正犯的行为所“实现”。例如,甲教唆乙去盗窃,乙是否现实地去实行了盗窃。如果乙实际上窃取了财物,无疑是完全地实现了甲的教唆意图;或者乙在行窃过程中转化为抢劫,但可以规范地评价为包含了盗窃,这时也可以说乙的实行,实现了甲的教唆意图。于是,乙成立抢劫罪,甲则因为教唆盗窃并通过乙的实行而实现了对财产法益的侵害,当然也成立盗窃罪。如果乙并没有着手实行,则甲的意图没有实现,两者都不成立盗窃罪。无论怎样,在上述场合,都不可能存在甲和乙的盗窃构成要件行为共同的问题。总而言之,狭义共犯本身不能独立成立犯罪而需要依赖于正犯的实行,正犯实行则共犯和正犯一起成立犯罪,正犯未至实行则两者皆不成罪。在此,只有狭义共犯相伴于正犯是否成立犯罪的问题,而不存在两个独立罪的犯罪或构成要件行为是否共同的问题。因此,不可以说广义共犯也会涉及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
根据完全的犯罪共同说,共同正犯之间的罪名是相同或一致的。但是部分犯罪共同说和构成要件行为共同说的结论都是,共同正犯之间的罪名不需要相同,即否认了罪名一致性。由此看来,理论上采取的学说不同,会导致共同正犯之间罪名是否一致的差异。但是,尽管根据有的学说共同正犯之间罪名一致,有的学说否认了罪名一致,却不能说,罪名一致表示罪名具有从属性,罪名不一致就是罪名独立性。因为如上所述,共同正犯不具有从属性,又何谈罪名的从属性呢?事实上,共同正犯各自具有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直接成立相应的犯罪,罪名又何需从属。认为共同正犯之间的罪名具有从属性,或者说共同正犯具有罪名从属性,本身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而且,共同正犯之间是否需要罪名一致性,本身不是前提,而是采取犯罪共同说或行为共同说所得出的结论而已。更何况,该学说对立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共犯是否被限定为故意犯,即在过失犯的场合能否成立共犯;共犯之间欠缺意思疏通能否成立,即是否承认片面共犯等),意义远超的简单结论。因此,将针对共同正犯本质的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对立的某一方面的结论(“罪名是否需要一致”),归纳为罪名从属性概念,毫无意义。
其次,关于共犯是否具有罪名从属性。从前面分析可归纳出,罪名从属性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不是一回事(内涵和外延均不同),后者是有关共同正犯的本质的争论,共同正犯之间不存在罪名从属性的问题。抛开两说的对立,接下来进一步探讨,狭义共犯对正犯是否具有罪名从属性。
狭义共犯依赖于正犯的实行,正犯着手实行后,共犯和正犯一起成立犯罪(客观违法意义上的共同犯罪);正犯未至着手实行,则两者皆不成罪。既然共犯从属于正犯而成立犯罪,那么一般来说,只要正犯和共犯的罪过相同,正犯之罪即为共犯之罪,共犯和正犯的罪名具有一致性。比如甲教唆乙杀丙,乙顺利杀死了丙,乙成立故意杀人罪,甲当然是没有任何意外地从属于该罪名,即成立故意杀人罪。但是在以下情况中,正犯的实行因出现意外发生转化,或者正犯和共犯在意思疏通之时,彼此的罪过内容就不同时,根据责任主义原则,任何人只对自己的罪过支配下的行为和结果承担罪责,共犯和正犯当然就应该成立不同的罪名。比如甲教唆乙盗窃,而乙转化为抢劫,由于乙的抢劫并非甲的主观故意内容,尽管客观上乙是在甲的教唆下实施盗窃,没有甲盗窃的教唆,也不会去实行并进而发生意外转化为抢劫,但甲仍只能在自己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承担乙的抢劫中可以规范地评价所包含着的盗窃罪的罪责,(45)即甲、乙成立共同犯罪,但乙成立抢劫罪,甲不从属于乙的罪名而只成立盗窃罪。
由此可见,狭义共犯和正犯的罪名保持一致性,并不是必然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依据的并不是所谓罪名从属性中的“犯罪共同”或“行为共同”,而是根据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理论,判断狭义共犯是否具备“客观违法”,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以下的犯罪论基本原理,即犯罪成立取决于客观违法和主观责任,行为人只对自己罪过支配下的行为和结果承担罪责,最终确定犯罪(罪名)的成立。立足于因果共犯论(惹起说)的共犯处罚根据,(广义的)共犯是教唆犯和帮助犯通过介入正犯,或者共同正犯和其他共同者一起,基于引起的构成要件事实(构成要件的结果),以其固有的违法、责任为根据而受到处罚,共同犯罪现象是“数人实施(各自固有的)数罪”。也就是说,只要将共同犯罪理解为违法形态,是共犯人实现各自犯罪的方法类型,那么共犯和正犯的罪名不一致,便不存在任何障碍。作为结论,共犯和正犯成立共同犯罪,但完全可能构成不同的罪名,并基于不同罪名承担相应的罪责,共犯对正犯不具有罪名从属性。
山口厚在教科书中,将共犯从属性分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三个方面加以检讨,但是他承认,就教唆和帮助而言,罪名从属性原则上要否定。理由是,仅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及违法性尚不成立犯罪,还必须进一步存在责任。对人们存在的故意、过失这样的责任要素的责任非难才是正当的,所以即便是在共犯人之间,责任也应该个别地加以判断。从而,就客观上引起的构成要件该当事实而言,责任内容(故意)不同而罪名(该当的犯罪类型)也不同的场合,不同共犯人之间罪名当然也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对应于自己的责任(故意)而成立相应的共犯。比如,A出于杀人的意思而想去砍人,B误认为A只想实施伤害而借给了刀子,在被害人受到伤害的场合,B不成立杀人未遂的帮助,而成立与自己的责任相对应的伤害帮助。(46)山口厚认为,在上述正犯认识超出了共犯认识的场合,否定罪名从属性是妥当的。本文认为此论完全正确。但他同时指出,一部分场合要肯定罪名从属性,即与上述相反的共犯认识超出正犯认识的情形。(47)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在共犯认识超出正犯认识的场合,鉴于共犯的“二次责任”类型,共犯不能超出正犯的限度去允许刑法的介入,因而共犯成立与正犯一致的罪名。换言之,共犯虽能较正犯的罪名成立更轻的罪名,却不能成立较之更重的罪名。对该部分理由,本文也是完全认同的。因为,“违法的连带性”应该得到一般承认,这意味着,应坚持实行从属性说和限制从属性说,正犯违法则共犯原则上亦违法,因此在共犯认识超出正犯认识的情况下,共犯至少是可以成立能被其罪责包含的(正犯认识范围内的)正犯罪名。我们也承认一定条件下“违法的相对性”,根据混合惹起说的立场,可以存在“无共犯的正犯”,但不存在“无正犯的共犯”,因此,超出了正犯的认识而共犯有所认识的那部分罪责,共犯不应承担,此即我们不能承认的“无正犯的共犯”。结论便是,在共犯认识超出正犯认识的场合,共犯也只能在正犯不法的范围成立犯罪,此时共犯和正犯的罪名保持一致。固然如此,但是表述为(一部分场合下)共犯对正犯具有“罪名从属性”,其妥当性值得推敲。
最后,关于中外刑法学者对“罪名从属性”的论证过程和逻辑。赞同者大都是对该概念一介绍了之,随即将其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联结”起来,然后就把全部笔墨花在该学说对立上。上述学者都不否认该学说对立关涉共同正犯的本质,只不过同时又主张狭义共犯也涉及该对立,于是就认为,狭义共犯存在罪名从属性。这样的论证逻辑,无异于只是给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戴了一顶“罪名从属性”的帽子,以罪名从属性之名,探讨两说对立之实。至于狭义共犯是否以及为什么具有罪名从属性,罪名从属性概念有什么内容和意义,都缺乏直接、深入的论证,多有“公式代入”的痕迹,完全经不起推敲。罪名从属性本身并不能作为一个理论前提,去辅助指导和解决其他的共犯问题,而只是一个单纯的结论而已,而且这个结论还不能成立,其存在价值大可质疑。
综上所述,所谓罪名从属性概念探讨的问题,属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对立的内容,且只是该对立内容的一部分。罪名从属性或独立性其实就是,共同正犯之间的罪名是否需要一致的意思,由于共同正犯不具有从属性,当然也不存在罪名从属性的问题。大塚仁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即“平野博士的分类虽可以说对错综的共犯从属性问题进行了一个整理,但是,把不同性质的从属性的各方面并列地加以思考,有扭曲对事态本质的认识之虞”。(48)因此,探讨共同正犯本质涉及所谓“罪名从属性”内容时,应避免使用该概念,而直接表述为“是否要求罪名一致”。由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针对的只是共同正犯的本质,因此,狭义共犯不存在罪名从属性,有关共犯和正犯的相关内容,也可表述为“是否要求罪名一致”。总之,共犯不具有罪名从属性,应将罪名从属性概念逐出共犯论领域。
(三)可罚从属性与处罚从属性
一般来说,可罚从属性和独立性探讨的是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植田重正、山中敬一),即共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是来自于共犯自身或者说共犯本身所固有,还是来自于其加功的正犯或者说从正犯所借用?前者的观点是可罚独立性说,后者的观点是可罚从属性说。正如所述山中敬一所指出的,现在已没有人采纳共犯借用犯说(可罚从属性)。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通说认为,共犯具有自身独立的处罚根据,而关于该处罚根据为何,学说史上大致存在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因果共犯论(或惹起说)这三种见解。如今,因果共犯论(或惹起说)已占据绝对地位,争论焦点存在于该说内部的纯粹惹起说、修正惹起说和混合(或折中)惹起说之间。
如前所述,根据齐藤金作的理解,处罚上的从属性是指,为了教唆犯或从犯被处罚必须要正犯被处罚,正犯被处罚则意味着教唆犯或从犯亦被处罚。本文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行为人成立犯罪和接受刑罚处罚,往往前后相继、相伴而生,无前因则无后果,由此可以说,行为人的犯罪性和处罚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除非承认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并且具体犯罪要求该条件)。但是,并不能由此就导出,共犯因为从属于正犯的实行而成立犯罪,则共犯的处罚也必然从属于正犯而被处罚,这样的结论。在共犯理论上,“违法的连带性、责任的个别性”是一般原则,那么,“刑罚个别化”就是必然之理。刑罚的轻重受到个人的身份等因素影响,共犯和正犯因具有不同的身份而受到轻重不同的刑罚,是完全正常的。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1条第二款规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关系致刑有重轻或免除者,其无特定关系之人,科以通常之刑”。《日本刑法》第65条第二款、《德国刑法》第28条以及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刑法,都有类似的明确规定。因此,从理论上看,共犯被处罚不必从属于正犯被处罚。而且,从实际追究共犯刑责和处罚共犯的程序来看,即使正犯因为在逃等因素未被追诉和判处刑罚,也并不影响共犯在犯罪指控被确认后,被判处应受的刑罚。日本曾有判例指出,“从犯对正犯具有从属性,只有在正犯成立的场合,才能成立。但是,正犯尚未被起诉,也未受到确定判决的事实,并不妨害先于正犯对从犯论罪,在这种场合,应当首先根据证据确定正犯的事实,然后判定从犯的事实”(大判1917年7月5日《刑录》第23辑,第787页)。该做法具有妥当性,因而受到学界支持,大塚仁在论及对教唆犯和从犯的处罚时说,《日本刑法》第61条第1项规定对教唆者科以正犯之刑,第63条规定从犯之刑减轻正犯之刑,其趣旨都是在与适用于正犯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相对应的法定刑范围内处罚,并不意味着对教唆者或帮助者的处罚要从属于对正犯的处罚。应该分别考虑独立存在于正犯者与教唆者、帮助者的刑罚加重减轻事由,对教唆者、帮助者量定比正犯者更重的刑也无妨。因此,作为处罚教唆者、帮助者的前提,没有必要起诉或处罚了正犯者。(49)韩国学者也指出,在共犯从属性中,共犯的成立并非以正犯受到处罚为前提(处罚上的从属性)。(50)法国学者在注解法国刑法规定时说到,成立共同犯罪,必须要有应当受到惩处的主犯的行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定要主犯的犯罪行为已经“实际受到惩处”,共同犯罪始能成立。即使是以下表述的情形,共犯仍然可以受到追诉和处罚:在主犯尚未受到追诉时,或者由于主犯尚未查明、已经死亡,或者由于主犯是未成年人,或者主犯在实行犯罪时是处于精神错乱状态,或者主犯已经得到个人赦免,或者由于检察机关尚未对主犯提起追诉等原因,因而尚不可能对主犯进行追诉、惩处时,对共犯仍可受到惩处。(51)因此,共犯被处罚不从属于正犯被处罚,处罚的从属性既缺乏理论基础,也无现实必要。概言之,共犯不具有处罚上的从属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可罚从属性和处罚从属性是不同的概念。我国有学者在谈到这两个概念时,认识到了两者不同这一点。但是认为,“犯罪上的从属性”和“处罚上的从属性”常常相提并论,指共犯本身没有犯罪性和处罚性可言,而是来自于正犯实施的犯罪行为,是从正犯那里借用过来的,由此体现出从属的一面。“可罚”是指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可罚性”即“不法和罪责之外的可罚性条件”,比如客观处罚条件是否具备、是否有处罚阻却事由等,可理解成第四个犯罪成立要件。可罚的从属性说认为,若正犯不可罚则从属性共犯亦不可罚,它主张的是最极端的从属形态。(52)对于这些表述,本文认为有纠错辩误的必要。其实,共犯固有犯说、共犯借用犯说正是可罚从属性的问题,而不是处罚上的从属性。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可罚性概念本身存在多义性,比如植田重正的可罚从属性概念,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指共犯为了成立犯罪和处罚,要求正犯的行为作为犯罪成立,并进而具备客观处罚条件,从而具有现实的可罚性这一意义,而是仅指共犯的可罚性根据的问题。(53)论者将处罚从属性理解为共犯借用犯说,而将可罚从属性的可罚性理解为客观处罚条件,是将词汇简单对应,望文生义,这必然导致对概念本身错讹的理解。
鉴于可罚性的多义性,且学界使用可罚从属性、处罚从属性概念时,出现了指称不一致的现象,(54)因此,有必要明确其含义,厘清相互之关系,规范化地使用这些概念,以便为开展共犯从属性研究扫清概念和术语上的障碍。本文认为,可罚从属性探讨的是共犯处罚根据的问题,即作为狭义共犯的教唆犯和从犯,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而应被处罚。共犯借用犯说和共犯固有犯说分别对应于可罚从属性和独立性,前者从共犯之外的正犯身上,寻求共犯可罚性的依据,后者认为共犯可罚性来自于共犯本身。责任共犯论、不法共犯论和因果共犯论都是在可罚独立性说的立场上,探讨共犯本身可罚性内容的学说。处罚从属性指的是,共犯被处罚是否应以正犯被处罚为必要,是否以正犯被现实地受到追诉和处罚为前提,共犯的刑罚轻重是否也应正犯的刑罚保持一致。
(四)犯罪从属性
犯罪从属性也是不少学者提到的概念(植田重正、大野平吉等)。犯罪即可罚的行为,或者说有责、可罚的违法行为,行为成立犯罪就应被刑罚处罚,至于是否被现实地科处刑罚,则是另一回事(比如,如果承认客观处罚条件但该条件尚不具备、鉴于罪责事实和情节而在量刑时被免予刑罚处罚)。因此,犯罪性和可罚性基本上可以作同义的理解。正是如此,学界在介绍“共犯固有犯说”、“共犯借用犯说”时通常说,其对立内容是共犯的犯罪性或可罚性由来于自身还是正犯。由此可见,“犯罪从属性”和“可罚从属性”基本上是相提并论的,探讨的都是共犯自身是否具有可罚性以及可罚内容是什么的问题。
如前所述,植田重正将所谓罪名从属性的问题,归纳为犯罪从属性,而大野平吉所提的犯罪从属性,指的却是要素从属性。因此,他们理解的犯罪从属性,指的是共犯为了成立犯罪,需要怎样从属于正犯,即罪名是否要求从属,或者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违法和有责中的何种程度。也就是说,他们将“犯罪从属性”中的“犯罪”,理解为了(共犯)犯罪成立条件,而不是探讨共犯在根本上应否具有“犯罪性”。若非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犯罪从属性概念,其完整含义就应是“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如前所述,不应承认罪名从属性概念,罪名只存在是否一致的问题,而不是从属),与此相对,犯罪独立性就是“实行独立性”(如此则没必要再讨论要素从属性的问题)。
无怪乎人们感觉,从属性的概念繁多、指涉颇乱。概念必须承载一定的功能(归纳、区分等),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一个概念完全可以被其他概念代替,不能提示新的思路和内涵,同时还会造成无端的分歧,就没有保留的必要。理论术语和学术概念同样如此,必须着眼于对建构理论体系与开展学术研究的裨益。既然在犯罪成立条件意义上理解的犯罪从属性,指的就是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不如直接以广为接受的后两者来指称。况且“犯罪从属性”和“可罚从属性”根据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两者基本上相提并论,那么,不使用犯罪成立条件意义上的犯罪从属性概念,也可以免除很多理解上的混乱。既然“犯罪从属性”和“可罚从属性”基本上相提并论,两个概念探讨的是同一问题,而可罚从属性概念更为人熟知(在探讨共犯处罚根据本身的时候),不如干脆就尽量不使用犯罪从属性的概念,彻底免除误解以正视听。
(五)概念从属性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提到过共犯概念上的从属性,“盖从属云者,乃指共同加功于犯罪之各人间互相依倚或一方依附于他方之关系,就法律所规定各种共犯(广义)之涵义而言,不仅教唆犯帮助犯有其从属性,即共同正犯相互间,亦不免此从属关系,申言之,法律认某一犯罪者构成共同正犯,至少须以另一共同加功者之存在为前提,倘二人中有一方不成为共同实施者,则他方亦无共同正犯之可言。依同理,法律之承认有教唆犯或帮助犯,必以他方有一被教唆者或被帮助者为前提,倘无人被教唆或帮助,则此方之教唆或帮助行为亦必无从发生,职是,此种从属性,乃共犯之本质使然,实无可避免,堪称为共犯概念上的从属性”。(55)显然,概念从属性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当然结论,学界对其表达的意思,不存在任何争议,即使共犯独立性说也不否认。日本学者对此作过阐述,“在共犯从属性的问题上所说的从属性,有必要明确是意味着这种论理的从属性,还是意味着从属于现实存在的正犯行为?所谓共犯论理性的从属性既然不否定共犯独立性的理论(共犯独立性论),当然要被确认,而且不是共犯从属性问题中所说的从属性,所以用它作为共犯从属性的根据也是错误的”。(56)团藤重光也指出,“共犯必定是某个罪——杀人罪或盗窃罪——的共犯,纯粹的共犯是没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共犯概念可以说在论理上必然从属于正犯概念。但是,成为问题的不是这种论理的从属性,而是实质的从属性。即,应该讨论共犯之成立,是否要求正犯行为现实地实施(从属性的有无),并进而是否要求该正犯行为具备何种程度的犯罪要件(从属性的程度)”。(57)因此,所谓共犯的概念的从属性,不属于共犯从属性的理论范畴。事实上,此从属性概念之提出,仅止于一名称耳,本身无甚实质意义,提或不提皆无所谓,不如不提。
三、共犯从属性理论的体系框架
日本学者对于共犯从属性应包括哪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从属性的整序问题,倾注了极大热忱,由此提出了诸多从属性概念。但是,各学说对于若干方面从属性内容,具备或体现了怎样的逻辑关系,探讨的却极少,结果反倒是影响了对共犯从属性的本来内涵的理解。典型的例子就是,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戴上“罪名从属性”的帽子,不恰当地整合到共犯从属性理论之下。我国在开展共犯从属性的研究之初,就注意到了各从属性概念及其内容的逻辑层次和相互关系问题,并有学者初步尝试建构共犯从属性的理论体系。
(一)我国共犯从属性的范畴与体系研究
李洁教授等认为,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内涵存在多层次性。第一个层次是共犯处罚根据问题,解决没有实施基本构成要件行为的共犯的可罚性何在,即共犯为何要受到处罚的问题。对此形成了共犯可罚性从属说(借受说)和共犯可罚性独立说(固有说)的对立;第二个层次是共犯在何种情况下成立犯罪予以刑罚处罚的问题。对此形成了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独立性说的对立。实质上是基于对共犯行为性质的不同认识,而对共犯成立的条件产生的分歧;第三个层次是基于在第二层次中采共犯从属性说的情况下,对于共犯成立要求正犯具体具备何种要件的问题。也就是共犯从属性说内部所产生的关于共犯从属形式的不同观点。在上述三个层次的问题中,可罚从属性关系到共犯行为成为刑法评价对象的实质根据,关系到共犯行为进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因而处于共犯论的基础地位。而且,在实行从属性问题和要素从属性问题的内部争论中,采何种立场却往往要借助于共犯处罚根据的判断。即实行从属性的有无以及采何种要素从属性这些关于共犯成立的形式问题,最终要到共犯处罚根据中来寻找实质根据。只不过共犯处罚根据对于实行从属性的有无以及要素从属性的选择只产生影响而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在论者看来,可罚从属性、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是共犯从属性理论体系的内容,而罪名从属性则不是,理由是罪名从属性涉及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两说的对立是共同正犯本质的争论,共同正犯本质上是正犯,不应包括在共犯从属性中“共犯”的概念之内,因此罪名从属性不在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射程之内。(58)叶良芳博士认为,共犯从属性应当是指实行从属性、罪名从属性和可罚从属性。实行从属性是指共犯成立要件是否需要正犯现实地实施了实行行为的问题,即确定共犯的犯罪性是否需要正犯实行犯罪,这正是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独立性说直接对立的问题,因而也是共犯从属性说的根本问题。罪名从属性说是指共犯是否需要与正犯使用相同罪名的问题,主要是从形式上解决共犯的犯罪性问题。可罚从属性是指共犯的处罚是否必须以正犯的处罚为前提,主要是解决共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刑从罪生,实行从属性必然带来罪名从属性和可罚从属性问题,后两者是共犯从属性的派生问题。共犯从属性和独立性之争首先是共犯的定罪问题,与该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共犯处罚问题和罪名确定问题。因而,前两者解决共犯的定罪问题,后者解决共犯的量刑问题。至于要素从属性,实际上是指从属性的程度问题,与前三者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因而不宜将其与前三者并列考察。(59)阎二鹏博士认为,共犯从属性说、独立性说也是关于共犯处罚根据的学说。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本质是法益侵害,只有在正犯着手实施实行行为时,狭义共犯对法益的侵害危险才能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这时对共犯的处罚才是合理的。而独立性说则认为,对行为人“危险性格”的处罚才是刑法的目的,因此,当共犯实施行为时,这种“危险性格”即征表出来,不待正犯者实施实行行为即可对共犯者进行处罚。两者的争论反映了客观的犯罪论和主观的犯罪论之间的对立,所探讨的无疑也是共犯行为为什么值得科处以及如何才能论处的问题,应视为对其处罚设立根据的学说。不仅如此,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对于责任共犯论和不法共犯论等处罚根据学说而言是更为前提的讨论,后者基本上可视为对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的进一步阐明。(60)
应该说,我国学者并没有提出超越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从属性概念,那么,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就应理解其本来含义,否则会造成误读误解。首先,关于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的关系,李洁教授和叶良芳博士都认为要素从属性是以实行从属性为前提的次一层次的问题,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因为,“所谓实行从属性本来是与这样的前提问题相关的,即教唆犯、从犯是能够自身独立存在还是只有从属于正犯才能存在,而要素从属性则是站在教唆犯、从犯只有从属于正犯才能成立的立场上,进一步以从属于具备何种犯罪要素的正犯这种论点为内容的,与实行从属性处于不同的思考层次,使两者在同一层次上并列应该说不妥当”。(61)但是,不能由于要素从属性在逻辑上与实行从属性不在一个层面上,就将要素从属性排除出共犯从属性的内容。在大陆法系共犯从属性理论中,要素从属性甚至比实行从属性更加受到重视。而且,尽管对共犯从属性的内容存有不同见解,但在包括了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这两方面内容上,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界没有任何争议,也就是说,要素从属性属于共犯从属性的内容,已为学界公认。因此,叶良芳博士否认要素从属性是共犯从属性的内容,在论理上是说不通的。另外,他关于可罚从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颇,可罚从属性不同于处罚从属性,它不是解决共犯的量刑问题,而是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即使如李洁教授等正确地理解了可罚从属性的含义,并且合理地评价了它在共犯论中的逻辑地位,但如前文所述,可罚从属性并不属于共犯从属性的内容。至于罪名从属性是否属于共犯从属性的内容,李洁教授等对此予以否认,叶良芳博士持肯定意见。我们认同李洁教授等的判断,理由不再赘述。其次,阎二鹏博士关于共犯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的定位值得商榷。刑法学上对于犯罪行为的所有问题的探讨,包括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和成立条件等,都是为了在遵循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的基础上,科学地量定不法和罪责,以便使犯罪行为得到公正、合理地处罚,从而实现刑法的目的(处罚本身不是目的,论者有的表述存在瑕疵)。但是,为了更好地处罚与凭什么处罚不能完全等同,前者谈的是“条件”,后者论的是“根据”,这一点从论者自己的表述即“如何(才能对其论处)”和“为什么(值得科处)”中也可看出。应该说只有“为什么”才是处罚“根据”的问题,即是可罚从属性需要探讨的。由是而论,可罚从属性和实行从属性分别探讨的是共犯的处罚根据和成立条件,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不应将后者等同于前者。
(二)共犯从属性理论的体系建构
共犯的从属性和独立性是有关狭义共犯的性质或本质的争论,探讨的是狭义共犯本身的特征、属性或者与正犯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属性,共犯从属性显然是与独立性相对的,经学术研究而对具有共犯从属性的内容,进行的学说阐述和理性归纳,便形成了共犯从属性理论。因此,共犯从属性理论不包括共犯具有独立性以及与共犯属性无关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共犯从属性理论是在不断廓清共犯的从属性或独立性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决定了,尽管如今可能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某方面内容不具有从属性,因而它不属于共犯从属性理论的范畴,但毕竟在学说史上,它经历过与从属性说的对立,因而可以说与从属性具有紧密的关系,那么,在论述共犯从属性理论时,对这样的内容就不可能避免涉及。相反,通过对其论述和检讨,有利于明确从属性本身的内涵和合理性。所以说,不是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内容,不代表不能涉及,反过来,在开展共犯从属性研究时,对某内容涉及并展开讨论,也不表示它就属于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内容。“相关”不意味着“包容”,这是必须明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下述见解不能被认同:即认为共犯从属性理论作为一个包括了诸多内涵的体系,不同内涵涉及的问题完全可能采取不同的立场。可罚从属性问题中否定从属性说而采独立性说,而实行从属性问题中采从属性说而摒弃独立性说,这并不是矛盾的。各种从属说和独立说是对共犯从属性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应将各种独立说排斥在共犯从属性理论之外。(62)论者意在构建共犯从属性的理论体系,但实际结果是模糊了共犯从属性理论本身。下面围绕中外刑法理论中出现的从属性范畴,逐一进行检讨其是否属于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内容。
其一,在关于共犯从属性的种种学说中,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都是公认的共犯从属性的内容。实行从属性说和实行独立性说的对立,是共犯从属性研究的固有、核心内容。现在一般提到共犯从属性说时,就是指实行从属性说,而提到共犯独立性说时,即指实行独立性说。随着实行从属性说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中取得牢不可破的通说地位,要素从属性便成为主要的争论点,成为当今的共犯从属性研究的中心议题。
其二,罪名从属性之争的内容表现为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一般认为前者支持罪名从属性,后者主张罪名独立性。随着理论的变迁,犯罪共同说内部产生了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内部产生了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分别是修正取代已有学说、相互借鉴的产物。部分犯罪共同说是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但行为共同说正逐渐变得有力化。两说针对具体犯罪的结论大体一致(不可避免地存在细微差异),但在共同犯罪理念和论证逻辑上存在根本差异。时至今日,尽管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还在继续,但对罪名的严格的从属性可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尽管原则上要求共犯与正犯的罪名应当一致,然而,至从部分犯罪共同说崛起,不一致的现象就得到了一般性地承认。作为有力说的构成要件行为共同说,并不要求共犯与正犯罪名的一致性。因此,罪名的从属性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中已不复存在。
其三,可罚从属性探讨的是共犯的处罚根据,不同于探讨共犯成立条件的共犯从属性。如今,可罚从属性说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中也不再有人主张。因此,可罚从属性不属于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内容。
其四,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独立性说对立的初期,由于深受刑法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基本立场的影响,实行从属性说、罪名从属性说等“坚定团结”在同一阵营,并存的是各自对应的独立性说所组成的阵营。然而,随着客观主义确立起在刑法学中的地位,以及共犯论的深入发展,共犯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的对立模式已然发生了变化。正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所言,“日本以前的通说观点将实行从属性、极端从属性、罪名从属性三者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采取(综合)从属性说。也就是共犯本身并不单独具有犯罪性、可罚性,而是通过借用正犯的犯罪性、可罚性,才具有可罚性;而且,正犯的可罚性只有在正犯着手实行犯罪而构成未遂之后,且正犯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之时,方可加以肯定;并且,由于正犯的可罚性是由罪名、处罚条文来决定的,共犯当然应从属于正犯的‘犯罪’的理由也在于此。这里采取的是硬的‘犯罪’从属性说。但现在与犯罪共同说相对立,行为共同说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提倡。这也是共犯的处罚根据由责任共犯论转化为因果共犯论这种学说变化之归结。在行为共同说看来,存在否定罪名从属性的可能。这种理论发展的结果便在于,有关上述三种从属性的问题,已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整体解决,而是有可能且必须个别解决”。(63)“个别解决”意味着共犯从属性理论包括的几个方面内容发生变化,实际上是排除了罪名从属性和可罚从属性。
综上,共犯从属性只包括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两个方面或层次的内容。实行从属性探讨的是狭义共犯的成立或可罚性是否要求正犯着手实行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实行独立性说和实行从属性说的对立。要素从属性是在坚持了实行从属性说的前提下,即在狭义共犯成立或可罚性要求正犯着手实行以外,进一步探讨还要求正犯具备何种程度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最极端从属性说、极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和最小从属性说等争论。从逻辑上看,探讨要素从属性的问题,表示对于共犯具有实行从属性是业已解决的问题。因此,实行独立性说和实行从属性说是对立的关系,而实行从属性说和要素从属性说是递进的关系。共犯独立性说即指实行独立性说,而共犯从属性说的完整含义是“实行从属性说+要素从属性说”。由此可见,实行从属性是共犯独立性和共犯从属性之间的问题,而要素从属性属于共犯从属性内部的问题。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说上,前者是较早时期的课题,目前基本尘埃落定,现在的主要课题是后者。总而言之,共犯从属性理论就是探讨狭义共犯的成立或可罚性是否从属于正犯的实行,以及从属之正犯应具备何种条件的理论。
注释:
①转引自[日]高桥则夫:《共犯体系と共犯理论》,成文堂1988年版,第22页。
②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③参见张开骏:“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与‘规范的形式客观说’正犯标准”,《法学家》2013年第4期,第56页。
④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第3版),创文社1990年版,第375、384页。
⑤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四版),有斐阁2008年版,第285~286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3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408页。
⑥[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Ⅱ》,有斐阁1975年版,第345~346页。
⑦参见[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Ⅱ》(第2版),成文堂2008年版,第797~798页。
⑧参见[日]齐藤金作:《共犯理论の研究》,有斐阁1954年版,第120页。
⑨参见[日]植田重正:《共犯の基本问题》,三和书房1952年版,第163页。
⑩参见[日]大野平吉:《共犯の从属性と独立性》,有斐阁1964年版,第36、39页。
(11)参见前注⑥,[日]平野龙一书,第347页注(1)。
(12)参见前注④,[日]团藤重光书,第376页注(二)。
(13)转引自前注①,[日]高桥则夫书,第22页。
(14)参见陈培锋:《刑法体系精义——犯罪论》,康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以下。
(15)参见陈子平:“论共犯之独立性与从属性”,《刑事法评论》2007年第2期,第1~3页。
(16)参见陈子平:《刑法总论》(2008年增修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17)参见郑逸哲:“修法后的‘正犯与共犯’构成要件适用与处罚(上)”,载《月旦法学教室》2006年第40期,第72~82页。
(18)参见[日]野村稔:《刑法总论》(补订版),成文堂1998年版,第390页。
(19)参见前注④,[日]团藤重光书,第385页注(二十三)、第422页注(八)。
(20)参见前注⑤,[日]大塚仁书,第283页注(十五)。
(21)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增订十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22)[日]草野豹一郎:《刑法总则讲义》(第一分册),南郊社1935年版,第194~195页。
(23)参见[日]齐藤金作:“共谋共同正犯の理论”,《刑事法讲座》1952年第3卷。
(24)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25)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有斐阁2007年版,第297页。
(26)同上,第297页。
(27)[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17~818页。
(28)[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
(29)[日]川端博:《共犯の理论》,成文堂2008年版,第28~29页。
(30)[日]木村龟二:《犯罪论の新构造》(下),有斐阁1968年版,第248页。
(31)参见甘添贵:“正犯与共犯:第一讲——共同正犯的本质”,《月旦法学教室》2003年第6卷;前注(16),陈子平书,第331页;陈子平:“共同正犯之本质”,载《刑事法学之理想与探索:甘添贵教授六秩祝寿论文集》(第一卷),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93页。
(32)参见[日]曾根威彦:《刑法の重要问题》(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5年版,第311页。
(33)前注⑦,[日]山中敬一书,第794页。
(34)前注(29),[日]川端博书,第28页。
(35)[日]内藤谦:“犯罪共同说と行为共同说”,《法学教室》1990年第116号。
(36)参见[日]龟井源太郎:《正犯と共犯を区别すゐとぃぅこと》,弘文堂2005年版,第16页。
(37)参见前注⑤,[日]大谷实书,第406页;[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006年版,第373页;陈子平:《共同正犯与共犯论——继受日本之轨迹及其变迁》,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20页。
(38)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页注⑩。
(39)参见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朴宗根:《正犯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40)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41)参见前注(36),[日]龟井源太郎书,第18页以下。
(42)参见[日]大塚仁:《犯罪论の基本问题》,有斐阁1982年版,第309页。
(43)参见[日]立石二六:《刑法总论》,成文堂2004年版,第293页。
(44)参见前注(29),[日]川端博书,第30~31页;前注⑥,[日]平野龙一书,第365页。
(45)此处构成要件行为的包含的评价,是一种刑法学的规范解释方法。虽然部分犯罪共同说也采用了这种解释方法,但并不表明此处运用了部分犯罪共同说。因为狭义共犯不存在专门探讨共同正犯本质的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抢劫构成要件规范地评价为包含了盗窃构成要件,都是针对正犯乙的构成要件行为而言的,由此被评价为实现了的盗窃构成要件,可以基于违法的连带性,为教唆犯甲承担盗窃的罪责提供客观基础。并不是说,乙的抢劫构成要件行为包含了甲的盗窃行为,因为教唆犯甲的行为本身不是构成要件行为。
(46)参见前注(25),[日]山口厚书,第313~314页。
(47)同上,第314页。
(48)前注⑤,[日]大塚仁书,第283页注(十四)。
(49)同上,第316、327页。
(50)参见[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相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51)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52)参见何庆仁:“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两种涵义”,《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45~46页。
(53)参见前注⑩,[日]大野平吉书,第41页注(五)。
(54)比如,大塚仁说过,“从犯的可罚性不从属于正犯的可罚性”。前注⑤,[日]大塚仁书,第327页。书中虽然使用了“可罚性”一词,但所表达的意思是,处罚共犯不需正犯实际被处罚,共犯的刑罚也不必与正犯保持一致,即指共犯不具有处罚从属性。
(55)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56)[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郑树周等译校,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49页。
(57)前注④,[日]团藤重光书,第375页。
(58)参见李洁、谭堃:“论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内涵”,《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2~104页。
(59)参见叶良芳:《实行犯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6页。
(60)参见阎二鹏:《共犯与身份》,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脚注①。
(61)前注(42),[日]大塚仁书,第346页。
(62)参见前注(58),李洁、谭堃文,第104页。
(63)前注(37),[日]西田典之书,第3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