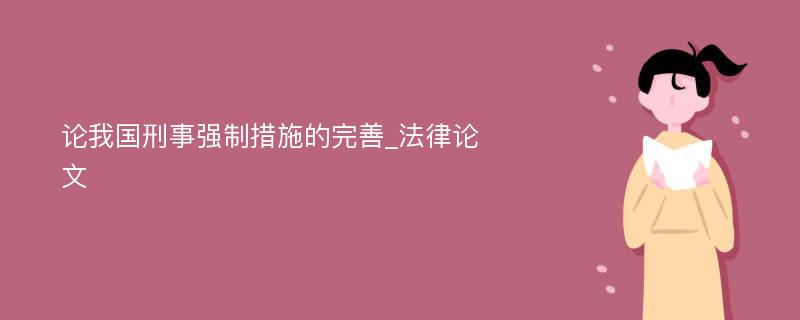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制措施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刑事强制措施。司法实践表明,这五种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现有强制措施的预防性和实用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刑事诉讼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亟需在立法和实践中加以完善。本文就如何改进与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略陈管见。
一、关于拘传
根据传统的刑诉理论,拘传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未被羁押的被告人,强制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方法。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看,涉及拘传的部分仅有寥寥的二十八个字,它除了说明拘传的机关、对象、方法和目的外,没有其他内容。由于规定的过于抽象,在适用中逐步暴露出下列问题:(1)适用面过窄。拘传是我国现有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最轻微的一种,它的方法和目的仅仅是强制被拘传人到案接受讯问。这种对被拘传人约束力极其有限的强制措施,如果仅适用于单一的被告人,那么它的实用性也就微乎其微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拒不到案的情况比较少见,而较多的是那些尚未立案的犯罪嫌疑人以及拒绝提供案件情况的知情人,但这两种人又恰恰被立法者排除在拘传的适用对象之外。(2)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对于拘传应适用何种方式?是有证拘传还是无证拘传?需经何级审批?拘传后应否立即通知被拘传人家属或单位?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均无明确规定。这在实践中既容易出现拘传的滥用,又极易在适用中各行其事。(3)缺少必要的时限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拘传措施仅原则规定:“可以对被告人适用”,而没有具体规定拘传的适用时间、拘传的解送时间以及被拘传人到案后的留置时间,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这些问题。以被拘传人到案后的留置时间为例,根据传统的刑诉理论,一般不能超过24小时,如果24小时尚不能讯问完结,应该将被拘传人立即释放,然后根据需要再进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拘传。这既容易打草惊蛇,给被拘传人留下逃跑、串供、伪造、毁来证据的可乘之机,又容易在群众中造成“随抓随放”、出尔反尔的不良影响。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针对上述问题,对现有拘传措施作如下改进和完善:
(一)从立法上扩大拘传的适用范围。
拘传措施,除对被告人适用外,对犯罪嫌疑人、拒绝提供案件情况的证人也可以适用。理由是:(1)这是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需要。刑事强制措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及时完成。而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到案,其行为如同被告人一样会对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起着延缓作用。把他们列为拘传对象,正是为了体现拘传的目的并符合立法原意。(2)已具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基础。目前诉讼法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应将犯罪嫌疑人列为拘传对象,而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采用拘传措施的并不鲜见,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具有一定基础。(3)把证人列为拘传对象有利于公民履行作证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虽然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但对有义务履行、也有条件履行而拒不履行作证义务的公民则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刑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一些了解案件真实情况,有义务作证的公民拒绝履行向司法机关作证义务的现象,致使一些案件难以处理。如果把证人列为拘传对象,不仅可以约束公民更好地履行作证义务,而且可以防止和减少拒绝作证现象的发生。(4)有外国立法可资借鉴。当前,在英国、德国等国家刑事诉讼法中,均把被告人以外的人列为拘传对象,这对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我们也可以从中借鉴。
(二)、明确规定拘传程序,以增强适用中的可操作性。拘传程序主要应考虑三个方面内容:(1)明确拘传的审批程序。·拘传必须经县以上司法机关负责人批准,以防止滥用。(2)确认拘传的形式。即在一般情况下采取拘传措施的,应向被拘传人出示拘传证。拘传证应载明被拘传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或住所,以及拘传的理由和解送处所。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无证拘传,但执行后必须按照审批权限,补办审批手续。(3)拘传后应立即通知被拘传人的家属或工作单位。
(三)、明确规定必要的期限,防止适用中的随意性。拘传是刑事诉讼中的执法行为,应当有明确的时限加以规范,这对促使司法人员抓紧时间办案,防上随意性和保障人权均有重要意义。拘传的时限主要应明确三个方面:(1)拘传的适用时间即拘传这一强制措施应从什么时间开始适用。笔者认为,拘传的适用时间应与适用对象相一致。如果适用对象扩大到犯罪嫌疑人和证人,那么其适用时间也应提前到立案前审查阶段。(2)拘传的解送时间即执行拘传后到指定场所的时间。应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和一些涉案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特点,对本地拘传和外地拘传的解送时间加以不同规定。在本地拘传,一般不宜超过24小时;到外地拘传的,其解送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如果超过这一时间才能执行,则不宜适用拘传措施。(3)拘传到案后的留置时间。主要包括24小时内必须讯问和就同一案件事实24小时不能讯问完结的,可以接着讯问不算超限两个方面,无需履行第二次拘传手续。
二、关于取保候审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措施,实际上仅是一种人保形式,即由司法机关责令被告人提供保证人,并由保证人具结保证书,保证被告人在不受羁押的条件下,不逃避侦查,起诉、审判,并能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应该说,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中曾起过有益的作用。但由于该措施的执行主要靠保证人对被告人进行约束,缺乏来自外界和有关机关的强制力,因而存在着较大的弊端。主要表现在:(1)对职保候审适用的条件规定的不明确。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地规定:“根据案件情况”,没有具体规定应具备哪些条件。致使一些司法机关在掌握取保候审条件时宽严无度,甚至有些人把取保候审当作变相释放被告人的一种手段。(2)对保证人条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常常是被告人随便找一个亲属、朋友或同事即可,至于保证人是否对被告人具有约束力,具有多大的约束力,能否承担法律责任,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司法机关很少认真审查。因此,使法律规定流于形式,起不到保证人应有的作用。(3)对被告人和保证人没有足够的法律约束力。由于立法上没有规定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也未规定保证人未尽到担保义务时,如何处理,使得保证书在出现问题后成为一纸空文,根本无法追究其责任。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弥补这一立法上的漏洞,曾经发了《关于取保候审的被告人逃匿如何追究保证人责任的批复》,但该批复中只规定了两种特殊情况,即:一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由保证人承担应由被告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二是保证人若与被告人串通,协助其逃匿,其情节已构成犯罪的,可追究其窝藏罪的责任。但在一般情况下,即在没有附带民事诉讼,而保证人又没有窝藏行为,只是对被告人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的情况下,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仍未明确规定。这就容易导致保证人对被告人不管不问,使被告人不能受到应有的约束,为使取保候审措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条件。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1)可能判处管制以下刑罚而不需要逮捕的;(2)对需要逮捕,但证据还不充分的;(3)应当逮捕的人犯,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婴儿的;(4)已被羁押的被告人,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5)逮捕后发现具有上述第(3)项情形的。
(二)明确规定保证人应具备的条件。取保候审措施能否奏效,保证人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作为保证人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与本案无利害关系;(2)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一定的经济能力,能承担保证的法律责任;(3)有便于在工作或生活中经常与被告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固定职业或住所;(4)取得被告人的信任并能约束被告人的行为。
(三)明确规定保证人未尽保证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取保候审期间,如果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而发生被告人逃跑、自杀、毁灭证据等有碍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事件,视情节轻重,追究保证人的法律责任和给予其他处罚。如果保证人有意将被告人放跑或帮助其逃跑,或者明知被告人串供、毁灭、伪造证据而不制止、不报告,应按刑法第162条的规定,以包庇罪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情节一般的,可给予罚款、行政拘留等处分。
(四)明确规定保证金制度,把人保与财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时,被告人和保证人应同时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可以随案移交,在变更或解除这一措施时,视被告人及保证人履行义务情况决定是否退还,促使保证人认真履行其保证义务,以约束被告人的行为。
三、关于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是司法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依法限令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区域,并对其行动自由进行监视的一种强制方法。就立法本意来看,监视居住介于拘传、取保候审与拘留、逮捕之间,属于一种有条件地相对限制人身自由的中性措施。但由于立法当时对这项强制措施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弹性过大,加之又未充分考虑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两个极端。具体表现在:(1)对监视居住不用或少用,使其流于形式。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乡、镇)被告人所在单位执行”。这一规定,显然没有认真考虑执行机关的实际承受能力。姑且不论执行单位在主观上能否尽职尽责,就是在客观上要真正适用这一措施,也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保障。加之不能有效排除被监视居住人利用他人或现代通讯工具串供、转赃的可能性,实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因而司法机关常用其他强制措施代替它,即使偶尔使用,也因执行单位不配合,而使其放任自流或执行不了。(2)滥用或误用,违背立法原意。由于法律在监视居住的“区域”上规定的不明确,而“指定”又是由司法人员来进行的,所以监视居住的地点往往选择那些便于控制的地点。有的把监视居住的区域限定在招待所或办公室的某一房间,由办案人员轮流看管,同吃同住,昼夜监视;有的为了节省人力和安全,就将监视居住的区域指定在公安机关的收审站或行政拘留所,由收审站或行政拘留所的专门人员看管,法律手续则使用监视居住决定书。这些现象不仅使监视居住措施失去应有的作用,而且使公民的合法利益遭到严重侵犯,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故一些学者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取消这项强制措施,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为了保持原有强制措施体系的完整性,增强取保候审与拘留、逮捕之间的衔接性,取消监视居住以后,可以考虑把收容审查升格为刑事强制措施,取代监视居住。理由是:(1)收容审查与拘传、取保候审相比,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的可靠程度高,把其作为一项刑事强制措施,更能适应当前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2)收容审查与拘留、逮捕相比,适用条件宽,对人犯人身自由限制程度低,在实践中不仅被广泛使用,而且深受司法工作人员普遍欢迎。(3)收容审查虽然是一项行政强制手段,但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刑事强制属性,在同刑事犯罪的多年斗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把收容审查作为刑事强制措施之一,可使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进一步完善。
四、关于拘留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措施,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刑事诉讼中紧急情况而采取的紧急处置手段。它在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中起着重要而又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近年来刑事诉讼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增多,拘留措施中逐渐暴露出一些亟待改进和完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立法上规定的时间过短,影响了使用效能。法律规定拘留时间一般为三天,特殊情况下方可延长四天,加上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的三天,被告人实际拘留期限最长为十天。而我国幅员辽阔,司法人员办案路途遥远,交通又不十分发达,少数边远地区更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人员流动越来越大,要想在限定的三至七天内查清主要犯罪事实,达到批准逮捕的程度,显然是不客观的。另外,随着《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国家实行平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作制度,如果已拘留报捕的案件正好赶上本周休息2天,那么,检察机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无法在一天内做出捕或不捕的决定。(2)立法上对拘留的实质性条件限定过严。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罪该逮捕的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这一规定说明,采用拘留的条件有二:一是罪该逮捕,即被拘留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可能会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二是情况紧急,即来不及按逮捕的程序正常办理逮捕手续。从实质条件来看,与逮捕毫无区别。(3)立法上规定拘留措施仅限于公安机关独家行使欠妥。检察机关虽然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它也同时承担了二十余种案件的侦查任务,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其自行侦查的范围将会逐步扩大,一些跨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犯罪案件,甚至是涉外案件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要想应付突发而又紧急情况,就缺乏必要的应急措施和手段。为此,对拘留措施,在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一)适当延长拘留期限,以增强其实用性。尽管我国刑事拘留期限在世界各国同类措施中是比较长的,但从国内司法实践中需要来看,仍然过短。公安机关常常是采用变通办法来使用这项强制措施。即先将现行犯或犯罪嫌疑分子收审,待查清主要犯罪事实后再转拘留报捕。这样一来,拘留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应急措施了,而成为促使批捕机关在三天内作出捕或不捕决定的一种手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拘留时间过短,在实践中起不到应有作用所致。为此,笔者认为现有的拘留期限仍有适当延长之必要。根据一般案件在提请逮捕前侦查工作实际需要的天数,同时考虑当前我国各地司法机关现有的侦查条件,能力以及承受力等因素,将现有的三至七天延长到15至20天,以增强拘留措施的实用性。
(二)放宽拘留条件,使其与逮捕措施相区别。拘留和逮捕是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其适用条件和对象应该有所区别,才能拉开档次。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第41条对拘留的限制条件过严与逮捕适用的实质性条件没有区别,建议取消刑事诉讼法第41条中“罪该逮捕”这一限制条件,该条可以表述为:“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分子,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三)明确赋予人民检察院以拘留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赋予公安机关以拘留权,人民检察院没有这种权力,这对检察机关有效地办理自侦案件十分不利。在实践中,常常遇到某些案件中的被告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的五种情形,需要对其及时拘留控制,但因为没有拘留权,只有商请公安机关进行拘留。如果公安机关不同意或虽然同意但并未及时对被告人进行拘留,侦查活动就无法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一些权大位高、关系网密的被告人,往往由于检察机关在侦查中无权及时拘留他们,而得以四处活动,通过种种手段和上下左右的关系,或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或毁灭、伪造证据,给侦查工作造成严重的被动局面。为防止上述弊端的继续发生,有效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建议立法上应尽快赋予人民检察院以拘留权,包括执行拘留权。
五、关于逮捕
逮捕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措施,也是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多的一种。尽管立法当时对这一措施规定的较为详尽,但在实践中仍反映出一些问题。主要是:(1)逮捕条件弹性较大,实践中难以把握。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了适用逮捕的三个条件,即:一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二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这三个条件,最容易掌握的仅仅是第一个条件,而第三个条件最难把握,例如,社会危险性指什么?怎样认定被告人有可能继续犯罪、逃跑、自杀、行凶报复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其判断依据及尺度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难具体把握,结果只能凭侦查机关或有权批准、决定逮捕的机关自由认定。这样一来,在实践中就很容易导致宁愿将可捕可不捕的被告人加以逮捕,也不愿将可捕可不捕的被告人采取其他强制措施加以限制。(2)法律对被逮捕的人犯在情况发生变化时的变更权、撤销权规定的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51条只规定“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至于由谁释放,是由原批准或决定逮捕的机关,还是由执行或发现的机关,法律均未作明确的规定。(3)立法上的审查批捕阶段的补充侦查规定的不完善。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或者补充侦查的决定”。但未规定补充侦查的期限,这会影响到案件的及时查处。(4)法律规定“逮捕人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有点欠妥。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逮捕人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这一规定从立法原意上看是为了加强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但实际上,公安机关除对自行侦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人犯派人执行外,对检、法两家自行受理的案件需要逮捕人犯的,基本上不派人执行。以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为例,检察机关决定逮捕后,不要说到外地捕人,就是在本地公安机关也很少派人。只是由检察机关拿着公安机关开出的逮捕证,以公安人员的名义自己去执行。这种纯形式主义的制约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鉴于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逮捕措施加进与完善:
(一)减少逮捕条件中的弹性,以增强实际操作性。只需规定:“重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有逮捕必要的”即可。删去“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这段话。因为有无逮捕必要已经包含了类似内容。至于何为“逮捕必要”,可以掌握这样一个标准,即凡具备逮捕条件中第一、二两个条件,而不具备其他强制措施适用条件的,即可视为有逮捕必要。
(二)明确规定人民检院和人民法院行使已逮捕人犯的变更权和案件撤销权。凡是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人犯,因患有严重疾病或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而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必须经原批准或决定的机关同意才能变更,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变更或释放。凡公安机关侦查已经检察机关批捕的案件,需要撤案的,需正式写出撤案报告,说明撤案的理由和依据,经原批捕机关批准后方可撤案。
(三)明确审查批捕阶段补充侦查的期限。刑事诉讼法对不同的诉讼阶段均规定了补充侦查内容,但由于没有具体退补期限和次数的限定,所以往往成为办案单位延长办案期限的一种手段,审查批捕阶段的补充侦查也是如此。为此立法上应明确限定各个诉讼阶段的补充侦查期限和补侦次数。审查批捕阶段的补充侦查时间以一个月为宜,补侦次数限定在一次,如果在一个月内尚不能补侦终结,检察机关有权催办。
(四)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逮捕执行权。其基本构想是,谁负责侦查由谁执行逮捕。这既可以减轻专门执行机关的负担,又能有力地把握侦查的及时性,防止因原来执行机关不予执行或不及时执行而出现的各种弊端。
总之,通过对现行强制措施的上述改进,可以使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进一步完善。使各项强制措施之间具有较强的衔接性,以应付刑诉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对象,充分发挥刑事强制措施自身的预防和保证功能。
标签:法律论文; 取保候审论文; 检察机关论文; 保证人论文; 刑事强制措施论文; 刑事诉讼法论文; 司法拘留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