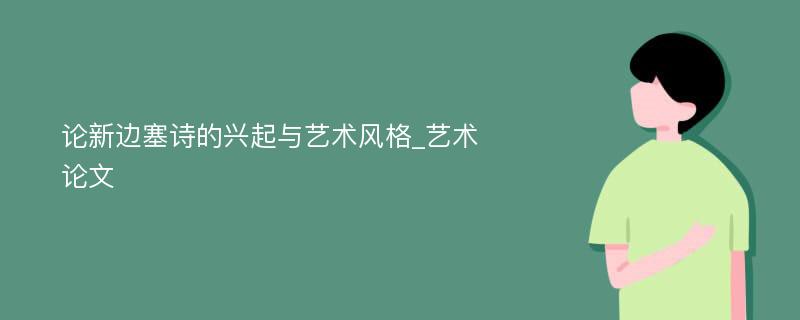
论新边塞诗的兴起及其艺术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塞诗论文,艺术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实际上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全国一些有影响的著名诗人都曾先后涉足过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写下了一些反映西北边疆生活的新边塞诗。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吐鲁番情歌》和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田间的《天山诗抄》,李季的《河西走廊行》,张志民的《西行剪影》等诗集;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的《西出阳关》、《雪满天山路》、《伊犁河》、《夜进塔里木》、《昆仑行》、《喀什一条街》、《在大沙漠中间》、《他们下山开会去了》、《春歌》,艾青的《年轻的城》、《烧荒》、《帐篷》、《地窝子》以及李瑛、袁鹰等人描写西部生活的作品,可以说是为新边塞诗的萌芽与兴起起了催生的作用。特别是闻捷的作品,为新边塞诗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起了开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创立新边塞诗这个主张还来不及正式提出;大多数诗人来去匆匆,缺乏对西部生活长期的、深入的积累和体验(闻捷除外),缺乏对西部各民族古老的历史、璀璨的文化的深刻的研究和了解,缺乏对西部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气质和心理的深入了解和认真的思考。尽管他们当时写下了一些优秀之作,但大多数作品在反映西部生活方面浮光掠影,题材开掘不深,过于表面化,缺乏深刻的思想力度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显得比较单调,缺乏阳刚之气、雄浑之风。当时生活在新疆的一些诗人,虽然也写下了一些富有边地特色的作品,但由于大多数诗作者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都很不够,其作品的思想内容比较平庸,艺术水平还处于低级阶段,在全国诗坛上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也不可能出现风格相近的诗人群,更谈不上有共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见解之类。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部诗坛上虽然产生了象闻捷这样杰出的诗人,新边塞诗的创作刚刚萌发,但新边塞诗作为一个流派还没有开始形成。一直到80年代初,新边塞诗的创作才出现了空前兴盛和繁荣的景象,一个引人注目的、崭新而独立的文学流派——新边塞诗派开始形成。
新边塞诗的兴起和新边塞诗派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首先,西部涌现出了一批人数众多、实力雄厚、阵容可观、长期生活在西部和共同以描写西部生活为题材的诗人群。其中出现了不少在全国诗坛有影响的优秀诗人。如杨牧、周涛、章德益、昌耀、林梁、杨树、李老乡、马丽化、李瑜、张子选等。他们大多数是生活在古老、荒凉、辽远、神奇而又富饶的西部土地上的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感受。他们所依赖的生活是丰富的、独特的。这片土地养育了他们,给予了他们诗人的特殊的气质和才智,正如他们在自己诗中所描写的那样:
它打破了我的外壳,然后/象一个最爱护我的亲人那样,/和着血和泪水,用它黑色的泥土,/深深地重新塑造了一个我……它把无与伦比的色彩给了我,/它把坦荡舒畅的旋律给了我,/它把古老的传说也给了我,/它把草原的气质也给了我。
——周涛:《伊犁河》
土地哟!/我只比你多了一首急切的诗,/但这诗,也是你孕育的胚胎。/土地存在我存在。
——杨牧:《我从土地来》
我在大漠的浊黄里,/在落日的血光中,/在蓝天的澄澈间,/积累着色彩。//我在风沙的怒啸里,/在流沙的尖嘶中,/在足音的回响间,/积累着词汇。//我在炊烟的袅娜里,/在小路的曲折中,/在地平线的一抹间,/积累着线条。//我在篝火的庄严中,/在日出的神圣里,/在大漠的无穷间,/积累着素材。/瀚海呵,我永恒的画页,/沙山呵,我们诗情的所在。/愿我能画完自己全部的生命,/原我能写尽自己全部的热血。
——章德益:《我的画与诗》生活在西部这片土地上的诗人,他们本身就是名符其实的开拓者。他们看到的并不全是荒凉和悲伤、贫困和落后,他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那种大气磅礴式的进取和开拓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心理意识,因而他们深深爱上了这块广袤而偏远的土地,以新的视角对整个历史、民族、现实、人生的独特观察来抒写自己心中的激情。“为拉起一块大陆的重载,聚拢一个民族的力量,扶起一代人心的憧憬,绷紧一个时代的信念”(章德益:《我自豪,我是开荒者的子孙》),而努力开掘我们今天时代的主题而引亢高歌。周涛以自豪和骄傲的激昂声音高歌:“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来写伊犁河,/相信吧,我也决不会胆怯,/因为伊犁河是我的河。”(《伊犁河》)“我的灵魂属于这边远的角落/全世界最崇高的山峰属于我/全中国最浩瀚的大漠属于我。”(《我的位置在这个边远的角落》)章德益庄严宣告:“我自豪,我是开荒者的子孙。”杨牧大声疾呼:“人类的希望永远系在拓荒者的肩上。”昌耀情深意切地立誓:“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这块土地的家族,被自己的土地所造化。”(《西北角》)李瑜笔下的西部:“天空是静寂的,大漠是静寂的,只有坚韧的拓荒者的心在静寂中有节奏的跳动。”(《飘浮过来,晶莹的冰山》)这里,我们看到新边塞诗人他们大都有共同的生活感受、崇高的信念和对人生的追求,这正是新边塞诗能激起读者强烈共鸣、撼人心弦的重要因素,也是新边塞诗诗风粗犷、韵味迥异、笔力不凡的关键所在。
其次,新边塞诗的兴起与天时、地理、人和有关。
所谓天时,是指有利于适合新边塞诗发展的气氛条件。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完成了文艺工作者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文艺工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实行了对文艺工作的稳定、正确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局面。”[1]宽舒和谐的气氛,艺术自由的气氛,使新边塞诗人的创作人性和艺术特色得到可喜的发挥,有利于新边塞诗派的形成和发展。新边塞诗人长期的开发生活,多年的默察与潜思“已在无形中,沉默里长成茂草修林了,只待一星之火,便足以击成辉煌的火底大观”(梁宗岱语)。这“一星之火”就是党的文艺政策的正确,就是宽舒和谐、艺术自由的气氛。二是进入80年代,在我们民族和历史经过了苦难的思想道路之后,新诗获得了艺术思考的权利。在一大批蕴含着新鲜的艺术气息和深刻的思想内容的朦胧诗冲击之下,新边塞诗在自身挖掘的基础上,也向诗歌的崇高的理想境界迈开毫不示弱的脚步。他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反映西部边地生活的表象,素描速写式地去描写生活场景,以及对西部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作单纯的牧歌式的吟唱,而是在创作中严肃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抒发开拓者恢宏的理想,表现人的尊严,开掘和阐发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内容。在艺术上他们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囿于传统的手法和格式,而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大胆借鉴,不断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这就给新边塞诗创造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促进了新边塞诗的发展和新边塞诗派的形成。
所谓地利,是指地域上的有利形势。地域特色是构成新边塞诗美学特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域辽阔、粗犷,地质和地貌复杂,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丝路文化,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开发者奔驰耕耘、建功立业之地。生活在这片奇异土地上的诗人在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容易找到特殊的感应对象(大漠、戈壁、冰山、雪峰、枯林、黄沙、风暴、长河、落日、草原、骆驼、奔马、城碟、古战场、雪崩、辽远的地平线……)。他们在这些感应对象面前,往往能生发出一种壮美的豪情、旷达的意志和无穷的力量。这种特殊的感应对象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是极难找到的。新边塞诗中的地域特色,应体现西部人对环境独特的感应和行为特点;新边塞诗所抒发和描写西部人的思想意识、民族性格、气质心理应打上地域特色的鲜明印记。从新边塞诗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主体与客体、诗人与环境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达到了物我同一的艺术境界。正如诗论家谢冕所说:“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物我两方的彼此认同,从而有意地模糊主客体的明确界线。西部诗的作者大体都具有这种鲜明的意识。他们总是置身于西部特有的氛围中,向着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推进。”[2]这正是新边塞诗(亦称西部诗)地域特色的精髓所在。杨牧讲:“我的生活放牧着我,我也放牧着我的生活”。(《野玫瑰·扉页题记》)周涛讲:“不仅是我们在挖掘着生活……生活同时也在以它特殊的诱因挖掘着我们每个蕴含在内心的矿藏。”(《马蹄耕耘的历史·历史与诗人》)生活“打碎了我的外壳”,然后它又“象一个最爱护我的亲人那样和着血和泪水,用它黑色的泥土,深沉地重新塑造了一个我”(《伊犁河》)。章德益讲:“大漠有了几分象我,我也有几分与大漠相象。我象大漠的:雄浑、开阔、旷达;大漠象我:俊逸、热烈、浪漫。”(《我与大漠的形象》)从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养育了新边塞诗人,新边塞诗的地域特色体现了中国西部人的本质力量——觉醒意识、忧患意识、开拓精神、坚韧的意志,这正是新边塞诗的阳刚之美、动态之美、悲壮之美、力量之美的客观因素。特别是新疆地处亚洲中部的内陆地区,一方面它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同时它又是连结相邻强国形成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而丝绸之路又是东西方文明传播的纽带。古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化,中国的中原文化都通过这条纽带相互融合和交流;世界上的几大宗教:拜火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曾经略此地。同时由于丝绸之路的作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频繁,有许多民族文化就是多种文化混融合成的变种之花。这种无所不包的博大正显示了中华民族博大、宏深的民族性,它也影响着西部文学和新边塞诗的兴起和发展。所以,我们说西部本土的地域特征往往是影响这一地域文学作品的气质和格调,因为它是由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所谓人和,是指人民的欢心。古人云:“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话颇有道理。特别是当时中国诗坛,曾一度阴柔之风盛行,阳刚之气不足,在新诗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新边塞诗以其粗犷、豪放、刚健、沉雄之风和凝重的内容而跃进诗坛,确实令人振奋,使人面目一新。所以,新边塞诗一出现,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和欢迎,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重视和承认。特别是在新边塞诗刚起步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和《阳关》两家刊 物发了谢冕、余开伟、刘湛秋、高戈、郑兴富、杨牧、孙克恒等人11篇 文章,给予大力支持,对新边塞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继《上海文学》、《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萌芽》、《当代》和西北五省的文学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新边塞诗和有关评论文章,可谓云蒸霞蔚,蔚为大观。
第三,新边塞诗的兴起,是西部诗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进行了坚持不懈、卓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出版了大量诗集,如杨牧出版了《绿色的星》、《复活的海》、《野玫瑰》、《塔格莱丽赛》、《夕阳和我》、《山杜鹃》、《边魂》、《雄风》,周涛出版了《八月的果园》、《牧人集》、《云游》、《神山》、《野马群》、《鹰笛》、《幻想家的病历》,章德益出版了《绿色的塔里木》、《天漠和我》、《西部的太阳》、《生命》、《黑色戈壁石》。其中杨牧的《复活的海》、周涛的《神山》两部诗集同时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1983-1984)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杨牧的《野玫瑰》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1985年正式藏书;杨牧的《我是青年》获1982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章德益1990年荣获“庄重文文学奖”。二是他们的作品在中国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读者中享有盛誉,许多著名评论家、诗人,如顾骧、谢冕、公刘、绿原、周良沛、周政保、张同吾、唐祈、杨匡满、谢昌余、燎原、张志忠等,纷纷为之撰写评论和专著。他们一致认为:“新边塞诗的产生,是80年代变革现实的产物,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的精神风貌的感情结晶”(周政保:《新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新边塞诗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创造性地把中国当代人的思考溶解于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之中”(谢冕:《崭新的地平线》);新边塞诗“不仅是属于中国西部的,它也是属于全民族的,它不仅在当代诗坛上树起大纛,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中可为翘楚。新边塞诗,体现着我们正在腾飞跃起的中华民族之魂,使我们看到一个进取民族的伟大形象”(顾骧:《开一代诗风》);“这几位诗人在诗篇中所表现的粗豪、沉郁、勇敢、温柔和坚决的性格,作为我国民族伟大性格的反映,实在是值得诗歌界认真借鉴的”(绿原:《周末诗话》)。给予了新边塞诗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新边塞诗派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卓然崛起,确实是一个艺术世界的奇观,它不仅以崇高、深邃的思想力量和深沉的历史感、时代感、高扬的民族精神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而且以其粗犷、豪宕、强悍、雄奇、刚健、深沉、悲壮的艺术风格丰富了当代人的审美空间,开了一代诗风。正如著名诗人昌耀所说:“西部诗属于新的气质、新的壮举、新的审美效果,因而具有可抗板结、可抗封闭、可抗凝固的穿透力。”[3]
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氛围,以及新边塞诗人共同的人生经历和顽强执着的艺术追求、深沉多思的心理形态,形成了他们大体相近的艺术气质(风格)、审美理想和创作原则。
在创作方法上,他们开宗明义地宣称“信奉现实主义”,寻找“一条在现实主义的土地上,既能连接着民族传统又有某些现代手法,真正属于现代中国读者的路”,并希望“在现实主义的砧木上嫁接着一点别的东西”。这个“别的东西”,就是要有一点理想色彩。所以杨牧的现实主义,是带有理想色彩的现实主义,是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现实主义。他的目光永远注视着正在腾飞、正在前进的现实生活。这样,他反映的现实生活,就有他所说的“时代感”、“历史感”、“分量感”,有“实在的内涵”。周涛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是具有宏伟深沉的历史感。如果不能成为整个历史的儿子,就算不得真正的诗人。”他又说:“我渴望能从我生活的这块异常奇特的土地上,挖掘出粗犷、顽强的人生。”(《马蹄耕耘的历史·历史与诗人》)昌耀认为“西部诗人视自己为西部时代的孪生子。”他视“西部诗为时代潮流、时代审美心理、开放意识的派生物,是西部中国时代精神的辐射。西部诗,只能首先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西部,或被这一时代精神照射的西部诗。”(《西部诗人与西部诗》)他们都强调诗歌创作不能脱离诗人所处的时代精神,只有这样诗歌才会有“实在的内涵”,诗人才会成为“真正的诗人”。
从诗的审美角度,他们主张“高尚,应该是诗的灵魂。健美,应该是诗的肌体。信念,应该是诗的血素。进取,应该是诗的踪迹”(杨牧:《痛弃》);诗人应该探求着“生活的美,精神的美,心灵的美”(章德益:《天山的千泉万瀑》);新边塞诗应该倾向于“力量之美,速度之美,动态之美”(周涛:《从沙漠里拾起的传说》)。他们不喜欢“人比黄花瘦”的悲切,不喜欢“病态和静态的美”。章德益在《地平线》一诗中说:“不,悲凉与苦涩,不是我的地平线,只有希望与开拓,才是我的地平线。”杨牧在《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一诗中说:“准噶尔是旷达的。他们几乎每天都看到地平线——那是希望和美升起的地方。”周涛在《从沙漠里拾起的传说》一诗的序中说:“正如我从小就酷爱画马一样,我力求我们的诗能达到马那样完美的境界;那种体魄匀称足堪入画的雄健,那种长鬃披散无拘无束的潇洒,那种奔路时充满节奏的豪放,那种嘶鸣时常带给人们悲壮苍茫之感。”他们在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情感等方面不约而同,不谋而合。
新边塞诗人长期生活在西部这块异常奇特的土地上,丰富的自然景观和自然环境,多彩的边地风俗,丰富的民族生活,大致相似的生活经历,使他们通过创作实践,逐渐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文学主张,美学理想和创作追求。他们在创作中已经不满足于象五、六十年代诗人那样,仅仅只停留在描写边地生活的表象,浮浅地捕捉普通的生活场景和镜头,以及简单牧歌式的歌唱。在创作活动中,他们有意识地以西部自然景观的历史和现实为广阔的背景,努力开掘我们时代的主题,抒发开拓者的美好理想和高尚情操,探索真正意义的人生,表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开拓和阐述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和历史内容,有意识地形成以粗犷豪放、昂扬雄健、苍凉悲壮的阳刚之美而又充满浓厚的边地气息和民族风采的新边塞诗和新边塞诗派。
没有共性,不足以形成流派;没有个性,也出现不了满枝斗艳,繁声竞响的生动艺术局面,新边塞诗派之所以能卓然崛起,赢得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是因为新边塞诗人各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独特的观察社会生活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
注释:
[1]《文艺报》评论员:《创作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1986年2月6日。
[2]谢冕:《崭新的地平线——论中国西部诗歌》,《中国西部文学》,1986年第1期。
[3]昌耀:《西部诗人与西部诗》,《阳关》,198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