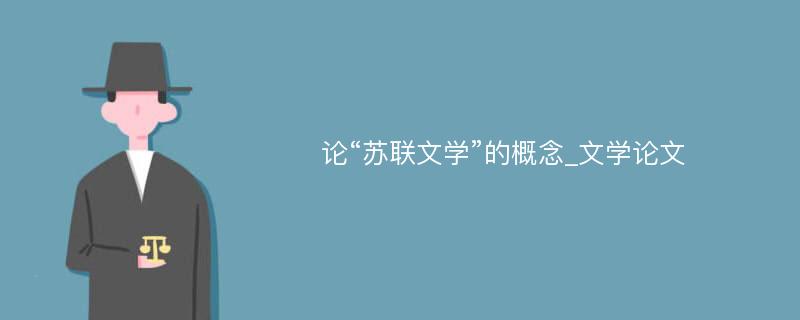
关于“苏联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概念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贾华峰 河南大学
不同年代的被禁作品得到公认,俄罗斯国外文学获得合法地位,未见天日的手稿,特别是纪实文学作品、回忆录、日记、书信大量发表,这一切都使我们应对二十世纪祖国文学史的概念不断进行重大修正,破除种种刻板的论调和模式。
起初,有人试图把回归的作品摆在次要地位,使其成为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主要经典文学大师”或“纵队辅导员们”创作的陪衬。然而,情况表明,形势似乎不久就翻转过来,“纵队辅导员们”的作品不仅被排挤,而且对它们能否有权代表祖国文学也愈加怀疑。于是,有人开始匆忙地“追悼苏联文学”了。
维·叶罗菲耶夫①文章的标题就是这样。据《文学报》预测,这篇文章会引起激烈地争论。确实有过争论,但很快就平息了,变成了怨恨或肯定,显而易见的事实,即1917年以后出现了与半官方文学的劣制品相对立的作品。
目前大量出版的不为国内读者所了解的作品、随笔和评论文章证明,关于“苏联文学”的问题早就有人深思熟虑了。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作家的命运》(1946年)一书反映了一种观点:“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没有任何‘无产阶级文学’,有的只是这边的或那边的俄罗斯文学,一边是言论自由的幸福环境下的文学,另一边是书报检查制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强求一律”②。
别林科夫未完成的谈索尔仁尼琴创作的论文表达出另一种看法:“俄语中的文学有两类,苏联时期的文学和苏联文学”③。我认为,别林科夫的看法更接近真实情况,虽然他对苏联文学的谩骂攻击(“革拉特柯夫和潘菲洛夫是祖国艺术的墓石”等),与其说澄清问题,不如说把问题简单化。
重要的是指出,“苏联文学”这一术语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文章中出现的。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流行的是其它概念,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或者广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的著作,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苏联的”这一修饰语只出现一次,作者写到必须创作苏联的喜剧,即揭露新生活中出现的丑恶现象的作品,苏联生活中的喜剧。
沃龙斯基是最早使“苏联文学”这一概念通用的人们中的一个。这位评论家和《红色处女地》的编辑在1922年《真理报》上提到新出现的名字和作品时,这样评述这一过程的特点:“大体上这就是苏联文学,侨民和最后的文学‘巨擘们’都敌视的文学”。④
从以上所述看出,这里是从政治方面谈的。评论家使用新的术语还有一个目的:避免把语言艺术家们划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使所谓的“同路人”,即使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拉普派污辱的、而沃龙斯基主要指望的艺术家们取得合法地位。
沃龙斯基的理论和批评文章表现了美学上的敏感性。他同拉普派和列夫派的庸人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时,敢于为空前未有的新文学的思辩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为三十年代前半期出现的“苏联文学”概念的演变作了准备。
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1934年)上,日丹诺夫发言时肯定地说:“我们的文学是所有民族和国家中最年青的文学。它同时是最有思想性、最进步和最革命的文学。”⑤
托洛茨基还在十余年前就吹毛求疵地和细心地寻找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结果只在杰米扬·别德内和别泽缅斯基的作品里找到。按托洛茨基的说法,别泽缅斯基是比马雅可夫斯基更有前途的人物,因为这位共青团员诗人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艺术反映比较固定……他不是以成熟的诗人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在精神上诞生于共产主义中。”⑥还在不久前,托洛茨基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未来,现在却以命令式的语气断言,这种“纯而又纯”的文学已经形成,它是与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相对立的。
骤变发生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时,对普拉东诺夫进行了猛烈抨击,结果使他许多年不能从事文学活动;重又禁止出版布尔加科夫的作品;禁止上演埃德曼的剧本《自杀者》;对扎米亚京和皮利尼亚克展开规模空前的迫害运动,因为他们在国外发表作品。如果说以前这种狂暴的批评是来自拉普派的话,那么现在所有报刊都参加了对作家们的辱骂。根据上级命令改造整个文艺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其结果就是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
这种时代骤变感反映在福尔什的《发疯的轮船》(1930年)一书,书中写了20年代传奇的艺术宫及其成员,以及文艺的状况:“在‘发疯的轮船’中,俄罗斯最近时期的文学作品被历史遗忘,而且不只是这一时期,还有整个古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更确切地说,为了要用苏联最迅速地替代俄罗斯,就把昔日还不过时的形式全都废除了。”⑦
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文学的定义成为日常通用的概念,并用于中小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因此,当开始艰难地重新评价时,一切都变成对斯大林——日丹诺夫的专横进行批评,而苏联文学本身被当成光天化日下行将消失的游戏。
然而,应该谈到创立对国家有益的文学时独一无二的实验⑧。有人认为,这种文学的创立与高尔基的《母亲》有关,更确切地说,与列宁对该作品的评价有关。众所周知,高尔基同列宁谈起这部作品时回忆说:“我说,我匆忙地写完了这本书。列宁肯定地点了点头。我自己对列宁点头肯定的解释是:我赶写出来,这很好,书很需要,许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而现在读《母亲》对他们很有好处。”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列宁特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政治实用功能。⑨这种对待创作的态度具有悠久的传统,源于柏拉图的论文《国家》。那些“制造虚幻、而不是真正的存在”的诗人们,注定要被逐出这个理想国的。只有那些其作品能带来益处,比如能促进尚武教育的诗人们才能得到公认。
沙法列维奇在其论文《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中指出,柏拉图主要注意的是能够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艺术。因此,艺术应该受到经常地监督:“首先,我们也许应该监督神话的创作者们,如果他们的作品好,我们就允许其存在,如果不好就予以否决”。他认为赫西奥德、荷马和其他诗人们讲述的神话不好:“难道我们能够允许孩子们听到和接受随便什么神话吗?他们不知是什么人杜撰的,而且大部分同我们认为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应该具有的见解相对立”。
根据柏拉图的思想,应该禁止一切对神灵产生谬误印象的神话,以及关于神灵的残酷行径、他们之间的纷争和离奇爱情的神话,应该取消谈及关于地下王国和死亡的各种残酷景象,谈及恐怖和悲惨的所有作品,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会妨碍培养勇敢精神。禁止讲述不公正的命运以及正直的人们可能不幸或不正直的人们可能幸福。不允许责备上司、不许写饥饿、恐怖和死亡:“我们请求荷马和其他诗人们原谅——请他们不要生气,如果我们勾掉诸如此类的诗篇,这不是它们没有诗意,令大多数听众厌恶,正相反,它们愈富有诗意,就愈应该少听”。⑩
当代学者在分析种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指出,使他们连接起来的是,要求艺术创作有规章,服从于社会任务,共性高于个性,实行禁止和处罚制度。
1917年以后所进行的把乌托邦思想用于现实生活中这一戏剧性的实验并未避开艺术创作。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实质上是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古代哲学家对艺术提出的那些要求。
例如,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经常强调,“艺术……总是社会公务性的,历史实用性的”,它是“对群众进行艺术和社会教育的”工具,艺术家执行“艺术以外的任务”。(11)
在组织文学创作过程中,这种要求经常是以“社会订货”的形式实现的,而“社会订货”决不受列夫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局限。这个组织正是把“社会订货”这一思想摆在自己美学纲领的首位。
有作家集体写的、刊登在高尔基提出的《工厂史》丛书上的《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史》(莫斯科1934年)一书,就是“社会订货”作品的一个例子。索尔仁尼琴看到了这本书,而且似乎在《古拉格群岛》中把它重写一遍。对比两种叙述,使我们更清楚苏联作家和俄罗斯作家之间的区别。
苏联作家通常是遵照来自上级的思想行事的。参观过该运河的作家们的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是千篇一律的:由于强制而有益的劳动,昨天的罪犯,无论是“工程师——破坏分子”,还是刑事犯,都得到了改造,成为新社会享有同等权利的成员。
虽然所有作家的个性各不相同(参观的作家120人,其中36人是本书的作者),但其中没有一个人敢于探察一下“思想背后”,更不用说怀疑其口号。即使有了这种愿望,也马上打消了。
这一点可从半个世纪后阿夫杰延柯所写的回忆录《隔离》中得到证实。当时“被提拔的”年青作家、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我爱》的作者参加了有卡达耶夫、伊万诺夫、托尔斯泰、亚先斯基、泽林斯基、什克洛夫斯基、左谬柯等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们乘坐林肯牌敞篷汽车走遍莫斯科、列宁格勒、彼得戈夫,尝尽山珍海味(“这是在饥饿年代”,阿夫杰延柯指出)。照顾他们的是一个负责的肃反工作人员、白海一书编辑委员会的未来成员菲林,他经常同高尔基和阿韦尔巴赫在一起。
怎么能看清运河上实际上发生的事呢?根据阿夫杰延柯的证明,确实有过几次“露馅”的情况。从国外回来不久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向菲林提出了许多问题:设计中是否有错误?运河工程花了多少钱?依靠什么得以减低运河的造价?是无偿劳动吗?正如《隔离》的作者所说的,听到这些问题后,菲林开始回避好寻根究底的公爵,他用公爵长期居住国外来解释公爵提出的令人尴尬的问题。
白俄罗斯人库帕拉发起愁来:
到处都是男子汉,
全是我们的老乡。
脱离故乡的土地,
被钉在陌生的地方。
卡达耶夫开着玩笑、耍着活宝,突然问到:“修运河大军有没有死亡现象?”
“有。我们大家都是凡人。”
“为什么我们在岸上没看见一座坟墓呢?”
“因为建在这里不合适。”
性格爽朗而又好客的菲林,面带愠色走开了。
卡达耶夫沉思地望着肃反工作人员的背景,以他惯有的方式说道:
“您温顺的仆人大概说了傻话。这在我是常事,因为我是党外人士,没有修养,没有掌握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对我能要求什么呢?”(12)
俄罗斯作家不是从口号出发,不是从“辩证的方法”出发,而是根据人,根据《古拉格群岛》里提到的14岁的小男孩。他对“革命的海燕”说:“‘喂,高尔基!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你想了解真实情况吗?要讲讲吗?’高尔基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并吩咐大家,连孩子们和陪同的劳改营耳目都出去了。于是,小孩用了一个半钟头对这个又高又瘦的老人讲了一切。高尔基走出工棚时泪流满面。马车接他去别墅,劳改营主任请他吃午饭……
热爱真理的小男孩讲述了一切的一切!!!
但是,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高尔基乘船离开了。他的船刚走,小男孩就被枪毙了。”(13)
“小男孩的眼泪”使俄罗斯作家不得安宁——如果人的处境不好,任何思想,即使是最崇高的思想,都是腐朽的。拨开思想上的迷雾,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所有在运河上干活的人都是“罪犯”吗?或者他们是制度的牺牲品?被判有罪的工程师们是破坏分子吗?为什么要在参观的作家面前装模作样呢?
索尔仁尼琴的叙述辛辣和尖刻,结尾是作家1966年的运河之行。原来,伟大的、大肆宣扬的工程处于完全荒废的状态:不能行驰大船,更不要说是军舰,几乎半年处于冰冻之中。“噢,离群索居的暴君,黑夜里的狂人!”作家激动地喊到,“你在什么样的谵妄中臆造出这一切?你这该死的东西,匆匆忙忙要去哪儿?什么使你感到难过和刺痛——在这20个月里?要知道这25万人是可以活下去的。”(14)这就是对白海运河一书的判决,在这本书里“以高尔基为首的36位苏联作家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歌颂’了奴隶劳动”。(15)
法捷耶夫在创作长篇小说《黑色冶金业》时,遵循了“社会订货”的宗旨,结果在创作上遭到彻底地失败。应时剧本《别人的影子》的作者西蒙诺夫以他为榜样。关于这一点,西蒙诺夫在临终前口授的关于斯大林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在分析他所支持的书时”,西蒙诺夫回忆说,“我看到他要求作品应具有现实意义,归根结底回答以下问题:我们现在需要不需要这本书?需要还是不需要?”(16)
把苏联文学作为体现国家利益的文学思想,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情理上都是不可否定的。正象西尼亚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积极运用社会主义古典主义诗学,其主要原则是“把应当的作为现实的来写。”(17)
但是,要实施这样的原则,必须履行一系列条件,首先应该使新文学独立出来,把“异己的杂质”剔除出去。起初这涉及到国外和国内的侨民。由此就不止一次地匆忙贬低俄罗斯国外文学的作用。主要的方法是毫无根据地辱骂。列宁对柯罗连科致高尔基信中人道主义立场的评价,斯大林论高尔基《不合时宜思想》的文章,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关于罗扎诺夫、扎米亚京、吉皮乌斯的论述都属于这种情况。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迫害的是“异己分子”,是侨民们,那么到20年代末轮到了“自己人”和那些与巩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不相符合的人们。这种同异端者的斗争将进行数十年,结果形成一种“背阴文学”。它起源于《不合适宜的思想》,柯罗连科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件,并被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左琴柯、阿赫玛托娃、杜金采夫、帕斯捷尔纳克、雅申、阿勃拉莫夫、格罗斯曼、东布罗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所继承。
随着苏联文学思想的实现,另一种危险也暴露得愈来愈明显。对“功能性”的强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美学的要求放松。按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说法,“主题”、“标题”开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就为广泛传播粗制滥造的作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扎米亚京的预言应验了。他在文章《我害怕了》(1921年)中写了懂得“某一季节什么时髦和什么色调流行”的“机灵的作者们”。(18)令作家不安的是,革命后出现了一批诗人,他们把完善“公式化”的情节当作主要事情。这样的“机灵作者们”的数目逐年急剧递增。
但是,忠于国家文学原则形成的最有戏剧性的后果也出现在法捷耶夫、吉洪诺夫、费定等富有才华的大师们的创作中。通常,他们的道路从大有希望的处女作开始,显示了这些年纪还很轻的人们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们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写得充满活力,有分量,语言感染力强。他们的诗集情节生动,但他们的创作道路却以长期默默无闻而告终。
对彻底被确定下来的有益文学的原则的忠诚,常导致同艺术家创作的兴趣及信念发生戏剧性的矛盾,结果产生危险的分裂现象。法捷耶夫的命运就是这种悲剧的例子。他确信,有国家通用的文学和仅供内部使用的文学,这一切最终导致艺术语言和艺术家的使命本身毫无价值。(19)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人是许多人中的一员,他是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而对于真正的文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文学不泛泛地空讲人道,而是坚决主张关注个别人命运的独特性,他操心的是人要有名字,而不是仅有Д—503号(扎米亚京《我们》),Щ—854号(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常有这样的年代,国家利益和个人存在紧紧结合在一起,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就是这样。当时许多作家都有内在的自由感(别尔戈里茨在《二月日记》中令人吃惊地承认),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创作了伟大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也不是偶然的。正是在战争年代,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感觉到了在精神和艺术生活中正在发生变化。
1946-1948年的决议似乎使这些希望化为乌有。不过,它们更是国家文学和艺术思想开始作最后挣扎的证据。很难抓住选择批判“对象”以及使文学、电影、音乐处于无人领导局面这一残酷作法的逻辑。在这些谩骂中表现出的与其说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理由,不如说是一个走向衰老的君主的古怪念头。
不久前还无限忠实于意识形态指示的作家们也越来越有危机感。它使法捷耶夫于1956年5月13日遭到了致命的一枪。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感到越来越不顺利。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工作笔记》中写到利用“主题和标题”的拙劣作品造成的恶劣影响,他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1954年)前夕草拟致中央委员会的发言提纲中写道:“我们忘了别林斯基有这样一句话:‘在谈论作品的思想倾向前,应该解决一个问题: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吗?’按照诗人的观点,应该重新学习的不是写作,而是生活,要汲取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知识,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有价值。”
在《工作笔记》中有谈及法捷耶夫的严厉的话语。法捷耶夫“不想承认,他撒了弥天大谎,陷入了窘境,特别是他虽企图用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来挽回局面,但结果却砍倒了自己”(指的是他对《黑色冶金业》的创作)。
对我们的争辩特别有代表性和重要的是这样一段话:“过去一向是这样,而且我引以自豪的是,不出版我不能什么也不写,我要为‘自己’储存起来,为‘后代’而写。而这是舍己为公的、有战胜一切的信念的最幸福的时候。可现在不一样,至少现在是另一种情况:我认为,不能不为‘自己’而写(的确这也是非常相信自己的证明),为‘后代’储存起来,否则不得不放弃许多东西并把自己限制到极端,走到自杀的地步。”(20)
这些话是解开诗人创作命运之谜的钥匙。他不仅能够克服战后的危机情绪,而且成为数十年来对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心人物。
我认为,正是在50年代中期,建立完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文学实验接近结束。竭力使创作服从于意识形态支配的企图还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因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1958年)而引起的批判运动发生在60-70年代。最后的例子似乎是对《京地》的作者们有组织的、但软弱无力地围攻。
与此相抗衡的是,新倾向产生了并越来越强大:出现了公然以俄罗斯古典作品传统为指针的所谓“农村”散文,索尔仁尼琴在文学中的出现成为“转折点”(特瓦尔多夫斯基语)。为国外的俄罗斯文学、秘密的被禁的文学“平反”是很难的,但却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切必然使数十年来祖国文学的分裂现象得以克服,使它的个别支流汇入崭新的俄罗斯文学共同的河床里。
(译自《圣彼得堡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注释:
①维·叶罗费耶夫:《悼念苏联文学》,载《文学报》,1990年7月4日。
②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作家的命运》,载《回归》第一辑,莫斯科,1991,第348页。
③阿·别林科夫:《为什么刊登〈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载《星》杂志,1991,九期,160页。
④阿·沃罗斯基:《文学论文选》,莫斯科,1982年第286页。
⑤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1934年,速记报告,莫斯科,1990年复印,第3页。
⑥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莫斯科,1991年,第117页。
⑦福尔什:《发疯的轮船》,列宁格勒,1988年,第98页。
⑧参阅叶·达勃林柯:《国家即作者》,载《文学报》,1992年4月15日。
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莫斯科,1956年,第515页。
⑩沙法列维奇:《俄罗斯有没有未来》,莫斯科,1991年,第23-24页。
(11)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莫斯科,1991年,第134,111,112页。
(12)阿夫基延柯:《隔离》,载《旗》杂志,1989年第3期,第20-21页。
(13)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莫斯科,1991年,第二卷,第23-24页。
(14)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莫斯科,1991年,第二卷,第95页。
(15)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莫斯科,1991年,第一卷,第12页。
(16)西蒙诺夫:《通过我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人的眼光》,载《旗》杂志,1988年第4期,第61页。
(17)西尼亚夫斯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什么?》,载《隐喻》杂志或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艾尔的《罪与罚》,莫斯科,1990年,第450页。
(18)扎米亚京:《两卷选集》第二卷,莫斯科,1990年,第349页。
(19)详细参阅拉夫洛夫:《实验》终结,或《论对国家有益的文学》,载《涅瓦》杂志,1992年,第516期。
(20)特瓦尔多夫斯基:《工作笔记》(1953-1960),载《旗》杂志,1989年第7期,第149、151、145、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