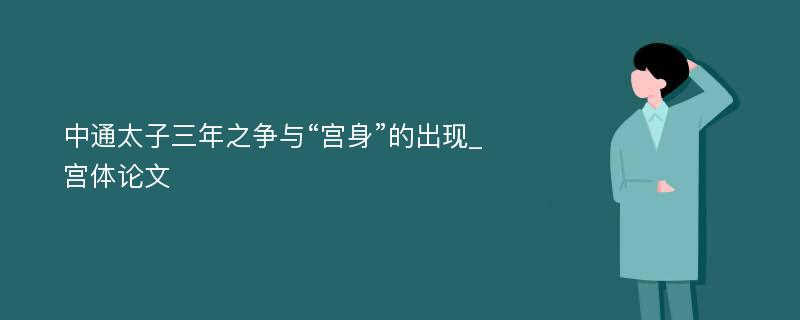
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与“宫体”登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通论文,之争论文,太子论文,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0)05-0020-05
一、萧纲回京城与萧统的紧张
普通四年(523),萧纲为雍州刺史。在雍州任上几年后,萧纲非常想从藩地回京城任职,其愿望的表达,一是直接请求朝廷,其《在州羸疾自解表》先称:“昔违紫複,曾不弱冠,今梦青蒲,逝将已立”,指自己离开京城已久;“愿归之谒,不逮宸矜,民请之书,遽降天允”,称说自己的愿望。二是以文学作品进行情感诉求,其《阻归赋》云:“观建国之皇王,选能官于前古,元帝慈而布教,岂齐圣而作辅,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汉而自通”,先述分封在外;“终知客游之阻,无解乡路之赊”,又述回乡之难。此作一般认为成于中大通元年(529)。此三年前普通七年(526)三月,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以疾累表自陈,诏许解扬州;普通七年四月,萧宏薨,扬州刺史暂缺,由孔休源代行其职(见《梁书·孔休源传》)。如果把扬州刺史暂缺与萧纲非常想从藩地回京城任职联系起来看,《在州羸疾自解表》与《阻归赋》二作就显然有萧纲诉求扬州刺史位子的意思。所谓“贵戚王公,咸望迁授”,可见当时向往此缺者非独萧纲一人,其热衷于任职扬州刺史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其热衷程度较其他人更为强烈。不久,萧纲回京城的愿望终获实现。《梁书·武帝纪》载,“二年春正月戊寅,以雍州刺史晋安王纲为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南史·梁本纪下》称中大通三年萧纲“被征入朝”。
晋安王萧纲的进京引起太子萧统的紧张与恐慌。《南史·梁本纪下》载:
普通四年,(萧纲)累迁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弈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
除了任扬州刺史外,萧纲“被征入朝”还有什么要事,史不明载,但足以表明梁武帝对萧纲心有所寄,于是萧统有所忧虑,忧虑又表现在梦上。“对弈”,即下棋;“道”,古代棋局上的格道,《楚辞·招魂》:“菎蔽象棋,有六簙些”,洪兴祖补注引《古博经》:“博法,两人相对,坐向局,局分为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扰道”,当是对奕者阻扰了自己的棋道、棋路。《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王导与其子王悦弈棋“争道”之事:
(王悦)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导甚爱之。导尝共悦弈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那得为尔邪!”
“对弈”时的“扰道”,有时可能会演化成很严重的事件,如《史记·吴王濞列传》载:
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
对晋安王萧纲的“扰道”,梦中太子萧统以怀柔处之,所谓“以班剑授之”。班剑,有纹饰的剑,为朝廷之物。汉制,朝服带剑;晋易以木,谓之班剑,取装饰灿烂之义。班剑后用作仪仗,由武士佩持,是天子以赐功臣宠臣的。但是,对自己的“以班剑授之”,萧统又有焦虑,他猜测“王还,当有此加乎”?如真“有此加”,那就是晋安王萧纲得到梁武帝的宠幸,那自然是对自己的某种威胁,起码是削弱了自己。如果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太子萧统在现实生活中的两重焦虑,其一,萧纲“被征入朝”,表明梁武帝对萧纲心有所寄,于是会有晋安王萧纲对自己的“扰道”;其二,当自己“以班剑授之”处理“扰道”,梁武帝或又会“以班剑授之”,岂不是使自己地位岌岌乎危哉!
这种焦虑是有依据的,这就是“埋鹅”事件引起的太子萧统与梁武帝的隔阂。《南史·昭明太子传》载: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
由此可见,若非徐勉之谏而梁武帝“穷究其事”的话,萧统此时或已有可能被废。宋代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曾言“(徐)勉救昭明及沈约事,有补于时”。《南史》又称“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资治通鉴》卷一五五称“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由于“埋鹅”事件,梁武帝对太子萧统有所不满,太子萧统当然有焦虑,这时又听到晋安王萧纲进京的消息,左忧虑,右猜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遂产生对自己太子地位将要不保的焦虑,那是自然不过的事。
二、萧统之死与萧纲为太子
中大通三年(531),又一件大事发生了,《南史·昭明太子传》载:
(太子萧统)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
“动股”与《诗经·豳风·七月》“斯螽动股”之意不同。这里的“动股”,当是“动”了“股”的脉气。《伤寒论·辨脉法》云:“阴阳相搏名曰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风胜则动。”即风邪过盛,则发生痉挛、动摇乃至惊恐。“动股”,即“风胜则动”,集中表现在大腿上,或是由大腿症状引起。《南朝五史辞典》解释为“大腿颤抖,谓寒冷或惊恐”。“动股”而“深诫不言”,是说萧统在封锁其患痉挛、惊恐之病的消息,如此百般遮掩耽误了治疗,导致病情加重才死亡的,如果不拖延的话可能不至于丧命。如此百般遮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里是说“恐贻帝忧”,这是其一;更重要的应该是怕自己这种痉挛、惊恐之病,会使梁武帝有所疑心,或会使梁武帝有理由下定某种决心,而影响到自己的太子地位。于是,“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之语,当为多重含义的呜咽之语。
太子萧统终于逝世,梁武帝一方面忙于为太子萧统办丧事,另一方面,册立新太子的事也提上日程。《梁书·文学·谢徵传》:
中大通元年,以父丧去职,续又丁母忧。诏起为贞威将军,还摄本任。服阕,除尚书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将出诏,唯召尚书左仆射何敬容、宣惠将军孔休源及徵三人与议。
或许就是在“将出诏”之时,梁武帝召集何敬容、孔休源及谢徵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的,《梁书·孔休源传》载,“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孔休源本是晋安王纲旧臣,又是扬州府实权人物。何敬容倒多有萧统府太子东宫任职的经历,但他是贪贿之人,《南史·何敬容传》称:
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晋魏以来旧事,且聪明识达,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职隆任重,专预机密,而拙于草隶,浅于学术,通苞苴饷馈,无贿则略不交语。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贪吝为时所嗤鄙。
足见此乃一无操守之人。谢徵,据《梁书·文学·谢徵传》载:“时年位尚轻”,则梁武帝在谋划新立太子一事时,有意避开了一些人,如萧统旧臣及可能坚持立嫡的保守臣僚。
且晋安王萧纲此年已早在京城,梁武帝亦足有天下社稷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南史·昭明太子传》载:
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又以心衔,故意在晋安王,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
不立萧统子嗣而立萧纲为太子也有麻烦,除下述“海内噂沓”及萧统的几个儿子心中很不满外,又有《南史·袁昂传》载袁昂“独表言宜立昭明长息欢为皇太子”,《陈书·周弘正传》载周弘正上奏记劝萧纲“谦让”,《南史·邵陵王传》载萧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的讥语,等。但是倒过来讲,梁武帝“以心衔”而废太子本来就是可能的;现在太子萧统自然死亡,当然比起撤换萧统改立他人要省事得多。
萧纲被立为太子后,有几件事做得极不光彩。其一,萧纲立为太子,有《谢为皇太子表》、《拜皇太子临轩竟谢表》;但是,萧纲对立为太子只有“谢”而无“让”,不合乎礼教社会的传统。《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载:
丙中,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司议侍郎周弘正,尝为晋安王主簿,乃奏记曰:“谦让道废,多历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将圣,四海归仁,是以皇上发德音,以大王为储副。意者愿闻殿下抗目夷上仁之义,执子臧大贤之节,逃玉舆而弗乘,弃万乘如脱屣,庶改浇竞之俗,以大吴国之风。古有其人,今闻其语,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使无为之化复生于遂古,让王之道不坠于来叶,岂不盛欤!”王不能从。
这段文字本自《陈书·周弘正传》。古时有所谓“三让”之风,晋安王萧纲本有此风,他并非是不懂“谦让”之礼,《梁书·简文帝纪》载“中大通元年,诏依先给鼓吹一部”,萧纲作《让鼓吹表》;中大通二年,徵为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萧纲得到最想得到的位子,他也是要作《让骠骑扬州刺史表》的;而此时此刻萧纲毫无此风,在曾任其主簿的司议侍郎周弘正“奏记”提醒下,仍“不能从”,可见其“被征入朝”与现在的被立为皇太子,是与梁武帝有着默契的,也是有自己的想法、活动的。其实,《陈书·周弘正传》所载“奏记”中已称“夏启、周诵、汉储、魏两”不能与萧纲相比,他的提醒萧纲“谦让”,也只是让让而已,但就是如此的表面文章,萧纲也不去做,又可见其“被征入朝”后的心态。萧纲提倡“立身先须谨重”(《诫当阳公大心》),而且自认为“立身行道,终始如一”(《自序》),而此时此刻对有利于消除影响的“三让”之礼,萧纲不从,梁武帝也默许,这是异乎寻常的。
其二,梁武帝对萧统“心衔”之事即“埋鹅”事件,萧纲是知道此事为“冤”的,《南史·昭明太子传》载:
后邵陵王临丹阳郡,因邈之与乡人争婢,议以为诱略之罪牒宫,简文追感太子冤,挥泪诛之。
“埋鹅”事件的起因,是鲍邈之为了个人不被宠信的私怨,而无事生非地告密,致使梁武帝与萧统有隙,萧纲明知萧统有“冤”却不予说明。
其三,萧纲立太子后所作《谢为皇太子表》显示了其为皇太子的迫不及待。《表》中萧纲先称被立太子为“事异定陶之举”,《汉书·成帝纪》载汉成帝为太子时之事:
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为嗣。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
所谓“事异定陶之举”,是说自己并不像定陶恭王凭着宠信要去顶替原来的太子。而《表》中又称被立太子为“有类胶东之册”,《汉书·外戚传》载:
景帝立齐栗姬男为太子,而王夫人男为胶东王。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栗姬日怨怒,谢长主,不许。长主欲与王夫人,王夫人许之。会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谮栗姬短。景帝尝属诸姬子,曰:“吾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心衔之而未发也。长公主日誉王夫子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耳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男为太子。”
所谓“有类胶东之册”,是说像初为胶东王的汉武帝一样,是因为原先的太子犯错误被废而自己被立为太子的,这不是对萧统的诋毁吗?
此时,大唱颂歌者也已经出现,如《南史·始兴忠武王传》附《子晔传》载,“简文入据监抚,晔献《储德颂》”。待萧纲入主东宫,撤萧统的旧人,换自己的新人,《梁书·刘杳传》称,“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整个太子的变更顺利完成,据《南史·梁本纪下》载:
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晋安王为皇太子。七月乙亥,临轩策拜。以修缮东宫,权居东府。四年九月,移还东宫。
三、萧纲入主东宫后的行动与“宫体”时代的开启
萧纲入主东宫后,雄心勃勃要做一些事情,政治上,其《答徐摛书》说:
山涛有言,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惶,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他不愿意只是“养德而已”,而是要尽到自己“监抚之务”的责任,这就是所谓“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
在学术上,《南史·许懋传》载:“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与诸儒录《长春义记》”;《隋志》经部“《论语》类”著录为一百卷。召诸儒编撰儒家书籍,这本是太子的传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曹丕“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号曰《皇览》”,据《三国志·魏书·刘劭传》载,刘劭“黄初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但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编撰《皇览》之类,是“帝初在东宫”时立下的宏愿,“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另一项工作就是开始整顿文风。其《答湘东王书》云:
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
如果萧纲不是太子,作为储副坐镇京城,批评“京师文体”这样的话,是他能够说的吗?萧统的辞世标志《文选》时代的结束;而萧纲政治权力的获得马上就表现在文学思想的更替上,即“宫体”时代的开启,《梁书·徐摛传》载:
(晋安王)王入为皇太子,(徐摛)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宫体”自春坊而天下,“宫体”强势登场,但“宫体”时代的开启并不温馨。
所谓“宫体”,就是宫中流行的文体。《梁书·简文帝纪》载梁简文帝“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隋书·经籍志四》云: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又据刘肃《大唐新语·公直》载:
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寖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萧纲的宫体诗,论者常提起的如《咏内人昼眠》,既然标明是写“内人”,那就是与倡家对立的,可说萧纲写起自己的妻或妾来,也写得如同倡家,可见宫体诗的影响之大。萧纲还写过性变态的《娈童》: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翠被含鸳色,雕床镂象牙。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袖裁连璧锦,牋织细种花。揽袴轻红出,回头双鬓斜。嬾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
宋人谢惠连有“娈童”这方面的爱好,《玉台新咏》又录有萧纲《戏作谢惠连体十三韵》,此《娈童》之作,是写自己的想法做法呢,还是依谢惠连而写?如果我们把“宫体”定位为叙写女性及男女交往,那么应该说,在萧纲的大力推动下,“宫体”不仅仅表现在诗歌领域里,而且泛滥、蔓延到其他各种文体中。如赋,萧纲、萧绎、徐陵、庾信都有《鸳鸯赋》,构成系列,萧纲写道:
朝飞绿岸,夕归丹屿。顾落日而俱吟,追清风而双举。时排荇带,乍拂菱华。始临涯而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丽自如神,宜羞宜笑复宜颦。既是金闺新入宠,复是兰房得意人。见兹禽之栖宿,想君意之相亲。
全写女性,似乎是寄托,实际应该是物与人的对举,以赋鸳鸯而写人。又如连珠体的写女性,有吴均《连珠》“盖闻艳丽居身,而以娥媚入妒”云云,虽然是“喻”,叙写女性是实实在在的;后来又有题目上标明“艳体连珠”之类,如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则“假喻以达其旨”的“喻”与“旨”全是关乎女性了。还有表、书、启、序、铭等文体,其中叙写女性的文字,香艳绮丽,很像宫体诗的骈文化表述,如江总《为陈六宫谢表》、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庾肩吾《谢东宫赍内人春衣启》、徐陵《玉台新咏序》、萧纲《行雨山铭》等。下面仅以萧纲《行雨山铭》为例,其铭云:
岩畔途远,阿曲路深;犹云息驭,尚且抽琴。兹峰独擅,钦崎千变;却绕画房,前临宝殿。玉岫开华,紫水回斜;溪间聚叶,涧裹萦沙。月映成水,人来当花;藤结如帷,碛起成基。芸香馥迳,石镜临墀。
本来是何等严肃的文体,在这里竞全是吟咏男女交往。
“宫体”风气在各种文体中蔓延开来,这就是所谓“宫体”时代,这无疑是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在日后的影响所致。
[收稿日期]2009-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