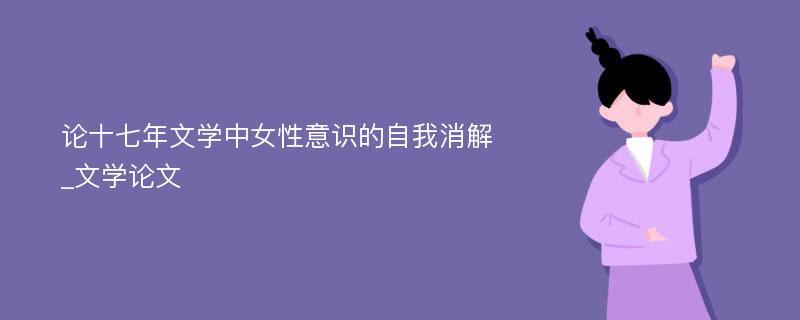
试论十七年文学女性意识的自我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意识论文,自我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十七年文学的女性形象塑造,从表面上看,她们已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努力反拔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异常自我的女性形象。实质上,她们仍没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男性目光的观照之下,她们或成为完全泯灭了女性意识的“铁女人”,或成为赤裸裸的性符号,二者不约而同的成为作家们适应时代的某种表意策略,作家们在这种“表意”之中是以牺牲自己的艺术个性为代价的。在女性主义文学已成浩然之势的今天,回头去反顾“历史”,仍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时代,“十七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研究的话题。“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已成为评价十七年文学的一个基本定位标准。在政治强光的笼罩之下,人物形象的塑造被纳入到一个共同的主导意识状态之中:好人与坏人的区分成为人物塑造时首先要面对的选择,在这种截然对立的选择之中,人的许许多多的自然性征大多被过滤掉了。无论男人、女人,共同的本质压倒了个性的挖掘与表现。本文试图从十七年文学中有关女性塑造这一问题,阐述十七年文学创作过程中文学本性的迷失,从而对那个特定的文学时期加以重新的描述。
一
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永恒的关系。在渊源流长的文学创作中,女性一直承担着重要的文学角色。在许多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都极尽描写之能事,充分展示女人作为女人的性别特征及性意识。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作家们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区别于古典的,现代的女性形象,她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之上,呼风唤雨,淋漓尽致的展现女人的“雄姿”。如果客观的对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加以描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十七年文学给当时读者的震撼,不仅在于它塑造了梁生宝、周大勇、许云峰、朱老忠这样具有崇高意味的男人,也在于它为当代读者贡献了李双双(李准《李双双小传》)、新媳妇(茹志鹃《百合花》)、卜翠莲(周立波《山那面人家》)、肖淑英(李准《耕耘记》)等崭新的女性形象。这一系女性形象,完全摆脱了以往女性满身粉黛气的娇柔形象,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但我们又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塑造(其他类型的人物塑造亦如此)明显的存在着共性大于个性的缺憾,作为单个人来考察,形象塑造得“生龙活虎”,作为系列考察,则给人似曾相识的雷同之感。作品中作为主要人物而出现的女性,她们表现出了共同的精神气质,即,革命的本质特征掩盖了女性的自然性征。洗尽铅华后的女人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之上呼风唤雨,极力弱化自己的“女儿性”,从而获得与时代协调一致的精神色调。康濯曾有一段话评论胡万春的小说《“一点红”在高空中》的主人公“一点红”,“就在这火热宽广的熔炉的高空,有个外号‘一点红’的娇惯的姑娘阿珍,经受了锤炼和正在成长;就是说,这位‘一点红’正在红光普照的高空里,消失于一片金红的人海,熔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集体之中。”(重点号为作者所加,选自《工人短篇小说选》的序言《为工人创作而歌》,1964年工人出版社出版。)“消失于一片金红的人海,熔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集体之中”,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的至高境界,表面上看,作家康濯评论的是“一点红”在高空中作业时的景观,实际上概括了十七年文学人物性格塑造上的一个普遍的特征:泯灭个性,努力使自己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无可争议。女人,在十七年文学作品中是被异化了的,无论是李双双,管家嫂子(建才《管家嫂子》),还是肖淑云,她们身上女人的自然意识处于沉睡状态,儿女情长,夫妻之爱,与她们是不屑一顾的。“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恩格斯《路德维熙·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人为的去回避这个问题,从而出现了一大批非凡人形象。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塑造,比较执著于自我的情感世界的自白,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私小说。而十七年的作家在努力的反拔这些,描写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在这一反拔中却完全走向一种迷失,即:女性意识的全面丧失。“咋看去活象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李金山《锻炼》)”,走路“登登登,说话瓮声瓮气(建才《管家嫂子》)”,“高喉咙大嗓子(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这是作家们塑造女性形象时常用的描写,这些描写都在强化女人的男性特征。在十七年中,作家们为适应统一的政治标准和艺术规范,是以泯灭自己的艺术个性为代价的。此种观念反映到作品中,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塑造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特征靠拢,决不能旁逸斜出,那么作为女性形象所固有的那种气质,那种独特的感情世界完全淹没于时代的“红”洪之中。
“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兽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类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人性或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在基督教里才找得到。”(恩格斯《反杜林论》)而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由于各种非文学的评价标准把没有人的自然本性的“英雄形象”推到一种极致,显然是人为的拼凑。而女性形象的塑造(尤其是正面女性的塑造,这种非人道的情况更为严重。
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茹志鹃与周立波的创作显得异乎寻常,在这两位作家笔下,塑造了几位很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这原本天经地义的描写,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却成为“例外”。茹志鹃无论是在《百合花》中塑造的娇羞的新媳妇,还是《春暖时节》中追求女性人格独立的静兰都给人留下温馨美好的回忆。新媳妇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真、善、美的象征。如果说《百合花》虽写于十七年,却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积淀,所以较少时代对作品、人物影响的话,那么《春暖时节》完全是十七年应运而生的,这篇作品以五八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作为背景的,但在作品中茹志鹃没有象其他作家那样把浓烈、奔放作为作品的风格,也没有把女性塑造成锋芒毕现的“铁女人”形象。主人公静兰也是一个追求女性价值实现及人格独立的形象,但作者并没有让她去刻意追求与男子行为特征的相似性。茹志鹃在描写这个人物时,注重女人与男人精神的平等,在这种精神平等的追求中,静兰并没有牺牲自己的女性意识,既与男人在精神上站在了同一地平线上,又保留了女性特征,因而,这个形象在十七年中不能不说是独特的,即使到今天这个形象对女性文学创作仍具有借鉴意义。同时期的周立波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很独特,十七年文学大多数作家似乎都在用一个“忙”字来概括女人的全部生活,而作为女人对生活的其它体味、感觉都因此而被掩盖。周立波曾受到批判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中对女性的生活做了别外一番的描写,“青春、健康、无挂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翡青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工分,以及这迷离的月色,清淡的花香,朦胧的或是确实的爱情的感觉,无一不是她们快乐的源泉。”在这里,女性恢复了她对生活全部的感觉、青春、健康、劳动、田野、月色、花香、爱情,如诗如画的生活,无忧无虑的青春少女,这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花木兰驰骋疆场的雄姿固然可敬,而“对镜贴花黄”的木兰更显女性的本真。《山那面人家》表现的即是女人的本真,生活的本真。周立波在铺天盖地的浓烈、火爆之中,吹出一只清凉,悠徐的曲子,显得格外的清新可人。
二
相对于正面女性形象的塑造而言,十七年文学中,作为反面角色或落后人物出现的女性反倒塑造的更自由,舒展一些。“在刻划素芳、李翠娥(柳青《创业史》)、张桂贞(周立波《山乡巨变》、辛俊地《管桦《辛俊地》)、“惹不起”、“能不够”(赵树理《三里湾》)……等人物时,作者似乎少了许多禁忌,只要符合当时所谓“坏”的标准就成,而这个“坏”的标准是相对于“革命”同志的正统而言的。那么,革命同志所绝对排斥的追求享受、欲望、快乐——做为女人所需求的一切世俗的快乐,都可以淋漓尽致的在“坏女人”身上表现出来。在此,我们以《创业史》中几个年轻女性为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创业史》中写了几个着墨较多的女性:徐改霞、梁秀兰、素芳、李翠娥。在整个十七年文学中,改霞是一个卓然不群的女性形象;聪明、美丽、多情,又拥有知识,她代表了作者一种潜在的审美理想。作品细致的描绘了她处于恋爱时期微妙、复杂的感情。改霞不同于秀兰,秀兰身上更多具备的是那个时代文学中进步的女性所共同拥有的性格特征:强壮、勤劳、朴实,为社会、为亲人,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意识,但由于缺乏个性,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很一般。改霞虽然很独特,但作者没有让生宝选择她,而是选择了一位更适合当时读者口味的“革命同志”做为生宝的伴侣(《创业史》第二部有所描写)。素芳在《创业史》中塑造的最令人揪心。她是那个充满着污垢的文化时代的牺牲品,素芳其实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女性,但她没有一个苦大仇深的出身,反而有那样一个烂脏的父母,所以作者把她作为被批评,被教育的对象来刻划的。这样就有机会展示她作为“坏女人”的方方面面:不忠实于自己愚笨的男人栓栓,渴望着年轻、向上,充满青春活力的邻居家小伙子梁生宝。与姚士杰的非正常关系恢复了素芳压抑过久的性意识,“她感谢堂姑父给她的温存,使她的生活有了乐趣”。也许这是一个健全女人最基本的欲望,但在十七年文学中,只属于“坏”女人。素芳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公公的冥顽不化,瞎眼婆婆的不够精明,丈夫的愚笨,不谙世情)本能的渴望挣脱,这种挣脱表现在一个没有文化,没有任何地位的女人身上自然的异化为对男人的渴望。作者柳青是怎样叙述素芳的这种行为的呢?“当一个女人还没有阶级觉悟,还没有自觉到劳动最崇高的时候,她能从什么旁的角度看人生呢?”作者把素芳的这种“堕落”归结为她所隶属的阶级,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说,一个有了阶级觉悟,热爱劳动的女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性意识了。这恰好是我前文所论述的十七年文学女性塑造上存在着的问题,柳青虽然没有在《创业史》中没有去着重刻划一个相当有“时代感”的女人,但他却用素芳这样的女性去反证他的作品相当强烈的时代性。而在作品中出现的另外两个年轻女人形象是作为“性符号”而出现的,李翠娥倚门卖笑,专司勾引男人之职;在作品中只提到一次的姚士杰的三妹子是这样出场的,“当姚士杰的三妹子,用胖奶头碰高增福肩膀的时候,他只感到全身针刺一般的不舒服”。她们只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因为她们一个是兵痞白占魁的女人,一个是富农姚士杰的妹妹。在《创业史》中,“三妹子”没有名子,姚士杰的三妹子,姚士杰这三个字无疑在她脸上划上了记号,所以她只能是“坏”女人。在这里,女人们的“坏”无一例外的成为男人的反衬,素芳的卖弄风情衬托梁生宝的正直无私,三妹子的放荡衬托出贫农高增福的嫉恶如仇,政治立场坚定。对女性的这种艺术安排,虽然作者强调了她们都是“坏”女人,强调了她们所隶属的阶级,其实是作者还没有走出中国传统文化把女人放在男性目光的观照之下这样一个樊篱之中。
“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莫洛亚在给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评传里说的这段话,借来评价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系列问题是颇为恰当的,在女性形象塑造上也同样如此,长期被人们所漠视的形象,将重新引起读者的注意。
在现代文学史上,以卢隐、冯沅君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由于过分沉溺于自我情感的圈子,而创作了大批的“私小说”。十七年的作家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冲出了自我的小天地,看到了社会的阔大,但又过分强调女人的社会性而牺牲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强调共性而失去个性,这一系的偏颇只有到了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才得到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