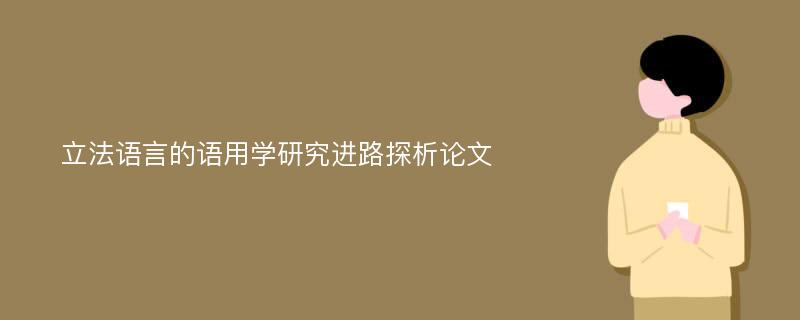
立法语言的语用学研究进路探析
李 晓 辉
(贵州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贵阳 550004)
摘 要: 我国当前立法语言研究的进路主要是以语言哲学中的语义学为依归,而忽略了语言哲学向语用学转向且在推进人类智识上所取得的丰厚成果。实际上,语用学下的立法语言概念更接近立法行为和过程的本质。在语用学进路下重新理解立法语言,自然会将论证概念引入立法理论与实践中,从而开启深化立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 立法语言;语言哲学;语义学;语用学;立法研究
立法与语言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从立法活动的开展到立法文本的生成都需要借助口头或书面语言来完成。这就使得立法语言成为立法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面向,并也因此产生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应采用某种方法作为其思维分析的工具,于是就有了对研究方法的再研究。随着人们对立法语言研究的深入,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当前立法语言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反思。基于此,笔者认为,这种反思的结果是把立法语言研究从以语义学为方法的立法语言属性研究,带向以语用学为方法的立法论证的研究。
一、当前我国立法语言研究现状
目前,从我国立法语言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即使切入立法语言研究的视角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围绕法律文本中的语词和语句展开研究的,从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对立法语言及其研究对象的界定中可见立法语言的研究进路。邹玉华等学者认为,“立法语言,是指国家出台或发布的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条约、条例所使用的语言,主要表现为书面形式”[1]。周旺生认为,“立法语言是书面语而非口语,是规范用语而非习惯用语。立法语言是表达立法者意图、立法目的、立法政策的文字载体”[2]。杜金榜认为,“立法语言是指语言记录的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条约、条例的文本,主要表现为书面文本形式”[3]。陈炯认为,“立法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用语言记录的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等的文本语言结构”[4]。如此定义立法语言,必然会为立法语言的研究设定一个核心的问题域,即如果要制定出一部好的法律,就必须清楚地掌握法律文本中所使用的语词属性,并依据这些属性来考量如何运用语词撰写法律文本。这被概括为“语言性质”的法律语言研究范式[5]。近年来,作为立法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就属于这一研究范畴。周赟曾对这种对立法语言属性的研究进路提出过一些质疑,认为“它们都是一种描述性分析,但却都没有进一步深入地揭示出立法语言为什么应该具有、或是否应该具有如此特点等问题”[6]。但遗憾的是,周赟从研究进路上仍未跳出对立法语言属性进行分析的范畴,区别于其他学者仅在于,其主张从司法(执法、守法)的视角进行一种“反观式”研究,即立基于司法(执法、守法)实践中法律运用过程,来反观立法语言的属性,并分析之所以要具备这些属性的原因。基于此,周赟提出用“立法性”“语用性”“规范性”来解释、证立和扩展关于立法语言属性的描述。对此,笔者认为,这种更深入地挖掘立法语言属性依据的理论价值值得肯定,但总体而言,在立法语言研究进路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向。
尽管本研究中两组糖尿病病程和HbA1c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进行相关分析时校正了HbA1c,但仍不能排除糖尿病本身对NAFLD发生的影响。此外,本研究样本相对较少、随访时间相对较短(平均3.26年),且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不均一,不能代表所有糖尿病人群。
上述学者将立法语言仅仅界定为法律文本中的语词和语句,并钟爱对立法语言属性的研究,是与他们对立法本身的认识密切相关的。由于制定法正是借用语词和语句,并形成书面文本形式,才成为人们能够真真切切看得见的“实在法”,亦即立法被认为“必然是文字到文字”[7]的一种活动。对于此点,美国学者萨默斯提出,富勒在划分“默示法”(implicit law)和“创制法”(made law)时有明确的阐述:“默示法”包括习惯和其他某些具有规范意义的人类交往活动形式,此类法事实上可能无法被还原为语词,更别说以权威文本陈述的形式出现了。“创制法”由表达清晰的规则和其他规定构成,包括制定法和明晰的合同条款[8]。可见,制定法作为一种法律,有其他形式的法律(如习惯法、道德规范)所不可比拟的特性,那就是制定法可以从语词和语句上“被看见”,进而可以从理性上“被掌控和分析”,并且也正是通过书面语词和语句这一媒介,盘踞在立法者头脑中的思想意志才可能被真切地转化为法律。因此,从最终能被感知的意义上讲,法律文本中的语词所阐明的内容就是立法者的理性意志本身。于是,立法活动的理性与否就直接体现在法律文本的语词上。如果要使这些法律文本在生效后能够准确无误地在司法、执法和守法环节中为人们所理解和奉行,那么基于语言的立场,首先要对法律文本中的语词所应具备的属性进行分析和研究,以确保这一语言运用形式能够有效地传达立法者的意志。有学者甚至认为,“立法技术最终要落实到立法语言,在立法中要克服重实体内容、轻立法技术的倾向”[9]。这里隐含的深意是,立法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其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准确地将立法者的意志转化为明晰的书面语词和语句。
由式(6)可知,l0实际上是液压缸的“等效长度”,其物理意义为:保持液压缸总容积不变,液压缸截面积等于活塞与液压介质接触面积时,计算得到的液压缸等效长度。由式(5)和式(6)可知,变截面液压缸产生的载荷特征仅与液压介质的总体积及活塞与液压介质接触面的半径相关,而与液压缸的其他尺寸无关。因此,在液压缸内设置滤波结构,不会对产生载荷的峰值、冲量产生影响。
总之,只有将立法语言扩展理解为是立法活动中的言语交流和互动,才能开启对立法行为、立法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全面分析的大门,因为“只有语用学才涉及到行为的整体”[19]6。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全面地正视立法作为言语交流和互动过程的属性,而非仅仅将其当作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仍然使用立法语言这一概念术语的话,就必须将立法过程中的言语交流和互动纳入其研究视域。最后还需申明的是,立法语言的语用学研究进路并不是排除之前的立法语言的语义学研究。“道理很简单,如抽象掉语句的用法维度,仅凭句法—语义维度,我们所构成的意义只能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当我们从上述抽象返还到语用学的具体时,同时也就把句法—语义维度包容于自身之中了。语用学不是对句法与语义的排斥,而是兼容。”[19]6如前所述,书面文本中的语词其实也是在进行一种语言交流和互动的形式,之前的立法语言的语义学研究完全可以囊括在新的语用学研究进路中。
二、立法语言: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
这里可作为例证的是,同属于法律语言概念之下,司法领域中的语言研究更多指向的是动态的言语活动,如庭审中的法官打断、法庭话语中的言据性等。这种差别地对待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是因为在法学理论研究领域人们已经习惯将立法当作结果来研究,而忽视了立法的过程。这种思维源自于一直被人们强调的立法被当作一种政治行为的属性。对此,沃尔德伦曾这样描述过:“法学理论中弥漫着这样一种意象,即常规立法活动除了不是一个具有原则性的政治决策之外,可以呈现为是交易(deal-making)、讨价还价(horse-trading)、滚木立法(log-rolling)、[注] 滚木立法,也称肉桶立法。取意于美国西部开垦盖房子时,大家相互帮忙“滚木”。放在议会中意指,一位议员愿意投票支持某一项议案,以换得另一位议员对另一项议案的支持。议员以彼此投票赞成或反对议案的方式来取得互惠式的同意,但其结果往往可能会使公共利益受损。因此,此种行为常被批评为是议员为图己利、讨好选民、浪费公费的一种陋习。 为利益拉皮条(interest-pandering)、争取政治拨款(pork-barreling)等诸如此类的活动。”[17]由于担心政治运作中的各种“潜规则”会给将要作为司法实践大前提的制定法带来太多不确定性,进而损害其正当性和权威性,于是“掩耳盗铃”,把立法当作政治并与法律相隔离,然后欺骗自己相信法律是一种客观知识。正如比利时学者卢卡·温特根斯所说的:“强式法制主义”(strong legalism)法律思维模式,即“法律与政治相分离是出于一种政治原因。这种分离是以有助于隐藏所作政治选择的认识论依据为基础而运作的。因此,价值领域包括政治的和道德的,被建构在一个会妨碍一种理性的立法理论的确立的‘中立’的基础之上”[18]。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对于立法语言的研究,语用学获得彰显也就自然而然了。因为交流实践中的语言必然会涉及有关价值判断、政治立场、伦理道德等内容,这些内容往往都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论辩性,从而无法满足人们对法律确定性和客观性的需求,而用语义学研究法律文本则不然。此时,法律就在那儿,人们只需反复推敲和分析其语词和语句的构成来获得和准确传达所谓立法者原意即可。至于立法者是如何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原意则无须过问。如果我们接受哲学语用学转向的深刻影响的话,这种规避立法过程中言语交流的立法语言研究,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立法是一个通过制定法律来政治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过程,这虽然与司法过程解决个案纠纷有很大不同,但和司法过程一样,定纷止争也是立法者对某项社会活动进行立法的最终目的。在这种情形下,进入立法过程的人们在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就不会是漫无目的的闲聊,也非一团和气的社交,而是以谋求将符合自己利益的诉求写进法律为目的展开说理的唇枪舌战。作为一种正式的说理,在立法过程中,参与立法的人都致力于通过给出合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当性,从而说服他人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主张,这实质上正是一个论证的过程。可见,立法中的言语交流是以说理论证为宗旨和内容,而与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交流相区别。甚至可以说,立法中的言语交流具体就是以说理论证的形式呈现的。因此,如果将言语的交流和互动纳入立法语言的研究视域,那么必然要对立法过程中的说理论证进行研究。
其实,论证在哲学语用学转向后早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范畴,而将论证理论应用于立法研究也并非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由立法法理学的主要倡导者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卢卡·温特根斯教授所创办的期刊《立法法理学》,在2010年5月第1期中以立法论证专刊的形式发表5篇不同国家学者的相关论文,标志着立法论证业已成为立法学以及法理学关注的对象。这说明立法是一个动态的言语交流过程,早已为人们所认识,相形之下,再次凸显我国当下将立法语言理解为是构成法律文本的语词的思维亟须转变。
好学校的保障是有良好的学校文化。学校应该有鲜明的教育个性:给你一部历史让你翻阅,给你一种文化让你感受。教育的目的,不光是教学生挣到面包,而且要让学生品味每一口面包的香甜。这就需要有学校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学校精神。“自豪、努力、成才”就是广州五中的价值观,它的内涵是:我自豪,我是光荣五中人;我努力,我与五中共发展;我成才,我为五中添光彩。我们正是用这种人文情怀激励师生奋进。
如果将立法语言研究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就需要充分认识立法活动的本质。通常,人们在提及立法时,总是将立法界定为一种国家行使立法权能的政治行为。但是,这种停留在表象的政治层面对立法活动进行的界定,却是对立法活动另一个重要的“非政治”属性的忽视,因为立法活动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言语交流的过程。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立法活动,就会发现在立法过程中,任何参与者都是通过在某个程序环节中的言语表达和互动才得以加入其中,从而完成立法任务。换言之,立法活动是以立法参与者之间言语交流的行为方式得以展开的,也正是通过参与者之间的言语交流,才使立法活动得以循环往复的启动、完成和推进。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发声的、沉默的立法过程。而“立法人(机构)只要说话,其言语就是立法言语”[10]。作为立法结果书面形式的法律文本,也非言语交流的终结,相反,它开启的是另一形式的言语交流。比利时学者马克·范·胡克有过这样的论述:“立法是一种特殊的沟通形式,通过立法,立法者设立规范,传达给许许多多当下和/或未来的(法律上的)人,这些人被期待会尊重并遵从这些规范。这不仅是关于新制规则之内容的一种信息传递,还是一种典型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或一种施为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据此,法律变更才得以出现。”[11]可见,立法活动不仅是当下立法者之间的言语交流和互动,也是当下立法者与未来将会受到法律约束的人们之间的言语交流和互动。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言语交流是人们能够贯彻始终观察立法活动的最根本的外在形式,这种交流既包括动态的语言活动,也包括静态的语词文本。因此,如果我们仍然使用“立法语言”这一概念,就应该指称一种处于交流和互动状态中的语言,并且需要把视角从法律文本延伸到形成该法律文本的整个立法活动过程。这一延伸过程,本质上就是要将立法语言的研究方法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
显然,这种将立法语言限定在法律文本书面语词上的研究进路,却忽视了语言的另一特性,即语言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立法是通过一系列依据程序展开的动态活动过程,而这个活动过程同样是借助语言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书面文本绝不是立法过程中唯一运用语言的地方。相反,书面语词所要表达的具体内容,首先取决于之前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所进行的互动和言语交流,之后才会遇到如何遣词造句进行准确传达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法律的书面文本其实正是以言语交流形式展开的动态立法活动的结果。依此逻辑,学者们为什么会忽略立法过程中这个显而易见的动态语言交流活动,而将立法语言的研究界定在对静态法律文本的分析上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学者们将立法语言中的语言概念放置在语言哲学中的语义学研究范畴内,而尚未意识到可以用语言哲学转向后的语用学来审视整个立法活动。本文的主旨是,在理解和分析语言哲学从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向的基础上,尝试如何进行语用学进路下的立法语言研究。
三、语用学进路下立法语言研究的旨趣
以主体间的语言交流和互动为核心的语用学研究进路,到底能给立法语言研究带来哪些新的旨趣?换句话说,在语用学研究进路下,立法语言的研究任务包括哪些内容?这也是本文写作最终要落脚的问题。结合当今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语用学研究进路下的立法语言研究,必将把“论证”这一概念引入人们对立法行为和立法过程的本质认识中。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研究如何在立法过程中展开说理论证
众所周知,语言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从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化的过程。在语义学研究阶段,以弗雷格、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受过数学训练的哲学家们,首先认识到语言构成中的哲学问题。美国哲学家威廉·阿尔斯顿提出:“能够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不仅是思想的,也是能存在的,当我们考察语言、从而考察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就会发现某种关于世界本质的东西。这是因为,语言、思想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行关系。”[12]这些哲学家笃信,通过运用数理逻辑,人们可以对语言——这种外化的“理性”进行形式分析,能够把有关世界本质的推论变成一种对句子的逻辑演算,“从语言的结构推出世界的结构来”[13],进而更清晰地捕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种静态地对语言逻辑结构进行的考察,明显脱离了语言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背景,忽视了语言的多样性以及人在使用语言时的心理等因素对语言的影响。正如英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游戏”概念所指出的那样:“用语言来说话时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14]哲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把语言研究放在人类生活实践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和认识,这带来了哲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这种转向后的影响是,“一种科学的语用思维在整个思维领域逐渐树立起来。现代哲学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建构,而是一种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有规则的语言游戏,因此是参与者(包括讲话者和听者)间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单纯的主客体模式,可以说,语用思维构成了‘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15]。基于这种思维,再次进入人们研究视域的语言就不是一种自言自语式的独白,而是主体间的表达和对话。于是,语言哲学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使命,将研究放置到主体间可传达和理解的语言上,“主体间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成为哲学的中心话题[16]。
哲学研究从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向带来的最深刻改变就是将人的思维模式从主客体转向主体间。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的思维和认识取决于主体间的语言互动,人的理性是在语言互动中体现出来的。之前的语义哲学虽然认识到人的认识能力蕴含在语言之中,但仍是将语言当作客体进行研究,而语用哲学则认识到语言即是主体本身。只有研究语言在主体之间互动使用的过程,才能将一个不被异化的主体和世界完整地呈现在人的认识视域。基于此,如果将立法语言仅限定为是一种语义学研究,那么同样存在的问题即是割裂主体(立法者)与客体(法律文本)之间的联系。在民主政治下,立法不是一人所为,而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复数立法者共同为之。在立法过程中,法律文本内容所反映的并不是单个立法者的思想,而是在多个立法者之间进行讨论、协商、辩论等一系列言语交流和互动后所形成的共识。法律文本是共识的反映,实际上用什么样的文字和语句表达法律文本的内容,是立法过程中语言运用的最后一个步骤,而之前为达成共识立法者进行言语交流的过程,则更实质性地决定着法律文本的内容。所以,将立法语言限定为法律文本所使用的语词和语句不仅有失偏颇,低估了立法语言这一概念内涵的丰富性,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忽略了立法活动过程中法律文本内容所起的实质性作用。
(二)研究如何制定立法论证的程序规则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无规则即是无理性。”[20]从这一意义上讲,规则是人类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是外化的理性。与一般的言语交流不同,立法过程中的言语交流是一种说理论证,彰显的是人的理性。那么,如何证明这一说理论证过程能尽最大可能地发挥人的理性呢?这就要看其所遵循的程序规则。正如德国学者阿列克西所总结的:“道德论辩是受规则支配的、以理性的方式平衡利益的独特活动。实践论辩理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阐明支配该活动的规则。”[21]也就是说,正是程序规则将说理论证这一言语交流的过程变成人们可以理性批判和反思的对象,一旦所有参与者认可和接受了论辩的规则,则意味着依据这一规则进行的活动过程将被认为是理性的,其结果必然也就是理性的。如果说研究立法言语交流就是对立法过程中说理论证的研究,那么这种研究必然会具体落脚到研究说理论证所应遵循的程序规则上。按照通常的理解,立法程序规则作为制定规则的规则,是人们完成立法活动所遵循的步骤和方法,属于程序法的一种。因此,人们更习惯从立法机关内部组织结构的设置及其工作惯例等方面来探讨立法程序。这一点在我国《立法法》的制定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不得不说这种认识是普遍的,并一直禁锢着人们对立法程序规则的探讨。实际上,从立法语言的语用学视角来审视立法程序,就是要深入挖掘立法程序规则彰显理性的价值内涵,以期能反过来重构立法机关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进而更实质性地发挥立法机关作为议事机构的功能。
(三)研究如何达致立法共识
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22]与习惯、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比较而言,制定法并非自发产生,也非自发能为人们所接受。在“祛魅”后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生而平等的,要在排除暴力的情形下获得对制定法的接受,就只能依靠人们在立法过程中以言语互动和交流的方式通过达致共识来实现。也就是说,现代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只能来自于基于立法共识而做出的接受,因为唯此才会使公民“时时都能把自己理解为他是作为承受者所要服从的法律的创制者”[23],进而使法律之治成为可能。可见,对制定法达致共识正是立法作为法治一个环节所必需完成的使命,这就给立法过程中的说理论证及其所要遵循的程序规则提出了更为实质性的要求。之所以说是实质性的,是因为上述提及的论证的程序规则虽然能够体现和确保理性,但受自身程序属性所限,其仅能最大程度地从形式上关注立法所涉的利益分配是否公正,对一些诸如价值、信仰、伦理、情感、心理等问题却难以完全兼顾。而后者往往是立法过程中为化解利益纷争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所以,立法语言研究不仅要研究立法论证如何通过形式上遵循程序规则体现理性,更要研究在遵循程序规则的前提下,如何通过主体间真实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和互动来促进达致立法共识。
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能力是指“完成对船舶污染物的分类存储、接收、转运和处理处置等一系列活动所必需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总和,是为防止到港船舶正常运营所产生的污染物对港口水环境造成损害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水平。”
综上所述,将立法语言的研究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其意义不仅是对立法语言研究的再认识,更是对立法研究的再认识。因为在以往的立法研究中,立法活动的言语属性一直被立法活动的政治属性所掩盖,而使得人们总是从政治的视角去看待和研究立法,并认为立法是一个受国家政治体制制约的活动。这一观点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如果将立法活动首先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言语交流过程,就可以倒过来看问题,即可以藉由立法语言、立法论证的研究,来反思我国当前立法体制中尚存在的问题。依据本文的前述观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必将会以在立法活动中如何能充分展开立法论证来衡量。
参考文献:
[1] 邹玉华等:《立法语言现状及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67页。
[2] 周旺生:《立法学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3] 杜金榜:《法律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4] 陈炯:《立法语言学导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 胡范铸:《基于“言语行为分析”的法律语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89页。
[6] 周赟:《立法语言的特点:从描述到分析及证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第135页。
[7] 黄震云、张燕:《立法语言学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8] 萨默斯:《大师学述:富勒》,马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9] 陈炯、钱长源:《对于立法语言作为立法技术的几点思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2期,第52页。
[10] 廖美珍:《语用学和法学——合作原则在立法交际中的应用》,《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5期,第83页。
[11] 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12] 威廉·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牟博、刘鸿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13] 伯特兰·罗素:《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贾可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03页。
[14]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5] 殷杰:《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57页。
[16] 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的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9页。
[17] Jeremy Waldron, The Dignity of Legisla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
[18] 卢卡·温特根斯:《作为一种新的立法理论的立法法理学》,王保民译,《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4页。
[19] 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20] 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9页。
[21] 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22] 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23]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85页。
中图分类号: D90-0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 2019) 03-0120-06
基金项目: 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依法立法视野下授权立法的控制研究”(CLS2018C38)
作者简介: 李晓辉,1978年生,贵州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肖海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