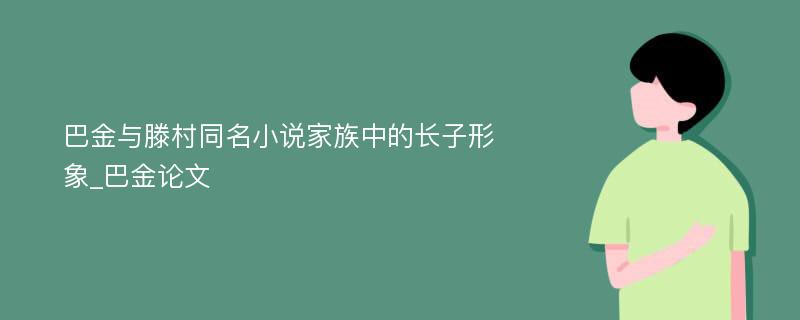
巴金与藤村的同名小说《家》中的“长子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子论文,巴金论文,形象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岛崎藤村在本世纪初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做《家》。本世纪30年代初,巴金也以同样的标题发表了一部影响了几代青年的小说。尽管这两部长篇发表的时间相隔近二十年,但是它们的叙述背景颇为相似。这两部长篇所描述的“家”都处于一个向近代转变,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而且,这两个“家”都在历史地走向瓦解。同时,两位作者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了从封建专制时代向近代民主时代转变过程中家族关系上必然要碰到的几个问题。这就是“家长制”问题、长子问题、婚姻问题和妇女问题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仅对两位作家塑造的“长子形象”进行分析,同时对隐于其后的文学与文化的诸种因素进行探讨。
一
“正太”是小说中桥本家族的长子。他接受过新的思想,喜欢具有新思想的三吉(正太的舅舅)写的书。在他的眼里。家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窒息,阴暗,单调”。(注:岛崎藤村:《家》(上),日本新潮社1978版,15页。以下出自岛崎藤村的《家》的引文均据此版本。)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包括婚姻恋爱的自由。但是,婚姻在母亲那里首先是“家与家的婚姻”。(21页)而且,整个家族都在指望着他,依赖着他,认为他有责任牺牲他个人的一切。面对着这一切,正太虽然觉得“家随它怎么样都成”,(28页)但是在行动上却不得不屈从于“家”为他所安排的一切,与母亲为他相中的女人成家婚配,并在父亲离家出走以后去收拾负债累累的残局,履行长子的义务。与达雄一样,正太也不是藤村着意塑造的一个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但是,他身上发生的一切却与巴金着意塑造的大哥“觉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巴金的《家》里的大哥觉新也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的、有着个人追求的人。他也同样有着相爱的恋人,也同样感受到了旧式大家族的沉闷、窒息、束缚,也同样希冀着自由,希冀挣脱现实束缚在他身上的锁链。但是,他也和正太一样,没有忘记自己作为长子、长孙的责任以及义务。为了家庭,他牺牲了他个人的一切,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恋人,被迫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被迫作出许许多多有违他个人意愿的事情。中日两位作家的《家》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过,藤村和巴金处理小说素材的着眼点却丝毫也没有因为这一相同的事实背景而有所改变。藤村写出了正太对于“家”的感慨与不满,却没有让他因此生出对于整个家族制度的痛恨。与此相反,巴金却时时刻刻在试图让觉新说出他对于整个家族制度的仇恨,试图借觉新这个人物形象揭露封建家族制度对于年轻人的精神摧残。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来自于两位作者本人认识的不同。同时,也与日本的现实生活中长子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度大于中国的“长子”,与日本现实生活中的家长的专制程度低于中国的“家长”有关。也许正太离开家庭、走向都市的时候,也曾和他的母亲有过对抗或者摩擦。但是,藤村作为小说作者对此却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在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正太轻易地就实现了他走出大山的愿望,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同样,尽管正太身上也存在着新与旧的矛盾,藤村却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无意在作品中去表现这种矛盾所带来的种种冲突。假若是巴金,恐怕不会轻易放过这种矛盾,很可能会在这里费些笔墨。
大山里的家在藤村的笔下是一种陈旧的象征,都市似乎成了新的天地。在表现正太走出大山来到都市找寻他的人生目标的时候,作者试图强调的不是新的思想、观念对正太的浸润、影响,而是正太本人的焦虑、冒险,还有他的与生俱来的不安份。这些也许正是现实中的正太的形象。如实、自然、客观地描写之当然不能说是藤村的什么过错。相反,藤村出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家的立场,作出这样的处理是再为正常不过了。在藤村的笔下,来到都市里的正太仅仅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做股票生意,二是周旋于艺妓吧女之间。与女人们的异常关系在藤村看来,正是正太从他的父亲那里承继下来的“坏毛病”。而正太染指股票则被藤村解释为与他的父亲相同的不安分的性格所致。换一种角度看,正太来到了都市,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但实际上他仍然处在父亲的制约下。这种制约并不是来自于父亲的直接力量,而是父样的“遗传”作用。在藤村的这种素材处理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藤村所关心的是对于生物性的人的探究。他在试图向读者诉说“遗传”的力量是何等的巨大。同时,我们还可以读出藤村无意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一个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类似于巴金笔下的“大哥”的那种形象。当然,藤村也就不可能去关心处于社会变动时期之中的人的矛盾与斗争了。
与藤村笔下的“正太”的形象比较起来,巴金的《家》里的觉新显然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他的身上有着巴金大哥的影子。巴金之所以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就是因为他试图借这个典型人物来“挖掘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我们民族怯懦苟且的国民性”,(注: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版,175页。)来揭示在封建大家庭中开始觉醒的长子的悲惨处境和无奈的生存状态,使人们看到觉新也就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凶残暴虐,从而也就会唤起人们对于陈腐的封建主义观念,对于专制的封建家长制的敌视与仇恨。这正像巴金本人所讲的:“我能够描写觉新,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人。我对他有感情,我为他花了那么多的笔墨,也无非想通过这个人来鞭挞旧的制度。”(注: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版,178页。)因此,巴金在小说的第六章的开始处就决定了觉新的命运。“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注:巴金:《家》,人民出版社1978版,404页。以下出自巴金的《家》的引文均据此版本。)长大成人后,父亲用拈阄的方式决定了他的亲事。尽管他感到了幻梦的破灭,但是“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父亲在他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把这一房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了”。“他平静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他的年轻的肩上”,“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他渐渐地“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到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成为了人们攻击的目标”。他心中尚未熄灭的“青春的火”使他愤怒,使他奋斗。但是,奋斗的结果却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于是,“他发明了新的处世方法”,极力避免冲突,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周围的人。“五四运动”为他带来了新的理论、思想。他“信服新的理论”,但同时又“喜欢无抵抗主义”,喜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35-41页)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旧家庭的暮气十足的青年,与两个兄弟相同的新青年。他读的是新思想的书报,过的是旧式的生活。
然而,觉新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彻底麻木。他仍然有着无尽的痛苦。这种痛苦正是巴金特别留意的。在第12章里,巴金让觉新作了大段的内心独白,以袒露自己的内心痛苦。在巴金的笔下“牺牲者”正是对觉新这样一个“长子”的命运的概括。在巴金看来,处于旧式封建大家庭中的长子们为了家庭,为了父母,为了自己的亲人,是不得不抹杀自己的个性,放弃个人的希望,牺牲一己的幸福与青春的。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牺牲者”。但是,巴金没有仅仅将觉新描写成一个单纯的牺牲者,他还看到了觉新的所谓“牺牲”所造成的其他的“牺牲者”。因为觉新的怯懦、屈从,使得他的恋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样,巴金试图深掘的“我们民族的怯懦苟且的国民性”的可悲之处也就显露了出来。在对觉新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巴金显然不仅仅是要写一个为家庭牺牲的旧式的封建大家庭的长子,更主要的是要深掘我们的国民性中可悲的一面,以引起读者的反思。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从单纯的个人经历的角度看,巴金的“觉新”与藤村的“正太”十分相仿。这与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处的极为近似的时代文化背景关系很大。不过,巴金和藤村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时,其着眼点却大不相同。巴金在塑造觉新这个人物时,其重点放在了对他的双重性格的塑造上。同时,巴金还着意发掘觉新性格上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心动荡和痛苦。
正太在藤村的《家》中也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但是我们对他的内心世界却无法看得十分清晰。我们可以感知到他不愿守旧、不断求新的急切,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时代牺牲者的悲哀,但是我们却无法看透读懂他的内心的一切。这也许和藤村的日本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念有关。他可以把另一个主人公三吉的内心表现得真真切切,却无法让正太以及其他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袒露在读者的面前。因为三吉的内心就是作者本人的内心,描写自己的内心对于藤村来讲显然是游刃有余的,也是他的自然主义文学观中的“客观、如实、自然的描写”所容许的。而在对于正太的描写上,他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他只能从正太的言谈举止神态这些外部世界的客观描写来表现正太的内心变化。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藤村无意像巴金那样去塑造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其根本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的这种文学观念。正太虽然有着因“家”所造成的苦恼,但是在藤村的眼里他并不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牺牲者。藤村也无意将他写成一个这样的牺牲者。这在《家》的下集里,我们看得最为清楚。
在下集里,藤村主要写了三吉和正太。而正太在下集中所出现的苦恼、奋斗以及他的失败、痛楚与他的“家”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正太与其父达雄的“遗传”的关系。正像达雄为正太的母样阿种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痛一样,正太也因他本人的放荡使自己的妻子长久地陷入苦恼之中。如同三吉兄弟所讲的那样,“只要没有沉溺于女人的毛病,桥本父子(达雄和正太)是无可挑剔的”(注:岛崎藤村:《家》(下),日本新潮社1978版,104页。以下出自岛藤村的《家》的引文均据此版本为准。)沉溺于女人的毛病对于正太来讲,或者在藤村看来,并不是正太本人的问题,而主要是因为“有其父便有其子”。对于这一点,三吉兄弟的对话讲得更清楚。“(在那出剧里)有个叫宗七的人,是个很懂得——情趣的人。而且,还是个感情充沛的人。——一个颇爱冒险的人。这种人一旦投入,就会走向极端。正太就有点像这个宗七。”“哪儿,他爸爸才是宗七,他是宗七二世。”(104页)在三吉眼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藤村的眼里,正太的人生虽然有别于他的父亲,但是从根本上讲,正太并没有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正太仍然是那种旧式的家庭所培养出来的“情趣高雅”、“享乐人生”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事业上略有起色时便像他的父亲达雄那样去寻花问柳,挥霍钱财,消耗自己的情感。
假如说正太也是在追求“新”,那么他的所谓“新”在小说中也仅仅体现在新的职业上,也只是区别于旧式的药商的股商而已。而在他的骨子里,他仍然没有超越他的父亲达雄。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正太的那番感慨了。“人们都说旧时代的人不行,——可是,新时代的人难道说就可以信赖了吗?!”(126页)在对正太的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治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新的时代里,藤村所关注的并不是新与旧的碰撞、冲突、矛盾,而是生存于这个时代的人与“旧”的联系,而这种“旧”又主要体现在血缘的遗传上。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藤村看到了正太身上存在的矛盾,这就是正太试图寻求光明未来的愿望与现实黑暗的矛盾。只是藤村对于这种矛盾并不打算在小说中展开。这一点与巴金比较,也是有着显著不同的。
巴金以觉新的内心矛盾塑造了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弱者形象,以此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怯懦的国民性,暴露出封建专制家族制度对青年人的精神摧残,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家庭中长子可怜可悲的境遇。而藤村只是试图告诉读者在他的家族里曾有过正太这样一个背负过家庭重担的年轻人,而他又在历史的变动过程中轻易地扔掉了这副重担。让读者在正太这个求新又难以脱旧,生活和事业上都是失败者的人身上感受人生的悲凉。巴金在他的人物形象上凝聚着的则是对于社会的控诉,对于封建旧制度的批判与反抗。对巴金来讲,写个人不是为了记录、表现某一个人,而是要通过一个人的典型塑造写出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痛苦。藤村在他的人物形象上集中着他对人的观察,体现着他的客观如实自然的文学理念和实录精神。我们当然不会否认藤村也写了社会,但是他笔下的社会只是为了描写他的人物形象的一个背景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尽管巴金和藤村都在他们的《家》里写了处于历史变动中的旧式封建大家族的衰落,都写了这种大家族的长子形象,但是他们的创作意图,他们的具体的形象塑造却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着中日两国近现代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实践的不同。
二
在表现具有相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长子”形象上,藤村与巴金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毫无疑问与他们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创作意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原因。从外部社会文化背景看,中日家族制度的不同,或者说中日家族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的不同也促成了巴金与藤村在他们的同名小说中的长子形象的不同。从文学内部的审美因素来看,中日传统的小说审美观念的差异也构成了两位作家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不同的潜在因素。
巴金笔下的高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这种大家族在中国社会中是一种理想的传统家族类型。它标志着人丁兴旺、家境富裕、幸福和谐。能够作到四世同堂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家族人员的长寿,还有保持稳定的秩序。而这一切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作到的。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位于最高位置,高老太爷是颇为自得的。高老太爷竭力保持家族的稳定秩序也是可以理解的。藤村也在他的作品中向读者展现了日本的两个旧式的“大”家族。在小说的第一章里,藤村就让读者看到了桥本家族的风貌。这个家族是由桥本达雄、他的妻子阿种以及他们的一双儿女,还有家中的众多雇工所构成的。最能体现这个家族之大的就是三吉与桥本一家还有他们的雇工一同就餐时的场面。事实上,如果将桥本家的雇工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大”家族也就谈不上有多大了,与平常的普通人家没有多大的差异。即使加上“正太”以后娶的妻子、阿种收养的“养子”,也是远远比不上高老太爷的那个四世同堂、拥有数十人口的封建大家族大。再看藤村笔下的另一个“家”——小泉家族。这个家里除了长兄阿实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只有一个身有残疾、需要他们照料的弟弟和他们共同生活。阿实的其它两个弟弟,一个早就成了人家的养子,一个也另立了门户。在这个家族里,不仅没有了以往的显赫,也没有了旧式大家的形式,有的只是旧式大家的意识。
所谓家族的大小,一方面和家庭的人口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几代(或几对夫妇)同堂有关。中国的四世同堂就是家族之大的典型例子。由于过去生育人口较多,四世同堂的家族往往是五、六对夫妇,甚至七、八对夫妇加上他们的子女同居一堂,人口要有数十人之众。高老太爷的家族就是如此。而日本的家族构成,依据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的调查,最多也就是三对夫妇加上他们的子女在一起生活,人口也就在十人上下。(注:中根千枝:《以家族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日本讲坛社1977版,35页。)多对夫妇、众多人口同居一堂,共同生活,必然就会使得家族关系复杂化。要使家族人员的关系和谐稳定,就需要一种可以维持家族秩序稳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就体现在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合一的封建宗族组织以及因此而生成的封建宗法伦理。这种组织、伦理与封建社会的组织、伦理是相通的。在封建社会中,要求人们对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尽忠,以维系封建王朝的牢固稳定。在封建家族里,则要求人们对以家长为代表的长辈们尽孝,以求得封建家族结构不失衡。所谓“孝”就是要求把“孝顺父母,养亲事亲,儿子绝对服从父亲,尊重祖宗作为伦理道德行为的根本规范”,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成为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和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杠杆”。(注: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272页。)在高家,处于家族最高地位的高老太爷的权威的基础就是这个“孝”。他与觉新三兄弟的冲突也来自于这个“孝”。在高老太爷看来,遵守孝道,绝对服从,抹杀个人意志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对觉新他们来讲,这一切都是对个人的束缚、压迫,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在一个近代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里,反抗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这样的家族关系反映的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巴金将高家看成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试图通过写高家表现社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样,这样的一种家族关系也就使巴金以描写高氏家族来表现现实社会成为了可能。对于这样的文化背景,我们是无法忽略的。
日本的家族制度是“长子继承制”。在名称上,它与中国的长子继承制没有差别,但是在实质上却是不同的。在日本,一旦长子成为了家长,长子就要继承家庭的主要财产,家庭的名分、门第,而他的兄弟则要离开家庭,只继承很少的财产,以“分家(家庭的分支)”的形式另立门户。这样,能够留在家里的只有长子一家人以及他们的健在的父母。所以,在日本,旧式大家的“大”在相当的意义上是指其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拥有较多的财富,并非人口众多。由于实际家庭结构简单,人与人的关系便被集中在“父”与“子”的纵向关系上。这样的关系也同样以服从作为基础,“子”要服从“父”。不过,这种服从不是以“孝”为基础的,而是以家长的权威为其根底的。中根千枝在《以家族为中心的人际关系》一书中认为:“(在日本社会中)并不是因为作了父亲就有了权威,而是因为当了家长才有(权威)的。事实上,当家长权让给了儿子以后,父亲也就没有了权威,成为了隐退之人。他也就必须从家族的最高地位中退出。”(注:中根千枝:《以家族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日本讲坛社1977版,102页。)同时,她还指出:“中国的孝的概念与日本的孝有着极大的差别。”(注:中根千枝:《以家族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日本讲坛社1977版,102页。)中国的“孝”强调的是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不论长辈是否还处于“家长”的地位,也不论长辈的要求是否违背晚辈的个人意志,都需要晚辈服从长辈。而日本的“孝”则是对于长辈抚育之恩的报答,并不要求晚辈在任何时候都对长辈绝对服从。但是对于作为家长的“父”,“子”却是要绝对服从的。因为此时“父”代表的是家族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太要在婚姻大事上屈从于家庭的原因所在。这种“父”与“子”的关系反过来被运用到社会、集团中。“天皇”与“人民”的关系被视为父与子的关系,在集团中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关系都可以说是这种家族关系的变异。
在日本,作为长子,他服从的对象只是作为家长的父亲,而不是其它的长辈。一旦他继承了家长的位置,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主宰整个家族的拥有最高地位的人。在藤村的《家》里,正太的父亲达雄、正太的舅舅阿实虽然都是长子,但是由于他们很早就继承了家业,成为了家长,在家族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们作为“子”与其父的冲突很早就被减缓了。藤村没有在作品中表现这两位长子与其父的对抗、冲突,我想主要是因为缺少创作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藤村虽然也表现了这两位长子与“父”的关系,但是他的着眼点却在于追究“父”与“子”的血缘联系、遗传联系。由此看来,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个“长子”正太,他与家族的最早冲突表现在婚姻问题上。而那正是其父在家中执掌“家长”之权时。因此,“视家为无所谓之物”的长子与试图振兴家业、讲求门当户对的“父”的冲突也就自然难以避免。藤村在作品中表现它自然也就不是无中生有了。但是,当达雄离家出走,主动退出家长位置时,正太没有依恋这个位置,也离开了大山,走向了都市。这样,正太的“父与子”的关系也就得到解除,同时也使遵循如实描写原则的藤村无法继续表现这种关系。不过,藤村在正太身上仍然看到了他与其“父”的联系。这就是作为“子”从“父”身上继承下来的血脉与精神。探究这种遗传的关系,固然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接受佐拉的自然主义时的“误读”有关。但是,我们相信这也是藤村找寻正太与其“父”联系的一种方式。
三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小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文学观念的引入。但是,日本小说创作中的审美意识却没有由于西方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大量涌入而受到根本性的改变。社本武在他的《日本小说的美意识》一书中,认为“一元性结构的小说”充分显示了日本小说的特点。(注:参见社本武:《日本小说的美意识》,日本樱枫社1980版。)当然,他并不否认日本小说中“多元性结构”的存在。但是,他以为这种“多元性结构”是有别于西方小说的。所谓“一元性”实际上是讲小说作者在小说创作中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塑造一个主人公,作者可以随时进入到这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同时整个小说的建构都是围绕着这个主人公所进行的。而其它的小说人物多是附带的、不清晰的配角形象。有时,甚至这个主人公就代表着作者本人。在相当多的场合,作者本人的观念、认识、思想甚至一些生活事实都会投射到作者“格外倾心”的这个人物之上。所谓的“一元”在这种意义上又是小说人物与作者之间的“一元”。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的许多作家的创作自不待言,就连夏目漱石、有岛武郎这些被视作深受西方文学技法影响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小说写作中不自觉地采用了这种结构。
藤村的《家》自然也没有冲破这种结构的束缚。平野谦在《家》(新潮文库版)的“解说”里认为《家》的“所有的场面几乎都有三吉的存在”,可以说“几乎没有三吉不在的时候”,“三吉是贯穿全篇的唯一人物”。当然,平野谦同时又指出尽管如此读者却很难从中感受到私小说的味道,原因就在于作者“对小泉三吉(的描写)几乎没有用特写镜头,总是在用长镜头在跟踪他”。(注:岛崎藤村:《家》(下),251页。)对于平野谦的“三吉无处不在”的结论,我们无疑是赞成的。但是,要是说从中感受不到私小说的味道,却是有些牵强。事实上,三吉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被看作藤村本人。也正因为如此,三吉在藤村的笔下才成为了形象最为鲜明的“唯一”。三吉是藤村笔下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没有他的存在,也就没有其他人的存在。即使像达雄、阿实、正太这样在家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同样需要借助他的力量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样的一种创作上的审美意识对于全面、整体地把握人物与人物的关系必然要形成障碍,妨害作者立体地塑造人物形象。铃木修次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里说:“在艺术欣赏中,日本人特别喜欢一种带有模糊、幻晕感的东西,比之现实的、形象的,更喜欢超现实的、抽象的、幻想的东西。”(注: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版,90页。)在藤村的小说里,表现现实自然应该是他的主要目的,也是历史的变革、近代文学的变革对藤村这些作者的要求。同时也是藤村对于这种要求的回应。这看起来与铃木修次的结论颇有些距离。但是,在模糊三吉以外的其他人物形象上,藤村创作上的这种美学意义上的选择还是与铃木修次所指出的现象相符的。这一事实也证实了藤村在积极引入西方文艺观念的同时也在竭力地遵循着传统的审美习惯。藤村的这种选择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藤村本人缺少总体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性能力。同时也反映了日本传统审美习惯力量的强大。其实,即使在藤村花费了大量笔墨塑造的“三吉”这个人物形象上,也同样有着不少需要读者细心琢磨的模糊之处。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模糊之处给予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在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作品创作的意义上,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学的创作特点。当然,与此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妨碍了一个立体的、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出现。藤村与巴金的长子形象的不同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来源于此。
在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小说中的传统审美意识是与之相左的。中国小说美学强调小说的真实性,所谓“天地间有奇人始有奇事,有奇事乃有奇文”,“世上先有水浒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注:孙逊、孙菊园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47页。)同时,中国小说美学还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并非事要有其事、人要有其人。在强调小说材料的真实上,中国小说美学与藤村所处时代的作家的创作意识并没有冲突。但是,在“何必实有奇事、实有其人”的美学观念上,藤村那一代的作家却与中国小说美学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以他的文学观念来讲,事一定要有其事,人一定要有其人。所以,在他的作品《家》里,父乃实有之父,子乃实有之子,事也是实有其事。这种无法作出大剪裁的对现实的实录,很容易妨碍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集中、凝练,也有碍于作者理性能力的充分展现。此外,小说作品的“社会作用”也是中国小说美学强调的重要的一点。巴金的《家》的主题本身就体现着这一点。而且,在他的《家》里,巴金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强调这种作用。但是,从日本纯文学小说的角度来看,是不屑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作大量描写的。相反,那种与外部现实世界隔离的、对个体的人的内心世界作出了细腻描写的小说往往会得到较高的评价。日本纯文学小说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可以说就是对功利性的剔除,“非功利性”成就了一批日本近代小说名著的产生。仅仅从这一点看,中日两国小说也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藤村强调他的《家》只写“屋内”,不写“屋外”实际上也是要消除他的作品的“功利”的作用。
另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中国小说美学强调人物性格的鲜明性、立体性、复杂性。巴金在他的《家》的创作中可以说完全遵循着中国小说美学的这种传统。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复杂,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无中生有”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矛盾、展现人物的心理冲突,制造震动人心的情节高潮。觉新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就是在这样一种美学观念的引导下形成的。中国小说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描写,强调对人物性格的本质的把握。除了一个主人公外,他们还可能塑造复数的主人公形象或其他的人物形象。而且这些形象的性格一般都是鲜明的、立体的,使读者读后难以忘怀。巴金在他的《家》里所塑造的觉民、觉慧、梅表姐、琴、鸣凤等等人物形象都没有丝毫的模糊、含混,个个都是让读者过目难忘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与藤村的《家》里的人物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中也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小说美学的相异之处以及对两国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