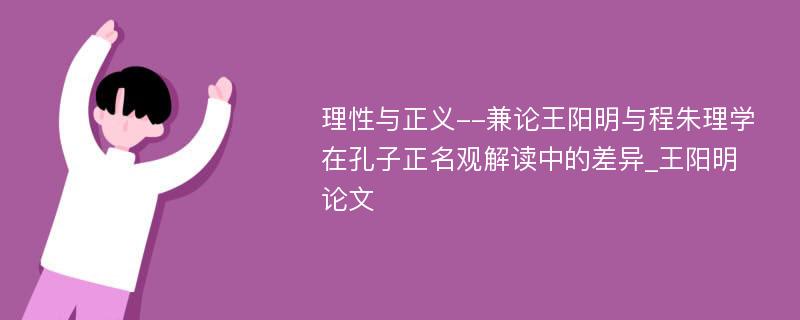
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解读孔子正名观念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义理论文,理学论文,情理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5-0035-07
一、基本史实
据《左传》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性淫,与宋公子朝私通,卫太子蒯聩以之为羞,愤而蓄谋杀死南子,结果事败,出奔于宋,既而投奔晋国,卫灵公尽诛其党。
哀公二年,卫灵公过世。灵公死后,在继承人问题上曾有过一段曲折。蒯聩出逃后,卫灵公曾打算立另一个儿子郢为继承人。但郢以不能担此大任为由予以拒绝。灵公死后,南子又宣卫灵公生前之意,试图立郢为国君。然郢仍然拒绝,否认灵公有此遗嘱,并且提出太子蒯聩之子辄还在。最终,卫国立卫太子蒯聩之子、卫灵公之孙辄为君主,是为卫出公。
与此同时,流亡国外的蒯聩亦得知灵公丧讯,在晋国的帮助下试图回国继位,然遭到了卫国的抵制,被迫居住于卫国的戚。自此,蒯聩居于戚,与卫出公辄形成对峙,父子相持十余年。直到哀公十五年,蒯聩在自己的姐姐孔伯姬及其佣人浑良夫的帮助下,挟持了当时专政卫国的外甥孔悝,发动政变,赶走了卫出公。孔悝拥立蒯聩为君,是为卫庄公。
二、孔子的态度
孔子正好生活在这一时期,显然清楚卫国这一父子相争的事件。在《论语》中,有两节语录涉及此问题。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述而》)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在第一则材料中,冉有想知道老师是否愿意帮助卫出公治理国家,因而由子贡去询问孔子的意见。然而子贡并未直接问以卫国之事,而是请老师评价伯夷叔齐。在孔子看来,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他们互相推让君位,并不以没得到君位而产生怨恨,所以是“求仁而得仁”。由历史上的兄弟逊国到现实中的父子争国,子贡推断孔子不赞成卫君的行为。然而这段对话中,孔子毕竟没有直接评价卫出公,我们只能间接地推断,即“孔子赞美伯夷、叔齐,自然就是不赞成出公辄了”[1](P75)。
在第二则材料中,我们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当时的背景。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
是时,卫出公辄已当政,孔子的不少学生仕于卫,如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正是在卫国父子争国的背景下,孔子来到了卫国,并且“为辄所宾礼”[2](卷七),即受到卫国的礼遇。子路想知道如果卫君请老师主政,首先将采取什么行动。孔子明确指出以正名为要务。那么孔子的“正名”具体何指?为何而发?对此,后世儒者有不同解读。
第一种观点认为正名为“正百事之名”,或正文字之误,马融、郑玄、班固、皇侃、邢昺等持这种观点。如马融注曰:“正百事之名也。”[2](卷十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亦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皇侃曰:“所以先须正名者,为时昏礼乱,言语繁杂,名物失其本号,故为政必以正名为先也。……郑注云:‘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记》曰:‘百名以上则书之于策。’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3](卷七)
第二种认为正名乃正人伦,尤其是指端正君臣父子之名,如正世子之名。宋明理学诸家、清儒全祖望、刘宝楠等多主此义。依据孔子的春秋笔法,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经文“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中的“世子”一词进行推断:
“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聩父既死矣,而称世子者,晋人纳之,以世子告,言是正世子,以示宜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卫国,无可褒贬,故因而书世子耳。”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亦曰:
“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谓不以蒯聩为世子,而辄继立也,名之颠倒,未有甚于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辄之不当立,不当与蒯聩争国,顾名思义,自可得之言外矣。”
考察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尽管孔子的正名可以诠释为正一切事物之名,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①,但在“卫君待子而为政”这个特殊的语境里,在卫出公辄与其父蒯聩一国相峙的背景下,此处的正名主要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正君臣父子之名。此时卫国国君的家庭伦常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首先是蒯聩作为子欲杀母,与父卫灵公为敌,父子关系已经破坏;既而卫出公辄立为国君,以国拒父、父子对峙十余年,已经实质性地破坏了父子关系。由此可知,卫灵公、蒯聩、卫出公辄三代人,每两代之间都是父子伦常关系遭到破坏。这种特殊父子关系的破坏,直接影响到君臣关系。本来蒯聩为世子,如继承君位,则与辄的父子关系同时又呈现为君臣关系;而实际情况是子辄为君,而父蒯聩在外为臣,违背了子不敢臣父的礼制,造成了君臣关系的紊乱。因此,孔子的正名首先应当是端正父子之伦。
而在子路看来,孔子的正名是迂腐之举,不合时宜。毕竟卫出公已经在位多年,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还要去正名,势必会引起新的动荡。孔子对子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名不正”会导致一连串的恶果,首先会导致言语不能顺理成章,事业不可能成功,国家的礼乐制度随之废弃,从而刑罚不会得当,最终百姓惶恐不安,整个社会秩序陷入紊乱与动荡之中。事实上,后来卫国的局势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孔子的卓识体现无疑,反而是子路的浅陋最终丧命于这场父子争国的斗争中。
三、程朱理学的解读
唐宋以后,学者们大都认为孔子之“正名”意在“正父子君臣之名”,然而在具体处理措施方面,后儒有较大差异。宋代理学的兴起,为重新诠释孔子正名思想提供了契机,理学家们以《论语》与《春秋》为基础,对孔子之正名思想进行了解读,下面以程颐、胡安国、胡宏、朱熹为代表进行分析。
第一,程颐的理解。程颐认为父子争国破坏了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因而反对卫出公辄的做法,“伯夷、叔齐逊国而逃,谏伐而饿,终无怨悔,夫子以为贤,故知其不与辄也。”[4](P1145)同时他认为,“孔悝受命立辄,若纳蒯聩则失职,与辄拒父则不义,如辄避位,则拒蒯聩可也。如辄拒父,则奉身而退可也”[4](P123)。据此可知,不管是孔悝的助辄拒父,还是助蒯聩夺位,都遭到程颐的批判,因为这两种行为都直接破坏了蒯聩与辄的父子关系,乃是不义之举。那么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程颐提出:
蒯聩得罪于父,不得复立,辄亦不得背其父而不与共。国委于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从父则义矣。[4](P402)
程颐认为蒯聩首先破坏了与卫灵公的父子关系,因而丧失了立为国君的德性条件。而辄也不能对抗父亲,破坏父子之伦常,从这个角度而言,辄亦不能立为国君。对于辄来说,以身从父,即恢复父子关系才是天理,是合义之举。然而国不可无主,因此国君应另立合适之人,这个合适的人选在程颐看来是“郢”,他说:“公子郢志可嘉,然当立而不立,以致卫乱,亦圣人所当罪也,而《春秋》不书,事可疑耳。”[4](P123-124)程颐的解读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理学家们。
第二,胡安国胡宏父子的理解。胡安国问道程门后学杨时,继承了程门宗旨,以治春秋学而著名。他首先批判了卫灵公:
“世子国本也,以宠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国,以欲杀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是轻宗庙社稷之所付托而恣行矣。《春秋》两着其罪,故特书世子,其义不系于与蒯聩之世其国也。而灵公无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国本,至使父子相残,毁灭天理之所由着矣。”[5](卷二十九)
就这个事件而言,直接批评卫灵公的较为少见,胡安国剖析了事件产生的根源。在他看来,蒯聩杀母乃是因为其淫荡,而卫灵公又宠爱她,荒废国政,这是危害父子之伦的根源。
其次,他从三个不同伦理角色的角度批判了蒯聩。作为儿子,杀母是不孝;作为太子,不顾自己身上的责任而出奔则是轻国;作为父亲,人“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贵也”,而蒯聩则与子夺位,胡安国认为“蒯聩之于天理逆矣,何疑于废黜?”[5](卷二十九)他认为《春秋》经文之所以说“纳卫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乃是明其罪,而非表明其可继承君位,而称“纳”则表明“见蒯聩无道,为国人之所不受也”[5](卷二十九)。
再次,他批判了卫人,尤其是卫国大臣。《春秋》之所以称“世子”,乃是因为卫灵公生前并未正式废除蒯聩而另立太子,因而卫人不能拒之。而灵公卒后,卫人并未“谋于国人,数蒯聩之罪,选公子之贤者以主其国”[5](卷二十九),而是立辄为国君,客观上帮助辄拒父,破坏了父子关系。
最后,他批判了辄。“然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辄乃据国而与之争可乎?”[5](卷二十九)在他看来,无论蒯聩怎么无道,作为子的辄都不应以国拒父。总之,胡安国在此事上的基本原则是“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5](卷二十九)?据此,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是故辄辞其位以避父,则卫之臣子拒蒯聩而辅之可也。辄利其位以拒父,则卫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乌有父不慈,子不孝,争利其国,灭天理而可为者乎?”[5](卷二十九)
胡安国的最终处理意见显然与程颐保持了一致,并且进一步表明蒯聩与辄父子均违背了基本的伦理秩序,既然“父不慈,子不孝”,则父子均不可立为国君。胡安国不愧是宋明理学中治《春秋》之大家,其分析之深入与全面,鲜有及之者。其子胡宏继承了他的基本观点,在《论语指南》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蒯聩无父,辄亦无父,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尚可以事宗庙社稷,为人上者哉?故孔子为政于卫,则必具灵公父子祖孙本末,上告于天王,下告于方伯,乞立公子郢,然后人伦明,天理顺,无父之人不得立,名正而国家定矣。”[6](P312)
显然,胡宏的主旨仍然是“无父之人不得立”,认为如果孔子为政卫国,其正名首先必定是理清卫灵公父子祖孙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上告于天王,下告于方伯”的程序,从而回答了程颐的“国委于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的问题,即最终“乞立公子郢”。
第三,朱熹的理解。在《朱子语录》中,朱熹对此事有直接的阐述,如他说: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輙亦不当立,当去輙而别立君以拒蒯聩。”[7](P1100-1101)
“若就卫论之,輙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7](P1100)
“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7](P1102)
在这几段语录中,朱子首先肯定孔子之正名必先正君臣父子之名,进而明确指出蒯聩与辄父子相争,破坏了父子关系,因而均不得立为国君,并且推断“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最后指出国君应另立郢。在《论语集注》中他引用了胡氏②的说法:
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8](P142)
这一方案与胡宏的主张基本相同,朱子显然赞同这种处理策略。
至此,我们分析了程朱理学中几位重要理学家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解读,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无论是程颐,还是胡氏父子,以及朱熹,他们的基本观点保持了高度一致,那就是蒯聩与辄均有违背父子伦常的事实,均属于“无父之人”,而无父之人不可以立为国君,国君当立“郢”。
四、王阳明的诠释
在《传习录》上卷中,王阳明与弟子对这件事有一段对话,表明王阳明在此事上的基本观点。原文如下: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先儒主要是指前文提及的宋代理学家们。针对孔子的正名思想,王阳明提出了一种与程朱理学不同的解读。下面我们分析一下阳明的这一解决方案。
首先,王阳明认为孔子受到卫出公的礼遇,为“公养之仕”(《孟子·万章下》),亦即“一人致敬尽礼”。卫出公以礼相待,假设孔子为政就先去废除他,阳明认为不符合人情。并且当时孔子在卫国待过一段时间,考虑孔子基本上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而在鲁哀公六年,即卫出公四年,孔子自陈入卫,到鲁哀公十一年归鲁,大概待了五年左右,据此可知孔子基本赞同卫出公的治理国家,废除国君显然有违天理。
其次,王阳明提出了正名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孔子必然要以父子亲情感化卫出公,让他知道“无父之不可以为人”,父子之爱,本于天性。因此,卫出公必要迎父亲蒯聩。如果辄能够真诚恻怛,迎回父亲,并且“致国请戮”,则蒯聩必感动,加上孔子调和其间,则绝不肯受国,仍然命辄为国君。这样便出现了类似伯夷叔齐兄弟让国的理想情景。
最后,协调君臣父子关系,实现正名的目的。王阳明认为,卫国在卫出公的治理下已经基本稳定,因此群臣百姓“必欲得辄为君”。而辄从父子亲情角度来考虑,则必不肯,而是希望致国于父;而蒯聩则与群臣百姓深表辄的仁孝与悔悟,希望辄复君卫国。在此情形下,王阳明提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辄不得已尊父命仍为国君,但子不敢臣父,所以尊父为太公,备物致养。至此,君臣父子之名各得其正。
诚然,王阳明的这一解决方案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现实中各种利益纷争显然难以如此理想化地解决,然而他以“无父不可以为人”为主旨,又确实遵循了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考察王阳明的解决方案,只有孟子设计的舜窃父而逃的理想方案与之有几分近似。③
五、理论分歧:情理与义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王阳明与程朱理学对孔子“正名”观念的不同解读,显然,两者都认为正名主要是正君臣父子之名,蒯聩与辄都破坏了父子关系,造成父不父子不子,家庭伦常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具体到处理方案上,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那么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何处?其思想根源何在?
首先,王阳明的“无父不可以为人”与程朱理学的“无父不可以有国”。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父母,这是人伦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因此,他始终强调“人”的成立,即成为一个伦理上适格④的人。人的任何其他社会角色都是建立在适格的人这一普遍性基础上,只有首先“成人”,才可能进一步靠近理想的圣人人格。是故,王阳明提出的解决方案始终是以普遍性人格为基础,而没有跨越到特殊的治理者人格层次。程朱理学则强调国君这一特殊身份的合法性,尤其是伦理上的适格。既然君主自身的伦理关系都出了问题,则不能为君。比较两种解决方案,程朱理学所设计的方案显然有不足:其一,卫出公辄的继位按照周朝礼制本是合法的,因为郢拒绝为君,则辄与郢的关系由伦理上的侄儿与叔父的关系转变为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已经持续了数年。“废辄立郢”显然颠倒了已有的君臣关系,造成新的名实紊乱。其二,这一解决方案最终忽略了蒯聩与辄父子关系的恢复⑤,胡安国甚至提出了“辄辞其位以避父”的处理方案。既然蒯聩与卫灵公之间的父子关系已经破裂,且随灵公的去世而无法弥补,孔子人依据人之本性阐发人伦的重要⑥,主张正名,岂能放纵现实父子关系的继续破坏而不挽救呢?胡氏父子以及朱熹的解决方案显然缺乏对亲情伦理的恢复与重建的考虑。是故,王阳明认为他们的解决方案不合人情,不合天理。
其次,王阳明的“无父不可以为人”与程朱理学的“无父不可以有国”的背后是情理与义理之分,体现了心学与理学的不同道德本体思路。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人的各种情感无不是本心所发,从人的基本情感出发来阐述天理,则天理不外乎人情。父子之爱是人之真实情感,即“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9](P26),因而现实的父慈子孝完全是发自人的内心,是良知的呈现,而非外在的规范制度来促成。既然情由本心所生,本于良知,则阳明主张尊重这种人情以及本于人情的基本伦理关系。是故,他主张首先要唤醒父子的真实情感,促成父子关系的恢复,维护这一基本人伦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国家政治关系的建构。
程朱理学则普遍强调了“义”的重要性,这里的义指符合各种礼仪规则,包括国家政治方面的诸多理则,如君主的合法性。万物皆有其理,让万物皆当其理,则是义,“义”本质上强调了对普遍天理遵循。在蒯聩与辄父子争国这一事件上,从程颐到朱熹,处理方案的核心词是“义”与“天理”,即都强调父子相争的不义,违背天理。在他们看来,父子关系本有其天理所在,父慈子孝才是天理,违背此天理,则丧失了成为其他角色的基础。从天理出发,他们强调国君这一特殊角色上的天理,即作为国君首先必然要遵守家庭伦常,如果破坏了家庭伦常之理,则丧失了承担政治角色的资格。
总之,不管是王阳明还是程朱理学,都实质地遵循了儒家内圣外王的逻辑,即主张修身齐家的内圣功夫对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具有优先性,个人德性之修养对于成为一个合适的君主具有优先性。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主张符合人之本性即是符合天理,人情是良知的真实呈现,最终确立了道德行为中人的主体性。而程朱理学则着重强调天理不可违背,以天理来规范人的情感与行为,强调各种道德行为中天理的客观存在,只有遵照天理,才是“义”,这就使得天理以及“义”的说法始终有一种外在超越性,甚至可以说是威严性。尽管程朱理学亦强调道德修养中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然而普遍性的天理之网又最终架空了道德主体的自由选择。这种倾向在处理国家政治事务上,则明显体现为对个体的忽视,对国家的偏重,政治中的正义理性超越于个人的情感理性之上。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程朱理学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都强调君位的适格,而几乎不约而同地忽视了父子关系的恢复与重建。
六、现实分歧:大礼议中的不同态度
如果说王阳明与程朱理学在解读孔子正名思想上的差异还只是彰显了理论上的分歧,那么我们不妨看看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明代大礼议活动中的现实分歧。
明朝嘉靖年间,刚即位的明世宗朱厚熜因其生父尊号问题,亦即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的问题,与以杨廷和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产生了争议与斗争,历时三年(1521年至1524年),史家谓之“大礼议”。大礼议的发生首先当然是因为明武宗无嗣,而其父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因而只好从明孝宗兄弟辈中寻找后继者,而朱厚熜正好是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具备合法继承性。明世宗继位后,随即面临着如何称呼自己生父生母的问题。于是,世宗命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礼部尚书毛澄上奏曰:“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10](卷191)据正统程朱理学的观点,则要以明孝宗为皇考,世宗生父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然而,这种主张显然不能让明世宗满意。
那么王阳明在此次大礼议中态度如何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大礼议中来,但阳明的很多学生与友人均牵涉其中,尽管王门中亦有分化,如邹守益即持不同的观点,但总体上来看,王阳明的立场显然与杨廷和、毛澄所持观点相反。他在回复邹守益的书信中写道: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一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实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焉。[9](卷6)
王阳明的出发点仍然是一个“情”字,此人情乃是人的真实情感,是人之本性,亦即良知之呈现。礼制当然要遵循情感,完全违背人情的礼显然不可能适用,也不是天理。因此,礼制是否合适只需“反之吾心”,此心即纯乎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具体到大礼议,明世宗与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任何礼制也无法否认与忽视的;从情感上说,他也不可能真正地做到认亲生父母为伯父母。世宗虽然贵为皇帝,然仍有他自己的家庭,首先他是作为父母之子,然后才是天子。以家庭伦常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皇帝这样的尊贵政治地位,明世宗也不愿意。是故,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尽管初临君位,势单力薄,但明世宗仍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他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最终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显然,这种妥协已经预示着大礼议的最终结局。三年后,明世宗羽翼丰满,高压反弹,更加上一些先前遭贬斥的旧臣拥护,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后来又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最终取得大礼议的胜利。
诚然,大礼议不是一次简单的礼制上的争议,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这一点史学界研究颇多,无需赘言。然而放置在儒家思想层面来看,我们自然也不能忽视这场争论背后的思想分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大礼议的根本动机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如何,都不该忘记,至少在形式上,那仍是一场以儒家内部不同观点为背景的学术论争”[11](P78)。
至此,从理解孔子正名思想上的理论差异,到大礼议中的现实分歧,王阳明与程朱理学在道德本体上的分野十分明显。有学者指出,用“人情”和“天理”这样一对概念来大致区分王学与朱学,仍有其客观的意义,综观议礼两派的理论基础,大礼议实际表现为一种“天理”与“人情”之争,说穿了,便是作为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王学之间的斗法[11](P78)。这种论断大致不错,但严格说来仍略显不足,即容易产生误解,似乎程朱理学不重视人情,而阳明心学不注重天理。本文标题概括为“情理”与“义理”,旨在表明,王阳明的心学在“心即理”的命题下,从人的情感出发来诠释天理,天理不外乎人心,符合本心良知的即天理。简言之,从人情到天理。程朱理学强调万物之理的普遍性,理一分殊,物各当其理,也就是符合总的天理,也就是“义”,因而天理具有外在超越性,规范性,以天理规范人情,则人情得以发而皆中节。[12]简言之,从天理到人情。
注释:
①董仲舒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鹢之辞是也。”朱子《论语集注》引谢上蔡之言曰:“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由此可知,孔子之正名已经具有普遍意义。
②此胡氏究竟是谁,实难得知。陈荣捷先生认为胡安国、胡寅、胡宏三个人最有可能,而据朱熹所引,则似指胡安国或胡寅,而据三胡留下的现有文本来看,则胡宏在《论语指南》中的一段话与朱熹所引大致相当。参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81页。
③钱穆先生认为:“惟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之而逃,视天下犹弃敝屣之说,乃为深得孔子之旨。”参见《孔子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6页。
④“适格”本为一个法律概念,指当事人能够成为某一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承受者的资格,本文借此概念表达应当满足一些基本条件才能成为伦理上合格的人。
⑤程颐提到了“身从父则义”,但仍然没有重点强调父子关系的恢复。
⑥《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非不知攘羊不对,此不涉及是非判断,而是从伦理角度,儿子告发自己的父亲显然不符合人的真实情感,会破坏父子之伦,孔子从人之本性角度来阐述父子相隐的合理性,反对破坏这一人伦关系。
标签:王阳明论文; 孔子论文; 程朱理学论文; 卫灵公论文; 儒家论文; 大礼议论文; 春秋论文; 国学论文; 心学论文; 卫国论文; 胡安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