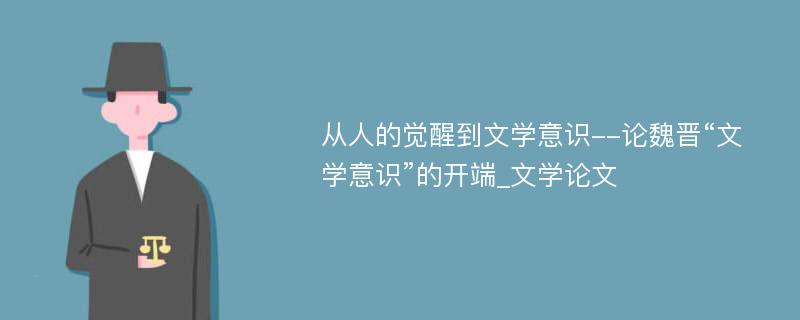
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文学论文,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文学自觉时代是从魏晋(含汉末建安时期)开始的。这种说法最早由鲁迅先生提出,见于他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章原是1927年七月在广州的一次演讲的纪录,“文学的自觉时代”用了引号。此前,即同年三月,日本弘文堂书房出版了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其中第二篇第一章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话是否引自铃木氏的《中国诗论史》,现已无从验证了。
一
现在学界有少数学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应该从魏晋上推到汉代,也即是说,汉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早已进入独立、自觉发展的阶段。这种看法当然可备一说,但我以为他们列举的理由或根据似乎并不充分,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
譬如说,他们将汉代文人已明显分为“文学之士”(主要指儒生)和“文章之士”(主要指文学家)作为文学独立的确证之一,这就很值得商榷。尽管汉代确立的“文章”的概念一直影响到后世的文学观念,但“文章”的涵义与文学毕竟还有较大的距离。汉人说的“文章”实际上包括了辞赋、史传、奏议三大文体,其中纯粹属于文学的只有辞赋;作为文学大宗的诗歌并不包括在内,这在素有诗国之称的中国,谈文学而忽略了诗歌,总是不应有的一种缺陷吧。到魏晋时,人们谈论“文章”则明显包括了诗歌,且将诗赋、铭诔、奏议、书论等体式分为两大类: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还指出诗赋的美学特征在一个“丽”字。〔1〕当然,诗赋还不能涵盖全部文学, 但诗赋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文学的主体,具有代表当时文学的资格却是毫无疑义的。魏晋人将诗赋与史传和其他应用文区别开来,比起汉人对文学的认识,不仅更贴近于文学的本质,而且开始注意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这应该是对文学本质认识的一大突破。再说,汉人即使有了“文学”与“文章”的划分,但在他们的观念中,文学并未从儒学附庸的地位独立出来。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诗歌上,如当时《诗经》被抬高到“五经”之一的神圣地位,汉儒的“诗学”就是经学的一部分。他们对于楚辞的理解和评价,用的也是经学的眼光和标准。汉代诗坛十分沉寂,《诗经》那种以四言为主的诗体衰落了,句式比较灵活的骚体也难乎为继,新兴的五言诗直到儒学式微的汉末才趋向成熟,其中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经学对于诗歌的束缚,诗歌创作未能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不能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主张汉代文学已经独立,并进入“自觉的时代”的另一个理由或根据,是认为汉代出现了“专业”的作家队伍,被列举的专业作家有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刘向、扬雄等。这里说的“专业作家”本身就不准确,因为莫说汉代,就是魏晋以后的漫长封建时代,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职业的作家是不多见的,除了隐居山林(或田园)和流落市井的少部分人,大多数作家还是以仕宦为主,文学创作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副业”而已。汉代的确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文学集团,先是某些诸侯王,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他们仰承战国的养士遗风,或“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或“招宾客著书”〔2〕; 在闻风趋慕的游士中,确有一批游士兼文人的知识分子(如邹阳、枚乘、庄忌、司马相如等)。这些人聚在一起著书立说、竞写辞赋,促进了楚辞向汉赋的演进。汉武帝践阼之后,更是罗致了一大批言语侍从之臣,养在宫中,“朝夕论思,日月献纳”〔3〕。而公卿大臣中如倪宽、 孔臧、董仲舒等,也善辞赋,时有所作。这个阵营可观的宫庭文学集团,是汉武帝大兴礼乐,为“润色鸿业”的政治需要而拼凑起来的。就是这样一群作家,除枚皋外,大多都有官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作家。这些人有两大特点:一是唯皇命是从,“上有所感,辄使赋之”〔4 〕,或“有奇异,辄使为文”〔5〕, 他们的创作是帝王心意的传声筒,揣摩主子的心思意态成了他们创作的唯一目标。这种毫无主体意识的创作,能有文学的独立可言吗?有可能写出富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品吗?所以如枚皋之流,虽作赋百余篇,却没有一篇流传下来。二是作家身价地位卑微,帝王固然视若俳优,旁人或他们自己也觉得“如倡”、“似优”。辞赋被看成“俳”,赋家的身份与倡优、滑稽、博弈之徒无异,仅供帝王娱悦耳目而已。当时连司马迁这样地位不算太低,也不以辞赋为专业的朝官在《报任安书》中竟也沉痛地感到自己(一介文士)“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辞赋创作宛若“雕虫篆刻”,被人视为“小道”。文人作家如此屈从于封建权势,受到社会上下普遍的贱视,不具备起码的独立人格,这种文学不可能按自身的规律健康而独立地发展,那又何来“自觉”可言呢?
其实,如果因为汉代出现了以言语侍从为主的宫庭文学集团就断言汉代文学已跨入独立、自觉发展的时代,那么,这个独立、自觉的时限还可推前至战国;因为战国后期,至少在楚国就已存在一个以侍从文人为主的宫庭文学集团了。其中著名的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这些人都有“楚大夫”的头衔,比汉代的宫庭文人体面得多。虽然没有实际的权力,但也因为做着体面的闲官,有着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比之汉代的宫庭文人,无论如何要多几分创作上的自由。所以,不能因为汉代出现了这类宫庭文学集团就断言汉代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
至于汉人的文学观,无论是对文学本质和特征的认识,还是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都尚未达到“自觉”的程度。一是当时关于文学的言论,大多仍散见于其他论著之中,多属零星片断之谈,或是阐释诗赋的“序”、“传”,真正在形式上独立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专论还极为罕见。二是这类言论基本上没有超出经学的大范围,儒家的诗教原则——一种服从于封建实用功利的文学观仍占压倒的优势;重视个体人格、追求个性解脱的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思想)在儒学一统天下的汉代被压抑了四百年之久。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带上经学色彩的时代氛围中,即使有个别论及文学自身特性和规律的言论,一般也是极简略、极肤浅的。真正探讨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专论,那是到魏晋时才有的事。
文学“自觉”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要认清这一历史转折的轨迹,除了微观的定量分析,还要从宏观上对当时文学发展的环境和趋势作总体性的把握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断。
二
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而在汉代,文学本身以及文学理论批评都未曾挣脱经学的束缚,奉命文学、帮闲文学乃是文学发展的主潮,作家缺乏创作的独立自主精神,艺术上的追求和新变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有汉一代,诗坛显得十分沉寂,辞赋(堪称汉代文学的代表)创作从它的兴起到繁盛,都离不开帝王的提倡和扶持,具有宫庭文学的鲜明特征和“润色鸿业”的总体倾向;尽管实际上它并不那么适合封建正统的胃口,但表面上还得卑屈地夹一条微不足道的“讽谏”尾巴,以标榜它对儒家诗教的皈依。汉人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和探讨,大体上还停留在文学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政治教化)的关系上,与先秦时代相比,主要表现为更理论化。至于文学自身的艺术法则和创作规律,人们还很少顾及,偶有涉猎,也多是只言片语之谈,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概念的清晰度。
文学的“自觉”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因为艺术的创造,从来就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创作主体的相对自由,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发展。这一点,只有历史的车轮进入魏晋之后才有可能。
汉代社会是结束战国的“百家争鸣”而集权一统的时代,儒学独尊,经学成为压倒一切的官学,维护封建统治,以宗法群体意识和等级观念为内核的礼法名教被推崇到至尊至显的地位,先秦时代兴起的其他学术派别被视为异端,道家强调的自然哲学和个体意识长期受压。虽然随着西汉王朝的崩溃,反传统的异端有所滋长,如桓谭、王充的思想,已孕育着、引发着主体精神的萌芽,但只有到东汉末年社会大乱,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冲垮,其他思想才有可能迅猛地发展。尤其是“庄”学的复兴,成为汉魏之际思想解放潮流的一面大旗。风靡魏晋南朝数百年之久的玄学,实际上主要就是“庄”学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它吸收儒学的某些成分,抛弃先秦“庄”学那种大而无当的空想,正视现实人生的种种复杂问题,尤其注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的思考,力求从整体上调和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并对个体人格作出既是本体论的解释,也是现实性的把握和抉择。这种人格的价值取向,在传统儒家看来,不能不具有强烈的挑战意味。
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具体表现在对生命个体的价值评判上,这种新的价值判断与传统的价值观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物品鉴上,“德”的标准越来越淡化。
汉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格外受到尊重,正如曹操所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6〕儒家素来标举以“德”取人;曹操出于现实利害的考虑,大胆起用那些地位卑微,“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甚至是“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7〕的能人,公开打出“唯才是举”的旗号, 向儒家传统的“仁”、“孝”之类道德教条挑战,最能反映人的“本质力量”的才能智慧被推崇到空前的高度。刘劭的《人物志》就是在这种品鉴人物的新观念、新标准影响下产生的人才学专著。他在该书序中公然宣称:“智者,德之帅也。”将人的智慧、才能提到用人标准的首位。这种观点在徐干的《中论·智行》中也有所反映:“圣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汉高祖数赖张子房权谋以建帝业;四皓美行,而何益夫倒悬?”认为历史上那些成大业的人都是靠的真本领,徒有德行虚名,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渴求人才,人的智慧才能得以大放光采的时代;而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以及儒学自身的僵化,也为人才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传统的道德教条的失落,更能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才能、智慧的倍受青睐,正反映了人对自身价值的新认识、新觉醒。
玄学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人们对社会人生和自我价值作更深层的理性审视,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找到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确认理想的人格就在人自身展示出来的智慧和风采。因此,对人物的品鉴,不仅继续强调汉末建安以来标举的才能,而且直接对人的风姿神采表现出由衷的赞美。
“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8〕丞相王导对儿子王恬(字敬豫)的遗憾是才不称貌。 换句话说,如果姿容俊美的王恬才能出众,那就达到理想的极致了。说明当时被看重的是人本身的智慧和容貌举止中焕发出来的人性之美。而原先看重的品德,在魏晋的人物品鉴中则明显地被淡化了。一部以反映魏晋风度驰名的《世说新语》,虽然首列“德行第一”,但其中记述的故事,有些并不符合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在“德行”之外,设置了更多的门类(如“言语”、“文学”、“识鉴”、“赏誉”、“品藻”、“捷悟”、“夙惠”、“容止”、“企羡”等),从不同方面展示了魏晋所标举的才性之美,对人的智慧和生命表现出一往情深的叹赏。人们对人性之美的企慕,有时竟到了倾倒、着迷的程度。与此同时,“德”的观念则普遍地淡薄。这是个体意识高扬,人的自身价值被发现,从而推动了人的觉醒的重要标志。
第二,强调个性和个性自由。
在我国历史上,道家学派最早阐扬自然哲学。《老子》一书认为,至高无上的“道”,其本质特征就是“自然”,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各自都有一个自生自化的过程,故主张“无为”。所谓“无为”,实际上就是提倡尊重万物各自的个性,反对形形色色的掩盖和扼杀个性真实的伪饰。可见,“自然”一词的原始含义与自由是相通的。《庄子》一书较少使用“自然”一词,因为《庄子》一般不在探讨宇宙本源,而是在论证人性问题时谈到“自然”,故常常用“真”来替代“自然”,以之对抗一切约束、破坏人性真淳的社会规范——“伪”(包括儒家的礼法名分在内)。庄子的理想人格就体现在能够永葆自然天性的“真人”(或称“至人”、“神人”)身上;这与儒家理想的人格化身“圣人”,是针锋相对的。总之,先秦道家所说的“自然”、“真”、“朴”、“淳”等概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其所强调和标举的是一种对抗儒家礼法名分的任真率性的个性。
“真”与“伪”的对立发展到魏晋,首先表现为“自然”与“名教”的论争。这是道家思想重新抬头,高举个性主义旗帜不可避免的一场论战。尽管名教一度受到司马氏篡权集团的支持,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当时高举“自然”之旗向名教开火的人确实表现了惊人的勇气。他们声称“不崇礼制”、“礼岂为我辈设?”〔9 〕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10〕,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踏名教,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11〕。这种对抗名教的行为常常表现为某种近乎歇斯底里的狂热和怪诞: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或纵酒放达,与群猪共饮;或脱衣裸形,自谓以天地为栋宇。这种极端放纵个性的行径,尽管有乖常情,但不能不是汉儒标榜的名教的失落,个性解放的思潮不可抗拒的特定历史的产物。
魏晋风度,其实就是标榜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潇洒。当时的人,不像儒家认为的那样,个人价值要通过功名的追求去实现,而是把功名富贵看成扼杀个性才情的桎梏。嵇康有诗云:“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12〕“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13〕“肆志”、“纵心”指的就是冲破功名、富贵、荣禄等羁縻人的个性的身外之物而获得的精神上的自由感。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也说:“人亦有言,称心是足。”〔14〕“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15〕“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16〕将儒家看重的“名”视若浮烟,认为“称心”(精神上的自由)是人生的最大满足。玄学家们常说“体玄适性”,“体玄”或曰“体道”,指超越世俗功利而与“道”同一;“适性”则谓精神上的逍遥、洒脱。这是魏晋人从现实苦闷中解脱出来,重新认识自我,恢复真我的一种新尝试,尽管也有某种理想的成分,但比之先秦道家那种近乎梦幻的逍遥,毕竟要实际得多。
三
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无论文学理论批评或是文学创作,都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
文学主体精神反映在当时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就是对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进行了多方面的审视和思考,从而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飞跃到一个新的段段,其涉及领域之广,探究底蕴之深,审视角度之新,创获成果之丰,不仅超乎先秦两汉之上,就是与后来的隋唐相比,也决不逊色。这一点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可,这里无须详述;只想就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中与个体意识或主体精神直接相关的问题略陈管见。
(一)文学抒情功能的重新强调和发扬
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志”和“情”两个概念常常是交织或相通的。“志”可以指整个内心世界(情亦包容其中),也可以专指志向抱负或具体的“情”。本来,诗歌的抒情功能在秦汉以前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儒家诗教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对诗歌的感情问题论述不多。《毛诗大序》曾讲到诗歌“吟咏情性”的问题,但在肯定“发乎情”之后又特别强调“止乎礼义”的重要。这是用儒家的政治、道德原则去规范、限制诗歌感情的表达。显然,这是荀子“以道制欲”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对诗歌表达感情的丰富性,无疑是一种强制性约束,带有封建功利的鲜明色彩。儒家这种诗教观对于汉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诗》、《骚》开创的抒情性传统,到汉代已十分微弱,有汉一代举不出一个像样的诗人,就足以说明抒情文学的衰落。随着汉末社会大动荡、儒家思想失控而带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的抒情功能才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抒情小诗的崛起,在当时是那样震撼人心,后人亦惊呼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这倒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太多的惊人之处,它的轰动的艺术效应,其实主要就在“善言情”〔17〕。从内容看,它所吟咏的不过是游子、思妇之类世俗之情,但真率自然,表现了对人生短促的清醒认识,对世事多艰的失意喟叹,对现实人生的无限依恋,调子虽然感伤,却充满了对传统的观念和信仰的怀疑或否定,与汉魏之际思想解放的潮流互为呼应,因而成为震撼人心的时代强音。这是人的觉醒引发文学“自觉”,文学主体精神注入诗歌而获得的重大成功。
谢灵运说:“诗以言志,赋以敷陈。”〔18〕其实,“敷陈”仅只是汉代大赋的艺术特征;随着汉王朝的衰落,大赋也呈江河日下之势,一种文辞清丽、体制短小的抒情赋应运而兴,魏晋南北朝正是抒情小赋大盛的时代。从艺术上看,抒情小赋实在是向楚辞的回归,许多作品应归于抒情诗的范围。魏晋南北朝不仅是五言抒情诗绝唱诗坛的时代,也是抒情小赋称雄赋坛的时代。抒情文学如此发达,难道不是因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附庸,致使文学主体精神长期受压而作出的一种符合逻辑的反弹吗?
文学创作中抒情功能的强化,反映到文学理论的研究上,就是陆机《文赋》中对诗歌特征的新概括:“诗缘情而绮靡”。这是对《诗》、《骚》开创的优良传统和魏晋诗歌创作实践的科学总结。“诗缘情而绮靡”,不仅将“情”从“诗言志”的“志”中凸显出来,看作诗歌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大胆地摆脱了《毛诗大序》的“止乎礼义”的说教,代之以“绮靡”这一体现诗歌艺术本质的美学特征。这里,“绮靡”不仅是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也是对诗歌总体风貌(甚至包括诗歌所表现的感情本身)的规定。这是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一次大解放,符合历史潮流的总趋势,也是汉末建安以来,五言抒情诗蓬勃发展,显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从而要求诗歌理论给予认可的历史必然。
(二)文学题材的大开拓
魏晋时代,文学主体精神的解放和弘扬,有力地促进了文学题材的开拓。以诗歌为例,魏晋以前,诗歌表现的空间基本上还限于社会生活的领域;魏晋以后,诗歌突破原有的题材范围,将艺术触角伸向以山水为主体的自然界,实现了中国文学题材的一次大拓展。山水诗和其他山水文学的兴起,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辟出了一片大展才情的新天地。这一题材上的大突破,其实也只有在人的个体意识大觉醒,文学主体精神得到弘扬的历史氛围中才能实现。
魏晋人追求个性和精神的解脱,直接受到玄学崇尚自然的时代思潮的启导。玄学的自然观与先秦道家的自然哲学虽是一脉相通的;由于时代不同,彼此的认识和理解也有显著的差异。先秦道家强调的是个体的精神超越,明显带有空想的性质;魏晋玄学则更关心将理想化为一种可行的现实追求。在魏晋人的观念中,“自然”既是一个广义,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具体指某种理想的生活境界,如世俗社会之外的山水胜境,就体现了自然之道的精神。因此,人们要想实现个体与“道”的沟通,获得身心的真正解脱,最理想,也是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投身到大自然的山水中去。当时上层社会中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教养的人在玄学感召下走向山林湖海,客观上为山水美的开发并转化为文化的形态准备了人文方面的条件。以山水为题材的山水文学的兴起,正是那时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脱的时代思潮、文化趋势与江南优美的自然山水相契合的产物。
田园诗与山水诗一样,也是在崇尚自然的思想的催化下产生的。它以冲决“樊笼”、“尘网”,追求个性自由为先导,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辟出了又一片广阔的天地。田园诗的开山祖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里,“自然”与“自由”是相通的。“矫”指造箭时用的一种正曲使直的工具;“厉”是质地较细的磨刀石,可以磨利刀刃。“矫厉”组成复合动词,实指人为的加工。正是这种人为的加工,才使原物失去自然的形态。显然,在陶渊明笔下,“矫厉”与“自然”正相对立,其义相当于“伪”与“真”的矛盾关系,反映了“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追求个性解脱的理想和愿望。陶渊明有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9〕他把自己比作锁在笼中的鸟儿,视黑暗的官场为鸟笼,而他所追求、向往的“自然”显然含有双重意思:既指具体的农村园田,也指抽象的精神上的自由解放。陶诗中常常出现酒和鸟。萧统说他的诗篇篇有酒,未免言过其实;据他现存的一百余首诗统计,大约有五十多处写到酒,三十余处出现过不同形象的鸟。他戏称酒为“忘忧物”,说酒能“远我遗世惰”、“忘彼千载忧”。其实,酒对他的作用就是使他暂时麻醉,忘掉世事烦扰,保持心灵的自由平和,反映了诗人渴求精神解脱的苦闷心理。鸟在陶诗中是作为艺术形象出现的,是被“人化”了的自然物,如“高鸟”、“羁鸟”、“失群鸟”、“倦鸟”、“归鸟”等,实为诗人在不同环境中思想感情的艺术再现,充分反映了诗人向往自由解放的情怀。
总之,自然山水和农村园田是魏晋时代人们追求个性解放所向往的两片“净土”,现在看来,尽管带有理想的色彩,但毕竟还在现实世界的“此岸”,不像庄子的“无何有之乡”那样虚幻。况且,魏晋的文人作家确实亲临其境了。没有这种对理想的热切追求,没有亲身的体察和感受,就决不会有山水、田园诗派辉煌时代的到来。
(三)对艺术表现方法的探究
魏晋时代,文学主体精神的觉醒和高扬如何推动了文学自身的艺术方法的更新和改善,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他们彼此对立,但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又是互为补充的,构成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博大精深的总体。然而,也应该看到,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特色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道家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哲学派别,他们从本体论的高度研究了人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种种关系,审视了人自身的本质和价值,力图将人(自我)从社会的各种规范和自身的物欲情累中解放出来,达到与“道”同体的逍遥之境,获得精神的解放和自由。老子和庄子的言论的确很少直接谈到美和文艺,偶有涉及,也多持否定态度;道家(主要是庄子)对于中国文艺美学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道家思想对后世美学思想、文艺理论的启发性、暗示性以及后人受其启发、暗示而作出的创造性发展。这种影响和接受之所以能在美学上大放异彩,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中结出丰硕之果,实因为在老庄的哲学体系中,本来就蕴涵着某种独特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常在其论“道”或体“道”的言论中自然地闪现出来,与真正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境界不谋而合。而魏晋,正是接受老庄哲学的启发、暗示,并结合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譬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引起广泛注意的言意、形神关系的研讨和论争,虽然焦点仍在哲学或思想的领域,但对当时的美学和文艺创作的震撼也是不可抵估的。言意问题的提出始于《老子》(五十六章)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进一步阐述了“言不尽意”的思想,并提出“得意忘言”的主张。魏晋人从这些言论中得到启示,并结合《易经》的“象”加以变通,创造出“得意忘言”的新理论:意→象→言,这样就把言意问题的讨论引向文学语言、文学形象的思考中。人们从中得到启发,开始意识到抽象的精神活动,总是要借助一定的物质的、有形的东西才能表现出来;而有形的物质性的东西又总是具体的、有限的。文学艺术在表情达意上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与文艺表现手段的物质性、具体性、有限性势必产生某种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启发并推动历代文学家们不断地进行探索,力求通过文学的有限的语言手段去表现无穷丰富的内容,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创作出言简意赅的佳作。言简意赅不仅是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也是中国文学最富民族特色的一个美学范畴。
形神问题原本是《庄子》中关于哲学本体的一个论题。到东晋时,慧远提出“形尽神不灭”的观点,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论争。也就在差不多同时,这个论题被移植到文学艺术的理论和创作中来,孙绰有“艺妙者以入神”〔20〕的言论,顾恺之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以及“传神写照”的经验之谈,都已初具理论的形态。它要求文艺创作在刻划形貌上要“切状”,在揭示对象的内在精神上要“传神”,形神兼备是艺术形象的最高境界。这无疑也是我国最富民族特色的审美理论。至于唐以后形成的意境理论,实际上也是受到与形神理论密切相关的虚实相生的理论的启发(同时还借鉴了佛学唯识学关于识与境的关系的理论和概念),在总结诗歌(尤其是山水诗)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的。
总之,魏晋以来关于文学创作本身的艺术规律的思考和探索,一般是在人的觉醒的时代思潮的推动下,文学主体精神得到弘扬而作出的反观和自审。这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关于文学内在规律的重要研讨,往往是在先秦道家哲学的启示下展开,并根据创作实践提供的新经验,不断引向深入,最终形成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法则和审美理论。这些理论的要旨是如何通过有限的艺术手段去表现对象的无限丰富的内容,达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抽象与具体在艺术上的辩证统一。魏晋南北朝四百年,虽然没有产生像唐代李白、杜甫那样顶尖的大家,但如果没有这四百年的艰苦探索,勇于创新,将前人的哲学思考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理论和创作实践,就决不可能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我们常说先秦是哲学辉煌的时代,唐代是文学昌盛的时代,都常常有意无意地贬低魏晋南北朝,殊不知正是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完成了哲学与美学的沟通,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这段文学建立的殊勋。
注释:
〔1〕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
〔2〕《汉书·地理志》。
〔3〕班固《两都赋序》。
〔4〕《汉书·贾邹枚路传》。
〔5〕《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6〕《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7〕《举贤勿拘品行令》。
〔8〕《世说新语·容止》。
〔9〕《世说新语·任诞》。
〔10〕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11〕嵇康《释私论》。
〔12〕《赠秀才入军》之十八。
〔13〕《与阮德如》。
〔14〕《时运》。
〔15〕《饮酒》之十一。
〔16〕《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17〕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18〕《山居赋》。
〔19〕《归园田居》之一。
〔20〕《文选》卷五十六《新刻漏铭》李善注引《孙绰子》。
标签:文学论文; 魏晋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儒家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