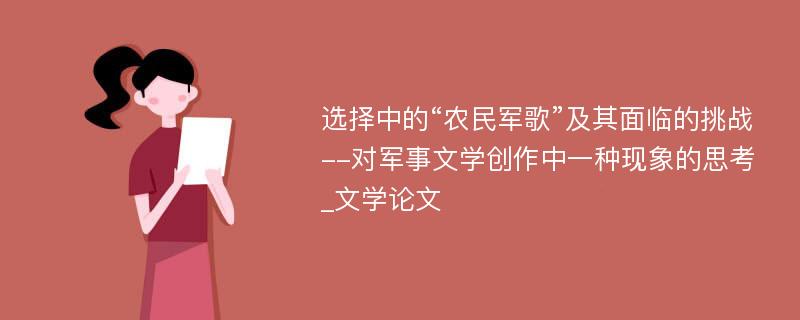
选择中的“农家军歌”及其面临的挑战——对军事文学创作的一种现象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歌论文,农家论文,文学创作论文,现象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初期逐渐兴盛的军事文学,在经历了不到10年的辉煌和繁兴之后,终于在商潮不断涌起和冲击的情势下,不情愿地步入了低谷期,而其曾经出现过的头绪众多的创作现象以及倾向分明且齐头并进的创作流脉,也是显得日趋冷寂、单薄和黯然失色了。那个时期所形成的军旅文学队伍在浮躁之风的吹拂下,开始由轰轰烈烈的集团冲锋、兵团作战转入了更为务实的单兵操练和游击式运作。这个判断并非出自故弄玄虚的目的——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的热度过高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发展的正常状况,倒是人们不再为某种文学现象激动不已的客观现实却恰恰说明了社会经济生活已步入正轨,——我想强调的是,同那个时期所形成的军事文学创作的某个流脉相涉、而其自身又有特别倾向的一种文学现象,在现今显得冷清的局面中,反而以醒目的姿态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假如我们顺着这个文学现象追溯到新时期军事文学发韧之初,便会发现它一开始就是由一些农裔军旅作家造成的。“农裔军旅作家”的概念是否准确或者是否带有杜撰色彩并非紧要,因为它主要基于借指的思考。譬如,相对于那些从小生长在军营尔后又服役于部队“军干子弟”的作家——诸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等,在军旅文学队伍中,还有一个人数不算很少的农家出身尔后参军尔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群体——最早奠定名声的李存葆、刘兆林、唐栋、李斌奎等人,后来崛起的周大新及至近几年出道的阎连科、陈怀国……军装虽然把这些农家子弟整齐划一地列入军旅方队之中,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用以观照生活和审视军营的方式,而且显然是不同于“军干子弟”作家群的方式。
李存葆之于《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唐栋之于《雪线》中的汪哈哈,周大新之于《汉家女》中的汉家女……一律是军人与军人——农裔军人写农裔军人。他们熟悉农村,也熟悉军营,更熟悉从农村步入军营的军人。在一种责任感和生活负重意识的驱使下,他们以旺盛的热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质朴淳厚、勤奋诚恳而又不时为来自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所困扰的军人形象。同那些经常以豪气十足、孤傲清高的城市兵或者“军干子弟”兵为主要观照对象的“军干子弟”作家相比,他们在军营这块土地上有着更为广阔的选择余地,其原因不言而喻——无论军官还是士兵,这支军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来自农村,这在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国度中,是极为自然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农裔军旅作家置身的环境中,生活着大量与他们自身的境遇、感情、观念以及生存方式极为相似的“战友”。因而,在整个八十年代,塑造农民出身的军人形象成为军事文学创作的一大景观。
尽管十多年的历史进程已经为这一文学现象烙下了不同的印迹,但它毕竟以题材与人物的相对一致性持续下来了,而且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军旅作家赖以生存的环境看,社会经济生活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影响到军队成员结构的基本成分,官兵来源(主要是士兵的来源)依然以农村为主。除了依照法律服兵役的意识所起的作用外,出于生活价值取向上的各种考虑,农村青年仍然把军营看做人生道路的最好选择之一。在由各种亚文化因素构成的有着特定内涵的军营文化中,农民文化无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虽然这种文化经由军营之炉的锻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其基本内核无论如何仍会保留下来。他们的行为、意识和生活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对部队建设产生着较大影响。无论作家以何种方式反映军营生活,都不能漠视这样一个颇有规模的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军人群体的存在。
从军旅作家队伍的整体情形看,除了因为时尚的缘故去“赶海”而脱离了创作队伍的作家们,屈指可数的几位义无反顾地探求于纯文学领域的执着者,以及相当一部分倾心于务实的文种写作的弄潮儿外,还有一些仍然有着特殊追求而且把文学与自身命运相联系的农裔军旅作家。他们的情况不尽一致,有的在创作上还尚嫌稚嫩,而有的则已显出较好的实力。总体上说,他们是按照既不高雅神圣,也不随波流俗的原则,以一定的规模和速度保持与发展了形成于八十年代的创作追求。应该承认,在时下讲包装、讲实惠的大背景下,他们是属于那种甘于寂寞、不事喧哗的作家类型,这似乎多多少少体现了与他们最初的“本色”——例如踏实、勤奋、刻苦等素质紧密相关的特点。而这一点,对如今的严肃文学和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当年颇为走红的“军干子弟”作家群中的绝大多数,现今已是人到中年,且不说他们感受生活的条件以及现时的军营环境与当时相比有了诸多不同,就是他们的创作心态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更为严峻的是,这部分人事实上几乎没有了可以待援的“后续部队”——社会的变化使得军营中不可能再有条件产生那样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个群体在过去的年月中曾引起人们的普遍羡慕),或许他们以及他们代表的那部分人已经成为历史的标志;相比之下,农裔军旅作家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只要这支军队存在下去,只要还有文学,农裔军旅作家的行列便会不断加入新人。
在如此条件下,“农裔军旅作家”创作现象得到了映衬,它的存在并且引人注目,是军事文字在特定历史时期发展的一种结果,一种的确值得人们深思的结果。
军艺文学系毕业生陈怀国大约没有想到,他于数年前发表的一篇小说的题目,一个平常之极的题目——《农家军歌》,居然成为这个延续下来的“文学现象”的代名词。这个很会寻找故事眼的文学后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把一种对生活的新的理解以及情感寄托悄悄地带进了军事文学领域,使人们渐渐觉察出目下流行于理论批评界的有关“后”之概念的特殊含义。
那是一个鲜有选择的年代,对“农家”来说,有条件唱“军歌”的便意味着生活有了转折的契机与可能。生存境况的艰辛使他们对军营充满了向往之情,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在他们看来,军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职业的标记,而是迈进新生活之门的入场券,是获得命运选择的资格证,因而他们会无比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时代的发展虽然已经格外垂青于今天,使人们看到了“电话村”、“亿元乡”这样的农村富裕楷模,但“脱贫”依然是中国广大农村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无论八十年代还是现今,反映在作品中的这种情形本身似乎没有根本的变化。
不能否认,中国的很多家在农村的军人是背负着双重责任跨入军营的,“保家”与“卫国”在他们内心具有同样重要的蕴含。《高山下的花环》虽然极力状写了新一代军人的英雄主义品格,展示了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但作者并没有因此遮掩历史所客观留下的另一种印迹。例如,梁三喜的帐单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了这些军人所面临的两难抉择;李镜并非农籍,可他的小说《冷的边关热的血》中边防排长蓝禾儿的经历却十分深刻地表现了农籍军人在生活重负与创造辉煌之间留下的足迹及其复杂内涵。蓝禾儿对边防军人事业的理解是多维的,崇高的献身精神之中也混合了某种个人自我利益考虑的狭隘成分,他担心转业而宁愿留在艰辛的铁舰山哨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盼妻子的随军。同梁三喜不谋而合的是,作为军人,他要为戍边守国尽职尽责;作为农家子弟,他要为养家糊口做出最大努力,而从军几乎成了像他这样的人改变家庭困窘境地的唯一可能。这种带有苦涩意味的现实是一种历史的负荷,对于那些出身在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完全摆脱贫困之地的农籍军人来说,他们正是要在这沉重的历史负荷下完成军人的使命。显而易见,李存葆们提供的作品文本更具凝重、悲壮以及类似古典主义风范的色彩,这种美学特征十分贴切地与那个时代联系起来了。
就内容而言,现时的“农家军歌”也在重复着这个已经并不新鲜的故事:对军旅乃至于企盼通过军旅改变生存命运的渴望,生活的负重意识,军人的职业角色与农家出身的不协调性。陈怀国的《毛雪》以一种复杂的口吻记述了主人公渴望参军的迫切心情,全家人的欣喜、不安、焦虑乃至于泪水,实际上成了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最初动力,也为他日后所要承担的并不轻松的责任埋下了伏笔。天宝在中篇小说《门朝你开》前边的作者自白中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如今,我的老父亲也去世了。他没能等到我在部队提干,每月寄钱给他花。也就是我们老家所说的享福。”尽管这段表述与他的小说情节无关,但其中透出的精神实际上却代表了他和他这一代人的心声。阎连科、蔡秀词、柳建伟等人的小说创作无一例外地触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他们与八十年代的兄长们并无二致。贫困的土地养育了他们,给了他们生命和欢乐,给了他们磨难以及对这种磨难的思考,也使他们过早地成熟起来,并意识到生活之路的坎坷曲折。
“时势造英雄”的箴言似乎是划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一有联系然而却不尽相同的两段“农家军歌”的界标。这一判断分别包含了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两项指谓。从现时的角度看,八十年代的文学(尤其是初期和中期的文学)是幸运的,那时,作家是社会注目的中心,文学所造成的社会轰动效应不仅使作家,而且使整个社会都对文学充满了信心。就像李存葆与《高山下的花环》为社会接受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可以让寻常人将其互为指代一样,著名的作家或作品常常可以成为某个普通社会议题的常用佐证。与此同时,那场局部的边境战争又使得作家们获得了练笔和发现英雄的良好时机。事实上,那场局部战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以极强的魅力吸引着渴望在文学上建功立业的军旅作家,甚至反映它的内容一度构成了军事文学创作最热门的主题。正因如此,文学作品中的农籍军人,无论怀抱何种个人目的,最终总是在飘猎的军旗下踏上同步,在英雄主义的感召下找到共同的价值。而在社会已经多方位跨入转型期的今天,相对和平的生活环境与多元的生活内容,使军事文学一贯以之为特质的英雄创造与基调的一致性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中多了琐碎,少了崇高;多了平淡,少了轰轰烈烈。虽然在诸如抗洪救灾一类的行动中还能不时闪现军人的光亮之处,但就整体情形而言,军旅所提供的素材似乎渐渐趋于日常化了。于是,“农家军歌”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演绎出了全新的话题——探索农籍军人的心灵世界,从外在的行为描写转入内在的性格挖掘。
与周大新有着某种相似,阎连科的创作也是两点支撑的。我们暂且不论他的“瑶沟系列”,而聚焦于他的军事题材创作。他的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连队的基层军官。对要完成“当兵、提干、家属随军”三部曲的农籍军人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前两部曲,正处在进一步提高“档次”的关键时期,因为距“副营职”——这个按规定可以使家属随军的“门坎儿”只差一步之遥了,而这也恰恰是他们心理活动与情感变化最为复杂的时期。阎连科很会写故事,善于设置矛盾冲突,常常把他的人物放在命运的紧要关头加以表现。
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围绕一起枪丢兵亡事故的调查处理,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同为农籍的两位连队主官的复杂心态。只要证实他们和事故责任有关,不仅提为“副营”成为泡影,而且很可能立刻面临转业退伍——这将使他们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而只要证实责任由其中一人承担,那么另一人就有希望继续留队,这也就意味着可能盼到家属随家。与其两败俱伤,不如保全一人。在保全谁的问题上,两个灵魂的较量与冲突便在和风细雨的交谈的掩饰下展开了。这一情节的构置未免有不近人情或残酷之嫌,譬如说教养、人格、觉悟或者文化等力量的因素为何不能起作用呢?判断的标准只能是主人公的,对他们来说,比较起更为务实的时机把握与命运选择的因素,上述因素似乎便显得相形见绌了。按照务实的生存准则理解,一旦被某种可能获得的“好”生活所拒斥,那么所有风度与教养便失去了物质的基础,从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大约就是阎连科说过的“无战的和平亦消耗军人的生命”的缘由所在。
柳建伟的中篇小说《王金栓上校的婚姻》则提供了一则相反的例证。就“家属随军”条件而言,农籍军人王金栓的职务已经绰绰有余。不过他原本就无须为此烦恼,因为他很早就摆脱了家乡为其定亲的束缚,新生活对他来说是垂手可得而且应该是无所顾忌的。问题的症结在于王金栓对于城市文明有一种本能的或者说潜意识的抵触。在实在无法适应城市姑娘对他无休止的苛刻要求的情形下,他终于在故乡完成了他的终身大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随军而成为城里人的妻子偏偏适应性极强,在她有了几番新潮时尚的表现后,王金栓决定同已经失却乡村本色的妻子离婚。其后,他故伎重演,两度在农村寻找对象,使其相继随军,再相继离异。故事当然是以荒诞手法写就的,但王金栓式人物的心理演绎过程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农籍军人在生活选择上的又一种困惑。
“向内转”的结果必然使作家开始思考农籍军人在生活或命运选择上的文化依据与可能性,这就引出了又一个话题——观念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困惑使主人公在生存价值的自我认同上出现了障碍。
无论怎么说,军营毕竟给农籍军人提供了选择生活的机会。在主、客观种种因素的促成下,总有一部分人会如愿以偿的。阎连科中篇小说《和平战》的主人公郁林其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从外在条件说,一个农家子弟所企盼的一切郁林其都有了——身为院校毕业的连职军官,部队驻防城市,尽管家系农籍,却有了城籍妻子。对很多农家子弟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境界了。但郁林其并未感到自己的幸运,因为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城市生活因素(这个概念也包括军旅的工作境况)仿佛都对他有一种明显的排斥力。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王金栓的情形相反,王金栓不断排斥着纷至沓来的城市文明,而拼命想得到城市文明的郁林其却不断受到它的排斥。实际上,两人的境遇从不同方面共同反映了两种文化在兼容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上,郁林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痛苦之中。似乎是一种象征,郁林其获知自己已患染癌症之日起,便结束了对某种并不实在的生活的盲目追求——他以大彻大悟的态度开始坦然面对工作与生活中的一切:包揽事故责任,接受降职处分,答应妻子的离婚要求并放弃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在参加了阅兵——他的人生的最后一次辉煌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贫瘠然而却是他的故乡的农村,在病魔的伴随下,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
郁林其生存目标的设置无疑具有代表性,问题在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舍弃许多对人而言是极有价值的东西。这样一来,生活的意义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维持无爱的婚烟以确保已然到手的“城籍”地位的做法,对一个以追求所谓幸福为目的的人来说显然是悖谬无稽的,这就如同“有”与“无”构成的怪圈。郁林其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农家军歌”的吟唱结果竟然是苦涩而酸楚的,先前亢奋的“企盼”最终变成一厢情愿的梦幻——这个代价的付出显得昂贵而无谓,因为它不仅包括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牺牲,也包括多年铸就的道德标准、处世法则的毁灭。
新话题的出现使人们对军事文学的根本意义与作用产生了怀疑:文学何以反映军人?何以在题材的分类上划出所谓军事文学?倘若我们封闭了必要的价值通道,那么这些问题的确令人深思。
军人这个古老的职业是因为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伴生物——战争的存在而存在的。战争的阶级性、民族性以及它的人类文化学方面的意义又赋予军人以不同内容、不同方式的解释。假如我们抛开种种特殊的可能,而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以反映包括战争、军人生活在内的各种军事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文学,我们就不能也无法回避它所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精神:这就是人物、作品基本内容的尚武风范以及附着于此的阳刚之气。这是由军事文学的特性决定的,也是由军人的职业和与军人职业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战争的特性决定的。事实上,如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或界定了军事文学的一般品格及其美学意义。正因如此,新一代“农家军歌”实际上等于为自己行进的路途安设了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
譬如,主人公失落意识之于作品阳刚之气实现的障碍。此类作品主人公大都怀有失落感,在经过一番苦苦奋斗而且小有收获之后,他们发觉生存现状每每并非遂愿,而这已不是靠吃苦、忍耐等付出所能够改变的,因而他们不再愿意保存最初年月的那些精神了。从写法上说,低调的生活氛围或许与人物的心境殊途同时,却与人物承担的社会角色之要求相悖。似乎他们当兵就单单是为了改变终生务农命运的,除此之外,别无他图,一旦这种“改变”遇到问题,当兵的所有意义都毫无价值了。我以为,在如何塑造军人形象的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其社会角色的特点——你写的是谁?这不仅仅是要求于中国军事文学的,任何民族或国度的军事文学都必须如此。一如我们所知,前苏联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许多作品被公认为军事文学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在描写大小事件、战争场面和军人个体的同时,几乎都涉及到了成份十分复杂的苏军官兵的构成——哥萨克、农民、工人、学生,可谓“五湖四海”,由此所反映到军营中多样的文化背景自然也就构成当时苏联军人不同的从军观念。然而,复杂的文化背景并没有影响这些被称为军事文学作品的主旨的表现。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欧文·肖的《幼狮》,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尽管人们把它看成通俗作品)等优秀作品,在抒写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军人方面,可谓极尽渲染之能事,但军人的尚武精神,爱国情结,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气质……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军事文学的独特魅力,在这些作品中差不多也都得到了充分表现。
无可讳言,由失落感所奠定的作品的灰暗基调与军事文学自身应具有阳刚气韵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这就如同动人心魄的摇滚乐之于传统的抒情小调无法合奏一般。我想,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看法,军事文学反映的实质总是与战争或者与为战争而做的各种准备发生着密切联系,因为对任何参战者来说,取胜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要达此目的,在信念上保持一定的气度则是必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军事题材为创作内容而又悖谬于阳刚气度的要求,显然是不符合军事文学创作规律的。
再譬如,狭隘的自我意识之于作品的大气风范实现的障碍。此处所谓“自我意识”并非一般性指言一种强调个性与个体重要性的时尚表现,而是更多地指言一种过于敏感的自我暗示意识。例如,与其说王金栓与他的几任妻子或者郁林其与吴萍的矛盾冲突是因双方的情趣及观念的不合谐所造成,不如说是他们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严格的界限,而且这种界限事实上使他们根本无法趋于心理平衡。王金栓、郁林其们的自卑,在某种条件下就是一种自我暗示,把由于自卑所导致的强烈的甚至有些变形的自尊推向极端,便是这种自我意识不断得以产生的症结所在。换句话说,在如何被一种生活方式抑或一种文化接受的问题上,他们以自己的理解为自己的奋斗和自己的信念划定了不可逾越的框式。这种理解无疑是偏执而畸形的,它带给他们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世界,一个气氛沉闷、互相猜疑以及充满自我暗示色彩的世界。“农民的出身”如同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使他们无法真正投入生活并且正视自己。
小说《和平战》中的女主人公吴萍与郁林其的婚姻分明缺少爱情基础,她的那句身上就像“爬了一个农民”的告知,原本是对无爱婚姻的绝望表白,却被郁林其理解为对其出身的蔑视,因而更加重了他的悖反心理。他们的解脱方式也是病态的——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老话去概括尽管不妥,却也不乏这样的意味,例如他们的人生奋斗史大体上都是按照先是卧薪尝胆、绞尽脑汁、全力以赴,然后看破红尘、听天由命或者破罐破摔的行进过程安排。基于如此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打垮(假如把他们的奋斗信念的破灭看成是被“打垮”的话)他们的不是环境,也不是疾病,而恰恰是他们自己。作为众多艺术方式的选择,军事文学的观照视角固然可以是局部的,甚至有时为了某些特殊效果也不妨可以有别常理常情,但从根本上说,它的精神品性却应该是恢宏而广博的,它透视出的社会蕴含和人生哲理应该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性。于是,“超越自我”的口号在这里便有了“提高”、“升华”这类寻常解释以外的一层意义,这个意义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从狭隘走向宽广是军事文学创作所必须的审美观念转变的需要;其二,从封闭走向开放是我们目下的共同课题——生活观念转变的需要。事实上,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军营生活方式,都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余地。例如,紧张而富于节奏的军旅生活对于青年人品质和毅力的锻炼;军人的职业特点给予社会与普通百姓所提供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奉献精神之于军旅的普遍意义等等。
新一代“农家军歌”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时代与生活的变化,也来自军事文学自身的要求。我们不能一方面不断感慨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又恪守许多年之前铸成的观念,并且以为这种观念仍然是今天创作的制胜法宝。毫无疑问,农籍军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依然是军事文学的主角之一,只不过我们需要调整创作视角,渗入一种正面的、昂奋积极的意识,赋予他们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品格。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能够给人们、给历史留下深刻印迹的军事文学作品,都是或者都将是因其精神实质得到了鲜明的展露和充分的张扬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