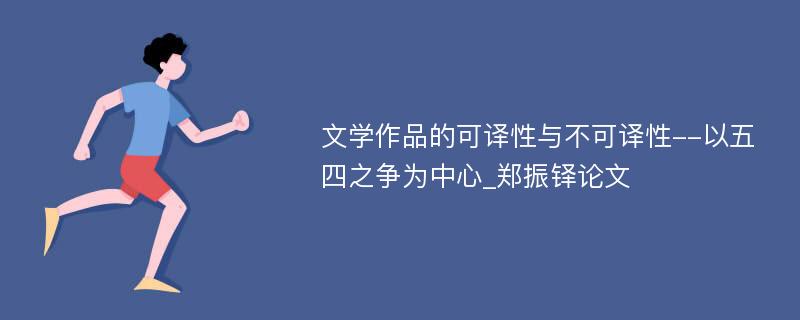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作品论文,中心论文,可译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5-0175-04
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翻译作品数量的增加、体裁的扩大、译者队伍的壮大,以及对原作的精选、翻译态度的审慎等方面,更表现在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921年,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兄弟之间发生了一场论争,其主题是文学书是否具有可译性。虽然就此次论争的规模、涉及人数、延续时间而言,难以与同时期的另外两次论争①匹敌,但就其对翻译问题思考的深度而言,意义却不可低估。本文通过缕析双方立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而探寻这场论争的延续,分析引发论争的根源,希望能对可译性问题的理解有所裨益。
1921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3期上发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揭开了此次论争的序幕。该文旗帜鲜明地表明其立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同年,沈泽民在《小说月报》第5期发表了《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书不可译”。翌年,茅盾以“玄珠”为笔名,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翻译问题一译诗的一些意见》,阐述了他对译诗的看法,与沈泽民的观点基本一致。
坚持可译论的郑振铎和坚持不可译论的沈氏兄弟都承认翻译是不完美的,但其结论却截然相反,这与立论的出发点不无关系。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从英文转译了大量印度、俄罗斯和古罗马、希腊文学作品,其中很多译作获得好评。基于个人丰富的翻译实践,又受到轰轰烈烈的翻译热潮的激励,郑振铎鼓励更多地译者加入这个大潮,满怀信心地进行翻译。沈氏兄弟则更多地看到了翻译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的诸多无奈。五四时期,直译方法盛行,一些译者“一字一字的勉强写出,一句和一句,像连又不连,像断又不断,假是不念原文,看也就似懂又不懂”[1]。这样的译文是否具有艺术性与可读性,成为译者思考的焦点。沈泽民提出不可译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从双方的论述中可看出明显的局限性。郑振铎的局限表现在:首先,他主要依据的是Rannil所著“Element of Style”,但其“翻译思想而为文字”并非特指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而是指文学创作中将思想变为文字的过程。创作和翻译的差别很大,将此定义作为论证的依据,其结果可想而知。其次,对通俗不可译论的反驳实例是要表明原文的“全体的结构,节段中的排列,句法的组织乃至用字的精妙”都可以移译,翻译不会丧失原文的艺术美。众所周知,不改变原文的情节结构、段落顺序、语句组织,未必能保持原文的艺术美。再者,论述前后矛盾。“文学书能够译么”的前半部分认为,“艺术极好的翻译家,用一句一句的‘直译’方法”保留原文的句、段、结构,原文的风格与艺术美不会丧失。但在后半部分的论述中却认为,“思想在译文里常是不能表现得如在原文里一样的充分而且好看……无论是最精密的句对句的翻译,也是一种‘意译’”。那么,连最精密的句对句翻译也是意译,如何翻译才是前文所述的“直译”呢?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风格与艺术美还是否可能?
沈泽民坚持不可译论,是基于传统的原文中心论。首先,作者的中心地位不可撼动。在他看来,作者的“情绪”和“灵机”赋予原作生命,作者的创作经由生活的体悟、激情和灵感而来,而译者的翻译是经由文字、体悟再转化为文字。在这个过程中,“文中的情绪要损失不少”。其次,原文的中心地位不可替代。他认为,原文是艺术品,译文是仿制品,即便非常逼真,其艺术性也要大打折扣。艺术品的主要作用是观赏和收藏,而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我所用,或开启民智,或改进旧文学,倡导白话文。再者,艺术形象“乡土气息”的改变。沈泽民提出,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一经改变,其精神气质也就不同了,译者对此无能为力。既然是翻译,语言和时空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译者所不能控制的。就如相同的服装,模特在舞台上穿是一种效果,在日常生活中穿则是另外一种效果,这是因场景而异。模特穿是一种效果,普通人穿是另外一种效果,这是因人而异。艺术形象的变化亦然,即便不经翻译,将原文放到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经由不同的读者解读,其艺术形象也不尽相同。
诗歌翻译也是论争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在该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共识。郑振铎承认诗歌的音韵有时无法转移到译文中,但音韵的缺失不会影响情绪的发抒,所以诗是可译的。沈泽民认为,诗歌翻译如同散文翻译一样,关键在于情绪的表现,音韵的转译和格律的转译皆在其次。这与郑振铎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沈氏兄弟认为,这不能说明诗可译,音韵、格律不能转译,正好说明诗如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是不可译的。
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关于可译性问题的争论未能继续下去。直至1940年,贺麟在《论翻译》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阐释,其立场与郑振铎基本一致,但其论证则更严谨。与郑振铎论证不同的是,贺麟不赞成以是否保留原文的句、段、结构作为可译性的指标,他认为,“翻译应注重意译或义译。不通原书义理,不明译者意旨,而图斤斤计较语言文字的机械对译,这就根本算不得翻译”[2](P126-132)。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1984年,对此问题的探讨寥寥无几,冯世则《风格的翻译:必要、困难、可能与必然》一文探讨了风格的可译性问题、徐永煐《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中提到了“翻译的可能和限制”问题[3]。1985年至今,有关该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大致状况和发展趋势如下:
1.论题具体化。有关可译与否的论题逐渐变得具体化、微观化,涉及隐喻、意象、修辞、广告、笑话、谜语、幽默、俳句、双关语、中医术语、文言虚词、“文化衫”、格律诗、风格、古典名著文体、美学功能等方面。
2.文化的视角。翻译研究在1990年代经历了文化转向,可译性问题的研究亦然。在文化的视角受到重视之初,多认为文化不可译,世纪交替后又多认为可译[4](P118)。卡特福德(Catford)关于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的分类成为被援引的经典,从反面论证语言可译性与文化可译性的研究也不断出现。
3.跨学科意识。翻译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跨学科趋势,哲学、历史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比较文学等学科对翻译研究皆产生了影响。一些研究运用功能主义、关联理论、解构主义、系统论、控制论、范式、符号学等方面的理论,阐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
4.发展的观点。可译性问题的探讨由基于过去的实践、当前的思考到放眼未来。有学者认为,语言或文化所造成的不可译性是暂时的,不可译性总会向可译性发展演变,译者、论者应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般来说,此类研究会列举成功翻译的例证,并就当前的不可译问题提出翻译补偿的具体原则。
5.文本研究。从翻译文本研究解读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涉及鸿篇巨著《红楼梦》、诗歌《锦瑟》、话剧《茶馆》、散文《背影》、诗经故事《螽斯》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鲁迅作品等。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来验证可译性或不可译性。
以上关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出现五四时期的唇枪舌剑,但两种声音总是交替存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论争的状态。这些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那场论争的延续。坚持可译性的论者往往会列举翻译实践中的优秀个案,认为其符合翻译的某种标准,文学作品具有可译性;反方则列举若干让译者无能为力的事实,比对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距去验证不可译性。从“论题具体化”、“文本研究”两个趋势可以看出,这些微观研究为可译性问题提供了例证,或者将“文学作品的可/不可译性”缩小至“诗歌、风格等的可/不可译性”乃至“某词语的可/不可译性”。“文化的视角”和“跨学科意识”无疑扩大了研究视野,丰富了可译性问题的研究。但以不同学科的理论为依据,又引发了“A理论可以验证可译性,文学作品具有可译性”,“B理论能够否定可译性,文学作品具有不可译性”的循环往复。
如此下去,文学作品可译性论争永远不会有结果,这个悖论式的循环仍将延续。依笔者看来,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当今翻译界关于可译性问题的争论,主要基于双方不同的出发点、立场、论据及表述方式。
(一)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
自古至今,翻译的定义多种多样,现代人对翻译的界定日趋全面,有的从语言方面切入,有的从符号学着眼,有的重视文化因素,有的关注话语理论,反映了对翻译本质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观察。如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信息”包括“意义、思想内容、感情、修辞、文体、风格、文化及形式等”[5]。那么,满足多少要素才说明文学作品可译,满足多少要素才说明文学作品不可译,这些问题与对翻译实质的认识密切相关。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实际上是对翻译本质不同认识的反映。
郑振铎与沈氏兄弟关于可译性问题的在讨论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郑振铎把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翻译等同于风格的翻译,思想内容的可译性等同于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沈泽民则认为,文学作品中附着原作者的情绪与灵机,这些因素在字句之间,而不在字句之中,绝对不可以复制,因而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
(二)不同的翻译标准
一般而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涉及对翻译标准的不同设定。翻译标准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规范性要求,即等值、体裁修辞、翻译言语、语用以及沿用标准[6](P60-63)。在翻译实践中,这些翻译标准不可能同时实现,为了实现翻译的语用标准而牺牲其他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便在同一翻译标准中,各个要素也未必能够一一实现,往往会由于不同语言、文化等差异而顾此失彼。
在郑振铎和沈氏兄弟的论述中,涉及翻译的等值标准和体裁修辞标准。诗歌、散文、小说的艺术特征不同,评价相应译作的标准也就有所不同。双方都将诗歌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显然是意识到不同体裁作品的翻译具有不同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有共识的。翻译的等值标准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基本层次上的等值指译文与原文思想内容保持最大程度的一致,而更高层次上的等值则包括“语言单位和言语单位的感情、修辞、形象、美学等功能”[6](P61)。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较为尊重原作内容的真实性,基本层次上的等值得到译者的高度认可,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等值标准的更高层次上。郑振铎认为,文学作品“全体的结构,节段中的排列,句法的组织乃至用字的精妙”都可以移译,原文的艺术美不会丧失。但沈泽民认为,即便文字上惟妙惟肖,原文的精神还是有所毁损,译者对此无能为力。
(三)不同的理论依据
郑振铎的主要论据是D.W.Rannil关于“风格”的定义。多数译者认可文学作品的思想可译,争议集中在风格的翻译上。郑振铎推导出文学作品的风格亦可译,据此反驳不可译论。而沈泽民的不可译论,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译论。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生活在特定的语境中,一经改变,则精神气质完全不同,而翻译必定要改变文学作品的生存语境。他认为,翻译只是“文化穷荒”时做一件不得已的工作而已。这让我们想起洪堡之语:“翻译无异于试图完成根本就完不成的任务,译者注定要在两大障碍前失败:要么过于拘泥原文而牺牲本民族语言及其韵味,要么过于注重本民族的语言特色而牺牲原文及其韵味。折中的解决办法不是难找,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找到。”[7](P35)
1980年代后的可译论者往往援引雅各布森、卡特福德、费道罗夫等人的理论。不可译论者则会提到洪堡、威斯葛伯、沃尔夫、萨皮尔等。名家的论述无疑为双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中间派一般援引乔治·穆南“翻译可行但有限度”的观点。理论依据不同,也使得论争愈发复杂化。
(四)不同的描述方法
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论争,也有一些观点大致相同,只是重视结论而导致论争白热化,其分歧源于描述方法的不同。可译论者多数认同可译的相对性和限度,承认翻译中原作各种因素可能的缺失与变形;不可译论也认为原作思想内容、结构等层次上的可译性。论辩双方忽略对方的论证过程,重视结论,因而各执一词。郑振铎与沈氏兄弟在关于诗歌是否可译的问题上可以说并无多大分歧,都认为诗歌翻译中音韵节奏有时难以译出,关键是要保持原诗的情绪,但在可译性与否的结论上却大相径庭。
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的描述大致有四种:可译性,可译性但有限度,相对可译性,不可译性。可译论者往往以几千年的翻译史和优秀的译例反驳不可译论者;而不可译论者也能举出若干让译者无奈的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不可译论者及可译相对论者往往是从原作与译作的比对角度出发,两个文本及其阅读效果肯定会有诸多差异;而可译论者除了承认两个文本中的共性外,更多地考虑原文与译文的互补关系、原文与译文生命延续的关系。除了以雅各布森、洪堡为代表的绝对可译论者和绝对不可译论者外,多数论者在承认相同事实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同的描述方法。以对地球形状的描述为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地球是赤道略鼓、两极稍扁的椭球体,这早已得到科学家的广泛认同。而对地球形状的表述通常有几种:地球是圆的,地球是不规则的球体,地球是一个椭球体,地球不是圆的。这几种说法在现实生活中并行不悖,虽然“地球是圆的”和“地球不是圆的”论断截然相反,但实际所指并无差别,人们对实际所指的认识也并无二致,只是描述方法不同而已。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论断也是如此。
从传统的角度看,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相似是译者的本能、译事的追求。然而,对翻译史的研究表明,改造和背离原文往往是出于某种需要,并非译者的能力和语言文化差异所致。伪译是很极端的例子。图里、韦努蒂等都将伪译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之一。如果没有原文的“伪译”都是翻译,还有什么是不可译的呢?因而,论争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关键是双方论证的前提是否一致,如果前提相互抵牾,则结论大相径庭。
厘清导致论争的根源,为悖论添加前提条件,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争执。在前文提及的四个根源中,前两个尤为重要。若认为翻译是从不同层面在译语中完全再现原文,评价的标准是比对译文和原文的完全相似度,则会持不可译论,译文总会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如果退而求其次,认为翻译是在某个或某些层面在译语中再现原文,评价的标准是某个或某些方面的相似度,则会持可译论,译文在某些方面再现原文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持解构主义翻译观,关注译文在译语中能否产生陌生感,实现某种功能而不是相似度,则一切文学文本皆具有绝对的可译性。
注释:
①一为新文化人与林纾之间关于是否用古文进行翻译以及翻译的选材、译笔等方面的论争;一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关于翻译的作用、目的和翻译批评等方面的论争。
标签:郑振铎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文化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语言风格论文; 沈泽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