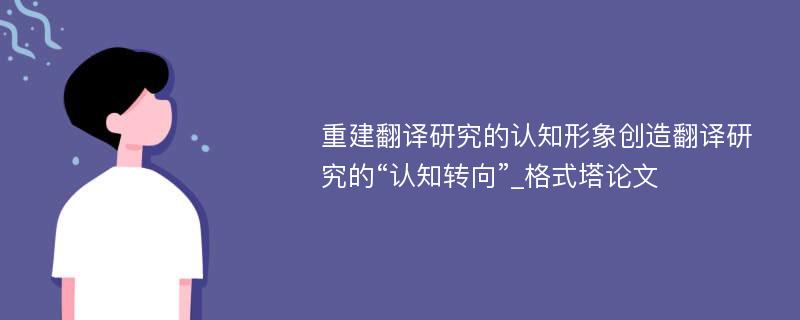
重构翻译研究的认知图景 开创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图景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述
Cognition的词源本义是“感知”、“识别”。认知的内部结构和过程包括知识的习得和使用,它涉及到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和推理等过程。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范畴观界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通过亚氏的范畴理论,我们能够有序地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认知的探索。柏拉图认为,虽然人脑中的理念不能完整地反映现实世界,但它毕竟构成了我们的认知思维。对于笛卡儿、洛克和休谟来说,思维以一种认知的形式存在,它与物质实体互动,通过神经和大脑接受有关世界的信息,由此而构成了知识的基础。哲人们认为,语言是人类普遍的认知组成部分,语言和认知能力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新的学派。它主要涉及到范畴化、原型理论、隐喻概念、意象图式、象似性、语法化等诸方面内容。近20多年来,一些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与乔姆斯基(N.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相对立的观点。其主要代表人莱可夫(G.Lakoff)和约翰逊(M.Johnson)等学者致力于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将人类的概念系统与身体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朗艾克(R.Langacker)等人尝试建立认知语法体系。由于认知语言结构是认知过程的产物,所以它反映了人对世界的感知、理解或信念而形成的概念结构。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中新的“认知转向”。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以通过语汇和概念来表达。但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将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不是“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冲击和提供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因为翻译活动本身是语言活动,有不少翻译理论家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翻译理论。雅各布逊(R.Jakobson,1959)从符号学角度出发把翻译分成语内、语际和符际三类,强调语言分类和认知体验都是可以转换的;20世纪60年代奈达(E.Nida,1964)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出发,把原语的核心句经过转换后翻译成目的语的句子,而总结出翻译的对等原则;英国的卡特福德(J.G.Catford,1965)从“阶”(rank)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从词素、词和短语等成分研究翻译,以期达到“文本对等”;70年代博格朗(de Beaugrande)和德斯勒(Dressler,1978)等人在篇章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认知交际目的的翻译方法;斯奈尔·霍恩比(M.Snell-Homby,1988)的整体语言翻译观注重话语分析和文本理解,提出了综合翻译法中格式塔原则的应用;迄止90年代,贝尔(R.T.Bell,1991)受认知科学的信息处理过程的启迪,系统地研究了翻译的过程;纽伯特(A.Neubert)和西瑞夫(G.Shreve,1992)阐释的“自上而下”的翻译模式,从语用和交际的过程来探讨译者的动态心理过程。而威尔斯(W.Wilss,1995)则提出,解释翻译研究的认知过程是翻译研究的重点的观点。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者沈家煊、陆俭明等人从汉语的词汇、语法或语篇着手,探讨了人类语言的认知共性。在翻译理论界,学者们试图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或概念来阐释英汉语中的翻译现象。有的学者从格式塔意象再造探讨文学翻译研究的审美过程(2002),有的学者从句法相似性角度研究英汉句式(2004),有的学者从语篇类型研究翻译的对等与认知的关系问题(2006),有的学者从译者主体性角度讨论译者的认知主体作用(2007),有的学者从英汉语对比研究出发阐述英汉语隐语认知的异同(2007)等。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扩展翻译研究的构架。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已经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二、翻译中“认知转向”的基本研究范围及方法
由于翻译活动既是人类最重要的语言交际活动,又是人的一种认知活动。从认知的角度去研究它,将会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启迪,翻译研究中不能没有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主要包括(不限于)以下研究领域或范围:认知格式塔与翻译再现、认知隐喻与翻译、翻译中的认知对等、翻译的动态认知过程、认知与文化翻译、认知模式与语篇翻译、认知的象似性与翻译、认知与译者主体性研究、认知与语用翻译;认知语境与翻译、认知科学与机器翻译、认知取向的翻译教学等。从方法论上看,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于其跨学科的特点:它将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为主要基本框架理论,同时切入翻译理论,注重描写和整合认知与翻译的关联,以探究英汉语翻译中的认知心理过程、认知模式和运作机制。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由于认知语言学是对语言本质的共性的研究,它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共同规律,从而对翻译实践活动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结合前期的研究成果,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应该把研究重心放在以下诸方面:
(1)现代认知语言学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映照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编码,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因此,翻译研究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由于体验是认知的本质,且以体验为本原的认知模式具有普世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此决定了语言本质的普世性,这就是使语际转换——翻译成为可能的认知理据。(2)信息的双重编码和重构。认知语言学证明,脱离了人对客观世界的一般认知和对经验进行组织的机制,语言是不可能产生的,通过体验将外部刺激的物理特征转换成心理事件,形成信息的心理表征。不同的语言之所以可以转换,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以体验为本原的认知结构。认知意义上的翻译过程可以理解为:语码和意向之间是相互激活的双向运动。在一般情况下翻译材料是以文字即语码形式出现的,故在文本翻译中是原语语码激活意象,而在形成目的语时则是先由意象图式还原为意象,然后才产生匹配的符号表征。(3)等值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尽管人们的认知模式大致相同,但由于其历史、文化进程不同,而呈现有区别性的文化特征,这正是翻译中的难题。认知模式的相同性和具体文化的相异性是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随着人们对认知环境和经验结构的了解,翻译中的动态对等则成为可能。由于人类认知模式的相似性,造就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和趋同性,这就为我们翻译新的表达方式提供了认知基础。(4)认知框架是基于文化约定俗成的知识构型(configurations),框架连接多个认知域的知识网络并与某个特定的语言形式相关联,从而建立概念与概念之间相对应的模式。用框架结构来看翻译,就是译者在目的语中所采用的语言表达能否激活与原语相同或相似的框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对框架系统的相应调整、根据语篇对文化框架进行协调处理等。(5)认知环境与关联理论:关联理论对翻译和可译性有较强的解释力。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的理解是一个动态认知过程,翻译是一种明示——推理活动,推理包含了译者要从交际者的明示中确定其交际意图,交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方的意图被另一方识别,成功的译文是原交际者的目的和受体的要求在认知环境相关方面与原文相似。因此,关联理论赋予译者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变通空间,并且,语言的能产性、人类的认知能力为翻译的重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译者的任务就是,循着主题语境这条脉络,在译语中寻找铰链,使目的语联想语境与原语联想语境具有相关性。(6)语义中的认知域和“识解”(construal)的应用。翻译中的意义包括语义内容以及译者对语义内容的识解。由于认知方式不同,作为认知主体的译者可能强调不同的认知域,其结果是,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语义表达。译者的认知内容由认知域提供,而译者的认知能力赋予他不同的识解。翻译中的识解是人们对原语相同的语义内容进行的不同的认识、翻译的结果。译者的认知结构既是他的知识结构,又是“识解”的结晶。例如,在诗歌翻译中,人们由于对一首诗的“识解”大异其趣,通常被指责为误读或“借题发挥”,这是译文所唤起了不同的格式塔知识产生的解读,因此,所有的阅读都涉及到不同的认知域和“识解”,翻译中的意义不仅仅包括语义内容,更重要的是译者对语义内容、特别是隐喻性语义的识解。
三、认知中的“格式塔”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总的来说,认知语言学主要集中探讨概念的分类的心理现实。研究发现,许多分类围绕“原型”组织,原形赋予分类以突出特点,能够影响记忆和推理。其中,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完形心理学的“图式”也是认知关注的内容。“图式”(schema)理论的首倡者应该是英国心理学家巴特雷特(Frederick Bartlett),但更早的来源则是哲学家康德,后者使用了Schema一词,意指“地图”或“计划”。巴特雷特将格式塔的记忆理论运用于语言理解。其基本点是,新的经验可以通过人的记忆中相类似的经验来理解。[1]16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由于“图式”可以解决视觉识别和文本理解问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为了探索普遍的认知模式,认知学家发展了三个基本模型:信息处理模型(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s)、认知发展模型(cognitive developmental models)和感知经验模型(perception and experiential models)。[2]260这些模型对语言学、翻译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的认知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试以信息处理模型为例,在翻译及话语分析中,“格式塔”对文本的处理就起关键作用。一般认为,人类的语言用于操纵环境、维持社会关系。但是,在“格式塔”面临新的问题出现时,大脑必须建立新的“格式塔”以适应新的经验。与文本互动的知识论由“格式塔”概念作支撑,它们也是不同类型的心理再现。在文本的信息处理过程中,文本的语言因素会激活文本,或者是激活“格式塔”,用于判断文本的意义。对于文本翻译来说,不同的文化呈现不同的心理积淀,翻译不仅体现着文本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文化、概念范畴和“格式塔”的沟通活动。我们生长在不同的文化中,这一成长过程既是“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文本、概念网络对我们的思维起作用的过程。文化利用不同的文本网络(textual grid)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西方文化分享着“两希”(希伯莱及希腊)文明的共同历史,也就是分享着共同的文本网络结构,他们之间的语言转换不存在太大的认知冲突。相比较将中文翻译成西方语言,由于其文化迥同于两希文化,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就会遇到较大的格式塔障碍。大部分格式塔网络就认知的突出性、非对称性和显性出现,也即是“母体”(matrix)某些成分更为重要、更为显性。这些认知特点尽管是人为的、历史的、先在于语言,但也决非一成不变,译者通过后天知识的积累和学习,例如通过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可以改变其世界的表征,也改变译者的格式塔。认知的翻译观试图提供化解这类“显性”特征的种种补偿手段。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也会以认知的方式楔入我们的格式塔,或者“离经叛道”地改变常规,提出新的格式塔模式。例如,在翻译中原文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如果要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必须要有两个前提,其一是译者在目的语中能够找到与原文相类似的语言等值并且有等同的文学效果,其二是译者在目的语中增加了原文没有的新的词项。就前者来说,翻译具有文学性,但是,这种文学性的审美是其自身的特点,而不是来自于原文。另一方面来说,原文的文学虚拟世界可以保留,虽然语言词项不同,语义所指相同。语言形式虽然有变化,但是文学的真实性通过翻译保留下来了。这一观点与建构主义的原则相吻合:语言再现(翻译)是通过心理再现的另一种形式转换的。原文和译文之所以是等同的,是因为她们有相类似的格式塔。[3]97-98在翻译实践活动中,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存在,独特的文学性可以通过精心选择的对等物保存下来,有些文学特点可能会失去,但总体文学效果会保存下来,这是由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有相类似的认知心理。格式塔的心理变异可能带来语言变异和结构变异。由此,我们知道,话语的格式塔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格式塔加强”、“格式塔保存”和“格式塔更新”[4]10。在这三种类型中,第三种类型对翻译的认知的研究颇有启迪,这是因为格式塔的“更新”的前提意味着格式塔的破坏(所谓破旧立新),所以“更新”的认知过程是一个解构、建构和链接的过程。如翻译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时间简史》时其中有关宇宙的大量的新颖词汇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认知结构,也“更新”了译者的思想和语汇。例如,在翻译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时,杨献益夫妇更注重的是原文的文化与语言形式,原作者为其格式塔基点,而霍克斯与闵福德更注重目的语的格式塔接受心理,而采用以读者为基点的方法。在翻译章回目录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区别:
蒋玉涵情赠茜香罗,薛保钗羞笼红麝香(第二十八回)
Jiang Yuhan Gives a New Friend a Scarlet Per-fumed Sash
Baochai Bashfully Shows Her Red Bracelet Scented with Musk.(杨译)
A crimson cummerbund becomes a pledge of friendship;
And a chaplet of medicine-beads becomes a source of embarrassment.(霍译)
杨译在句法结构、习语、物饰方面的翻译将原语的内容几乎完全保留下来了,反映了重视原文格式塔,而霍译的回译是:“一条深红色的腰带成了友谊的保证,一串带有药效的念珠成了困窘的起因”。原文是人做主语,而在霍译里物体取代了人而成为主语。这是东西认知的格式塔差异而产生的翻译的语言差异。“潇湘馆”杨译为“Bamboo Lodge”,而霍译为“Naiad's House”,成为希腊、罗马神话中住在河湖中的“仙女”。霍译中大量格式塔的转换其目的是用目的语文化取代原语文化,通过其文化同化达到文化征服的意图。
格式塔在认知过程中的使用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互文性的翻译。原文的特定群体的读者心理产生的互文联想需要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互文暗示需要在译文中以同等的格式塔表现出来。事实上中西诗歌中的暗示、隐喻随处可见,翻译和阅读这些经典诗歌需要十分强的互文性鉴赏力。同时,互文性的使用也给研究翻译的认知提供了新的源头活水和灵感。马致远的“枯藤老树”写的是乡村的荒凉,艾略特虽写的是都市的荒凉,但二首诗却在最后用上带感情的字眼(断肠人;lonely);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情景十分相似。
《断章》是卞之琳的名作,只有四行,引录如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钟爱的《花间集》,内有冯延已的《蝶恋花》,此词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二句。《断章》与这两句有多么神似的联系啊!而卞氏的创造性的吸收与转化达到了不露互文性痕迹的程度,体现了译者格式塔与古代诗人相契合与映射。再例如,英国一战后有名的诗人欧文(Wilfred Owen)在其诗作中大量采用了《新约圣经》中的暗示,诗句“like sheep…abattoirs”来自于《以赛亚》“He was brought as a lamb to the slaughter”;诗句“We will never forgive”使人联想到《路可》“Then Jesus said,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怎样在译者的选择与原作者之间建立一种认知关联?诗人乔治·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诗句“Gather ye rosebud while you may”翻译成“花开堪折直须折”,与金昌绪的《春怨》在认知意境上有相似之处,而且译者本人也悟到这种相似之处才挥笔而就的,用“花开堪折直须折”直接套用,出于考虑到原语和目的语读者的格式塔心理是可行的。而译者要了解中西诗歌中的互文性和相同的认知心理,需要有敏锐的嗅觉和深厚的学养。[6]55-59真可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中借用宋明理学大家陆象山的话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正说明了中西存在相同的格式塔心理。翻译文本既可看作是同一文化源流中的契合,也可以看作是不同文化的认知相似性。作为译者需要对原文作者、作品、读者进行解读,同时也要将文本内的互文认知传递给目的语的读者。[7]55-58
四、认知的隐喻与翻译
在认知翻译过程中,我们不仅用格式塔模式来对应两种语言的认知心理,而且作为构成认知活动基础的隐喻也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了解的一个方面。
汉语的语词最初原本隐隐地指示着两种基本存在:人和自然。语言最初作为一种命名活动,不仅仅给予事物一个名称,而且给予事物一个人格化的品格。中国哲学中“远去诸身,近取诸物”显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隐喻系统。因此,隐喻不仅是语言的构成方式,也是文化构成的基本构成方式。中国语言文字及其表征上的隐喻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关于“隐”,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作了解释。在他看来,就语言的建构而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隐以复意为工”。而就语言的效果而言,“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隐者,不可明见也”。所以“情在词外曰隐”。刘勰所谓的“重旨”和“复意”,实际上就是隐语表达方式中符征和符意之间的张力结构及其所造成的效果。且不说汉字本身的“观物取象”和“书画同源”呈现了汉语是一种心灵语言的特点,而且汉语表达中隐喻的丰富存在显示了中国人存在的样态。“岛”是由“鸟”与“山”组成,“美”是由“大”和“羊”组成;古人所说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形容说不出的美丽,曹植写洛神的美用的语言更让人难忘:“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显示了隐喻无处不在,魅力无穷。
与中国的象形文字不同,西方的拼音文字从符号层面上消解了隐喻的先天优势。尽管如此,作为修辞手段的隐喻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布罗姆说过:“诗歌在本质上是浓缩的隐喻语言,它在形式上富有表现力和唤起联想。比喻是诗歌本身的直接形式出发,它可以是转喻(trope)或修辞。”[8]1故而西方的隐喻通常包括转喻、提喻、代喻和比喻,甚至反讽的范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强调比喻就是把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另一事物。(Tropes a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me of a thing to something else.)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范围已经超越了词项和句子,具有认识论价值的语言结构,成为评价和解释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甚至凸显人的存在的本性。有人甚至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的。“不管我们对世界、科学、诗学或隐喻如何认识,这些不可避免地都是隐喻的,因为我们从来不是对本义的或真的事物作‘本义的’介绍。”[9]5-7莱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隐喻部分地构筑我们日常的概念,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除此之外,关于隐喻有如下四种理论:(1)张力理论(Then Tension Theory);(2)冲突理论(Controversion Theory);(3)变异理论(The Deviance Theory);(4)语义变则理论(The Semantic Anomaly Theory)等。[10]10隐喻与认知的研究范围主要有处理常规和新隐喻、在语句或图形中发现隐喻、隐喻语句的翻译、隐喻的推理及内涵意义、隐喻与人工智能、隐喻与认知的非本义形式关系等。隐喻的种类有概念隐喻、基本隐喻、诗性隐喻、根隐喻。它的实质主要是替代、互动、比较与创新。作为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在人类其他的文化和艺术活动过程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隐喻的存在。”[11]28语言中的隐喻产生于人类的隐喻性思维过程,如象形文字的视觉表达,它反映了大脑认识世界的方式。例如如果我们说“人体就象一台机器”,我们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医生好像是维修工或钳工的印象,影响了部分人对待医生的心理效应和潜能态度。由于隐喻的鲜明性和图象性,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它,越来越多的人的思维认知方式受其影响。翻译是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翻译中的符号的视觉性会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视觉感知,这样译者的意象视觉、知觉与想象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由于隐喻中的意象作为代表物体和事件的非言语的心理表达,体现了一种心理认知过程,它涉及到情感、思维、心理状况或视觉体验。译者的认知也随着阅读到的不同意象,而凸显不同的心理意象。意象的存在需要人的观察,人对意象的理解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诗歌中意象是其灵魂,其意义部分是意象的。对于庞德来说,意象是“理性和情感的复合体”。其翻译思想是准确地翻译细节,准确地翻译每个词,保留每一个不完整的意象。《诗章》中的数百个这样的意象,其中许多来自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解读,而形成认知上的心理认同。对意象的认同也就是对“默认概念”的认同,也就是译者形成不同于自身的概念一种能力,这种语言的使用直接体现在意象传递中。简言之,将一种语言的意象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意象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转换(mental transfer)。译者的主体化产生心理转换有关,也就是说,作为译者,他一方面是意象(概念化)过程的观察者,他也是概念化的目标。译者与意象的互动反映了认知微妙的复杂过程。翻译与隐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特别是对于有高度隐喻性的文字来说,隐喻就是译者的思考方式。在方面过程中,他既需要用隐喻来思考原语语言,又需要思考目的语语言,看看二者是否“兼容”,在两种语言或文化中,如果隐喻不可通约的情况下,他还要考虑到置换原语隐喻形象,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
五、结语
限于篇幅,认知的翻译过程以及认知与等值的关系等重点在这里不能逐一探讨。目前,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在于,首先,“认知模式”强调个体认知体验,虽然该模式建立在对所拥有知识的假设之上,它最终还得依赖“文化模式”,而“文化模式”也可以被看作是“认知模式”,怎样阐述二者之间的作用和关联,这是翻译研究中的“认知转向”应该考虑到的问题。其次,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和想象性尽管被证明是共有的,“客观的”,但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怎样沟通主客?再次,目前研究的重心主要放在微观的句子一级上,关于宏观的文本转换以及语言和概念之间的处理关系,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最后,“体验哲学”中译者的主观作用如何得到发挥?作为译者如何考虑主客体的互动关系?此外,有关翻译中的“直觉”和“灵感”等方面的内容,我们还要从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去作跨学科的关照和研究。
近年来,从国内外认知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和影响来看,翻译研究试图从认知的角度切入,拓展自身的框架结构和空间,为翻译研究的过程提供可证实的答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的确如此,翻译研究目前正在悄悄地发生着一场“认知转向”,面对这场机遇和挑战,国内翻译理论界准备好了吗?
标签:格式塔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认知语言学论文; 格式塔理论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重构论文; 认知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