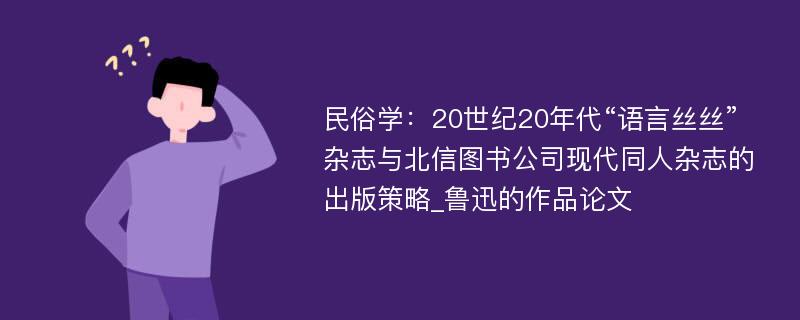
民间化:现代同人杂志的出版策略——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杂志和北新书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丝论文,杂志论文,书局论文,同人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同人杂志逐渐取代社团会刊成为了北京出版界的主流。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北京最著名的同人刊物《语丝》为标本,通过讨论该刊以北新书局为根据地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运作手段,揭示知识分子团体为谋求独立精神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作为《语丝》杂志的实际主持人,周作人曾经在多个场合赞扬《语丝》“在北京——或者中国杂志界中”(注: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京报副刊[N].1926-01-21.)的与众不同:“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改别人的话,本不是什么为世希有的事,但在中国恐怕不能不算是一种特色了罢?”(注:岂明(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J].语丝.第54期,1925-11-23.)当然,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最初的目的是因为《语丝》和《现代评论》笔战正酣,所以“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注:启明(周作人).《语丝》的回忆[N].羊城晚报,1957-10-03.)不过,周作人显然也很清楚,在以报章杂志为阵地的舆论体系中,言论的自由除了精神上的“大胆与诚意”外,还必须以经济的独立为基础和前提,不然便只能是纸上谈兵。胡适就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注: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文集[M].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民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P258)然而,经济上不仰仗于人说来轻松,实际操作起来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为了以身作则地改变出版界因没钱而经常延误的通病,《语丝》在筹备阶段就对自家刊物的资金来源有过规划:“至于《语丝》所需的印刷费,当时商定:由鲁迅先生、周作人、伏园和我,四个人来按月分担。李小峰当时没有职业,恃译书为生,就多出些劳力”。(注: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N].文艺报,1956年第16号.)虽然说内部集资是大部分同人杂志解决经费问题的主要途径,但这种方式的不确定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事的变动、薪金的增减、物价的涨跌,甚至交通和通讯等等,都有可能对资金的到位和利用产生影响。好在《语丝》从一开始销售情况就好得出乎意料,“第一期就再版了七次,共印了一万五千份”,此后也基本上维持了每期7千份左右的销量。非但不再需要个人支付印刷费,而且有了盈余,因此免去了几位先生的负担。只是支付各种费用虽已
不成问题,但以往的经验让主事者很难对刊物的运作太过自信。负责承印的北大印刷所坚持“先付钱再开工”的原则,让《语丝》不太满意。而且李小峰等人工作量繁重,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也非长久之计。因此,“成立一个自己的书局,以推动新文艺工作”(注: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J].出版史料.1987(2).)的议案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李小峰、孙伏园等人的这些提议,是在他们主持后期新潮社的工作时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后期新潮社的失误和教训,直接促成了这些建议的提出,并为《语丝》的运作提供了直接的借鉴。
新潮社既是闻名遐迩的北大学生社团,同时还是一个出版机构。尤其是改组成学会之后,编辑《新潮》杂志只占据了社务的一部分,重心被转移到出版丛书这方面了:“发布些小册子,编辑一种人事学科丛书,一种思想潮流丛书,一种文艺丛书和其他刊物,这是我们的事业;此外也再没有我们的事业了”。(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第2卷第1期,1919-10-30.)然而,作为出版单位的新潮社远不如作为学生社团的新潮社成功。这种虎头蛇尾的局面,固然和主力成员相继离校或出国,以及校园团体本身的流动性相关,但主事者严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对书刊经营方式不熟悉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简单地说,新潮社曾在两个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失误。其一,盲目乐观地估计销售情况,以致大量丛书严重滞销,到新潮社停止活动时,尚留下了“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干部《点滴》”。(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鲁迅全集[C].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240)其二,新潮社从成立以来,就自动放弃了对经济的控制权:“银钱出入由学校会计课负完全责任,社的干事概不经手银钱。”(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第2卷第1期,1919-10-30.)在“五四”那个特殊的时期,由校方支付全部费用的方式,固然给风行一时的《新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得还是学生的编辑们无需为资金来源四处奔波。但是,这种筹款方法也为刊物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一旦校方的经费补贴不能按时到位,团体的各种活动就会立即陷于困境,刊物就无法准时出版。后期新潮社之所以变成了“一个一面积货一面负债的团体”,(注: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C].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P230)与当时全国教育经费的紧张很有关系。此外,《新潮》虽然是进入了市场渠道、对外公开发售的刊物,但社内无人关注具体的经营过程:“本社的成员向来不经手银钱的出入,所以印刷需款若干、售书得价若干,照例是不问的。”(注:新潮社的最近[N].北京大学日刊第1141号.1922-12-27.)不但经费的获得和支出都缺乏有效的管理,而且不得不长期拖欠印刷厂的费用,以至书刊的印刷和出版难以为继:“因印刷费的拖欠而影响了出版物的愆期,因出版物的愆期而本社失信于读者,影响到书刊的销路;因销路的减少而经济来源更加呆滞,印刷费遂付清无期,终至印局不肯再接受本社的印件。”(注: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C].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因此,当李小峰、孙伏园等人有意对新潮社进行改革时,首先就从纠正这两方面的失误着手。一方面,直接经管刊物的出版和销售,收回经济的控制大权;另一方面,想办法解决积压的书刊,以求重整旗鼓:“《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第一个字,叫‘北新书店’。”(注: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A].五四运动亲历记[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P282)然而,作为经济实体的书局和作为学生团体的新潮社之间,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不难从他们各自经营的刊物《语丝》和《新潮》不同的运作方式上略窥一斑。
在《语丝》面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被看成是“他们新潮社里的几个人编辑的”。(注:1925年2月17日鲁迅致李霁野.鲁迅全集[C].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436)当然,《语丝》首页上标记的“社址:北大一院新潮社”的字样,也的确很容易让人得出类似的结论。其实,除了《语丝》的几个撰稿人确实曾有过新潮社成员的身份外,当时已经形同虚设的新潮社对《语丝》的影响实在有限,“只是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做《语丝》的一个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注: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N].文艺报,1956年第16号.)不过“五四”尚未走远,《新潮》昔日的辉煌大多数人还记忆犹新。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新潮社的特殊背景也不利于《语丝》作为独立期刊的地位,“完全用北大新潮社的名义,印行书籍与杂志,很有不便的地方”。(注: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A].鲁迅回忆录[C].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P160)因此,在1925年3月北新书局正式成立之后,《语丝》的发行工作就转移至翠花胡同李小峰的住处,首页上也将社址改为“北大一院语丝社”。关于这个变化,周作人还特意在刊物上做了说明:“现为办事便利起见,规定办法如下,请读者诸君注意:(一),凡关于编辑的事务,请寄信至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君处。(二),凡关于发行的事务,请寄信至北京东城翠花胡同十二号北新书局。(三),凡关于交换的事务,请寄信至北京大学第一院内语丝社。”(注:语丝社启事[J].语丝,第90期.1926-08-20.)
事实上,“语丝社”并不是一个挂牌成立的经济实体,它可以被看成是《语丝》编辑部的代称。这也就是说,在北新书局参与《语丝》的业务之后,维持刊物正常运转的日常工作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以周作人为中心的编辑部,负责刊物的组稿、编选以及与其他刊物的联系;以李小峰为老板的北新书局,负责刊物的印刷、发行和销售等事务性工作。此外,从声明中还可以看出,北新书局除了自己份内的业务之外,无权干涉刊物的编辑大权,事实上这也是这份声明的主要用意所在。由于李小峰和语丝社大部分同人的特殊关系,尽管《语丝》杂志上从来没有缺少北新书局各种篇幅的广告,但这条“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至少在《语丝》的北京时期得到了很好的维持和贯彻。(注:《语丝》转移到上海出版后,因为李小峰违规插手稿件的选择,又未经允许插入商业广告,造成了鲁迅先生愤然离去,这是后话。可参见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
其实,以某个出版机构为根据地,通过发行期刊和出版书籍来影响文化界和舆论界,晚清以降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尤其是“五四”以来,在出版机关从为圣上立言到逐渐民间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对现代出版业的关注和参与,看重的就是它们在改造民心和宣传思想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胡适之于亚东图书馆、鲁迅之于北新书局,都不仅仅是一般作者和出版社的简单关系。他们虽然都不是这些出版社的正式成员,但大到选题策划和稿件取舍,小到印刷字体和封面设计,他们的建议对决策都曾有过重要的影响。由于他们的主动参与,亚东版的重印古籍和北新版的名家专著,在现代文化界和出版界都堪称经典。更准确地说,教育和出版,对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既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工具,也是他们借以表述自我、影响社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当年还是北大学生的傅斯年等人创办新潮社和出版《新潮》时,就已经意识到“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第2卷第1期,1919-10-30.)至于出版家张元济所说的“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注:1917年2月20日张元济致蔡元培.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R].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147)也足以代表相当一部分人对出版业的特殊情怀。
对于大部分并不以赢利为目标的同人刊物而言,与固定的出版社合作,充分利用书局的社会关系、组织能力和专业化的营销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外在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变故。虽说大多数书局在经济上并不依赖这些刊物,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可以说是互惠的“双赢”结合。出版《甲寅》和《新潮》的亚东图书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店、与创造社有合作关系的泰东图书局等,在接手这些刊物之前,都是籍籍无名的小书局,借助这些期刊或团体的巨大影响力,他们才能够“名字叫人认识了”。(注: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文集[M].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民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更为重要的是,在日益商品化的时代里,十年一剑、藏之名山的学术理想已经不再流行。随着作家和文人对图书出版市场的依赖性逐渐明显,出版社不但要密切追踪读者的需要,而且必须具备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经营策略,既要满足作者和读者的需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文化潮流的方向。因此完全可以说,书局在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单纯作为出版发行机构所体现的价值。
尽管如此,在当时行业规范很不健全的出版界,书局与作者和编辑者之间的矛盾依然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某些以赢利为唯一目的的书局面前,甚至连基本的稿酬和版税都无法保证。即使是鲁迅和李小峰这样密切的关系,还出现了北新长期拖欠版税的情况,其他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矛盾也就可想而知了。郭沫若就曾经直斥一些不良的出版家为“文化强盗”,抨击他们无非是在“榨取作家的血汗,读者的金钱”。(注:郭沫若.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A].郭沫若选集[C].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P422)鲁迅先生也曾一针见血地讽刺大部分的书局“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花本钱,四欲大发其财”。(注: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C].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李小峰主持北新后,也对出版界的积弊予以了批评:“这几年来经营出版事业的几家书局,稍好一点的,只保守着它十年二十年前的状态,迎合旧社会的心理,稍新一点的学理,即不敢介绍,怕影响了他的营业,所有的出版物都索然无生气,实在不足应时代的需要;那些下流的书局,更专门出些荒唐无聊的东西来骗钱,读者要想得到一点好的读物,苦不可得。”(注:北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J].语丝第99期.1926-10-02.)
正因为如此,在创办之初,北新就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改变以往编辑和出版脱节、作者的意图难以完全落实的弊病。只有彻底摆脱书商的剥削和控制,使书刊从编辑、印刷到出版和销售,都处在团体内部的掌控之下,同时保持经济上的完全独立,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势力,才能真正做到“一切都由自己来,自己著译,自己设计,自己定价,自己发行,不受书商的掣肘,完全自主,就有条件来掀起一次出版界的大革新,印出一批兼顾内容与形式的好书”。(注: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C].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所谓“兼顾内容和形式的好书”,原本就是很多撰稿者长期的梦想,可以用鲁迅先生确定的三项原则来具体说明:书要印得精美,售价要低廉,对作者要优待。(注: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J].出版史料.1987(2).)在这些方面,北新不但要求“所有出品必求于文艺上,科学上,国学的研究上有相当的贡献”。而且颇有“于出版界辟一新纪元”(注:北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J].语丝第99期.)的充分自信和勇气。鲁迅曾对北新的不随波逐流有过夸赞:“看看各出版店,大抵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绍介,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注:1927年12月26日鲁迅致章廷谦[A].鲁迅全集[C].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605)而事实也证明书局的定位并非空中楼阁:“千年来的努力出了六十余种书,颇受读者意外的欢迎。每一书出,销数往往逾万。著作者亦以本局可靠,纷纷以稿件将赐。”(注:北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J].语丝第99期.1926-10-02.)
关于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李小峰自己也承认,“初开办时,资金是极少的,仅靠发行《语丝》及《新潮社丛书》的一些利润和代售书刊的些微回扣以及我在新潮社出版的五六种书的一点版税”。(注: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J].出版史料.1987(2).)但因为在北京文人圈里建立起了广泛的信任,出版的著作和刊物可以保持相当高的水准,北新对读者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出版的书最合青年的脾胃,新文学一类的书更是受读者的欢迎”。(注:语丝.第83期的北新书局广告.)再加上精明的李小峰经常采用一些很有诱惑力的促销方式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例如预约定购、优惠售书和赠送长期优待券,以及“凡直接向书局购买者,可享特价七折优待”等手段,都是北新惯用的招数,也多次被证明是比较成功和有效的。尤其是书局对麾下所属的三种定期刊物《语丝》、《北新》和《沉钟》,北新实行了“联定优待”的政策:凡定阅两种以上的刊物,且定购了全年的《语丝》的读者,可享受八折优惠。(注:三种定期刊物欢迎联定,特别优待[J].语丝.第111期.1926-12-25.)这些很有商业噱头的促销手段对于“志在改进”的鲁迅等人而言,未免感到“老病又出现了”的失望,(注:鲁迅.书籍和财色[A].鲁迅全集[C].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161)但在读者中的反响还是相当不错的,“因此书局的地址虽偏僻,登门光顾者仍不少”,(注: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J].出版史料.1987(2).)成立之后不久,“北新书局就渐渐发展起来,生意也特别兴隆”。(注: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A].鲁迅回忆录[C].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除此之外,北新对作家们同样具备相当吸引力,在于它所提供的待遇。按照章程的规定,北新向作者支付稿酬大致是这样结算的:“抽版税办法:创作及翻译等,作者得定价百分之十至廿;标点及编集之书,作者得百分之十至十五之版税。卖版权办法:创作及翻译,每千字自一元至五元,由作者与本局商定之。”(注:北新书局新订书稿酬金章程[J].语丝.第140期.1927-07-16.)按照当时业内的通行价目,这两种付款方式都出价不低,尤其是比较常用的版税制的结算方式,即使是中华和商务这些大书局,一般开出的版税也只在百分之十二左右,特殊情况下才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在当时经济状况普遍比较混乱的出版界,北新对作者的态度应当算是比较公正,这显然与北新的同人背景和民间色彩是有关系的。(注:这里指的是北京时期的北新。)
北新在成立的广告中,就表达了“使智识阶级与本局更加密切”的理念:“本局同人,有鉴于目今出版界之混乱,印刷之不精良,与夫著作家与书贾间之隔阂,特剏办本局,力图改善。”(注:北新书局开幕前大廉[J].语丝.第44期中缝广告.)北新被视为“五四运动后期带点同人性质的新型出版社”,(注: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P27)正在于他们部分实现了这一理念。对《语丝》来说,一个成功的、由自家人运作的出版机构的出现,不但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而且能最大限度地维持不受外来势力支配的独立品格。而北新也因为和《语丝》团体及北京大学的密切关系,得以笼络到许多很有影响的文人和教授作为自己的长期客户。当时还是北新练习生的萧乾对此印象尤其深刻:“如果把当时每天进出翠花胡同的文学界人物开列出来,也许会占那个时期半部文学史”。(注: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因此,各类文化期刊和同人杂志,尤其是北大师生们主编的刊物,一直都是李小峰手中的王牌。当时由北新营业部负责销售的期刊主要有七种:《语丝》、《莽原》和《沉钟》的印刷及出版由北新全权代理,《国语》、《文学》、《赏鉴》都是京报附设的周刊,它们和《京报副刊》月订本一样,都是由北新书店代销。不难看出,除了《现代评论》和《猛进》之外,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的几大主要期刊都和北新保持了密切的业务往来。
虽说北新只是个规模不大的小书局,但从成立以来,非但不要四处约稿求援,更无需为选题而忧虑,稿件的数量和质量还都能得到保证。李小峰自己也说过,“当时稿件是不用愁的,鲁迅先生主动把他的著译交书局出版,并为书局编了两套丛书;‘语丝社’同人也把他们的作品及译稿交给书局;述有外来的投稿,就是尽最大的努力,还是应接不暇的”。(注: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J].出版史料.1987(2).)正是因为这种得天独厚的稿源优势,使得北新在出版界的地位迅速攀升。张静庐先生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的出版界状况时,称北新为当时“新文艺书店的老大哥”,对它周围良好的人文环境不无艳羡之意:“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近水楼台,得到拉稿的许多便利。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小说旧闻钞》等陆续归北新印行,声誉日隆,营业也日见发展。”(注: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P123)直至20年代后期,在上海的北新已经呈现出“死样活气”的懒散和没落,但还能“依然为新书店的魁首,闻各店且羡而妒之”,(注:1929年3月15日鲁迅致章廷谦[A].鲁迅全集[C].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655)依稀可见昔日鼎盛时的余威。
在《语丝》的同人圈子中,与北新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算是鲁迅。周作人虽然因主编《语丝》的缘故和李小峰、孙伏园有过合作,但他与北新的接触主要是业务往来,并没有如鲁迅那样,对北新书局“不无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注: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A]许广平忆鲁迅[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P287)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几乎将所有的著作和主编的刊物都交由北新出版。鲁迅去世之后,从北新登载的“鲁迅先生遗作特价纪念四十天”的广告中可以看出,由北新出版或发行的鲁迅各类著作共39种,此外还有两种关于鲁迅的研究论著。(注:鲁迅先生遗作特价纪念四十天[N].时事新报.1936-10-24.)除此之外,从筹备阶段开始,在北新的大小事务上,鲁迅都参与了不少意见:“鲁迅先生很关怀自己培植的、新诞生的书店,常到小店来坐坐谈谈,有所指示,如书要摊开,要允许读者翻阅,有时询问外地有哪些读者来信购书之类的事。”(注: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J].出版史料.1987(2).)有人还指出,“在金钱方面,使先生牺牲最多的,是北新书局的创设。先生在帮助北新的成立及发展,除经济之外,精神牺牲,亦是很大的”。(注: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A].鲁迅回忆录[C].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这里所谓的“精神牺牲”,主要指的是鲁迅和北新的版税纠葛。北新给鲁迅开出的版税一般是百分之二十五,在所有作者中是比较特殊的,但事实上能够到手的远未达到这个数目:“先生在初创时,拿出去的钱,不特未收回一文,而北新予先生的稿费方法,亦特别得使人吃惊。民国十三四年在北平时,李小峰偶而从旁人口中,如章衣萍、许钦文等处,知道先生有所需要时,就随便拿几十元或一百元送去。”(注: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A].鲁迅回忆录[C].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在自身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鲁迅之所以长期容忍北新拖欠版税,还对书局如此不遗余力地帮助,并不仅仅因为“先生与它的历史关系最为深厚”,更主要的是“其时做新文化事业的真可说是凤毛麟角,而出版的书,又很受读者欢迎,象这样有历史基础的书店,先生不愿意随便给他打击”。(注: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A]许广平忆鲁迅[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鲁迅自己也说过:“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力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颇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注:1933年1月2日鲁迅致李小峰[A].鲁迅全集[C].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137)因此,对于北新迁沪之后“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注:1929年8月7日鲁迅致韦丛芜[A].鲁迅全集[C].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680)鲁迅一直耿耿于怀,甚感痛心:“北新的灾难也真多,而且近来好像已不为读书界所重视,以这么多年的辛苦造成的历史而至于如此,也实在可惜。”(注:1932年12月23日鲁迅致李小峰[A].鲁迅全集[C].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134)不难看出,鲁迅对北新的重视和支持,是希望在汹涌的教科书和通俗刊物的出版大潮中,能保留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注: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A]许广平忆鲁迅[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作为自己和同人团体的长期出版基地。当然,北新最终没有“坚持早先的立场”,还是被这股利益丰厚的大潮裹挟而去,让鲁迅等人甚感失望。
一个优秀的非官方出版机构,赖以成功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充足稳定的物质基础、经营有道的管理人员、有号召力的作家群体和一定数量的固定读者。应该说,北新书局在这些方面都有过比较成功的时期,尤其是在北京发展的那几年,表现得更加突出。当然,也应该看到,随着经营过程中商业化气息的日渐加强,作为经济实体的北新也不得不偏离预想的模式,逐步向外界妥协。鲁迅提出的好书三原则中,他曾极力倡导的“毛边书主义”这类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主张,就是为了迎合读者的要求首先被牺牲了。(注:据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的记载,鲁迅要求他在北新印的书必须是毛边书,一本都不许切边。但等书印好以后,却发现都已切好边了。李小峰在回答先生的质问时说:“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卖,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兴都切了边。”在鲁迅明确表示反对后,李小峰的办法是:“此后为先生送的,虽然都是毛边,但寄到外埠分店的,还是切边本,在北平,恐怕先生看见不答应,便将毛边本送上街坊上了。”鲁迅回忆录[M].上册第14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北新后期的转变固然原因很多,但市场的影响和左右,以及主事者对商业利益的盲目追求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出版界的文化理想和市场效益之间的矛盾,其实也不是北新一家独有,这里不妨引用出版家张静庐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钱是一切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报酬者,其演出方式相同,而其出版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注: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P4)
从新潮社并不成功的出版业务,到翠花胡同的曾经辉煌,直至书局后期由盛转衰,由引人瞩目而渐趋平庸,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过程。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学生团体向商业机构的转变,还有这个转变过程的必然性,以及北新与生俱来的特殊色彩。不能否认,正因为语丝社等文人团体和鲁迅等个人将北新当作固定的出版社,而由他们运作的刊物大多具有鲜明的同人色彩。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北新包揽了他们的著述和编辑物的出版与发行,也使书局本身表现出了浓厚的集团性和民间化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