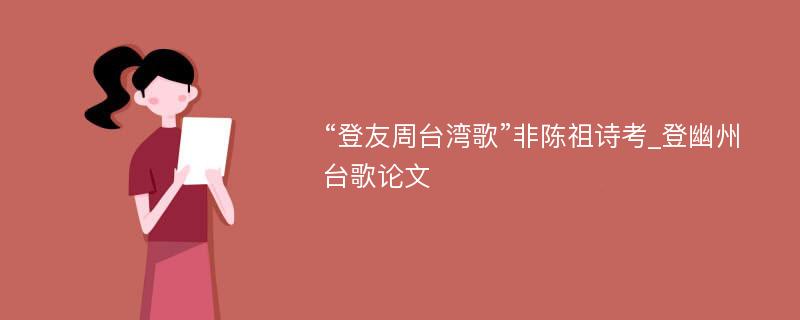
《登幽州台歌》非陈子昂诗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幽州论文,陈子昂论文,诗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早报》(上海)2014年11月23日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先生一篇2000余字的大作《〈登幽州台歌〉献疑》。该文说:“如果此歌为陈子昂所作,卢藏用编集时为何不加收录呢!如果说是记录陈子昂登台时的歌唱,但卢藏用则明明在幽州二千里外的终南山隐居。”陈先生怀疑《登幽州台歌》不是陈子昂的诗,这种感觉和眼光是敏锐的。但是,怀疑的这二个理由得不出《登幽州台歌》不是陈子昂的诗这样的结论。一个原因是,古人集子漏收作品是常见现象,不能因为一篇作品没有被作者原来的集子收进去就认为不是作者的作品。另一个原因是陈子昂临终前将诗稿托付给卢藏用时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年在二千里之外登高所喊的内容告诉卢藏用或者写下来交给卢藏用。这样,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就可以引用了。另外,陈先生还提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南朝宋武帝说过的话,还提到了明以前唐诗选本未收《登幽州台歌》,还提到了明代杨慎第一个称赞《登幽州台歌》。但是,这三个事实同样得不出《登幽州台歌》不是陈子昂所作的结论。或许正是因此,陈先生自始至终没有敢断定《登幽州台歌》不是陈子昂的诗,于是在题目上使用了“献疑”这样的用语,正文中使用了更加慎重而又严谨、准确的措辞:“那么似乎只有一种可能,即此四句是卢根据陈赠诗的内容,加以概括而成,目的是在为陈所作传中将他的孤愤悲凄作形象之叙述。” 实际上,对“陈子昂是《登幽州台歌》的作者”这个命题,需要的不是“献疑”,而是否定,然后理所当然地推出一个新命题:“陈子昂确实不是《登幽州台歌》的作者。”这两个(旧和新)命题不仅在文献源流上有清晰的脉络,而且在事理上有更加强大的理由。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登幽州台歌》原始出处的分析 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有如下记载: 陈子昂,字伯玉……属契丹以营州叛,建安郡王攸宜亲总戎律,台阁英妙,皆署在军麾。特敕子昂参谋帷幕。军次渔阳,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三军震慑。子昂进谏曰:“大王诚能听臣愚计,乞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驱,则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斗士,以子昂素是书生,谢而不纳。子昂体弱多疾,感激愤义,尝欲奋身以答国士(笔者按,“士”,疑为“事”),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钳然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之知也。及军罢,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1]2412-2413 所谓“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就是说,即使“歌曰”二字“曰”出来的话是诗,那也不在“赋诗数首”的“数首”诗之内。那么,“歌曰”出来的话和“赋诗数首”的“数首”诗是什么关系?这需要看看那“数首”诗。幸运的是,这“数首”诗今存于《陈子昂集》卷2,全文如下: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 丁酉岁(697),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 轩辕台 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空黄埃。尚想广成子,遗迹白云隈。 燕昭王 南登碣石坂(一作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王道已沦没,战国竟贪兵。乐生何感激,仗义下齐城。雄图竟中夭,遗叹寄阿衡。 燕太子 秦王日无道,太子怨已深。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 田光先生 自古皆有死,徇(一作循)义良独稀。奈何燕太(一作丹)子,尚使田生疑。伏剑诚已矣,感我涕沾衣。 大运沦三代,天人罕有窥。邹子何寥廓,漫说九瀛垂。兴亡已千载,今也则无推(一作为) 郭隗(末缺) 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隈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2]25-27 显然,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从序到诗都为卢藏用写《陈子昂别传》中“前不见古人”等22字(即明代嘉靖以后世人所称的《登幽州台歌》)提供了素材。例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所写“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就是以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这组诗为背景的;“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和“独怆然而涕下”对应着《燕太子》中的“千载为伤心”、《田光先生》中的“感我涕沾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对应着《燕昭王》中的“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和《郭隗》中的“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这下就清楚了,《陈子昂别传》中“前不见古人”等22字及陈子昂“泫然流涕而歌曰”的场景,只是卢藏用依据他对好友陈子昂的了解自己创作出来的。据罗庸《陈子昂年谱》,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到二年(697)七月这10个月的时间里,呆在幽州的陈子昂游览过燕国古迹,那是无疑的,这有陈子昂的几首诗为证[2]340-342;陈子昂登蓟北楼时因为主将武攸宜没有答应陈子昂愿带一万人作前驱的请求而抑郁寡欢甚至内心悲慨,触景生情,向往重用人才的燕昭王和燕太子,甚至登在楼上大声呼喊或者吟唱,这都是完全可能的,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对此提供了逻辑上的证据。但是,陈子昂登到蓟北楼上究竟喊了没有、歌了没有,这就两可了。可能喊了歌了,也可能欲喊而未喊,欲歌而未歌。再进一步讨论,假如陈子昂在楼上喊了歌了,而且陈子昂自己把“喊”和“歌”的内容写下来交给了卢藏用,这样,“歌曰”的内容显然就是陈子昂的作品了(是诗,是文,暂且不论),那么,陈子昂去世后为陈子昂编文集的卢藏用把这“歌曰”的内容当作陈子昂的作品了吗?没有。嘉靖26年(1547)杨慎《丹铅摘录》刊刻前,不仅陈子昂集的所有版本全都没有把“前不见古人”等22字当作一首诗收进去,而且所有古籍,不论是总集、别集,还是选集,全都没有把“前不见古人”等22字当作一首诗予以收录或者提及。那么,这22字是怎么被当作一首诗归于陈子昂名下,还广受好评和广为传播的呢?这得从杨慎《丹铅摘录》说起。 三、《登幽州台歌》被归到陈子昂名下的历程 嘉靖26年丁未岁(1547)所刻杨慎《丹铅摘录》(13卷)卷8有如下记载: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辞简质,有汉魏之风,而文籍不载。[3]卷8 这是“前不见古人”等22被视为陈子昂作品的第一次记载。这里杨慎并没有明说“前不见古人”等22字是诗还是文,也看不出杨慎给这22字标了个题目《登幽州台歌》,因为杨慎这话完全可以断句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杨慎弟子梁佐几年后就是这么断句的,详下。 7年后,即嘉靖33年甲寅岁(1554),梁佐刊刻杨慎《丹铅总录》,该书卷21有如下记载: 幽州台诗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辞简质,有汉魏之风,而文集不载。[4]卷21 这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梁佐加了个题目《幽州台诗》,这说明梁佐对杨慎原话的断句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就是说,梁佐不认为“前不见古人”等22字的题目是《登幽州台歌》。 过了28年,即万历10年壬午岁(1582)四川巡抚张士佩刊刻了杨慎的《升菴集》(81卷)。该书卷59有记载如下: 幽州台诗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辞简直,有汉魏之风,而文籍不载。[5]卷59 这记载显然是对梁佐记载的因袭,说明张士佩同意28年前梁佐的断句,认可“前不见古人”等22字的题目是《幽州台诗》,而不是《登幽州台歌》。 明万历17年己丑岁(1589)进士郑明选《郑侯升集》(40卷)卷35《陈子昂逸诗》云: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6]卷35 郑明选这话显然是抄录杨慎《丹铅摘录》卷8关于“前不见古人”等22字的记载,而且只抄了前半段,省略了后半段杨慎“其辞简质”之类的评价。郑明选这话也看不出他是否给“前不见古人”等22字起了个诗题《登幽州台歌》(如前文所述,杨慎的话就看不出杨慎是否有此意)。 明万历46年戊午岁(1618),钟惺、谭元春合编完成《唐诗归》(36卷)。《唐诗归》卷2选收了《登幽州台歌》,并有二人的简要评语。钟惺曰:“两不见,好眼。念天地之悠悠,好胸中。”谭元春曰:“至人实有此事,不是荒唐。”[7]卷2这是“前不见古人”等22字被标上题目《登幽州台歌》的第一次出现(但不是“前不见古人”等22字作为一首诗被标出的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64年前即嘉靖33年也即1554年梁佐标出的《幽州台诗》),也是“前不见古人”等22字得到的第二次好评,也是《登幽州台歌》第一次出现在诗歌选本中。从此,《登幽州台歌》这个题目和这首诗就固定下来。 陈维崧(1625-1682)《陈检讨四六》卷4第一篇《序·续臞菴集序》注释“恨古人之不见,知来者之为谁”云:“世说张思光居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陈子昂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8]卷4可见,陈维崧认为“前不见古人”等22字是“古诗”。认为《登幽州台歌》的体裁是“古诗”,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陈维崧。 清黄周星(1611-1680)于康熙19年庚申岁(1680)前编成唐诗选本《唐诗快》(16卷)。《唐诗快》卷2收录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并有评语曰:“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泣鬼神。”[9]卷2这是《登幽州台歌》第二次出现在诗歌选本中,也是“前不见古人”等22字第三次得到好评。 清徐倬所编《御定全唐诗录》(100卷)卷5“古体诗”的最末一首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10]卷5。这是《登幽州台歌》第三次出现在诗歌选本中。这次入选时,《登幽州台歌》被置于“古体诗”中,这是该诗第一次被认定体裁类别是“古体诗”,之前只有陈维崧认为是“古诗”。需要说明的是,《御定全唐诗录》(100卷)成书于《全唐诗》(900卷)编成的前一年,故不可认为徐倬《御定全唐诗录》是从《全唐诗》中选录的,也就不可认为徐倬选《登幽州台歌》受到了《全唐诗》的影响。还需要说明,虽然《御定全唐诗录》后来的名气并不大,但因为该书的书名标明是康熙皇帝“御定”的,而且该书有康熙皇帝写的序。故从理论上说,次年(1707)编成的《全唐诗》之所以会收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应该受到徐倬这本《御定全唐诗录》的影响。 康熙46年丁亥岁(1707)《全唐诗》(900卷)编成时,卷83倒数第二首即《登幽州台歌》,与上一年(1706)编成的《御定全唐诗录》所收《登幽州台歌》字句完全相同。《全唐诗》(900卷)不但象《御定全唐诗录》(100卷)一样是康熙皇帝御定,而且是唐诗总集,故《全唐诗》的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 康熙56年丁酉岁(1717)沈德潜(1673-1769)序《唐诗别裁集》(20卷)、乾隆28年癸未岁(1763)沈德潜又序《唐诗别裁集》。《唐诗别裁集》卷5“七言古诗”第11人为陈子昂,陈子昂名下仅收一首《登幽州台歌》,题目下注释云“不另列杂言一体,因附七言古内”[11]158。这是《登幽州台歌》第四次出现于诗歌选本中,也是第一次被视为“杂言”体,第一次被附于“七言古诗”。沈德潜对此诗还有批语:“余于登高时,每有今古茫茫之感,古人先已言之。”[11]158意思是他与陈子昂互为知音。沈德潜这话是对“前不见古人”等22字的第四次好评。 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徐兰英夫妇《唐诗三百首》(8卷)编成于乾隆28年癸未岁(1763),与沈德潜给《唐诗别裁集》第二次作序定稿为同一年。但《唐诗三百首》刊刻于乾隆29年甲申岁(1764)。《唐诗三百首》卷2“七言古诗”第一首即《登幽州台歌》,但未有《唐诗别裁集》卷5收《登幽州台歌》于“七言古诗”类时的注释:“不另列杂言一体,因附七言古内”。这是《登幽州台歌》第五次出现于诗歌选本中。《唐诗三百首》这次选录《登幽州台歌》与上次《唐诗别裁集》选录《登幽州台歌》相比,在体裁和注释上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唐诗三百首》比《唐诗别裁集》更流行,这就使“《登幽州台歌》系陈子昂诗”这个说法更加广为人知。 四、杨慎错在何处? 既然把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中“前不见古人”等22字视为陈子昂的诗并按上一个《登幽州台歌》的题目是错误的,该错误的源头在杨慎。那么,杨慎错在何处呢?这个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杨慎误记卢藏用说陈子昂登高而唱“前不见古人”等22字的地方为“幽州台”。 卢藏用说陈子昂“因登蓟北楼”,注意陈子昂登的是“蓟北楼”。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从诗题到序言到诗,都说他登的是“蓟丘”。从《陈子昂集》看,“蓟丘”还有另外3个称呼:蓟楼、蓟丘楼、蓟城西北楼。这可从《陈子昂集》中的诗题和诗句看出来。例如《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有句:“暮登蓟楼上,永望燕山岑。”[2]39《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有句:“蓟楼望燕国,负剑喜兹登。”[2]25-51“蓟北楼”的称呼出自前文所引卢藏用的《陈子昂别传》。对在昔日燕国国都登高览古的地方叫什么名字,陈子昂自己都确定不下来,称呼多达四种,那么卢藏用将“蓟城西北楼”称为“蓟北楼”应该不算错。有人也许会问:“既然卢藏用可以增加一个称呼‘蓟北楼’,那么,杨慎就可以增加一个称呼‘幽州台’。难道不对吗?”回答是:不对。卢藏用称为“蓟北楼”之所以是可以的,那是因为陈子昂怀念的是燕昭王,而燕昭王时代确实有蓟地,陈子昂也确实登过蓟地的楼。称为“幽州台”之所以是不可以的,那是因为燕昭王时代没有“幽州”这个地名,那么“幽州”这个地名是何时出现的呢?这在《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中有答案:“幽州大都督府:蓟,州所治。古之燕国都。汉为蓟县,属广阳国。晋置幽州,慕容隽称燕,皆治于此。”[12]1516《旧唐书·地理志》这注释是说,昔日的燕国国都“蓟”,从晋朝的幽州到慕容隽的燕国,再到唐朝的幽州府,一直都是州治所在地。这样看来,陈子昂说他登的是蓟丘,杨慎改口说陈子昂所登的地方在“幽州”也没问题。说陈子昂所登的“蓟丘”在幽州,这当然没问题,但是,不能把陈子昂所登的“蓟丘”称为“幽州台”。因为“幽州”这个地名是晋朝(265-420)建立后才出现的,这时距燕昭王时代(燕国于公元前314年迁都于蓟)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了。说陈子昂登“幽州台”而怀念燕昭王,就象说下一个世纪某个人登“奥运台”(假设昔日燕昭王之地的某个台被改名“奥运台”)而怀念燕昭王一样荒唐。 还有,燕昭王招揽人才的那个台,没见陈子昂登过,从陈子昂的诗看,陈子昂显然没登过。如前文所引,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第二首《燕昭王》云:“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陈子昂说得很明确,是“遥望”,既然是“遥望”,就说明没有登。另外,燕昭王置千金招揽人才的台,唐代人称为“黄金台”或者“郭隗台”。称“黄金台”者有陈子昂,刚才已说过,不再重复。称“郭隗台”者较多,例如《唐文粹》(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五(上)收晚唐皇甫松一首诗《登郭隗台》,又如罗隐《罗昭谏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县斋秋晚酬友人朱瓒见寄》云:“千枝白露陶潜柳,百尺黄金郭隗台”、徐寅《徐正字诗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草》云:“燕昭没后多卿士,千载流放郭隗台”、贯休《禅月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陈情献蜀皇帝》云:“自惭林薮龙钟者,亦得亲登郭隗台。”总之,燕昭王置千金其上而招揽人才的台,唐人称“黄金台”或“郭隗台”,从未见有人称“幽州台”,而且称“幽州台”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在杨慎之前,从来没有“幽州台”这个地名或词汇,“幽州台”这个地名是杨慎的独创,而且其使用仅见于《登幽州台歌》这首诗。 第二,杨慎误把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所说陈子昂“乃泫然流涕而歌曰”的话当作诗。 卢藏用《陈子昂别传》说陈子昂“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之知也。”“赋诗数首”后“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很明显,“歌曰”的内容就不再是诗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依据卢藏用的叙述,确实是陈子昂“歌曰”的内容,但这二句一看就不象是诗句,很可能是口头语。孟棨《本事诗》之《嘲谑第七》曰:“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13]20孟棨是唐僖宗(873-888年在位)时人,在陈子昂(661-702)之后100余年,宋武帝指南朝宋国的开国皇帝刘裕(420-422年在位)。虽然说这话可能是孟棨从《陈子昂别传》中借用的,但至少说明,孟棨认为四世纪时的宋武帝刘裕已经会讲这话了。当然,也不能认为陈子昂说几句别人说过的话或者别人的口头禅就一定不是诗。所以,这里关键的一点仍然是,卢藏用说陈子昂“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既然“赋诗数首”后才“歌曰”的,则“歌曰”出来的内容显然不再是诗了。 第三,杨慎对“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后面的话理解有误。 《陈子昂别传》说陈子昂“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后面有五句话:“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之知也。”这五句话有几句是陈子昂说的?杨慎认为前四句是陈子昂说的,问题是,如果前四句是陈子昂说的,最后一句“时人莫之知也”为何就不能是陈子昂登高而歌的内容,这一句的意思和屈原《离骚》中“国人莫我知兮”是一个含义,也符合孤独失意者的心理和口吻,杨慎为何就没有将“时人莫之知也”当作《登幽州台歌》的内容呢?也许有人会说:“‘时人莫之知也’不象是诗句。”可是前四句也不大象诗句。其实,从上下文意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二句无疑是陈子昂“乃泫然流涕而歌曰”的内容,后面三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之知也”应该是卢藏用对想象中陈子昂登高场景的描述。只是这样理解的话,仅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二句,不但不象诗句,而且明显感觉断气了。这就是卢藏用的责任了,他的《陈子昂别传》至少在这里写得有问题,写得很不好。 五、如何从《登幽州台歌》的文本发现疑点 在不检索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能不能从《登幽州台歌》这首诗的文本发现这首诗是值得怀疑的?也可以。笔者2012年4月上旬在给《登幽州台歌》写鉴赏文章时突然想到:“这不可能是陈子昂的诗吧?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笔者觉得,陈子昂登高不可能喊出这样的句子,任何人登高都不可能喊出这样的句子。道理是这样的:既然题目是《登幽州台歌》,是作者登在一个台子上念的或者唱的,那么,他当然可以想到天地之悠悠,当然可以流眼泪,还可以把想到天地悠悠的事情说出来,也可以把流眼泪的事情说出来,但是,想天地悠悠的“那一刻”,流眼泪的“那一刻”,绝不会把自己“想”和“流”这两件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那是违反生活常识和常理的,是不可思议的。其原理是,一个人做一件事的“同时”,不可能把他“正在做这件事”这件事说出来。换句话说,一个人正在做什么是一件事,这个人意识到自己正在做这件事是另一件事,这两件事的发生总是有个时间差的,不可能“同时”发生。这样解释了之后估计还是有点难懂。那还是举例子吧。例如,两人见面打招呼,一个人问:“吃了吗”,另一个人如果正面回答,那就是“吃了”或者“没吃”,但是这个回答的人绝不可能说:“我说吃了”或者“我说没吃”,除非他是第二次回答或者向他人转述(或者记日记)。再例如,张三在路上走,李四从后面追上去一棒子打在张三腿上,把张三打倒。张三肯定会惨叫一声:“啊,痛死了。”但是,被一棒子打倒的张三绝不会喊道:“我惨叫一声,啊,痛死了。”同理,一个人登在台子上,想天地悠悠就想吧,流眼泪就流吧,绝不可能说“我想到天地悠悠,我泪流满面。”尤其是,陈子昂登高而大声呼喊:“我想到天地无穷无尽,我一个人悲伤地流下眼泪。”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不查任何资料就可以断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10个字有可能是陈子昂登高所喊的话(至于陈子昂喊没喊这10个字,并不重要,卢藏用说陈子昂喊了,那就只能认为陈子昂喊了,因为陈子昂喊这10个字是可能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12个字不可能是陈子昂所喊的话。这12个字到底是陈子昂登高喊的?还是卢藏用作为旁观者的评论?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没有说明白,再加上古书无标点符号,就更容易让人误解了。(如果卢藏用说这12个字是卢藏用自己的评价,那就不能认为是陈子昂的诗句。如果卢藏用说这12个字也是陈子昂喊的,那卢藏用在撒谎,这个谎撒得很不圆,破绽太明显,因为陈子昂不可能喊出这样的话,就象张三被人一棒子打倒后张三不可能喊“我惨叫一声,啊,痛死了”一样)。然后,笔者电子检索了一下,发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子昂《陈拾遗集》十卷的正文果然没有《登幽州台歌》(《登幽州台歌》在《补遗》中)。然后通过电子检索和多种方式查阅,弄清了《登幽州台歌》被误归于陈子昂名下的过程。 综上所述,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中陈子昂“乃泫然流涕而歌曰”的五句话中,前二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卢藏用想象中陈子昂对自己心声的剖白,第三句、第四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卢藏用对自己想象中陈子昂登蓟北楼“泫然流涕而歌曰”情景的描摹;第五句“时人莫之知也”是卢藏用对陈子昂不被时人理解这种处境的交代。这五句话都不是陈子昂自己的作品,故卢藏用编《陈子昂集》时未收这五句话;唐宋元三代直到明代嘉靖26年(1547)前长达八百余年的历史中,从未见有谁视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中“前不见古人”等22字为陈子昂的作品或者诗的,更不用说给予好评了。将这22字视为陈子昂的诗并给予好评,首先源于杨慎的一时不慎,其次是因为后人的惯于盲从。杨慎之后所谓的《登幽州台歌》,既不是诗,更不是陈子昂的诗。即使今人仍然认为“前不见古人”等22字是一首好诗,那么在文学史、作品选等著作中表述的时候,对以前的说法也应该有所修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