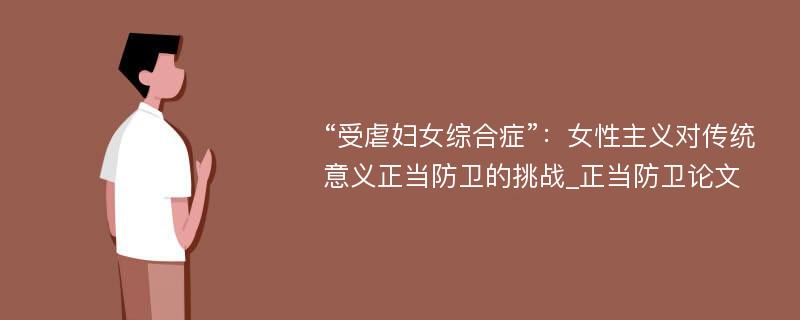
“受虐妇女综合症”——女性主义对传统意义正当防卫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当防卫论文,综合症论文,受虐论文,妇女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方掀起的女权运动无疑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主义理论以全新的视点和价值观对一切固有的、传统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评价。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女性主义法律改革运动的视点主要集中于家庭暴力、性骚扰以及对儿童的性虐待等问题上,其中最有成效的方面表现于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关注。
一、女性主义法律改革对传统意义的防卫概念的突破
近些年来,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在家庭中对暴力或暴力威胁的反应方式,以及法律体系如何评价这种反应进行了大量颇有价值的探索,提出刑法中运用“防卫”的概念必须要反映出女性的特征和经历。女性主义认为,传统意义的法律中的“防卫”都是基于一个“合乎情理”的行为标准,对“合乎情理”的解释往往是把基于男性在特定情景下的合乎情理的反应的经验作为评估的标准。如要成为正当防卫,就要证明有一个即刻的对人身的侵害以及与此对应的合适的反应,而这一“合乎情理”的认定标准及应用是歧视女性的、有缺陷的,它是男性文化主导下的产物,它仅适合于一个合乎情理的男性的行为,而并不适合于一个合乎情理下的女性的防卫特征,尤其不适合于那些长期遭受男性配偶在身体、心理及情感上虐待的女性的情形。
(一)正当防卫(Self—Defence)
各国立法普遍规定,正当防卫可完全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的提起要具备二个基本条件:1.防卫人的行为须基于对即刻的、致命的或严重人身伤害的侵害的合乎情理的理解;2.防卫人在合乎情理的理解下进行反击的不法侵害必须是正在发生的或者即刻要进行的,而且基于合理的基础上相信,除了以暴力反击的方式保护自己免遭死亡或严重伤害外别无选择,否则将面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厄运,这一要求意味着正当防卫不适用于那些当更轻缓的自卫可能性存在的情况下却采取致人死亡的防卫手段。这些传统的与正当防卫相关联的因素的要求使得认定那些杀死施虐配偶的女性是实施正当防卫非常困难,尤其是那些出于害怕自己或家庭将来遭受的致命的暴力侵害而实施杀害施虐者的情形。因为根据上述要求,如要成功地提起正当防卫,她必须证明她的行动是在特定情形下的合乎情理的反应,这就意味着她所采用的反击手段是与所受到的人身威胁程度相适应的,且这种对人身的威胁又是即刻的,即她除了给予暴力反击外,别无选择。然而对于在家庭暴力中处于高度恐惧状态下而通常在体形和体能上处于劣势的受虐女性,她唯一合乎情理的选择手段只能是在遭受暴力之后当她感到安全时才采取行动,这也许是在整个受虐过程中的一个间隙,如当侵害者正熟睡时或醉酒后无力反抗之际。然而,法律就会将她的行为界定为长期怨恨积蓄下的有预谋的行为,而不是在特定事件触发下的正当防卫反应;再则陪审团与法官往往对家庭暴力对女性的伤害及影响缺乏切身的理解,他们难以视女性的行为是合乎情理的,尽管事实上这些人身伤害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而他们往往将她使用凶器等器械对付毫无准备的施虐者视为是主动性的攻击行为,他们认为她并非别无选择,“为何她不简单地离开家庭呢?”女性主义认为,这种观点正是忽视了暴力对女性的作用力以及现实的困难,如她哪里可以去?如何维护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以及在警察的帮助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离开后对可能遭致报复的恐惧等等因素,说明离开并非是受虐女性一个合乎情理的选择。
(二)激情防卫(The Defence of Provocation)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行为人因激愤情形下而实施杀人者,可以部分地免除刑事责任。激情防卫要成立,被控者须证明他(她)因受害者的言行而导致其突然地、暂时地失去控制能力,即在激情状态下而实施了暴力攻击行为。与正当防卫的适用类似,由于女性反抗配偶的虐待而杀人的行为,因时间、采用的手段等因素难以符合法律的要求,也难以适用激情防卫。
鉴于在立法与司法中“防卫”界定的种种缺陷,女性主义一致认为法律中有关防卫的概念是建立在男性行为特征标准的基础上,由于女性出于防卫而杀人的方式有别于男性,故并不适合于受虐女性反抗暴力的反应。为此,女性主义提出刑法中防卫概念应体现出女性在遭受暴力侵害下自我防卫的经历、特点。
二、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en Syndrome)
作为对法律中“防卫”不足的反应,“受虐妇女综合症”发展为作为证据向法庭解释长期受虐妇女的行为特征。最先提出这一理论的是美国心理学者、女性主义先锋雷妮·沃克(Lenore Walker),她认为,长期生活在受虐关系下的女性,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综合症有两个特征在理解女性的防卫行为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被称为“沃克暴力循环理论”,沃克认为,许多在暴力关系下的女性能够预见下一轮暴力事件发生时间及其严重程度,因为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往往呈现出阶段循环式特征,即起始于“紧张关系形成阶段”,进而上升为“痛苦的殴打阶段”,随之进入施虐者“爱的痛悔”阶段,暴力的循环性特征意味着女性能够感觉到何时“紧张关系形成阶段”即将结束而“痛苦的殴打阶段”的开始,这也意味着女性能够从常规的暴力方式的细微变化中感受到更为危险暴力侵害的即将来临,即她们能感受到她们正面临着致命的不法侵害的威胁。
二是家庭暴力下的受虐女性经常感到有陷入感而难以离开这种关系,沃克称之为“学会无助理论”(Learned Helplessness)。沃克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说明“无助”的形成:研究者将狗放入笼中,并随意掌握电击频率,这些狗很快就明白了无论它们如何反抗,都无法控制电击。起初这些狗通过各种有意识的行动尝试着逃跑,然而所做的一切都难以阻止电击,这些狗随即放弃任何努力而变得消极顺从。当研究者试图改变一下步骤,引导这些狗可以从笼子里的另一端逃跑,它们仍毫无反应。事实上,这时笼子的门已开,出路也被展示,而它们仍消极、被动、拒绝离开,也不躲避电击。沃克认为将无助概念运用于受虐妇女,她们成为受害者的过程就变得清晰了:屡屡受虐,就如这电击,削弱了受虐女性反应的能动性,她们变得消极、被动;其次,她们对获取成功的感知能力也变了,她们不再相信她们的努力将会或可能导致任何有益的结果,她们明白无论如何都难以逃避暴力。“无助”使她们难以离开这种暴力关系,也无法改变现状、控制事态发展。
“受虐妇女综合症”对受虐妇女的偏见提出挑战。“无助”理论多方面地回答了“为何她们不简单地离开”这一问题,从而使受虐女性摆脱要么被视为受虐狂,要么是撒谎者的两难境地。它也使妇女在“无助”的心理状态下面维持暴力关系的行为被人理解。“受虐妇女综合症”指出防卫中严格“即刻”并不适应于重复发生的暴力关系。因此,女性主义学者相信“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应用有助于家庭暴力中受虐女性的“正当防卫”的要求被陪审团所接受,从而将受虐妇女视为合乎情理的防卫人。
“受虐妇女综合症”通常以专家证言的形式在法庭被展示,它有助于陪审团从几方面考虑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请求。首先,它可以消除对受虐妇女的偏见和模式化,这些偏见包括受虐妇女是受虐狂,她们喜欢暴力或者这些暴力并不如受虐妇女所说的那么严重,否则,她们早就离开了。其次,专家证言能够解释受虐妇女是如何合乎情理地感受到她正面临着死亡或致命的人身伤害的威胁,即使在一个局外人并没感受到即刻的侵害的来临。这些证言能够解释受虐妇女为何要维持这种暴力下的婚姻关系,为何受虐妇女未以“离开”作为合乎情理的选择,而是采用致命的方式对付施虐者。最根本的是,“受虐妇女综合症”能够说明受虐妇女是合乎情理地感受到即刻的人身侵害的来临,合乎情理地深信除了采取致命的方式对付施虐者外别无选择——即正当防卫适用的条件。
三、“受虐妇女综合症”在司法中的运用
“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证据的使用已在加拿大、美国以及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的司法中被接受,它大多情况下用于被控杀了施虐配偶的妇女案件, 同时也扩展到更广泛的案件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当归1992年在加拿大的“莱维丽”(R.V.Lavallee)一案。莱维丽被控犯有二级谋杀罪,杀害了她的丈夫鲁斯特(Rust),对这一事实,莱维丽供认不讳。她承认当她丈夫离开她的卧室而准备返回到正在他们家举行的聚会时,她向他后脑射击而致他死亡。本案的争议是莱维丽在这种情景下的行为能否被视为正当防卫。而出示在法庭上的证据显示鲁斯特长期对莱维丽施虐,即使在莱维丽开枪之前,鲁斯特还殴打了她,并扬言待晚会结束之后要杀了她,然而莱维丽对鲁斯特射击是发生在他正要离开卧室之时,并不符合传统的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因为莱维丽的射击行为是发生在鲁斯特正准备离开卧室返回晚会现场之时,故对她的人身威胁并非是即刻的;其次,莱维丽难以证实她是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而采取防卫以避免人身遭受侵害,即由于鲁斯特的攻击并不是即刻的,意味着莱维丽还存在其他选择:她可以选择离开家以保护自己免受鲁斯特的伤害,或简单从参加晚会的客人中寻求帮助,或者直接报告警察等等。
在法庭上,一位心理学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专家证言的目的是通过提供给陪审团长期施虐对女性的身心影响方面的资料,以克服莱维丽在提起正当防卫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专家证言的最基本内容是从莱维丽的行为方式的特征而推论出她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她是一名受虐妇女,因对鲁斯特的恐惧而感到难以摆脱,易受伤害、“无助”,难以逃避这种关系。专家证言还指出莱维丽在射击时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我认为,她感到,感到在这最后悲惨的时刻她的生命已到了极限,除非她防卫自己,除非她以暴力方式进行反击,否则她将会死去。”故专家的证言说明了莱维丽能够感觉到一个致命的攻击即刻来临,感受到她唯一的保护自己的方法是首先致鲁斯特于死地。莱维丽被法庭宣告无罪,但这一判决在上诉法院排除了专家证言的基础上被否决,而戏剧性的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坚持认为专家的证言是能够保证公正的审判的重要条件,又恢复了莱维丽的无罪判决。
莱维丽一案的判决极大地鼓舞了女性主义者,其产生的影响力远不仅在于对加拿大的司法,而是整个英美法系国家。然而在司法中类似于莱维丽如此成功的判例却并不多,莱维丽一案也并未引起受虐女性提起“正当防卫”的成功率的神奇增长。但无论如何,“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证据在法庭上的广泛使用,在司法中已被接受、运用,并对传统的意义上的“正当防卫”产生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受虐女性的处境、行为被司法实践理解、认可。莱维丽一案,虽然并不意味着所有被控杀死施虐者的受虐女性都能获无罪判决,但此案对司法的影响至少在两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莱维丽一案对公诉人的影响,此后凡是明显属于莱维丽一案类似范畴的案件,公诉人随即放弃指控;其次,莱维丽一案的主要影响还在对受虐妇女杀死施虐者的案件,检察官更愿意在被告接受伤害罪指控下达成控辩交易,而法官则趋于考虑在最低法定刑给予量刑。
四、女权主义者面临的难题
女性主义者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提出使得防卫中“即刻”的要求被重新审视,通过审视受虐妇女的行为是合乎情理及顺从理性的,而使陪审团能够理解、接受受虐女性的正当防卫请求。
然而,自“受虐妇女综合症”在法学领域最初被运用时,女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了依赖于“综合症”去解释受虐妇女的行为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首先将维持受虐关系的女性喻为患有一种“综合症”——通常与疾病或不正常相关联的词——“受虐妇女综合症”冒着将受虐女性描绘成心理不正常之风险,而容易忽视她们作为理性的、合乎情理的行为者。此外,赋予受虐妇女一系列特定的受虐特征,“受虐妇女综合症”就受制于确立了一个“真实的”受虐妇女的模式,从而将某些未能显示这些特征的受虐女性排斥在正当防卫的法律适用之外。
(一)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问题之一是冒着将受虐女性视为心理不正常之风险,因为它试图为受虐女性难以离开暴力关系提供一个心理学的解释。这一理论指出屡屡受虐导致女性处于“无助”状态,从而阻碍她们去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来反对施虐者。以这个模式,“无助”并非是受虐女性天性所具有的,而是在长期受虐下的自然反应,换言之,“无助”不是对长期受虐的一种病理性反应,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甚至一种正常的反应。
然而,在无助理论试图显示受虐女性在一定条件下的预期反应的同时,它也将受虐女性描绘成因心理遭受重伤而其感知与现实不符的病态个体。根据沃克的观点,“无助”破坏了女性的感知能力,使她们不能感受到她们“真正”可以的选择方法,限制了她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它使女性深信她们难以离开这种关系或阻止暴力,即使是现实并非如此。“无助理论”认为女性不能脱离暴力关系的感觉是非理性以及想象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意喻着女性维持受虐关系是由于她们受到严重的伤害以致于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去感受现实。
“受虐妇女综合症”也意喻女性维持受虐关系纯粹是心理原因,而不是因为“真正”的限制。这就掩盖了一个事实,即除心理受到伤害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会发现难以离开受虐关系是由于众多的外部因素所致,诸如须面对的安全问题以及经济上的承受能力。此外,传统的维系家庭完整的文化、宗教及社会压力也使女性缺乏能力离开受虐关系。所有这些须面临的顾虑对女性来说也许更为痛苦。女性主义者认为考虑这些因素对于女性维持受虐关系的原因有个全面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显示了“离开”并非如其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陪审团理解女性可能无处可去或得考虑社会压力而维持关系,他们就更可能会视女性在有限的选择方法中决定维系暴力下的婚姻关系为一个合乎理性的选择。
女性主义者提出,如果陪审团知道离开受虐关系并不能自然地结束暴力,他们就会对女性的决定有更为深切地理解。研究表明,受虐女性正是在离开施虐配偶之后常常被骚扰、被殴打甚至被杀害,对许多女性来说,离开受虐关系往往意味着比维持这种关系面临更大的危险,因而离开并不总是一个对付施虐的最好的选择方法。而“受虐妇女综合症”却使人感到受虐女性是因为心理不健全而作出留在这种关系的错误选择,这样“受虐妇女综合症”难以提供给陪审团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受虐女性是理智的行为者,而不是心理病态的受害者。
“受虐妇女综合症”试图说明女性采取致命的自我保护的方式对付施虐者是如何的合乎理性,然而通过强调因“无助”而使感知能力受限制,“受虐妇女综合症”却将女性描绘成非理性的行为者,这就难以适用正当防卫了。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陪审团越是将受虐女性视为心理偏差的群体,就越是难以接受受虐女性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正当防卫。结果是女性们基于“受虐妇女综合症”而提出的正当防卫的适用将更为困难。
(二)
女性主义者们也关注通过赋予“无助”一系列确定的特征,“受虐妇女综合症”也趋于将受虐确立一个固定的模式,即她们应是消极的、顺从的,对施虐者及在生活的所有其它方面均表现为无能的、懦弱的。问题是受虐女性并不是同一模式的,受虐关系中的女性完全能够以坚强及智慧的姿态出现,而不仅仅是无助和消极顺从。例如,受虐女性会机警地试图阻止或至少控制配偶的暴力,许多女性还能采取主动攻击的行为去对付施虐者,要么防卫自己免受施虐,要么当殴打发生时快速促成一个暴力的间隙作为一个控制方法。另外,在家庭中遭受暴力的女性并不意味着她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具备竞争力。总之,由于“受虐妇女综合症”寄如此大的希望于“无助”,陪审团可能会将那些具有主动攻击行为的或者显示出自我保护能力的女性视为因“无助不足”而不是真正的受虐女性。
陪审团也会期待受虐女性为“真正”的受害者,正如模式中“受虐妇女”的原型。结果女性越是远离品行良好的女性形象,陪审团也越是难以视她为受虐关系下的无助的受害者。那些具有酗酒或吸毒劣习、使用粗俗语言或曾涉嫌违法活动的女性,使用“受虐妇女综合症”成功的可能性较小,并非是她们提出正当防卫的理由不够充分,而是陪审团不太可能将她们看作是真实意义的受虐妻子。这种模式化的适用可能对那些有色、土著以及贫穷女性来说更为苛刻。
尽管“受虐妇女综合症”在适用时有着诸多问题,但是女性主义者们还是希望它的适用在总体上的效果是积极的,使正当防卫的理论更适合于女性,以保证在司法中的性别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