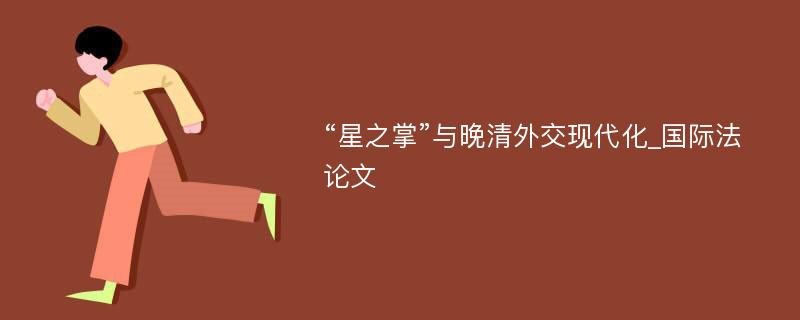
《星轺指掌》与晚清外交的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外交论文,近代化论文,星轺指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 (2006)06—0074—08
《星轺指掌》是清光绪初年继《万国公法》刊印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与同文馆学生合作翻译的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外交礼仪制度的国际法著作,它的翻译刊行,将晚清外交近代化及对国际外交礼仪制度的掌握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一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于1869 年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兼公法学教习。他重视西方“实学”的介绍,同治十三年(1874)即提出译书计划,开列六条章程,呈请总理衙门批准在案[1](P64)。为了系统地向中国介绍国际法,使中国人了解并使用国际法,以利于对外交往,他表示将“陆续增译各国名家著作,俾中华文人学士虽未通习洋文,亦得窥泰西往来交涉之道,庶几对镜参观,不致为一国议论所囿从”[2](卷首“自序”,P1第2面),并着手翻译其他国际法著作,其中最早的是翻译《星轺指掌》。此书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证和澄清。
其一,关于《星轺指掌》翻译时所依据的外文原书,学术界的研究和叙述并不详尽。在《星轺指掌》卷首的“凡例”中,译者提及了原书情况。第14条称,原书“于道光初年初刊”,“原书行世既久,复经名士葛福根者重行刊印,加以注解”;第16条称,“原书分为二部,兹所译者首部”;第22条称,“是书原刊以法文”[3](卷首,“凡例”,P3—4)。以上材料表明, 《星轺指掌》所依据的外文原书为法文版,道光初年出版,后经葛福根作注并重印;原书分为两部,译出部分为首部。
笔者在美国查阅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图书馆收藏的《星轺指掌》最早的1822年和1866年两种法文版原书。此书1822年在法国巴黎由Treuttel et wurtz出版公司出版,作者为Charles De Martens,简写书名为“Manuel diplomatique”,全名为:“Manuel diplomatique:ou,précis Des Droits Et Des Fonctions Des Aagens Diplomatiques; suivi D'un Recueil D'actes Et D'offices Pour Servir De Guide Aux Personnes Quise Destinent A La Carriere Politique”。全书624页,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0章173页,为叙述性内容;第二部分为附录,是各种文件汇编。1832年在巴黎再版,书名改为“Guide diplomatique”。1851年又在巴黎以法文出版,书名改为“Le guide diplomatique”。1866年,德国莱比锡(Leipzig)F.A.Brockhaus出版公司又以法文出版(应为第五版),书名与1851年版相同,作者名字为Le BN Charles De Martens,作注解者的名字为M.F.H.Geffcken,即《星轺指掌》中所写的葛福根。全书12章300页,无附录,只有一页勘误表。1822年到1866年版的书名虽不同,但简写书名的意思基本相同,可以翻译为《外交指南》。
《外交指南》原书有以上版本,丁韪良等翻译时依据的是哪种版本呢?从内容上分析,书中第一卷第二章第二节叙述了日耳曼各邦于1864年派遣柏思为钦差大臣前往伦敦大会;第二卷第六章第一节记载了1859年和1861年,萨国君主改称意大利君主[3](卷一,P11第1面;卷二,P2第2面)。书中记载的事件到1864年,原书出版应晚于1864年。笔者又核对了目录,发现《星轺指掌》的章节编排与1866年法文版基本相同,只是此法文版为12章,而《星轺指掌》为14章,这与《星轺指掌》第十三章开头注明的“论领事原归一章,因过长,分为三章”的说法正相吻合,原书的第十二章分为《星轺指掌》的第十二至十四章。由此推论,《星轺指掌》翻译时所依据的外文原书,应为1866年德国莱比锡法文版。但如何解释《星轺指掌》“凡例”第18条中“原书第二部系各种文件程式,其国书、照会、信函、节略、条约皆有之”,而1866年版并无以上内容?笔者认为,“凡例”中所讲的各种文件程式, 应是指1822年版第二部分的相关内容,或1832、1851、1861年版中可能包括的第二部分内容(注:笔者未见到这三种版本)。
其二,关于《外交指南》原书的作者。译者在“凡例”第13条中介绍说,“原书为布国马尔顿所著。按马氏不但博考诸家,融会贯通,且身膺公使,历有年所,故其撰述通使条例,见重于世。”[3](卷首,“凡例”,P3—4) “布国”在《星轺指掌》中经常出现,现在译为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在1822年和1866年法文版《外交指南》中,作者全名为Charles De Martens,有时写为Martens,Karl freiherr von,freiherr意为“男爵”或“贵族”,放在姓名中间,为习惯用法。按现代音译标准,Charles de Martens的中文译名应为查尔斯·D·马顿斯。 笔者查阅了美国英文版《新世纪人名百科全书》,在Martens,Baron Karl von(Baron与法文freiherr的意思相同)的条目下记载他1790年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ort on the Main),1863年3月28日卒于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曾任外交官,是国际法专家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的侄子,著有“Guide diplomatique”一书[4](P2639)。以上材料证明,查尔斯·D·马顿斯是德国人,是《外交指南》一书的作者。
关于《星轺指掌》外文原书及作者,丁韪良在英文回忆录“A Cycle of Cathay”(《花甲忆记》)中亦有简单记载,他记载的作者名字为De Martens,书名为“Guide Diplomatique”[5](P235),这与本文上述的考证基本相符。
其三, 关于《星轺指掌》中文版最早刊行的年代。 对此学术界有光绪二年(1876)和三年(1877)两种说法。笔者查阅了国家图书馆分馆古籍部收藏的《星轺指掌》的几种版本,其中最早为一函四册大开铅印线装本,四册封面各以“元”、“亨”、“利”、“贞”汉字排列顺序。扉页中间题写着篆体“星轺指掌”书名,书名右边为出版年代“光绪二年仲秋月”,左边标明“同文馆聚珍版”。这是本书出版年代、刊刻机构的一种记载。书中还有总理衙门大臣董恂为该书写的序言,落款时间是“光绪丙子夏五之闰”。“光绪丙子”即光绪二年,“闰”即闰月,光绪二年为闰五月。按此记载,董恂的序言应是1876年6、7月间写作的。另外,“凡例”第23条记载:“泰西纪年悉从耶稣降生始……至今阅一千八百七十六年”[3](卷首,“凡例”,P3—4),此年代即写作凡例的时间。以上从序言到凡例到扉页的三种记载,均证明该书刊印于光绪二年。据此,笔者认为,《星轺指掌》正式刊印成书时间是“光绪二年仲秋月”,即1876年9、10月之间,或稍晚一些,但不会迟至光绪三年。
根据以上考证,笔者认为《星轺指掌》翻译时所依据的外文原书,为德国国际法专家查尔斯·D·马顿斯所著的《外交指南》,版本为1866年法文版, 该书中文版最早刊行于光绪二年,即1876年。
二
《星轺指掌》的“凡例”指出,此书“其翻译华文,系同文馆学习人员联芳、庆常初稿,而贵荣、杜法孟稍加润色,复经丁总教习为之校覈”。对这几位译校者,在此略加叙述。
联芳与庆常为满族人,翻译《星轺指掌》时是同文馆学生。在丁韪良主办的《中西闻见录》第11号和21号中刊有联芳的译作。他们肄业后留在同文馆,并参与翻译《公法会通》,稍后被派往法国,任清政府驻法公使馆翻译。丁韪良于光绪六年十月游历各国,抵达法国时,联芳曾“伴游于名胜之区”,庆常也与他会面。不久联芳任署驻俄参赞[6](卷上,P28)。在《花甲忆记》中,丁韪良称“庆常君在欧洲政绩卓著,曾数次出任驻巴黎代办”[7](P221)。
贵荣也是满族人,肄业于京师同文馆。《中西闻见录》第20、23和25号刊登了他的“同文馆月课格物试卷”等,后来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在光绪三年三月号又刊登他在同文馆的“算学奇题”。如此频繁刊登他的试卷等,说明其成绩优秀。除参与《星轺指掌》的润色,贵荣还参与翻译《公法便览》和《公法会通》。《公法便览》“凡例”称,此书“司校阅者二人,为贵荣暨前同文馆学生桂林,而贵荣更于前后加以琢磨而润色之”[2](卷首“凡例”,P5第2面)。《公法会通》的“凡例”称,此书“前半为法文馆副教习联芳、庆常、联兴繙译,余为余(注:丁韪良)口译,由天文馆副教习贵荣、前同文馆学生桂林笔述,复经贵荣前后逐细校阅”[8](卷首“凡例”,P2)。
贵荣还曾为丁韪良的著作《西学考略》写“跋”,对他与丁韪良的师生关系稍有描述,“荣肄业同文迄今十有六载矣。从壬叔(注:李善兰)先生攻历算之学,从冠西先生(注:丁韪良)攻格致之学,凡观察、推步、测量、创造之实际,星电、水火、光气、声力之要端,极承两先生口讲指画,几阅寒暑,殚思日久,始窥其奥窍于万一。同人繙译西书十余年来,如《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俄国史略》,蒙冠西先生任以校字之役,复为之朝夕讲解,始知邦国往来之道,战和交涉之例,以及世代盛衰之由。上下四千年之久,东西七万里之遥,犹全豹之见一斑也。”字里行间,表现出贵荣对丁氏的感激敬佩之情,对他的《西学考略》也极为推崇,称此书“可以不朽矣”[6](卷下,贵荣:《西学考略·跋》,P1—2)。贵荣称自己在同文馆肄业已16年,应是指从开始在同文馆学习,到结束学业、留馆任教直到写此跋的时间。此跋语写于光绪八年十一月,即1882年底。由此推算,他入馆应在同治五年(1866),当时丁韪良刚入馆任英文教习。京师同文馆创办于1862年,贵荣是较早入馆学习者,结束学业后留馆,后官至内务府郎中,同文馆天文馆副教习。
杜法孟(Tufamen)也是同文馆学生,同治十二年二月刊印的《中西闻见录》第8号刊出了他的试卷。杜法孟应是同文馆的“大龄”学生,丁韪良称他是已经当上了祖父的老学生,1874年曾随一位学政赴湖南作为数学主考官[7](P216)。
贵荣、联芳和庆常与丁韪良的师生关系密切,他们能参加译书,说明语言能力很好。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中曾指出:“同文馆最初设立的目标是为了培养口译人才,但从口译转向更高一层的别国文献翻译,以为己用,则是一个自然而又必然的发展步骤。我就任总教习之后,便组织了一班译员,其中有教习,也有冒尖的学生。这是经总理衙门批准成立的,凡工作勤勉、成果斐然的人都能得到奖励。”[7](P216) 他们参与翻译的国际法著作,从文字上讲,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
丁韪良是《星轺指掌》的审定核校者,与此书关系极为重要。可以说,从确定书名,到挑选翻译人员,以及最后核校定稿,都由他一手操办。所以,人们在介绍《星轺指掌》时,都要重点介绍丁韪良。丁韪良的基本情况和经历无需赘述,笔者只想讲明以下几点。第一,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校定的《星轺指掌》,以及稍后的《公法便览》(1878)、《公法会通》(1880)、《陆地战例新选》(1883)这五部国际法译著,基本上将西方最新、最有代表性的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这些译著涵盖了国家主权、外交、战争、海洋、公民权利等国际法的主要内容。第二,丁韪良是较早向中国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西方人,另外的一些国际法译作,如傅兰雅的译作,基本上都晚于丁韪良主持的译作,从这点来讲,丁韪良是中国国际法的奠基者。第三,丁韪良系统地向中国介绍国际法,目的是希望中国人掌握国际法,以利于对外交往。在《公法会通》的“自序”中表明,编辑国际法名作,是为了“用资印证,则中华士大夫虽未肄习洋文,而于公法之学,亦得悉其梗概”[8](卷首“万国公法会通序”自序)。在《陆地战例新选》的自序中也指出,“公法原有息争免战之策,然战有不可免者,则邦国扬威而不失仁,力争而不忘义,岂不美哉?”[9](P46) 显然,他翻译国际法书籍的主要目的,是要使知识界了解国际法,并使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加以运用。
三
中国古代习惯上称皇帝的使臣为“星使”,称使臣所乘车为“星轺”,至晚清仍沿此习。顾名思义,《星轺指掌》即使臣必备之书,此书主要论述西方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之后,各国因相互交往而逐渐形成的外交制度、准则和礼仪。由于作者既出任过外官,又有家学渊源,其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该书正文三卷14章,续卷一卷。第一卷通使总论,叙述了外交缘由,主持外交事务的总理大臣的职责,各国通使之例等。第二卷论使臣与礼节,这是全书的重点,包括使臣享有的各项权利、职责及往来礼节等。第三卷论领事官,包括其选派、职责等。续卷介绍公文程式,包括国书、照会、信函及呈递国书礼节。该书的翻译刊行,将叙述外交制度的专著介绍到中国,填补了晚清外交制度书籍的空白,这是此书的重要价值所在。它给晚清统治下的中国介绍了近代西方新的外交制度、国际关系准则、外交礼仪规范,以及新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关于外交制度的起源、机构及通使之权。西方外交制度起源于欧洲分为群国之后,各国因互相往来,“始而遇事偶有通使,继则遣使常川驻扎。”遣使目的,“一则通两国之好,一则察邻国之政,达之本国”。各国也在京师设立专办外交的衙署,“始而名曰外务部,继则名曰会议部,后则定为总理外国事务衙署”[3](卷一,P5)。关于通使之权,《星轺指掌》将各国分为自主、半主、众邦合一和数邦联合之国,“自主之国,方可遣使接使。半主之国……其能否通使,当从上国之命”。“众邦合一之国,其通使之权,皆归上国。至数邦联合之国,其通使之权,仍操之各邦。”[3](卷一,P10—11) 通使之权对各国非常重要,“惟国主能操其权”,“国内不可一时或缺。”[3](卷一,P12第2面)
第二,关于使臣等级、遴选标准及应具备的才能。在第一卷中指出,使臣分为常使、特简和密使三类,常使又分为四等,即安巴萨多尔(大使)与教皇使臣、特简公使与全权大臣、驻京大臣、署理公使与办事大臣[3](卷一,P19第2面,P24—29)。使臣“须精通通使之学”,重要者包括公法及各国通例、律例,历史大势、富国策、风土人情、户口,各项文件程式,还要通晓各国语言文字[3](卷一,P2—3)。在第八章中又论述了使臣要勤于公务,包括通晓两国交际之道,要与本国执政大臣意见相同,尽心办事,体察彼国情形。使臣的处世之道,包括与人相处,要小心谨慎;与人会晤不动声色,不使喜怒达于面目;谦虚而不自满;衣冠整肃;要有辩才并通杂学;交友贵乎亲近,择友贵乎详慎;要保守秘密,善为应酬,不可一味俭啬,更不可欠债不还;应以廉耻为重,勿赌勿淫[3](卷二,P33—40)。这些标准及要求,不但对于使臣,即便对于各界人士,至今都具有指导及借鉴作用。
第三,使臣的权利及职责。第六章集中论述了使臣权利,包括使臣不得禁锢;诸事自由;使臣及公署不归地方管辖;使臣有罪案和争端地方不得拘审。使臣还享有免税、在公署礼拜、管辖随使人员、在路过之国享有特殊权利等[3](卷二,P1—21)。使臣职责,主要有管辖、保护本国人民,为本国人民颁发护照; 在驻扎国“广询博访,据所见闻,随时奏报本国”,包括该国兵势军情、通商船只、工艺制造、库帑与地丁钱粮、炮台武库、市镇信局、运河铁路等;使臣还有商议公事,议立条约,调处两国争端等职责[3](卷二,P40—50)。
第四,关于各国往来礼节。主要包括使臣与驻扎国君主及宗亲往来礼节,使臣之间往来礼节与文件程式,国君、公使、领事官在海口、洋面相遇的礼节等。根据国际公法,“凡自主之国,俱用平行之礼。虽国势强弱不一,其权利并无参差,则均有自主之权也。故无论何国,应以国体为重,而遇有屈抑藐视等情,均应一体伸雪,以昭平允。”[3](卷二,P60)
第五,关于领事官的遴选标准、权利及责任。领事官的设立,始于八九百年前,“查设立领事之意,实系驻扎外国口岸,专办通商事务之员”[3](卷三,P2第2面)。国君操简派、接纳领事之权。由本国特遣之领事,“必遴选品学兼优之员,在本国既素所亲信,在他国必令人敬服”[3](卷三,P4)。领事官的权利不能与公使相等,但也享受格外优待,包括可将国旗悬于公署门首; 如非驻扎之国人民,亦无另有经营,即不输纳各项饷钞,不可因争讼而拘禁,地方官一般不得追究;领事公署文件,地方官不得借端搜查抄封。领事官的职守,“系稽查航海、通商事务,保护本国人民安居乐业,代办约契字据,代向地方官伸诉冤抑,为本国人民调处争讼等事。”[3](卷三,P1第2面) 即领事有审断之责,本国人民有不协之处,可由本国领事审断讯办;领事应保护本国船只水手,遇险当救,有冤代伸;处理本国人民在外身故遗产;为本国人民办理登记、发给文证。领事官还应“勤于实学”,“其尤要者,如两国航海、通商律例,与吏治章程,并富国策、百物表等事,皆当实力讲求。并应学习方言,交接绅民,采访舆论,广其闻见。至彼国制造各法,土产货物,每年所产大概数目,以及每局工人若干名,工价若干,领事必须考察,与本国土产、通商事务互相比较”,“如查两国通商,似应推广,方可隆盛,即当禀明本国,设法办理。”[3](卷三,P11—26)
第六,《星轺指掌》还介绍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在《万国公法》的基础上,《星轺指掌》对西方国家的思想观念及政治制度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在“凡例”中介绍了“民政之国”、“国会”及三权分立原则,“庶民公举国主,而其在位限有年数者,是谓民政之国”,“凡君权有限之国与民政之国,皆公举大臣,会议国政,是谓国会。君位虽尊,而权势往往操之于国会”,“君权有限之国与民政之国,率由国会公议以制法,国君秉权而行法,复有专设法司以执法,而审讯不法之事者,此谓之法院或法堂”[3](卷首“凡例”,P2第2面)。在“通使总论”中提及了富国策,第一章中提及了“国体”,第二章提及了“政体”。第二卷第六章叙述了“公罪”与“私罪”之分,“公罪”即妄用权位之类,“私罪”即伤害人民之类。同时,书中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近代邮政制度、铁路设施等。
另外,《星轺指掌》还介绍了国家之间遇有纷争时的调处,水师、商船在洋面相遇的礼节,使臣、领事的随员及眷属的权利,国际会议的相关问题等新知识。
四
《星轺指掌》一书刊印之后,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先进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首先,此书的刊印正值清政府向外国派遣使臣之际,它为早期驻外使臣提供了较好的教科书,使他们通过阅读此书,了解西方近代外交制度、惯例和礼仪。清政府向海外正式派遣使臣,始于光绪二年九月底(1876年11月)郭嵩焘出使英国,而《星轺指掌》的刊印也恰在此时,其后清政府向海外派遣的外交官员,基本上都阅读过此书,并将其带到出使之国,以供参考。可以说,此书是晚清30余年间使臣们的必读书。郭嵩焘在出使前即与丁韪良有一定交往,在1876年2 月所写的《中西闻见录选编序》中即提到了《星轺指掌》,当时该书尚未刊印,郭嵩焘可能见到了书稿,称其内容“有济实用”[10](卷首,P2)。二月十四日(3月9日)丁韪良向他出示《星轺指掌》译本,郭嵩焘在日记中认为第49、50节“尤多见道之言”,在出使前数次与他相谈[11](卷一,P6—21)。在英国期间,他所阅读的书籍,即有《公法便览》和《星轺指掌》。他对国际法方面的一些学会组织及活动较为关注,这与他和丁韪良的交往及其译著是有关系的。继郭嵩焘之后的使臣曾纪泽与丁韪良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他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多次提到阅读《星轺指掌》及《公法便览》等书。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也曾携带此书,光绪十七年四月十五日(1891年5月22日),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根据《星轺指掌》的内容,分析了以参赞署理公使(或称“代使”)的情况,他认为,“各国皆派专使,必其使臣有事请假,乃用参赞署理。中国使者兼摄数国,往来驻扎,未尝离任,安有另增一署理公使之理乎?此其沿用洋例旧称,本属不合,亟应厘而正之。此事使臣有应为之权,不必请示总署,但咨请立案,或云令参赞某转报而已。”[12](P367—368) 而且,自晚清开始向国外派驻外交人员,他们的职衔称谓,包括公使、参赞、总领事、正副领事,以及国书、护照等外交专用名词,或出自《星轺指掌》,或由此书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其次,此书及丁韪良本人,为清政府提供了对外交涉的措施和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万国公法》一书,只简单地提及领事官,《星轺指掌》则详细论述了领事官的设立、分等、权利、职责等,这些新知识被清政府接受和采用,1877年后在新加坡、日本、古巴等国设立了领事馆,派遣了驻外领事,对保护海外华侨、发展海外商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驻外使节也能引用国际法知识为中国争取权益。如驻美公使崔国因曾就禁止华人条例与美国多次交涉,使美国自1888年开始施行的苛待华人条例在两年后废除,事后他曾指出:“此例属违公法而背条约,废之自是理所当然”[13](P156)。光绪十七年正月,据薛福成日记记载,当美国派遣煽动排华与迫害华工的参议院议员布雷尔继田贝为驻华公使时,清政府即电告驻美公使崔国因知照美国政府,拒绝接受他出任驻华公使,“盖因其挑唆美民,不许华工入境”,“迎合众情,创立新例,禁绝华工,实与条约命意相悖”。其后,美国国务院只能撤销对布雷尔的任命,将行至旧金山的布雷尔召回。薛福成认为清政府此举是正当的,并有前例可寻,“中国如不愿接他国派来使臣,自有此权利也”[12](P305,361)。在出现战争状态时,清政府也能妥善地处理侨民问题,如中法战争发生后,清政府及时征询丁韪良关于如何对待敌方非战斗人员的意见,在上谕中保证保护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法国人免于伤害,只要他们静处其地,从事和平职业,不以任何方式参加冲突。最后,居于内地的法国传教士无一被害,丁韪良称这场战争“对中国而言,这种结果就等于胜利。她坚强起来,不再像从前那样让自己因受战争的威胁而遭受欺侮”[5](P396—397)。
又其次,《星轺指掌》的刊印,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阅读之后,更进一步地了解国际法及外交准则,促使他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王韬、陈炽等都曾阅读此书及丁韪良组织翻译的其他国际法著作,并对中外关系及国际法有所评论。王韬认为此书“纪海外诸国遣使往来之事特详,凡膺海外皇华之役者,可取资焉”,他期盼在外交中与西方“结信讲好”,但也认识到与列强打交道的艰难,因为列强在华“官以卫商,兵以卫官,似若有所恃而不恐”,他将外交看成一场战争,提醒外交官们“宜若何郑重哉?!”[14](卷九,P1—2) 薛福成在1892年所著《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一文中指出中外通商之后,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如各国商埠,独不许中国设领事官;而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相埒;洋人杀害华民,无一按律治罪者;近者美国驱禁华民,几不齿中国于友邦”[15](P157)。郑观应将实行公法与国势强弱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16](上册,P314)
当然,《星轺指掌》等国际法著作如拘泥条文不思变通,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有些官员在对外交涉中过于依赖国际法,使国家民族利益受到损失,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战前,面对日本的备战挑衅,他告诫叶志超“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17](卷16,P25,总第7册,P3891)。丰岛海战后,他又幻想英国干涉及列强调停,导致贻误战机,战败求和。直到病逝前夕,他仍未觉悟,将国际法看成公正之体现,认为“守之则治,违之则乱”[18](第1册卷首),仍没有真正领悟“弱肉强食”的道理。
五
《星轺指掌》一书存在严重的消极内容,即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宣传了对非洲及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在《星轺指掌》第三卷及续卷中,都有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历来欧洲各国领事,俱有审断之责,迩来其权稍杀。原审断之权,出于管辖之权。而管辖之权,本出于国之自主。故各国恐领事审断案件,与地方官互相牴牾,于国体有碍,遂渐减领事之权,以免争端。”[3](卷三,P11) 这里讲明欧洲各国由于管辖权、自主权的逐渐扩大,使领事审断权逐渐被削弱和控制。西方各国实行领事审断制度的大旨,一是“奉教诸国,所立条约内载,本国人民遇有不协之处,愿请本国领事审断者,即由领事讯办。如不欲请领事审断,或领事审断不公,俱准呈诉地方官”,这相当于仲裁制度,领事官无最后决断权;二是“领事之权若无条约可循,则照领事则例,并两国法律,及国君谕旨办理。然祗查则例、训条等件,不足定其权利,仍俟驻扎之国允准,始可行其权”,这强调了驻扎国的主权;三是领事官在审断中的权利是有限和受到制约的:本国人的轻罪可由领事审理,“其罪重者,不准领事查办”,本国商民、船主等彼此争执,“领事当设法调处,使不成讼。……至已经官者,无论词讼罪案,俱归地方官办理”,“遇本国人民因案被地方官缉拿,或案情重大,恐其监禁与拟重辟等情,领事亦可亲到公堂指示该犯,但不得袒庇”[3](卷三,P11—12)。总之,基督教各国之间实行的领事审断制度即领事裁判权,基本上不危害驻扎国的主权。
但是,西方殖民者在东方各国所实行的领事裁判权制度,却是另一种情形。泰西各国间实行的“无论何国人民,居住某国,即归某国管辖,故遇有不法情事,无论何国人民,应由犯事地方官审办,别国不得与闻”的平等制度在信奉伊斯兰教各国不能实行,理由是,“回国法律风俗,与泰西各国大相悬殊,而领事之权利,亦有别也。况各国人民前往土耳其等处贸易游历者不可胜计,若任凭土国管辖,是交良民于污吏之手耳,故与回国议立条约,不可不设法杜弊”,“西国领事驻扎土耳其等国,按约享受权利,异于寻常,俾得保护本国人民”。
基于上述理由,西方各国以条约为依据,强迫土耳其、埃及、波斯等伊斯兰教国家接受领事裁判权制度,内容包括:第一,本国商民水手人等归领事管辖,遇有彼此不协,由领事自行审理;第二,本国人民与回民互起争端,及杀伤人口重案,地方官不可自行查办和定案,必须与领事及翻译官公同审讯,“以免屈抑”;第三,地方官查拿领事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一经领事收留,则回人及“地方官概不准擅入领事公署追捕罪犯”;第四,“本国人民及别国人民被地方官拿获,若领事愿具保释禁,亦听其便”;第五,本国人民犯有重罪,或被人呈控举报,领事要进行查证,“如查该犯果有罪名,即应照例差缉”。“一俟拿解到案,由领事传集人证,严行审讯,并将原控各节会同绅商逐细查询。如果情真罪当,即将该犯拘禁,俟船只回国之便,将人犯及卷宗、证据解送本国上宪审办。”[3](卷三,P28—32) 这种制度凌驾于驻扎国主权之上,严重地破坏了伊斯兰教国家的管辖权和自主权。
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侵略者也将领事裁判权制度强加给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星轺指掌》续卷中记载了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第一,美国人民在中华、日本等五国领事界内犯罪轻重(一切犯法之举),皆由领事官审讯;第二,美国人在领事界内因财产等而起争端,可由领事官断定。同时规定,在中华、暹罗两国,此等案件由领事官会同地方官审讯[3](续卷,P9,P31—32)。
规定美国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最早的不平等条约是1844年7月3日的中美《望厦条约》。条约第21款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拏(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拏(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第25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第24、26等款也有相关规定[19](P54—56)。这些规定,与《星轺指掌》的记载基本相同。 丁韪良及《星轺指掌》宣扬了领事裁判权制度,意在维护美国在华这一侵略特权,暴露了他的殖民主义心态。
《星轺指掌》在翻译中,也存在着与《万国公法》一书相类似的问题,一是对原书有所删改,如第二章第二节“论通使之权”删去了一些注释内容。二是有些专有名词的翻译采用音译,如将总统译为“伯理玺天德”,将ambassadeurs译为“安巴萨多尔”(法语“大使”之意)。这些译法有其局限性,未被后人采用。
总之,《星轺指掌》一书作为较早翻译的西方国际法及外交学专著,填补了中国外交学著作的空白,开阔了中国国际法的领域,虽有消极内容,但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对先进中国人思想的启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 2006—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