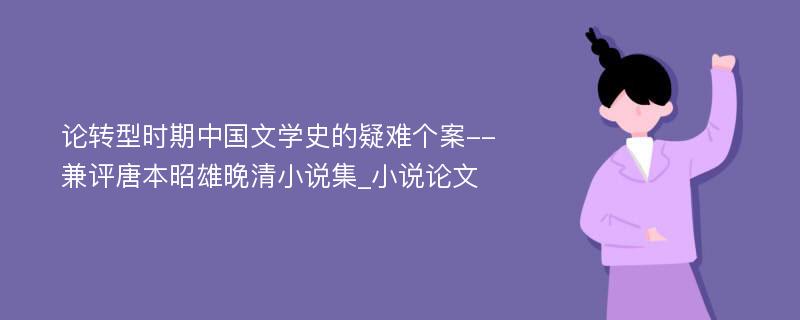
为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史破解疑案——推介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案论文,转型期论文,清末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的樽本照雄教授是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专家。他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于2002年由齐鲁书社译介到中国来之后,已成为我国研究该时段小说的学者案头的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樽本先生的著述甚多,主要著作有《清末小说闲谈》、《清末小说论集》、《清末小说探索》、《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清末小说丛考》、《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增补版)》和《汉译天方夜谭论集》等等。其实他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比齐鲁书社出版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更为实用,更能一目了然地看清我国该时段小说出版发行的系年系月、甚至是系日的著译情况。这一“年表”在日本还荣获1999年的“芦北奖”,可惜至今还未在中国出版。
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樽本先生对中国文学转型期的许多精彩的见解还未能为中国同行们所知晓(虽然他有时也用汉语撰写文章在中国刊物上发表,但为数不多)。这次,齐鲁书社又出版了樽本先生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2006年8月版,陈薇监译),这使他多年来的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有创见性的重要结论,比较集中地得到了一次展示,大大有助于他与中国同行之间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
一
樽本先生研究清末民初小说始于我国的“文革”时期,1977年他创办了一种研究清末小说的专门刊物《清末小说研究》(年刊,自第8期起改名为《清末小说》),至今已出版了29个年头(也即出版了29期);他于1986年为了便于与国内外同行专家交流又创办了《清末小说通讯》(季刊),现已出版至84期。他自述之所以以研究清末民初小说为自己的主要课题,一方面是因为他陆续“在日本竟意外地发现了若干珍贵的文献资料”,对清末民初时段的“长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他对“五四”以后中国学界给予清末民初小说的评价表示堪忧:“从五四以后文学革命的角度来看,清末小说应成为打倒的对象。……清末小说所受到的评价非常低,资料很难保存。没有资料,就不能进行研究。没有研究,评价就会更低,研究者就更会失掉收集资料的热情,从而引起恶性循环。”其实清末离现在不过百年左右,可是有些重要作品的作者的真名实姓与生平事略已经“失传”。例如以中外商战等为题材的《市声》,是清末少数写商业题材的重要作品之一,可是作者姬文的生平背景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小说《禽海石》一开头就对孟子所说的男婚女嫁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的话提出了指责与控诉;在艺术上,此书也是首次将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真正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的优秀章回小说,可是作者符霖的生平也鲜为人知。我们只是在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62页)中查到他的真名叫“秦如华”,咸丰至光绪年间人。可是陈玉堂并没有注明他根据的是何种典籍,而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叫“秦如华(字镜如)”。那么作者是用自己的真名作为书中主人公的名字的?既然在小说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名,还有必要再用一个笔名吗?这也是一个至今无法得到答案的谜团。凡此皆是“恶性循环”所留下的严重后果,都有待于我们以后下工夫去破解的。
樽本先生这本《清末小说研究集稿》的确为清末民初的小说研究中的若干谜团解疑。可是仔细阅读他的篇篇论文,我们才知道,他的所谓“疑”和“谜”,在我们过去看来是一点也不疑的,可以说大多是已经有了“定论”。这些定论又曾被学界同行在自己的论文上反复加以引用。樽本先生却通过大量的资料挖掘与积累,从这些“定论”中找出了疑点,他的解“谜”的过程就是用自己的“考证”推翻这些“定论”,得出新的结论。正如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的任何论文是在完成了对资料的考证之后进行论证的,我的若干见解,将否定历来的定论。这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例如,过去阿英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写道:“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的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的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①阿英是根据他的“家藏”晚清小说编出了《晚清小说目》。他的家藏的确丰富,据他的统计,在1004种晚清小说中翻译有590种,即翻译占60%。但是樽本所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比阿英搜集到的小说数量要多得多,除去民初小说外,其中晚清小说的总数是2632种,根据樽本的目录统计,创作小说为1531种,翻译是1101种。翻译只占42%。因此他的新的结论是:“创作显然多于翻译。这才是事实。”樽本解释说:“当然也有翻译比创作多的时期。从1902年到1907年,翻译比创作多一点。但没有明显的差别。从1908年创作开始比翻译多起来,它们的差别比较显著。”如果我们查阅樽本先生所编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1999年版),那么1908年的数字是创作254种,翻译153种。再分析创作在这一年会大大超过翻译的原因是:一方面,吴趼人主持的《月月小说》占了35种,而黄世仲主持的《中外小说林》占了20种。他们两人主持的小说刊物占了一个很大的份额。当然,黄人与徐念慈所编的《小说林》也占了7种,而他们与曾朴所办的“小说林社”也出版了8种书。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日后成为文学革命健将的年轻人也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如胡适参与编辑的《竞业旬报》在那一年就发表了13篇小说。再加上商务印书馆和改良小说社等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创作小说的数量也在节节上升,种种因素都促成以后的创作数量高于翻译数量。这篇细账算下来,对我们特别有启发的是:一批后来被指认为鸳蝴派的所谓“旧”作家,在晚清的文坛上起着顶梁柱的作用,他们在清末民初是撑大旗的,他们的“小说生产”越来越旺盛;而新兴的日后成为文学革命中坚力量的新作者,也在成长之中,蔡元培在1904年发表了《新年梦》,陈独秀在同年连载《黑天国》,而周作人的创作是起步于1905年的《女子世界》,胡适在1908年就发表了3篇小说;紧接着是1909年《小说时报》、1910年《小说月报》等多种小说杂志的创刊。这种种因素,使中国的创作小说从1908年后方兴未艾,中国的小说创作显得后劲十足,终于使中国20世纪的文坛,几乎成了小说世纪。樽本这一对文坛的总体估价是十分重要的,而得来也是不易的。这不仅是一个下工夫广搜资料和细心编目的问题,而且要对清末民初这个转型期的文坛新的动向有新认识,才能得出这个新结论。樽本充分肯定阿英的《晚清小说目》的成就,指出它有四个特点:1.收录的小说种类多,大大超越前人;2.不是根据第二手资料,而是根据原物编目;3.过去的目录只收单行本,阿英收录对象扩大到杂志,这是他的创见;4.重视并收录翻译小说。但是樽本也指出了阿英所收的小说书目的不足,那就是他还是受“单行本主义”的影响太深,他只是“以单行本为主,旁及杂志所刊”,这样收目就必然很不彻底。因此樽本提出了他的编目原则:“众所周知,清代末期发表的小说多首先发表在杂志上,其中有一部分后来被集中起来出单行本。从杂志初出到单行本,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全新的出版形式。”“清末是杂志的时代。新时代有新办法。为了反映新时代,编辑小说目录也一定要有新办法。要是明白清末是杂志的时代,那么编辑目录时也一定要采用杂志主义。这就是我的看法。”于是樽本先生所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基本编辑方针就是“从杂志到单行本的任何作品全都收录”。这样他所收录的清末民初的小说创作目有11074件,小说翻译目有4972件,一共是16046件(包括重版)。除去民初部分,他的清末小说目录比阿英的收目多了1.4倍,阿英的清末小说收目只是他的同期收目的38%。樽本先生既对清末起始的“杂志时代”有了新体认,相应采取了与时代新特点合拍的新方法,经过扎实而细致的工作,就会有超越前人的新成果的出现。可是樽本先生也表示过自己的遗憾,那就是他没有条件再进一步将清末这一初兴的大众媒体时代的大量的报纸上的小说目“一网打尽”。因为只有这样,清末民初的小说的总数才会基本见底。据笔者所知,这一面广量大的极有意义的工作,目前在中国大陆是有若干人正在“埋头苦干”之中。未来的清末民初的小说目的数量将会有新的幅度的增加,这是可以预期的。
二
在论文集中樽本先生说:“搜集资料,弄清事实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谁也不能否认基础工作的重要性。”“我的兴趣在于通过挖掘事实来研究清末小说。”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史家就是要“凭原始资料说话”。樽本又在“弄清事实”、凭事实说话这一基本原则之中,再根据清末民初时期有一定特殊性的情况,又划出三个具体的研究准则来:1.研究作者“就是要把模糊不清的生平经历弄清楚”;2.“研究翻译作品,就是一定要找到原作”;3.“研究杂志,就是要解开其发行时间等谜团”。第一点关于弄清作者的生平,我们是能理解其重要性的。樽本是研究《老残游记》及其作者刘铁云的权威专家,在这本论文集中,他将刘铁云的日记与《老残游记》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写作过程研究得清清楚楚,澄清了过去的一些疑案。而在《李伯元和吴趼人的经济特科》一文中,对于他们两人的有关拒赴经济特科的问题也作了有据、因此也极为有理的阐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当时在上海除了做官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别的世界可以维持生计。李伯元和吴趼人选择了新闻界。他们大概在新闻界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并且充分体会到生活的价值。不用说他们也是经济上独立的。事已至此,他们完全不想到北京去投考。李伯元和吴趼人不去投考经济特科这件事,也象征着新闻界在上海已经形成了。”
第二点,研究翻译作品,要找原作有时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清末的中国早期译作,不规范操作也太普遍了,还往往不注明原作者的国籍与姓名。有一种叫做“豪杰译”,这一名词来自日本,明治初年日本译者常将原作的主题、结构乃至人物均作修改,再将小说中的人名、地名、称谓、典故乃至生活习惯统统改成日本式。而中国译者从日本转译时,又将日本化的西洋原作再作一番中国化。因此,为清末的译作找“娘家”也就特别困难。据笔者所知,樽本先生为了研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曾远涉重洋,到英国去找原著。而在这本论文集中他举了使吴趼人最早成名的《电术奇谈》(又名《催眠术》,由吴趼人“衍义”)的原作问题为例。连载在《新小说》第8号至18号上的这篇小说署“日本菊池幽芳原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主人评点”。幽芳是日本的一位名作家,但他的全集中根本没有这篇小说。于是樽本遍查报纸,在1897年1月1日至3月25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上找到了这篇小说的连载,原名叫做《卖报纸的》,它不是幽芳原著的,而是幽芳翻译的英国作家的作品。自费留学生方庆周用文言翻译了这篇小说,吴趼人将它衍义并改用俗语介绍给中国读者。樽本得出的结论是:“我把《电术奇谈》对照《卖报纸的》加以比较之后,发现了吴趼人衍义得非常好。一、吴趼人基本上没有改变原作的情节。二、有的地方吴趼人稍做了修改。更加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增加了故事的伏笔……吴趼人的这些修改对《电术奇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主人公描写得非常生动。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小说家吴趼人的本领。”
特别是樽本先生所谈的第三个具体的研究准则:“研究杂志,就是要解开其发行时间等谜团”,这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但是这却是清末民初研究杂志要弄清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该时段中,杂志的脱期现象非常普遍,有的杂志说是月刊,但脱期甚至近乎了“年刊”。在论文集中,樽本考证出《新小说》从第1号至第24号都是在日本印刷后运到中国来的,而不是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的,《新小说》第1号至第12号是在日本横滨印刷的,以后就迁到中国上海来出版了。他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是他对杂志发行地点的考证。当然,他对《新小说》的多次脱期现象,也有专门研究。至于他在论文集中所举的确定杂志发行日期的必要性,则使我们觉得在这一问题上更是大有讲究。例如,过去我们都将李伯元的逝世与《绣像小说》的停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也即是说,李伯元是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逝世的,而过去认定《绣像小说》出到72期停刊是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如果《绣像小说》是正常按期出版、不存在脱期现象,过去的这一“定论”是可以成立的。但据樽本的考证,《绣像小说》的出版有迟延现象,他是根据天津《大公报》、上海《东方杂志》、《消闲报》的出版广告,推断出《绣像小说》发行是“到光绪三十二年(中间有闰四月)年底出齐,并结束。比‘预定’的‘计划’晚了十个月。”由此,樽本得出了自己的几个新的结论,他写道:“《绣像小说》的‘出版延期’问题,不只是一个杂志的出版日期问题,它意味着要改正近代文学史的记述:(1)李伯元去世后,《绣像小说》还在继续出下去。(2)历来大家都认为《文明小史》、《活地狱》是李伯元的作品,因为延期,《文明小史》和《活地狱》的一部分不会是李伯元所写,而是别人用南亭亭长的笔名写了这两个作品的一部分。”樽本又根据包天笑的回忆:“后来钜源告诉我,他(注:李伯元)的《游戏报》,完全交给了钜源,自己完全不动笔,即小说亦由钜源代作。……据欧阳钜源说:伯元的许多小说,都由他代做,但用伯元的名。不过《官场现形记》是否也有他笔墨,却不曾问他。(我想伯元熟于官场事,必由他自写)若《文明小史》等,则我曾见过原稿,确有钜源的笔在内咧。”②包天笑与欧阳钜源是同科秀才,他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况且包天笑还看过原稿。因此樽本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南亭亭长不是李伯元一个人的笔名,而是跟欧阳钜源一起使用的共同笔名”。(3)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绣像小说》不采用刘铁云的《老残游记》第11回的稿件,刘铁云因此中断了给《绣像小说》供稿,可是在《绣像小说》中的《文明小史》第49回,却盗用了《老残游记》的“恃强拒捕的肘子”、“臣心如水的汤”等描写,这是李伯元还在世时的事,此事应与李伯元有关;后来在《文明小史》第59回,又抄袭了《老残游记》第11回(未用稿)中的1038个字。这是李伯元去世后的事。那时《绣像小说》的编者由欧阳钜源继任,因此这次抄袭是欧阳钜源的问题。樽本在考定杂志的出版日期的重要性方面,举出了这样一个实例,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考定杂志发行日期是研究一本杂志时所必应严守的一道“关卡”。
从上述的樽本提出的他所遵循的研究三准则,都显示了他的治学的严谨态度。正因为用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史上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小”问题,所以才能对过去大家视为是定论的结论,产生怀疑,再用“追根究底”的挖掘资料的办法,加以细致而精心的考证,才能使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真相大白。在这本论文集中,樽本先生专门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做《不要轻视小事——广智书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出刊日期》,对我们很有启迪。
三
樽本先生是日本学界的一位重视国际交流的学者,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小说研究方面,他也特别重视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他不仅自己发表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且发行两种刊物,就是上文提到的《清末小说》年刊与《清末小说通讯》季刊,有时也以清末小说研究会名义出版资料丛书。他在论文集中的《清末小说资料在日本》一文中说:“‘发、情、继、交’是我办杂志的编辑方针。即要登载有‘发现’的文章,要收集整理‘情报(信息)’,要‘继续’出版,要进行‘交流’。”读他这两本杂志总觉得文章的质量都是较高或很高的,其原因就是刊物发表的文章都能有“新的发现”。“发现”是樽本先生所编的这两本刊物的关键词,他的取稿标准是:“研究论文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有没有‘发现’,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过去的研究成果上要是没有加上新的‘发现’,那么这篇文章就不值得发表。”他接着也不无遗憾地说:“明白这个道理的研究者还不多。”他自己的研究就是规范地遵循他自己所规定的信约的,而且大有知难而上的态势。他说:“我在继续做着有关翻译小说方面的调查研究,比如柯南道尔、《天方夜谭》、哈葛德等,正是这些缺少文献资料的研究课题,才大有干头呢!”他目前的这几个研究对象是清末翻译小说中的重要课题,这些翻译小说的绍介,对中国转型期的小说的推动与促进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在中国,对清末民初小说的研究正在升温,那种曾被作为“打倒对象”的清末小说正在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其流失的资料正在有关学者的深挖细找中得以逐渐恢复其原貌。樽本先生所说的“恶性循环”正在被打破而引向良性发展的路上去。诚如樽本先生所认为的,一个新时代应该有新的认识,并采用相应的新的研究方法。清末民初是一个中国文坛的转型期,转型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也是一个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期;也是一个现代化的文化市场的初创期,可以也应该研究,也必须和值得研究。过去的某些“权威”的结论,其中也不免存在着若干“疑点”和不实之词,应该靠今天的学者作进一步的掂量,甚至破解。我们绝不能因为它是一个“转型期”而原谅它可以在艺术上是低档次的。事实上过去有的学者在评价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例如胡适就认为,《红楼梦》“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③。而他又认为谴责小说的作者带给我们民族的是一种“反省的态度”与“责己的态度”,是医治民族“夸大狂”的良药,也是“社会改革者的先声”,因此应该“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④。再说,即使是清末的两部未竟之作——《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两座高峰。胡适充分肯定《老残游记》的描写技术,“无论写人写风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的了。”⑤如果拿《儒林外史》与《孽海花》的结构相比:《儒林外史》的花序是开一朵谢一朵,“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而《孽海花》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是一朵珠花”⑥。鲁迅也不得不承认《孽海花》“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⑦。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像樽本先生一样,深挖资料,澄清事实,对过去貌似不可动摇的“定论”提出质疑,得出新的科学的结论。另一方面,则要对那种把清末小说看成“打倒的对象”、“评价非常低”的“疑案”——甚至是“冤案”——进行重新审视与破解,拨乱反正,还清末小说以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
2007年1月22日于苏州
注释:
①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新1版。
②包天笑:《晚清四小说家》(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9期,第34-35页,1942年4月1日出版。
③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胡适文存》第3集,第393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⑤胡适:《〈老残游记〉序》,《胡适文存》第3集,第40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⑥曾朴:《谈〈孽海花〉》,《〈孽海花〉资料》,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8卷,第2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晚清论文; 老残游记论文; 读书论文; 孽海花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文明小史论文; 吴趼人论文; 李伯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