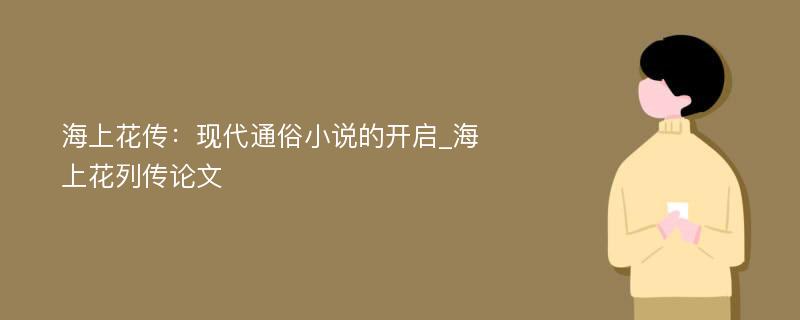
《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山论文,列传论文,之作论文,通俗论文,海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的线路图,从文学的古典型转轨为现代型时,是要有一个鲜明的转轨标志的。正如从电车或地铁的某号线路到达某一站点时,要换乘到另一条新的线路上去一样,它要给乘客一个提示,要给大众一个醒目的信号。文学的列车亦然。经过反复的勘测与论证,我们选定《海上花列传》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站点。那就需要拿出若干可信而实证的根据来,显示它就是文学列车从古典型驶向现代型的转轨换乘交接点。下面我们列举《海上花列传》的六个“率先”,说明它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一、《海上花列传》是率先将频道锁定、将镜头对准“现代大都会”的小说,不仅都市的外观在向着现代化模式建构,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异。它虽然被称为狭邪小说,但当时的高等妓院,首先是发挥高级的社交场所的职能,而不是现在概念中可以与“性交易”画上等号的门庭。在男女禁隔的社会中,她们“扮演”的是一种大众情人或红粉知己角色。她们的生活起居是作为一种“时尚”与都市现代生活方式同步演进,甚至是起着“领跑”的作用。二、上海开埠后成为一个“万商之海”,小说以商人为主角①,也以商人为贯穿人物。在封建社会中,商人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而在这个工商发达的大都市中,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飙升,一切以“钱袋”大小去衡量个人的身份。在这部小说中已初步看到资本社会带来的阶级与阶层的升沉浮降。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的几部著名的狭邪小说中,它率先打破了该类题材“才子佳人”的定式,才子在这部小说中不过是扮演“清客”的陪衬角色。三、在世界步入资本化时代,许多国家的著名作家都曾以“乡下人进城”作为自己的题材。这是资本社会的一个具有世界性的题材,因为很多现代化大都市皆是靠移民大量涌入,形成人口爆炸,劳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交通便捷才得以运转、扩容和建成。而在中国,《海上花列传》率先选择“乡下人”进城这一视角,反映了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农村的式微,使贫者涌向上海;即使是内地的富者,也看好上海,将资本投向这块资本的“活地”。作品以此为切入点,反映了上海这个新兴移民城市的巨大吸引力,以及形形色色的移民到上海后的最初生活动态。四、《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胡适曾认为其在语言上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吴语当时是上海民间社会的流通语言,特别是上层社会或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人们以一口纯粹的“苏白”以显示自己的教养与身份。这部书成了当时想挤入上层社会的外乡人学习和研究吴方言的“语言教科书”。五、作者曾“自报”他的小说的结构艺术——首先使用了“穿插藏闪”结构法,小说行文貌似松散,但读到最后,会深感它的浑然一体。在艺术上它也是一部上乘、甚至是冒尖之作。六、韩邦庆是自办个人文学期刊第一人,连载他的《海上花列传》的《海上奇书》期刊又利用现代新闻传媒《申报》为他代印代售,他用一种现代化的运作方式从中取得脑力劳动的报酬。
这六个“率先”,以一股浓郁的现代气息向我们迎面扑来,《海上花列传》从题材内容、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等方面都显示了它的原创性才能。作为中国文学转轨换乘的鲜明标志,它可以当之无愧。韩邦庆使通俗文学走上现代化之路当然不会是完全自觉的;但惟其是自发,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推进与文学发展的自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文学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社会的阳光雨露催生的必然结果——由于现代工商业的繁荣与发达,大都市的兴建以及社会的现代化,民族文化必然要随着社会的转型而进行必要的更新,也必然会有作家对它有所反映与回馈。《海上花列传》就是这种反映与回馈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知识精英文学是受外来新兴思潮的影响而催生的;但中国通俗文学则证明了即使没有外国文学思潮为助力,我们中国文学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我们民族文学的自身就有这种内在动力。
(二)
韩邦庆(1856—1894),江苏松江人(今属上海市),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花也怜侬。父宗文,颇有文名,官刑部主事。邦庆少小时随父居京师。他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约20岁时,回籍应童子试,为诸生。次年岁考,列一等,食饩禀。后屡应乡试不第。曾尝一试北闱,仍铩羽而归。那是1891年,当时孙玉声与他同场赶考,又同舟南归,两人在船上已互换阅读《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的部分初稿。孙玉声的这段回忆极为重要:
辛亥年(1891)秋应试北闱,余识之于大蒋家胡同松江会馆,一见有若旧识。场后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长途无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说稿相示,颜曰《花国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时余正撰《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读,喜此二书异途同归,相顾欣赏不止。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海上花》。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朆”、“覅”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况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逮之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使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予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以《石头记》并论也。②
孙玉声毕竟还只能是孙玉声。他还看不出韩邦庆定见之深意。孙玉声确有他的一定的成就,但他在文学史上无法与韩邦庆并肩。正如陈汝衡对孙的这段有些沾沾自喜的话所作的评语:“孙漱石所言,未必可信。《海上繁华梦》虽能邀誉于一时,而文学上之价值自远逊于《海上花列传》。今日孙氏之书已少人读,其描写之引人入胜,尚在狭邪小说《九尾龟》之下,韩子云之《海上花列传》,则文艺批评界久许为有数之晚清现实小说矣。”③ 韩邦庆有着一种“不屑傍人门户”的气势。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觉得自己在“原创性”上,要有那种与仓颉、曹雪芹平起平坐的开拓型的“冲动”。但孙玉声的这段笔记,却为我们留下了极可珍贵的文学史料。至少对这位具有开创性的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抱负,有了立论的根据;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的小说的创作进程。例如说他在1891年已有初稿24回。到1892年农历二月初一,韩邦庆出版第1期《海上奇书》。第1期至第10期为半月刊,以后5期为月刊,共出版了15期。每期刊登《海上花列传》2回,应刊登至30回止(胡适说共出版14期,共刊28回)。④ 那么就是说,韩邦庆南旋后,他又写了40回。其中1891年所写的24回初稿经修订后再加6回,是先在期刊上刊出的。到1894年出版时,未经连载的新回目有34回。其实他胸有成竹,《海上花列传》的续集也已有腹稿。可惜在出版全书的当年,韩邦庆就因贫病而与世长辞,年仅39岁。这确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海上花列传》以妓院为基点,用广阔的视野写上海的形形色色社会众生相。刘复说:
花也怜侬在堂子里,却是一面混,一面放只冷眼去观察,观察了熟记在肚里,到了笔下时,自然取精用宏了。……不但是堂子里的倌人,便是本家、娘姨、大姐、相帮之类的经络,与其性情、脾气、生活、遭遇等,也全都观察了;甚至连一班嫖客,上至官僚、公子,下至跑街、西崽,更下以至一般嫖客的跟班们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他所收材料如此宏富,而又有极大的气力足以包举转运它,有极冷静的头脑足以贯穿它,有绝细腻绝柔软的文笔足以传达它,所以他写成的书虽然名目叫《海上花》,其实所有不止是花,也有草,也有木,也有荆棘,也有粪秽,乃是上海社会中一部分“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明白了这一层,然后看这书时,方不把眼光全注在几个妓女与嫖客身上,然后才可以看出这书的真价值。③
《海上花列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光芒四射的。至少有四位大师级的文学家——鲁迅、胡适、张爱玲以及上面已引用了他一大段话的刘半农,他们都给予它高度的评价。
最先评价它的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虽然也写妓女,但不像《青楼梦》那样的理想,却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这样,作者对于妓家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是溢恶”⑥。这里的“真”与“写实”,还得应该用鲁迅说它“甚得当时世态”的话来作解。那就是说,韩邦庆笔下人物的个性是与当时的世态密切相关,是转型环境中的转型性格。例如在第23回,姚二奶奶到卫霞仙堂子里去向卫“讨”姚二少爷,大兴问罪之师的一段,简直可称得上通俗小说中的经典“唱段”。
姚二奶奶是姚季莼的正室夫人。这位“半老佳人,举止大方,妆饰入古”,乘一顶轿子,带了一帮娘姨丫环,“满面怒气,挺直胸脯踅进大门”,一见卫霞仙劈头盖脸地责问:“耐拿二少爷来迷得好,耐阿认得我是啥人?”看样子今天只有卫霞仙低头服输,作出保证,从此不许姚季莼再踏进门来,才能罢休。否则姚奶奶一声喝打,不但自己受辱,连这房间也有被砸得落花流水的危险。大家七嘴八舌劝解之际,被卫霞仙一声喝住道:
“覅响,瞎说个多花啥!”于是卫霞仙正色向姚奶奶朗朗说道:“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耐个家主公末,阿是勿许倪做嗄?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管牢仔,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二少爷末怕耐,倪是勿认得耐个奶奶啘!”⑦
卫霞仙一席话说得姚奶奶大哭而回。胡适称赞卫霞仙的“口才”,说他一席话说得“轻灵痛快”,吴方言中就叫做“刮辣松脆”。作者当然是将这个妓女“鲜明个性”写了出来,可是我们还应该看得更深一层,那就是“当时世态”,即卫霞仙所说的“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夷场即洋场,洋场浪的“规矩”是妓院要交捐纳税,然后发经营牌照,这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生意”,是一种“正当”营业。你管得牢你丈夫就是你“狠”,你管不牢你丈夫,就是你无能,你丈夫有他进堂子的自由。这里就有一个观念的改变问题,卫霞仙懂这个“规矩”,她有恃无恐。这位“妆饰入古”的姚奶奶在封建社会中有权兴师问罪,在这个洋场资本社会中,就是她“理亏”,只好哭着“落荒而逃”。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体会在这“写实”中不仅写出了人的个性,而且写出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异。
但鲁迅对《海上花列传》的最高评价往往为人们所忽略。鲁迅说韩邦庆“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第1回)之约者矣”。这才是最高的评价。也就是说,韩邦庆在第1回中自定要达到这16个字的艺术水准,鲁迅认为他已经不折不扣地“自践其约”了。也即是在人物塑造上,在事件描写上,在情节设置上,皆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以致达到了“跃跃如生”的神境。鲁迅还说小说写得“平淡而近自然”⑧,这是将它提到中国传统美学观中的高度来加以鉴赏的。“平淡”绝非平庸与淡而无味之谓。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范畴中,平淡就是王安石所说的“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而苏东坡则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是非平淡,乃绚烂之极也。”⑨ 而“自然”当然应作“浑然天成”解。
继鲁迅之后,刘半农在1925年12月所写的《读〈海上花列传〉》对其人物塑造与方言运用也大为钦服:他提出“平面”和“立体”两个概念,认为韩邦庆笔下的事事物物“好像能一一站立起来,站在你面前”,他笔下的人物确有立体感。作为一位语言学大师,刘还盛赞小说在语言学上的贡献:“若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做依据,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一个什么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很好的本文;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结语了。”⑩
第三位大师就是1926年为《海上花列传》(东亚版)作《序》的胡适了。为了作《序》,胡适先“内查外调”考证韩邦庆的生平。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涉及韩的作品时,还只看到蒋瑞藻《小说考证》中所引的《谭瀛室随笔》资料一条。而胡适知道孙玉声与韩相熟,正要拜访时,就读到刚出版的《退醒庐笔记》。当胡适再请孙玉声深入开掘时,由于孙的打听,却引出了颠公的《<海上花列传>之著作者》一文。这些珍贵的作者生平皆——收入了胡适的《序》中。如说韩:“为人潇洒绝俗,家境虽素寒,然从不重视‘阿堵物’;弹琴赋诗,怡如也。尤精于弈;与知友楸枰相对,气意闲雅,偶下一子,必精警出人意表。至今松人之谈善弈者,犹必数作者为能品云。作者常年旅居沪渎,与《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士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可以说,胡适的《序》是既有资料,又包举了鲁迅与刘半农的论点,还有许多自己的见解。特别是胡适认为“《海上花》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论证颇详:
但三百年中还没有一个第一流文人完全用苏白作小说的。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受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暗示,不顾当时文人的谏阻,不顾造字的困难,不顾他的书的不销行,毅然下决心用苏州土话作了一部精心结构的小说。他的书的文学价值终久引起了少数文人的赏鉴与模仿;他的写定苏白的工作大大减少了后人作苏白文学的困难。近二十年中遂有《九尾龟》一类的吴语小说相继出世。……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11)
而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张爱玲在晚年用了将近10年时间,二译《海上花列传》,先是将它译成英语,以后又将它译成“国语”——普通话。通过这两次“翻译”,可以说,张爱玲将《海上花列传》的每一个字进行了“掂量”。与鲁迅、刘半农、胡适不同的是,他们是“评价”、“推崇”《海上花列传》,而张爱玲则侧重于“理解”、“阐释”《海上花列传》。张爱玲说,《海上花列传》的“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这“禁果的果园”的五个字,可说是道尽了书中的奥秘。张爱玲解释说:“盲婚的夫妇也有婚后发生爱情的,但是先有性再有爱,缺少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在男女禁隔的社会里,只有未成年而情窦初开的表兄妹之间才能尝到恋爱的滋味,“一成年,就只有寻院这脏乱的角落里也许有机会。”早婚的男子对性已失去神秘感,他们到妓院中去,有人是想品尝“红粉知己”赐予的“恋爱”的滋味。“‘婊子无情’这句老话当然有道理,虚情假意是她们的职业的一部分。不过就《海上花》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幺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会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12) 这种剖析,才是真正的“理解”与“阐释”。可是在这种地方品尝“恋爱之果”是有危险性的。人类的老祖宗在伊甸园里受了诱惑,吃了禁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上帝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13) 在禁果的果园中摘果子吃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海上花列传》中,这些吃禁果的人“概莫能外”。黄翠凤该算是有情有义的侠妓了吧?可是她在权衡鸨母与罗子富利害轻重之间,还是选择了帮助鸨母敲了罗子富一个大竹杠,她得最后为鸨母赚一笔养老钱。至于其他如王莲生、朱淑人之类,就更不在话下了。人说妓女是“卖笑生涯”,可是王莲生买到的是什么?是“气”,是“泪”,是“累累伤痕”。他常常是“长叹一声”,“无端吊下两点眼泪”,还时不时被沈小红用“指甲掐得来才是个血”,他简直是花钱买“私刑”。而朱霭人本来想施行他的特殊教育法,带他年轻的弟弟到社会上来“历练历练”,好让他的弟弟日后见怪不怪,可是经过他弟弟的一“劫”,他“始而惊,继而悔,终则懊丧欲绝”。即使是像陶玉甫和李漱芳那一对具有“天长地久,海枯石烂”忠贞之心的爱侣,结局也是如此悲惨,他们自身双双食了苦果;所不同的是仅仅剩下受人敬佩的“吊唁”而已。看来为了品尝恋情的滋味而拼死食禁果,这也是当时中国某些男子的矛盾人生吧?因此,作者开宗明义就说:“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14) 这话倒不属“头巾气”的说教。但也像“围城”一样,在风月场中尝到禁果的苦涩的人冲城而出;而在城外的人还想夺门而进,想去领略园中的旖旎风光。按照上述所引的刘半农与张爱玲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海上花列传》实际上是一部通俗社会言情小说。
(三)
韩邦庆的作品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的熟悉社会与熟悉花丛的生活当然有关,但孙玉声的熟悉程度绝不在韩之下,为什么孙玉声小说的成就比较的低呢?关键在于韩邦庆有见解——有深入洞悉文艺规律的奥秘的不凡见解。而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就是很深刻的文艺理论。例如他说写“列传”有三难: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15)
这前两难韩邦庆果然是解决了。这第三难恐怕就不易解决。可是当他阐明了自己的“见解”后,似乎也“迎刃而解”了。他将读小说与游太行、王屋、天台、雁荡、昆仑、积石诸名山作比:
今试与客游太行、王屋、天台、雁荡、昆仑、积石诸名山。其始也,扪萝攀葛,匍匐徒行,初不知山为何状;渐觉泉声鸟语,云影天光,历历有异,则徜徉乐之矣;既而林回磴转,奇峰沓来,有立如鹄者,有卧如狮者,有相向如两人拱揖者,有亭亭如荷盖者,有突兀如锤、如笔、如浮屠者……夫乃叹大块文章真有匪夷所思者。然固未跻其巅也。于是足疲体惫,据石少憩,默然念所游之境如是如是,而其所未游者,揣其蜿蜒起伏之势,审其凹凸向背之形,想像其委曲幽邃回环往复之致,目未见而如有见焉,耳未闻而如有闻焉。固己一举三反,快然自足,歌之舞之,其乐靡极。噫,斯乐也,于游则得之,何独于吾书而失之?吾书至于64回,亦可以少憩矣。64回中如是如是,则以后某人如何结局,某事如何定案,某地如何收场,皆有一定不易之理存乎其间。客曷不掩卷抚几以乐于游者乐吾书乎?(16)
看来韩邦庆对读者的要求也是极高的。他竟然将“无挂漏”这一要求“转嫁”给读者了。其实一般读者,只是读懂了他作品的故事情节,因为他的作品毕竟是通俗的;但读者也是分层次的,他还要求读者进而“一举三反”地深得其中三昧。真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了。他期望读者去看他的“门道”。他认为我既然已经写出了“这一个”的个性,又在作品中为他们铺设了生活道路,读者就可以揣想他的未来。正如俗语所说的“三岁看到老”了。优秀的通俗小说往往是经得起“雅俗共赏”的。但雅俗读者之间的所得也往往是不平等的。世界上恐怕找不到对每一位读者都“平等”的雅俗共赏的作品。
至于小说的结构,韩邦庆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指导下的小说,当然使他的结构艺术优胜于前人: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求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17)
从穿插法而言,书中的五组主要人物是作品波澜迭起之源。一、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二、罗子富与黄翠凤、蒋月琴,还加上一个钱子刚;三、陶玉甫与李漱芳;四、朱淑人与周双玉;五、赵二宝与史公子、癞公子。而又以洪善卿与赵朴斋甥舅两人为串线。作者就是靠这五组人物之间的瓜葛,掀起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动感,指挥着忽南忽北,忽东忽西的调度。至于藏闪之法,因为是“劈空而来”,真有使人“防不胜防”之感。例如沈小红人还未出场,韩邦庆就为她定了“调子”:当洪善卿到沈小红堂子里去访王莲生时,扑了个空,连沈小红也不在,说是“先生(妓院中的下人称妓女为“先生”——引者注)坐马车去哉”(第3回)。 从此“坐马车”就成了“轧姘头倒贴”的代名词。张蕙贞在王莲生耳边影影绰绰揭沈小红倒贴姘头,说她“常恐俚自家用场忒大仔点”。王莲生还不大在意地茫然答道:“俚自家倒无啥用场,就不过三日两头去坐坐马车。”说明他当时还对沈小红是深信不疑的;后来略有觉察时,曾向洪善卿探问沈小红是否有姘贴?“沉吟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第24回)。直到第33回,王莲生亲眼看见沈小红与小柳儿“搂在一处”,才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以前的一切暧昧情节。包括第9回中,向沈小红报信,使沈与张蕙贞大打出手的,皆是小柳儿所为(小柳儿为京剧武生,当时嫖界皆以妓女姘贴“戏子”与“马夫”为大忌,视为是对恩客的奇耻大辱——引者注)。因此韩邦庆说:“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才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可待,特先指出一二。……写沈小红,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18) 这样的“藏闪”之法,在作品中形成若干“暗纽”,直到作者在关键时刻为我们点亮,才知全文之丝丝入扣。无怪胡适对韩邦庆的文学技巧如此钦服,以致说:《红楼梦》“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19) 张竹坡在给《金瓶梅》写回评时说:“做文如盖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20) 韩邦庆的确想做到“合得无一缝可见”;可是反复阅读、而又二译《海上花列传》的张爱玲就生怕韩邦庆因“渐老渐熟”,达到了化境,“乃造平淡”;而行文的“浑然天成”又使它一半反面文章还藏在字行之间,以致读者容易被它的“穿插藏闪”弄得眼花缭乱,拆解不开。因此她在《译后记》中以调侃自己方式出现,说:“《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没完,还缺一回是: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21) 张爱玲的“调侃”用意倒还是想告诉读者,这部书要细读才能咀嚼出兴会无穷的味汁。关于这一点,今天张爱玲在天之灵倒是可以不必再担心的了。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不会再有的了。当我们知道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后,我们当然会从各个视点去解读这部优秀的作品。当我们发现《海上花列传》这六个“率先”,它的文学史身份也随之提高而会引起多方的关注与开掘。当我们尊它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时,实际上就将它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换乘点”的鲜明标志,它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点;因为知识精英的文学丰碑还要迟四分之一世纪才诞生,而它作为通俗小说之优秀代表作却早已悄悄地开拓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垦地。
注释:
① 说到以商人为主角问题,《谭瀛室笔记》中说:“书中人名,大抵皆有所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接着点出了书中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10个名流的姓名。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49)〈海上花列传〉》的译者太田辰夫按图索骥地找到了其中8个人的传记,除小柳儿是京剧名武生外,其他7人的背景皆与商业有密切的关联。在这里我们不想指出真名实姓,对小说的原型可作考证,但也不宜一一坐实,因此下面只作介绍,说明原型的某些背景,使读者有所参照。如黎篆鸿乃“红顶”巨商,曾得钦赐黄马褂;王莲生从事外事工作,担任过招商局长;李鹤汀是财界大亨,后任邮传部大臣;齐韵叟官至安徽巡抚、两江总督;高亚白博学而擅长诗词,辞官后客居上海,与《申报》有关系;方蓬壶,诗人,曾是《新闻报》总主笔;史天然,京师大学堂总办,参议院议长,辞官后隐居天津。译者在最后说道:作者在例言中讲到“‘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有人认为,正因为是原型小说,才放这样的烟幕弹来蒙混过关。”
② 孙玉声:《退醒庐笔记·16·〈海上花列传〉》,第113~114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陈汝衡:《说苑珍闻》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魏绍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1)》第46~47页:“花也怜侬(韩子云)于上海创办《海上奇书》……本年出版15期,前10期为半月刊,后5期为月刊,点石斋石印,申报馆代售。……《海上花列传》,自撰的吴语长篇小说,每期刊2回,共刊30回……”而胡适则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海上奇书》共出了14期,《海上花列传》出到第28回。先是每月初一、十五,各出一期的;到第10期以后,改为每月初一日出版一期,直到壬辰(1892)十月朔日以后才停刊。”(《胡适文存第3集》第359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笔者在上海市图书馆仅看到第1~10期,而北京图书馆也只有第1~10期,因此姑存二说。
⑤ 刘复:《半农杂文·第1册·读〈海上花列传〉》第241页,星云堂书店1934年版。
⑥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第3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⑦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第192~19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⑧ 以上所引用的均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卷第224~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⑨ 这里对“平淡”、“自然”的理解,皆参照英国汉学家卜立德的《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中的《“平淡”与“自然”》章节(第100~102页)。陈广宏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 刘复:《半农杂文·第1册·读〈海上花列传〉》第247页,星云堂书店1934年版。
(11) 以上所引的胡适的话均出自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第3集》第352~369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12)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落〉译后记》第6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3) 《圣经·创世记·第3章》第3~4页,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88年版。
(14) 《海上花列传·例言》,《海上花列传》第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5) 《海上花列传·例言》第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6) 《海上花列传·跋》第52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7) 《海上花列传·例言》,《海上花列传》第4~5页,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8) 《海上花列传·例言》,《海上花列传》第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9)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0)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本,第2回的回评,第40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
(21)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第6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标签:海上花列传论文; 张爱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九尾龟论文; 韩邦庆论文; 申报论文; 孙玉声论文; 吴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