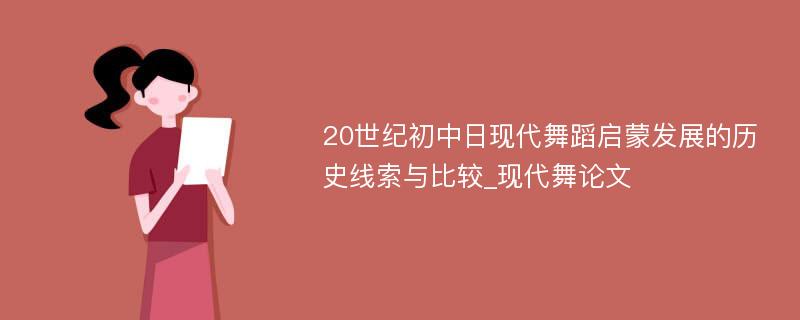
20世纪初日本与中国现代舞启蒙发展的历史线索及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舞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线索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7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18(2013)05-0034-05
一、20世纪初日本现代舞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超越其他亚洲国家。西洋舞蹈这种西方舞台艺术的舶来品也随着这股浪潮率先进入日本人的视野。1911年(即大正天皇登基前一年),日本修建了一座可容纳1700人的法国式近代建筑,取名为“帝国剧场”。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座西式剧场。同年,帝国剧场开设了歌剧部并招收学员,第一期学员包括石井漠、小森敏、泽森野、河合几代等15人,第二期学员有高田雅夫,三期学员有原世子(后冠夫姓称高田世子)。
在日本,现代舞启蒙阶段以1926年为界,分为启蒙前期的自由主义阶段和启蒙后期的国家主义阶段。之所以将1926年作为分界点,是因为这一年是大正朝代的结束、昭和年号的开始。此前此后的日本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社会风貌及人文特征。
(一)启蒙前期
大正时代(1912-1926)是日本近代史上短暂且相对稳定的时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在城市和乡村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和普选,并积极推动民主主义运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基调就是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在哲学和思想领域,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波及整个知识界,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日本思想界。正是在大正时代的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来自西方的现代舞艺术开始落地生根并茁壮成长起来。
1916年6月,石井漠同导演兼剧作家小山内薰、作曲家山田耕筰在帝国剧场上演《舞蹈诗》[2]。《舞蹈诗》共有两部作品,第一部为石井漠的独舞《日记的一页》(山田耕筰作曲),第二部为石井漠和音羽金子的双人舞《物语》(门德尔松作曲)。两部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区别于日本传统舞蹈和西方芭蕾舞,是一种全新的身体表现。作为第一个在本土正式上演现代舞的日本人,石井漠的演出无疑成为日本现代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第一部作品开始,石井漠就表现了他鲜明的创作风格。他的作品注重探索内心,一般通过日本民间传说等故事题材表达个人的特殊境遇。如《日记的一页》(1916)、《明暗》(1917)、《囚徒》(1923)、《登山》(1925)[2]等作品多以独舞为主,情感的戏剧性表现是作品的主要风格。以石井漠自编自演的独舞《囚徒》为例,“舞者赤裸上身,腰胯上只围着一片褴褛的短布片,双手缚于背后,面部表情狰狞、头发凌乱。舞者伴随着音乐从舞台后方斜角不断向舞台前方反复冲出、后退”①。通过激烈的动作表达内心深处的无言挣扎以及试图挣脱束缚的困境。这部作品表现了石井漠作为现代人所持有的自我意识以及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如果说石井漠是一个创造者,为日本现代舞点燃了一盏明灯,那么把灯光照亮更远的则是伊藤道郎。在《舞蹈诗》公演的两个月前,23岁的伊藤道郎在伦敦举办了《鹰之井畔》的试演会。该剧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叶芝根据日本能乐创作的一部剧作,伊藤道郎担任作品里“鹰”的表演者。《鹰之井畔》在伦敦上演后,伊藤又赴纽约、洛杉矶等地公演。1918年秋天,伊藤道郎在纽约创办学校“MICHIO ITOW'S SCHOOL”,开始海外舞蹈生涯。1931年伊藤道郎带着自己的舞团返回日本,在朝日讲堂、帝国饭店演艺场、大阪朝日会馆等地举办公演,演出作品受到日本舞蹈界的关注②。
这一时期,活跃在日本舞蹈界里的除了石井漠和伊藤道郎,还有同在帝国剧场接受过芭蕾舞蹈训练的高田雅夫、高田世子、岩村和雄、小森敏等人。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展了同石井漠《舞蹈诗》一样的舞蹈创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成了日本早期现代舞的开拓者。
(二)启蒙后期
1926年,大正天皇辞世,昭和时代开始,成为日本走上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对外侵略道路的开端。在政府鼓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战前的日本文化逐渐失去生机,国家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
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的新文艺也在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昭和初期,日本现代舞仍在进步,德国表现主义在日本的登场给现代舞坛注入新的活力。1933年,江口隆哉、宫操子夫妇从德国回到日本,于1936年举办了为期三周的“现代舞讲习会”,主要内容有舞蹈基本理论、创作方法以及音乐节奏方面的练习。他们将在德国学习的玛丽·魏格曼的表现主义舞蹈体系介绍给日本舞蹈界。这种具有革命性的身体表现和崭新的表演体系给日本舞蹈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随着表现主义关于身体表现理论的不断普及,日本舞蹈界人士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现代舞和芭蕾舞之间最基本的差异,他们认同魏格曼所提出的“舞蹈是通过人体的运动来表现灵魂的艺术”③的舞蹈理念,并且认定德国表现派舞蹈就是所谓的“最正统的现代舞”。由此直到二战结束,德国表现派成为日本现代舞的代号。
然而,30年代后期纷繁复杂的历史,使日本对德国表现主义的引进不再只停留在纯粹的艺术领域。受纳粹德国的政策影响,日本思想界对文艺的思考与国民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受主流社会思潮影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石井漠开始编创战争题材的舞蹈作品,并在同年12月上演。次年,石井漠带领舞团前往中国战区,在两个月内为驻华日军巡演了57场。演出纪录中包括《突击》(1937),《战车》(1938)等多部作品[4]。
此外,日本新舞蹈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日本舞“藤荫流”的创始人藤荫静枝也曾于1931年创作了以战争为题材的舞蹈作品《构成231》。藤荫曾于1928年留学巴黎等地,并接受了魏格曼的舞蹈概念。《构成231》选用瑞士作曲家阿瑟·奥涅格的代表作《太平洋231》作为背景音乐,描绘了在充满机枪、炮火、战斗机的战场上人们坚强的生存意念。在此期间,高田世子、江口隆哉、宫操子夫妇、石井绿、津田信敏等人也相继演出与战争相关的舞蹈作品。作品主题除了鼓舞斗志之外,还有“思乡”的内容。例如在宫操子的巡演记录中,可以读到她不可避免地遇到残酷战争对她所造成的内心震撼——“呼喊着战士们的心、一边留着泪水一边舞动着”[5]。
至此,以自由创作为根本目的现代舞在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盛行下的日本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日本舞蹈人士的创作实践逐渐由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凸显个体性,转向了作为日本国民共同体一员的群体价值理念。
二、中国现代舞启蒙阶段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国道路,积极引进西方新知,反对禁锢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信仰、旧风俗、旧习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启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启蒙者和奠基者,吴晓邦最早将现代舞引入中国,并致力于采用现代舞的表现技法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可以说吴晓邦早期的现代舞探索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现代舞在启蒙阶段的实践成果。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吴晓邦三次东渡日本学习文艺。在1929-1931年第一次留学期间,吴晓邦在早稻田大学观看了学生舞剧《群鬼》。《群鬼》用种种人格化的“鬼”来影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启发吴晓邦认识到“新舞蹈”具有组织和鼓舞群众的作用。此后,吴晓邦开始关注石井漠等舞蹈家的现代舞演出,他对文艺的追求逐渐聚焦到西方舞蹈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晓邦被迫回国,但学习舞蹈的志向已经深入内心。
1932年,吴晓邦第二次留学日本,师从于高田世子。高田世子曾游学巴黎,也在帝国剧场接受过G.V.罗西的芭蕾舞蹈训练。在舞蹈风格方面,高田世子反对矫揉造作、因循守旧的表演,支持学生尝试新题材的创作。这次学习加深了吴晓邦对舞蹈表演技巧的掌握。学习期间,吴晓邦创作了一部叫做《傀儡》的节目,以木偶戏作为舞蹈动作和姿态的根据。这部作品因为题材新颖引起了高田世子的关注,并在学生创作演出会上演出,让吴晓邦得益不少。
1934年吴晓邦因养母病逝回到上海,次年创办了“晓邦舞蹈研究所”。9月,吴晓邦在上海兰心剧院举行“第一次舞蹈作品发表会”,演出《傀儡》、《送葬曲》、《吟游诗人》、《和平幻想》、《小丑》、《浦江夜曲》、《爱的悲哀》等11个独舞节目。但这次演出除应邀来观赏的上海文艺界人士,仅售出一张票,购票的是一位波兰妇女,因为其中三个作品配用了波兰作曲家肖邦的音乐。吴晓邦在回忆录中讲到,“这是我把外国现代舞蹈形式引进中国来的最初尝试……观众的反映很冷淡……我深深地感到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倾向性比较鲜明的节目才能吸引观众”[6]17-18。这次演出失败说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西方舞蹈艺术相对于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过于超前。现代舞脱离了客观的人文环境,也缺乏生存和推广的社会基础。
受第一次尝试失败启发,吴晓邦结束了上海的舞蹈研究所,于1935年第三次赴日本留学。这一次,吴晓邦不仅继续在高田夫妇的舞蹈研究所进修,还于次年6月参加了江口隆哉、宫操子夫妇舞蹈研究所举办的“现代舞讲习会”。吴晓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接触现代舞只有短暂的三个星期,但它对我的思想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的艺术思想第一次得到解放,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二十世纪舞蹈艺术的科学方法及其发展的远景。从僵化到自由,需要一个较长的认识和时间过程……我对这种科学法则的基本训练,则感到十分舒服,不仅全身轻松,还促进了我的思想的活跃……不仅使我得到了需要经过长期学习和探讨才可能得到的收获,而且帮助我消除了长期以来认为舞蹈无理论的想法”[6]27。这次进修结束后,吴晓邦返回上海,再次开办“晓邦舞蹈研究所”,推行“人体自然法则运动规律”为基本训练的舞蹈教学法。
1937年4月,吴晓邦在上海卡尔登戏院举办“第二次舞蹈作品发表会”,除了曾经发表的《傀儡》、《送葬》等作品外,还初步尝试创作了三个现代舞作品。三个现代舞作品均是吴晓邦用“讲习会”上所学的现代舞创作方法编创的舞蹈。吴晓邦在这次发表会上的作品不仅扩大了题材范围,追求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创作方法上更系统地采用了现代舞的创作方法,因此在动作表现的灵活性和自由性上都更加具有了生命力。
第二次作品发表会结束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吴晓邦加快了创作风格由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创作征途。1937年到1942年,是吴晓邦舞蹈创作的黄金时期,期间他创作并演出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舞蹈,例如抗日主题的《义勇军进行曲》、《打杀汉奸》、《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1937)、《游击队员之歌》(1938)、《饥火》(1942)等。
以吴晓邦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舞创作完成了启蒙阶段的历程,中国对现代舞的启蒙实践最终以西方表现形式与本土传统的充分结合而告一段落。
三、中日现代舞启蒙历程的差异与共性
(一)差异及原因
中国现代舞启蒙走向终点的历史过程与日本的历程并不完全一致。吴晓邦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和他坚定的民族化美学追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是自成一派的自我完善,而是与中国深厚的艺术传统充分结合,并升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舞剧”。换言之,日本现代舞的先驱们在昭和时代的社会变迁下,未能坚持现代舞的自由主义实践,被动地走上了国家主义的道路;而中国的吴晓邦则是从踏上现代舞的道路开始,就自觉地向一个较为明确的方向前行了。
然而,吴晓邦作为个人,其价值取向也是在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如果只突出舞蹈家的个人因素,就忽略了中日反差所隐含的社会背景和艺术传统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文化环境远比中国优越。特别是大正十四年(1925年),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了社会思想界的主流,不论在哲学、文学还是艺术方面,日本知识分子和普通社会阶层的思维开放程度和对西方文明的接纳程度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尽管当时中国也在经历新文化运动,但其运动的宗旨还停留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已经落后于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和“明六社”④四十余年。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时间再把玩新文艺的纯粹美学,他们对文艺的价值追求必须是现实主义大于自由主义。
其次,从文化传统来看,日本和中国对舞台艺术的传统审美追求也造成两国艺术家对西方现代舞的认识不同。中国的舞台审美传统主要是戏曲审美。在诸多评价因素中,中国观众很注重鲜明的角色、清晰的人物关系和剧情化的情节,然而这些都是西方现代舞所淡化的方面。相比之下,日本人有欣赏“能”的传统,能剧本质上是种舞剧,剧本只是用来创造舞蹈动作的背景。能剧的主旨不在戏剧行动的呈现,而是致力于以抒情的形式表达一种情境。这种创作和表演方式与西方现代舞的理念非常契合。
(二)共性与启发
在感叹中日现代舞发展历程的差异之外,我们也未尝不可思索最终导致两国殊途同归的原因:
其一,古典主义的缺失。在引入西方现代舞之前,中国和日本都缺乏西洋舞蹈的古典体系。如同日本舞蹈史研究者国吉和子所指出的,尽管现代舞先驱对于新事物吸收得很快,但是毕竟缺乏必要的艺术传统,舞蹈家对外来的舞蹈表现形式和理论缺乏检讨的基础。在启蒙阶段,虽然舞蹈家能够领悟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通过身体动作表达内在体验与感动或是探求通过解构元素展现主题等核心主张,然而个人的情感、感动、体验却也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内涵⑤。在体现自由与自我的个人过程之上,创作者最终要回应的还是更大的社会文化命题。
其二,现实主义的内在需求。对比石井漠和吴晓邦最初的创作经历,不难发现二者最初的现代舞蹈创作都不是源于邓肯或者魏格曼的现代舞理论,而是在接触西方古典芭蕾后自发的艺术探索。例如《舞蹈诗》和《物语》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区别于日本的传统舞蹈和西方芭蕾舞,是一种全新的身体表现;吴晓邦在前两次留日期间创作的习作也是在参加“现代舞讲习会”系统学习魏格曼理论之前。石井漠和吴晓邦艺术实践的出发点都是现实生活,他们认为艺术活动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两位舞蹈家展现的务实倾向与20世纪初期流行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潮不无关系,但是从客观条件来讲这也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吴晓邦反思第一次舞蹈作品发表会失败的原因就是最好的例子。西方现代舞作为一个舶来品,不论之于日本还是之于中国,一旦表现内容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就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艺术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此,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西方现代舞艺术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都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内在需求。
其三,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价值取向。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与中国的现代舞启蒙都以同国家主义相结合而告终。尽管在表象上,由于日本和中国所处地位的对立,导致两国舞蹈家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为其民族性或意识形态的使命而战,然而从舞蹈实践的社会价值取向来看,二者的动机并不矛盾。选择这个方向,一方面与两国舞蹈家共同的现实主义倾向相联系,更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不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让现代舞艺术形式生存下来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舞蹈家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他们的历史使命予以回应。因此,在日中现代舞启蒙的终点,两国舞蹈家追求现代舞的初衷已经无关紧要,现代舞的思想根源和艺术实践彻底分离,演变成为充分本土化和时代化的“新舞蹈”。具体而言,这种“新舞蹈”,从思想根源上说,是传到日本的欧洲现代舞蹈思想;从实践取向上说,则是服务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使命的一种表达形式。
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的现代舞共同经历了曲折且精彩的启蒙历程。现代舞的引进就像当时其他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一样,开阔了两国知识界的视野,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尽管日中两国在现代舞启蒙道路上最终分道扬镳,但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日中两国现代舞的发展脉络并未偏离西学东渐的普遍规律。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思考不应再停留于东亚格局下某一个国家的成败得失,而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下,两国如何在现代艺术领域为世界做出自己的崭新贡献。
[收稿日期]2013-02-01
注释:
①根据2004年日本社团法人現代舞踊协会《日本现代舞踊の流れ 第一部 開拓期の人びと》的影像资料整理。
②参考1995年日本新书馆出版的《ダンスの20世紀》(市川雅)总结归纳。
③参考2002年日本新书馆出版的《夢の衣裳·記憶の壺—舞踊とモダニズム》(国吉和子)总结归纳。
④明六社:由曾先后留学英、美的日本外务大臣森有礼于1873年7月发起并成立,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成员有西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敬宇、西村茂树等核心人物。共出刊四十三期,每期销售量最高达到3200多份,1875年停刊。
⑤参考2002年日本新书馆出版的《夢の衣裳·記憶の壺—舞踊とモダニズム》(国吉和子)总结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