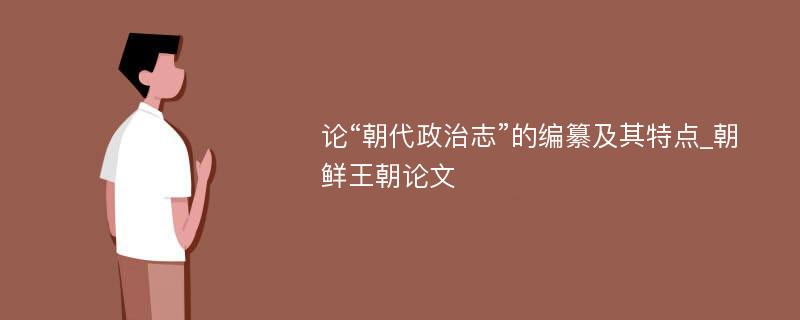
论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朝鲜论文,时政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3-0102-07
中国史学史上,《时政记》曾是一种重要的官修史书,兴起于唐朝,盛行于宋朝,元、明、清三朝则不再编修。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制度上多仿效明朝,文化上有强烈的“慕华”思想。对于文化繁荣的宋朝,朝鲜王朝也多有仿效,《时政记》的编修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时政记》之编修多有论及,却鲜有学人注意到朝鲜王朝的情况。本文试爬梳《朝鲜王朝实录》等原始材料,略加论及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并试图透过这个例子,分析朝鲜王朝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以求方家指正。
一、唐宋《时政记》之编纂及其特点
《时政记》兴起于唐朝,确切地说是兴起于武周时期。唐初建立了周密的史馆制度,沿袭汉朝旧制,设立起居注。起居注官随文武百官上朝,记录帝王起居言行、国家政事以及大臣廷对等重要的“军国政事”。唐太宗时期,太宗皇帝有时退朝后还与宰相等大臣单独商议要事,多涉及国家机密,起居注官亦可参与,并作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1]。但唐高宗时期,宰相许敬宗、李义府专权营私,他们密谋之时,经常不准起居注官到场,使得起居注多有缺漏,原来所定制度遂坏。武则天时期,宰相姚璹认识到“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他“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于是“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2]。其编撰方式,则是“以事采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2](卷43《职官志》),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军国大事以及典章制度方面的原始记载。这样就从姚璹开始,为了弥补起居注制度的缺陷,由宰相撰著《时政记》。可见当时《时政记》乃是从起居注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史书。纵观有唐一代,《时政记》时断时续,并没有坚持下来。李吉甫分析其原因:“(宰相)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寿,及璹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2](卷148《李吉甫传》)故而有唐一朝,编修《时政记》只是为了弥补起居注缺漏而设的一项临时性修史制度,且真正成书的只有姚璹的《时政记》四十卷。不过,这一制度在宋朝得以发展,成为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后,《时政记》的编修成为一项定制。有宋一代,其编撰制度也多有变化,初例以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后来以中书门下及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二府职掌不同,事务亦少有交集,乃由参知政事和枢密院副使各一人或二人负责编撰。从淳化五年(994年)开始,“自今崇政、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每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于对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条报本院,以备编录。”[3](卷439《文苑·梁周翰传》)乃明确中书省与枢密院所编《时政记》的具体内容。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丙午,进一步明确枢密院《时政记》的编撰,“月终送中书。……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4](卷1)每月汇总于中书省,再交史馆。太宗祥符五年(1012年),由李昉开始,开由皇帝先阅览、再付史馆的制度。当时三省及枢密院分设时政记房,为汇集材料、掌管杂务的机构。南宋时期,继续实行《时政记》的编修制度。故而宋代制度屡有变更,并非一成不变,但已是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元明以后,此项制度则废止不存。元朝“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字椽掌之,以事付史馆”[5](卷285《徐一夔传》引其《致王祎书》)。明清二朝也不再有《时政记》之编修。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政记》编修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最初它是从起居注制度中分离出来的,由宰相撰修,以弥补起居注之缺而设立,主要关注的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军国大事。尽管宋朝将这项制度由唐朝的临时性变为常设制度,基本内容则没有太大的改变。其由中书省所编之《时政记》和由枢密院所编之《时政记》,内容虽有不同,但以皇帝为中心则是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基本特点。编修的主要人员则是宰相,宋朝则为中书省及枢密院之堂上官,尽管设立时政记房,其房吏只负责杂务,并不真正参与编修事务。
第二,《时政记》乃是直接为编修日历而作准备的,并间接服务于实录的编修。南宋章如愚谈及当时的史书:“(本朝修史)其凡有二:曰纪载之史、曰纂修之史。时政有记,起居有注,其纪载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实录云者,左氏体也;正史云者,司马体也;纪其大事,则有玉牒;书其盛美,则有圣政;总其枢辖,则有会要。其曰日历,合纪注而编次之也;其曰宝训,于实录、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6](卷16)可见依当时人看来,《时政记》与起居注一样,乃是“纪载之史”,而“日历”正是“合纪注而编次之”书。宋人对《时政记》的价值品评甚高。朱弁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7](卷9)诚如蔡崇榜所言:“编次《时政记》、起居注为日历,删日历为实录,修实录以成国史。《时政记》与起居注实际是宋朝国史修撰之初最为重要的史料汇编,是构成国史的史料基础。”[8]谢贵安亦指出:“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9]诚哉斯言。
第三,《时政记》编成之后,月终实封,送史馆保存,除了为编修日历之用外,并不能随意取看,乃因其“事关机密”,必须严加保管。
那么,这项修史制度是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朝鲜王朝的呢?传到朝鲜王朝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编撰之原则与特征
朝鲜王朝初期,并未编撰《时政记》,其最初始于世宗年间。世宗李裪(1397-1450年)乃是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他励精图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颁布《训民正音》,创制了韩国文字,并大力组织朝臣编修各类史书,如由郑麟趾(1396-1478年)编修了《高丽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编撰《时政记》也被提出来了。世宗十四年(1432年,宣德七年),同知春秋馆事郑麟趾上书:
今进欧阳修论奏,甚得史官之职。今我国家礼义政刑及可否论议,一依欧阳修所论,令春秋馆逐时修撰,名曰《时政记》,其余机密事及人物贤、不肖等事,自如成法,以待后日,则国史庶几不至于疎漏。[10](卷58,世宗十四年十一月壬午)
这是《朝鲜王朝实录》中最早出现有关《时政记》的史料。郑麟趾是朝鲜王朝的重臣,四朝为官,先后任过吏、工、礼、兵曹判书,最后官至领议政。他亦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学者,既是创制韩国文字的主要组织者,又是《高丽史》的主编。春秋馆则是朝鲜王朝重要的史馆机构,“掌记时政,并用文官,以他官兼”[11](卷1《吏典》)。其最高长官领事一员由正一品的领议政兼,监事二员由正一品的左、右议政兼。因为朝鲜初期并无严格为实录编修准备史料的制度,在编修太祖、太宗实录时,史料零散,难以成篇,而当时郑麟趾为同知春秋馆事,负责实录编撰事宜,遂以欧阳修之论奏文,提出应当仿效宋朝建立编修《时政记》的制度,由春秋馆负责,以确保以后编修实录有充足的史料,世宗国王表示支持。两年后(世宗十四年,1432年),春秋馆呈上更为详细的计划,详谈《时政记》等史书的编撰事宜:
一、艺文、春秋二馆,本为一体,且艺文直提学直馆二员,别无职事,宜择清直有文学者,依式兼带史官,日坐本馆,凡大小衙门供报文书,常加点检,编次年月,随即撰录。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悉皆书之,使无漏失。依宋朝故事,名之曰《时政记》,以为后日修史之用。一、台谏上疏及臣僚上书言事,令记事官录呈,以备记载。一、堂上官一人,每月一次坐于本馆,《时政记》修撰勤慢,严加检察。一、凡本国出使人员,其关国家军民事体者,依书状官闻见事件例,备书首末,进呈本馆,以为恒式,令本馆检察。一、《时政记》,但书见行之事而已。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私自藏置,以待收纳。一、《时政记》一副,每当曝晒年次,依式藏之忠州史库。[10](卷66,世宗十六年十一月戊寅)
这是春秋馆事提出要扩大编辑史料的奏书,详细讨论了《时政记》的编撰,相当重要,以此就奠定了朝鲜王朝编修《时政记》的具体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编修《时政记》的机构是艺文、春秋馆,由专职史官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承政院日记》及各衙门紧关文书,每岁季启册数,艺文馆参下官奉敎以下,置八员,专掌修史。下番捡阅,常仕政院,腾(誊)出《(承)政院日记》。上番以上,常仕春秋馆,取考各衙门紧关文书,纂修《时政记》。下番所书,如有踈漏,则上番纠检,而又有踈漏,则次次纠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可见,朝鲜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艺文馆乃是“掌制撰辞命,并用文官”[11](卷1《吏典》),置正七品的奉教二员、正八品的待教二员、正九品的校阅四员共八员,这就是“下番”史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从正三品的修撰官、编修官到正五品、从五品的记注官,他们再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紧关文书”为基础,加上大臣的上书、谏言以及诸道资料进行核对,最后撰为《时政记》。“上番”史官有监督“下番”史官的职责。弘文馆被视为“翰林院”,其“掌内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12](卷1《吏典》),也参与《时政记》的编撰,“翰林常所书者,《时政记》也。使其堂上,别为检摄,亦祖宗之制也”[13](卷36,中宗十四年六月甲子)。其实,弘文馆的官员兼任春秋馆修撰以下的官职,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员。朝鲜的弘文馆、艺文馆、春秋馆、承文院等皆是正三品衙门,官员互相兼任,一身数职,虽说艺文春秋馆负责编修《时政记》,实际上弘文馆等其他衙门的官员也全力参修。
《时政记》由史官编修,艺文春秋馆之堂上官负责督察,以便及时完成。其编修的机制,乃是史官分成小组,即如梁诚之曾建议:“以艺文馆禄官五人,兼官五人,二人为一厅,各分三年而编摩之。仍令春秋馆堂上考察,以为日课,以成重事。”[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史官分工合作,春秋馆堂上官加以监督。不仅春秋馆堂上官监督修撰,同时另派员查检核正,以免出错,“自祖宗朝,以弘文馆二员,定为常坐春秋,使之捡核修正”[13](卷77,中宗二十九年六月己酉)。但有时也无官督查,致使《时政记》不能按时修完,成宗年间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凡时政,春秋馆逐年修之,谓之《时政记》。然己丑年即位以后,适因多事且无监董之人,专不撰录,请以职带史局位高者,常仕监之。”[14](卷66,成宗七年四月甲申)朝鲜史官高位兼职者甚多,成宗遂采纳这条建议,以确保《时政记》能够按时编完。
与此同时,《时政记》编修的好坏成为评判史官的一种重要依据,“每当褒贬之时,将所撰《时政记》,春秋馆堂上齐会查看,以凭殿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所谓“褒贬”,乃是朝鲜每年皆进行的一项官员考察制度,“京官则其司堂上官提调及属曹堂上官,外官则观察使每六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等第启闻”[11](卷1《吏典》)。实际上是每年由各衙门堂上官,分别于六月和十二月两次给属员根据政绩定等级,上报朝鲜王廷。何谓“殿最”?“殿最,所以区别贤否,以凭黜陟,以示劝惩,所系至重。”[15](卷3,文宗即位年九月庚戌)也就是考察官员之时排定等级,“下功曰殿,上功曰最。殿,后也,言课居后也。最者,凡要之首,言课居先也。”[16](后集《注解上·户典》)“殿”乃是最下者,“最”乃是最佳者,根据官员的政绩排出他们考核的等第级别。“京外黜陟,每五考三上以上加资,三中仍旧资,四中罢黜,虽一考,不可不察也。今京外官褒贬之时,以被劾而不列等第者,后日考绩升黜之际,考据为难。请自今毕推后,殿最等第,随即启闻,追录官案,以凭后考。”[10](卷35,世宗九年二月己巳)可见,所谓“殿最”就是考核时之高下等级,乃是官员奖惩的依据,因而相当重要。《时政记》的好坏作为史官考核“殿最”的重要依据,可见监督甚严。光海君年间,《时政记》一度阙修,引得春秋馆官员不满,因为无《时政记》,史官“褒贬”就缺少依据[17](卷158,光海君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春、夏考核无凭,故而引得春秋馆的官员不满,希望能够稍作变通。这是常考制度。有时也因为《时政记》不修而直接惩处史官的。若史官不能按时完成《时政记》的编撰,拖沓不成者即被处罚。孝宗三年(1652年)四月,前正言赵嗣基下狱,乃因“嗣基曾经史官,而《时政记》未修正者,至于累朔。大臣以怠废职事,陈达于筵席,命拿推”[18](卷8,孝宗三年四月癸亥)。因之,朝鲜王朝对编修《时政记》的史官,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和考核制度,以确保《时政记》能按时保质完成。
可见,朝鲜不仅有专职的史官编修《时政记》,而且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不仅“上番”史官督察“下番”史官,而且由弘文馆之堂上官监督整个编修史官,以确保史书编修进度;若是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还要加以惩处。《时政记》的好坏成为朝鲜王朝考核史官的重要依据,因之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编修,不仅是一项常设制度,而且是由专职史官修成,为了保证史官尽职尽责完成编修任务,遂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
第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的内容并非完全以国王及朝廷为主,所包括的范围更广泛,乃是“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凡朝中一切礼乐制度正在实施者,皆是所书范畴,其特别强调“但书见行之事而已”,那些以前虽有但不再实施的制度不在所书范围之内。其中虽包括国王之举止言行,但不是重点内容,反而着重于现行制度的记述,这与唐宋不同。对于这种差异,朝鲜君臣也很清楚。成宗年间经筵日讲之时,讲及武周时期的《时政记》,成宗问朝鲜《时政记》何以为之,左承旨李克基对曰:“今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耳,唐时则不然。宰相畏其物议,故撰之饰美掩过耳。大抵史官畏大臣害己,故不直书其事。”[14](卷77,成宗八年闰二月丁卯)尽管这里对唐朝《时政记》的评价并不确切,不过其所言朝鲜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则基本恰当。其之所以将现行的制度文书全都包罗进来,乃是担心若不编辑成册,很可能会散漫无存。世祖年间大司宪梁诚之曾上书言:“《时政记》不可不急也。若岁月差久,则文籍散失,国家大典,诸臣拟议,泯没无传,诚为可虑。乞自壬申五月,至今丙戌年十一月,议政府、六曹、台谏、承政院文书,聚于春秋馆。”[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可见,乃先是将朝中各衙门的各种文书送交春秋馆收藏,史官就在这些文书资料基础上编成《时政记》。《时政记》是实录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大抵《实录》修撰之例,《承政院日记》、《时政记》、《经筵日记》、诸司《誊录》,凡可考文书悉皆裒集,分年分房,使各斤(斧)正编辑。诸臣史草,随年月日,直书全文,附入其间,片言只字不得有所增减编成”[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乙卯)。可见,《时政记》是编修实录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其编撰的最初动机也是为实录准备材料的。
同时,《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叙史实,而是有许多评论,几乎每一条史实史官都附上自己的评论语,甚至对国王的行为他们也敢于评论,这同中国的史书不同。仁祖九年(1631年,辛未)《时政记》中,多未附评论语,引得春秋馆史官不满。春秋馆诸堂上启曰:“史臣之设,不但为记录时政而已,所以褒贬是非,以为后世公论者也。今此冬等褒贬时,考见辛未年《时政记》,则全无史断之语,殊失修史之体。当该史官请推考。”[20](卷27,仁祖十年十二月甲戌)故而《时政记》中,史官评论相当重要。不过,评论是否得体,则是考察史官的一条重要标准。全湜(1563-1642年)讲了一个随意乱评的例子:
以记注官仕宣宗实录厅。一日,见《时政记》中有尹相斗寿在湖南状启,盖军粮措备事也。语不紧切,特循例催攒者也。史臣赞之曰:“以如此忠诚才识,不难于廓淸恢复,而为柳某(西厓)所沮,不得设施,呜呼痛哉云云。”其日堂上吴判书亿龄、郎厅则校理朴思齐、修撰朴曾贤及余也,相顾不即取舍。朴曰:“可以抹去矣。”余曰:“修史大事也,言虽不伦,不宜任意去取。徐待总裁官齐坐,处之如何?”吴曰:“是言是矣。”即付长标朱书以识之。不久,总裁官来坐,三房堂上亦会,一坐传看,皆笑之。总裁亲自抹去曰:“如此之处,如此议处甚善云。”[21](卷6《随手札录》)
全湜所讲的故事,乃是史官评论不合情理。他因此评论曰:“国朝设史官,例以新进少年,主莫大之事,以致论议如此,岂不谬哉!如使久于谙练稍有识虑者当之,虽不免为知己有所云云,而岂于尹相事,有如此笔法哉!可笑可惧也。”[21]可见,新进史官任意褒贬、不着边际,实在有些过分。但是《时政记》中又必须有评论语,如何写出恰如其分、论断得体的评论语来,并非易事。尽管《时政记》现皆不存,但《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史评相当丰富,或许是受到《时政记》的影响,将这种评论继承下来了。
第三,《时政记》所涉范围固然广泛,所书内容也力求详尽,一旦有缺,总设法补修。“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一旦有缺,当立即补修。仁祖初年发生李适之乱,“江都之变,本馆实录、《时政记》之移置者,尽皆散失”[20](卷34,仁祖十五年二月丁酉),致使“《光海日记》、《时政记》,散失殆尽,购得之数,不满十分之一矣”[20(卷4,仁祖二年二月丙午),一方面追究当时负责《时政记》等史书保管的史官检阅金光炫的责任,“以《时政记》、《日记》移置江华事,受点之后,未及输运而尽为散失。虽缘事势忙迫,駄马不具之致,而其不察职事之罪不可不惩,请命罢职”[20](卷5,仁祖二年三月戊午)。另一方面,组织史官重新补修,“请依《政院日记》修正例,别出兼春秋二员,收合各处所存朝报及其时史官家藏草册,使之逐日仕进,与时任史官,同察修正,而本馆堂上,亦令输回检饬”[20](卷6,仁祖二年五月戊午)。“《时政记》修正事,已为设厅,将依当初建请之意,撰集填补矣。”[20](卷6,仁祖二年六月辛亥)得以批准。
第四,实录未编前,保存《时政记》也有一套完整制度。《时政记》编修完毕后,乃由春秋馆“私自藏置,以待收纳”。当曝晒之年,方要求史官将《时政记》稿交付忠州史库收藏,以后作为实录编修之史料。实录修完之后,《时政记》与史草一并洗草不存。孝宗年间,《仁祖实录》修成后,实录厅上书征求如何处置《时政记》,认为“实录今已完毕。初草、中草及史官《时政记》,皆应入于洗草之中”。但有人认为“《时政记》当还于春秋馆,不可并洗”,随引起争论,询问以往史官前朝的处置办法,“则皆不能记忆云”,故而《时政记》是否洗草,实录厅官员“不能遽尔断定”[18](卷10,孝宗四年六月庚申)。四年后,有史官认为“或以为《时政记》,则不可并洗云。无前例可据,而揆以事势,则累朝史记,不可以两件流传”[18](卷19,孝宗八年九月庚申),最后得到国王批准,将《时政记》与史草一并焚毁。以后《时政记》皆在实录编完后,与史草一并毁掉,大多采取洗草的办法,乃是将这些史书放入汉江之遮日岩处,以水将文字洗掉,而将纸浆留存,作为制新纸的原料。肃宗年间,想改修《显宗实录》,但《时政记》已被洗草,“今当改修,无可考据。自己亥至甲寅,史官私藏草本,请使收纳”[22](卷10,肃宗六年十月庚寅)。可见,《时政记》在实录修成之后一并洗草,成为后来遵循的一种定制。英祖年间,亦是如此。英祖七年(1731)五月辛巳,国王与朝臣讨论实录编完后如何处置《时政记》,英祖决定:“先朝实录,事体至重,洗草之时,不宜埋没,故尚今迁就,意故有在。而《时政记》不宜一向留置于馆中,速令洗草可也。”[23](卷29,英祖七年五月辛巳)英宗八年(1732年)三月庚午,史官请曰:“《景庙实录》既成,《时政记》及中草,臣等请与实录堂郎,齐会遮日岩,依旧例洗草。”得到批准,是日实录堂郎会遮日岩洗草[23](卷31,英祖八年三月庚午)。宪宗四年(1838年)闰四月己亥,“纯宗朝《时政记》及实录初草、中草、初再见,洗草于遮日岩”[24](卷5,宪宗四年闰四月己亥)。因此,实录修成之后,《时政记》与实录之史草一并洗草,成为朝鲜后期的一项制度。尽管朝鲜花费很大人力物力编修《时政记》,但只是为编修实录提供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草一样皆被洗草,不再保存。所以尽管朝鲜王朝现今还保留了很多像《承政院日记》这样的日记、《备边司誊录》这样的各司誊录,却无《时政记》留存,充分说明《时政记》编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实录编修保存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也就失去其保存的价值,因而皆被洗草。
综上所述,尽管朝鲜王朝《时政记》乃效仿宋朝制度,但仍有很大差异。其目的是为编修实录而准备资料,编修者是专职史官,为了确保史官尽职尽责,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史官监督与考核制度。《时政记》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收罗各司文书及档案资料为主,实录一旦编成,《时政记》就和史草一样一并被毁。可见,朝鲜王朝之《时政记》,和唐宋两朝之《时政记》,名虽同,实则异。
三、“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
朝鲜初期编修《时政记》,乃是为以后实录编修保存史料。但到了中后期,因为它是记载当朝之政事、人物、制度,《时政记》竟然成为朝鲜党争的一个重要阵地。朝鲜王朝党争激烈,发生了多次“史祸”,其中燕山君时期的“戊午史祸”与明宗时期的“乙巳史祸”,皆或多或少与《时政记》有关,或者对当朝《时政记》的编修有直接的影响。《时政记》尽可能保持各种原始文献资料,对国王行为举止也保持实录精神,这样使得某些国王担心不利记录,故直接干预,燕山君李漋(1476-1506年)就屡屡干预。燕山君臭名昭著,在位十一年荒淫无道,残暴不仁,屡兴史狱,残害士类,后来被文武大臣废掉而放逐于江华岛。正是在燕山君时期,朝鲜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史祸——“戊午史祸”,亦称“戊午士祸”。
朝鲜初期,儒林分为勋旧派与士林派,勋旧派乃忠实于朝鲜王朝并垄断朝政的一批朝臣,士林派则是忠于高丽王朝、不与新朝合作、隐居于岭南的一批在野儒士。成宗时期(1469-1494年)试图推行美政,开始起用士林派人物,金宗直、金宏弼等是其中代表人物,但引起勋旧派的强烈不满,冲突不断。燕山君四年(戊午,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士林派史官金驲孙编写《成宗实录》时,收入金宗直《吊义帝文》一文,勋旧派人士柳子光、李克墩指责该文借项羽弑义帝影射朝鲜世祖(1455-1468年)篡位,于是掀起了弹劾士林派的风潮。燕山君原本不喜儒士,遂借机惩处士林派人士,他指责金驲孙:“实录云者何谓也?若曰实录则当以实书之,汝之史草皆诬,何以曰实录?……世祖中兴,其功德逾迈乾坤,子孙相继至今。汝既畜反心,何以仕我朝?”[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丁未)认为金驲孙“以不道之言,诬录先王朝事”[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辛亥)。在勋旧派的推波助澜之下,燕山君将士林派人物金驲孙、权五福、权景裕、李穆、许盘等处斩,诛杀三十多人,金宗直被掘墓斩尸,其余士林派人士皆被驱逐出朝廷,史称“戊午史祸”。这是朝鲜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史祸,影响极坏。虽然是勋旧派与士林派的斗争,但燕山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桩“史祸”,燕山君对史书的编撰倍加关注,而对记载当朝的《时政记》更是处处干预。《朝鲜燕山君日记》论之曰:
甲子以后,王追罪言事之人,凡论谏国政、君上过失者,或杀或窜,犹谓有漏,考《时政记》,罪之殆尽。又虑过恶传后,命春秋馆,其有涉言己过而书于《时政记》者,尽削焚之,犹追考不已,人危惧,因嘱史官,尽去之。故疏论言谏,多脱略不全。事虽失传,因此免者多,时以为天使之也。[19](卷37,燕山君六年五月戊午)
燕山君十年(1504年),有大臣上疏论其行为不当,他说:“人君不道,虽甚于桀、纣,为人臣者,固当隐恶也。今此骑马之事,则是予所为,姑置勿论,如宫禁隐微之事,乃敢揣度而言之,甚不可。”告诫说:“凡政事间事,则虽议我为桀纣可矣,如此宫禁事,揣度而言之,甚不可。为史官者,若不肖则必私于彼人,任己低昻,书诸史册曰:‘疏论如彼,而今乃削去。’彼虽如此书之,予固不屑。”[19](卷53,燕山君十年五月癸巳)可见,他非常痛恨史官书其不当之行为。《时政记》应该依时编修不得延误,但燕山君担心《时政记》屡书其不道之事,故而痛恨,他甚至直接发布诏书,要史官为其隐讳:“前日不肖新进之辈,妄录不当书之事,是岂国家设史官之意乎?《春秋》传曰‘为亲者讳’,君父虽有过,犹当讳之,况书所无之事乎?前日金驲孙所书,若不暴着,何由得知?自今《时政记》五年一修撰,如有不当书之事,治罪。”[19](卷58,燕山君十一年七月辛卯)史书应该本着实录精神,他却以“戊午史祸”中被惩处的金驲孙为例,要求史官不应书“不当书之事”,也就是应该为他隐讳。燕山君十一年(1505年,弘治十八年)二月八日,燕山君命令春秋馆堂上官查考《时政记》,燕山君对所上《时政记》条目逐一加以评断,并追究史官责任。一共查了九件事情,一一惩处相关人士[20](卷57,燕山君十一年二月甲子)。他甚至指出:“史官记事,如用人、治民、政事等类外勿书。且以金驲孙为戒,作文以谕。”[19](卷62,燕山君十二年四月己巳)因为史官屡屡违反,他竟然将《时政记》的修撰改为五年一修,故意不令史官依时编修,史官动辄得咎,故燕山君一朝之《时政记》大多残缺不全。有史臣曰:“《时政记》,前此艺文馆、弘文馆,常仕修撰。今则不然,旷月未修,史事陵夷,渐不如古。自废朝以后,人心怯懦,士气沮丧。撰史者稍有危言,辄割去,至于日记撰集之时,了无可记之事。”有史官直接指出:
废朝日记撰集之时,臣亦参焉。考于日记,了无所记,求诸家史,但书阴晴,故废主行事,不能悉记,是诚弊习所使。且前时史官,非但记朝廷之事,兼书大臣之过,故起戊午之祸。以此为史官父兄者,戒其子弟,毋得如是,故士气日以陵夷,记史渐不如古。[13](卷13,中宗六年正月己卯)
可见,“戊午史祸”之后,士风不振、史官畏避、“但书阴晴”而已,一直影响到中宗年间。“戊午史祸”既是一起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党争,也是一起燕山君企图控制史官修史的事件,影响极坏。明宗二年(1547年),《时政记》修成后,以领议政尹仁镜、左议政李芑等为撰集厅堂上官,准备编修《续武定宝鉴》,乃将乙巳年(1545年,仁宗元年,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九月、十月《时政记》移往撰集厅以备参考,但引起艺文馆史官不满。他们上书反对,以为“当代史记,自古未有披览,虽兼春秋官,修史入藏之后,则例不得出见。今者……移送撰集厅,此古所未有,至为未安。若一开端,则恐违重史之义,而后世无史官尽职之路也”。进而指出:“况《续武定宝鉴》撰集,虽非《时政记》,既有《承政院日记》,又有罪人推案。当代史记,请还藏于春秋馆,以重史事。”[25](卷6,明宗二年癸卯)《续武定宝鉴》撰修官们辩护道:“顷者艺文馆官员等,不问于臣等,以当代《时政记》不可轻易出见之意,径自启达,即还藏春秋馆,其于事体至为颠倒。请并推考,《时政记》亦还移参考。”[25](卷6,明宗二年正月乙巳)明宗国王批准其建议,最终《时政记》还是作为《续武定宝鉴》的参考资料。就此乙巳年三个月的《时政记》,竟然又引出一桩史祸,史称“乙巳史祸”。
前面提到《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录事实,还有许多评论语,正是因为这些评论,引起领议政尹仁镜、左议政李芑等人不满,故而将其揭发出来。在这三个月的《时政记》材料中,既有指责朝臣不当之言,亦有讽谏国王行为不妥之语。如九月初三日《时政记》书:“上好鹿肉,尤好鹿尾。外方进上,或有不得生鹿者,有以生獐代进者,上谓近侍曰:‘十首生獐,安能当生鹿一首?’又于今六月患痢,思极新鲜之味,内侍传于承旨,承旨等承意图之,生鲋鱼及银口鱼等物,或多从外方而至,上命停之。”特别记载明宗国王好鹿尾,并批注曰:“主上今方宅忧,而年幼,故如此。”[26](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指出明宗国王当时尚在丁忧之时,尚思美味,似有不孝之嫌,以其年幼无知为其开脱。这种评论有大逆不道之嫌。除了说国王行为不当之外,尚有其他许多评论,几乎所引的史事都有修《时政记》史官的评论,引起了撰集厅诸官的不满,上书国王:
臣等以《武定宝鉴》撰集事,取乙巳年八月《时政记》披考,则罪人招辞,略而不书,逆贼供下,多书不祥之言。臣等见之,不胜惊愕。逆贼情状,甚为昭昭,而不以逆贼书之。史笔当直书,垂示万世,而此则皆以不实书之,不可以此传信后世。请推考后从实改正。其它不实之事,亦或有之,而非如此大关之事,故不为书启。且丙午年,自上好鹿尾等事,史臣书人君过举宜矣,而此则不实之事,若此已甚书之,故并启之。[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
认为《时政记》“多书不祥之言”,且所书多不实之事,且“郭珣、成子泽等推案,多有漏书事”[25](卷9,明宗四年正月庚辰),而所谓国王好鹿尾之事,即为不实之事。明宗震怒,指令:“情状之惨酷,莫若今时之逆贼,而何以人心不定、是非不明乎?今又有如此惊骇之事,以逆贼为是,朝廷为非,以此传示后世,则何有若此事乎?各日所书,细推其人,阙庭推问后,从实改正。其它不实事,亦并书启后改之。鹿尾事,安有如此事乎?若以为吾君,则岂以不明之事,如此书之乎?必有异心,并推可也。”[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于是追查何人所书,又将专记国王的日记拿来一并对照,发现日记中并无此事。查出所书史官为孙弘绩,乃将其审问。孙弘绩解释说此事乃是他私下听内廷官员所言,认为:“其时承旨,不知为某员,而小臣愚意,为史官者,虽私自闻见之事,固当书之于史册,而此则内侍,公然传说于政院而不书之,恐为非矣,故书之。而其所以为注之意,欲使后世,知主上年幼质弱,不得不如此之意耳。此小臣非敢欲彰君过,只记所闻,而实美自上命停,故亦书矣。”[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除这件事外,尚有其他数十件他们觉得不妥之事,逐一审问相关史官,最终乃将与此事相关的史官皆加以惩处,“(安)名世既被杀,(赵)璞与(孙)弘绩,相继远窜”[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而这几个月的《时政记》被重修。《朝鲜明宗实录》的撰修者论之曰:“一时权奸,恶其直笔,既杀其人,又改其书,将欲掩其恶也,而事迹在人耳目,终不可掩,则此所谓欲盖而弥彰者,其为计不亦愚乎?”[25](卷8,明宗三年十一月甲戌)此次史祸乃是朝中党争的具体事例。实际上,乃是执掌政权的小尹派为让自身地位合法化,借修《武定宝鉴》之机,矫诏篡改《时政记》,以诋毁失势的大尹派。因此“乙巳史祸”是一起典型的以《时政记》为借口,激怒国王,达到打击政敌目的的党争事件。
综上所述,因为《时政记》乃记载当朝人事和制度,朝鲜国王与朝臣都很关注,“戊午史祸”虽然是士林派金驲孙所书实录史草,在勋旧派的推波助澜下触犯了燕山君国王,却自此引起燕山君对编修《时政记》百般干预,不仅规定《时政记》所书内容,甚而停止《时政记》的正常编修,使得燕山君一朝《时政记》残缺不全。明宗时期的“乙巳史祸”,则完全是利用《时政记》所载史事而引出的一桩史祸,朝中党派斗争以《时政记》为借口,掀起打击政敌的斗争。因此,《时政记》并不仅仅是一种史书,还可以说是朝鲜政治斗争的缩影。
四、结语
东亚乃汉字文化圈,朝鲜半岛数千年来与中国一样,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即便是朝鲜世宗年间创制了韩文字母,但官方文书与史书还是用汉字书写。正因此,史书体裁也基本上是仿效中国古代史书的。一般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史书体裁,在朝鲜半岛历史上都曾仿效过,朝鲜王朝《时政记》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是这种仿效并非全盘照搬,而是结合朝鲜半岛的情况多有变更。朝鲜王朝也编修纪传体正史,但只留存了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郑麟趾主编的《高丽史》。朝鲜半岛历史上也编修实录,就朝鲜王朝而言,其实录编修制度较之明清更为严格,管理也更为细致,《朝鲜王朝实录》在体裁上也多有变更,如其有完整的人物传记、多重视史评等。可见,朝鲜半岛在仿效和吸收中国史书体裁之时,尽管源头来自中国,但有很多变更和创造。《时政记》的编修,尽管仿自宋朝,但无论从内容、编修史官、主要目的以及保存方式等等方面,都与唐宋有很大差异。透过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考察东亚文化之时,即便是同一名称的事物,弄清其源头与相似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一定还要分析其不同与独特之处及其背后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东亚文化的特性。
注释:
①有关中国历史上《时政记》的研究,参见何锡光:《唐朝“时政记”的修撰》,《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陈风:《姚璹与时政记》,《档案天地》1995年第5期;蔡崇榜:《宋修时政记考》,《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健、王玲:《宋代时政记的纂修》,《兰台世界》2009年第21期;谢贵安:《〈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另外,蔡崇榜在《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和王盛恩在《宋代官方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宋代的时政记房及《时政记》的编修制度都有较系统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