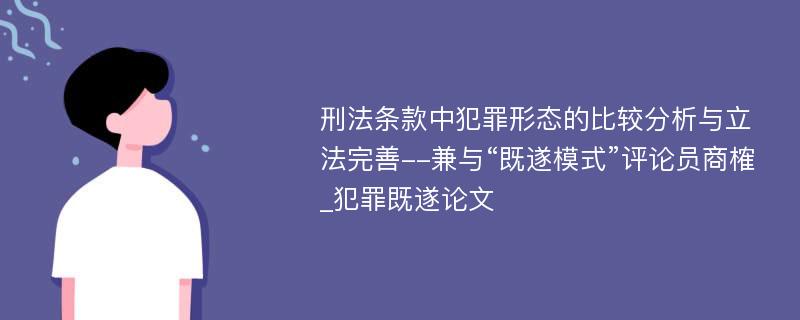
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比较分析和立法完善——兼与“既遂模式”论者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罪状论文,论者论文,刑法论文,分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91(2010)01-0020-07
长期以来,我国主流刑法理论认为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构建的。这在持该认识的部分论者看来,“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1]但这一“不言自明”的认识却遭遇了持续不断的诘难。面对质疑,近年来有学者对“既遂模式说”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为这一主张及其所支撑的犯罪既遂理论辩护。鉴于这一问题关系到犯罪既遂理论的合理建构,也直接关系到对某些具体犯罪罪状的正确理解与适用,通过深度交锋进一步澄清认识无疑是有益且必要的。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从实然和应然两方面对“既遂模式说”的辩护者做出回应,揭示其理论偏差的症结所在,对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形态的立法模式予以检讨并提出完善建议,探寻通过立法从根本上消除犯罪既遂的理论乱相及司法适用困难的有效途径。
一、国外犯罪形态立法模式之比较
按照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理论,“刑罚法规所表示的基本构成要件,本来是预想着既遂犯而制作的”,[2]因而“只要满足所有构成要件要素即构成既遂”;[3]而未遂罪则是“尚未完全实现构成要件的内容”。[4]这便是“构成要件齐备说”这一犯罪既遂理论的基本内涵,也是我国刑法学界的“既遂模式说”及其支撑的犯罪既遂理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的理论渊源。因此,在讨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罪状模式之前,有必要通过对外国刑法在犯罪形态上的立法模式做比较分析,探明其刑法理论上的立论根据及内在逻辑。鉴于我国刑法及其理论主要受大陆法系影响,这里的比较分析也局限于大陆法系刑法。
综观大陆法系及受其影响的各国刑法,对于有关犯罪形态的分则规定,大体上存在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模式:
第一种是意大利模式。其特点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罪状和基本法定刑都是以既遂罪为模式的。这体现在其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中。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75条对杀人罪的基本罪状及法定刑的规定是:“造成一人死亡的,处以21年以上有期徒刑。”第624条对盗窃罪的基本规定是:“为自己或其他人获取利益的目的,使他人的动产脱离持有人的控制,将其据为己有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6万至100万里拉罚金。”至于犯罪未遂,则根据刑法总则第56条规定的幅度减轻处罚。基于这样的立法,意大利刑法理论认为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以既遂罪为模式,并把犯罪既遂界定为“完全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5]具有法律上的根据。
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也采取了这种模式,并因此在总则第29条中对犯罪既遂做了如下规定:“如果犯罪人实施的行为含有本法典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则犯罪是既遂犯罪。”
第二种是法国模式。其特点是,刑法中的刑罚规定并不严格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法定刑不仅适用于既遂罪,也同样适用于未遂罪,相应的,分则中的基本罪状并非以既遂为模式,而是着眼于犯罪实行行为。虽然刑法总则有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但其意义主要在于明确刑事可罚的范围,而没有为未遂犯设立不同于既遂罪的刑罚规定。既遂与未遂仅仅只是司法上的刑罚个别化事由。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法国刑法理论并不认为刑法分则的规定是以既遂罪为模式的,也不以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齐备与否界定犯罪既遂与未遂。[6]
第三种是德国模式。德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罪状并不描述犯罪既遂要素,因而单从罪状本身看似乎并非以既遂为模式,但结合总则与分则的规定整体分析,实际上是以既遂罪为模式的。德国刑法典第23条规定,“重罪的未遂一律处罚,轻罪的未遂的处罚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未遂可比照既遂减轻处罚。”第49条对减轻处罚的规定是:终身自由刑由3年以上自由刑代替;有期自由刑可判处最高刑的3/4;规定了最低自由刑的,其最低自由刑为10年或5年的,减为2年,其最低自由刑为3年或者2年的,减为6个月……上述规定表明:(1)德国刑法通过总则规定与分则规定相结合的方式,明确限定未遂的处罚范围,即限于重罪的未遂及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处罚未遂的情形。其逻辑表达式是:刑法对于故意犯罪的处罚以既遂为限,除非法律明文规定处罚未遂者(“重罪”及分则有特别规定者)。此即德国刑法理论上所谓“以处罚既遂犯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2)在刑罚上,对于处罚未遂的犯罪,法律将未遂犯与既遂罪明确加以区分:刑法分则以既遂为标本规定法定刑,对于未遂则可比照既遂犯依照第49条减轻处罚。故其法定刑是以既遂罪为模式的。(3)基于上述两点,虽然罪状中没有明文描述犯罪的既遂要素,但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罪状在逻辑上是以既遂罪为模式的——对于那些未明文规定处罚未遂的犯罪而言,由于刑法将未遂行为排除在刑罚范围之外,其罪状自然是以既遂为模式的;对于那些明文规定处罚未遂的犯罪而言,由于刑法在基本罪状之外对未遂行为可罚性的补充式规定,亦间接表明基本罪状是以既遂为模式的。正是基于对这种立法模式的逻辑推断,德国刑法理论得出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罪状以既遂罪为模式的结论。(4)由于法条并没有明示犯罪既遂要素,既遂标准作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并不具有明确的法定性,因而在理论上被称为“不成文之构成要件要素”,或称“不加规定之构成要件要素”。[7]这就是说,虽然犯罪的既遂要素在逻辑上被认为是(既遂罪)法定构成要件的要素之一,但并不具有成文性。因此,犯罪既遂标准的确定,仍然是刑法理论的任务。这一点是其与意大利模式的基本差异之所在。
第四种是日本模式。日本模式类似于德国模式,所不同的是,日本刑法典第44条规定,“处罚未遂的情形,由各本条规定。”因此,日本刑法中未遂的处罚范围全部由分则条文具体规定。譬如,该法典第296-298条分别规定强奸罪、强制猥亵罪以及奸淫、猥亵幼年入罪之后,第299条规定,“前三条之罪的未遂犯,应当处罚。”在刑罚上,日本刑法典第43条规定,“犯罪未遂的,可以减轻处罚,中止未遂,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这表明,日本刑法中的基本罪状及基本法定刑都是以既遂为模式的。不过,其与德国模式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基本罪状中并没有描述犯罪既遂要素,使得犯罪既遂的成立条件成为所谓“不成文之构成要件要素。”基于这样的立法,日本刑法理论认为“刑罚法规所表示的基本构成要件,本来是预想着既遂犯而制作的,”[8]便是合乎逻辑的。
上述表明,在国外,既遂模式并非各国刑法分则在立法体例上的一致选择,“既遂模式说”也非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共识,而是一部分国家的刑法理论基于本国刑法做出的一种事实判断或者符合其法律内存逻辑的推论。
二、我国刑法分则中犯罪形态立法模式之辨析
我国刑法学界的“既遂模式说”是否具有立法上的根据呢?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对此予以论证,以回应学界对于“既遂模式说”的质疑。其基本论据有二:第一,既遂模式说在解释论上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为在罪刑法定条件下,不仅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需要有刑法的明确规定,而且对于行为构成何种形态的犯罪同样需要根据刑法的规定。刑法总则专门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特征及处罚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而没有对犯罪既遂作规定,说明刑法分则规定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的。第二,“坚持我国刑法分则条文是以犯罪的既遂为模式的观点符合我国立法者的意图和我国刑法的规定。”因为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条文中“比照”、“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等用语实际已经内含了我国刑法分则条文是以既遂犯为模式设置的命题。[9]如果单从法定刑而言,这一论证有其道理,但如果从罪状模式而言,这一论证则不能成立。下面以我国刑法规定为据做比较分析。
我国刑法与前述四种立法模式均不相同。其特点是:(1)基本罪状中没有描述犯罪既遂要素。这是其与意大利模式的不同之处。(2)在刑罚设置上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法定刑通常以既遂罪为标本。因为“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23条第2款),就意味着法定刑是以既遂犯为常态设置的。这是其与法国模式的不同之处。(3)以未遂行为的刑事可罚为原则,以未遂的不可罚为例外(至少立法上如此)。这表现在,刑法总则第23条确立了对未遂犯应予刑事处罚的一般原则,并没有对其可罚范围做特别限定;但在刑法分则部分,对某些危害性程度较轻的故意犯罪,通过将特定的危害结果设置为犯罪成立要素,以排除其未遂行为的刑事可罚性。譬如,现行刑法对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明文规定以行为“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为犯罪成立要素,从而将未遂行为排除在刑事可罚范围之外。这意味着,对于刑事违法行为的未遂,立法上是逻辑地将其纳入刑罚范围的,只有那些将犯罪既遂要素设置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立法上才绝对排除其未遂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其逻辑表达式为:对于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的故意犯罪,未遂原则上可罚,但刑法分则有特别规定者(罪状以既遂为模式者)除外。这体现出与德、日模式的基本差异:德、日刑法是在原则上排除未遂行为可罚的前提下,通过特别规定肯定部分未遂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我国刑法是在原则上肯定未遂行为可罚的前提下,通过特别规定(将既遂要素设置为犯罪构成要件)排除部分未遂行为的刑事可罚性。由于这种差异,德、日刑法理论可以逻辑地认为,虽然既遂要素没有描述在罪状中,但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构成要件“是预想着为既遂犯制作”的;而对于我国刑法规定而言,则应当得出另一种结论:除了刑法分则将既遂要素明文设置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以外,故意犯罪的罪状规定不是以既遂为模式的。例如,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立法上通过将前者的既遂要素设置为犯罪成立要素(即以既遂为模式),将其未完成行为排除在刑罚范围之外,而对后者则将犯罪既遂要素排除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外(即不以既遂为模式),从而将犯罪的未完成行为纳入刑罚范围。因此,后一种罪状模式将犯罪既遂要素排除在外,既不是因为立法技术上的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必要,而是立法上区分可罚的未遂与不可罚的未遂的一种逻辑选择。(4)对于处罚未遂的犯罪而言,刑法分则的规定在罪状模式与法定刑之间缺乏统一性:法定刑是以既遂为模式的,而罪状并非以既遂为模式。这一点是其与前述4种模式之间均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有待改进的一个重大缺陷(详见下文)。
上述表明,我国刑法分则对于需要处罚未遂的故意犯罪的基本罪状,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既不同于意大利式刑法明示的既遂模式,也不同于德、日刑法在逻辑上隐含的既遂模式,而是一种非既遂模式(但不是某些学者所主张的“犯罪成立模式”。“犯罪成立模式”以犯罪预备为起点,而分则条文描述的罪状是针对犯罪实行行为的)。同时,这种罪状上的非既遂模式与法定刑上的既遂模式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我国刑法学界“既遂模式”论者正是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到我国刑法与德、日刑法之间在内在逻辑上的差异以及我国刑法在罪状与法定刑之间的不一致,以至不当地借鉴了德、日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既遂理论及既遂模式说,并不当地通过“法定刑以既遂为模式”的论证代替“基本罪状以既遂为模式”的论证,以此支撑“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这一犯罪既遂理论。其结果是,不仅造成了其犯罪既遂理论的混乱,而且也造成了对某些犯罪的罪状在认识上的混乱(见下文)。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使就我国刑法的法定刑而言,所谓以既遂为标本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例如,我国刑法对放火罪的处罚,是直接根据后果严重与否,分别设置法定刑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所谓“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包括已经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行为和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这就是说,放火罪的未遂行为也是直接适用法定刑的。①
“既遂模式”论者将“既遂模式说在解释论上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作为“既遂模式说”的论据,不过是用“应然”替代“实然”,其逻辑上的苍白无需赘言。
三、两类犯罪的罪状模式辨析
既遂模式说不仅仅在理论上支撑着一个虚假的犯罪既遂理论,而且造成了对某些犯罪的罪状的认识混乱,其中最突出的是数额型犯罪(“数额犯”)和某些以特定危险作为犯罪成立要素的犯罪。
(一)数额犯的罪状辨析
这里探讨的数额犯,是指以法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定量标准的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有人基于既遂模式说,误将数额犯中作为定罪标准的法定数额理解为犯罪既遂条件。例如,“刑法第140条所规定的‘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既遂要件之一而不是本罪的犯罪成立要件之一。”并据此认为,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并已现实地取得了全部销售款,根据其销售金额是否达到5万元,分别认定为犯罪既遂与未遂。[10]在这里,决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既遂与未遂的,是现实取得的销售款的数额大小,而不在于伪劣产品是否销售出去。
这种认识,是对罪状和立法精神的误解。数额犯中作为定罪标准之一的数额,并非犯罪构成中的一个独立要件。因为,法定的数额属于犯罪构成中特定要件(如行为对象、行为结果)的定量因素,是对该特定要件的量的要求。被量化的要件不同,数额所具有的内涵与意义也不尽相同,定罪的标准也因此不同。根据被量化的要件,数额犯中的法定数额有结果数额与行为数额之分。前者是对构成犯罪在行为结果上的定量要求。例如,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构成,以“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为犯罪构成的结果要件。其中的数额巨大是对犯罪结果的定量规定,即只有发生获取数额巨大的非法利益这一结果,才能构成犯罪。后者是对构成犯罪在行为所及数额上的定量要求。例如,保险诈骗罪中的“数额较大”,并非以诈骗获得数额较大的财产这一结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是以诈骗数额较大的保险金这一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对于结果数额犯来说,由于发生符合法定数额的结果是犯罪成立要素,如果该结果不发生,犯罪就不成立,所以无犯罪未遂存在的余地。对于行为数额犯来说,由于法定数额是对行为所及数额在定罪上的定量要求,故只要行为数额达到法定标准,无论是否造成实际危害结果,均可构成犯罪。其中,发生立法所防止的危害结果的,是既遂,未发生这种结果的是未遂。至于法定数额,是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标准,而非犯罪既遂标准。[11]以盗窃罪为例,我们假设如下几种情形:(1)行为人甲在商店将一件价值200元的衣服偷走;(2)行为人乙在商店窃取一件价值200元的衣服时被当场抓获;(3)行为人丙成功地将他人价值15万元的一部汽车偷走;(4)行为人丁盗窃他人价值15万元的汽车,在撬锁时被当场抓获。上述四种情形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行为是否既遂。从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角度看,甲和乙由于盗窃数额不大,不构成盗窃罪(暂不考虑是否多次盗窃的问题);而丙和丁由于盗窃数额巨大,构成盗窃罪。从行为是否既遂的角度看,甲和丙的行为属于既遂,其中,甲的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的既遂,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丙的行为属于盗窃罪的既遂;而乙和丁的行为属于未遂。显然,数额大小是盗窃罪成立与否的根据,而非犯罪既遂与否的标准。如果将“数额较大”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就会逻辑地得出甲和乙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而丙和丁的行为均属于犯罪既遂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既混淆了盗窃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混淆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因此,数额犯中法定的基本数额属于犯罪构成的定量标准,其功能在于区分罪与非罪,而非划分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
(二)包含危险性要素的犯罪的罪状辨析
我国刑法对某些犯罪的基本罪状的规定中,包含有某种危险性的描述。这种在罪状中作了危险性描述的犯罪,被主流刑法理论作为犯罪既遂类型意义上的“危险犯”,而其立论根据,也在于把刑法关于这类犯罪的罪状规定理解为以既遂为模式,而法条上的危险性描述被认为是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规定。[12]这同样是对罪状和立法精神的误解。其实,这类罪状中的“危险”是作为犯罪成立要素的危险,而非犯罪既遂标准。对此,有必要区分两类情况予以说明。
一类是以发生客观危险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素的犯罪,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等。对于这类犯罪而言,如果不具备法定的客观危险,就不可能构成该种犯罪,因而并不存在危险意义上的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之分,也就不可能是这一理论所主张的既遂意义上的危险犯。譬如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以“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作为其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如果生产、销售的假药并不具有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就不构成该种犯罪,而只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需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由于“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危险要求是犯罪成立要素,而非犯罪既遂标准,故生产、销售假药罪也就不可能是既遂意义上的危险犯。刑法之所以将某种客观危险设置为这类犯罪的成立要素,是由这类犯罪的主观特征所决定的,即主观上对造成法益实害(如生产、销售假药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果)只限于过失和间接故意,而不包含侵害法益的直接故意。
另一类是要求行为具有特定危险性质的犯罪,如放火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等。刑法对这类犯罪在罪状上的危险性要求,如‘危害公共安全’、“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等,实际上是对罪质的说明,即对行为基本性质的要求。其意义在于从实质上明确这类犯罪与非罪、与他罪的界限,而不是确定犯罪既遂标准。原因在于,从主观上看,这类犯罪是包含了侵害法益的直接故意的故意犯罪。对基于侵害法益的直接故意犯罪来说,如果将某种客观危险状态设置为犯罪成立要素,就会将尚未造成这种客观危险的预备行为及部分实行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另一方面,如果刑法对这类犯罪只从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做客观描述,而不说明其危害公共安全的实质,就不可能把这类犯罪同非罪、同他罪区别开来。例如放火罪,如果法条只做“放火”的罪状描述,就意味着不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也构成放火罪。又如破坏交通工具罪,如果只做“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的罪状描述,就不可能把并不危害交通安全的破坏行为(如拆除汽车发动机的点火装置、毁坏火车坐椅等)以及虽然危害交通但尚不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破坏行为同本罪区别开来。所以,这类犯罪的罪状中所描述的危险是对行为危险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的要求,而非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或者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客观危险状态。其实,通过在罪状中描述行为的性质来限定犯罪范围的,并不限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刑法第252条对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的规定除了描述“隐匿、毁弃、非法开拆他人信件”这一行为表现形式外,还要求行为“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如此规定,是因为隐匿、毁弃、非法开拆他人信件,并不当然地具有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的性质(如毁弃他人已经开拆并知悉内容的信件),如果罪状只是描述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不够的。放火罪等犯罪中的危险规定在道理上与此是相同的。
既遂意义上的危险犯理论通常是以后一类犯罪中的危险规定作为立论的法律根据的,其症结正在于把法律关于行为性质的危险要求,理解为作为既遂标准的客观危险。[13]这样理解的结果,就使得这类犯罪同非罪、同他罪之间的实质界限将不复存在。例如放火罪,如果按照这种观点,能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放火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是犯罪既遂,未危害公共安全的是犯罪未遂。又如破坏交通工具罪,其逻辑结论是,破坏交通工具,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是犯罪既遂,不足以使交通工具倾覆、毁坏的,是犯罪未遂。如此,则拆除汽车发动机的点火装置、毁坏火车坐椅等行为就都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未遂)。这显然违背立法精神。
四、罪状模式的立法检讨与完善
对于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之分的犯罪来说,刑法分则的规定应当在罪状模式与法定刑之间保持一致:如果罪状不是以既遂为模式,法定刑就不应当以既遂为标准;反过来,如果法定刑以既遂为标准,罪状就应当以既遂为模式。否则,在具有承接关系的罪状与法定刑之间,就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但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罪状与法定刑之间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造成的逻辑矛盾,一定程度上也是构成要件既遂模式说这一理论主张形成的原因之一。
因此,如何消除罪状与法定刑之间在立法表述上的矛盾,使两者一致起来,是我国刑法的立法完善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比较国外的立法,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像法国刑法典那样,罪状与法定刑的规定均不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另一种选择是,罪状与法定刑均以既遂为模式作规定。比较而言,后者应当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前一种模式在对待未遂犯的处罚上,采取的是主观主义的立场,即不考虑犯罪结果,而是对犯罪故意进行惩罚,而且对未遂犯如同犯罪已经产生结果一样给予严厉惩罚。[14]显然,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而,对于那些需要处罚未完成行为的犯罪,从立法上对犯罪既遂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在刑罚上区别对待,十分必要。由于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般形态,刑法分则以犯罪既遂为标准规定刑罚,无疑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这就是说,法定刑应当以既遂为标准作规定,相应的,刑法分则的罪状规定也应当以既遂为模式。
确立罪状在立法上的既遂模式,就需要将犯罪既遂要素明文描述在基本罪状中。这不仅是消除立法表述矛盾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避免对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产生不必要的认识分歧,是罪刑法定的题中之意。在这一点上,意大利刑法典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显然比德、日刑法更具有借鉴价值。德、日刑法虽然从逻辑上说是以既遂为模式的,但由于法条没有将犯罪既遂要素描述在罪状中,使得犯罪既遂标准缺乏法定性和明确性,这必然导致对某些犯罪的既遂标准(乃至是否需要区分既遂与未遂)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认识分歧。
在罪状中描述犯罪既遂要素,就需要改变我国刑法对于犯罪的未完成行为在处罚范围上的确定方式。一如前述,我国刑法对于故意犯罪的未完成行为,原则上是纳入刑罚范围的,对于少数不需要未遂行为的犯罪,则通过将既遂要素设置为犯罪构成要件来排除其未遂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以这种方式排除部分故意犯罪的未完成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只有在罪状通常不以既遂为模式的前提下,才是可行的。否则,那些需要处罚未遂的犯罪与那些不需要处罚未遂的犯罪之间,在立法上就不再是明确的了。例如,对于诈骗罪,如果将“使财物脱离持有人控制”这一既遂要素规定在罪状中,那么,这种犯罪与那些不需要处罚未完成行为的故意犯罪(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间,在罪状模式上就不存在区别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三种可能的途径。
第一种是像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那样,只是对犯罪的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作明确限定(限定在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的犯罪之内),而对未遂行为的刑事可罚性,立法上不予排除,即全面确认各种故意犯罪未遂行为的刑事可罚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0条)。这种全面处罚未遂行为(至少逻辑上是如此)的立法,未免严酷,因而并不可取。尤其是考虑到我国采取的是刑事制裁与治安管理处罚并行的违法制裁体制,刑法对犯罪构成除了定性规定之外,往往还有定量要求,以限缩刑事处罚的范围,这种情况下对犯罪的未遂行为全面处罚就更不可取。
第二种是采取瑞士模式或者德国模式。前者将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和越轨,对于未遂的处罚,由刑法总则作概括性规定,即未遂的处罚只限于重罪和轻罪(瑞士联邦刑法典第21条、22条),对越轨的未遂不罚。后者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对未遂的处罚范围,由刑法总则与分则结合作规定,即重罪的未遂一律处罚,轻罪的未遂的处罚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德国刑法典第23条)。这种由刑法总则概括性地明确未遂行为的可罚范围的模式,虽然简约,但存在明确性不强的问题,并可能由此导致认识上的混乱。以德国刑法为例,其规定重罪的未遂一律处罚,但重罪中有些属于单纯行为犯(甚至有些重罪规范本身就是针对诸如预备战争罪等犯罪预备行为的规定,即独立的预备犯),这就可能导致理论认识上的混乱,即单纯行为犯是否存在未遂以及是否处罚未遂。德国刑法理论对某些犯罪在未遂问题上的认识分歧,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种是采取日本模式,即由刑法分则以具体规定的方式明确犯罪未完成行为的刑事可罚范围。这样规定虽然不如概括性的规定简洁,但明确性强,也能避免德国模式可能导致的某些认识混乱,是值得借鉴的。
综合上述,我国刑法分则的立法模式,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完善:(1)故意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都应当以既遂为模式,以消除现行刑法存在的罪状与法定刑之间存在的逻辑矛盾。(2)犯罪的既遂要素应当明确规定在基本罪状中,使犯罪的既遂标准具有明确的法定性,以免对犯罪的既遂标准产生不必要的认识分歧。(3)通过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明确未完成行为的刑事可罚范围,即对于需要处罚未完成行为的犯罪,在分则条文中以肯定的方式明确规定。其中,对于犯罪预备和犯罪中止的处罚,应限于少数性质极严重的犯罪。
与刑法分则的立法完善相关联,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也应当作相应的修改与完善。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犯罪未完成行为的处罚范围,应当确立以刑法分则规定为限的原则,以此将那些在分则中未规定予以处罚的犯罪未完成行为,明确地排除在刑罚范围之外。其二是,需要对犯罪既遂作明文规定,并对犯罪未遂概念作相应的修改。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虽然立法上对犯罪未遂的明确规定,也能使人们明了犯罪既遂的内涵,但从立法科学与严谨的要求看,在刑法总则中对犯罪既遂作一般规定是一种更合理的选择。因为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基本形态,从逻辑顺序上说,应当先明确犯罪既遂,再以犯罪既遂的规定为基础明确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及其刑罚。如此,刑法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规定才有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前提和明确的参照标准。在这一点上,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是值得借鉴的。不过,该法典第29条对犯罪既遂所作的如下表述并不可取:“如果犯罪人实施的行为含有本法典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则犯罪是既遂犯罪。”虽然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分则规定是以既遂为模式的,并且通常将犯罪既遂要素描述在罪状中,一定程度上为这一表述提供了根据,但如此界定犯罪既遂概念,仍然有欠合理。首先,这样的表述没有明确犯罪的既遂标准和犯罪既遂的实质内涵,并在逻辑上混淆了犯罪未遂与非罪的界限。因为非罪行为无疑是不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的。正因为如此,理论上不得不对这一规定作补充性的说明与完善:“既遂犯罪区别于未完成的犯罪之处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而只是一个要件,那就是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这个逻辑是一目了然的:未完成的犯罪未进行到底,而既遂犯罪已经进行到底,而这个底就是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其他要素的不存在不影响行为的完成。”[15]虽然在解释者看来,这是一目了然的,但其解释本身就已经否定了法定的犯罪既遂定义。其次,这样的表述泛化了既遂罪概念,将过失犯罪和单纯行为犯这类不存在犯罪进程形态变化的犯罪都逻辑地包含在犯罪既遂之中了,使这类犯罪的成立问题与犯罪既遂问题混为一谈。笔者以为,鉴于犯罪既遂的实质标准在于发生立法所意图防止的犯罪基本结果(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结果),[16]对于那些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之分的犯罪而言,在以既遂为模式规定罪状时,必定是将某种特定的危害结果描述在罪状之中,并以此作为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因此,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既遂的规定应当表述为,“实施故意犯罪,发生本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结果的,是犯罪既遂。”这样表述简单明了,并且将过失犯罪排除在犯罪既遂概念之外。相应地,犯罪未遂的规定应当修改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原因而未发生本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结果的,是犯罪未遂。”
按照上述方案,不仅犯罪既遂的概念和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明确,而且能够从立法上把下述三类故意犯罪明确区分开来:一类是处罚未完成行为的故意犯罪,其在立法上的特征是,将作为既遂要素的结果描述上罪状中,同时另款规定处罚该罪的未完成行为;第二类是不处罚未完成行为的故意犯罪,其在立法上的特征是,将作为既遂要素的结果规定在罪状中,但不规定对未完成行为的处罚;第三类是不存在犯罪既遂与未遂之分的单纯行为犯,其在立法上的特征是,基本罪状中只是单纯描述犯罪行为,而不规定犯罪的基本结果(但可能规定作为客观可罚条件的结果或者规定加重结果)。②
【收稿日期】2009-04-27
注释:
①我国刑法学通说主张放火罪在刑罚适用上划分犯罪既遂与未遂,并主张以独立燃烧作为放火罪的既遂标准,也是因为没有比较分析中外刑法的差异而对德、日刑法理论的盲目借鉴。
②这里的行为犯不同于我国学界一部分学者使用的行为犯概念。后者局限于从物质性实害结果的角度理解危害结果,并因此将强奸罪、脱逃罪等纳入行为犯概念之内。实际上,强奸罪致生性器结合之结果,脱逃罪致生脱离监管机关控制之结果,皆为立法所欲防止之基本危害结果,故强奸罪、脱逃罪应属于结果犯而非行为犯。
标签:犯罪既遂论文; 法律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犯罪未遂论文; 故意犯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