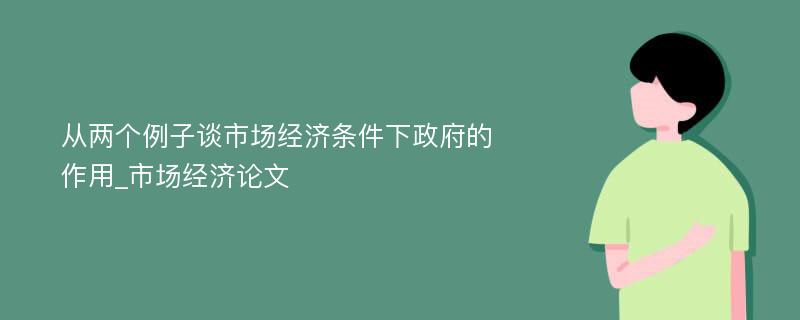
从两个事例谈起——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事例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作用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问题,联系中国的实际,我想先从两个事例谈起。
事例之一,某一大城市原为发展市场交通而经营大批“面的”,深受市民欢迎,不仅因为收费便宜,而且便于一家老小5—6人旅游,虽然稍许挤一点,其乐也融融。可是前些时当局以有碍观瞻为由对“面的”实行淘汰,而代之以本市组装的小轿车,结果市民们纷纷表示不满,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
事例之二,某一经济特区,过去十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商“三来一补”发展起来的。随着其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减退,随着全国兴起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当地有关部门曾一度明令停止接受“三来一补”,顿时该市经济下滑,进出口贸易下降,税收急剧下降,城市失业骤增,不到半年,当局再次重申“请回三来一补”。
在上面两事例中,问题都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者说,政府发挥了不应有的作用。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一般地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起什么作用,市场机制和企业又应起什么作用?二是政府还有中央政府与地方(省、市、县)政府之分,它们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应各起什么作用。我想,弄清楚上述两个问题,对于我们认清当前处于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症结所在,有很大好处;同时,也自然有利于我们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
(二)问题的实质
市场经济,毋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抑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以市场机制作为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由企业充当经济活动的主体,根据市场的供求,合理地组织生产和营销,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赢得最大利润。经济权力,特别是投资决策权,是掌握在企业而不是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作为“政治实体”,因其行为所遵循的多是“非经济原则”,本身并不适宜于掌握投资和营运资本。因此,凡属按经济原则经营的经济事业,均交给企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当然是私人企业)去经营,政府不要干预。然而,市场经济下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必须在自身财政能力所允可的范围内履行一些经济职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职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运用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尽可能防止过大、过频的波动;(2)举办基础设施工程及公用事业,创立一个有效、有利的投资环境;(3)确立各种经济立法及法规,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和正常秩序;(4)实施产业政策,指导或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5)运用收入政策及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及安定。总之,政府依靠自己的财政力量及各种政策,努力建造一个良好的可供千万家企业充分表演其才能的经济大舞台。宏观经济学习惯于把市场的活动譬喻为球赛,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否则导致混乱。我想,这个譬喻是恰当的。
前面引述的两个事例,问题就出在出现这种混乱。本来,汽车的生产与出租车的经营,均属竞争性行业。生产什么汽车或经营什么型号的出租车,完全属于企业决策的事,应由各有关企业在国家的产业政策指导下,根据市场的供求(特别是消费者的需要),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政府所应做的,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指导或引导,改善基础设施(如渠道、公路、高速公路和桥梁等),不应该有违于经济的规律“越俎代疱”替企业决策,用行政手段要求有关企业生产这个而不生产那个,或购买这个而“淘汰”那个,即使被指定“淘汰”的“面的”深受广大城市居民的欢迎也在所不惜。至于特区政府明令拒绝“三来一补”,更是明显的“越俎代疱”。应该说,该特区过去具有的相对优势(廉价劳力、地价)正在消失,有必要开始实行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政府的意愿是好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进行这种结构性调整,应靠市场机制而不应靠“命令”来进行。因为长期从事“三来一补”产业的人员不会轻易退出这个产业的,有的企业与个人甚至自愿自行降低工资也愿在竞争中求生存。政府应该根据产业政策进行指导和宣传,积极开发和引进新产业,组织人员转业培训,另方面帮助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在转移中帮助建立“内引外联”、“前店后厂”的地区间经济联系。至于如何转移、何时转移、建立什么样新联系则完全由企业自己决策。政府不应越俎代疱。当地政府的本意是想通过行政办法来加速产业转移,结果无异“拔苗助长”,适得其反。这是深刻的市场经济一课。
总之,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经济大舞台的设计师和建筑者,但不是演员,演员是企业;政府是球赛中的裁判和巡边员,但不是运动员,运动员是企业。切忌“越俎代疱”。这是一个方面问题。
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问题。政府的重大经济职能之一是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或调控)”。宏观管理的决策权应集中在中央,地方不应分享,所谓“二级调控”的说法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产业政策由中央制订,各地方的产业发展规划或产业政策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依据,应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具体化与补充,不应出现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宏观管理和产业政策的集中性,是市场经济的统一性所要求的。市场经济首先要求有全国统一的市场,不允许地方政府用各自的地方主义政策把统一市场分割开来,强令本省市的企业和居民只能购买本省市生产的产品,而不能购买外地生产的同类产品;或者明令本省市出产的产品(如某些原材料)不许售给外地而只能供给本地。否则,将形成各式各样的保护主义或地区割据。上述第一个事例中强令出租汽车公司用本地生产的轿车来淘汰外地生产的“面的”,就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某种程度的表现。其实,比这更为典型、更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如所谓“茶叶大战”、蚕茧大战之类),在其它地方屡屡发生过。
(三)问题的根源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上述政府“越俎代疱”、地方保护主义的事件而且屡见不鲜呢?当然,“政企不分”是原因,但其根子则在于“政治权力跟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体制。这个两种权力的“结合一体”,正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传统体制已朝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改了不少,但其核心——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结为一体,却未有根本性改变,已越来越成为企业改革以及整个经济改革的攻坚堡桑所在。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府从来都是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的。政治实体的组织形式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政府的经济支柱便是各级财政,财政一向遵循的是“无偿征收”、“无偿拨付”的非经济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实力掌握在企业(私人企业)手中,企业作为经济实体是按“等价有偿”原则行事的。政府依靠自身的财政力量,去履行为维护、发展市场所需要履行的经济职能(前面所述五种职能),而把投资决策、产品生产与营销等经济事务,完全交给私人企业去做,政府不加干预;凡是企业愿干和能够干的事,政府决不插手。在这里,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开,倒是泾渭分明的。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型国家,不仅是政治实体,掌管全国政治权力;而且还是经济实体,拥有全国自然资源、经济命脉和绝大多数企业,掌握着经济权力。传统的集中的计划化体制,更是把政治权力跟经济权力紧紧结为一体。以“非经济的”原则为基础的财政性收支,跟以“等价有偿”的经济原则为基础的企业经营性收支混搅在一起。结果,经济从属于政治,经济活动的“等价有偿”原则被“无偿调拨”的非经济原则(或“财政”原则)所取代;企业经营性收支变成财政性收支;经济手段被行政手段所取代;企业只不过是国家这个大工厂里的一个车间而不是独立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失去了内在经济动力,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产品经济(或“自然经济”)。传统国有经济的种种弊端便由此而滋生。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传统体制朝着市场经济方向改了不少,但其核心——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却未有根本的改变,成为各种矛盾的交叉点。
——正是这个“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使得国有企业几十年来患有“政企结合”形成痼疾,至今企业的投资决策权、人事决策权(特别是企业主要负责人的选拔)等权力仍掌握在政府的有关部门手中,“政企分开”成为今日企业改革的症结之一;
——正是这个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使得中央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不仅是企业和居民户,也有各级政府;“投资饥饿症”患者既有国营企业,更主要的还有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这就给宏观调控大大增加了难度,多次成为宏观失控的突破口;
——正是这个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容易使某些地方政府把它们各自管辖的行政地区看作是自己的“领地”或“食邑”,盲目追求经济扩张,搞“小而全”或“大而全”,并且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
总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已成为经济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症结所在,还是多次投资膨胀,宏观失控的主要根源。解决这一问题已刻不容缓,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二者“分开”。问题是如何将二者“分开”。
(四)途径的探索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由私人经营,经济权力掌握在私人手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分开,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既是政治权力承担者,又是经济权力的承担者,那么,要求将二者“分离”岂不是意味着要摒弃“国有”而主张“私有化”了吗?回答是:“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为其基本特点。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目前全民所有制所采取的“国有制”形式,并不是公有制的最好形式或最后形式,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的恰当形式,因为,在这阶段能代表“全民”的还是“国家”。旧体制的弊端,根源并不在“国有制”本身,而在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便是这种“结合”的产物。“改革”要完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不意味着要根本摒弃社会主义国有制,而是要根本摒弃那种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结合为一体的传统体制,要将那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跟那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彻底分开,以便把以国家为“代理人”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从各级政府的行政羁绊中解脱出来,而完全纳入市场经济的体制与轨道。
所谓把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跟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分开,关键在于将各自的经济基础分开,也就是说,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的行政性收支(财政)跟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的经营性收支(资产收支)分开,而且用不同的组织形成系统进行分渠分流。
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其组织形式就是各级政府。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就跟它对其它企业(私人企业、合作企业、三资企业)一样,都只有经济行政管理职能与权力以及提供各种社会服务:(1)工商行政管理和国有资产登记;(2)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手段进行宏观管理;(3)制订中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给企业投资以指导;(4)筹建公共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水电以及环境保护等);(5)开发高科技及基础研究;(6)开发人力资源,举办教育;(7)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8)举办社会保障事业;(9)建立各项经济法规;(10)运用收入政策及其它手段,调节收入分配。上述种种,归结起来,正是前面所讲的政府五方面经济职能:稳定经济、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执行产业政策、维护市场秩序和确保社会公平与稳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职能就是当好“裁判员”,而且严格在财政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职能,不进行经营性投资活动,也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资活动。
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其组织形式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分别设“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分别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负责,接受其领导及监督,但不受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这些“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指导、监督各种“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营投资公司)的经营活动;而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营投资公司)完全实行企业化经营、主要任务是对企业投资并代表全民“掌管”(或“营运”)国有资产,各企业应对投资公司及其投资负责,并以独立“法人”身份进行自主经营。这样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跟企业之间便形成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贯彻了两权分离的原则。
本来,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只当“裁判员”而不当“运动员”;只有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实体”,而不是拥有经济权力的“经济实体”。这本是有关市场的共识或常识。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当前条件下,还会出现前面所引述的两个“政企”错位的事例呢?很明显,问题主要不在于认识,而在于体制。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依然相结合的体制下,这类事例很难避免,甚至说“理所当然”地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将两种“权力”截然分开。把经济权力尽快从各级政府的行政羁绊中解脱出来,而完全纳入市场经济轨道。
为此,一是需要切实的共识,二是更需要决心。所需要深切的“共识”,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两种权力“分开”的必要性,出自市场经济的要求;(2)这种“分开”的艰巨性,因它涉及各级政府,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改组利益格局;(3)这种“分开”的紧迫性,即两种权力的结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是廉洁或比较廉洁的,而两种权力的结合跟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就容易滋生腐败,这种状态存在时间愈长,被腐蚀的程度将愈趋严重,甚至可能出现“官僚资本”(如北京市的王宝森之流),而且这种腐蚀性的既得利益将使得改革越发难以进行。这就把分开两种权力的紧迫性尖锐地、严重地提到了我们面前。只有在上述三方面的深切的认识基础上,才能形成政府的坚强决心,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讲的“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任何改革,没有这种“政治意愿”是不行的。
实行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分开”,虽很艰难,但可采用不同方式分步推进。现提供一些思路。
思路之一:通过改组、合并方式建立一些跨省市(或地区性)的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所属企业,可以是生产同类或相近产品的水平型分工企业,也可以是分别生产上、中、下游不同产品的垂直型分工企业。这些企业或分布在不同省市,或跨几个不同产业部门,因而它们既不属于所在地的地主政府,也不属于中央某一部门,而属于全国性的国营投资公司或专业投资公司;这类大集团性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不一定由国家独资,可由国家控股并吸收其他投资者,公司经营由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并对股东负责。这样,大型企业集团既跟地方政府“脱钩”,又跟中央部门“脱钩”,自主地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奋斗拼搏。
思路之二:通过对国营企业整理债务,对某些目前负债较重,但有发展前景的国营企业,由当地的、外地的或全国性的国营投资公司替该公司承担债务,但把债权变股权,由投资公司通过扩股而实现控股,并对企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企业,自然与政府“脱钩”。
思路之三:发展资本市场。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扶植发展由国家金融机构严密监控的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投资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是属于全民所有制范畴的。这些机构投资者应积极对国有企业“参股”、“控股”以至改组国有企业。从近期看,这些机构投资者可帮助国有企业从政府的行政羁绊中解脱出来,实现“政企分开”;从长期看,随着这些机构投资者不断壮大,这些机构投资者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控股者)。这时,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将从国家所有制,通过国家控股制形式逐渐过渡到一种以机构投资者所支配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它将是一种比“国有制”(即使经济权力跟政治权力分开之后的“国有制”)更为完善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因为它提供出一种新机制——“投资者主权”,即通过有价证券“分散化”把广大公众个人跟国有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公众来讲,不仅不再是“只看得见而摸得着”的东西,而且有可能对企业行为和表现给予“反馈”。这种“社会所有制”,能更好地使全民的意志与利益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得到贯彻与实现。关于这个问题,须写另一篇文章,不过,一些基本观点,我在1989年一篇文章(“股份制——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刊《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中已有所阐述,这里就不进一步阐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