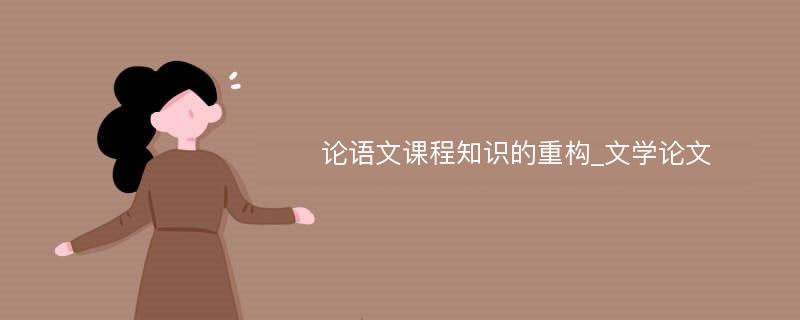
语文课程知识重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语文课程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教育自从遭遇上世纪末的尴尬之后,在本世纪初开始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有意“淡化知识”,由此引发了研究者对语文课程知识存在必要性的论争。课程的核心是内容,内容的元素是知识,可以说,语文课程内容的核心是语文课程知识,语文课程知识支撑着或表现为语文课程内容。在取得语文课程知识需要除旧纳新的共识之后,研究者开始了持续至今的语文课程知识重构运动。本次重构运动出现了与此前几次有所不同的新质,但所建构的知识的合法性、适宜性和时效性问题也应引起注意。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设计语文课程知识建构的未来路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虽然删除了此前课程标准中“不刻意追求知识的系统性”的相关规定,而且在“课程目标”之后增加了“内容”一词,但是依然没有像其他学科的课程标准那样系统地、具体地列出语文课程知识这个语文课程内容的核心,故本文也将论及语文课程标准吸纳新建的语文课程知识的困难及时机问题。 一、对当下语文课程知识重构运动的审视 关于本次语文课程知识重构运动的价值,有人对其估计过高,认为能从根本上解决语文教育低效的问题;有人评价过低,认为建构者只不过是在充当知识搬运工的角色。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重构者所做出的贡献予以客观评价:语文课程知识重构运动的意义十分重大,历史的发展赋予了语文研究者重任,但是任何一项建构活动都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尽善尽美,更何况所有的改革都将是承上启下的“中间物”,因此,对重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要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近几年语文课程知识重构已有的成果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方面。 1.知识的合法性 目前,语文教育研究者所建构的语文课程知识主要来源于国内外文学、语言学、母语教育等领域的著作。只要论著系公开发表,某些观点得到学者共同体的认可,都可以作为知识合法性的依据。然而,就语文课程知识来说,判断其合法性,除以上两点之外,还要注意另外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所选知识是否正确。大概因为现有的语文课程知识过于陈旧,而研究者重构的心情过于急切,于是对国内新出版的某些文学、文艺学著作以及新翻译的国外的相关著作中的理论奉为至宝,觉得其所述什么都好而照单全收。但是,对于这些著作所阐发的是否是真知,并不能单纯由语文教育者这个群体来断定。因为这些知识多出自其他学科专家,所以首先应由其他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对其合法性进行确认,然后由语文学科专家从课程与教学论层面对其合理性进行判断。第二,所选知识是否适合汉语言教育。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支撑其进行的知识也必须是符合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特点的知识,如果简单照搬套用,必然会水土不服、削足适履。现在一般研究者已意识到学习汉字、汉语要用符合汉字、汉语特点的知识。可是,一旦拓展到整篇文章的阅读、写作等,这种母语教育意识就开始弱化。例如,在语文阅读知识重构运动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做法,就是积极引入西方的叙事学理论,视角、虚构、隐含作者、叙述者、叙事时间、话语模式、故事、人物、情节、叙事语法等知识,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基于西方叙事文学总结出来的知识是否可以解读中国固有的文本样式呢?很显然,有时是难以解读的。因此,目前有必要召集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各科专家会商,对各种知识进行判断、筛选,以确保这些知识的合法性。 2.知识的适宜性 如果知识来源合法,那么接着就要考察其在实际教学中是否有用。判断的标准是其在教学过程中和结束后对学生的知、情、意等各方面的发展是否产生正向的效果。知识对于学习者来说,相当于建筑工人所用的支架和工具,没有牢固的支架、合用的工具,就无法施工建设。例如,阅读时如果不具备文章体式方面的知识(其他语文知识)就很难准确地理解文本,因为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及其他应用文体各有不同的体式,只有根据这些不同文本特有的体式方面的知识才能运用相应的理解方式(方法),如不能把小说《孔乙己》当成诗歌来读,不能把诗歌《乡愁》当成剧本来读,因为在《孔乙己》中我们找不到多少意象、意境、节奏、音韵等诗歌解读要关注的重点,在《乡愁》中找不到台词、舞台说明、激烈的矛盾冲突等剧本解读要关注的内容。阅读教学往往就是凭借范文让学生掌握这些知识,然后让学生在以后解读同类体式的文章时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知识(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构成要素),所以这些知识对解读任务的完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以前语文研究界提出的语文知识教学要遵循的三原则相似,语文知识的选择也要遵循“精要”“好懂”“管用”三项原则。不过,目前从其他学科引入的课程知识往往是繁复、难懂、无用的。以叙事学知识为例,其中关于叙述者与隐含读者、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虚构与真实等术语的内涵及两两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文艺理论界尚存分歧,一般语文教师怎能掌握?即便语文教师能掌握,是否有必要将其全部传授给学生?换句话说,学生对叙事学知识的掌握,是否可能、有无必要掌握得如同教师、学科专家及文艺理论专家那样全面而精深?其实用“人称”(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来解释叙事的角度,比“视角”(内部视角、外部视角)更符合“精要”“好懂”“管用”的原则。 3.知识的时效性 知识是生成的,往往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形、转化。以文学为例,盛唐的时候词这类文体还没有出现,当时不可能产生用以解读词的知识;同理,宋代不可能有用以解读散曲的知识,明代不会出现解读白话文的知识。又如,“五四”之后大量翻译文学进入中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相应地为了解读这些不同时代的文本就需要相应的不同的知识。正因为新的文学样式、新的语言现象的发生,才会产生相应的对其进行理解与运用的知识。因此,知识建构的过程是一个除旧纳新的动态生成的过程,永远不可能停止,只能呈现暂时的确定的状态。由此看来,重构语文课程知识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也并非完成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 二、对未来语文课程知识重构路径的设计 语文课程知识的建构程序应该首先组建权威的学术共同体,然后制定明确的选择原则,在对语文课程知识进行初步搜集之后再进行严格审查,并经过教学实验进行检验,将其中一部分吸纳进语文课程标准以确立其合法性。 1.组建权威的学术共同体 目前重构语文课程知识者绝大多数学科背景是语文教育,因为缺乏文学、语言学等背景知识,所以难以对这些知识的合法性、适宜性等做出合理的判断;因为对这些学科的隔膜,也造成语文教育研究者难以通过特定的组织和表述方式使已选用的这些学科知识转化为适合接受的语文课程知识。这和20世纪前期语文教育研究界情形有异。国文独立设科之初,1908年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的我国最早的文选型国文教科书《中学国文读本》和《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者林纾和吴曾祺,就分别著有研究古文作法的著作《春觉斋论文》和《涵芬楼文谈》。《中学国文读本》的“凡例”称:“本书于文中之大节目处特加圈点并附评语以引起读者之注意”;《中学国文教科书》则在“书眉加以细批,题下略述评语”,其题下的评语综述文章的主旨、内容、风格或成就,书眉的细批则关注其局部作法,其“例言”称,评点的目的在“言其命意所在,兼及其经营结构之法”。两位编者分别在这两套教科书中以批语的形式将自己所建构的古文作法知识转化为语文课程知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从事文学、语言学的学者如黎锦熙、陈望道、钱基博、傅东华、罗根泽、胡怀琛、孙俍工、叶圣陶、夏丏尊等积极编写教材,借助教材的编写把文学、语言学等学科建构出来的知识转化为语文课程知识。这首先就基本保证了知识来源的合法性。此外,由于这些学者介入语文学科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语文学科的教学质量,所以他们也研究中小学的教学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保证了知识转化的适宜性。因此,为了保证所重构的语文知识的合法性,首先需要组建权威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应来自古汉语文学、现代汉语文学、翻译文学、语文教育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一流专家,尤其是语言、文学等领域的学者,而且在研究语文教育时应转变立场,从自己学科出发来讨论语文教育,而不是就语文教育来说语文教育。成员之间通力协作,对语言、文学、其他国家母语教育领域里的知识进行判断、选择、转化,从而最终使其成为我国的语文课程知识。 2.制定明确的选择原则 在当前的语文课程知识重构过程中出现的乱象与没有明确的知识选择原则有一定的关系。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说:拿来主义者“要放出眼光,运用脑髓,自己来拿”。这三项基本原则同样可以用作语文课程知识选择的原则。第一,“放出眼光”,就是在选择前要视野开阔,放眼古今中外与语文课程相关的各种知识,尤其是要清理我国历史上的语文课程知识。例如,有人提出对议论文三要素的批判与重构,论者对“论点、论据、论证”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价值性、发现性、说服性”予以替换。之所以要批判传统的“议论文三要素”知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运用时容易导致写作者认为议论文写作就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正确,这就无法支撑驳论文、论辩文等需要证伪的议论文写作。[1]其实我国历史上对议论文的分类很细,写作要求等也不一致,如1920年左右出版的《江苏各校国文成绩精华初集》(邹东泰评选、毕公天校阅、上海扫叶山房与苏州振新书社发行)卷三中的论说文就分成说、问、议三类:“说”是明确单一的论点让写作者去论证,“问”是只提供话题让写作者提炼论点,“议”是同时提供相对、相反的论点让写作者去辨析。现在所说的“议论文三要素”是从1922年陈望道在《作文法讲义》提出论辩文写作要注意论题、证据、证明法式后逐渐形成的。如果能结合20世纪前期当时学生的作文集(以议论文为主)及所出版的大量研究议论文写作的论著来看这个问题,可能就不必急于“重构”而是适当地“回归”即可。第二,“运用脑髓”就是在选择时要判断准确。前述“精要”“好懂”“管用”并不过时,仍应是当下选择语文课程知识的基本标准。“精要”是指要选择对听说读写中某项学习任务的完成起关键作用的知识,或者说是日后形成语文能力的核心要素。“好懂”指这些知识的名称、呈现、组织等均容易被接受,如果这些知识只是以新奇的术语出现,而不能准确界定其内涵,不能普遍运用到日常的语文活动中,那么这些知识(概念、术语)的引入只能是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学习负担)。“管用”,既指够用,又指好用。师生在教学时,容易理解,通过一定的训练便能熟练地迁移运用。课程改革应该使得课程内容简要、明确、适合教学,而不是越改越繁难、含混、远离现实。第三,“自己来拿”,就是要主动选择、转换应用。语文教育研究者要有自觉的课程知识建构意识,主动联合其他学科的专家合力研制语文课程知识。一方面,要看听说读写等方面的知识哪些是匮缺而不够用,哪些是陈旧而不够用;另一方面,要对传统母语教育的库存进行清点,对国外各类知识的清单进行研读,然后加以甄别、选择,看哪些该淘汰,哪些可利用。 3.进行科学的教学实验 已建构出来的新知识,虽然可通过设计教学案例来呈现,或结合课文来阐述,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教学检验、没有被广大教师所接受,这种知识仍有可能是“无用”的。1925年,教育家廖世承在报告道尔顿制实验时说:“自来教育研究,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权威的时期。例如有疑难问题,往往取决于名人学说或在上的意旨。第二个时期为研求的时期。有问题发生时,先多方讨论,然后折中群言,藉以探真相的究竟。第三个时期为实验的时期。先采取各人的意见,定为‘假设’,然后用科学方法,证明假设的确否。是三种方法,虽因性质不同,分为三个时期;实则相互为用,缺一不可。”[2]语文课程知识的建构也是如此,不能仅靠学者躲在书斋里从书本到书本研读,或在会议中交流讨论,而是要进行科学实验,让这些知识走进课堂,通过对教师教、学生学的效果来检测其适宜性。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许多“知识+选文”式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傅东华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夏丏尊和叶圣陶主编的《国文百八课》是其中的代表。1938年,叶圣陶撤退到重庆,在巴蜀学校重拾教鞭时所用的教材就是《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结果发现教学效果很差,他由此想到了该书及《国文百八课》中所选择的知识的适宜性问题。1938年3月8日和5月8日,他在给夏丏尊等人的信中写道:“弟在巴蜀教国文,用东华所编之书,觉所选文章多不配十余龄学生之胃口,而所谓‘习作’者,讲得吃力而学生大半茫然。我们所编的书大体与之相类,其不切实用自可想见。闭门所造之车难合外间之辙,今益信矣。至少初中国文教学还得另起炉灶,重辟途径也。”“‘百八课’题目来时,当抽余暇徐徐为之。我近来觉得书上讲得好是一事,学生是否能容受又是一事。象东华这部书讲得何尝不好,但学生实在消化不来,弟讲得吃力,而他们至多领受十之二三。我们的书大概也是如此而已。”[3]当然,教学效果不好有些并非因为语文课程知识不适宜教学,而是因为教师的教法不当所致。如清末现代语法传入我国以后,不少人认为教授语法可以有利于写作,所以语(词)法开始进入教学,但教学时多是空讲其用法,结果造成教学效果低下。如1911年安徽寿州蒙养学堂四年级国文科教员权骅在描述当时教学情形时称:“近日教国文者,有一种通弊,其授课时,遇然而等字,则告生徒,曰此转词也,遇也矣等字,曰此虚字也,或语助词也。即生徒还讲时,亦曰转词也,语助词也,诘以何为转词,何为语助词,则茫然矣”,他提出应该结合课文讲词性及用法。[4]这也告诉我们,合宜的语文课程知识建构出来之后,还需要研究如何培训教师,让其掌握呈现、解释、传输这些知识的方法。 4.适时吸纳进课程标准 近年来,有人批评语文教育界对文学界、语言学界研究成果的吸纳滞后几十年,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首先,接受这些新的语文课程知识的师范生轮换更替要一个过程。其次,适当滞后也是有必要的。上文提到,知识的新颖不等于科学,在文学、语言学领域里有用的知识不见得在语文教育领域里有用,所以这些新的知识要先让多学科专家判断其科学性,然后再经教育界检验其适宜性,最后才能推广开来。与之相关的是,这几年不少专家批评语文课程标准缺乏以语文课程知识为主体的语文课程内容[5],使得教材编写、教学开展以及测量评价失去了标准。对此,需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课程标准对新建构的课程知识的吸纳有滞后的必要。课程标准之所以没有立即吸纳、规定这些新知识,是因为一方面说明制定者对其可靠性与可行性尚未有定论;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各界对此关注,促进各科专家投入研究。其实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语文课程知识建构运动,都是由从事语言学、文学研究的学者自己或教育学者通过编写教材的形式,将其他学科学者建构的知识转化为语文课程知识的,这些知识并没有在课程标准(教材编写的主要依据)中体现。最为典型的就是上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中期出现了大量由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编写的“知识+选文”型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但是这期间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并没有具体呈现教科书中所编排的语文课程知识。换句话说,就语文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呈现来说,这些教科书并非“照章执行”(课程标准),而是各行其是。然而,这些学者之所以“不等不靠”而主动大量尝试建构这些语文课程知识,是因为在语文独立设科、白话文教学、现代汉语新体系建构等几个关键时期,无法用旧有的知识去支撑(解释)新的教学材料,或者说旧知识无法满足新课程思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需要。不过,适时地将已证明科学、适宜的语文课程知识吸纳进语文课程标准也是有必要的。课程标准作为法律文件,首先具有法律的权威性。课程标准吸纳这些知识,既是对这些知识的科学性、适宜性进行确认的必要工作,便于统一研究者和广大教师的基本认识;也是促进这些知识通过师范生培养、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等多种渠道去推广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课程标准也具有学术性。作为学术性文件,因为其内容涉及多种学术问题,而学术需要不停地进行证明与证伪、批判与反驳,所以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是很自然的事。 综上,就语文课程知识缺失、多变等特点及其建构的艰难程度和时间长度而言,我们认为,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语文课程知识的学术组织或设立“语文课程知识研究院”之类专门的研究机构,促使多学科成员长期投入研究,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