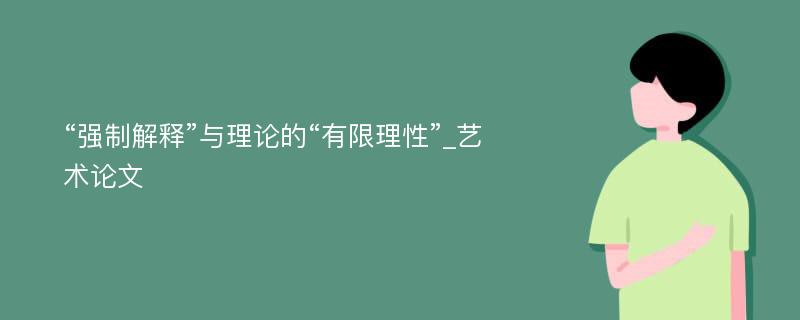
“强制阐释”与理论的“有限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也制造了一系列新的热点话题,大大促进了我国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这是思想解放的硕果,值得充分肯定,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西方文论本身以及我们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译介存在的问题也极为严重。对此,我国学界一直缺乏深入反思。值得关注的是,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有多篇论文和会议发言,专门探讨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负面影响,分析深入细致,见解深刻独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强制阐释”是张江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当代西方文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核心缺陷”的概括。笔者认为,学界有必要就这一提法展开讨论。下面我就围绕这一概念谈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所谓“强制阐释”,用张江的话说就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①。我理解,如果概而言之,就是先有一种理论模式和立场,把文学作品作为证明此一理论合理性与普适性的材料。“强制阐释”所得出的结论,不是对文学作品本身固有意蕴的揭示,而是先在地包含在理论模式与立场之中。这确实是西方文论中存在的一个极为明显而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浸润下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更是如此。这些文化理论都有预设的理论观点和立场,面对任何文学作品,都能以不变应万变,得出符合其理论预设的结论。就拿后殖民主义来说,按照这一理论,“东方”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被西方学者建构起来的话语存在,因此,东方学也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问,而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这种观点有其深刻性与合理性。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得益于工业革命的强力推动,在很多领域都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这也导致了殖民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泛滥。那些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上的优胜者、引领者。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国家与民族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其文化、历史乃至身份都成为发达国家学者们话语建构的对象。“东方”因此也就不是自主的和独立的存在,而是为“西方”的存在而存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揭示的这一情形确实存在,而且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因此,如果从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审视东方主义话语,确实可以发现其殖民主义的内核,其理论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是否一切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言说都可以纳入这种东方主义的框架来阐释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如果承认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的确存在发达与不发达、科学与不科学、文明与不文明、卫生与不卫生、合理与不合理、进步与落后等文化差异,那么,许多以客观的或科学的态度对东方社会与文化的书写,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东方主义话语建构。这里存在的客观性不容置疑。许多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均属此类。其次,有些西方学者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力求找出二者各自的特点,进而说明某些现实问题的形成原因,其关于东方的言说也不能笼统地归之于东方主义,马克斯·韦伯关于儒教与道教的研究就是如此。最后,西方文化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而那些以自身文化困境为反思对象的思想家或学者,为自己的文化寻找出路,把目光投向东方,试图从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中寻求参照与启发,他们关于东方文化的言说往往充满赞誉,对东方文化采取了接受、吸取的态度,目的是借以改造自己的文化。这类言说也不能简单名之为东方主义话语。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郝大为、安乐哲、弗朗索瓦·朱利安等许多西方哲学家关于东方哲学的思考都属于此类。 这就是说,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确实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开启了一个重要的论域,揭示出一系列被遮蔽的问题,其理论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即便如此,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涵盖全部西方语境中关于东方的言说。换言之,后殖民主义理论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超出其适用范围,人为地赋予其普遍有效性,就必然导致谬误。其他各种文化理论也同样如此。实际上,西方学界对那种“理论的越界”现象也一直有所反思,许多学者对理论的“强制阐释”倾向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与反思。后殖民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赛义德就有“理论旅行”之说,涉及在不同语境中出现的“理论越界”问题。②美国艺术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论文集《反对阐释》中,就对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主义与社会批评提出过质疑。她强调面对艺术时的直觉与感受力,反对那种轻视“表面之物”而去挖掘文本背后“真实意义”的艺术阐释。她尖锐地指出:“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象还有另一个世界)。”③人们通过这种阐释来“驯服”艺术作品。显然,在苏珊·桑塔格看来,“阐释”的最大弊端是对艺术品本身不尊重,是一种“强制阐释”,也就是张江所批评的“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 在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出版的第二年,即1967年,美国文论家赫施的《解释的有效性》出版了。这部著作是针对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而发的,也是针对当时在文学批评领域居于主流地位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而发的。在赫施看来,文本有含义与意义之分,前者与作者创作意图直接相关,是不变的,后者则与解释相关,是变化的。他说:“显然,作品对作者来说的意义(Bedeutung)会发生很大变化,而作品的含义(Sinn)却相反地根本不会变。”④因此,赫施强调文学阐释活动应该对作者的意图即文本的固定含义给予充分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赫施的主张也是对那种“强制阐释”倾向的矫正。到了90年代初,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安贝托·艾柯在《过度诠释文本》一文中,在“作者意图”之外提出“文本意图”、“作品意图”以及“标准读者”等概念,旨在对文学阐释的范围予以限定,“试图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保持某种辩证关系”⑤,也表现出对作者与文本固定含义的尊重,这同样是对“强制阐释”或曰“过度阐释”的抵制。 1994年,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出版《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在该书序言中对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提出尖锐批评,为之命名曰“憎恨学派”。他说:“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我把上述这些人都称为‘憎恨学派’的成员。”⑥布鲁姆之所以对“憎恨学派”持憎恨态度,是因为他们都一无例外地试图“颠覆经典”。在布鲁姆看来,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审美价值的作品,代表了人类的崇高品质,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是不容亵渎的。他特别强调了经典的“美学尊严”与“美学权威”,对那种无视作品审美特性的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批评表示强烈不满。他要维护的依然是文学作品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同样是对形形色色的“强制阐释”的否定。 在近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西方文论一直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其“强制阐释”倾向也就显得格外突出,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江的批判较之西方学者的反思更加深入而全面,也更加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其《强制阐释论》一文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四个方面进行的剖析是细密的、说理的,因此也是极有说服力的。难能可贵的是,这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以平等对话的态度对西方文学理论给予的整体性的批判性解读。 西方文学理论与其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是一种具有很强反思性、自我批判性的话语实践,为什么会产生“强制阐释”的问题呢?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追问真相的恒久冲动。所谓“追问真相”,我们用以指称这一思考方式:认为耳目感官所能及的经验世界是不可信的或非根本性的,经验世界背后隐含着的才是真实的和根本性的。西方思想,从其源头古希腊哲学开始,即有强烈的追问真相的冲动,这集中表现在对“本体”的痴迷上。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是本体论,其核心是对人们生活的经验世界抱有深刻的怀疑,认为它们都不过是某种人的感官无法把握的“实体”的派生物或表征。这种实体可能是物质性的,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也可能是精神实体,如柏拉图的“理念”;也可能介于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之间,例如毕达哥拉斯的“数”。总之,在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并证明万事万物之后的“本体”。古希腊哲学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也构成了西方哲学“追问真相”的恒久冲动。这种冲动在中世纪演变为对“上帝”存在方式的追问,近代以来则演变为对主体能力特别是认知能力的追问。无论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是如此。德国古典哲学把这种追问推到极致,每一种哲学都是无所不包的体系,无论是“绝对同一性”还是“绝对精神”,或者还有“意志”,都是作为世界本体而存在的,都是哲学所要追问的“真相”。这种“追问真相”的冲动构造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对这一传统,有人称之为“概念形而上学”,也有人称之为“误置具体性”。19世纪后期,尼采开启了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旨归的现代哲学潮流,但“感性”、“生命”、“存在”、“结构”等一旦成为哲学概念,我们在其中就依稀可见“本体”的影子,追问真相的古老传统并没有断绝。这种追问真相的传统,对人们把握自在的客观世界——宇宙万物、社会构成、经济状况等,是极为有效的,这也就是西方自然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所在。但是,一旦面对精神存在例如文学艺术时,问题就出现了。在两种心灵之间,在实际上是“主体间性”的对话关系中,采用那种对象化的、追问真相式的理论与方法,就只能陷入“强制阐释”的谬误。事实上,从康德、谢林到黑格尔,那些知识渊博、修养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面对文学艺术时,也同样存在“强制阐释”的倾向。 造成“强制阐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构的冲动。尼采开启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与批判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确实动摇了西方古代的本体论追问与近代的理性中心主义。作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最终成果,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两千多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与颠覆。“解构的冲动”亦由此而代替了以往的“追问真相”的冲动。所谓“解构”,是指这一思考方式:面对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个命题或者一个文本,不是按照它们固有的思路给出赞成或否定的意见,而是通过揭示它们在形成过程中与其他诸种关联性因素的关系,打乱其表面的逻辑顺序,从而颠覆其合理性。任何完整、神圣的东西面对“解构”的利刃,都会像被拆解的七宝楼台一样不成片段。用张江的话说,这种“解构的冲动”只告诉人们这不是什么,却不告诉人们这是什么,因此无法构成“知识性遗产”。正因如此,解构的伟大意义在于破解神话,让人们从那些被建构起来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人们自由思想的空间。然而,一旦面对文学艺术,解构冲动就不那么有效了。何以见得?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艺术与宗教一样,需要以“信”为前提。宗教需要信仰,只有在信仰的框架内才能讲道理。文学艺术则需要“信以为真”,就像做游戏,如果不信以为真,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文学批评应更多地尊重体验、感受、想象、联想、直觉等思维方式,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艺术性与审美特性。解构冲动则不管什么艺术品与非艺术品,都用同样的解读策略与方式来面对,只对作品背后的非艺术性因素感兴趣,完全无视文学艺术的独特性,因此必然导致“强制阐释”。 除了西方文论自身的原因之外,对中国学界而言,“强制阐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削足适履式的盲目照搬。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文论时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预设其合理性与先进性,对每一种理论,我们几乎都是当作“灵丹妙药”来看待的,诸如精神分析主义、原型批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等等,每一家、每一派,我们都曾如获至宝般地对待,一旦时髦过了,大家就弃之如敝屣。这些五花八门的批评理论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在接受和使用这些理论时,几乎没有什么批判眼光,往往是囫囵吞枣式地照搬,完全不考虑在西方语境中产生的这些批评理论与我们的文学现实之间的错位现象,因此更加凸显了其固有的“强制阐释”倾向。张江《强制阐释论》的重要价值之一,便在于启发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平等对话的态度对待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既无“我注六经”式的仰视心理,亦无“六经注我”式的随意态度。 面对西方文论存在的“强制阐释”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抵制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呢?当然不是,相反,我们应该了解更多的西方文论,以便更全面、更系统地吸收其有价值的因素,从而丰富和推进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为了避免“强制阐释”,我认为坚持“对话”立场十分重要。这种“对话”立场首要地表现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上。我们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强制阐释”倾向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但对这些理论的“有限合理性”也要给予充分认识。尤其需要注意区分“强制阐释”与“有限合理性”之间的界限。另外,有些来自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在被引进我们的文学研究时,它所引发的可能不是关于文学文本本身的艺术魅力与审美特性的讨论,而是对文学文本蕴含的意识形态、身份政治、政治无意识以及其他文化意蕴的揭示,其结论并非预先包含在理论与方法中,而是对文本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之后得出的合乎逻辑的判断。对此类研究,也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入“强制阐释”之列。对中国学界来说,西方理论既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致人死命的毒药,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恰当的选择与利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选择的标准,则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用中国文学经验印证西方理论的合理性与普适性是毫无意义的,用西方的理论重新命名中国的文学经验也不是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西方理论对我们的真正意义在于:借鉴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视角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发现并解决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学术得以推进和深化。 注释: ①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②参见爱德华·W·赛义德:《理论旅行》,《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第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④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第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⑤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第77-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⑥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14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