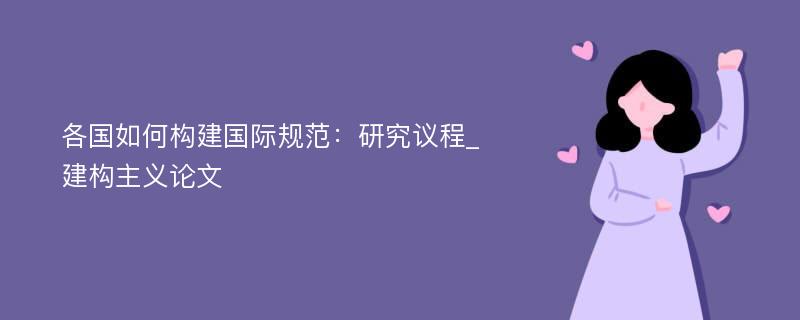
国家何以建构国际规范:一项研究议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程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07-07-19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5-0007-1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理论向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渗透以及建构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更加关注国际规范的研究。但由于结构主义的强大作用,学者们一直努力将建构主义理论建设成一个体系理论,即从研究方法来说,一般将国际规范当作一个自变量处理,观察其变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种研究倾向导致学者们对国际规范自身的生成与变化关注甚少,即国家→国际规范这个维度被研究者们“忘却”了,形成了一个理论“盲点”。本文认为,研究者可能需要从国家属性的变化入手,来探讨国家对国际规范变迁的影响。
一、建构主义国际规范研究的路径与不足
建构主义国际规范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规范的类型、演化机制以及规范对行为体的作用等方面。但是,由于建构主义者致力于将国际规范理论建设成一个体系理论,所以没有特别关注规范演化的起因、过程和机制。本文通过对建构主义国际规范研究成果的分析与批判,阐明两个问题:一是建构主义无法处理在国家属性发生变化时的国际规范演化模式;二是国际规范的体系理论倾向存在逻辑困境。
国际规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结构。温特提出的无政府文化实际上是由一些国际规范构成的。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有时对两者进行混用。比如,他使用“文化规范”这样的说法,并称霍布斯文化为霍布斯规范。① 温特所谓的文化转换涉及国际行为体的共有知识、共享预期以及与此相关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的调整。总之,三种无政府文化转换可以等同于国际体系规范的变迁。
以温特为代表的结构建构主义者亟欲以观念结构代替权力分配来创建一个体系理论。② 温特早年提出的是观念结构与国家之间存在互构关系。③ 既然是互构,行为体在建构结构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就不能被忽视。但是后来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模仿和将建构主义建设成为体系理论的需要,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极大地弱化了行为体建构结构这一维度,而只强调结构对行为体的建构作用。所以互构变成了单向建构,在研究方法上就是将研究层次定在体系层次上,将国际规范(对温特而言即是观念结构)视为自变量,着重考察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建构作用。如果温特欲将建构主义发展成一个体系理论,那他就必须建立一个静态的国家理论,即假定国家的理性和单一性。所以,温特不讨论国家形态的变化问题,而只承认国家的身份会发生变化,而且,国家身份的变化是由国家间互动带来的,因而与国家自身的属性没有任何关系。④
某些建构主义学者曾经注意到,在由不同属性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下,国际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克里斯蒂安·于斯—斯密特发现,古希腊国家之间一度盛行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这与当代国家主要通过国际法或者外交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是不一样的。⑤ 罗德尼·霍尔认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构建了一个封建等级制式的神权政治体系,圣经和教谕成为国际规范的主要来源。这与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国际规范截然不同。⑥ 约翰·拉格发现,在中世纪,欧洲封建国家之间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它们之间并非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且各国“将自身视为一个普世性的共同体的地方性化身”。⑦ 在这种国际体系下,国家之间不是按照主权规范来进行互动。不过,这些学者关注的是国际规范对国家的影响,而没有讨论这些规范的产生与维持和国家类型的演化有何关系。⑧ 换句话说,这些学者只关注在国家属性既定的情况下,国际规范对国家的影响。⑨ 所以,结构建构主义的国际规范研究存在一个理论“盲点”:当国家属性发生变化时,我们不知道国际规范是否会有变化以及如何变化?
另外,拉格还研究了欧洲国际体系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问题。他认为,体系转型的实质是行为体身份的变化,即从封建社会中个人化和分割性的政治权威关系结构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形式。转型的原因是:在中世纪基督教体系中出现了新的区分体系单位的规则,取代了原有的否认主权的构成性规则。在此之后,才出现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只有相互承认主权的构成性规则得以确立之后,才会形成现代国家体系。⑩ 可以看出,拉格认为先有新的主权规范,然后由主权规范建构了不同于中世纪政治实体的主权国家。我们的疑问是:中世纪政治实体之间如何会产生主权规范,即拉格所谓的“新的区分体系单位的规则”?
温特的行为体—结构互构论和内化论给他的无政府文化变迁研究带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逻辑困境。温特认为,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了共有文化,即观念结构,这种观念结构反过来又塑造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进而规定了国家的行为取向。温特同时承认,当国家的身份发生变化之后,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就会发生变化,新的互动方式将颠覆既有观念结构,导致体系文化的改变。温特虽然承认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存在互构关系,但是他更看重的是结构对行为体的作用,而不是相反,这从《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篇章结构及主要内容即可看出。(11)
在讨论无政府文化的变迁时,温特的互构论和内化论有相互矛盾之处。当一种无政府文化,或者说,一种国际规范成为主流规范时,国家应该内化这种文化,并根据这种文化的要求产生相应的身份、利益和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的结构选择。而且温特认为,文化结构的稳定性要高于物质结构的稳定性,因为文化有自我实现、自我加强的性质,所以建构主义的观念结构可能比新现实主义的物质结构更难发生变化。(12) 可是,温特又承认无政府文化确实发生过变化(从霍布斯规范到洛克规范),而且还有继续发生变化之势(从洛克规范到康德文化)。根据其施动者互动造就结构的理论,必定是国家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才导致观念结构的改变;但根据其结构造就了施动者的理论,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施动者的身份、利益和行为模式都是既定的,怎么会发生互动方式的变化?假如在国际规范A背景下,甲、乙两国均按照规范A的要求来互动(内化的结果)。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国际规范发生了变化,由规范A转换为规范B,那么根据施动者造就结构理论,则是甲、乙两国的互动方式发生变化,规范B由此产生;可是,根据结构建构施动者身份理论,在规范A下,甲、乙两国对规范A是高度认同的,它们的身份和行为模式是既定的,那么新的互动方式又如何产生?温特的文化变迁理论在这里陷入了一个逻辑困境。
二、为什么没有单元→结构的能动理论
由于建构主义者出于构建结构理论的需要而假定国家属性不变,导致其无法从国家→国际规范的维度观察国家对国际规范的建构作用。为什么不存在一个关于单元→结构的能动理论呢?这是由于国际关系学界仍然笼罩在结构主义的氛围当中,结构→单元的研究视角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思路。根据这一思路,结构是能动的,而单元是被动的,结构限制了单元的行为。
自1979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以来,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迅速向体系理论发展,一切从行为体出发探讨国际政治的理论均被斥为“还原主义”,也就不能进入主流理论的行列。(13)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尽管存在种种观点上的不一,但其共通之处就是,它们都强调体系层次因素—权力分配结构和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塑造作用,而对于行为体的性质问题却从不考虑。在华尔兹那里,国家被黑箱化、原子化,国家之间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差异被一概抹杀,剩下的只是各个国家实力的差异。华尔兹后来也承认国际体系性质的转变动力来源于单位因素,但他认为只有“政治高手”才能让国家变化起这种作用,言下之意是说,发生这种变化的几率微乎其微。
在现实主义者中,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注意到了国家性质的变化对国际体系性质变化的影响。吉尔平提出,国际体系是由行为体、有规则的互动和控制的形式(包括实力结构、威望、权利与规则)三者构成。(14) 国际体系的变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内部变化,即实力结构的变化;另一种是体系性质的变化,即国际体系无政府性质的类别变化。吉尔平认为,行为体性质变化可以改变国际体系性质,行为体互动变化可以改变国际规则。(15) 然而,吉尔平的研究到此为止,他没有继续深究行为体究竟存在哪些类别,由不同类别构成的国际体系有什么不同。行为体互动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是否与行为体自身的变化有关?
为了跻身主流理论行列,温特也试图将建构主义构建成一个体系理论。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观念本体(实际上就是国际规范)代替了物质本体,观念选择代替了权力选择,体系文化代替了体系的物质权力结构。建构主义者虽然承认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会发生变化,但认为这种变化不是源于国家自身,而是源于国家间的交往实践。体系理论模式对建构主义国际规范研究的影响是:研究者普遍不考虑国家对国际规范的生成作用,而将研究精力集中于国际规范的扩展及其对国家身份和行为的影响。在建构主义者的眼中,国际规范一旦进入内化,就成为一种自在和自为的实体;一旦内化完成,国际规范就“异化”成国家的对立物,也就是说,创造者反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16)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恰好也都是体系理论)都承认国家的变化可以改变国际规范,甚至国际体系的性质,但又都没有指出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如何改变体系性质和国际规范的。迄今为止,我们尚不清楚体系理论家们为什么会对这个理论盲点总是“视而不见”,或许是建构体系理论的要求迫使他们必须放弃从单位层次出发的研究。在结构主义的强大影响力笼罩之下,没有什么学者反其道而行之,认真考虑单元对结构的能动作用。
三、国际规范、国家属性与国内政治
学术界对什么是规范并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规范是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惯例。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将规范定义为:在给定的社会背景下,个体通常的、确定的行为方式。如果个体的行为有违这种方式,则将经常受到惩罚。(17) 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也持这种观点。(18) 二是认为规范是一种存在于行为体之间的共享信念(也可称共享知识或共享预期)。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者通常持这种观点。建构主义学者玛莎·费丽莫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将规范定义为“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与私人拥有的信念不同,规范是共享的和社会的,它们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主体间的。”(19) 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上两种观点的综合,即规范既是一种行为惯例,也是一种共享信念。哲学家戴维·刘易斯对社会惯例的定义是:在一个人口群体P中,当其成员在反复出现的情境S下,作为行为人常规性(regularity)的R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且成为人口P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惯例:(1)每个人都一致遵同 (conform)R;(2)每个人都预计到他人会遵同R;并且 (3)因为S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同R又是S中的一种协调均衡,在他人遵同R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20)
本文持第二种观点,即认为规范是一种共享信念。本文决不否认规范必须通过行为模式得以表现,但更强调规范的背后都必须有一种信念的存在,以使规范为行为体提供了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指南,这就是费丽莫所说的“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21) 规范是对人类行为的非正式约束。面对规范,行为体可以有其它选择,规范只是其具体行为的指南,而不是强制。但社会规范仍能对人类行为起到极大的约束作用,是因为多数人承认规范所体现的共享文化,自愿按照规范的要求行事,而不为少数人因蓄意违反规范而获利的行为所引诱。所以,国际规范就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对什么是适当行为的共同信念,其功能是调节和约束国家间的行为。
从时间角度而言,一个国际规范变迁的完整链条应该包括:旧规范合法性的丧失→新规范的出现→新规范的扩展→新规范的普遍遵守等四个阶段。结构建构主义者更关心的是新规范的出现→扩展→普遍遵守这个链条段,而本文所关心的是旧规范合法性的丧失→新规范的出现这一链条段。合法性的丧失意味着某些自愿遵守旧规范的国家开始不认同旧规范所体现的“适当性逻辑”,这也意味着维持旧规范有效性的“共享信念”开始遭遇信仰危机。当这些自愿不遵守旧规范的国家就行为的合法性达成新的共识之后,新的“适当性逻辑”就产生了,这也意味着新规范的生成。
在行为体如何通过互动建构一个文化结构的问题上,建构主义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逻辑。它没有告诉我们,在既定的无政府文化结构下,互动规则如何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一个新的无政府文化结构的出现。本文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从国家属性入手,探究属性变化对国际规范的影响,因为国家属性不同,则其互动方式各异,这些不一样的互动方式就体现为不同的国际规范。
什么是国家属性,我们如何对其进行观察?本文认为,国家属性是指支撑国家创建或维护国际规范的国内载体在国家层次上的外在表现,这个载体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或是军事的,但不管是哪一类,都必须是物质性的。比如,主权规范是维持近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规范。然而在中世纪,主权规范是不存在的。导致主权规范的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家类型这一属性发生了变化,即由非中央集权式的非领土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式的领土国家。可以看出,支持国家类型变化的国内载体就是政府对领土的控制制度。不同的控制制度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类型,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互动方式,继而导致主权规范的产生。
当然,物质性载体之内也可以“固化”某种政治理念。比如,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签订的《国际联盟条约》中包括了民族自决、限制国家战争权等规范,这些规范的背后体现出了自由主义、特别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阐述的和平联盟的理念。(22) 然而,康德在十八世纪末就写就了《永久和平论》,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个理念才得以实现?原因在于,作为学术理论的自由主义需要首先上升为国家实践,也就是先要有民主国家的出现,然后才能由民主国家这个物质性载体在外交实践中体现自由主义理念。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被固化在民主国家制度当中的政治理念出现的。
建构主义者常常使用身份(identity)这个词,那么身份与国家属性是什么关系?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观念,身份需要他者的认同。但是,身份并非建立在一个纯粹观念的基础之上,它必须有国内政治的载体作为其基础。再以主权规范为例。根据国际法,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领土、政府、人民和国际承认。(23) 但是,主权不能由一个国家自主地获得,而必须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承认,所以从非主权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化就不是自主发生的,而是来自于被认可,是一种被他者赋予身份的过程。(24) 但是,他者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具备主权国家的条件时,仍然需要观察主权的国内物质载体是否存在,即领土、政府和人民。(25)
国家属性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或社会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制度、利益、价值观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被改变了,也就是旧属性转变为新属性。当几个具有相同新属性的国家进行互动时,一种新的互动模式就会出现,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新的国际规范。所以,研究国家属性需要打开国家这个“黑箱”,通过国内政治的变化来透视国家属性的生成与变迁。从研究层次来说,这属于国内政治层次,属于华尔兹所说的“还原主义”研究法。(26)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来源于国内的自变量来解释一个本质上属于结构层次上的因变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属性扮演的是一个中介变量的角色。(27)
四、无政府文化与国家属性
温特未能建立一个关于无政府文化如何发生变化的、强有力的因果逻辑。如果无政府文化是由国际规范所体现,且其变化与国家属性的变化有关,那么,我们应该在无政府文化和国家属性之间建立何种可观察、可验证的联系呢?很遗憾,迄今尚无学者做过此类研究。笔者这里提出一个粗略的研究设想,供有关人士参考。
在国家属性方面,我们似乎可以观察国家类型的变化。前文提及的斯密特、霍尔和拉格都曾注意到,在由前现代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互动规则有其独特之处。不过,他们更关注的是这种独特的互动规则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互动规则独特性的根源。本文认为,前现代国家与近现代国家在国内政治结构上的不同可能是这种互动规则独特性的根源。然而,要想提出一个抽象的国家分类标准却是很有难度。困难来源于我们观察国内政治结构的哪一部分,或者说,如何对国家进行分类。是按社会形态的不同来划分,还是按国家政治权力归属的不同来划分,还是按政府内部权力的分配结构来划分,还是有其他的划分方法?这仍有待研究。
在无政府文化方面,我们需要将抽象的文化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的国际规范。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无政府文化都很难用一个规范体现出来,因此,一种无政府文化应该由具有内部逻辑相似性的一类规范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三种无政府文化可以转换为三类国际规范集。这里的问题是:三类国际规范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哪些规范体现的是敌对关系(霍布斯文化)、哪些规范体现的是对手关系(洛克文化),哪些规范体现的是朋友关系(康德文化)?比如,根据温特的描述,三种无政府文化都涉及到生存、领土完整和武力使用问题,那么有关这三类问题的国际规范可以放入规范集当中。是不是还有其他规范可以纳入其中,这也有待观察。
在理论解释方面,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国家属性与无政府文化之间对应关系的因果逻辑。为什么一些具有属性A的国家会形成敌对关系,从而构建了霍布斯文化;而另一些具有属性B的国家会形成对手关系,从而构建了洛克文化。国家属性与无政府文化之间到底存在何种逻辑关系,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在实证研究方面,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三种无政府文化具体对应的历史时期,然后观察在这些历史时期内,国家的属性是什么,是否与某种无政府文化存在对应关系。最后,我们要探寻国家属性形成的国内政治、经济或社会过程。这其实是最关键的一环。国家本身不会思考、不能行动,能思考、会行动的是组成国家的人,国家属性是人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结果。只有把握国内因素的变化过程,才能把握国家属性变化的方向,继而才能发现无政府文化变化的逻辑。
五、结语
建构主义者出于主、客观原因而假定国家属性不变。从主观上说,这是他们建构体系理论的需要;从客观上说,确定能够引起国际规范变化的国家属性并非易事,而更困难的是寻找构成这种属性的国内政治、经济或社会过程。此外,有些国家属性的变化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例如,国家类型这种属性就存在高度的稳定性。在人类文明史中,国家类型不过发生过数次变化,每次变化的间隔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因此,研究者们将之作为常量处理而不加以考虑确有客观事实的基础。这并不表明研究者们没有认识到国家类型会发生变化,而是他们并不涉足跨国家类型下的国际规范变迁问题。
从国家与国际规范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国际规范规范着国家的行为;另一方面,国家塑造了国际规范,因而也只有国家才能改变国际规范,即国家才是国际规范发生演化的源动力。但是,国家有意改变规范可能是由于其国内因素运作的结果,而不完全是基于先验理性所作出的决策。(28) 所以说,国内因素会在国际层面形成结果,单元也有能动作用,这个世界并不象结构主义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注释:
①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第338页。
②秦亚青认为,当前的主流建构主义出现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以温特、费丽莫为代表的结构建构主义;二是以江忆恩、卡赞斯坦为代表的单位建构主义。本文涉及的建构主义学者均有结构建构主义的理论倾向。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彼得·卡赞斯坦等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译者前言,第13—14页。
③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3( Summer 1987) ,pp.335-370.
④在这一点上,新现实主义对国家的假定更为严格。华尔兹假定国家的形态、身份和利益都是既定的。
⑤Christian Reus-Smit,"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 Autumn,1997) ,pp.555-589.
⑥Rodey Bruce Hall," Moral Authority as a Power Resour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 Autumn,1997) ,pp.591-622.
⑦约翰·拉格:《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⑧拉格是个例外。他在《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一文中着重探讨了中世纪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差异,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华尔兹关于国家功能无差异的理论假定。我们不清楚他对国家形态与国际规范的关系持何种观点。
⑨从研究方法来说,假定国家属性不变也是一种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对于那些研究在国家属性既定情况下的国际规范问题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
⑩约翰·拉格:《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卡赞斯坦等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第274、276页。另可参见John Gerard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1( Winter,1997) ,pp.136-174.
(11)这是秦亚青称其为结构建构主义者的原因。卡赞斯坦等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译者前言,第10页,第13页。
(1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387页。
(1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7页。吉尔平所谓的规律性互动(regular interactions)即是指国际规范,但这与体系控制中的权利与规则一项在概念边界上有重叠之处。
(15)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第41—42页。
(16)“异化”是指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比如,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异化关系。人创造了神,但人却反过来被神所控制。
(17)Robert Axelro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0,No.4( Winter,1986) ,pp.1096-1097.
(18)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第40页。
(19)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20)David Lewis,Convention:A Philosophical Stud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58.
(21)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M〕,第37页。
(22)康德:《永久和平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0—155页。关于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请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86页。
(2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6页。
(24)国际法学者在承认问题上有“宣告说”和“构成说”之争。“宣告说”认为,新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公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构成说”主张,没有现在国家的承认,新国家就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没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构成说”似乎占主导地位,否则的话,现在世界上决不止只有191个国家(联合国成员国),因为任何组织,只要控制了领土、人民,建立了政府,都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并没有自动获得主权国家的身份,比如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关于“宣告说”和“构成说”,请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M〕,第78页。
(25)也有极少数例外情况。比如,巴勒斯坦政府曾经不控制一寸土地,但仍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台湾当局控制了台湾和台湾人民,但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26)关于还原主义,可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第2章。
(27)建构主义者将国际规范归于结构层次上的变量,本文承认这一分类,但这可能引起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反对。他们一般认为国际规范属于国际互动层次。
(28)本文并不否认从先验理性出发对规范的演化进行研究也是一种研究路径。这种路径排除对国内因素对国家进行理性决策的影响。不过,作者仍想指出的是,国家理性的内容和标准是会发生的变化的,这种变化可能来源于国内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变动。
标签:建构主义论文; 文化属性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