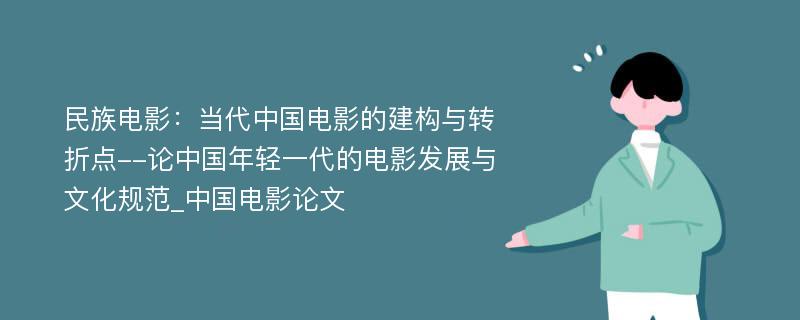
谁的民族电影:当代中国电影的建构与转折——论中国年轻一代的电影发展及其文化语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谁的论文,中国电影论文,中国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1)01-0022-11
新生代电影及其文化语码,是时代语境和民族电影不断发展的产物,呈现当代电影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一个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电影范式改变的进程和固有的制片管理体制之间矛盾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不妨把年轻一代电影导演看做是打破中国电影旧有的国有制片、发行、放映机构垄断格局的青年力量,从此之后,中国电影的投融资模式、发行模式、制作模式,以至民族电影表现形态与多种意义,都开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甚至是看不见的角落里,都有青年电影光辉的种子,时代在等待他们。
年轻一代的电影,按时序发展,可分别被名之以新生代、第六代和后第六代电影。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因为他们也在等待时代,自身存在一定的动态的复杂趋向。从年龄来看,实际上这里的“代”并不是真正的一代人。这些新生代的导演最早一批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后来又有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导演加入进来,现在更有“80后”的青年导演加入进来。从学历身份来看,既有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为代表的学院派创作者,也有美术师、演员、作家、编剧等的加盟。统观年轻一代电影的发展,第六代影片的叙事主题,“基本上涉及了青春期的成长、焦虑、先锋艺术、精神分裂、窥视症、感情多边化及人生残缺等所有城市亚文化层面的内容”,[1]到当下的积极参与电影市场,形成青少年观众受众群,应该说,年轻一代电影并非一个电影流派,它更多成分上是一种重新想象、不断建构的青年电影现象。
说“代”是个好东西,过去我们也有过“代”的成功经验。中国人说“代”准给人以人多势众、势不可当的感觉。我的很多搭档是我的同学,我们年龄差不多,比较了解。然而我觉得电影还是比较个人的东西。我力求与上一代人不一样,也不与周围的人一样,像一点别人的东西就不再是你自己的。[2]
新生代导演与之前以“代”概之的导演群落相比,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其构成相当庞杂,人员来去自由、散漫,但正因如此,它也有活力,不断会有新生力量冒出来,充实到队伍中来。自由化审美、体制外,再加上年轻,成为新生代身份、权力与文化的象征,成为电影青年的象征化的资本。
新生代电影的发轫期,创作主体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摄影系85级、87级学生为主。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85级“全体毕业生”集体署名发表“宣言”,说:中国电影需要一批新的电影制作者,“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是做了五年之久的《黄土地》梦,而今无梦醒之时的《黄土地》已成过去,而我们每个人的脚下却找不到一块坚硬的基石”;“第五代的‘文化感’乡土寓言已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负,屡屡获奖更加重了包袱,使中国人难以弄清楚究竟应如何拍电影。”[3]宣言似乎努力使自己的存在不仅合理、必要,而且获得了一种道德价值。
新生代导演在崛起之初,给人留下青年电影革新者鲜明的视觉形象。英国评论家汤尼·雷恩认为新生代艺术上有不少新的革新[4](P367)。如用纪录片手法进行创作;街头现实主义,使角色在环境中得到很好的定位;即兴创作,演员不使用剧本直接进行表演。这些都成为一个个很重要的革新。
张元的《北京杂种》,作为完全不经官方电影审查通过的“地下”电影的代表作,以独立资金①拍摄完成。影片关注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排挤”的社会边缘群体,有较强的探索性,曾获1993年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评委会奖、1994年新加坡电影节评委会奖、第22届荷兰电影节最有希望导演奖、第6届《中国时报》电影奖大陆电影推荐奖。影片用近乎纪录片的风格记录那个时期“看不到未来却又为未来拼搏着”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借用片中人物卡子的话:“由着性子活的那种人,想怎么着怎么着,都是社会的异己分子。”影片在结构上并置五条情节线,插入六章摇滚乐。“其在叙事上明显受到一批带有后现代风格的新好莱坞电影如《不准掉头》、《低俗小说》等的影响。”[5]雨夜的街头,摇滚乐手卡子劝女友毛毛打掉孩子,没有成功。崔健(由崔健“扮演”自己)和他的乐队经济拮据,自弹自唱自言自语,流转四处。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仿如北京杂种从自身出发,在困惑和迷茫里挥霍着他们的青春,高亢的摇滚是他们心中的愤懑叹息与呐喊。原创摇滚音乐的创作由崔健、窦唯、何勇担纲②。始终贯彻影片的摇滚歌手忘我的演出歌声和画面蕴蓄关于过去的意象、信息和记忆。
这一时期“七君子”的作品《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冬春的日子》、《红豆》(又名《悬恋》)、《自我画像》、《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我毕业了》、《蓝风筝》、《诱僧》和张元的《北京杂种》等,除《蓝风筝》经北影厂审查未予通过外,其余影片均未经过电影局审查而私运出境,参加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对此,广电部电影局及我驻荷兰大使馆与电影节举办方交涉均未果,遂取消原定派中国电影代表团赴电影节的计划。上述情况在日本东京电影节也发生过。为严肃纪律,广电部电影局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电影制片厂、洗印厂和电视台、电视制作单位,在上述影片与有关人员问题未得到处理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协助其拍摄电影、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及影视后期加工等。由于被列入禁拍电影导演的名单,张元几乎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独立制片”的代表,被称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奠基人。
张元此后的影片《东宫西宫》(1996,片长90分钟)改变纪录风格,以戏剧性手法致力于写同性恋。作为“地下”电影的该片以王小波短篇小说《似水柔情》为蓝本,王小波、张元共同编剧。导演张元选择这一题材进行描述和展示,同样充满争议性。片中的阿兰是个同性恋作家。他的故事里有他守寡多年的母亲,有中学时期班里的漂亮女生“公共汽车”,有他的同志恋人,还有“审讯”他的警察小史。“审讯”的一夜,小史和阿兰关系微妙,假面中有真情,同性恋不加掩饰地出现。
故事片《回家过年》是张元被解禁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并未设置相互独立的反题,其回归传统的叙事方式,帮助了他自己对世界的体验。
王小帅本可以很快融入主流,成为正统制片体系中的一员。但他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分到福建电影制片厂,酝酿的几部片子、写的5个剧本都没有通过。既然没办法再等待组织给他机会,也没有第五代导演那样用国家的资金拍片的幸运,那么就自己干。
《冬春的日子》(1993,片长75分钟)这部处女作没有光芒四射,却有着王小帅式的阴冷的调子。此片写一对青年画家冬和春的故事。两人十六岁起一块儿上课、学画、恋爱、留校。“日子年复一年,就像一对老夫老妻,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卖画成了他俩唯一的希望。”后来生活、感情都发生了变化。春办了移民手续出了国,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好,而心碎的冬重新回到了他的画室,继续画不出画,经受双重打击。
《冬春的日子》像张元的《妈妈》一样,以纪录片的方法拍摄虚构类的故事影片,全部由非职业演员出演,资金由自己去筹集,剧本也由自己去创作。冬、春的扮演者是导演的朋友刘晓东和俞虹。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对前卫的画家恋人。影片冷峻地记录了一对青年画家夫妻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困扰。诸多感情、精神上的可爱东西日渐消逝,令人困惑。所以王小帅曾经感叹:拍这部电影,就像写我们自己的日记。[6]虽然题材、人物不同,但在题旨和形式上却与《北京杂种》略微接近。1995年,《冬春的日子》被BBC评为“电影诞生百年百部经典影片”之一,是唯一入选的中国电影。
纪录片的方式普遍胜过了戏剧性的叙事技巧,这是当时的王小帅所深信不疑的。多年以后,王小帅说:“最初我只是想单纯地拍东西,当然,我们没有钱,没法拍好莱坞那种大片,但我们听说过,新浪潮戈达尔那些人拿起机器就拍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要求不一样而已,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不过要拍什么大家也不知道。我们能拍的就周围这几个朋友,找职业演员肯定不行,得支付酬金。我只能拍我身边朋友的故事。我是导演,从导演的角度看,任何人都能演,没有一定要请大牌演员的想法。还有一个想法是,我看了许多当时的中国电影都感觉不对,很假,没有讲出人们真正的心理状况。《冬春的故事》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情节,但至少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当时的状况、生存的状况,真实地讲了出来。一个人心里若有疑问,有困惑,就会很担忧、很焦虑,生活没有意思,这些很普通的心里话,都是非常真实的,也是这部电影想捕捉的感情。谁说电影一定要有戏剧性?这也是一种拍电影的方式,我相信这肯定是对的。”[7](P55)1994年王小帅接着拍了《极度寒冷》,一个关于前卫艺术家齐雷的故事,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齐雷以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去创作所谓“冰葬”的行为艺术,这样的行为艺术有一种被杜撰出来的不可信的语言,充满个人空间的经验,这种语言中充满一种让人关切、探究的精神与话语,有着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
何建军的《邮差》(1995)也是一部极具风格化的作品。它的纪录性,简单而富于灵感,但观看此片,人物那难以压抑的个体叙事的欲望,如何真正融入城市文化的人文关注,还是让人感到惴惴不安。影片由冯远征主演,拘谨内敛的表演致使小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凸显,平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邮差》是何建军在《悬恋》(史可主演)获得鹿特丹电影节奖项以后拍摄的。《邮差》的70万元投资主要就是来自鹿特丹电影节和香港独立电影制作机构的赞助。该片曾获希腊国际电影节金亚历山大奖,第24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金虎奖、影评人奖,以及1995年新加坡电影节GOLD奖,因“违规操作”,影片被禁播映10年。
新生代电影“先锋也保守,边缘又主流”,因此较为复杂。他们的影片特点鲜明,富于前卫意义,但他们的探求与追索,还要走过一段相当长的旅程。从张元的“地下”电影《妈妈》、《北京杂种》、《广场》、《儿子》、《东宫西宫》,胡雪杨的《留守女士》、《湮没的青春》、《牵牛花》,娄烨的《周末情人》、《危情少女》,管虎的《头发乱了》、《都市情话》,到李欣的《谈情说爱》,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阿年的《感光时代》、《城市爱情》,路学长的《长大成人》,何建军的《悬恋》、《邮差》等,大都不够成熟,也缺乏相对统一而明确的美学风格,但其以前卫性姿势和比较客观的视点,描写置身“边缘”的一群边缘人的边缘生活,往往拍得比较精致而流畅,镜语充满才气,色彩鲜明,叙述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倾向,结构散文化,有时还采用了纪录片或MTV手法,显示与众不同的视听风格,呈现出了较强烈的探索性趋向。
显而易见,以怎样一种表达方式或镜语形式,表现有关生命、生存、人性的纯粹事实,是他们所关注的。但是,作品技巧智慧太多,而灵魂血肉太少,太过自恋或主观化,一味表达自我,影响观众面的拓展,是新生代的不足与缺失。张元在开拍新片《回家过年》之前也开始意识到,这部影片,将面对整个中国的观众。[2]颇具纪实风格的这部故事电影,是一部关于爱和宽容的影片,表现的是“极端状态下的人道主义”。它于1999年9月与张艺谋执导的《一个不能少》一起,参加了第56届威尼斯电影节,并获最佳导演特别奖。张元登上领奖台时,说:“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威尼斯电影节首次给中国青年导演颁发最佳导演奖,这是对中国电影的支持。”当时的《人民日报》还专门连续发表了相关消息和报道文章③。在一定意义上,这部影片也可以被视作张元改变“地下导演”的身份成为主流导演的标志。
胡雪杨拍摄的影片《留守女士》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出品④。此片除在美国、埃及等国获得奖项以外,还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也因此,它年轻的导演宣称“89届5个班的同学是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工作者”。这部电影片长90分钟,手法纪实,具有生活流的特点。作为这位青年导演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目光聚焦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改革开放初期“出国潮”带来的“留守者”,描绘了出国热潮中他们的内心矛盾和无解状态。此片中的乃青与嘉东因“留”而“守”,进而相互填补空白,在斯美塔那《我的祖国》旋律中,相同的处境让两个“留守者”走得越发近了。最后,怀了嘉东的孩子的乃青还是决定离开。望着远去的飞机,嘉东独自落泪,置身更加失落与迷茫的感情境地。编导努力运用场面调度和细节处理,揭示人物内心。胡雪杨在此片之后,接着一鼓作气拍摄了《湮没的青春》(1994)、《牵牛花》(1995)等片,尤其是后一部影片,叙事技巧和表现内容值得肯定。
娄烨1994年拍摄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周末情人》,片长98分钟,由福建电影制片厂出品。此片写三角恋情中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故事。在一个雨夜,张弛(王小帅饰)乐队的摇滚秀激情上演的夜晚,阿西(贾宏声饰)刺伤了拉拉,然后倒在了拉拉(王志文饰)的刀下。若干年后,拉拉出狱,乐队成员到场,大家谈笑风生。李欣(马晓晴饰)长发浓妆,呈现出秋天的美丽,旁边还站着一个孩子。电影中李欣的旁白:“我们把自己当成社会上最痛苦的人。后来我才明白,不是社会不了解我们,而是我们不了解社会。”此片于1996年获第45届德国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法斯宾德最佳导演奖”。
《苏州河》(片长:83分钟)拍摄于1999年,由周迅主演,分饰美美、牡丹,先后获第2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第25届巴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奖。影片写送货员马达与自己接送的女孩牡丹日久生情,因为马达卷入绑架牡丹勒索其父的阴谋中,牡丹伤心绝望之际,纵身跳下苏州河,并留下一句话:“我会变成一只美人鱼回来找你的!”五年后,出狱的马达懊悔不迭,思念牡丹,四处寻找,遇到了在一间酒吧扮美人鱼的美美。美美与牡丹长得很像,几经周折,马达终于在美美摄像师男友的帮助下找到了牡丹。最后,马达和牡丹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坠河身亡。而美美也离开了男友,消失前她曾问过男友:“如果我走了,你会和马达一样到处找我吗?”
影片重点表现的一个情节与意象是,污浊的苏州河畔出现了一个金发“美人鱼”,它使得丑陋的现代城市带上了魔法般的魅力色彩。北欧童话般的“美人鱼”,不过是低贱、粗俗的酒吧里的表演女郎而已,它假扮成一条美人鱼,在水池里游泳,目的是赚钱,靠取悦观众“愚人”而已。影片聚焦在城市边缘一个公众视线之外的地方,通过污浊的苏州河边发生的关于谋杀、爱情和双重身份的神秘故事,表现对自然、人性和现代城市环境的重新思考。其中的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和批评性,是比较突出的。
鹿特丹电影节的颁奖词是:“为了影片在电影叙述形式上的实验,以及为影片成功地唤醒那些在现代城市中迷路的人们。”
1994年管虎的《头发乱了》(片长100分钟),原名《脏人》,出品单位为: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此片以编导募集资金制作完成,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名下发行。虽然影片进入了体制内的主流发行渠道,但其将历史变迁融入个人体验之中,表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的一个残酷的青春故事,亦有第六代独立电影人的特色。叶彤考起首都的医学院,回到了儿时的老胡同。胡同还是当年的胡同,朋友们却有了各自的变化,卫东当了片警,卫萍离婚又怀着孩子……叶彤认识了摇滚歌手彭威之后,如何在片警卫东和摇滚歌手彭威间的情感与权力关系间作出选择,让她陷入两难之中。有学者这样评论:“管虎的《头发乱了》等新生代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多与音乐(特别是具有青春反叛意味的摇滚)有一种‘血缘’联系,但这些影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音乐为叙事载体的音乐片,而是一种表达音乐情绪的影片。故事情节往往难以传达他们动荡、迷离斑杂的生存体验,于是他们都借助于音乐的节奏和情绪来表达自我,大量采用超广角镜头,镜头不断地运动甚至可以说是晃动,画面构图动荡倾斜,装饰性的影像、鲜艳的色彩、螺旋似跳动的结构、MTV的节奏、自传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还原他们自己在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相当个人化的希冀、惶惑,无所归依的生存体验。”[10]影片尝试进行有别于传统作品的风格化叙事,全片镜头多达一千多个,蕴蓄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是一种着意表现“都市感觉”的“感觉化”风格影片的代表。
第六代导演被称为“城市的一代”。在第六代这些初出茅庐、虽然稚嫩却极具表现张力的作品中,城市是其当然的叙事主角。“面对城市的推土机,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开始心理失衡,一方面是麦当劳文化的诱惑所引发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则是融入都市过程中的种种挫折导致了他们的失落和迷惘。贾樟柯的《小武》、《站台》和《三峡好人》等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农村与小镇居民面对都市化浪潮时的价值失衡。小武被捕后在大街上抽烟时冷漠的表情,旁观者对于小武仿佛鲁迅笔下‘看客’般的漠然,如此真实。”[11]街道、公园、露天舞台、郊区,流动的人群,作为自然主角的完全自发者及其命运,反空间的街道,成为第六代影片中的重要场景。“场所的对照和它们之间的界线被视为强调素材的意义、甚至确定其意义的主要方式。”[12]某些不起眼的细节表现,去精致化、不化妆、不打灯,影像和画面极具张力,非职业演员,使用方言,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原貌,表现边缘人生,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和真正结构也许是非他们所能知的,但是生活就是生活,影片只能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并倡导的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是早于剧情片的独立制片浪潮。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它的特点,一是脱离官方正统电视或新闻电影制作机构;二是将镜头对准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形态样式和呈现对象区别于主流作品;三是充满人道精神。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江湖》,时间、陈爵的《天安门》,时间、王光利的《我毕业了》,段锦川的《广场》、《八廓南街16号》,蒋越的《天主在西藏》、《彼岸》,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等。这些电影化的纪录片,采用介入式的拍摄风格,有些甚至可以归入人种学电影,所采用的文化、纪实策略,对虚构性的影片,特别是年轻的独立电影制作者,影响也非常大。娄烨拍《苏州河》,纪录影像的纪实方略起了作用,他最初就是从纪录片开始的:“我当时还犹豫,我是不是真的要从纪录片开始,后来我就干脆从纪录片开始,真到苏州河上去拍。实际上就一个人拿着一个超8,拍了一个月,每天在苏州河边溜达,两岸景物非常熟悉,从这个开始进入到故事。”[4](P258)因纪录片的成就,最终参与故事电影的拍摄活动。张元曾拍摄过《广场》、《疯狂英语》,贾樟柯拍摄过《公共场所》,后来拍摄过纪录三峡移民生活状态的《东》,余力为拍摄过《美丽魂魄》。这种互动的情况,在新一代导演那里非常普遍。贾樟柯甚至还形成拍一部剧情电影,拍摄一部纪录片的创作习惯和方式。这样的“一种接近于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手法产生的”电影[13],具有一种自觉介入式的现场感。
高度个性化的介入式特色,与新一代电影家们的现实主义诉求不无关联。执拗追求个性表现,不加掩饰地勇敢选择独立制片,新生牛犊无所畏惧,往往也最有冲击力和爆发力,也颇富电影史的重大意义。事实上,第六代电影最具有创造力,整体性特征最突出、最明显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边缘性的题材选择,青春、死亡、成长、暴力等等主题的关注,成为年轻一代导演艰难生存处境的映射,鲜明区别于新中国以来为国家民族宏大话语代言的电影主题模式。这个时期的第六代电影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具有不可低估的突破意义。它们的出现,扩大了中国电影的取材范围,改变了中国电影创作者惯常的人文情怀、道德立场和情感倾向,呈现了以往中国电影创作中被遮蔽的影像和声音。这个阶段的第六代电影部分仍没有合法身份、脱离官方的制片体系与电影审查制度,且大多是以个人集资或凭借欧洲文化基金会资助完成的低成本故事片。它们的题材类型、制片方式与传播方式与当时中国相对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是相抵牾的。因而尽管第六代电影导演们曾高喊“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尽管不少影片成为中国影史上“看不见的影像”,但观众一旦看了(比如通过盗版VCD),就会因其视觉冲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一直到新世纪,这一时段可以视为年轻一代电影发展与转折的新阶段,也即后第六代电影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出现《小武》、《站台》等影片,虽然贾樟柯1999年受到禁拍处理,让人很难不视这一阶段很多电影创作不是前一时期第六代导演作品的发展。但这一时期,适逢中国电影发展的产业低谷期与探索期,年轻一代电影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和变动,试图扩大自身的艺术文化影响力和商业运作空间。严峻的市场为青年导演们塑造新形象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张扬认为:“我自己觉得‘第六代’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第六代’。以前我认为王小帅、贾樟柯他们是‘第六代’,他们以后还是‘第六代’吗?还是哪一种类型的电影是‘第六代’的?开始可能像‘地下电影’这种比较反叛的、非主流的电影,从学术角度好像归为‘第六代’,那我肯定不属于这一代。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所有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成了‘第六代’,都是‘第六代’。这有什么意义呢?”[14](P388)可见他的电影创作和前一时段的青年导演作品,区别比较大。
如果说第六代尚且存在一些共性,那就是都在不断地蓄积自己的能量,持续为自己找寻一种合适的演变途径。而作为这一阶段的后第六代最为突出的一点也许就是,他们在“极力脱离早期‘SMHM’(Small Movie and Home Movie)的叙事类型与影像传播模式,试图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大银幕作品,以满足导演的‘影院情结’。”[15]与此同时,多个性、多重叙事共存相生局面逐渐形成。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为姜文编导的第一部电影,非常有个性叙事特点。
《阳光灿烂的日子》写一群十来岁的军干子弟在“文革”年月北京城里横冲直撞的故事。由夏雨饰演的马小军,率性、狂妄、自由,开锁、打架无一不能。他道:北京这城市是属于我们的。但也抑制不住青春的渴望、忧郁和躁动。姜文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挣脱伤痕、苦难这些“文革”陈腔,出神入化地叙写他自己关于记忆真实与虚构的认知。“在他的镜头下,‘文革’与浪漫、青春一样。当第五代导演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时,留在北京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反而过着无法无天的半逃学生活。父母、师长、兄弟,谁也顾不上他们,他们的成长有太多放任、恣肆、无政府似的蛮横……姜文对青春的回顾绝不像第五代导演有那么多的沉痛和反省,他的喟叹是对青春的恍惚和留恋,是对青春骤然消失的怅惘,然后更多的是对青春及那个时代的讴歌,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的伤痕南辕北辙。”[16](P86-87)贾樟柯称自己是有“农业背景”的一个导演,即使创作也不愿割断自己跟土地的联系。姜文似乎更愿意将自己的艺术电影(包括最新的2010年有娱乐化倾向的影片《让子弹飞》)和历史联系起来。这是姜文的偏好,也是他的过人之处。现实是升华还是浮华,变得又有多快,都是无关剧情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姜文说:“在《动物凶猛》中我找到了我当时自己认为的一种真实,这种真实还是主观的,我觉得王朔很人性地描写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这种描写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后来有人跟我说,你这个电影是写男孩变男人的过程的。”有关历史的主观与客观以及真实,他在影片中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影片放映后,曾受到质疑。有的批评非常激烈。有一篇批评这样写道:“凡是能够无私无情地复映出历史的真实与是非的郑重记忆,都是深切体验与超越自我的统一的结果。它不仅仅是记忆拥有者亲身经历的沉淀与凝结,而且,更是记忆拥有者良知的勃发、理性的升华,更是记忆拥有者的亲身经历在良知与理性的拷问下,对超越个人遭遇的民族命运与民族记忆的认同和尊重。我想,‘姜文们’应该与广大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一起拷问一下自己的良知与理性,叩问一下民族的命运与民族的记忆。这种拷问与叩问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们’用自己的并非伪造的灿烂记忆,在抹杀、篡改着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在粉饰、伪造着‘文化大革命’那黑暗、荒唐、耻辱的历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种时代大气候的风云一丝一缕也没有飘入‘姜文们’生活的具体环境中,‘姜文们’生活的具体环境完全隔绝于这种时代的大气候。如此说来,《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展示的环境是不够真实、不够典型的。”[17]批评者认为姜文用具体环境的真实描写来抹杀时代氛围,从而完成了对历史真实的歪曲与误读。但影片回首青春岁月,通过叙事使人得到救赎,具有重新代表与发现的意义。阳光而且灿烂,本身就是一种回述与记忆中的感觉,一种绝妙隐喻。关于男性成长的故事,是在大历史之中,也是在一己的记忆、感觉的层面与私人的空间中,真实抒写抑或虚构,有时界线反而不必也无需那么清楚。就像成年马小军的倒叙式的旁白所说:“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北京变得这么快……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又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别不清幻想与真实了。”逝去的一切令人留恋,却也感觉迷离驳杂,充满呓语和未定性,而这无异是对人自身的探索。
姜文的第二部导演作品《鬼子来了》,同样是一部高度个性化的电影。此片时长134分钟,2000年初拍摄完成。2000年5月获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2年获日本每日电影奖评奖最佳外语片大奖,并获夏威夷电影节Nitpick奖。此片未正式公映。
《鬼子来了》原著是尤凤伟的小说《生存》,电影文本改动较大,由军民奋勇抵抗侵略的主题,改变为更复杂、多元的论述与反思。片中的马大三由姜文饰演。马大三憨直、愚昧、胆怯、算计,又很实在,他说:“啥不如吃饭强。”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与村里人合计除掉神秘人(“我”)留下的两个包袱(日本俘虏花屋小三郎和汉奸翻译董汉臣)。然而马大三和村民们因为对杀人害命倍感恐惧,便希望以一种交易方式委托他人来完成这桩棘手的事情。村民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后,认为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两人秘密关押在村里。为活命,董汉臣道:“日本人生气及客气都是一个模样。”“日本人就是这样,爱哭爱唱。”等等。日本俘虏则给村民贺年:“大哥大嫂过年好,我是你的儿,你是我的爷。”不久,鬼子来了,挂甲屯变成了火海屠场。马大三因为去鱼儿娘家接鱼儿而逃过了这一劫。但是眼前的惨相,使马大三打算报仇。在国民党军队接管了日军俘虏之后,他扮成了卖烟的小贩,只身闯进战俘营狂剁猛砍。马大三最后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花屋小三郎的刀下。影片对白很多,影像与画面颇具张力,更重要的是,姜文努力使这部影片加入趣味、戏谑和特定的影调之外,从隐喻的意义上深入讨论人性与国民性问题,极具思想与新美学的光芒。2001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评价影片“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于迄今为止来自于中国的任何一种创作特点,它是一部迎刃而上的电影。”马大三与八婶的对话,村民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木然的面部特写,被卷入事件、惹来灭门横祸的山村,荒诞滑稽的审问俘虏,口沫横飞的讨论,国军“蹩脚”少校(吴大维饰)以不那么标准的国语做的官式训话,马大三与日本俘虏的关系位移,斩首时以手指弹去蚂蚁,挤出一丝笑来的马大三头颅,等等,都以另一种不同的调子侵入了历史本身之中。影片由此重点揭示深刻而复杂的人性议题,反思战争的荒诞与悖谬,从而有助于完整呈现真实的历史,重建想象,重寻国族身份和文化。
影片的结尾,马大三人头落地那一刹那,全片的黑白画面改换为含笑九泉的马大三的视点,观众看到耀眼的红色充满画面。这样的超现实处理,极具表现主义色彩。
这种经验个体本身,在创作者身上是一样强烈的。章明的《巫山云雨》(1996)虽然不能取得《鬼子来了》一样的优异成绩,但所获奖项很多,影响较大,也是一部叙事上别出心裁的电影,比较个性化。此片以三峡搬迁的灾难性隐喻为语境,表现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生活片段,叙事看似松散,情节自成段落,最后回归统一与互联。章明说到他以三个段落结构拍摄这部影片时,说:“我这个电影不是为主流拍的,是为边缘的观众拍的。”“吴刚作为一个警察并不重要,麦强作为一个航道工也不重要,陈青作为一个旅馆服务员也不重要,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这种生命的状态,这唯一是我们强调的。这个身份代表很多人,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光有这样一个题材、一个想法还是很浅的东西。关键是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电影很多年来一直在变的就是一种表达方式。”生活中的混乱、无序和茫然,很难撩起麦强、陈青和警察吴刚几声叹息。影片以平常心呈现他们所过的三种对比反差较大的生活。“几位非职业演员用几乎无表演的表演,说着一口‘地方’普通话,试图再现生存本身的平凡和单调;定点摄影、自然状态下拍摄、同期录音、长镜头等,似乎想还原出生活本身的复杂和丰富。影片借鉴和发展了世界影视史上的纪实传统,追求‘最常态的人物,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甚至最老套的故事,但它却要表现主人公有他们的非凡与动人之处;同样,最节约的用光,最老实的布景,最平板的画面,最枯燥的调度,最低调的表演,最原始的剪接方式,最廉价的服装和最容忍的导演态度,却要搞出最新鲜的影像表现’。”[18](P99)影片形成一种开放而又谨严的情节发展线索和结构,不着痕迹地展示一种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蕴藏其中的人性的共相。
王全安的《月蚀》,写胡小兵在邂逅了“雅南”之后,又复合了一个与“佳娘”的镜像故事,虽然没有采取非常过分的戏剧手法,但是影片中的颓废、殴斗、摇头丸反应、车祸死亡及神秘气息等,还是让人感同身受,产生复杂的心情。王超的《安阳婴儿》以城市为表现对象,写已经下岗、衣食无着的于大刚为了每个月200元的抚养费,收养一个弃婴的故事。他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和弃婴的母亲(妓女)相濡以沫。就在这时,婴儿的生身父亲、患了绝症的黑道老大刘四德在一帮马仔的簇拥下前来寻找婴儿,一场引发命案的夺子战争不可避免。为了描绘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王超把他的摄影机扛到很多地方:“灰暗、肮脏的街道上,促狭的房间里,低级的小饭馆里,还有昏暗的妓院里。”[4](P180)在影片编导看来,这不仅有助于影片叙事与表现,而且,这有可能成为推进电影发展的一种方式。影片成功地实现了充满人性和情感力量的个人化书写。有国外评论者做了这样的肯定:“王超属于年轻的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学派,他以其无可争议的才华描绘了一幅非常细腻的、物欲横流的当代中国城市的肖像。他让人看到城市的状态,有节奏地表现了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的延续和在突然的动荡中断裂了的世界。”[4](P179)⑤
1998年,路学长的处女作《长大成人》(片长108分钟)拍摄完成。此片表现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大成人”的一代人的故事,也是第六代导演影片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影片表达了作者对于成长、时代和生命的感受。《长大成长》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历经3年,修改8次[19](P129)⑥,光进棚补戏就达13次之多,公映后也取得很好的票房,是当年北京市十大卖座影片之一。新生代电影开始解脱于文化禁锢,浮出水面,并尝试将艺术和商业结合,是有意义的。同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着手实施“青年导演希望工程”,以每部180-220万的低成本给青年导演提供拍片机会。次年,“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在北京西山召开,代表着电影主管高层与年青一代影人开始互求默契共谋。这些举措标示着对第六代导演的“招安”。1999年上海的青年导演发起并署名发表过一篇题为《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的文章,以此回应一种主流化的要求,进行集体表白:“新主流电影试图在中心位置的电影、以政府公益为转移的主旋律电影、主流商业电影、处于边缘位置的电影、以电影节为转移的影片、以个性原因为转移的影片之间找到一种合适的演变途径。”这种意见表现出主动的皈依性的电影策略,虽然不能产生登高振臂一呼应者群集的效果,但还是富有标志性意义的。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群体也不断被充实,不断有学院派青年创作者以及其他行业从业者加入到电影创作中。在中国电影产业举步艰难的处境下,2001-2002年间竟然陆续出现二十多部由青年导演制作的电影“处女作”,包括李春波的《女孩不哭》、李继贤的《王首先的夏天》等。这是中国电影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政府行为推动下,借助市场和电影人的力量合谋创造的一个奇迹。从此,一代青年电影导演的构成越来越复杂,队伍也随之膨胀,但“代”的特征却愈发模糊。
青年导演们取得的杰出成就,向业内新人们展示最令人羡慕的生活与成绩。这一时期,电影剧本审查宽松,影片投资渠道宽泛,这给那些怀揣电影梦的青年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成为电影导演”这个在以往想都不要想的事,现在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
此时第六代电影内部分化趋势日益明显,是年轻一代电影的分化期和蜕变期。这一时期的年轻一代电影,体制外和体制内创作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区别。这里面既有依旧坚持自己的电影理想,固执地坚守艺术电影旗帜的,像贾樟柯连续创作“故乡三部曲”:《小武》(1997)、《站台》(2000)、《任逍遥》(2002),胡雪杨自编自导《牵牛花》(1995),刘冰鉴执导《砚床》(1995)、《男男女女》(1999)和《哭泣女人》(2002),姜文创作《鬼子来了》(2000),路学长完成《长大成人》(1995)和《非常夏日》(1999),章明拍摄《巫山云雨》(1996)和《密语拾柒小时》(2000),王小帅拍摄《扁担·姑娘》(1996-1998)、《梦幻田园》(2000)、《十七岁的单车》(2001),娄烨完成《危情少女》(1995)、《苏州河》(1999)和《紫蝴蝶》(2002)。另外还有:王超的《安阳婴儿》(2001),管虎的《西施眼》(2001),刘浩的《陈默与美婷》(2002),王全安的《月蚀》(1999)、《人间消息》(2002),王光利的《横竖横》(2000),唐大年的《都市天堂》(2000),朱文的《海鲜》(2002),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2002),马俪文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2002)。
在一个开放的空间系统里,年轻一代电影也开始在国际重量级电影节上频频亮相并不断折桂⑦。其中,《小武》、《十七岁的单车》在柏林电影节获奖,《过年回家》、《站台》、《海鲜》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鬼子来了》在戛纳电影节获奖。此外,还有王全安、王超、章明、娄烨、王光利等人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各有斩获。截至1999年年底,这类影片已有将近三十部,其中在国际影展上入围的已有二十多部,获得各类奖项(包括几项金奖)的已达十余部,占独立制片总数的将近一半。“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选,再一次作为‘他者’,被用于补足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再一次被作为一幅镜像,用以完满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反抗、公民社会、边缘人的勾勒。”[9](P370)年轻一代电影在国外的影响力开始不断扩大,而这个时候,国内普通的观众却并不是太了解他们和他们的电影。这一时期,年轻一代导演们经过初期的试探和摸索,在阵痛和挣扎中,开始意识到,封闭自我绝非发展方向。同时,过去的因为海外的奖项和资金影响文本的意义领域的情况,正在改变。
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洗澡》贴近生活是其温情隽永的审美化的重要前提。前者写即将步入礼堂的新人周建和夏蓓在欢快地准备着自己的婚事,见父母、置新居、买戒指、登记、婚纱照……后者表现消除父子代沟、弘扬传统人伦美德的主题,努力展示生活本来的面目。影片叙事结构比较独特,注意叙写不同场景、不同故事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细节设计细腻,情节表现流畅,得到观众认同。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以爱情喜剧的形式,表达导演的一种都市体验,节奏欢快,形式活泼,隐含城市电影对市场无意识的全面的还原,也具有极强的观赏性。
年轻一代全面融入了主流电影体系。四十岁以下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占年度国产电影生产总量的一半,《向日葵》、《我们俩》、《独自等待》、《静静的嘛呢石》、《跟头》、《相亲》、《阿司匹林》等等,都是充满特色的影片。以年轻的宁浩(《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刘江(《即日启程》)及张一白(《好奇害死猫》、《将爱》)、管虎(《斗牛》)、陆川(《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徐静蕾(《杜拉拉升职记》)、丁晟(《大兵小将》)等为代表,后第六代这一类新电影人正在逐渐建立起多元化的格局与趋向,票房高企,人气甚旺,受到人们更多瞩目和期待。如果说民族电影的理想主义坚持和顶级电影节的折桂为年轻一代电影拓展了文化和经济的交流空间,那么,青年电影人不断趋向主流、诉求商业,无疑进一步开拓了作为民族电影的代表的传播面和影响力。2010年中国电影产量超过500部,银幕数新增1360块(总数增至6080块),票房更达到创纪录的100亿,上演了民族电影史上最惊心动魄、狂飙突进的一页。而其中,年轻一代的电影已经成为最具标杆意义的活跃力量!
后第六代在重视影片艺术性的同时,深入关注影片的市场作为,向民族电影的主流、商业型靠拢,尝试回应主流观念,跨越艺术与市场的鸿沟,在本体论、叙事方式上讲求结构的巧妙和叙事的流畅,而且不断增加叙事的复杂性,情节桥段愈趋起伏跌宕,娱乐化、戏剧化的影像表达变得更为吸引观众,赢得市场与大众的普遍接纳。年轻一代电影尝试多种手段实现艺术探索与商业经营的联姻,艺术探索更加务实化,内容表达重于形式实验。同时在创作中借鉴商业美学原则和手法,如增强类型意识、积极邀约华人明星参与创作,引进流行文化元素,扩大了影片的文化效应。在民族电影业的多面向发展中,年轻一代的规模优势和主导权,已经日渐明显。
姜文的《让子弹飞》一片幽默、戏仿、荒诞、动作、惊悚等元素融合,人物形象鲜明,演员演技精湛,叙事和台词洗练,结构完整,影像表现独特,内含民间话语和正义的力量。影片上映11天顺利破4亿元,追平2010年年初上映的《阿凡达》最快纪录,而且成为2010至2011年贺岁片票房冠军,创造了近十余年来中国电影业最红火的贺岁档票房最新纪录。这是深具重大象征和转折意义的。
年轻一代电影如此独特而出色,虽然他们现在尚未拥有自己可能得到的一切,然而他们的作品在透过深度交流,帮助他们自己体验世界的同时,也提升和强化了民族电影的文化、产业质素,大大推进了电影产业结构升级,为建构民族电影国际竞争优势,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想象、重新建构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广大的主体性和民族性,为民族电影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注释:
①独立制片的资金来源有:个人集资、国内外公司或电视台投资、国外文化艺术基金或电影节资助等。张元的《妈妈》“募集”到资金20万元,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拍摄资金仅“募集”到10万元人民币,贾樟柯的《小武》花了30万元,主要来自香港的投资,而其《站台》一片则主要为法国资金和日本北野武事务所投资。
②在第六代电影初期的作品中,摇滚乐、先锋美术等元素散布其间。除了这部《北京杂种》之外,在《头发乱了》、《周末情人》、《长大成人》等影片中,摇滚这一烦躁而富有张力的艺术形式同样热力四射,表征他们内心的无方向的焦虑与冲动,彰显他们孤独中的欲望。
③罗晋标:《我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大奖》:“本报威尼斯9月11日电记者罗晋标报道:由张艺谋执导、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一个都不能少》荣获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艺术节最高奖——金狮奖;由张元执导、中国西安电影制片厂和意大利法布里卡制片公司合拍的故事片《过年回家》荣获最佳导演特别奖。”(《人民日报》1999年9月13日)[8]
④“1991年,独具优势与幸运的胡雪杨——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作业、表现文革时代童年记忆的《童年往事》,在美国奥斯卡学生电影节上获奖,他又身为著名戏剧艺术家胡伟民之子,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首先获得了独立执导影片的机会,于1992年推出了他的处女作《留守女士》。”[9](P363)2008年胡雪杨拍摄《上海1976》,内容表现大胆,影像叙事流畅,投资规模较大,几经坎坷,迄未发行。
⑤法国《世界报》2001年5月18日。
⑥据说,此片在电影审查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尽是技术上的枝节问题”。
⑦第六代获得国际电影节各种奖项,最初以独立制作的方式进入西方视野。电影史上的独立制片(indie film)通常指那些缺乏大财团支持下而拍摄的低成本制作电影。从一般意义讲,“独立制片”一词是指好莱坞的哥伦比亚、迪斯尼、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环球或华纳兄弟公司(及他们的新名称)等大片商以外的公司、个人制作的任何故事影片。现在,美国有75%的影片都属于独立制片,不乏优秀之作。仅筹得10万元人民币拍摄而成的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作为独立制作的影片,在获得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虎奖、希腊国际电影节金亚历山大奖以及新加坡电影节朱丽奖后,到他投拍《十七岁单车》时,已获得海外资金300万元。而贾樟柯由当年艰难筹得30万元拍摄《小武》,到2010年,他的西河星汇公司一年便募集到1亿元资金。
标签:中国电影论文; 姜文电影论文; 电影节论文; 第六代导演论文; 阳光灿烂的日子论文; 年轻一代论文; 冬春的日子论文; 电影类型论文; 北京杂种论文; 头发乱了论文; 邮差论文; 广场论文; 悬恋论文; 纪录片论文; 剧情片论文; 伦理电影论文; 青春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