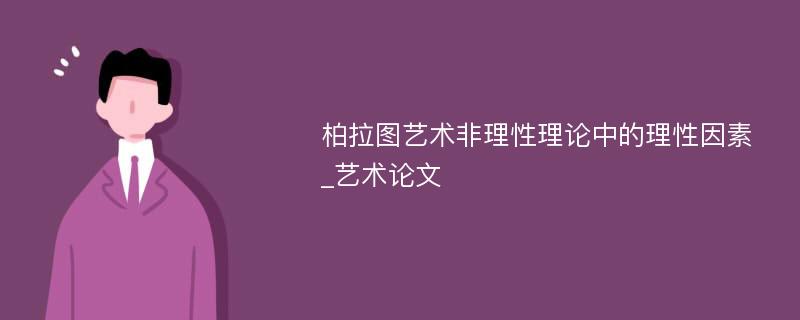
柏拉图艺术非理性界说中的合理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因素论文,艺术论文,界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分析了柏拉图对艺术的非理性界说中的合理因素。指出这些合理因素主要表现在:1.肯定了艺术的非概念性与艺术思维的非抽象性;2.开启了从人性价值的角度评价艺术的先河;3.重视艺术想象与艺术幻觉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柏拉图所说的创作灵感与今天所谓的创作灵感并不同义,实指艺术幻觉现象。
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主要是由“模仿说”、“灵感说”和“效用说”等三个部分构成的,历来屡遭我国学者批判的主要是前两个部分,其原因之一是它们对模仿艺术的本质和创作灵感的特征均作了非理性的界说。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是,勿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原因,批判中难免出现把婴儿与污水一同倒掉的缺憾,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再认识。
先看“模仿说”。柏拉图把艺术分为“模仿的艺术”和“灵感的艺术”两种。也承认模仿艺术是以物象世界为蓝本。不过他认为,这种艺术只能描模事物的外形,不能显现事物的真理。为什么呢?众所周知,柏拉图的哲学本体论把世界分为精神的理念世界与物质的现实世界两部分,并且认为前者是先在的,是本体,因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后者是派生的,是模体、是影子,是不真实的。所以,以现实世界作为模写对象的艺术,就愈加不真实,距离真理(理念)更远。为此,柏拉图认定:包括荷马在内的一切模仿的诗人和艺术家“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1 〕这样的艺术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认识价值可言。另外,柏拉图还认为,模仿艺术以“在行动中的人”为对象,离不开对人性的描写。而人性既有理性的部分,又有非理性的部分,模仿艺术描写的是人性中无理性的部分,如“感伤”“哀怜”“诙谐”“忿恨”等等。因为理性的部分“不易模仿,纵然模仿出来,也不易欣赏”。“模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模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艺术也就不求满足这个理性的部分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模仿。”所以,柏拉图在指责模仿艺术毫无认识价值之外,又加上了一条罪状:损害人的理性而培植和放纵人的情欲。这两点就是柏拉图要把模仿的诗人和艺术家赶出他的“理想国”的根本原因。
柏拉图在对模仿艺术的内容作了如上的界定之后,又进而分析了“模仿所关涉到的那种心理作用”,也就是作家藉以进行模仿的心理机制问题。他的结论是:因为模仿的内容既不关事物的真理,又无涉人性中理性的部分,所以,模仿所据的“那种心理作用也和理智相隔甚远”,只需感觉、知觉、情感等心理因素就足够了。总之,模仿就是“低劣者和低劣者配合,生出的儿女也就只能是低劣者”。这就从模仿的内容和模仿的心理过程两个方面都作了非理性的解释。
再看“灵感说”。柏拉图宣称:“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什么是灵感呢?柏拉图的解释是:因“神力凭附”,使诗人“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很显然,柏拉图的“灵感说”也是非理性的,而且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
在柏拉图的上述观念中,谬误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然而,以往的研究者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其谬论的挞伐上,对其合理的方面则很少顾及,以致妨碍了我们对这位古代哲人文艺思想内层中深邃之处的注意,这是多年来我们的文艺观念重理性而轻感性的必然结果。
柏拉图上述观点中的合理方面在哪里呢?
让我们仍从他的“模仿说”谈起。如上所述,柏拉图执意认为,模仿艺术只能模仿事物的外形与人性中无理性的部分,不能表现事物的真理与人性中理性的部分,所以模仿所据的那种心理作用也距理智甚远。要剥取这些论断中的合理因素,我以为关键是要搞清楚柏拉图所说的“真理”与“理智”的真正含义(所谓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也是指“理智”而言的)。以往的研究之所以存在简单化的缺点,原因之一就是对这两个重要概念仅作了一般性的理解,而缺少深入的辨识。
上面业已提到,柏拉图所说的“真理”就是他视为宇宙本体的“理念”,他之所以认定模仿艺术不能表现“真理”,就是因为它无法模仿“理念”。那么,“理念”又是什么呢?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论道:“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念(朱光潜译为理式——引者注)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念。”例如,“床也好,桌子也好,都有许多个例”,这许多个例“都由两个理念统摄,一个是床的理念,一个是桌的理念”。由此可知,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如果抛开那些唯心主义的解释,实质上就是概括同类事物相同属性及其规律的一般概念,抽象性与普泛性是其重要特征。本来概念是人对客观事物进行逻辑抽象的结果,它必须依赖于客观存在和人的思维活动才能产生,而柏拉图却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2〕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柏拉图所反复强调的模仿艺术同“真理”即“理念”的对立,也就是艺术同抽象的思想概念的对立。如所周知,这种对立确实是存在的。诚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和诗里,从‘理想’开始总是靠不住的,因为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3 〕“精神只有处在情感的形式里对于艺术才是可以掌握的”〔4〕。 别林斯基也一再指出:“在真正诗的作品里,思想不是以教条方式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艺术“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5〕。正因为艺术不表现抽象的概念, 只表现寓于情感、形诸意象、能够感觉和“看见”的思想,所以,认为“艺术即绝对理念的表现”〔6〕的黑格尔, 把他的“理念”同柏拉图的“理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一方面指出“柏拉图式理念的抽象性”〔7〕, 一方面反复申明:他的“理念就是概念与客观存在的统一”〔8〕, 已由“逻辑的理念”转化为“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9〕。 唯其如此,它才有资格成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不管黑格尔的这些论述具有多少唯心论的因素,他关于艺术不表现抽象的概念的思想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这样看来,柏拉图坚持认为模仿艺术不能表现他那个“理念”,如果除去那些唯心的解释〔10〕,仅就艺术规律而论,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它不是正好说明了艺术的非概念性即形象性与情感性的基本特征吗?问题在于柏拉图把艺术的这种特征绝对化了,他只看到了艺术同概念相互对立的一面,却认识不到它们相互统一的一面。黑格尔在论述审美心理功能时说:“在审美时对象对于我们既不能看作思想,也不能作为激发思考的兴趣,成为和知觉不同甚至相对立的东西。所以剩下来的就只有一种可能:对象一般呈现于敏感……‘敏感’一方面涉及存在的直接的外在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涉及存在的内在本质。充满敏感的观照并不很把这两方面分别开来,而是把对立的方面包括在一个方面里,在感性直接观照里同时了解到本质和概念。但是因为这种观照统摄这两方面的性质于尚未分裂的统一体,所以它还不能使概念作为概念而呈现于意识,只能产生一种概念的朦胧预感。”〔11〕黑格尔所说的“敏感”是介乎感觉与思考之间的一种心理功能。因为美是感性形式与理性内容的有机统一,所以用来感受美的心理功能就既不可能是单一的感觉,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思考,而是融二者于一体的“敏感”(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审美直觉),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在进行生动的感性观照的同时,直接了解到对象的内在本质。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对象的审美把握,主要依靠的就是这样的心理功能,所以,其结果虽然一般地不呈现为某种确定的概念,但是却包含着一种“概念的朦胧预感”,也可以称之为“潜概念”,这种“潜概念”是审美主体对对象的内在本质获得审美理解的一种标志。柏拉图由于其“理念论”的错误逻辑所致,对艺术与概念的关系自然不可能达到这样辩证的认识。
还应看到,柏拉图指责模仿艺术只能描写人性中无理性的部分,因而无益于发展人的理性,只能放纵人的情欲,作为一种普遍性结论,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柏拉图不仅把人性中的理性部分与感性部分完全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极力推崇理性,而贬低感性。但是,柏拉图在作出这种错误结论的同时,却开启了从人的角度、从人性价值的角度评价艺术的先河。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艺术的多种社会价值中,人性价值是其根本的首要的价值。正如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契所指出的:“人道,也就是对人性性质的热衷研究,属于每一种文学、每一种艺术的本质。与此紧密相关,每一种好的艺术,每一种好的文学,如果它不仅热衷研究人、研究人的人性性质的真正本质,而且还同时热衷维护人的人性完整,反对一切对这种完整性进行攻击、污辱、歪曲的倾向,那么它们也必定是人道主义的。”〔12〕正确地描写人性,积极地培植和发展与人的本质力量相一致的健全美好的人性,永远是艺术所应担负的首要任务,也是评价艺术的首要尺度。而最先从人性价值的尺度评价艺术的就是柏拉图,虽然他的人性观陷入了理性主义的偏执。
接下来再看柏拉图所说的“理智”一词的涵义。可以肯定,被柏拉图排除于艺术创作心理机制之外的所谓“理智”,就是今天所说的抽象思维。理由何在呢?
其一,如前所述,在柏拉图的“模仿说”中“理智”一词是同“真理”相互对应的一个概念,柏拉图认为模仿的对象不是“真理”,所以模仿所据的那种心理作用不是“理智”。我们通过分析确认,柏拉图所谓的“真理”即“理念”就是统摄同类事物相同属性及其规律的抽象概念,那么,作为获得这种概念的主要心理功能的“理智”,当然就非抽象思维莫属了,因为唯有通过抽象思维才能形成明晰的概念。
其二,在西方美学和文论中,“理智”一词通常多是在抽象思维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如在意大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马佐尼(1548—1598)的《〈神曲〉的辩护》一书中写道:“诗人所要求的诗的逼真在性质上是这样的:它是由诗人们凭自己的意愿来虚构的……这种能力决不能是按照事物本质来形成概念的那种理智的能力。”〔13〕所谓“按照事物本质来形成概念的那种理智的能力”,毫无疑义只能是抽象思维的能力。再如维柯(1668—1744)在《新科学》中论述原始思维的特征时说:“诗的智慧,即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所用为出发点的那种形而上学必然不是理智的、抽象的、象学者们所研究的那种,而是感觉到和想象到的。原始人的形而上学本应如此,因为他们还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14〕很显然,这里讲的与“感觉力”和“想象力”迥异的“理智”或“推理力”,也是指的抽象思维。此类例子在西方美学和文论中是举不胜举的。
当我们明确了柏拉图所说的“理智”即为抽象思维之后,他认为模仿所据的那种心理作用不是“理智”之说的合理之处,也就一目了然了,它反映了人类对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最初的、虽不完善但却是开创性的认识。
对于柏拉图在“灵感说”中讲的诗人若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不能做诗这段话中的“理智”一词,也应作如上的理解,所谓“迷狂”,实指诗人因想象力极度活跃而出现的一种心理幻觉现象。这里同样包含着柏拉图对艺术创作心理特点的可贵认识,说明了诗人只有中止抽象思维活动,放弃对事物的纯概念性思考,而代之以在强烈情感伴随下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幻觉,才能进行成功的艺术创造,写出迷人的作品。无独有偶,法国启蒙主义美学思想的杰出代表狄德罗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者之一席勒都提出过同柏拉图类似的观点。前者在谈及人在什么时候才开始运用想象问题时说:“那是当你以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迫使他想象的时候;也就是说由抽象的、一般的声音转化为比较不抽象的、比较不一般的声音,一直到他获得某一种明显的形象表现,也就是到达理智的最后一个阶段,即理智休息的阶段。到这时候,他成了什么呢?他就成了画家或者诗人。”〔15〕后者在给友人柯纳的信中写道:“你抱怨(此人抱怨自己写不出好的作品——引者注)的原因,在我看,似乎是在于你的理智给你的想象加上了拘束。我要用一个比喻把我的意思说得更具体些。当观念涌进来时,如果理智仿佛就在门口给予他们太严密的检查,这似乎是一种坏事,而且对心灵的创作活动是有害的。孤立地看,一个思想可能显得非常琐细或非常荒诞,但是它可能由于接踵而来的另一个思想而变得重要,或许与其他看来也很离奇的思想连接起来而形成一个十分合目的的系列。……这种神志纷乱的时间的长或短,就是精心的艺术家和作梦的人的区别。”〔16〕狄德罗所说的“理智休息”同柏拉图所说的“失去平常理智”同义;席勒的“神志纷乱”说与柏拉图的“迷狂”说相似。他们俩人也认为:要成为诗人和艺术家或写出好的作品,就必须变抽象思维为艺术想象或艺术幻觉,特别是在进入实际创作过程之后。
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学者们把柏拉图所说的艺术创作灵感同后来人们所说的艺术创作灵感等而视之,这恐怕是一种误解,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两者实际上是有区别的。通常所说的艺术创作灵感是指作家艺术家在体认现实、进行艺术构思乃至艺术传达的过程中,思维活动因受到偶然因素的触发而出现突发性飞跃(顿悟),并引致情感的极端亢奋和想象的高度活跃,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创造性成果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如列夫·托尔斯泰看见一兜鞑靼木长在尘土飞扬的灰色大道帝,它的三个枝丫有两个已被折断,第三枝也耷拉一旁,但依旧顽强地活着,枝叶间开了一朵小花,火红耀眼,这朵小花捍卫自己的生命直到最后一息。在这兜鞑靼木的触发下,早已埋藏在托尔斯泰记忆中的民族英雄哈吉·穆拉特的形象顿时闪射出夺目的光彩,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量的美激起作家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于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中篇小说便很快地写成了。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这种灵感须以直觉(顿悟)为契机才能够产生,确切地说,它是艺术直觉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柏拉图所说的灵感则与此有别,至少它的涵义更宽泛。这从下面这段谈论诵诗人的灵感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苏 请你坦白答复一个问题:每逢你朗诵一些有名的段落——例如俄底修斯闯进他的宫庭,他的妻子的求婚者们认识了他,他把箭放下脚旁;或是阿喀琉斯猛追赫克托耳;或是安德洛马刻,赫卡柏,普里阿摩斯诸人的悲痛之类——当你朗诵那些段落而大受喝采的时候,你是否神智清醒呢?你是否失去自主,陷入迷狂,好象身临诗所说的境界,伊塔刻,特洛亚,或是旁的地方。
伊 你说的顶对,苏格拉底,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就满眼是泪;在朗诵恐怖事迹时,就毛骨悚然,心也跳动。
这儿描述的这种“灵感”状态,显然是不能用上面讲的那种灵感的涵义来解释的,它实则是指创作主体被他的对象深深感动以至迷醉之后出现的一种如临其境、如为其人、主客两忘、虚实不分的艺术幻觉现象。日本心理学家依田新主编的《青年心理学》解释什么是审美体验时说:“所谓体验,是指被自然和艺术所感动,乃至入迷,把全身心都沉浸进去的心理过程。”出现在诵诗人身上的这种艺术幻觉现象就是审美体验的一种极致形态。如果说前面讲的那种以直觉为契机的灵感,在创作中不是经常出现,因而虽然珍贵却不是创作的必需条件的话,而这种艺术幻觉现象在创作中则是必需的和大量存在的。福楼拜告诉人们,他“写书时把自己完全忘去,创造什么人物就过什么人物的生活”〔17〕。陀斯妥也夫斯基说:写作时“我同我的想象,同我亲手塑造的人物共同生活着,好象他们是我的亲人,是实际活着的人,我热爱他们,与他们共欢乐,同悲愁,有时甚至为我的心地单纯的主人公洒下最真诚的眼泪。”〔18〕阿·托尔斯泰强调:“每个作家对自己要写的东西都应达到产生幻觉的地步。”〔19〕我国清代著名戏剧家李渔在论及人物塑造时也指出:“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20〕刘熙载把作家创作时这种如痴如梦的状态,用一个“醉”字来概括:“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21〕可谓精当至极!艺术创作活动是一种审美化的精神活动,具有特殊的心理结构。艺术家进入创作境界,就意味着要把理智活动占优势的日常心理转换为情感、想象、幻觉特别活跃,而又不脱离理性的控制的创作心理,没有这样的心理转换就无法步入艺术创造的殿堂。柏拉图所谓诗人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不能做诗,与其说讲的是灵感(通常所说的那种灵感)问题,还不如说主要讲的是作家创作时的这种心理转换问题更为妥贴,也更有理论价值。柏拉图的失误之处,如若排除掉宗教神秘色彩,单从心理科学的角度上讲,在于因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懂得人类的理性活动并不囿于抽象思维一种形式,而是向其他心理形式扩散。黑格尔早就说过:“人总是在思维着的,即使当他只在直观的时候,他也是在思维”〔22〕。马克思讲的更加明确:“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并不是永远存在于理性形式之中。”〔23〕又说:“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24〕阿恩海姆依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指出:“现在看来,有某些机制,不仅在理性思维水平上进行着,而且还在知觉水平上进行着。因此,类似概念、判断、逻辑、抽象、推理、计算等字眼,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描绘感官的工作。”〔25〕马克思所说的“理性形式”即抽象思维形式或逻辑概念形式。在艺术创造和审美欣赏活动中,理性就是以非自身的形式(感觉、知觉、直觉、情感、想象、无意识等)为其主要的活动方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对于艺术天性来说,理智是消失在才能、创作幻想里面的”〔26〕。
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是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古今中外大凡重要的美学家和文论家很少有人置身于这个问题之外,都力图做出自己的回答。答案不同,便产生了唯理论(如法国古典主义)、非理论(如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感性与理性统一论(黑格尔、别林斯基等)等不同的文艺思潮和流派。柏拉图作为这一理论课题的首要开拓者,尽管他的探索只获得了片面的真理,但仍功不可没,我们应当对其进行细心的、历史的考察,而不应否定一切。
注释:
〔1 〕本文中凡引柏拉图的话均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列宁:《哲学笔记》,第420—421页。
〔3〕〔6〕〔7〕〔8〕〔9〕〔11〕《美学》,第一卷第357 —358、87、27、137、142、166—167页。
〔4〕《美学》,第二卷第304页。
〔5〕《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51—52 页。
〔10〕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神创造的,它只存在于“上界”,生活在“下界”的人无法凭感官直接去认识,只能在神力的作用下用灵魂去回忆。
〔12〕《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第282页。
〔13〕〔14〕《西方文论选》上卷,第200、539—540页。
〔15〕《狄德罗美学论文选》,第162页。
〔16〕转引自弗洛伊德:《释梦》。
〔17〕转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第44页。
〔18〕《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
〔19〕转引自《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20〕《李笠翁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第36页。
〔21〕《艺概·诗概》
〔22〕《小逻辑》第82页。
〔23〕转引自《康德传》,第92页。
〔2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
〔25〕《艺术与视知觉》,第55页。
〔26〕《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442页注释。
标签:艺术论文; 柏拉图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化论文; 抽象思维论文; 人性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