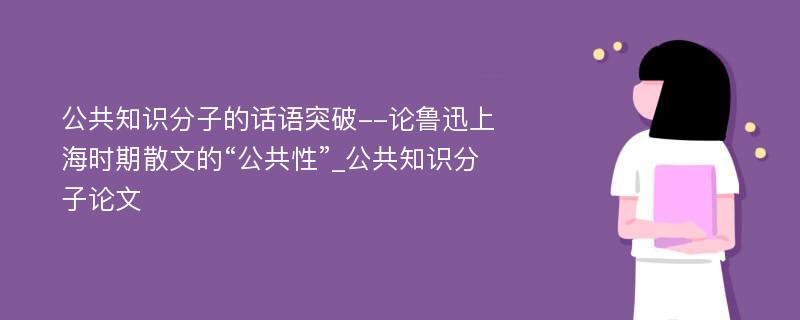
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突围——论上海时期鲁迅杂文的“公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杂文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上海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0)05-0041-05
“上海时期”相对于“北京时期”的杂文写作尽管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上海时期鲁迅的自我定位、心态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导致其杂文写作呈现出新的特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其杂文“公共性”的增强。公共性有时就表现为公共领域,其特征有三:第一,公民成为公众,私人走向公共生活,并坚持独立的话语立场;第二,批判性,私人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第三,通过传播媒介走向公共交往网络,形成一种公共舆论。从这几方面看,鲁迅后期杂文正是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公共舆论。鲁迅在上海彻底告别文化官员和大学教授的身份,成为依附市场的自由撰稿人,取得了自由说话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普及程度更高的上海报刊,及其商业化的运作方式给鲁迅杂文走向公共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其写作成为一种参与社会交往和对话网络的手段,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而非单向的讲述和阐发。
这种公共性如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是鲁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利用杂文和报刊网络对社会上流通的各种话语进行批判的活动,故可称为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所以考察鲁迅后期杂文的公共性就是要对鲁迅杂文进行微观的话语分析,考察杂文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看其如何深入到各种话语的内部,如何拆解、剖析话语背后存在的知识/权力关系。当然,这是个很大议题,本文仅从鲁迅的身份变化及话语策略上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上海时期鲁迅的自我定位与杂文写作
综观鲁迅一生,每一次空间的转换不仅标志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他思想状况的变化。来到上海,对鲁迅而言具有更重要意义:鲁迅由一个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转变为一个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一个亭子间的“市民”。挣脱体制的束缚使其获得了更为充分的自由发言权利,上海发达的商业报刊及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为其提供了驰骋疆场的外部条件。同时,由于政治的原因,30年代上海成为各类知识分子避难或寻梦的场所,当时上海云集的各路知识分子几乎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这也使当时的上海成为各种思想和话语交锋的是非之地,鲁迅的杂文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那么鲁迅面对新的空间,新的生活是如何定位的,这种定位对他的杂文写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鲁迅刚到上海不久,即应邀到各大学进行演讲,其中有两篇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鲁迅称为“知识阶级”)。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他说,“真的知识阶级”“与平民最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1]187-193。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他谈的是文艺和政治,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话题,这里的“文艺家”、“革命文学”等语几乎可以换成“知识阶级”。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中,……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2]113-119
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自我理解,“它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与行为的基本出发点”[3]261。考察鲁迅说的这种“真的知识阶级”,我们发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敏感,能首先感受到社会问题,具有永远的批判性;二是具有独立精神;三是不计利害,敢于公开为民众说话。这种界定其实正具有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
“公共知识分子”是美国的拉塞尔·雅格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而提出的,至今仍是学界热门话题。这里引入这一概念讨论鲁迅的杂文写作也是意在从“公共性”的角度审视鲁迅杂文的写作机制和功能。在一般的理解中,“公共性”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本有之义,不需要在前面加一个限制语,但是,随着大学体制的迅速发展,知识分子也逐渐体制化,公共性也就成了问题。“五四”过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他们关怀公共事务的精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也逐渐褪色,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分化,有的回到书斋,踱进“研究室”;有的进入政府机构成为官员,自身失去了独立的批判力量。鲁迅虽然一直关注社会、批判现实,但他教育部官员和大学教授的身份给他带来很多羁绊,他从北京到厦门、广州再到上海,是一个自我放逐的过程,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和政府体制不断冲突的过程。
在来上海之前,鲁迅曾有“作文和教书势不两立”的言论,但在犹豫之后又认为:“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4]182鲁迅最终选择作文,这里的“作文”,对鲁迅来说就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和安稳的教书生涯相比意味着要融进喧闹的社会生活。“作文和教书势不两立”之论实际上也暴露了鲁迅无法调适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和体制之间的冲突。鲁迅的个性注定他不能做公家人,只能做“流人”,漂流在体制之外。“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最普通的理解,它的本质不仅仅是‘公共性’(‘一位具有公共声音的思想家’),而且这种理解的一部分还是,知识分子相比学者、顾问、职业人士甚或许多政策分析人士而言,会为更加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5]26鲁迅到上海以后,没有了体制的束缚,使其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更加突出,上海繁盛的报刊业和广泛的读者群,使他的杂文通过报刊与论争对手、与读者、与社会形成一个开放的、对话的交往网络,从而更具有公共性。在上海实际上有“两个鲁迅”,一个作为学者的,从事翻译和学术研究,另一个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从事杂文写作。用康德论启蒙时的话来说,前者属于知识的“私下运用”,后者则是知识的“公开运用”[6]24。
二、“人话”:鲁迅后期杂文的话语起点
上海时期鲁迅以一个“市民”的姿态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利用上海发达的报刊网络,深入各种话语的内部,拆解、反思、抨击这些话语背后存在的压迫和谬误。他的杂文写作通常是以某报刊的报道开始的,到“自由谈”时期达到高峰,在他逝世前还写了一系列的“立此存照”,完全用新闻报道组成,也可见鲁迅对这种方式的钟爱。鲁迅后期杂文,虽然是最终指向现实批判,但首先是关于“话语”的批判,而这种关于“话语的话语”总是从对“人话”的审视开始的。
《伪自由书》中有一篇《人话》的杂文,历来因为里面讲述了一则“柿饼”的笑话而广为流传,但在笔者看来还有更深的意义:童话《小约翰》里,小约翰听两种菌类争论,在旁说道:“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说:“这是人话啊。”另一则引法布尔的《昆虫记》中以人的角度去形容鸟粪蜘蛛和残食交配对象的昆虫。鲁迅说:“这未免太说了人话。”然后鲁迅将此引申到人类,“人话之中,又有各种: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所以鲁迅提醒要分清讲的是“哪一种人话”。田间劳作的农妇想象皇后娘娘起床后情景是真诚的,一点不好笑,但经高等华人讲述后就成了笑话,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鲁迅在这里实际上区分了真的“人话”和假的“人话”,褒义上的和反语意义上的。他是呼吁讲真的“人话”的。比如下等华人自己的表述是真的“人话”,尽管幼稚,粗俗,但却真诚,可他们的声音却被“上等华人”代为讲述,被描写,真的“人话”被假的“人话”肆意的扭曲了。
在另一篇文章《立此存照·七》中再次抨击在儿童专刊上发文“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一半”的人不讲“人话”。因为他看出这里面潜藏着主奴关系,“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不是早经废止了么?”这种主奴意识不除,“我们的子孙”就将仍然沦于奴隶,“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也是极大的”,所以鲁迅最后说:“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其实这里鲁迅关注的重心不在杀哪国人孰轻孰重的问题,而在于该文所隐藏的话语关系。尤其是这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大朋友”对“小朋友”的教育、宣讲时所显示的知识/权力的悖谬。
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人话”几乎可以作为鲁迅后期杂文的一个核心范畴,他话语批判的基点就是“人话”。“人话”,首先意味着“常识”,而在30年代的上海租界,欲望、名利的纠缠使许多知识分子忘记了常识。比如,在《止哭文学》中,鲁迅引用了王慈的文章《提倡辣椒救国》,王文说北方用辣椒可止小儿哭,鲁迅讽刺道,“这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倘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的‘民族’了”,直指该作者不顾常识的胡说。“人话”,其次是对话语背后的“隐语”进行解码。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又不仅仅是谈常识,而是进一步指出:“然而我们也很分明的看见了这种文学的企图,是在给人辣而不死,‘制止他讨厌的哭声’,静候着拔都元帅。”“不过,这是无效的,远不如哭则‘格杀勿论’的灵验。”[7]73所谓“提倡辣椒救国”无异于叫被压迫和被侵略的人民不要抗议和呼喊,那样会误了党国的周密安排,这背后正是御用文人的“帮忙和帮闲”策略。显然,在揭示“常识”的背后仍然是权力话语的批判。翻阅后期的杂文,鲁迅大多从小事入手,从日常物理入手,但又远不止于此,而是意在穿透各种意识形态编织的权力网络,揭示各种语言暴力得以流行的文化机制。
再次,“人话”,还体现出鲁迅对“立人”思想的坚持,后期鲁迅关注的根本仍然是人自身的解放,仍然是“国民之自觉至,个性张”,“人国”[8]58。不过和前期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扩展了他的视野,使他看到了阶级的、大众的解放,尤其是“下等华人”的解放,但这是以“个人”为前提的。他晚年称赞苏联,正是因为他以为那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9]426,关注的重点仍是“支配自己命运”的个人。所以鲁迅后期杂文随处可见各种阶层划分法,如高等华人和下等华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等。
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说:“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9]460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不仅为现实中的被压迫者呼喊,而且更多的是用杂文解剖话语中存在的压迫和被压迫、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不仅反抗显在的压迫,而且反抗一种隐性的“有理的压迫”。《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一文提及报载公告:“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鲁迅就说“有理的不在此例”,如:“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真诚合作”,即应该顺从资本家之剥削和压迫。“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这种“有理”实质是一种“知识”的压迫,知识在背后提供压迫的合法性,让你不觉得这是压迫。《同意与解释》一文中鲁迅说:“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依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这种话语背后就是为奴役和压迫寻找借口,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
不讲“人话”的压迫者就是编造一套,或利用他们的“文化资本”来使被压迫者的“人话”发不出声音来,甚至是使他们认为“天经地义”。在《伪自由书·后记》里,鲁迅对当时《大晚报》报道新闻时用猎奇语言“以耸动低级读者的眼目”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指出:“杨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7]153在《准风月谈·前记》里又说:“假如出‘学而时习之’的试题让遗少和车夫做,绝对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胡说,但这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7]189鲁迅的后期杂文正是表现为“立人话语”的突围,表现为对上海各类知识分子的话语祛魅,他的目的就是要撕开这些假面,打破“非人话语”的“一统天下”。
三、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
由“人话”范畴出发,重新审视鲁迅后期杂文,呈现给我们的主体图景就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在鲁迅后期批判的谱系中,他总是对待国人要比外国人严苛,而国人中,对待上等华人要比下等华人严苛,而在上等华人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批判又比其他人更严苛。“生着人头不讲人话”的“大朋友”中,主要是知识分子。这里不仅有欧美派知识分子,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文人,更有殖民地情境下的“商定文豪”,还有狂热的、“唯我最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话语批判中,鲁迅始终关注的是人的自由和正义,凡是与此相违背的奴性、霸气等“非人话语”都是他大加讨伐的对象。
“新月派”在20世纪20-30年代一度聚集了中国主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不可否认,“新月派”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同样是参与公共领域、关心民族国家建设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一些理念和鲁迅的主张也多有相通之处。但是,在与“新月派”的论争中,鲁迅关注的是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话语方式,并不就有些具体问题展开辩论(除了“硬译”问题外)。以致于梁实秋说鲁迅只会“说俏皮话”,没有“严正”的批评态度[10]。比如,鲁迅的《卢梭与胃口》并不探讨卢梭的女子教育如何,而只抨击梁实秋的“等级论”的谬误:“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11]553也就是说,鲁迅所揭示的是梁实秋将压迫、等级制合理化的谬误。同样,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批评辨》等文中谈到的人性论,虽然从文艺批评角度来说颇有说服力,但是在社会政治层面,要人们安于秩序,反对民众的反抗诉求,这和鲁迅在《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一文中提到的“有理的压迫”有何区别呢?另外,《现今新文学的概观》和《大家降一级试试看》中鲁迅指出新月派的“话语霸权”:“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壁德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的学者。”[9]547“梁实秋有白壁德,徐志摩有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9]134这句话几乎成了鲁迅形容新月派的“口头禅”,这背后,鲁迅抨击的是只挂招牌而不和中国实际结合的狂妄心态。
上海的都市空间里还盛产“商定文豪”、“洋场恶少”及“西崽”。鲁迅后期杂文进入公共领域一个很大的批判内容是指向殖民地都市文化的,但这种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12]。这从鲁迅的这些命名即可看出。“商定文豪”的“根子在卖钱”,“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且投机性强,“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7]377。这本质上与文学无关。《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文床秋梦》等刺邵洵美的一批杂文,抛开具体的争端,鲁迅讨伐的实质也是这种“商定”现象。而鲁迅与施蛰存的“庄子与文选”之争则是“五四青年必读书”争论的一次重演,鲁迅对披着“新青年”外衣的旧道德格外的警惕,所以对那些“新青年”仍劝人读《庄子》、《文选》、玩古式信封等玩意儿非常不满。他说,他们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言下之意,仍是“五四”时反传统立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11]12反复古,可以说是鲁迅“立人”路径之一,且终生未变。
作为左翼队伍中的一员,鲁迅对自身的文化处境也有深刻的反思。面对革命话语,鲁迅也表现出“立人话语”的突围。这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第二阶段是与左联决裂时期。在第一阶段之后鲁迅和论争对手结成一条战线,也开始提倡“革命文学”(是他所理解的那种革命文学),但从其立人话语角度看,其反抗立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创造社、太阳社以一种政治思维给鲁迅定性、划线,强调其落伍和反动。而鲁迅虽然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积极意义,但他首先主张任何理论都要正视现实,尤其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他批评道:“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9]84“其实革命并非是教人死的而是教人活的。”[9]297鲁迅又指出创造社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流氓”是鲁迅后期杂文中一个重要“意象”,这里有鲁迅对上海殖民地文化的一种真切体察和感受,也有对中国历史(“人史”)深刻的认识。
第二阶段的话语突围表现在杂文形态上,主要限于《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半夏小集》,其它大量的文字都是在私人信件中。鲁迅的“横站”,仍然是以人的个性自由,思想的独立为标准去反抗革命话语中的霸权的:“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一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13]538他说周扬等人是“借革命以营私”,“自有一伙,狼狈为奸”[14]426,“群仙大布围剿阵”[14]416。在鲁迅的书信中大量出现“工头”、“做苦工”,“奴隶”词汇,说明鲁迅同指责其他社会现象中奴役关系一样正视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奴役和压迫,他要冲破这“新的奴役”的罗网。左联解散,他说:“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14]365“别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14]349鲁迅“立人”优先的个性自由思想使他注定不能以团体的面目进入公共领域,他只能以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去坚持公共性原则,保持话语的独立性,批判性。
在这种双重挣扎着“横站”的话语突围中,鲁迅始终坚持“人的话语”,反对一切奴役、反对一切压迫,鲁迅的写作是一种抵抗的姿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鲁迅的每一个话语就是一个实践,他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化实践。他在坚持着什么,他在攻击着什么,他在张扬着什么,他是用实践去证明。[15]”显然,鲁迅的话语突围对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领域问题也有积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9-10-20
注释:
①可参见忻平的统计,见《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