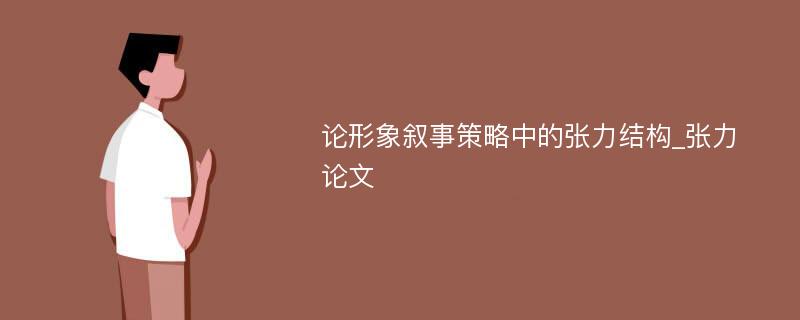
论影像叙事策略中的张力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像论文,策略论文,结构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02)04-0135-07
在许多电影批评家那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被认为是次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 是它们的本义是明确无误的,而倍受赞赏的艺术片则是吁请观众参与猜谜,表达了对20 世纪初讲究歧义性的艺术形式的感恩之情。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卡西尔宣称:“一切 时代的伟大艺术都来自于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注:卡西尔《人论》,第207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毋庸质疑,两种对立力量的渗透过程便是张力的表现过程, “对立、冲突的两极在撕扯、抵牾、拉伸中造成文本内部的某种紧张,并通过悖论式的 逻辑达成某种出人意料的语义或意境。”(注:王思淼《当代小说的张力叙事》,《文 学评论》2002年第2期)我们看到,当影像系统被纳入到语义学视野后,它提出了一系列 非常复杂的问题。与其他艺术一样,它通过类比式关系把能指与所指联系起来,完成语 义的传达。而与其他艺术不同的是,在所指语义内涵的层次之间,在能指与所指充满无 限可能的关系之间,在能指各种因素(形状、色彩、声音、形体语言、文字语言等等)之 间,充满了更为复杂的张力。这就使得影像叙事出现了一种自由(调度因素的主观自由) 与限制(叙事抒情的客观表达)的双重性。本文将以近来电影为例,从分析影像叙事的策 略出发,探讨张力在影像叙事中的重要作用。
(一)叙事的透明与反讽策略
说起影视的叙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活动的影像。事实上,在观赏影视作品时,观众 往往主动地放弃自我意识,听任影像的自由活动。这一“催眠”现象的出现与影像的形 色音的整体性特征密不可分,即是说,由于影像的这种整体性与现实的整体性相对应, 因此在观众的意义想象中,两者形成了一种“同语反复”关系,这便是影像叙事的“透 明”特征。R·巴尔特认为:“语言讯息可以轻而易举地同另外两者(被编码的肖似图像 与非编码的肖似图象讯息)区分开来,但是,既然后两者共用了同一种(肖似图像的)实质,又怎么合理地区分呢?可以肯定的是:两种肖似图像讯息之间的区别并非自发地产 生于通常水平的读解:影像的观看者在同一时刻接受了感觉的讯息和文化讯息”,但他 又认为,这种区分在实践操作层面显得十分必要。(注:R·巴尔特《影像的修辞学》, 《世界电影》1997年第4期)这里,观众接受的同时性与实际操作的异时性实则隐藏着两 种不同的叙事策略:透明与反讽。
透明策略带来了叙事的流畅:将叙事动作明晰呈现在每位观众的面前。这在电视剧中 表现得尤为突出,它的日常审美特性必然要求表达的清晰、叙事的流畅。而叙事的流畅 首先要求运用观众的感知、认知以及潜意识等反映,并以假想的在场观众注意力为标准 ,运用恰当的镜头调度、场景切换进行叙事传达。可以说,它要求每个新的镜头都必须 满足真实生活中把注意力转移的正常心理机制的要求。我们来看一看《十七岁的单车》 是怎样进行透明叙事的。当片头字幕结束时,画外音出现:“从今天起,你们便是公司 的员工了”,与之相对应的是。镜头从崭新的成行的自行车慢慢摇起,停在同样是排列 成行的员工身上;当画外音说到维护公司形象时,镜头先后两个特写,统一的背包,公 司的标志。然后背对着观众的公司老板出现,来回走动训话:“为什么要配备高级山地 车”,画面相继出现车灯与车把的特写,而当公司老板说到要背熟北京地图,一个推镜 头推向墙上的北京地图。在这个段落中,画面解释人物语言,回答着观众的心里疑惑, 不仅将信息清楚地传达出来,而且由于有了语言的铺垫,镜头切换自然流畅,达到了透 明清澈的语义效果。
与影像透明策略背道而驰的便是反讽策略了。它追求的恰恰是一种态度不明、叙事不 清、有意将观者与影片、与生活拉开距离的艺术效果。如果说前者表现出修辞的“可靠 性”、文本与现象的“同一性”,那么后者则体现出修辞的“不可靠性”,文本与现象 、文本与艺术家的“含糊性”。当我们将反讽策略放在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时,便可以发现,它实质上体现出艺术的进步、艺术家的高度自由与现代精神。在语义 流转渠道中,就艺术家与作品而言,可以是“透明”式的正面,所述之言正是艺术家之 言(如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第三、四代导演众多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是“反讽”式的反 面,所述之言恰恰是戏谑之言,戏仿之言(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 以及闻一多的诗歌《死水》等);就艺术作品与现实而言,可以是叙事流畅的真实,简 单的指认关系,同语反复的关系,也可以是变异的,夸张的,主观化的关系(如第五代 导演的作品);就艺术作品与观众的关系而言,可以是传统的宣喻关系,教化关系,也 可以是嘲讽关系,它不仅包括对观众观影经验的嘲讽,如美国影片《低俗小说》对暴力 片的消解,韩国影片《我的老婆是大佬》,《杀手公司》等对黑帮片的消解,而且也包 括对观众审美期待的嘲讽,如《苏州河》的外景拍摄与预想中的美感全然相悖,更有戏 谑嘲弄观众寄托在影片人物的情感和希望;或者中立关系,艺术家与叙述人失去了明确 的文化立场与价值指向,使得接受群体处在自由选择的状态,如韩国影片《咫尺恋人》 异常含蓄的爱情结尾;或者“可书写”关系(R·巴尔特语),接受群体可以根据提供的 信息,不仅自由选择,而且能自由地改写、重写,如电视剧《来来往往》的结尾,演员 直接出现,面对观众,谈论所扮演的角色,并设计不同的爱情结局。
众多复杂、变动不居的关系丰富了语义流转的渠道,同时也使语义流转充满了歧义与 张力。当我们关注文本反讽策略与张力的运用时,就不能不谈到《昨天》。在这部影片 中,文体的互文性引人注目,导演张扬有意识地将舞台剧、新闻采访、电影等文体融合 在一起,出现了文体叙事的张力。这种表面的文体差异的张力又统一于追求原生态的导 演理念,出现了更大的张力结构。舞台剧的表演性(人物的极度张扬)与当下性(与观众 的交互影响),使其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力,而且借用了舞台剧的独白形式实现贾宏 声在戒毒院里的情节突转,传达心灵的震动与瞬间的领悟,显得强烈而不夸张,深情而 不矫情,扩充了电影表达的强度。新闻文体的采用则显得顺理成章,导演理念便是真实 生活的原生态纪录,不仅绝大多数人物都是由生活的原型人物扮演,人物的采访则将生 活的本真状态与问题的多角度审视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内容上切合社会关注的热点 ,达到了艺术文体难以企及的真实。电影文体的运用,则在时空、表达方式、塑造人物 等多方面完善前两者不具备的自由表达方式,强力将其他文体纳入到影像语言之中。
不同文体的融合,不仅在纵深向度开掘了影片内容,使得人物形象内涵深刻真实,而 且使得观众与影片的关系处在一种不断调整、重新定位的变化过程,既对观众的观影经 验进行修正,又有对观众审美的心理距离的调整。毋庸置疑,舞台剧充满了文化仪式的 色彩,观众在审美过程中显得既投入又清醒,它有节制地中断了电影的低位叙事,让观 众从单纯的真实走出来,随着剧中人物的仪式化表演,进入知性的形而上之思;新闻文 体穿插在电影文体,则直接破坏叙事的流畅,将观众领引出情感的漩涡,使其从虚构的 电影叙事中撤退,并用生活经验加以对照。而这种种差异与变化都是基于导演为真实重 现贾宏声在毒品面前心灵裂变及其心灵重生的创作意图。
事实上,运用不同文体的艺术效果与张力在娱乐片中也是屡见不鲜。如《我的老婆是 大佬》中,甘书益决定与女主人公恩金结婚时,戏剧性地采用了舞台剧的朗诵方式,一 道强光从头顶照在身上,甘书益的表情显得庄重严肃,四周隐藏在黑暗之中。这里出现 了一种反文体的消解,舞台剧被电影的戏仿,戏谑反讽喜剧性地解构了舞台剧的严肃与 高雅。这在周星驰的无厘头影片中,我们看得更为清楚,如《大内密探00发》,在实现 叙事逆转后,却出现了给剧中人物颁奖仪式。凡此种种,都是或有意或无意运用多种文 体带来的艺术效果。
《芙蓉镇》则属于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昨天》的张力体现在文体的相悖相合上,而 这里却是一种反讽消解的张力,它体现在叙事人、人物之间与观众的关系上:叙事人所 叙之事,恰恰是不愿叙述之事,人物之间相互误解与嘲讽,而观众则在人物的误解嘲讽 中获得一种对人物背弃的快感。如一边是新楼落成的胡玉音,大宴宾客,一边是迎接土 改组长李国香的王秋赦。镜头在胡玉音热闹的场面与王秋赦又脏又乱的房间里切换。当 李国香知道胡玉音建新楼房时,便非常严肃地说,同志们,解放了十几年了,我们的土 改分子王秋赦还没有彻底翻身,是应该搞搞运动了。王秋赦说,要不是接你,我早就去 了,有酒有肉,咱们去吧。这里反讽的方式运用得出神入化。李国香语重心长的话,显 然是建立在王秋赦由于懒惰的陋习致使家里一贫如洗的观众心理基础之上。当李国香越 是庄重地运用社会宏大领域的名词,如同志们,苦大仇深,彻底翻身等等,便越是消解 了严肃色彩,透露出一种隐藏不住的反讽。如果说,这种隐藏不住的反讽发生在影片人 物与观众之间的话,那么影片中王秋赦的回答,就形成了人物间的直接反讽。李国香对 王秋赦的定性,显然遭到王秋赦本人的拒绝,他的好吃懒做,懒惰成性在人物语言中暴 露无遗。两人内心的黑暗、人性的扭曲以及叙事人的态度在反讽叙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
(二)叙事的对立与二度创造
在影像叙事中,反讽策略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对立策略显得十分广泛,甚至我们可以 认为,反讽亦是对立策略之一种。而在对立策略中,“有声沉默”与“沉默如雷”便是 一种典型的张力结构。在有声沉默中,叙事行为在语义指归上处在一种含混、歧异甚至 空白中(逻辑被废除,判断被悬置),叙事行为堆砌了一堵话语的高墙,割断了语义与指 归,两者沉默无声。张力在这里表现在有声与沉默之间:越是有声,越是沉默。与之相 反的是,沉默如雷是在艺术家退隐,叙事人沉默无语,将主体行为与意图统统遮蔽,但 叙事中的人物情欲,世俗力量,现实本质与人性裂变等等在沉默中惊心动魄,即是说, 叙事行为越是沉默,语义指归便越是惊人。(注:参见王思淼《当代小说的张力叙事》 ,《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应该说,《黄土地》在视听语言上作出的极端尝试是建立在张力之上的,这种张力隐 藏在对立叙事的策略中。对立叙事意味着两元或多元处在一种紧张的选择状态。在《黄 土地》中,顾青代表的是公家人,翠巧爹代表的是农民,而翠巧便是充满张力的中间选 择地带。影片的结尾更成为了对立叙事典型的隐喻,一边是向前奔跑的愚昧迷信的农民 ,一边是顾青走在山坡逐渐远去的身影,艰难努力、逆流而上地拼命向顾青奔跑的憨憨 完成了张力的紧张状态的表达。就影片的艺术境界而言,编导们所欲达到的“大象无形 ”,“大音稀声”的状态,本身便是张力的最为精当的阐释。在视听语言上,编导们在 “有声沉默”与“沉默如雷”之间充裕出入,完整地表达了对张力结构的理解。“大音 稀声”首先就要消解日常化的语言,我们看到,人物对白极少,而且有些对白处于“有 声沉默”的状态,如顾青刚来村落遇到婚宴的对白,对白属于同语重复。而在整个影片 的声音元素中,“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是对日常语言的消解。同时,民歌不仅处 于情节的线形发展之外,而且也游离于人物纵深内涵,它包含的情感强度与生命热力, 恰恰与情节中木讷的人物形象,困顿的生存境遇形成了强烈的张力。如翠巧爹在顾青临 走前唱的民歌,浓缩了对爱情的渴望、生命的焦灼感,但也正是他愚昧麻木地依照规矩 将翠巧出嫁,换取嫁妆。因此,影片中的民歌越具有感染力便越是一种“沉默”,一种 缺席,一种消解。
从“稀声”进入“大音”,则需要再度创造。在《黄土地》中,顾青刚到翠巧家的场 景调度成为经典。这里人物之间的沉默,画面的静止,除了拉风箱的翠巧与翠巧爹含混 不清的声音,似乎连空气都已经凝固,沉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家庭的物质贫瘠,人物 的心灵单纯与精神困顿,以及以翠巧爹为代表的民族的物质、精神的双重困境威逼着软 弱无力的顾青等等语义在沉默中传达无遗。画面静止与声音沉默的时间越长,反思民族 文化的优劣、重构民族性格的“大音”传达得越是强烈:这即是缺席的在场。
沉默如雷在叙事中,往往会出现情节的空白点,将情节的连贯性打断,而潜在地利用 情节发生发展的逻辑性,将观众强行纳入故事中,刺激观众想象,间接地补充情节的空 白,充分增强与完善情节的多义性,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张力。如《芙蓉镇》中,王秋赦 在回答李国香镇上的右派、富农分子的时候,有一只手的特写,他无声无息地用力扳动 手指计算人数,火在后景中熊熊燃烧。这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它在连续的情节发展中 ,画面突然静止,声音消失,出现了不连贯的“空白”。在这无声的场景中,隐藏着压 抑的爆发力,王秋赦扳动手指预示着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
事实上,有声沉默与沉默如雷的张力结构不仅在艺术片中得以运用,在娱乐片中也随 处可见。如《杀手公司》中有一细节让人玩味。在警察遭受挫折后,怎么来表达痛苦呢 ?编导们利用了两个具有张力的镜头,前景的警察坐在办公室里,低头抽烟,沉思着。 四周的同事在后景大声谈笑,嬉闹着,笑声、说话声清晰可闻。接下来,镜头切换到警 察站在街沿,仰头吸烟,后景一个路人停车打手机,说话声依然清晰可闻。这便是典型 的“有声沉默”,即是说,四周的声音对于情节的发展都是无价值的。笑声、说话声并 没有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里的声音是“沉默”的,是“无声”的。在近年热门的韩国电 影《我的野蛮女友》中,沉默与空白显得更为明确,如当女主人公的情感积淀了三年后 终于打开了男友的信时,镜头却从女主人公的脸容上慢慢移开,作为叙述人的画外音并 没有如观众所愿而叙述信中的内容,镜头移向远处,慢慢开始旋转,而将信中内容统统 省略。这在普通的言情片里是难以想象的,放弃煽情的手法恰恰是建立在煽情基础上, 女主人公看完信后,突然呼唤着男友的名字证明了信里的真挚动人的情感。因此,从表 面上看,沉默与空白打断了情节的发展,事实上却完成了情节的起承转合,实现了情节 的节奏感。
一般而言,“有声”与“无声”在影片中并没有截然分开,在同一场景也常常是“有 声”与“无声”并置,这种并置正是一种对立叙事策略的体现。如《杀手公司》中,警 察的有意义“沉默”与旁人的无意义“有声”相互并置。如果这里的并置是刻画人物心 理的话,那么,在《我的老婆是大佬》中,对立叙事策略则主要体现在场景设置上,如 动静的对照。在寻常打斗中,一个人在近景悠闲地吸烟,远处同伴却被众人围住痛打; 婚礼上,观礼的人们安静地坐在前面,楼上与后面却大打出手,婚礼主持人却解说成是 安排的武打节目。表面上热闹滑稽的打斗游戏实际上隐藏着敌意的严重危机,故事情节 在这种紧张的对立中得以推进发展。
当我们运用对立叙事策略时,在影片中的人物也常常具有一种张力。它不仅体现在人 物形象的设置上,如《红高粱》中强壮粗野的“我的爷爷”与老实细心的罗汉大叔,《 一个都不能少》中稚嫩固执的魏敏芝与调皮捣蛋的张慧科,《我的老婆是大佬》中温柔 老实且文雅书生气的甘书益与泼辣暴力的蔡恩金,《我的野蛮女友》中温柔体贴的王晶 与刁钻活泼的女友等等,可以说举不胜举。这种角色设置在对立叙事中,通过情节的演 进,两者逐渐相通相融。因此,随之而来的叙事策略便是角色换位,其艺术效果在不同 的语境中有很大的区别。在娱乐片中角色互换通常有一种轻松的闹剧色彩,如甘书益后 来也采用暴力的方式复仇,男性的王晶被迫穿上了高跟鞋等等。而在实验影片《昨天》 中,父亲与孩子也有角色互换,如父亲必须敲门才能进入孩子的房间,被迫穿上紧绷绷 的牛仔裤,在被迫陪同孩子喝酒时,被孩子打了耳光后突然象小孩子放声痛哭,这些角 色互换的细节将深沉含蓄的父亲非常传神地表达出来,让人唏嘘不已。
(三)叙事的反复与声画错位
在影像叙事中,反复策略的运用越来越普遍。从宏观的艺术效果来看,反复可以成为 建构故事情节的策略。一般而言,反复往往造成了故事线形的明晰,人物形象的单调, 个性风格的抒情。以反复建构故事情节的影片通常说来不以情节复杂紧张见长,而比较 易于张扬个性。因而在娱乐片中较少,在艺术片中较多,如《秋菊打官司》便是以秋菊 不断地出门上访为情节主线。从微观的艺术效果来看,反复不仅能够强调真实的情感, 突出重要的情节发展点,使人出其不意,实现情节的逆转。这在娱乐片中经常看到,如 《我的野蛮女友》中打壁球、练剑、游泳等场面的重复,尤其是在恐怖片中运用较多, 几乎成为了营造恐怖气氛的不可或缺的叙事策略,被称之为“回首法”、“再回首法” ,如《午夜凶灵》、《凶铃再现》、《闪灵凶猛》等等;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强调的基础 上夸张,如《黄土地》在红、黄、黑三种色彩上的反复,用夸张的艺术方式达到了象征 的艺术效果;或在真实的基础上虚拟,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挂灯 笼、捶脚的民风民俗,在反复运用后有了一种真实感,但这种真实恰恰是一种民风民俗 的虚拟;或在虚拟基础上实现情节戏仿,对情节的重新书写,这在当下的影片中运用较 多,如《我的野蛮女友》中,女友写作的诸多剧本,随着王晶多次的阅读,出现了剧本 中的剧情;再如《杀手公司》中,一个年轻杀手不愿按约定杀怀孕的女人,却向同伴撒 谎,此时,影片画面一分为二,一边是杀手向同伴讲述的场影,一边是讲述的虚构场面 ,而且根据同伴的询问与启发出现新的内容。又如英国影片《迷幻列车》中抛啤酒杯动 作的重复,啤酒杯突然在空中停住,而插入此前发生的情节等等。这种不同时空的随意 并置、假想场景的拟真展示正是一种情节的戏仿、随意书写的体现。
正如上文所说,反讽标志着一种自由的艺术精神,但要实现反讽常常借助反复策略。 这是因为在反复中情节得以强调,而在强调突出的过程中,观众的过分关注与过度阐释 ,使得编导者的主旨与之关系开始复杂化,出现了张力,才可能出现反讽的意味。在近 来的影片中,《寻枪》的反复运用可谓十分丰富,在宏观上建构了情节发展的主线,具 有影片突现的精神状态的隐喻功能,单线的情节发展在反复策略运用下表现出了一种生 命的荒诞与戏仿,马三的寻枪行为在陈军—老树精—周小刚之间来回循环,构成了情节 主线,形成了营造故事情节的单纯与探索深沉复杂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张力;而且在细节 运用上,反复具有多重含义,被编导们屡屡运用以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如在马三妹妹 家里,马三的再三追问,妹妹与妹夫反复回答的“不晓得”以及接电话行动的反复出现 ,问话人的满腹心事与回答者的茫然不知,接电话的惶惶不安与接电话时谈笑的神态反 差,使得这一场景颇具喜剧的色彩;当涉及老树精时,画面出现了战场炮火纷飞场面, 在后面的情节中又出现过多次,这里的反复显然是对战场的戏谑模仿,一种后现代主义 意味的拼贴戏仿;在周小刚与马三出看守所之后,同样也有反复。周小刚希望受到马三 的保护,于是一直追着马三,口里却不停地说“友情最重要啊”,这里的反复具有夸张 的色彩,而周小刚的语言则明显属于反讽。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反复的叙事策略比 较丰富,在不同的语境下能展示不同的艺术张力。
如果说《寻枪》的反复比较追求某种艺术效果的话,那么在巴西电影《中央车站》里 的反复则在谋篇布局以及情节运作上显示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片开始时,来来往往 的人流,鸣叫的列车进站出站,写信的口述声,镜头十分流畅,宛如行云流水,要求写 信的母子与写信人朵拉,在这样的非常舒缓、抒情的场景中出现。这里的反复,显然是 为了达到一种抒情的艺术效果。当要求写信的母子第二次出现时,便有了情节的逆转, 母亲被突如其来的车祸夺去了生命,幼小的孩子成了茫茫人海中孤独无助者。这里的反 复应该说成了推进情节发展的激励事件;当写信场面第三次出现时,它不仅实现了情节 逆转,在异地他乡,陷入困境的朵拉与小孩终于有了获救的生存方式,更为重要的是, 实现了人物情感的逆转,先前小孩的戒备、敌视与朵拉或多或少的不情愿、尽义务等情 绪终于在这里烟消云散。这个场景开始前的场景已经预喻朵拉与小孩之间情感的逆转, 小孩坐在空旷无人的地上,朵拉却躺在小孩的怀里,失去了救助者高高在上的地位,小 孩却有一种长大成人的庄严感,因此,接下来的写信场景显然不是朵拉单独的行为,而 是两人的互帮互助与情感交融。我们看到,在《中央车站》里,反复的运用如诗如画, 意味深长,极具抒情性,将人类的美好情感渲染得沁人心脾。
当我们将画外音、人物对白、音乐等等声音因素都归于影片听觉语言时,便会发现, 它在影视叙事中常常回答视觉影像的“这是什么”的问题。它的出现有助于完全识别画 面中的诸要素和画面,以及形状和块体所承载的没有把握的信息,既使观众集中了注视 ,也集中了知性。而到了语义象征层面,这种语言不再引导视觉的识别过程,而是进行 引导观众的阐释,它紧紧夹住了那些不断增殖的意义,指引着观众穿越影像的那些所指 ,促使他有所回避,有所接受。领引到某个预先选定的意义上去。因此,在语义层面上 ,由于象征的宏大主旨的参与,视觉影像与听觉语言具有多种结合方式的可能,有时可 能形成相离相背的张力关系,其中,尤其是画外音这种艺术方式的运用。毋庸质疑,画 外音标志着当下的时间性与空间感,实质上在影视文本中注入了两个时空系统,即过去 与现在。如近来的电视剧《绝不放过你》的处理方式,画外音处在当下的叙事时空,而 叙事内容,即影像展示的内容则属于过去发生的,产生过去真实重构与现在主观阐释的 比照效果。当魏涛在陈一龙赠送的房间里断然拒绝吴梦的要求后离开时,魏涛骑车的画 面与忏悔的画外音相互配合,一愤怒,一忏悔;一主观,一客观;一狂躁,一冷静,具 有一种强烈的张力,既具强烈的悲愤交织却又无可奈何的艺术感染力,又有极强的情节 悬念,让观众对吴梦的命运产生强烈的关注愿望。如果说这里的张力处在情节建构的状 态,画面与画外音的配合促使影像叙事增殖,意义衍生的话,那么在《杀手公司》里, 画面与画外音的配合则处在完全不同的状态。当“我”哥哥知道杀手不愿杀怀孕的女人 时,决定自己动手,这时画外音穿插进来,十分动情地叙说爱情的高尚与纯洁。此时镜 头转到三个杀手,画外音说他们被感动得流泪,而影像上的杀手们双肩抽动,却不是哭 泣而是强行忍住笑声。我们说,画外音就是叙述者,在一般的故事陈述过程中,叙述者 显然是可靠的,影像展示的内容正是建立在可靠的真诚的叙事基础上,这是叙事上的约 定俗成。而在这里,显然不符合这一约定。以郑重其事的面貌出现的现在时画外音,并 没有真正阐释滑稽搞笑的过去时影像,而是过去时影像嘲弄了现在时的画外音,颠覆了 现在时的叙事。因此,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杀手公司》的叙事不是传统黑帮故事 的陈述,它的人物设置(以几个稚气未褪的年轻人为主角),情节建构(既无黑帮内部的 争斗,又没有与警察悲剧性的冲突),情感指向(没有强烈爱情来消解兄弟友谊的传统套 路)等等特征,使其具有游戏戏谑的后现代意味。在达到这种后现代意味的艺术传达过 程中,画外音与画面错位形成的张力功不可没。
事实上,就张力在艺术的地位而言,已经早被其他艺术门类所察觉。如文学艺术上, “我们公认的好诗,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称之为‘张力’”(退特《论诗的张力》) 。而在影视艺术中,张力在各种影像叙事策略中都发挥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正如上文所 分析的那样,张力无论在艺术片,还是娱乐片中,无论是在主题建构,还是在情节叙述 上;无论是艺术理解,还是艺术传达上,都将有所作为。因此,只有当我们有意识有目 的地在影视文本中使用张力谋篇布局,处理人物关系,建构起引人入胜的情节,才能真 正开掘出丰富深邃的思想主题,传达出充满个性的艺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