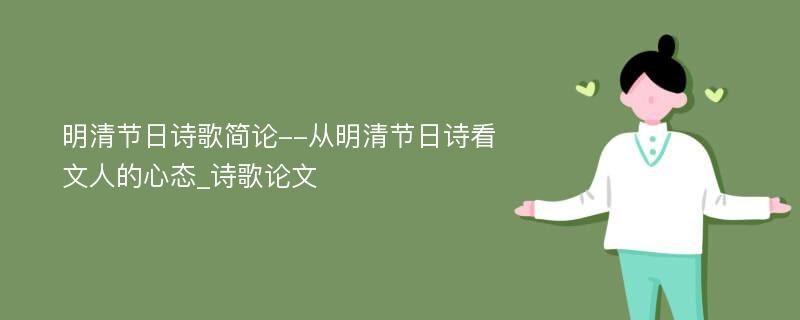
明清之际节烈诗歌小议——由明清之际节烈诗歌看士人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烈论文,明清论文,诗歌论文,士人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1)02-0152-03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亡是残酷的,却被国人赋予了太多意义。悲壮如战士战死沙场,崇高如屈原沉江,人生无常如朝不保夕的魏晋文人,凄美动容如为情而死的杜丽娘。然而,死亡这个肃杀悲凉的字眼,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眼中,却变得那么平静和正常。这样的一些作品散见于文人们的诗歌、序和墓志铭中。士大夫们用尽热情和心血,树立关乎世道人心的精神典范和行为楷模。“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慷慨捐生谓之烈。”[1]
女性用生命换来的是男性们热情高昂而近乎自私冷酷的歌颂:黄宗羲、顾景星、钱谦益、吴伟业、屈大均、施闰章、方文等等这些著名的士人创作了相关作品。其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而女性死亡的方式也骇人听闻。
回顾中国历史,对女性贞节观念的强调要求由来已久:
西汉时刘向编撰《列女传》,列《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孽嬖传》七卷。汉代班昭的《女诫》、唐代长孙皇后亲自撰写的《女书》、明代仁孝文皇后的《内训》都是自身言行举止以及生活作出的规范。比如女子应该谦恭卑弱不出风头、谨言慎行、将丈夫、叔弟置于第一位。到了清初王相把《女诫》、唐代宋若华《女论语》、明《内训》及其母亲的《女范捷录》合称为“女四书”。
另一方面旌表贞女的制度也促进了这种社会风气。《汉书·宣帝本纪》中载:“夏四月……及颍川吏、民有行义者爵,人二级,力田一级,贞妇、顺女帛。”[2]《明会典》中也提到:“民间寡妇,三十年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3]有文章为证:戴名世《李节妇传》:“康熙十有三年建坊旌表而节妇之名著于京师”,[4]其又一篇《吴烈妇传》中,戴氏于丈夫死后,自己吞金而死,于是,“自巡抚都御史以下皆祭吊烈妇而其亲党醵金建吞金祠于烈妇冢旁”。[5]这种社会制度对节妇烈妇的鼓励和奖赏,客观上鼓励刺激了女性的守节意识。
在思想教化方面,宋代司马光已经很明确提出了对女性忠贞的要求,之后二程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将之推到极致。在宋明理学的笼罩下,为自己立贞节牌坊也成为女性的自觉追求:《宋史》中有列女55人,《唐书》54人,《元史》187人,《明史·列女传》中说,以贞白自砥的妇女“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6]并记载有300多名妇女殉节的史实。越到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要求越严格苛刻。
《罪惟录》卷28也记载有烈妇87人、烈女35人,其中有所谓的“徐州十六烈”、“丰县二烈”、“萧县八烈”、“沛县八烈”、“砀山县十六烈”、“丰县五烈”、“歙县六烈”等。
另外,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地方志中也记载有大批烈妇、烈女。如安徽《休宁县志》记载,该县在明代就有烈妇、烈女400多人。由于中国古代盛行早婚,烈女自杀的年龄一般在14~19岁之间,正值青春年少之时。
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死于煤山,一发而不可收拾,随之上演了一出出将领士兵纷纷殉难的悲剧。大明王朝气数已尽,而守城将士们也纷纷以死报效朝廷和皇帝。1645年,扬州城被清兵攻下后,一时间官员、医生、船员及儒生以死殉城者很多,妇女死义者也不少。江都城陷后,殉城者更多,妇女中就有誉之为“江都程氏六烈”、“孙道升一门节烈”等。
文人们以客观冷静的描述了死亡的过程:
烈妇曹氏……年十九,归同邑唐之坦,归六年。之坦疾革。谓其夫曰君死,我不独生。乃营砒霜以待。烈妇沥桑灰为汁饮之。腹痛而不死,……明日,恐死不是及时也,碎钱为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殓,防之者欲虔,烈妇曰:“顷欲与夫同殓,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人定,烈妇潜起饮卤升余。号呼婉转,毒裂经时,复吐而下解。烈妇曰:我既求死不得,计惟有绝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迥然,夜半,启户出,投于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觉,出之池,已死。
——黄宗羲《唐氏曹烈妇墓志铭》[7]
从砒霜、殉葬、吞金、绝食再到投井这位正当二十五岁芳龄的女性无所不用其极而终于完成烈妇的愿望就是求得已死,可谓“求仁得仁”。作者描述死亡过程时流露出无比推崇赞扬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就作品本身又何谈美感?
诗人们还以热情高昂的激情赞扬了这种美德,黄宗羲《卓烈妇诗》:[8]
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
无数衣冠拜马前,独传闺阁动人怜。汨罗江上千年泪,洒作清池一勺泉。
问我诸姑泪乱流,风尘不染免贻羞。一行玉佩归天上,转眼降幡出石头。
王子才华似长卿,断肠数语写如生。至今杜宇声声叫,还向池头叫月明。
诗人将卓烈妇比喻为千古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可见评价之高。屈原怀抱美政理想,带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伤感而沉吟江畔,自投汨罗。可以说,屈原的人格是伟大崇高的,他因此而成为后世文人景仰的文化名人和大文学家。诗人作此比喻自然表明烈妇的死具有与屈子一样的文化高度。
方文,字尔止,安徽桐城人,明诸生,入清不仕。他的诗歌人称有少陵遗风。其《大明湖歌》叙张秉文在被清军杀害后,其妻方氏与另一妾投水死的壮烈场面。“吾姐闻难且不哭,立召二妾来咨谟。爷为大臣我命妇,一死之外无他图。……小妇亢言吾弗活,愿与母氏同捐躯。两人缝纫其衣带,欣然奋身投此湖”。何止礼赞,烈妇的死具有弘扬传统道德的伟大意义:“纵观往古,国家废兴,未有不由于妇之贤否,事君者,不可以不慎,诗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9]
由此可见,女子之规范不仅仅是一家之本,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顾景星《烈妇行》:“君臣夫妇两大伦,国破家亡死几人。息妃不笑何难殉,蔡琰还乡再误身。人间万事堪悲触,使我欷虚泪频续。请将烈妇乡里歌,弹入马上琵琶曲。”郑性《王烈妇》:“此妇沉晦久不彰,贞心耿耿埋尘土。我为烈妇扬幽芳,日月不灭妇千古。”曹溶《宋宋诗》:“嫁者得故夫,婚者得贤妇。薄俗行复敦,可以戒永久……婚姻人道纲,歌此上国史。”如此等等。
还有贾开宗的《卓烈妇》:“夫妻相向暮口顽,一笑凝睇岂惜死,夜静不闻儿女啼,芳兰萎谢金闺里。”女性的死亡就这样被赋予关乎国家社稷存亡的意义。
晚明之际,个性解放思潮进行得如火如荼,李贽作为急先锋,从肯定人的个人私欲出发他对传统的儒家道德礼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他也提出了在今天看来非常先进的女性主义观点。一个又一个充满活力和个性的女性形象生动活泼的展现在文坛上。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杜丽娘,徐渭的《四声猿》也如石破天惊之语,振聋发聩,小说方面冯梦龙也塑造了要求个人尊严的杜十娘等形象,诗歌创作上,公安三袁也主张“不拘一格,独抒性灵”。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文学创作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活泼而舒展、张扬而开放的气氛。在明清那个重视个人享受重视声色的时代。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襄与董小宛,吴伟业与妓女卞玉京,文人们数不清的风流韵事都成为当时文坛佳话,私人生活与文学作品的强烈反差使我们难以相信,这些残酷隐忍的作品竟然出自这些风流文人君子之手。
死亡在明清士人而言,已经不是生命的消失,生命本身并不重要。文人们可以那么冷静坦然地面对死,死亡也因此而成了士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高谈阔论、不厌其烦。所谓当死不当死,如何死等等,令人发指也难以置信。但是如此残酷和违背人性的事在明清之际就这样屡见不鲜甚至愈演愈烈。
黄宗羲认为死是可以分为几类的,主动殉身为守节,阵亡为战功赎罪而败死就不是死,只是失败而已。有立志要死亡的,有被人杀害的,还有偶然死亡并无存心要死的,自然,那种志在死亡的是守节具有节气,而没有死亡的愿望而死的只能称之为遇难了。
相类似的论述还有一些。如归庄“人处艰难之际,有不死而死则全名,不死则丧节者,有可以不死而不幸而死,亦足以明节者”。[10]更为荒诞变态的是,即将自杀的人们不会有任何惆怅惋惜还有闲情考虑人伦礼节之事。《明季北略》载王伟夫妇同缢:“乃为两环于梁间,公以便就。耿氏就左。既皆缢。耿氏复挥曰:‘止!止!我辈虽在颠沛,夫妇之序不可失也’复解环。正左右序而死,人比之,结缨易篑。”[11]
“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无能、好猜忌的崇祯皇帝于甲申年三月初三日吊死于煤山。天子自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崇祯皇帝的死在当时朝野上下惊心动魄,甚至震动了整个社会和无数士子们的心灵。
虽然崇祯皇帝几乎一无是处,但是在君主专制集权的社会里,皇帝的死在士人们的心中,无疑是重重一击,他的死仿佛是一个导火索,接踵而来的是将领大臣们的纷纷殉难以表衷心耿耿和崇高节气。于是,死亡在明亡清兴之际堪称蔚为壮观:“李邦华题阁门曰:‘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他。’”[12]施邦曜“惭无半策匡时难,惟有徵躯报主恩。”[13]“甲申之际,城陷而自殉义者,不可胜纪。其泯士尚有数十辈。”[14]
那么为什么会将女性自杀与男性的守城而死、为社稷而死联系在一起呢?
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见,妻子与臣都是处于一个维度的,要求女性的节烈推而广之也就是要求做臣子要效忠于皇帝。即所谓“女子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明代时已有人将烈妇忠臣相提并论,通过表彰烈妇以提倡忠义。明乌斯道《谭节妇祠堂记》:“乞降走匿不暇,岂肯死节者,曾几何人哉兹以一妇人,能慷慨死节,与同郡文文山,光焰相照,垂名史册,岂不重其慕耶。”(乌斯道:《谭节妇祠堂记》)[15]
邓汉仪《题息夫人庙》:“楚宫慵扫黛眉新,祗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息夫人,春秋时息侯的夫人,妫姓。楚文王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教及成王。传说以国亡夫死之痛,与文王不通言语!康发祥《伯山诗话》中载:“旧传此诗在龚合肥座中作,合肥为之色沮罢会。”[16]
从文学角度讲,以夫妇喻君臣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种传统的创作方法。最早是由屈原开辟了香草美人、以夫妇喻君臣的文学创作方法,这一方法后来也一直被文人延续下来:乔亿《剑溪说诗》:“张衡同声歌,繁钦定情篇,托为男女之辞,不废君臣义,犹古所谓之遗风也”,[17]“夫古人作诗,取在兴象,男女以寓忠爱,怨诽无妨贞正。”[18]其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在文学史上,此类既特别又委婉动人的作品为数不少:白居易被贬江洲,将自己的身世感慨寄托于琵琶女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凄楚婉转的哀叹。朱庆馀“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援引诗。张籍在婉言谢绝别人时则说“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李商隐很多朦胧诗也常常被人理解为政治隐喻诗。一生志在杀敌报国的辛弃疾,当人生失意时也同样“千里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因此,无论是文化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女性的节烈是和男性的忠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范畴。女性的节烈和男性的忠义都是专制集权的社会中抹杀个性、泯灭人性的变态以至于疯狂的产物。当士子文人们以欣赏的态度甚至无比欣羡、恨不能死的深情来赞美人的死亡时,我们可以知道,专制思想对人性的戕害以及人们自我毁灭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无疑是人类的一个悲剧。鲁迅先生说的“吃人的礼教”就是如此吧!
明清之际,注重内心修养的宋明理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忠君的强调尤甚以往。士人们奔走相告但是明王朝还是气数已尽,在沉痛的现实面前文人们以强烈的反思精神思考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而最终将世风日下看作是明亡的重要原因,忠义观更成为评价一个人道德是否高尚的一个标准。于是,贰臣们受到士人激烈的批判:“崇祯之末,风俗陵夷,廉耻道丧,其亦天宝五代之时乎,自流贼发难,十五年间以至甲申之祸,内外文武诸臣之为哥舒翰,段凝,冯道者何其多也!”[19]“夫人之无奈何者存乎气数,天之无奈何人者存乎人为,故功业有所不可,必而忠义无不可以自勉也,为人臣子不能回天而以忠义自见,虽非志之所愿而舍是,无可为矣!”[20]
可贵的是,在清代的作品里我们还是能听到一些进步民主的声音。《儒林外史》中王玉辉鼓吹正当妙龄的女儿殉夫因为那是关乎青史留名的大事,女儿一死他便近乎变态发疯的仰天大呼“死得好死得好”。当女儿被送烈女祠祭奠时,王玉辉“转觉伤心起来”。吴敬梓以卓越的讽刺手法冷静塑造了一位被封建礼教扭曲的人物形象,作者的爱憎褒贬已经浮现于纸上。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宝玉对明代忠臣烈士的死节死社稷进行猛烈抨击,所谓的忠孝节义在贾宝玉眼中不过是虚伪而懦弱的表现:“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节妇、烈妇以青春和生命的陨落换来的是时人对她们的略显僵硬而无比坚定的歌功颂德。这些文学作品仿佛一把钥匙,为我们了解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心态打开一扇门,打开这扇门,我们看到的是在僵化而失去人性的宋明理学观念指导下,文人士大夫冷漠甚而变态的人生观念。封建礼教对人们特别是对女性的扼杀,女性们对礼教自觉的遵守和皈依,对此扼腕叹息之余只有哀其不幸也怒其不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