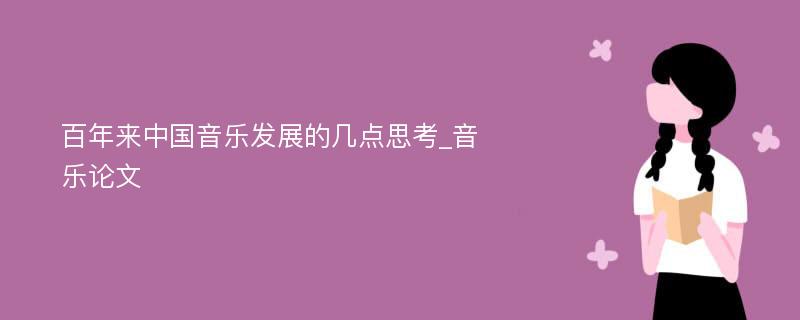
对中国近百年音乐发展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百年音乐文化是在继承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近现代西洋音乐文化的经验而产生、发展的、新的音乐文化。在这不到一百年间,经过几代中国音乐家的努力,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取得了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巨大进展和相当丰硕的成果。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中国近百年的音乐文化是遵循了一条既不断吸取以西洋音乐为主的世界音乐文化的影响,而又不断加深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的方向向前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新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又显示了它与欧洲音乐发展的特殊现象和规律。这是非常值得加以认真回顾、认真总结的。为此,大胆提出如下几点粗浅的认识,与同行们和广大读者讨论。
一,总的讲,从清代中叶、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原有的产生于封建统治下旧的一切,都不可逆转地朝着新的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演变开始比较缓慢,并历经相当复杂的曲折过程。但是,一切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都有利于加深这种由旧向新的演变过程。
作为文化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近代音乐,在整个社会演变的大潮推动下,也在不断地加深这种由旧向新的演变。只是在本世纪前的近60年间,仍局限于在原有各种传统的形式内部逐步发生的量变过程。当时一些外来的因素(如西方基督教音乐的传入、西方器乐形式的传入等)还没能对这些传统的音乐发展以直接影响。当时能够推动这些传统音乐形式的演变的因素,主要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中的影响的日益加强,中国农村经济的日渐趋于破产、大量农民群众的不断涌入城市,以及各种原来活跃在农村的传统艺术形式也随之进入城市、并加快其走向职业化和市场经济化的变革。从本世纪初后,在各阶层群众要求改革的革命浪潮日渐高涨、清政府被迫实行所谓“新政”的条件下,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才出现了质的飞跃,一种主要吸收西方音乐文化的经验而产生的新型的中国音乐“学堂乐歌”得以迅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整个社会的变革。自此之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开始了中国新音乐文化同中国传统音乐两种音乐文化同时并存地向前发展的过程。前者的演变比较迅速、紧密地跟随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而后者则由于暂时还游离于整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而相对比较缓慢。但是,这些原有的传统音乐,在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仍保持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今天还远没有、也不会很快消失)。
二,如上所述,在欧洲音乐影响下所产生的、以“学堂乐歌”为主要形式的中国新音乐,从一开始它就是中国新式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国近代新的音乐教育的集中体现,并被纳入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总潮。因而,它也成为日后推动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基础。但是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并非遵循欧洲音乐发展的道路。我们都知道,欧洲音乐的发展曾依附欧洲基督教和封建宫廷的统治长达近千年,后来尽管欧洲各国均相继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改造,欧洲音乐受上述影响仍很深。因为,在欧美各国,基督教曾是密切参与他们的人民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欧洲音乐的发展受基督教的影响较深是并不奇怪的。在中国,真正曾经参与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是基督教、也不是曾经在历史上有过相当影响的道教和佛教(如“五代”、“隋唐”等),而是以孔、孟、朱、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影响到清末,已经日益变为阻碍社会改革、阻碍新文化发展的旧势力的集中体现。所以,尽管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算短、中国还存在自己的独特的宗教音乐传统,尽管儒家思想在中国曾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它们都没有象“学堂乐歌”那样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所给予后来整个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如此重大的影响。由此可知,即使在我国新音乐发展的初期,我们的前辈音乐家还是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有鉴别地去学习欧洲音乐的有用经验,而并非是照搬欧洲音乐发展的老路。
三,本世纪初所产生的中国“学堂乐歌”,是主要选用欧美、日本的曲调加以填词的学校歌曲。它的演唱方式、记谱方法等,在理论体制上都与欧洲音乐是一致的,但是,既然已经填上了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人民愿望的中国歌词,并且已经作为中国新型音乐教育的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它已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一种新的形式。正象在当时逐渐发展起来的“洋学堂”,尽管它确实是主要吸取欧洲(包括日本的“东洋”)的学校教育经验办起来的,而与我国原来的“科举”教育体制是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的。但在当时,恰恰正是这些被旧的统治势力瞧不起的“洋学堂”,成了中国新型教育的最初形式,并作为当时中国“新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学习欧洲的文化教育,正是中国人民力图实行改革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不能把它视作为一种由于盲目崇洋而轻视、丢弃我国原有传统文化教育的表现。
同样,我们不应否认从“五四”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主要也是取法于欧洲音乐的教育体制。只是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又采取了对中西音乐“兼收并蓄”的方针,适当加进了一些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当时这种新型的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就是中国音乐家和教育家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并在它的基础上逐步开辟了建设中国音乐文化的新路。这都已为中国大多数文化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所接受,已成为中国近百年音乐发展的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在当时,有些新文化工作者确实曾一度对原有传统文化的落后面看得过重,对借鉴西洋的积极意义估计偏高。但是,必须首先承认,在当时,学习西洋仍是一种立志改革的进步的表现。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将中国文化和音乐的建设仅仅立足于我国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那就实际上意味着是历史的倒退。因为,这种企图将中国的文化教育拉回到封建传统旧轨道的见解实际上在当时就存在过,只是它并没有为大多数文化、音乐工作者所接受。
四,近百年来,中国各种传统音乐在新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下,也在缓慢地发展、演变。它们也应该与中国的新音乐文化同属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范畴。但是,这两种音乐文化在体制、形态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各个品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在本世纪的前半,它们基本上仍是作为传统形式的保存者发挥其社会作用,而没有被纳入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总潮。在这近百年间,尽管也曾有人企图对这些传统的音乐形式进行一定的改革(如在辛亥革命时期,京剧、秦腔等传统戏曲剧种就曾进行过现代时装戏的尝试;40年代,以袁雪芬为代表的“雪声越剧团”还进行过运用新音乐的创作方式来写曲,运用管弦乐队进行伴奏的尝试等);但是,从整体讲,当时这些改革的尝试只是极个别的、一时的,并带有明显的自发性,而且后来它们都因种种实际问题难以解决而未能坚持。推动艺术品种演变、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新的要求。任何艺术品种,如果不能在新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要求下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根本改造,它就只能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保存者继续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发挥其影响,它们不可能成为代表新时代意义的文化的体现者。应该承认,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根本改造是需要有一个相当长期的、艰苦努力的实践过程,它比引进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困难得多。
当然,中国的这些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保存者,它们除了仍然保持着满足人民群众原有审美情趣的作用外,它们对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包括对其它文化艺术的发展)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深远而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使这些基本以借鉴西方音乐的经验发展起来的中国新音乐不断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有助于使它们的发展不断加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助于它们更好、更快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五,因此,近百年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了两种音乐文化同时并存的现象,即一种是原有的传统音乐文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的发展,另一种是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所产生的中国新音乐文化的不断向前的发展。关于这点,我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1986)的“序言”中,就曾这样说: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和19世纪末以“学堂乐歌”为启基的“新音乐”同时并存、各自发展为其特征的。在本时期,这种特征基本上仍保持着。这可能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有别于西方各国的一个标志。……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演变和发展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分散的状态,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介入,它们的演变和发展是在有领导、有计划的全面改革方针下进行的。它们一方面仍保持着各自的基本特色,另一方面与新文艺、新音乐在艺术上的交融汇合的不断深化,它们还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影响的传统因素,促进了“新音乐”各种形式的不断民族化的发展。
但是,从50年代后,在社会主义的方针指导下,我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了为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生活要求的全面的改革。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人们也曾有意识吸取西方音乐的各种因素(包括创作形态、技术理论、音乐观念、音乐表现方式和乐器制作及演奏方法、以及有关的教育体制等),使得这些传统的音乐形式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明显的变化。例如在民歌的领域不仅出现了曲调有所改变、歌词完全不同的新民歌;还出现了以现代多声思维加工的艺术性民歌独唱曲和艺术性民歌合唱曲;在民族器乐方面则不仅出现了基本上运用传统音调和结构原则所写的新的创作乐曲,还出现了大量有意识吸取西方多声创作技法、西方乐曲结构原则的、各种带伴奏的独奏曲、各种重奏曲、各种合奏曲和协奏曲等。尽管由于经验不足,其中有不少作品还写得不够令人满意,或者说它们在如何运用这些西方的创作经验同中国传统的音调、音色、表演方式相结合,用在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方面,还缺乏经验、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这些新作品的出现,表明人们已不满足于对这些传统的音乐艺术品种仅仅发挥其“传统文化保存者”的作用,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希望使这些传统的音乐品种也成为与新的时代和社会生活密切相连的、新的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50年代后,在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注目的现象。即无论在音乐教育体制、音乐创作形态、音乐表演方式和方法、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范畴和对象等方面,受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的渗透和影响愈加深入了。例如对声乐的训练方面,尽管现在有所谓“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不同提法,但现在在我国音乐院校中所进行的“美声唱法”训练,实际上已跟50年代初、或50年代以前的所谓“洋唱法”有所改进;同样,现在在音乐院校和音乐团体培养出的所谓“民族唱法”歌手的演唱,也与50年代初、或50年代以前的“土唱法”不一样。现在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唱法,实际上已出现了不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变化。此外,在有些民族乐器演奏的学习中,类似的现象也存在。至于在现代的音乐创作中,西方的因素和我国传统的因素相互交融、渗透的现象就更突出了。
当然,到目前为止,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文化,对中西这两种音乐文化的相互交融和渗透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还有很长的路程需要今后继续去努力。但是,无论如何,这两种不同音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的关系,已不再是“五四”时期那种“兼收并蓄”的关系了,而是已经进入了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新的关系了。
关于这一点,最近修海林同志以“双文化”为名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见《音乐研究》1993年第四期《关于中国音乐“双文化”现象的若干思考》),值得引起重视。
六,中国近百年音乐文化(包括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研究、音乐出版等)的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反复不断地向西方音乐文化深入学习和反复不断向我国传统音乐深入学习中,在艺术思想和艺术方法上不断进行大胆创新的过程。比如,在音乐的基本思维和理论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西方积累了近千年的有关多声思维的理论体系和整套的创作技法经验(和声、复调、曲体、配器等),这一切确实与我国传统的、建立在单声思维的理论体系和主要采取基本曲调变头、换尾、加花衍变的创作方法有很大的差别。要接受新的,就不可避免要改变某些旧的,否则就谈不上是改革和创新了。同样,当我国的音乐工作者在接受西方的音乐理论体系和创作经验的过程中,逐渐感觉到单纯照搬欧洲音乐那一套也存在不完全适应用来表现中国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特殊风格的问题,因而又不断自发地对这些西方的经验进行种种所谓“民族化”实验。这也是一种艺术上大胆创新的表现。这是一种为了创造中国民族的“新”,而改变欧洲18、19世纪的“旧”的演变。一方面在反复不断地学习,一方面又在反复不断地创新,这就是反映在中国近百年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法”。
当然,任何学习和创新要取得积极的成果,都必须建立在正确的目的和正确的选择(时机的选择、内容的选择、方法的选择等)基础上。从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讲,它的最终目的一方面就是应使它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要使它在人类文化艺术、人类的精神文明的发展中起不断促进、不断更新的作用。这是判断人们对其学习和创新时所作的“主动选择”是否正确的试金石。回顾我国这近百年音乐文化的发展,可以说绝大多数音乐工作者都曾为了我国的民主自由和独立富强,为了培养新一代人才的全面健康发展,以及为了我国文艺、音乐事业的不断提高和繁荣,几十年如一日地刻苦钻研业务,不计报酬地埋头创作、研究、教学,满腔热情的为人民演唱、演奏、指挥、教歌、辅导。事实证明,这近百年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无论在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或是在表演、教学、出版等方面,都是经受了历史的和群众的考验的。对今天的绝大多数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及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讲,对那些主要源自我国传统音乐的新作(如刘天华的《病中吟》、阿炳的《二泉映月》等)固然觉得亲切难忘,但是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教育体制已经促使他们都习惯、喜爱了那种既体现了中国民族特色、又是创造性运用欧洲多声音乐创作技法创作的新的中国音乐作品(从沈心工的《黄河》、李叔同的《春游》、一直到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黄自的《长恨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近几年来,不少青年学生对60、70年代所产生的、适当借鉴现代多声创作技法和运用中西混合乐队伴奏的许多京剧现代戏(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等)发生很大的兴趣。这说明对大多数中国的音乐听众(特别是知识青年)来讲,他们绝不会因为作曲家在创作中运用了源自欧洲的创作技法(主要指和声、对位、曲体、配器等)而不承认它们是中国作品。相反,他们似乎对这些民族化的中国多声作品比那些完全是传统的中国作品更喜欢,更觉得亲切,更能引起艺术审美上的共鸣。这些都是已成的历史事实,不管那些外国人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总是首先沿着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喜爱的方向继续向前进的。轻率的将这些现象都视为就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就是所谓削弱民族“主体性”的表现,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的。
七,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近百年来,曾有相当数量的外国音乐家在中国的音乐院校、中国的教会学校、以及从事私人的音乐教学。其中有些外国的音乐家(如意大利钢琴家、指挥家梅百器,小提琴家富华;俄罗斯钢琴家查哈罗夫,拉扎雷夫,大提琴家舍甫磋夫,声乐家苏石林,小提琴家托诺夫;犹太小提琴家维登堡,作曲理论家弗朗克尔,施洛士;美国作曲家范天祥;立陶宛钢琴家夏理柯;保加利亚小提琴家尼哥罗夫等等)确实以其真才实学为培养我国许许多多优秀音乐家的成长付出了不少的劳动。另外,许多基督教会及天主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大、中、小学校(如北京的清华学校、燕京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的中西女校,苏州的景海女师,北京的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孔德小学等等)也都曾以其出色的音乐教学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本世纪50年代,为了更好地建设和提高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文化部还曾有计划地聘请了相当数量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音乐专家来华进行教学。这一切都说明,为了更快的发展我国的音乐文化建设,不仅我国许多杰出的音乐家曾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还有相当数量的、对我国友好的外国音乐家,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辛勤劳动。有的外籍音乐家(如查哈罗夫、维登堡等),甚至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这一点,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事求是地给以应有的评价。
八,在这近百年间,中国音乐的发展也呈现了类似过去欧洲音乐发展由“以声乐为主”逐步过渡到“声乐器乐并重”的现象。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与欧洲的情况是不同的,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欧洲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基督教统治的影响所造成的,而中国是由于受新式学校教育和群众歌咏运动的影响所造成的。因此,到目前为止,各类声乐创作仍然是中国广大群众最便于接受的音乐形式。并且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所取的成绩和经验还是比较突出的,绝不能妄自菲薄。但是,在近十年来,我们恰恰在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比较多,群众总觉得能够提供他们咏唱的好歌太少。因此,我们仍应对声乐创作的发展予以充分的重视。尤其对与广大群众和广大青少年关系最密切的、“雅俗共赏”的群众歌曲、抒情歌曲、学校歌曲等方面的创作发展,更应切实加强。
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要对器乐创作(甚至包括象古琴独奏、各类室内乐等主要提供少数人自娱与欣赏的音乐品种在内)的发展和提高有所轻视,更不能有意无意地加以排斥。相反,这方面的工作也丝毫不能放松。因为,从总的讲,我国各类器乐创作发展(尤其是各类小型器乐独奏曲的创作)比较缓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无法适应整个器乐演奏事业日益走向普及、器乐演奏水平迅速提高的发展趋势和需要。
九,在音乐创作中运用什么技法是应完全由作曲家根据对表达作品的内容、思想、感情的需要和他个人的审美情趣来决定的。但是,在创作中运用什么创作技法,并不是表明作品艺术成就高或低、优或劣的主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仍然偏爱传统的技法,还是热心于吸收、借鉴西方20世纪音乐创作的新技法,都是无可非议的。过去,音乐界一度在“左”的文艺思潮影响下,曾对借鉴西洋的创作技法、特别是西方20世纪现代音乐的创作技法,认为必须加以排斥的思想是片面的、错误的。但是,也不必反过来,将借鉴这些技法和经验看成是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和提高的必然趋势,不要有意无意的将此与运用传统技法的现象对立起来。在这方面应该提倡任由作曲家自由选择的方针。
因为,运用任何技法和经验,都应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音乐作品的内容和情感,都应是为了要使自己写出的作品为人们所理解、接收、喜爱,并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以及使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实践能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或艺术本身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这里又存在一个与大多数音乐听众的审美情趣的关系问题。从80年代以来,有一些所谓新潮的音乐创作,引不起多数音乐听众的兴趣,甚至也引不起演唱、演奏家的兴趣,这个现象值得引人深思。因此,一方面对作曲家个人运用什么创作技法进行创作不应该作任何干涉、非议(但不包括正常的音乐批评);而另一方面,从整个音乐创作的发展与社会、人民的关系讲,“雅俗共赏”的美学原则,仍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和大力提倡。
十,总的讲,近百年来,在中西两种不同音乐文化反复不断的交流、碰撞,相互吸收、渗透的交融过程中,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正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迅速地成长壮大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开始不断融入世界音乐发展的洪流、开始与欧美各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共同地向前进了。尤其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研究已逐渐跻身世界之林而无愧色了。我们许多音乐前辈所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开始逐步在变为现实。但是,百年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仅是转瞬之间的片刻。因而,一方面可以说,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我们所经历的变革和所取得的进展是相当可观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它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种“起步晚、底子薄、变化大、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可说是一种必须加以正视的历史局限。对这不到百年所取得的成绩固然不要妄自菲薄,但更不能盲目乐观地估计过高。我们只能说,既然已取得了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就应该进一步努力,去共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