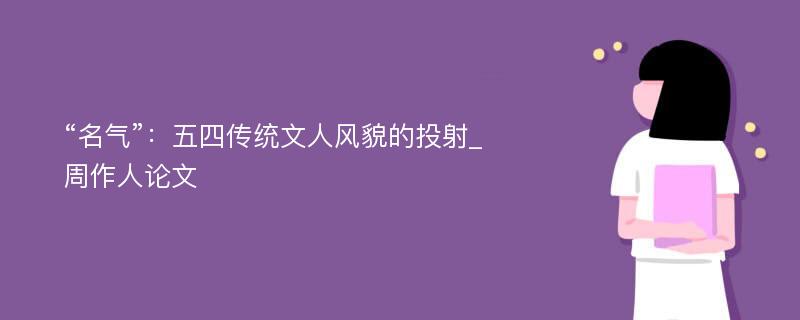
“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五四”的投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度论文,士气论文,文人论文,传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自序中回顾“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发展时说,这三、四年“确是绚烂极了”,“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事实上,不仅仅局限于散文,将之推及于一些“五四”作家,也是同样适用的,而“隐士”与“叛徒”一说,本来就出自文人的自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五四”新文学作家少有人不以旧思想旧文化的叛逆者自诩或相称,而他们所作的工作也印证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可敬可佩的决心和勇气,印证了他们精神人格的巨大裂变、思想观念的重大转折。然而,将西方的“民主”、“科学”当作意识形态唯一圭臬的“五四”作家,却始终无法真正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诱惑。文人精神、文人气质、文人风度潜移默化的承传,即使在“新纪元”的“五四”也不例外,“中国名士风”创作的存在,就是一桩足有说服力的案例。
一般而言,中国古典文学中名士派文学大多出自名士之手,比如明朝名士散文必定来自于那些“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的名士(注:参见周作人《〈杂拌儿〉跋》,《知堂序跋》第313页至314页,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7年2月。)。这样, 朱自清所说的“中国名士风”的散文——也许不止是散文,似乎应是现代“名士”的产物。但是,“五四”这样的时代不可能也不允许产生明朝的那种“名士”,当然,“中国名士风”的“五四”散文也肯定不同于公安派文人的文章。尽管朱自清也赞同周作人有关“现代散文历史背景”的论述,认为“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他同时又特别指出“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来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注:朱自清:《〈背影〉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378页,郁达夫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6月影印版。)。在朱自清看来, 连最能代表“中国名士风”散文的周作人的文章,也并非如周作人所说“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注:参见周作人《〈杂拌儿〉跋》,《知堂序跋》第313页至314页,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7年2月。)。 这应该说是朱自清不可动摇的立论前提。因此,我们的理解是:“中国名士风”的文章只是较之“外国绅士风”保留了更多些的中国古代名士的“情趣”,“中国名士风”的作者,也仅仅只是比写“外国绅士风”文章的人士体现出了更明显一点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风度……本文姑且称为“名士气”。这样,我们就很自然地将朱自清的前提,当作了揭橥“五四”作家人格建构中别一层面的出发点。
一
中国千百年名士风流的佳话,就行为方式而论,不出乎放达和隐逸两种,名士们也大致分为两类:“狂”与“狷”。“五四”作家的“名士气”也不外乎“放达”与“隐逸”的范畴,这与周作人关于“叛徒”与“隐士”的说法有些类似。如果单纯考察文人的气质,且不作道德追究,那么可以这样认为:“五四”作家中周作人固然曾经“浮躁凌厉”过,但终究倾向于“隐逸”;而郁达夫即使早年多愁善感、中年陶醉于山水之乐,可“放达”的代表还是非他莫属。
狂飙突进的“五四”高潮时期,是“五四”作家最富有青春锐气的时光。传统文化模式的突破,思想文化的多元竞起,为新时代“进取”的“狂者”提供了“放达”的契机。以勇于“暴露自我”著称的郁达夫,用一本《沉沦》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觉醒者“打破桎梏”的勇气。由于《沉沦》中大量性苦闷细节的渲染,有人指责它是“不道德的小说”,为此,周作人专门撰文辩诬。他认为《沉沦》属于“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周作人还“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注:周作人:《沉沦》,《自己的园地》第59页,岳麓书社1987年7月。)
虽然周作人出于“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的原因,从艺术的角度对《沉沦》中“猥亵”因素作了解释,但“猥亵”依旧是“猥亵”。郁达夫小说人物的消极颓废使郁达夫获得颓废作家的称号,这种将小说人物与作家本人挂号的做法,对于说明其他作家与作品的联系,也许过于勉强,但用于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80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9月。)原则的郁达夫, 却并无不可。他是抽取了自己早年放荡不羁的颓唐经验和情感,来塑造他的小说人物的。早期作品里每一个主人公差不多都是郁达夫的自画像。《沉沦》之后,他在《茫茫夜》、《秋柳》等作品里对主人公眠花宿柳、酗酒纵情的情节描摹更是愈益精细,郁达夫的“放达”趋于极致。魏晋一些以怪诞著称的名士离不开药与酒,郁达夫的放浪形骸少不了酒与色。他以沉湎醇酒美色来表明他的愤世嫉俗,同时在沉湎酒色中寻求表现自我的途径。对于他个人“任意的喝酒,任意的游荡”(注: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72页,花城三联版。)的“放达”,郁达夫在他的一些创作自述中从不讳言。而在稍后的《日记九种》里,他更是将世俗眼里的斑斑“劣迹”赤裸裸地加以袒露,这既是郁达夫“自叙传”理论的大胆实践,更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和示威。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自己酗酒醉色私生活“荒唐”一面的津津乐道,和当年竹林名士刘伶裸身待客,有着相似的动机。1927年1 月的《村居日记》,写于与王映霞相识却尚无结果之时,其中充斥许多这样的记录:“打了一夜麻雀牌”(1月1日);“又到酒馆去喝酒”(1月4日);“喝了十几碗酒”(1月11日);“酒还没有醒”(1月14日);“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1月21日);“遇见一个中年的卖淫, 就上那里去坐到天明”(1月25日);“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1月26日)……从上述日记来看,短短一个月时间,郁达夫可谓无所不为。这种买醉买笑的荒唐生活,直至得到王映霞芳心允诺方才告一段落。作为一个“五四”作家,郁达夫具有反叛旧传统的现代个性意识,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彻底去除了精神世界里残余的传统士大夫的趣味。对于他小说中的病态性欲描写,一般人都以为是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加上日本“‘自我小说’中‘颂欲’思想与手法的影响”(注:参见钱理群等《中国文学三十年》第9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 他的小说以及日记里无所不在的对陶醉于酒色的夸耀,却流露出他本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名士气”。在郁达夫大量的旧诗中,旧文人的意趣更为突出。如“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注:郁达夫:《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能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郁达夫诗全编》第14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之类的情调, 与其说是现代诗人的浪漫蒂克,不如说是古代名士的倜傥风流。
不仅仅是郁达夫,和他同时期的一些文人,其言语举止,在“五四”新环境下时而仍显现出尚未消除殆尽的陈旧痕迹。鲁迅在回忆“五四”期间的刘半农时说:“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所引《鲁迅全集》版本同此。)较之于刘半农,有些文人走得更远。类似郁达夫私生活的“放达”,即使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不能完全避免。“五四”时期的北大立有不嫖不赌不娶妾禁约的进德会,它的出现就是有相当针对性的。曾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注:参见胡适《〈吴虞文录〉序》,《胡适散文选集》第8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 )吴虞在“五四”落潮后很快变得判若两人。为了排遣寂寞,出入于买笑场所倚红偎翠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更为出格的是这位昔日的“老英雄”竟然将他狎妓的淫靡诗抄录成册供人欣赏。1924年4月9日,《晨报副刊》赫然登出吴虞以吴吾的名义写给妓女娇寓的“儿女诗”。其中如“英雄若是无儿女,青史河山更寂寥”,“烟水千年香不断,怪来名士爱南朝”等句,集中而又形象地表露了吴虞自呜得意自命风雅的无聊情调。吴虞的事例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中不具有普遍性,但从近代以来一些由急进转向消沉甚至复古倒退的文人的行为看来,他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不管怎样,作为“五四”文人,他的结局起码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思索。现代作家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吸收以及对传统文人包括具有异端精神的古代名士行为风度的摹仿,不应该是无条件的,必定要接受现代思想意识的衡量取舍,反之,他们很可能像吴虞那样不自觉地回到了曾令他们不堪的旧文人堆里去了。
由于受《沉沦》的影响,“五四”其他一些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与郁达夫相似的思想情调。王以仁的小说集《孤雁》、章衣萍的《春暮之夜》、林如稷的《流霰》、《将过去》,陈炜谟的《茫然》、《轻雾》等小说,都从不同的角度多少涉及到主人公醉酒与狎妓的描述。和郁达夫一样,王以仁他们也是想以世俗最为敏感的反叛方式来对抗在他们看来最黑暗、压抑的环境,来表明他们反抗封建礼教、肯定人的正常欲求的立场。但是,在他们的描述中,仍然或隐或现地披露了他们心灵深处无以消解的那种传统文人怀才不遇、自暴自弃的情绪。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文人如写了《性的屈服者》等小说的张资平,在前期尽管也有一些畸恋、多角恋的展示,却尚能遵循“五四”应有的游戏规则,而到后来却渐渐在反封建“禁欲”的旗号下,贩卖起封建男权社会的陈腐货色,那种着意渲染动物式生理冲动的游戏轻薄的态度,是“五四”文人“放达”范畴最具危害性的成分。
魏晋名士的“放达”是与他们种种为世瞩目的“异行”相表里的。嗜酒荒放、长醉不醒,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目的不外乎傲世绝俗。就像能为青白眼的阮籍对礼俗之士投以白眼,“五四”有些作家对世上最大的俗物——金钱予以了极度的蔑视。郁达夫将钞票置于鞋底,借此满足“受足了金钱迫害”“对金钱复仇的心思”(《还乡记》);郭沫若把一千元汇票扔在地板上狠狠踏上几脚,表示不甘受“金钱的魔鬼”“蹂躏”的决心(《漂流三部曲》)。此类视钱财为仇敌的举动虽然可解气泄愤,却少有魏晋名士的那种自得和轻松。以穷骄人,以穷示傲,是郁达夫、郭沫若等人不得不为之的姿态,这与许杰“啊!没有钱的人,简直是不该做人,简直不是人!”的愤慨如出一辙(《醉人的湖风》)。郁达夫、郭沫若,还有王以仁时常把贫窘挂在嘴边,似乎是哭穷,实质却是炫穷,仿佛惟有如此,方可显出他们的尊严。其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五四”文人真实生活的面影,但同时也包含着作家自己浪漫化了的虚拟和夸张。这符合郁达夫们一贯的“放达”作风,也是自命清高的传统名士物质观、金钱观潜在影响的结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轻利,“君子固穷”,这类价值准则可谓源远流长。对过去早已有之而“五四”创作中仍然常见的“哭穷”——“炫穷”现象,当时不少人曾表示过反感。沈雁冰就认为这是“旧的魔鬼”在扰乱“一般青年”的“灵魂”,此类牢骚不过是一种“名士派”特别的“风流腔调”(注:参见沈雁冰《什么是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57页,郑振铎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影印版。)。刘半农态度更为激烈,他说:“叫悲哀最可以博得人家的怜悯,所以身上穿的是狐皮袍,口里咬的是最讲究的外国烟,而笔下悲鸣,却不妨说穷得三天三夜没吃着饭。”(注: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第68页,周作人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影印版。)无论是郁达夫、郭沫若, 还是王以仁以及其他什么“五四”作家,他们的穷窘困顿绝不至于到了危及生命的绝境。在《“碰壁”之后》一文中,鲁迅也认为:“古人‘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所以待到磨墨吮笔,说什么‘饥来驱我去——’的陶徵士,其时候或者偏已很有些醉意了。”尚有几亩地的陶潜尚且如此,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哭穷”——“炫穷”,也不过是“五四”这些不无“名士气”的作家在精神上尚有良好感觉、在物质上尚能维持并有一定余裕时的一种“放达”行为,其目的和魏晋名士的傲世绝俗类似,不同的是“世”与“俗”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洗涤,为古代清高之士鄙薄的金钱越来越变成万能的法宝。到郁达夫、郭沫若生活的时代,随着资本工业势力的侵入,文人由经济困压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确实也已今非昔比。郁达夫他们的“哭穷”——“炫穷”实际上正是他们既不愿为金钱支配又不得不为其左右的矛盾心理的印证。
在“五四”作家群中,郁达夫无疑是最具任诞气质的一个,但唯一曾被列入《异行传》的现代文人却是徐玉诺(注:参见张默生《记怪诗人徐玉诺》,《异行传》第114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 一个小说、诗歌都有建树的“五四”作家。他的“放达”,重在真正的无视常规,不拘礼俗,放纵个性。如果说郁达夫的“哭穷——炫穷”的“异行”不无矫情的成分,那么,“具着一副似乎微笑的脸”(周作人语)的徐玉诺的种种“异行”,却是出自天性的自然,是常人无法企及而徐玉诺已经达到的一种境界。无论是他读书时期因不满学校的考试而不作解答以示反对,又画一大圈以示心地光明的天真,还是他为写一小说隆冬大雪之际一路陪人出殡至墓地,丧家走空他却独自匍匐坟边嚎啕不已的执着,都是他“放达”个性的天然流露。至于那个“送客数载”的故事,更是他异于世俗却本于天性的佳话。叶绍钧在谈到他的诗时说:“他并不以作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一样;当感觉强烈,情绪奋兴的时候,他不期然的写了。”(注: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诗话》第2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7月影印版。)原来, 那出色的《将来之花园》也不过是他放纵个性的一个痕迹。他随心所欲决不刻意勉强自己的生活态度,也渗透到他对艺术的把握之中。他身上的“名士气”虽不如郁达夫的意义鲜明直指反叛,但悖离世俗、凸现自我的精神本质却无何区别。当然,徐玉诺的悠然超脱在“五四”及以后的社会环境里,必定是有条件的。作为一个现代作家,他不会对家乡河南兵灾匪患中百姓的呻吟无动于衷,他的诗文里就留下了许多愤激的记录。当国难当头,他率领青年组织宣传抗日之时,仍不忘搜寻半布袋石块以宝物之名赠于一卫国将军,寸土必争之意尽在不言中。这或许就是徐玉诺的“名士气”最具风流的一幕了,蕴含其中的民族意识交融着现代知识分子鲜明的民族情感,也交织着传统文人士子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这样“放达”,完全可以与到南洋后的郁达夫的“壮烈”相媲美。
二
“五四”高潮转瞬即逝,文人“放达”的空间愈益狭小。1925年,周作人在为冯文炳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作序时说:“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阴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当“浮躁凌厉”之气越来越离他远去时,周作人开始向往“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向往“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注:周作人:《十字街头的塔》,《雨天的书》第67页,岳麓书社1987页7月。)的“隐逸”生活。 他虽然声称“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注: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知堂序跋》第13页,岳麓版。),在“五四”高潮期间依旧更近于“叛徒”和“流氓”,是“五四”的退潮滋养了他的“隐逸气”。这和陶潜出现于晋末有些相似。鲁迅说陶渊明“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这才成了“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注: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15页。)。如果说是晋末“篡”“乱”之后相对平静的风气造就了陶潜洁身自好的品格,激发了他避世隐逸的动机,那么,“五四”文人的“隐逸气”,则源于“五四”之后剧烈的社会动荡带给文人的思想困惑和精神迷惘。对周作人经历了“歧路”的徘徊和“寻路”的摸索后生活、艺术态度的转变,郁达夫曾作过这样的评述,他认为:周作人在“遭了三一八的打击以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射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作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益的玩意儿”(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14至15页,上海文艺影印版。)。郁达夫说的是30年代初的周作人,虽然在情感上不无偏袒,或者说彼此有点同病相怜,但基本上还是道出了几分事实真相的。在相当的意义上,这真相不只是属于周作人,也属于他同时代同样具有“隐逸气”的一些“五四”作家。
素朴淡远的山水田园,曾是古代隐逸之士赖以生存的理想空间。“五四”作家因时代环境的局限,不可能像陶渊明真正远离浊世,在幻想的世外桃源度实实在在的自耕自食的生活。但精神的疲倦、情绪的焦虑同样驱使他们去寻求宁静温馨的憩园,寻求内心的平衡。俞平伯于暑热之中游西湖,在“梅妻鹤子”的林逋昔日隐居处看葛岭晨妆,望远山晓日,听雨听雷,“凉随着雨生了,闷因着雷破了”(《孤山听雨》);王世颖去放生日的东湖,“远山平水,看着入胜,胸襟也就跟着步步开拓”,“要在尘嚣中找出干净土来”(《放生日的东湖》)。朱自清“惊诧于梅雨潭的绿”(《绿》),钟敬文感谢西湖的雪景所给予的“心灵深处的欢悦”(《西湖的雪景》),徐祖正沉溺于深山古寺的“清寂”(《山中杂记》),徐蔚南陶醉于山阴道上青山绿水“很少行人”的“清冷”(《山阴道上》)……他们流连忘返在山水花木之间,在对自然的体悟中感受个体生命的意义。借山水以解忧,藉花木以怡情,历代风雅之士屡见不鲜。魏晋时期即既有阮籍、稽康等七贤的竹林之游,又有王羲之等四十余会稽名士的兰亭之会。山水之乐的意义决不仅在对山水的爱好和欣赏,其实质源于文人内心的自觉。可是,忘我的真淡泊不是轻易做得到的,古代只有一个陶潜,而那些仍具“叛徒”面貌的“五四”作家自然也只是将山水景物当作灵魂暂时的避难所。这就像王统照所说的:“偶然得到一时的安静,偶然可以有个往寻旧梦的机会,那么:一颗萋萋的绿草,一杯酽酽的香酩,一声啼鸟,一帘花影,都能使得他从缚紧的、密粘的、耗消精力与戕毁身体的网罗中逃走。”(注:王统照:《阴雨的夏日之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391 页,上海文艺影印版。)大自然的魅力实在是妙不可言。
徜徉于绿草花影,甚至在“野花的瓣上,偷着睡觉”,“隔绝一切的苦恼”(王森然《野花》),毕竟有诸多的时空限制,要逃脱精神的“网罗”,摆脱沉闷的压抑,对于置身书斋的文人来说,最方便不过的是周作人那样信马由缰的“空想”。比如“在江村的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注: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一》第11页,《知堂序跋》,岳麓版。),这种“喝茶”被周作人看作是“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是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注:周作人:《喝茶》,《雨天的书》第49页、48页,岳麓版。)。因为有“空想”,身居京城的西北隅,照样可以听见江南乡间春日黄莺的“翻叫”、勃姑的“换雨”,照样可以回味遥远的故乡野菜的鲜美,感怀在那里坐乌篷船“行动自如,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的“理想的行乐法”(注:周作人:《乌篷船》,《泽泻集》第27页,岳麓书社1987年7月版。)……1928 年以前周作人留下的那些玲珑剔透质朴淡雅的“空想”的结晶,是他“因寂寞,在文字上寻求慰安”(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知堂序跋》第3 页,岳麓版。)的痕迹,更是他在闲情逸趣的抒写中固守“自己的园地”的见证。面对“五四”退潮后的风起云涌,周作人越来越失望地感到“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知堂序跋》第3页,岳麓版。),又由于深信“人类之不齐, 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注:周作人:《〈谈虎集〉后记》,《知堂序跋》第31页,岳麓版。),于是特别执着于独自走路。他称赞冯文炳平淡朴讷的小说,认为那些“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的描写,体现了冯文炳“独立的精神”(注: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知堂序跋》第299页,岳麓版。)。 这种“独立的精神”正是周作人理想中的文人精神。周作人说隐居于西郊农家的废名的文章“很有意味”,而其中“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注:周作人:《〈桃园〉跋》,《知堂序跋》第303页,岳麓版。), 这一客观的指证更适合说明周作人自己。他认定“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注:周作人:《〈燕知草〉跋》,《知堂序跋》第318 页,岳麓版。),因而情趣上愈益向闲适倾倒,行为上愈益向“十字街头的塔”里退却,也就十分自然。周作人一再声称喜欢陶渊明,喜欢他“对于生活的态度”,喜欢他的“气味”。而在东篱下采菊的陶潜尚且也有喜说荆轲之时,三十年代之前的周作人尽管“隐逸气”开始“很占了势力”,却没有“真的像瓶子那样闭起嘴来”(注:周作人:《怎么说才好》,《猛虎集》第296页,上海书店1987年9月影印版。),时常也有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举,这看来自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也不难理解。
山水风物,田园果林,其旷洁高远,其宁静平和,确实可令人神清气爽、心无旁鹜。但山水风物毕竟不是根治文人烦闷、抑郁、迷茫等精神病痛的特效药。所以,夏丐尊会感慨:“想享用自然的乐趣,结果做了自然的奴隶。”(注:夏丐尊:《长闲》,《夏丐尊散文全编》第4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这种“当初万不料及”的新的“苦闷”,正是源于作家原本黯淡的心境。因此,“同是一座山,山也会变了灰色,同是一片水,水也会皱得人心儿不安”(注:王世颖:《放生日的东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第449页, 上海文艺影印版。)。可见,“五四”作家在纪游纪风物中表现出的散发着“隐逸气”的闲情逸致,充其量只是他们被挤压在“前进”与“倒退”的时代夹缝中无计可施权且自慰的反映。“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注:周作人:《〈风雨后谈〉序》,《知堂序跋》第155页,岳麓版。), 这一说法被周作人用来作为他后来人生选择的一个辩解,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但用于揭示“五四”退潮后一些“五四”作家的“隐逸气”的本质,倒是恰如其分的。貌似出世,因为作家中有人特别钦佩诸葛孔明和陶潜的那种“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根底也就在这里。
“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注:周作人:《自己的文章》,《青年界》第10卷第3期,1936年10月出版。), 幽默和闲适是“隐逸气”的一对连体婴儿。中国现代文学的“幽默味”常常是紧随着“闲适味”而来的。作为一种艺术特征,“五四”文学现代意义上的幽默,比如周作人在《前门遇马队记》、《上下身》、《碰伤》等杂感中以反语著称的幽默,意蕴深厚,余味无穷,已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现在谈及的“幽默味”,则是指“五四”一些作家“名士气”的一种表现,一种类似于游戏意味的精神症状。1923年,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序中称自己写了一些“近于游戏的文字”,并说从中“也可以见我的一种脾气”。这种“脾气”在有“骂人”、“说滑稽话”之“真”的《语丝》出世后(注:参见章衣萍《语丝与教育家》,载于《语丝》第58期,1925年12月21日出版。),日益见长并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在小范围内竟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
以周作人等为中坚的“语丝派”文人曾耗费大量笔墨投入与陈西滢为首的“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在揭露对方接受章士钊的津贴一点上,矛头直指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注:《〈语丝〉发刊词》,《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出版。 )的不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然而,这种“不折不挠”里同时也掺杂着“文人意气”的因素。刘半农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中,就有人称陈西滢英文比狄更斯更好一事大加挖苦嘲笑。稍后他又写《奉答陈通伯先生》,答复对方对前文的反应,以三次重复“我并没有说你妹妹说你的英文比Dickens好”煞尾,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此外,刘半农、林语堂、 章衣萍等也因为反感有人奉徐志摩为“诗哲”、“中国的泰戈尔”,反感徐志摩说自己“虽不是音乐家,可爱研究理论的音乐”,专门撰文集中大堆的风凉话、“顽皮话”予以嘲弄(注:参见章衣萍《不行》、刘复《徐志摩先生的耳朵》、林语堂《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等文,分别载于《语丝》第5期,第16期,第63期。)。 这种以个人为攻击目标、以鸡毛蒜皮的琐事为嘲讽因由的论争,有时不得不沦为文人相轻的对骂。《语丝》第63期紧接着刘半农文章之后刊载了署名爱管闲事者列出的《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此表将闻一多、“徐诗哲”、凌叔华、郭沫若等与徐树铮、段祺瑞、章士钊同划在“水平线”以上,将刘半农、周作人、鲁迅与“其它‘学匪’”一起同划在“水平线”以下。严肃的政治分歧、思想分歧衍化成了一场不同派别文人之间互争文学史位置高低的较量。这种意气用事的做法,模糊了本有的思想原则,削弱了论战的政治意义,又因流于油滑显现了自己的空虚与肤浅。“名士气”较重的一些“语丝派”文人在与“绅士味”较浓的陈西滢、徐志摩的争论中,充分展现了他们宁折不弯的硬气,但在他们亢奋举止的背后,恰恰正隐含着他们于书斋一角玩味俏皮远离真正现实的超脱。
因为不满足那种“为严正的滑稽”,周作人特别希望在《语丝》上能多上些“为滑稽的滑稽”(注:参见周作人《滑稽似不多》,载于《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出版。)。在他的倡导下, 有些人开始热衷“可于苦闷中发一笑”的打油诗、滑稽话。尽管其中不无对现实的影射,但因为文人之间自娱互娱的游戏形式,常常陷于无聊。如江绍原《仿近人体骂章川岛》及川岛如法炮制的应答,本意在揭露章士钊、章宗祥,却纠缠于川岛之姓,指桑骂槐的手段操练得得心应手,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二章”精神实质的揭示。林语堂的《劝文豪歌》等也可作如是观。至于钱琴甫等《打油联句十六绝》、郭甲老人《拟古诗上山采蘼芜》、署名狗屁的摹某君新诗《我独在垃圾堆上看不见旁人》等,则更加离谱了。出洋数年搏得一张博士文凭的刘半农回国后写了一篇《老实说了吧》的杂感,揭露当时一些年轻人沽名钓誉的恶习,提出了他“要读书”、“书要整本的读”等劝告。由于刘半农的口气未免刻薄,加上居高临下的导师姿态,文章很快即激起了一些敏感而尚无什么地位的年轻人的愤慨。1926年刘半农的“幽默味”,和几年前与钱玄同一起写“双簧信”的“幽默味”相比,实在大有区别。“喜欢顽皮”的“天性”依旧,不满和反感的对象却从抱残守缺的复古派,变成了和他当初一样活力充沛却难免幼稚而急功近利的年轻人。刘半农“幽默”的变味,直接来自他文化精神的退缩。尚在国外时,他即对老友周作人称林琴南“终是我们的师”(注: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 1924年12月1日出版。)十分赞同, 并表示“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注:刘复:《巴黎通信》,《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30 日出版。)。他“浪子回头”般的“后悔”,正预示着他以后令他的另一个老友鲁迅深为遗憾的退隐。与此同时,刘半农特别感到气味相投的周作人当然更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他自己提出过的“滑稽”主张,在《语丝》上禁不住说了许多“幽默”的“茶话”、“闲话”,其中有不少颇有深意。但是,也有一些杂感的“幽默味”却显得不那么正。在写于“三·一八”惨案后不久的《死法》里,周作人照样用“趣味之文”的笔调,大谈“世间死法”,考证“非命的好处”,寓沉痛于油滑之中。他以为“幽默”可以无所不在,这符合他关于“‘幽默’即为‘中庸’的表现”(注:周作人:《上海气》,《谈龙集》第159页,上海书店1987年9月影印版。)的解释。然而,凭心而论,“三·一八”惨案中无辜的死者怎么可以随便被拈来作为说明“死法”的例证和揶揄调侃的资料,周作人在惨案发生后也是表现了值得称道的义愤的,但《死法》却无论如何同时也披露了他的“中庸”和摇摆。到1928年11月声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为第一要紧”的《闭户读书论》发表,周作人调和了“闲适味”和“幽默味”的“隐逸气”愈益浓厚,渐渐迷住了双眼,困住了身心,最终将他逼向了人生的悬崖。
三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狂”与“狷”,风度有别,内在的精神却别无二致。古代名士派人物以不同于世俗的特立独行来坚守“独善”的人格,“五四”那些散发着或隐或显的“名士气”的文人也以类似的方式表现了他们对古代名士人格精神的亲和。郁达夫对世俗的蔑视,周作人对现实的淡漠,都表现为与所生活的环境保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使人充分展示自我的个性,体现反叛的精神,也可以使人与前进的时代隔离,将自我封闭起来导致窒息。“五四”作家的“名士气”以及他们中国名士风的创作,其可取之处与致命弱点几乎融于一体。
“燕子去了”,“杨柳枯了”,“桃花谢了”,朱自清照样会感到“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的惶恐(《匆匆》),“逝者如斯夫”式的伤时之感千年如一。看到秋天黄叶飘落,钟敬文会觉得“孤冷清寒”、“零落衰飒”(《黄叶小谈》);望见夏日“青青的田禾里”“浮出咻咻的小鸭”(《夏日农村杂句》),何植三又会想象是田园牧歌式的“农家乐”。因景而悲、因物而喜,伤春悲秋,多愁善感,苦闷彷徨中的“五四”作家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感染了旧式才子的弱不禁风。他们大多善饮,失意时以酒浇愁,得意时以酒尽欢;他们无不好游,登山临水,访古问今,好不快活。生活的幽雅诗意尽在其中。毋庸讳言,振臂高呼、摇旗呐喊是“五四”文人行为方式的主导,但是鲁迅也承认“劳作和战斗之前”需要“愉快”和“休息”的“准备”(注:参见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7页。),周作人更相信“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注: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雨天的书》第47页,岳麓版。)。所以,闲暇之余翻翻昔日的旧课,摩挲摩挲过去的旧物,也实属平常。或许有人喜欢读点儿古书,抄点儿古碑,作点儿古代民俗考,发发思古之幽情;或许有人喜欢念点儿佛经,谈点儿老庄之道,挖掘挖掘宗教的源流。在古意盎然的气氛中,感受悠闲,也感受怅惘,前人的流风余韵在回味中久久不能散去。“五四”作家无疑是一代新文人,但他们毕竟刚刚才脱离旧文人的身分,思想进程中的犹豫和徘徊容易诱发他们情感上的怀旧,这自然也会影响到趣味上的偏向。
古代名士派人物不思衣食温饱的风雅做派,是以坚厚的物质基础为生存前提的。可是,“五四”作家却大多是破落户的子弟,精神的独立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去自谋其食,必定去饱尝生活的艰辛。于是,在情绪上,他们常常会有受挫的表现,这是他们大不同于古代名士风度的地方。倪贻德因昔日豪门的“零落”而感伤,内心执着于“重振门庭”的幻想(《零落》)。与其说是因为“钟鸣鼎食”的门庭的败落而失落,不如说是因为祖辈那种于亭台楼阁边伺花弄草、泼墨挥毫、结交四方名士诗酒风流的生活,和与此相关的“高雅”、“风趣”神韵的一去不复返,而情不自禁地黯然神伤。郁达夫感叹自己无法衣锦还乡的落拓,忆起“没有去国之先,在岸边花艇里,金尊檀板,也曾醉眠过几场”的潇洒,明月如故,不由对“依旧在那里助长人生的乐趣”的“越郡的鸡酒,佐酒的歌姬”产生愤懑之感(《还乡后记》)。这种愤懑显然是以对旧日“人生的乐趣”的认同为依托的。丰子恺怀念秋日的“围炉、拥衾、浴日”的惬意(《秋》),冯沅君向往清晨能一边在“被筒中展转”,一边随口吟诵李清照“扶手酒醒别是闲滋味”的舒心(《闲暇与文艺》),夏丐尊手捧《陶集》,孜孜以求“心有常闲”的境界(《长闲》)。生活中之不得或难得,遂成为念兹在兹的玄想。人生的失意,谁都难免。“五四”作家的精神痛苦有多种多样,但其中因昔日风光不再而生的失意,也是确确实实的。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的这种精神症状未免陈旧颓落,但他们对过去生活难以平复的某种惋惜之情,毕竟是他们作为站在新旧时代分水线上的一代人文化心理变革中留下的真实足迹,是他们人格结构中不可缺失的部分。
“名士气”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以古代文人“独善其身”的人格修养为基础的。这种道德追求在整体上毕竟有别于“五四”的时代精神。因此,“名士气”作家的有些创作,在一定的程度上偏离了“五四”“人的文学”主题,也就在所难免。闲愁泛滥,闲情丛生,“平民文学”的信奉者有时却染上“贵族”的气味;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刚刚确立的“自我”人格中包含的社会责任感有时旁落他处;“生命无常”,“一切都是梦幻”,失意的人生感怀中也透露出对禅佛“色空”的滞著。这些负面的因素常常遮蔽了“五四”文学的现代色彩,也削弱了“名士气”内涵中“反抗”的力度。“独善”的前提是与现存秩序保持距离,“五四”有些作家在表现自我个性时正是过分看重了与现实保持距离的自我。矫枉过正的结果非但无助于自我人格的发展,反而模糊了个性解放的真正涵义。这一点,也是毋庸讳言的。
“五四”文人意识深层的恋旧,同时也折射到审美趣味的选择之中。香草美人,是自古以来骚人墨客用以寄托功名的栖息物。“五四”作家当然不再持同样的胸怀,但美女的意像依然是其中一些文人理想中真善美的化身。郁达夫在坊陌之间寻求慰藉,他即便没有将对女人肉体的占有作为自己人生成功的证明,却至少也是把获得女性的爱情当作他人生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种极具“五四”时代特征的表现,在不同层面上显示出传统的色彩。美女的形象,既是情感世界中快乐的源泉,又是审美境界里完美含义的载体。俞平伯在读过白采的长诗《羸疾者的爱》后,不禁感叹“如逢佳丽”,而白采回复对方的称赞时则也相应谦逊地表示“可惜尘姿陋质,不足当君宠爱耳”(注:俞平伯:《与白采书》,《杂拌儿》第144页、14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这类将佳作喻为佳人的比喻,在古代文人那里常见不鲜,几乎是约定俗成的修辞法。在“五四”作家中,朱自清是最擅长用美女的形象来涵盖包容大自然的优美的。在《荷塘月色》里,他以“亭亭的舞女”之美、“刚出浴的美人”之美,“荡着小船,唱着艳歌”的采莲的“少年的女子”之美,来烘托荷塘月色的朦胧幽静。与此相似,在《绿》中,他又以少妇“拖着裙幅”的姿态,“初恋的处女的心”和“最嫩的皮肤”以及“轻盈的舞女”、“善歌的盲妹”、“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来形容梅雨潭的“绿”。朱自清将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受、带来心灵安慰的一切美的事物都蕴涵于女性之美中,将女性之美推至于理想化的极端。在艺术形态的表现上,朱自清与郁达夫大异其趣,而精神世界的一角却同样积淀着自屈原以降千百年文人士子始终解不开的“美女”情结。他们虽然不再以美人香草比作君王,也不再将沉浮于男人的擅宠与冷落中的女人喻为命运坎坷的文人自己,但是,他们照样将自己的情绪指向、趣味偏好融入抽象的美人形象。这种审美心理上无意识的偏执,正是“五四”作家审美思维势态的正常表露,有其深刻的文化内蕴作为前提和基础。
郁达夫放诞,朱自清拘谨。两人个性迥异,创作风格也无法类比,但情调的压抑和感伤却如出一辙。这不仅仅反映在他们借抽象的女性意像来演绎人生的失意和得意的概念之时,更无时无刻不渗透在他们的肌骨血液里,跳跃在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五四”文人的个性大致也不出郁达夫式的“狂”和朱自清式的“狷”两类,作品的风格也与此相应。但“五四”所谓的“狂”,并不是指艺术世界里豁达豪放、阳刚大气的壮美的展露。古代“放达”之士的豪迈乐观即使以放浪形骸著称的郁达夫也未能真正承袭,他反倒将古人的伤感模仿得维妙维肖。除写了《女神》的郭沫若等少数作家的部分作品之外,“五四”文人大多擅长细微柔弱、幽静安谧境界的刻画,春花秋月,草木虫鱼,桨声灯影,远山近水,即使较为开阔的画面,也难得形成汪洋恣肆的壮阔景象。这种“五四”特有的总体审美风格上的“阴盛阳衰”,单纯用作家个人气质的因素是无法说明的。壮怀激烈气吞日月的阳刚之美是充分的自信以及与此相伴的雄心胆魄催生而来的。对于“五四”作家而言,既然不能真正超脱于现实,现实加予他们的精神痛苦必定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因此,郁达夫只能自我怜悯身世之飘零,爱情之难得,徐玉诺也只能牵挂着在绝境中挣扎的乡人的生死。他们虽然在个人行为上傲世蔑俗狂放不羁,心灵深处的辛酸苦涩却不得不借助于创作予以发露宣泄,或沉郁,或悲戚,反正与阳刚大气无缘。“五四”退潮后,新文学作家苦闷彷徨的情绪弥漫丛生,必定也波及到他们对审美风格的把握,这种影响也许是潜在的,却又是具有普泛性的。朱自清、俞平伯借荷塘月色、桨声灯影来排遣内心的烦闷,周作人、废名在幻想的田园里啜苦茶、听鸟鸣,“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五四”作家的“名士气”不一,艺术视野和审美角度却常常雷同。
魏晋名士之所以为“名士”,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他们都出自名门。无论“仕”与“隐”,都改变不了家族带给他们的显赫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又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些名士优越的精神地位。魏晋以后的名士派人物也许不可能再以王、谢这样的豪门巨族为傲,但他们的出身不是与官场有瓜葛的官宦世家,至少也是祖上留有田宅的书香门第。他们天生拥有的社会地位依然能使他们始终拥有精神上的优越感。所谓名士的清高,不管是离经叛道的狂者的清高,还是离群索居的狷者的清高,都不过是这些名士派人物因所处的高于一般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自然而然产生的精神上的一种奢华。“五四”前后,文人作家的社会背景已大不同于过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出身早已无法与前辈相比,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也使他们不再寄希望于家族的荣光。然而,“五四”作家精神上的优越感较之过去的那些名士派人物却有增无减。他们照样清高,哪怕是自命清高,他们照样狂傲,哪怕是佯装狂傲。惟其如此,他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作为文人的价值。尤其是那些以启蒙者自居的“五四”新文学作家,更是从自己的精神优越感中汲取动力。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基本确定了文人应有的精神地位,即便是一介寒士,仍然会被认为,起码是自以为在精神境界上高于拥有万贯家财却目不识丁的土财主。这也许就是中国文人特有的精神魅力。“五四”作家如郁达夫等人常常为“零余者”的身分自艾自怜,但骨子里透出的却是文人的高傲。“五四”知识者包括“五四”作家占据了那个时代精神领袖的地位,他们的精神优越感几乎无以伦比。在这种无以伦比的精神优越感背后,正蕴涵着中国千百年文化传统对于文人以及文人所代表的文化一以贯之的尊重,“五四”作家的“名士气”正生存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五四”的“中国名士风”的创作也就是这种文化土壤里结出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