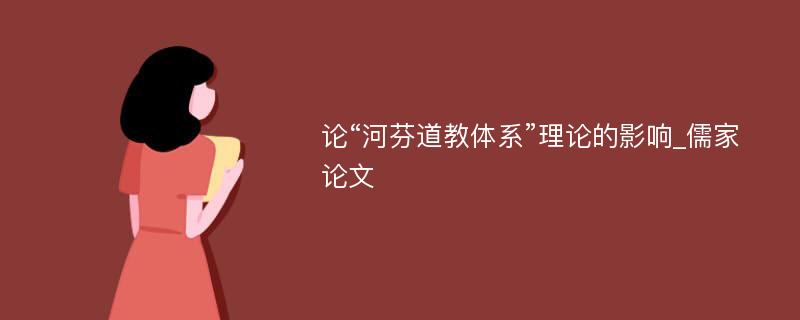
浅论“河汾道统”说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统论文,浅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哲学史上,历代哲学家对其前代或当代的哲学思想都作过“分其宗旨,别其源流”的梳理,他们有的从一个哲学家对一种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作了探究,有的则从一个学派在时代上或在地域上的影响作了分疏。这一工作,对一个学派或一种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后世学者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哲学史上,首先对学派进行褒贬的是《庄子·天下》篇,之后,又有《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史记·论六家要旨》等著作对先秦各学派及其哲学思想作了相对公允的评判。两汉时期,随着儒学地位的进一步确立,“独尊儒术”的提出,使得哲学家对学派的梳理专注于儒学一脉,董仲舒当时就指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开“儒学道统”之端绪。到唐宋时,便形成了流行于当时学界的“道统说”。“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注:《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与陆子静·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道统说”的提出,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儒家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规范了以后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然而,“道统说”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朱熹提出系统的“道统说”以前,韩愈在《原道》中已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统系,在这一点上,韩愈可以说是“道统说”的肇基者,他为儒家“道统说”勾勒出主流,为以后“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范式。“河汾道统”就是在韩愈这一范式影响下提出的,它上继韩愈,下启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说:“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尽管梁启超是在判定《文中子》为伪书时如是说(《文中子》一书不伪已成不争的事实,参见尹协理、魏明著《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但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河汾道统”说在当时之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可以这样说,王通“三教可一”思想及“河汾道统”把王通作为“道统”中的成员,直接推进了宋明理学思想的形成,开启了朱熹“道统论”的提出。如果说韩愈的“道统论”具有正统意识,朱熹的“道统说”具有弘道意识的话,那么,“河汾道统”说则既具有正统意识,也具有弘道意识。今天,对“河汾道统”说的提出及其影响作进一步的梳理,于深化中国哲学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再认识不无裨益。
一、“河汾道统”之提出
隋唐时期,随着魏晋南北朝对佛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佛教已是宗派林立,同时,佛家大量汲取儒家的“人性论”和“内圣”之道,又兼取道家“全身养性”的思想资料,大倡“心性本觉”、“方便成佛”法门,使印度佛教具有了中国本土传统的学术趣味,而此时儒学“师说纷纭,无所取正”,使得儒学呈现出衰败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王通以儒学为主,杂取佛教和道教思想,并力倡儒、释、道“三教可一”,其弟子“河汾门下”相与呼应,呈现了意欲使儒家学说取得一统的学术气度,王通及其弟子在彰显儒家思想的同时,对当时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亦作出了卓著的贡献。缘此,有人提出“河汾道统”说。
“河汾道统”说提出前,韩愈在《原道》中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精,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注: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由此观之,韩愈所指出的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把这一统系统一起来的是孔子的“仁”,这就是韩愈所指的“道”。这个“道”的核心是博爱,亦即孔子“仁者爱人”,做到这一点便是“德”,这里,韩愈阐释了孔子“仁”的全部哲学内涵:“仁”统摄了“智”又统摄了“勇”,还统摄了“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统摄了“恭、宽、信、敏、慧”(《论语·阳货》)等,“凡是以前属于‘德’的那些子目,都被孔子的‘仁’所统摄了。《庄子·缮性》曰:‘德无不容,仁也。’孔子的‘仁’,确是‘德无不容’,所以宋儒干脆称‘仁’为‘全德之名’”(注: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所以,韩愈所指的“道统”是专指儒家而言的,既为辟佛,故没有羼杂任何佛老的成分在内,是专指儒家主流思想言。所以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注:《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的评价。
王通虽没有明确提出“道统”问题,但他在儒学衰落的时候,力倡恢复尧舜、周公、孔子之“道”,并且以周公、孔子自喻。他竭力抬高孔子的地位,决心继承周公、孔子之道。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乃有“河汾道统”一说。陈叔达在与王绩的一封信中说:“……是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盖获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唐文粹》卷八十二《答王绩书》)唐末皮日休指出:“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贞观、开元,其传者醨,其继者浅,……文中于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注:《皮子文薮》卷九《请韩文公配饷太学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里,皮日休所说的儒家传道世系是:孔子—孟子—荀子—王通—韩愈。宋初的柳开对儒家的道统传道世系也作了论述,他说:“昔先师夫子,大圣人也,……厥后寝微,扬、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孟轲氏没,圣人之道火于秦,黄老于汉。天知其是也,再生扬雄氏以正之,圣人之道复明焉。……扬雄氏没,佛于魏、隋之间,讹乱纷纷,……重生王通氏以明之,……出百余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明于唐焉。……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复先师夫子之道也。”(注:《河东集》卷六《答臧丙第一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说:“隋之时,王仲淹于河汾间,务继孔子以续《六经》,大出于世,实为圣人矣。”(注:《河东集》卷二《补亡先生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柳开认为儒家的道统传道世系是: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不管是皮日休还是柳开,他们所提出的“道统”说都包括王通,又因王通传道授徒主要在“河汾”地区,所以,他们所说的“道统”世系,被人们称之为“河汾道统”。
二、“河汾道统”之地位
对于“河汾道统”说,近世曾因王通及《文中子》的真伪争论而为人们所忽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觏,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呜呼!读者当知,古今妄人非仅一王通,世所传墓志、家传、行状之属,汗牛充栋。其有异于《文中子》者恐不过程度问题耳。”(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梁氏此语一出,使得相传一千多年的“河汾道统”在责伪声中湮没。直到今人尹协理、魏明著《王通论》,为之钩沉,但因对大家、名家崇拜的普遍心理,多年来在人们思想中已形成了学术定式,这一钩沉并没有引起多少学人的注意。实为哲学史上一件憾事!
之所以称之为“河汾道统”,就是缘于王通是河汾地区人,其学术活动主要在该地,故给“河汾道统”定位,亦应从王通及其哲学思想的分析入手。王通出生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卒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中国哲学史上,此时正是儒、佛、道竞相发展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一度使儒家学说衰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在“三教鼎立”的情况下,王通既没有去反佛,也没有去斥道,而是提出“三教可一”,这一思想为以后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开了规模,定了范式,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王通作为大哲学家的真知灼见。
所以,后世儒家学者对王通的评价是十分高的。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认为,王通和孔子、孟子、扬雄、韩愈一样,都是圣贤,是王通挽救了被毁坏了的“王纲”和被遗弃了的“人伦”,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王道失叙,礼坏乐崩,三纲将绝,彝伦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删《诗》、《书》,定《礼》、《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注:《徂徕先生集》卷十三《上蔡副枢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说:“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扬子,扬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其验欤?孔子、孟子、扬子、吏部,皆不虚生也。存厥道于亿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注:《徂徕先生集》卷十二《上赵先生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还说:“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注:《徂徕先生集》卷七《尊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石介认为,尧舜之道的道统就是经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五人传下来的。象数派理学家邵康节也认为,王通虽然未能成圣,但他作为圣人的弟子是没有问题的:“传成,文正公问予大父康节何如。康节赞之曰:‘……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不废是,瑕不掩瑜,虽未至于圣,其圣人之徒欤?’”(邵博《河南邵氏见闻后录》卷四)理学家程颐则把王通的地位放在荀子和扬雄之上,“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也。’”(注:《二程遗书》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功利派代表人物叶适和陈亮也认为王通是传圣人之道而为之:“夫通既退不用矣,于是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正礼乐。其能以圣人之心处后世之变者乎!其见仁、义、礼、乐之未尝不行于天下者乎!其言曰;‘读《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孝,入则悌,多识治乱之情。’渊乎哉其明于道者之言乎!以道观世,则以无适而非道。后世之自绝于唐、虞、三代也,是未能以道观之者也。……善哉!圣人复起,必从之矣。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仁、义、礼、乐绳绳乎其在天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无不可矣。虽然,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孰知其道之在焉!”(注:《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八,中华书局1961年版。)叶适认为,王通从退隐以后,续《书》,续《诗》,修《元经》,赞《易》,就是用圣人之道教行天下,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孔子“仁、义、礼、乐”之道,从而使人们能“以道观世”,倘有圣人复出,也一定遵从他的这一思想。与叶适同时的哲学家陈亮也指出:“初,文中子讲道河汾,门人咸有记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盖尝参取之矣。薛收、姚义始缀而名之曰《中说》,凡一百余纸,无篇目卷第,藏王氏家。……盖文中子没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翼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河汾矣。虽受经未必尽如所传,而讲论不可谓无也。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不然,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及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修诸人,始知好其书。至本朝阮氏、龚氏、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独伊川程氏以为隐君子,称其书胜荀扬。荀扬非伦也;仲淹岂隐者哉!犹未为尽仲淹者。”(注:《陈亮集·类次文中子引》卷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陈亮认为,《中说》是王通在河汾地讲道时,由其弟子董常、程元等人记录其言语而成书的,藏于王通家中。李渊建唐初期,吸收了大批的文人雅士,这些文人雅士往来于河汾之间,虽然所接受的不是王通的全部思想,但他们的讲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王通思想的影响。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十分赞赏王通的哲学思想:“问荀扬王韩四子。曰:‘凡人著书,须自有个作用处。或流于申韩,或归于黄老,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不可一律观。且如王通这人,于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处,极见得分晓,只是于这作用晓得处却有病。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故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于大体处有所欠缺,所以如此!若更晓得高处一著,那里得来!只细看它书,便见他极有好处,非特荀扬道不到,虽韩退之也道不到。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功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仔细读书。他只见圣人有个六经,便欲别做一本六经,将圣人腔子填满里面。若是仔细读书,知圣人所说义理之无穷,自然无工夫闲做。他死时极后生,只得三十余岁。他却火急要做许多事。”(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朱熹认为,王通对世故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等认识深刻(主要指王通对儒、佛、道三教各有所识,并能指出三教各自的优点),对仁义礼乐的作用也落到实处,在这一方面,韩愈是不及王通的。朱熹所说王通之“病”是指其缺乏对“义理”的阐释。理学家陆九渊对王通的思想也甚是推崇,“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轲与焉。荀子去孟子未远,观其言,甚尊孔子,严王霸之辨,隆师隆礼,则其学必有所传,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轲,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张,又皆斥以贱儒。则所师者果何人?而所传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轲、子夏、子游、子张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说,而举无足稽耶?抑亦有当考而论之者耶?老庄盖后世所谓异端者。传记所载,老子盖出于夫子之前,然不闻夫子有辟之之说。孟子亦不辟老子,独扬朱之学,考其源流,则出于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辞,略不及于老氏何耶?至扬子始言‘老子槌提仁义,灭绝礼乐,吾无取焉耳’,然又有取于其言道德。韩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中国,在扬子之后。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其道之行乎中国始于梁,至唐而盛。韩愈辟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通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注:《陆九渊集》卷二十四《策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陆九渊认为,孟子以后,儒家学说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人,从荀子的《非十二子》及其言论看,荀子甚尊孔子,他的学说传自孔子;至于扬雄,虽提出“老子槌提仁义,灭绝礼乐,吾无取焉耳”,但他又援引和吸收了老子关于“道德”的说教,从传记的记载看,老子大约出生在孔子之前,当时,孔子思想与老子思想也没有相互抵触的说法,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事实,已为一九九三年十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墓竹简所证实:“……这主要表现在《老子》并无直接反对仁义学说的明证,联系今传本的某些内容,反而可以认为道之道德与儒之仁义,在老子那儿是并存贯通的,当然在二者的关系中道德是根本,仁义则是道德的内涵之一。”(注: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第69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佛教传入中国是扬雄以后的事,韩愈作《原道》,目的是为了排斥佛教,但收效不大;王通则主张儒、佛、道“三教可一”,希望“三教”得以统一。
从朱熹与陆九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对与“荀扬王韩”给予很大的关注,之所以把“荀扬王韩”一起讨论,是因为他们皆取了唐末皮日休和宋初柳开的“河汾道统”说,并把两种说法杂糅到一起,皮日休的“河汾道统”世系是:孔子—孟子—荀子—王通—韩愈,柳开的“河汾道统”传道世系是: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朱熹与陆九渊在谈论儒家思想时,是合二人之说而论之。明嘉靖九年,给事中张九功和大学士张璁提议,后由礼部裁定,把王通增入从祀孔庙之列,从祀的次序是:“董仲舒、后苍、杜之春、王通、韩愈、胡瑗、周敦颐、程颢、欧阳修、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扬时、胡安国、朱熹、张拭、陆九渊、吕祖谦、蔡沈、真德秀、许衡”(注:《明史》卷五十《礼记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说明王通的哲学思想及其所开创的“河汾道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河汾道统”说在中国哲学史上,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三、“河汾道统”之影响
有趣的是,儒家的道统说传到朱熹时,为了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朱熹不仅把王通排斥出其道统外,而且把道统说的肇基者韩愈也排斥在传道世系之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影响千余年的“河汾道统”说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道统说的发展及其内部的争论,而且对于其后儒学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河汾道统”说对后世的影响之大,首先在于王通的哲学思想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首先,从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争论愈来愈激烈,在争论过程中,佛教和道教的影响逐渐强大,地位也愈来愈高,尤其是佛教,在梁武帝时曾被尊为国教,以呈现了压倒儒家之势,改造传统儒学已成为当时急迫的任务,由此人们开始探索改造儒学的方案。在王通以前,虽有人提出“三教并用”、“三教平等”等主张,但他们大都不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也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他们有的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有的站在道教的立场上,那些站在儒家立场上的人,又拒绝接受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是主张排佛、毁佛、灭佛。只有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明确地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张:“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注:《中说·问易第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洪范谠义》即《皇极谠义》,是王通之祖安康献公王一所作,其书虽佚,但从书名可以推知是书为解释“皇极”之作,据清代学者俞正燮所说,“皇极”当指“中道”,“极,中也。此达诂。《吕刑》云:‘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下云:‘属于五极,咸中有庆’,言属于五刑之中,则皆中矣,故有庆也。中、极互出,古人复文相避多如此。”(注:《癸巳存稿》卷一《极中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初李光地也认为“皇极”即“中道”,他说:“《河图》、《洛书》所谓太极、皇极者,皆以中五之最中之一点当之。”(注:《榕村全集》卷二十八《复发示图象第四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说:“道以中为至,故极者,至也,中也。”(注:《榕村全集》卷一《观澜集·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通在读《洪范谠义》时,受其影响,将中道思想应用在对待儒、佛、道三教的态度上,提出“三教可一”。王通“三教可一”的思想,既为宋明理学皆取佛道二教思想开了先河,也为改造儒家学说指明了路径。其次,王通率先把“穷理、尽性”引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成为后来宋明理学的主要特征和核心范畴。“薛收曰:‘敢问天神、人鬼何谓也?周公其达乎?’子曰:‘大哉,周公!远则冥诸心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盖尊而远之也,故以祀礼接焉。近则求诸己也。己者,非他也,尽性者也,卒归之于人。推鬼于人,盖引而敬之,故以饷礼接焉。古者观盥而不荐,思过半矣。’”(注:《中说·立命第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王通也明确地提出“正心”说,他极力主张先“正君臣之心”,然后才可以“化人”。他要求人们“至心为之内”,要用诗“正性”,要“推之以诚,行之以恭”,要“明内而齐外”,从而做到“家道正而天下正”。这一理论也就是后来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最后,在人性论方面,王通认为,性是“五常”之本,先天为善,而情有不善,所以要以性制情,并将《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引入性情修养论中,从而指出“人心”与“道心”的对立。此外,王通也明确地提出“道”与“欲”、“道”与“利”、“德”与“功”等一系列范畴,为以后宋明理学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河汾道统”说对后世的影响之大,其次在于它提出的目的,不同于韩愈的“道统”说。我们不得不承认,韩愈的道统说提出以前,佛教内部已经有“灯灯相传”的“传灯录”,这种“灯灯相传”的佛家传钵世系,使得佛家教派师承清晰明朗,从而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和繁荣。受佛家“传灯录”的启发,韩愈提出道统说,目的也正是为了排斥佛教,他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扬,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注: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韩愈提出“道统”说的目的是为了把佛教和道教与儒家区别开来,佛教的法统与儒家的道统是不同的,儒家的道统起自尧舜,要比佛家的释迦牟尼要早,佛教是外来的思想,儒家道统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河汾道统”的提出不同于韩愈的道统说,不管是皮日休的“河汾道统”说,还是柳开的“河汾道统”说,他们所列的儒学世系都包括王通,虽说皮日休与柳开也是为了与佛、道二教对抗,但把王通列入,说明他们是赞同王通“三教可一”的哲学思想的,从中也可以看出,皮日休和柳开是继王通之后,继续探索儒家的革新和发展之路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后世“荀扬王韩”并称,使“河汾道统”为以后哲学家、思想家们所乐谈不休。
“河汾道统”说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还在于它成为其后哲学家们争论的内容之一。从朱熹与浙东事功派的辩论中可窥其一斑。辩论虽然围绕“义与利”、“理与欲”、“王与霸”展开,但辩论产生的分歧,主要源于他们对“道统”的不同认识。朱熹认为,两汉和唐的统治者所实行的是霸道,而不是王道,所以两汉不足采,也不能祖述尧舜,不应该赞扬。朱熹认为,“道”是超乎自然与社会之上的一种先验的道德,它“非人之能所预”,对此只能默默体悟,这种先验的道德就是尧、舜、禹、周公、孔子所传之道;这个圣传之道,是亘古常在的“不灭之物”,因为尧、舜、禹三王有义理之心,所以它行于三代是王道;可是,由于汉祖、唐宗有利欲之心,行的是霸道,所以汉、唐以下一千五百年却不能把它体现为人道,他与陈亮辩论时说:“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之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贯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为什么“道”在汉、唐离开人而不能体现为人道呢?朱熹又说:“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此汉唐之治所以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注:《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寄陈恭甫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是朱熹回答陈亮“道不可舍人而独运”时说的,朱熹认为,“道”虽然是运行无穷、永恒地存在着的,但如果人们不以义理之心去体验,就不会与天地之心相合,这不等于说“道”不存在,只能说是未把它体验为人道。人与道的关系是:人有赖于道,而不是道有赖于人。因为汉、唐人有欲,所以他们不能把天道体验为人道。从而汉唐就不能“无愧于三代”了。永嘉学者叶适与朱熹就这一话题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所以,朱熹在两汉问题上,既批评了王通:“……既不自知其学之不足以为周、孔,又不知两汉之不足以为三王,而徒欲以是区区者比而效之于形似影响之间,傲然自谓足以承千圣而绍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儿童之一戏。又适以是而自纳于吴楚僭王之诛,使夫后世知道之君子虽或有取于其言,而终不能无恨于此,是亦可悲也已。”(注:《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王氏续经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也对永嘉学派叶适等人作了评判:“或曰:‘永嘉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朱熹把王通说成“小土堆”,也是由于对王通赞扬两汉不满,“泰山”喻朱熹所传儒家思想世系,即朱熹所说的“道统”,“小土堆”喻王统思想体系,即其后皮日休、柳开所说“河汾道统”。说永嘉诸公爬“小土堆”而不登“泰山”,说明他们受王通思想影响之深。
最后,“河汾道统”说对后世的影响,还在于它对河汾地域儒家思想的影响。王通系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人,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王通西游长安,通过时任隋内史侍郎的薛道衡引见,拜见一些官员,同时,向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薛道衡与王通同乡,同为今山西万荣县人,薛道衡是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王通是万荣县通化镇人,两地相距不到十公里,薛道衡在当时也为影响较大的学者,从他引见王通一事看,是赞同王通的思想和主张的。他们相互交往,促进了该地儒家思想的繁荣和发展,到明初时,形成了具有地域性质的“河东学派”。王通哲学思想在河汾地的影响,可以从“河东学派”的代表人物薛瑄的哲学思想中得到管窥。同王通一样,薛瑄以继承和发扬儒家道统为己任。他提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至周(敦颐)、程、张(载)、朱”的所谓“圣贤万世所传之道”。同王通一样,薛瑄也认为儒家所谓道统的“道”,就是指“性”或“天地之性”而言,他说:“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曾、思、孟相传之道,又岂外于性哉?”(注:《续录》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说:“圣贤万世所传之道,只是天命之性。”(同上书,卷三)薛瑄在政治上主张行“王道”,以仁义治天下等主要哲学思想与王通也是相同的。在河汾地,薛瑄是继王通以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所以,清代纪昀有云:“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录凡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皋陶汤伊尹莱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许衡薛瑄二十六人,博征经史,各为纪传。复引诸儒之说,附于各条之下,而衷以己说。”(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传记类存目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清朝魏裔介著有《孝经注义》,在著录时把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皋陶汤伊尹莱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许衡薛瑄列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用以说明儒家发展的脉络。我们知道,在明初,由于理学内部的分化,程朱理学式微,在这种状况下,振兴儒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薛瑄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复兴儒学的,他说:“尝读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皆与斯之传者也,而朱子作《大学》、《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继孟氏之统,而不及三子,何邪?盖三子各自为书,或详于性命、道德、象数之微,有非后学造次所能窥测;二程则表章《大学》、《中庸》、《语》、《孟》,述孔门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进,自洒扫应对、孝弟忠信之常,以渐及乎精义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据。此朱子以二程上继孔孟之统,而不及三子欤?然朱子于《太极图》、《通书》,则尊周子;于《西铭》、《正蒙》,则述张子;于《易》则主邵子。又岂不以进修之序,当谨守二程之法;博学之功,又当皆考三子之书邪?及朱子又集《小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是则继二程之统者,朱子也。至许鲁斋专以《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辞,务敦实行,是则继朱子之统者,鲁斋也。”(注:《读书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薛瑄认为,朱熹是继二程之统,而许衡又是继朱子之统的,他所说的儒学道统世系也包含有许衡,清朝魏裔介是在薛瑄道统观的基础上提出其“道统”说的。据史籍记载:“天顺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先圣庙庭。”(注:《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薛瑄本人及其道统思想,在当时就得到官方的肯定,成为正统思想。从弘治中到嘉靖九年,前后二三十年时间,先是薛瑄从祀文庙,接着王通增入从祀孔庙之列,说明统治者对儒学的两汉经学化,魏晋玄学化,到隋末唐初儒学复兴和宋明儒学发展全过程的哲学反思,也是对河汾地域文化和“河汾道统”最有力的肯定。
如果我们把唐末皮日休和宋初柳开的“道统”说称之为“河汾道统”的话,清朝魏裔介的儒学世系难道不是理学式微时的“河汾道统”吗?毫无讳言,“河汾道统”说贯穿了北方儒学发展的全过程,是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条主线。
标签:儒家论文; 王通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韩愈论文; 四库全书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论文; 孔子论文; 原道论文; 朱熹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文渊阁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