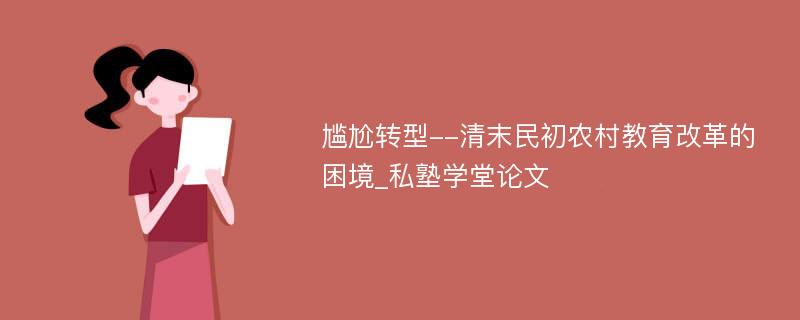
尴尬的转变——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变革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困境论文,乡村论文,尴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55(2011)02-0110-04
清末民初是中国教育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它的发展情况如何,不仅决定了此后几十年间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走向,还对整个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影响。我们看到,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变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清末民初乡村教育遇到了哪些问题?其成因和影响又有哪些?如何认识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的困境?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中国教育史的认识和研究。
1901年,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清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教育改革。源于西方的新教育在沿海口岸城市徘徊了近半个世纪后,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正式进入乡村社会,由此拉开了中国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帷幕。在各级政府和地方人士的努力下,至20世纪上半叶,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取得了一些成绩,学校数与入学人数较晚清都有很大增长,以初等小学为主体的乡村新教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然而,这种建立在西方近代工商业社会基础之上的新教育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从清末开始,围绕着新教育,乡村社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从消极抵制到对簿公堂,再到大规模毁学风潮,各种形式的乡村教育冲突事件不断。日本学者阿部洋从《东方杂志》、《教育杂志》、《顺天时报》、《盛京时报》上的报道和一些方志资料中整理出清末各地乡村发生的毁学事件就有151起之多。①有关教育问题诉讼案件的批文与报导充斥着清末各种报刊。以清末浙江为例,1908年7月至1911年7月这三年间,经浙江提学使司批饬的乡村教育诉讼案件就达256件之多(《浙江教育官报》(1908-1911))。甚至到20世纪20、30年代,新教育仍然无法得到乡村社会的普遍认同。1924年,舒新城在湖南、安徽等地乡村看到,农民们宁愿花费大量的钱财用于迎神赛会等活动而不愿捐给学校;教会学校可以轻而易举地筹集到大量教育经费,而却很少有人愿意捐款给当地的乡村新式学校。由此他得出结论:乡村教育经费匮乏不尽是经济问题,也不在于政府引导不力、管理不善,而在于它“不能引起一般人的信仰”,在于乡间民众对新教育缺乏认同。②
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目标是以近代化学校体制取代传统的以私塾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清末民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把改良和取缔私塾作为促进乡村新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制定的法规、办法、行政命令不可计数。面对各级政府的打压,私塾展现出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例如,1910年浙江县天台县西部9个学区中共有新式学堂数17所(其中简易识字学塾12所),学生共216名,校(塾)均学生12.7名。而同期该地区有私塾133所,学生人数达1941名,塾均学生14.6人。不仅私塾和塾生总数远远多于新式学堂及其学生数,而且私塾的规模也大于学校的规模。③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考察时指出:“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④1936年廖泰初通过对山东汶上县私塾与新学堂发展情况的调查后指出:“洋学在政府的严令下挣扎维持着,私塾则在百姓们的烘托里枝叶繁生,没有政府,洋学早是‘寿终正寝’叫私塾压死了。”⑤私塾的生存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清末民初乡村教育的变革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乡村新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新教育的困境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第一,中国的乡村教育现代化不是传统教育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把源于西方的近现代教育制度自上而下在乡村强制推行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近代乡村新教育是外部强加于中国乡村社会的产物,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权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强有力的政权不仅能够利用自身的权威动员各种资源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保证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而且能够促使基层社会尽可能地执行各项现代化措施。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清末政府,还是后来的民国政府都缺少这种能力。
第二,新教育是西方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产物,是与工商业生产与生活相适应的一种教育制度。而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仍然处于农业社会阶段。新教育在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乃至教学安排等方面,都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格格不入。正如舒新城所言:“我国现行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在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欲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捍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⑥举例来说,乡村新教育的教学安排,完全照搬工业化国家与城市里的做法,学期不按农业生产活动的规律进行调整,结果上课时间往往正是农忙时节,而节假日却是农闲时分。“村中上学的大多数是12岁以上的孩子,他们已到了需要开始实践教育的年龄。在农事活动的日历中有两段空闲的时间,即从1月至4月及7月至9月。但在这段时间里,学校却停学放假。到了人们忙于蚕丝或从事农作的时候,学校却开学上课了。”⑦相比较而言,私塾的个别教学形式较新教育的班级授课制更能适应乡村生活的需要,更易得到乡民的认可。
第三,乡村新教育经费大多取自乡村社会。无论有无子弟在新式学校中接受教育,乡村社会的每一个家庭都要承担一部分教育经费,这与传统私塾的“谁受教育谁出钱”的做法有着很大区别。再加上新的教育财政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在教育经费筹集中的缺位,教育经费征收和使用过程中的腐败行为,乡民往往会把不满迁移到新教育之上,新教育更难获得乡村社会的支持。
第四,乡村民众不欢迎新式学堂,更有其办理不善、内容腐败等方面的缘故。限于条件,乡村新式教育大多设备简陋,学科不齐,教师也多由一些腐儒担任,教育质量难有保证。如清末直隶“各属创设小学堂已五六年于兹矣,其中设备合宜、教授得法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因陋就简、敷衍塞责者则居十之八九。间有徒挂学堂牌额,并无学生,反不及向时私塾尚得按时上课”⑧。民国初年,“绍兴学校日见发达,各镇乡村亦渐设立。顾学校虽多,而私塾亦复不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学校虽多,亦复优劣不等,有办理完善而经费竭厥致困踬其进步者,有内容不整徒有虚表者,有经费充足而不悉心主持者,有意见龌龊不相融合者。求一成绩优美之校,实不多观,而私塾反得滥竽其间”⑨。由此可见,私塾得以“滥竽其间”,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新式学校的办理不善。
由于缺少乡村社会的支持,清末民初乡村新教育普遍缺乏经费。1908年浙江金华县28所乡村学堂中,年收入在100元以下者有8所,年收入在200元以下者有18所,其中东乡畈洪村私立安志初等小学堂和杜宅村公立平山初等小学堂年收入只有30余元。28所乡村新学堂中,常年教育经费入不敷出的有21所之多。⑩
新教育往往面临着严重的生源问题。1909年《教育杂志》第7期登载一篇介绍内地乡村学校情况的文章,作者以其亲身见闻,指出乡学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招生之难。“学校既设,招生为先,此校设立时,亦尝贴广告于通衢,招人就学。乃待之许久,初无来校报名之人。校董不得已,则择其家有子弟,而其力又足使之就学者,亲往敦劝。许以不收学费,然犹应者十一,拒者十之九也。”而所以能招到部分学生,原因在于“此校董本为乡中董事,颇有势力,乡人仰仗之处正多,不敢过拂其意,于是竭十数日之招致,遂得学生二十余人。然推其本心,乃迫于不得已,特以此为酬应校董之举”(11)。
由于投入严重不足,清末民初乡村学校多借用寺庙、宗祠等作为教室。但是祠堂和寺庙本非为学校而建,鲜有适合学校教学与管理的。大多数由寺庙和宗祠改设的学堂设施简陋,一些学校甚至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如黑板、桌椅等都不具备。如浙江金华县东乡浦口村公立英敏两等小学堂连计时钟也没有,上课下课全凭教员揣度。(12)再如浙江浦江县公立培贤初等小学堂,设于东岳庙,视学员评价此堂“规模简略,讲堂北向。学生皆东向,讲台前只几櫈各一,可列坐三四学生听讲,并无计时钟表,未能遵照定章教授,半沿从前训蒙性质。学生课程不齐者居多数”(13)。这种学堂绝非乡村中所仅见,新教育的处境可见一斑。
乡村教育的困境对清末民初乡村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兴学之前,私塾遍布乡间各个村落。塾师的工作除了教学与管理活动,还经常会为乡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帮助,是以“过去乡村中,秀才先生或书塾老师有极大的势力。他是一乡中的审判者,一乡中的号令者,一乡中的指挥者;他是一乡中所‘佩服’的人;假如这位秀才先生或乡塾老师,果真是道德高尚,则他的话差不多即可成为号令”。村中如发生纠纷,“往往请求他去判断”;有“新事情发生了,则一般民众大都不约而同去听受他的意见”(14)。廖泰初通过调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私塾或许不是直接干预地方行政,间接活动的力量却是值得惊异的”,所以“以塾师塾址为中心而形成一个近乎参议院的说法,并不是过甚其词”。(15)由此看出,乡村私塾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村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还是一种乡村社会组织,对下发挥着调节与整合乡村社会作用,对上则扮演着乡村社会代理人的角色。它对乡民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思想观念和态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它在传承乡村社会文化、维护与整合乡村社会秩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影响。
但是,在清末民初的乡村兴学过程中,私塾受到沉重打击。在政府的层层打压下,在与新教育的激烈竞争中,私塾要么接受政府改造,成为一种“学校化私塾”;要么从公开转入地下秘密状态;要么被迫解散。至20世纪20、30年代,尽管在乡村中仍然还有很多私塾,但它们功能的发挥受到极大限制,在乡村的影响力与往昔自然不可相提并论,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发挥“近乎参议院”的功能。
私塾在乡间的文化和社会作用本来应该由新式学校所继承。由于长期与乡村社会处于冲突状态,新教育很难获得乡村民众的认同,更谈不上得到他们的信仰。而乡村教师又多是“年纪青(轻),经验少,在乡间没有地位没有声望,老头子们看着他生,看着他长,在他们眼中,还不过是他毛小子,谁拿他当老师看,连写个账都不会,一切应用的知识全拿不出来”。“这种人物不能适应地方的需要,缺乏应付地方的力量,无法博得乡间的信仰。”(13)因此,乡村新教育一直无法取代私塾在乡村社会的中心地位,难以发挥传统乡村私塾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整合功能,乡村社会的调节与整合能力大为削弱。
中国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给乡村教育及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多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西方而来的近代新式教育,能否担负起促使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能否真正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如舒新城认为:“中国的社会除了少数都市外,内地至今还是小农制度与手工业的社会组织。三十年前,就是现今重要的京津沪汉亦还不曾为西洋文明所陶铸,社会生活尚多能保持本来面目;而现行的教育制度,则完全为工业社会的产物,其本质即不宜于中国的环境,所以兴学数十年,成绩极为有限”。“中国社会因还在小农与手工时代,对于现今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无迫切的需要,所以结果甚微。此种不择土宜的移植政策,为我国新教育失败的总因。”(16)一些近代教育家更是根据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教育及乡村社会危机的局面,得出了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的结论。
这些批评有一些道理。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乡村,以农业为生,乡村教育转型的确应当考虑到这种情况。但对近代中国而言,更为现实也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摆脱社会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富强,这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强调以“农业立国”固然是有益于民生,但却无力强国。这决定了中国教育不能死守着“农业社会”不放,而是必须走现代化发展之路。
教育固然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应当看到,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与欧美等国的现代化有很大的不同。在欧美等国中,教育现代化是在社会转型进行中或完成之后才开始的,教育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现代化最主要的任务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赶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但是在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启动、同步进行的。社会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需要教育为其提供人才和思想支持。因此,中国乡村教育不仅不应跟在乡村社会发展后亦步亦趋,而且应当适度走在乡村社会发展前面,才能更好地发挥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那种过分强调新式教育应与乡村社会相适应的观点,只是机械地理解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没有认清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没有理解乡村教育现代化特殊的历史任务,忽视了教育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转型的功能。
在强调乡村教育必须走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中国教育现代化从来就不等同于“西化”,不等于不顾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条件,对西方教育制度和现代化经验的照搬照抄。中国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过度抄袭与模仿有关。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在坚持现代化这一发展方向、保持现代教育核心特质的前提下,应当适当考虑乡村社会及乡村民众生活生产的具体情况,对新式教育中那些与乡村生活严重冲突的形式化的东西进行改革,使其尽可能地贴近乡村民众的生活,给他们的生活以帮助。从这个角度说,乡村教育的出路既不是对乡村传统教育的回归,也非完全对西方新式教育的模仿、移植,更不是削足适履,使西方教育适应中国乡村社会的需要,而是要建立一种立足于现代科学、民主及理性精神基础之上,同时又融入中国乡土特色的乡村新式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教育的“转型”并不仅仅是指从一种制度转变成为另一种制度,或者说用一种教育制度取代原有的教育制度,而应认做是一种“持久的并存以及产生新颖现象的混合”(17)。
中国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而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乡村教育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一个社会的核心结构,教育只是一个边缘结构,不能离开社会主要构成要素的现代化去谈教育现代化问题,因为教育的许多根本问题如教育目的、管理体制、学校结构、课程内容、教育条件(经费、师资)等皆非教育本身所能决定,也非教育本身所能解决。”(18)对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乡村新教育对乡村社会和乡村民众都有很大的依赖性。完全可以说,如果中国乡村社会仍然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如果乡村民众依然是分散、保守的个体农民,很难想象乡村教育问题会得到真正解决,也很难想象新式教育能够获得乡村社会的支持与广泛认同。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仅仅依靠对乡村教育进行调整(适)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加快乡村社会转型的步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手段教育乡村民众,开阔他们的眼界,使他们走出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时还应当切实提高乡村社会经济、文化水平,使乡村教育现代化有一个很好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这样才有可能消除现代教育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种种抵牾,促进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注释:
①[日]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第163页,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版。
②舒新城:《小学教育问题杂谈》,见吕达、刘立德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第44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天台县分划学区表续》,载《浙江教育官报》1910年第46期。
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第2页,燕京大学1936年刊。
⑥舒新城:《小学教育问题杂谈》,第437页。
⑦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51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⑧《直隶提学司通饬各属实行改良私塾文》,见李桂林、戚名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15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⑨《学校与私塾之消长》,载《教育周报》1914年第77期。
⑩《金华府县各学堂调查表》,载《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9期。
(11)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载《教育杂志》1909年第7期。
(12)《金华府县各学堂调查表续》,载《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10期。
(13)《金华府浦江县各学堂调查表》,载《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12期。
(14)鲍祖宣:《国难时期的妇女教育》,载《女子月刊》1936年第1期。
(15)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第39、69页。
(16)舒新城:《小学教育问题杂谈》,第665-666页。
(17)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8)吴式颖,褚宏启:《外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第12-1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