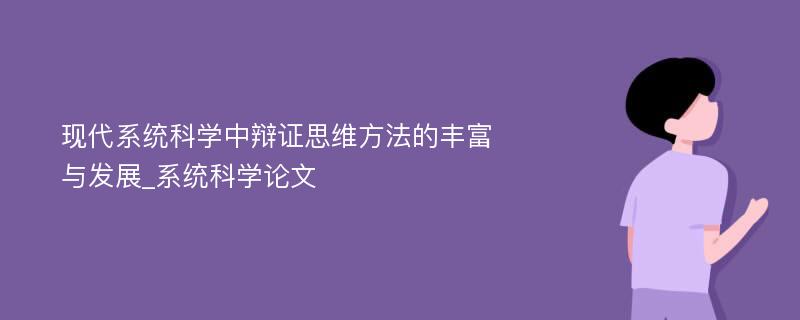
现代系统科学对辩证思维方法的丰富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系统论文,丰富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系统科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日益成熟和发展,正推动着人类思维方法的更新,尤其是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思维方法。
一、现代系统科学对分析综合法的丰富和发展
现代系统科学对辩证思维方法的丰富和发展,突出地体现在作为辩证思维方法的核心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以后简称“分析综合法”)上。
其一,系统科学丰富了分析综合法的内容。
分析与综合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早已被提炼并广泛使用。然而,长期以来,分析与综合法都是基于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上使用的:分析仅仅被认为是思维把认识对象的整体分解为它们的各部分;综合仅仅被认为是思维把认识对象的各部分联结为一个整体。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分析综合法内容的揭示,达到了较前人更深的层次:不是停留在部分与整体的简单组合关系上看分析与综合,而是联系事物矛盾运动的复杂关系去揭示分析与综合诸环节,从而使分析与综合真正成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①②
随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出现,分析综合法的内涵又得到了更深入的揭示。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深化了对事物结构的认识。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正是基于把生物有机体的组织结构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强调事物构成要素以一定方式联结而成的有机整体的整体功能,才得以创立一般系统论。“结构”是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事物的结构分析。如在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时,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利用图论等数学工具,经过结构网络模型分析,建立有关的数学—逻辑模型,把系统诸要素的结构联系清晰地表达出来,以供结构设计。择优分析或决策分析是系统科学的又一重要任务。择优,是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例如,系统工程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一般是大而复杂的系统,不仅有关的因素、参量多而不确定,而且系统的目标也有多个。对这样的复杂系统,可以提供多种模型;对所建立的每个模型又可分别不同条件与情况加以预测与测试,从而设计多种方案。择优的过程正是分析、比较这多种模型、多种设计方案的过程。现代科学的决策,尤其是重大战略决策,就是从这多种可能的状态或方案中,根据给定目标,进行择优分析,确定最优设计、最优管理和最优使用。择优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决策分析。
可见,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结构分析、择优分析和决策分析已日益成为分析综合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二,系统科学实现了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跃迁。
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因素的有机联系。对于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来说,这种多因素的相互关联就更为复杂。要达到优化目标的效应,必须设法从量上描述这种关联;这就要求对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的分析不仅是定性的,而且是定量的。非如此不能清晰地展现出系统内部的复杂关联性。运筹学正是为适应系统工程定量分析的需要而诞生的。它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数据库,采用科学步骤与数学方法来判定决策,成为对系统作定量分析的综合性应用数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运筹学应用范围的扩大,先后出现了规划论、博奕论、排队论、图论、库存论、决策论等多种分支;系统定量分析法也就渗透到各个领域。以往许多不得不靠经验、直观或猜测解决的问题,现在被置于精确的定量分析中。这是人类认识方法的一次大飞跃,是分析综合法的深化。
长期以来,分析综合作为哲学和逻辑方法,一直是作为定性的方法而运用的。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人们的认识对象越来越扩大,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活领域;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对象又越来越复杂,经常涉及高参量、超微、超宏范围问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分析与综合就不能仅满足于定性,而日益要求定性与定量的结合。系统科学体系的初步形成,正标志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崭新的分析综合法的初步问世。
其三,系统科学对分析综合二环节的统一性作了更深入的揭示。
黑格尔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尽管强调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但在有些地方还是把分析与综合作为两个环节、两个阶段,从时间上作了区分。例如,黑格尔就曾把分析作为推理的第一个前提,把综合作为第二个前提,先分析,后综合。①马克思在分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也曾把科学抽象看作是以分析为主;把形成思维具体的过程看作以综合为主。②系统科学对分析综合二环节辩证统一的新启示在于: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不仅在于“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以及两者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而且在于分析与综合的同步进行,即“分析同时又是综合,综合同时又是分析”。意为:分析在另一种意义上是综合;综合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分析。
在系统科学看来,首先,系统分析是一种整体分析。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特性,整体观念是系统概念的精髓。根据系统论,对系统构成要素的分析始终是在综合系统整体前提之下的分析。离开对系统整体的综合,对系统构成要素的分析就寸步难行。
例如,离开对登月球的阿波罗计划的通盘考虑,约42万参加人员、120所大学实验室和从事研制的200多家公司就无法确定其各自的地位和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分析同时就是系统整体综合,系统分析就是整体分析。
其次,系统分析的每一步又都是综合。系统分析必须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服务于优化的整体目标。因此,系统分析的自始至终同时又是综合。例如,对系统目的的分析、确定离不开对系统整体性质的综合把握;对系统的结构分析离不开对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系统内部各层次间、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参数、变量与系统特定功能间关联性的综合考察等。
再次,系统分析法本身也是多种方法、多种学科的综合。系统分析法是结构分析法、功能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的综合。把系统方法付诸实施,系统分析则成为一个多层次的方法系统。系统分析还广泛涉及多学科,遍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及哲学各领域。这也体现了分析与综合在现代系统科学中的高度统一。诚然,系统科学对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更深揭示并不否认一定条件下的分析与综合的有所侧重。
二、现代系统科学对科学归纳法的丰富发展
现代系统科学的诞生对科学归纳法的丰富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归纳侧面的拓展和加深以及促使归纳手段的完善和归纳可靠程度的提高两方面。
一是归纳侧面的拓展和加深。
辩证思维的科学归纳法在揭示对象事物的一般属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许多科学规律的揭示都首先归功于归纳法。然而,长期以来,科学归纳法往往以具体事物的“类”为基准,其涵盖面往往局限于“事物类”的各自不同领域。现代系统科学对归纳法的丰富和发展就在于突破了具体事物的“类”,从看来质料和性质极不相同的事物中归纳出共同的方面,抽象出一致性和同型性来。现代系统科学开拓出对客观事物的新的、更深的归纳侧面——系统性,并从不同角度对系统的普遍属性作了研究。
首先是对系统内在属性的研究——从“系统性”这一新角度归纳事物的一般属性。系统科学从宇宙间大量存在的系统中概括出系统的六大内在属性:目的性、集合性、相关性、阶层性、整体性和环境适应性;并由此出发,从系统这一新角度揭示了(即归纳出)宇宙的一般规律,诸如:系统存在律、系统结构功能统一律、系统整体律及系统自组织律等。现代系统科学为科学归纳开辟了系统这一新领域,提高了归纳层次,揭示了全新的宇宙规律。
其次是对系统外在属性的研究——从系统的行为方式上归纳事物的一般属性。系统科学舍弃了系统物质和能量的具体内容,从系统的行为方式和功能上概括其共性。系统科学发现,在生物、技术以至社会这些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控制系统尽管在物质结构形态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在行为和功能上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行为功能的同构性,如无论什么控制系统都有调节、反馈、组织、目的性等行为特征。这一新的归纳基础,不仅使我们对系统的属性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为我们研究系统提供了功能模拟法、黑箱方法等新方法。
再次是对系统过程的研究——从信息角度归纳事物演化规律。系统科学从系统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的研究中,又概括出一个共同之处:联系。包括:要素之间的联系(结构)、系统与环境的联系(功能)。从动态过程看,这种联系表现为一种流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信息流动。系统科学从信息过程对系统性的研究是对归纳侧面的又一拓展。系统科学把系统过程当作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过程,并通过对信息流程的分析和处理,以达到对系统运动规律的认识。在此,科学的归纳法又具体化为信息方法、控制方法和反馈方法。信息——控制——反馈方法是一个统一的方法,它们都是对信息流通规律的揭示,都为我们从系统信息流通过程概括事物属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是归纳手段的完善和可靠程度的提高。
归纳有效性问题是逻辑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才能完善归纳手段和提高归纳的可靠程度呢?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必须把归纳与分析相结合。③然而,长期以来,归纳与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它虽然提供了较完善的归纳手段,极大地提高了归纳的可靠程度,但毕竟还不能做到象演绎推理那么精确可靠。在这方面迈了一大步的是系统科学。系统科学把形式化、数量化的手段引入科学归纳,把归纳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它在揭示系统特性和规律时,首先把对象描述形式化,力求用统一的科学语言(科学公式)加以处理;然后尽力用数学工具去揭示系统的特性、结构、行为及演化规律,把对客观属性的科学归纳与数学工具相结合,创造了定量化的现代归纳法。系统科学还实现了科学归纳的现代技术化。系统科学与现代归纳逻辑一起具体化了形式化、数量化和现代技术化的科学归纳新手段,极大提高了归纳可靠程度。
三、现代系统科学对科学抽象法的丰富发展
现代系统科学启发我们注意研究“思维具体”的系统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新途径以及对思维规定的定量综合。
首先是对“思维具体”系统性和形成思维具体新途径的揭示。系统科学诞生以前。对思维具体的揭示往往只停留在宏观水平。系统科学把“全面地把握对象整体本质”这一原则加以具体化。根据现代系统观,“思维具体”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因而具备系统性。它告诉我们,对思维具体的研究必须重视:第一,全局性或整体性。因为系统的整体性质大于构成要素的性质,所以研究思维具体必须从其整体的全局性入手,而不能只注意“从抽象到具体”这一走向。依据这一思想,从具体向抽象的转化不仅表现为由感性具体向思维抽象的转化,而且表现为作为整体的思维具体对作为思维具体构成要素的思维抽象的统摄。第二,层次性(或等级秩序性)。系统具有层次性,因而对思维具体的研究必须确定其系统等级,弄清它是哪一些系统的要素,又是哪一级要素的系统,应当在哪个等级或层次上研究这一思维具体。第三,关联性(相关性)和结构性。思维具体既然作为一个系统,因而必然要强调构成思维具体的各思维规定的关联性,其内在结构和动态结构。第四,庞杂性。现代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系统,往往是由大量元素构成的庞大系统,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无疑对研究思维具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在辩证思维水平上再现那些构成要素庞杂的系统,如庞大的宇宙、复杂的人脑等。凡此种种,都为我们研究思维具体提供了新思路。
用系统观把握思维具体,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应是最简单的抽象规定,思维由此出发,逐步走向具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即是思维规定由简单到复杂的矛盾发展过程。这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思想:思维抽象在先,思维具体在后;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即从局部到整体、先分后总。现代系统科学突破了这一反映近代科学成果的传统思维方法。就象贝塔朗菲所说:“因为活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组织,对各部分和各过程的传统方法不能完整地描述活的现象。这种研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各部分和各过程的协调关系。”⑤沿着这个方向,系统科学形成了新思维方向:不是把系统分解成孤立的元素,而是把系统首先作为一个整体,从总体上去揭示和研究规律。系统整体在先,构成要素在后,任何构成要素的特性都体现在一定的系统整体中;离开整体功能、行为方式和目标,就不能准确地揭示出构成要素的性质。依据系统观这一原则,在确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时,就不能仅满足于找出研究对象的“细胞”或基本单位,而必须首先初步确定所要研究的思维具体的整体性质和功能,并从此出发揭示出该系统内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然后才一步步展开思维规定由简单到复杂的矛盾发展过程。在确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具体逻辑途径时,则不能仅满足于从简单的思维规定开始的逐步丰富、具体化过程,而必须在思维具体与思维抽象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展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这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又离不开“思维具体——思维抽象——思维具体”的过程。在此,体现了“思维抽象思维具体”的双向过程。当然,这里并未改变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而是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必须以思维具体为前提;也不是说,要改变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进程,而是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抽象与具体的相互关联。
其次是对思维规定的定量综合。依据系统观,为把握思维具体这一系统,必须对构成思维具体的各思维规定进行定量的系统分析,并作定量综合。现代系统科学的成熟使这种定量综合成为可能。现代系统科学的定量分析与综合不仅反映决定性的数量关系,而且反映随机和模糊的数量关系;而且这种定量综合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对系统内诸要素数量关系的综合把握;也可以是对信息流程系统中控制、反馈、输出、输入等诸多信息流量的综合把握;还可以是对从无序到有序、从一种有序到新的有序的自组织过程的诸多数量因素的综合把握。现代系统科学在这诸多方面都建立有精确的数学模型。这就为辩证思维对思维具体多侧面、多角度的定量综合创造了条件。
总之,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为辩证思维方法的充实和更新提供了重要契机。
注释:
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2-418页。
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111、122-125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8-549页。
④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410页。
⑤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载《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0-320页。
标签:系统科学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逻辑结构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科学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系统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