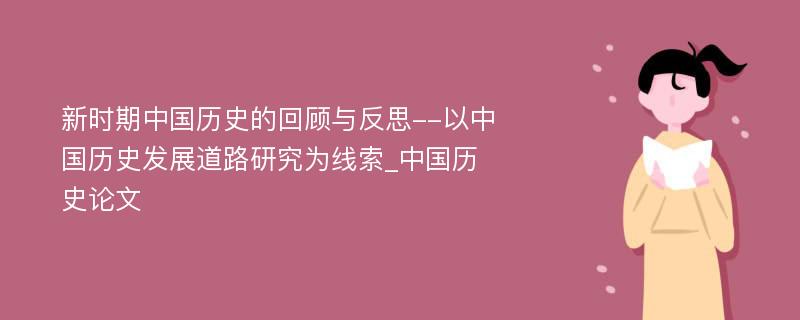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思考——以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历史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时期。如所周知,建国后至今,中国历史学经历了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期。前30年,中国历史学的最大成就是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历史学的发展一度严重受挫。后30年,中国历史学的最大成就是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得到全面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打破史学“禁区”,深化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研究方面,也表现在根据中国历史学全面发展的需要进行史学研究的结构性调整,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建设新的分支学科、关注新的研究热点方面,还表现在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转换新的研究视角,从理论到方法进行新的探索方面。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面。与此同时,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与上述基本面相背离的新倾向,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理论“创新”的名义下,竭力鼓吹历史研究的非社会形态化。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方面的状况进行回顾和思考,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
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特点和成就,也是新时期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方面,它主要反映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中。例如,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稿》编写组修订的《中国史稿》(7册),范文澜主编、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卷),翦伯赞主编、邓广铭等修订的《中国史纲要》(上下册)①和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等。
如所周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的构建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开其端;40年代,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承其绪。他们通过中国古代社会史和中国通史等历史著作具体构建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他们所构建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的基本特点是:运用唯物史观,特别是作为其基本理论构成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重新解释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把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看作是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根源和动力,并以此为指导线索贯串中国历史全过程,由此形成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认识,构建了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新体系,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他们所构建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他们用以阐释这一新体系的著作则成为这一结合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建国后,他们继续完善早已开始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的构建工作,修订原来的历史著作或重编新的历史著作。“文化大革命”前,他们的修订或续编、新编工作,除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于50年代修订完成外,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的修订、续编或新编的中国通史工作,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诸老的未竟工作,在其原来的合作者或后继者的努力下,沿着他们所开辟的研究道路,遵循着他们所确立的指导原则继续完成他们业已开始的中国通史的修订、续编或新编工作,从而为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新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的新力作。这部被誉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即多卷本《中国通史》,集全国二百多位老中青历史学工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之功,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最新成果。其最大特点是: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生产方式到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如实地把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看作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始终贯串着社会形态变迁这一指导线索。该书指出:自有文字记载始,中原地区即进入奴隶社会,而此前为原始社会。夏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商周是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秦朝完成了这一过渡而进入封建社会;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五代至元末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清是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1840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虽然这部多卷本的《中国通史》在大的历史时段的划分上沿用传统的提法,如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代,但是,就各历史时段的内涵来看,则是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过程中,它还注意吸收20世纪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史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在史书体裁方面,它创立了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组成的综合体,从而使史书所反映的内容更具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特点。唯其如此,我们认为,这部多卷本的《中国通史》不仅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且是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开创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代表了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最新成就。
三种“早期国家”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路径
新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新进展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从“早期国家”的新视角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它之所以成为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既与国内新的考古发现有关,也与20世纪后半期国外的“早期国家”研究热有关。
如所周知,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论断,②历来为中外学界所认同,认为这是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然而,国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它形成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或模式,这就是西方学界所说的“早期国家”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开始研究西方的早期国家理论,并从这一新视角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
回顾新时期的中国历史学,有三种“早期国家”说对中国文明起源路径提出了新的看法。
一是“酋邦”说。谢维扬首先结合国外酋邦理论探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他指出:所谓“早期国家”是指从原始社会直接演化而来的最初阶段,有着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中心和行政及政治管理机构,产生了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有领土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等;而从“早期国家”发生和发展的进程来看,有两种模式,即:直接从氏族社会演化而来的“氏族模式”和从氏族社会解体后出现的“酋邦社会”中演化而来的“酋邦模式”。中国文明的起源也经历了“早期国家”的阶段,它是由“酋邦社会”演化而来的,因此,称为“酋邦模式”。其历史进程是:由酋邦社会演变出夏朝国家,这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期;经商朝至周朝而进入鼎盛时期,这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春秋战国是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形态转型的时期;秦朝国家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终结和新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出现。③由于中国的早期国家是经由“酋邦社会”演化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谢维扬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称之为“酋邦”路径。
二是“聚落形态”说。王震中首倡此说。他认为,“早期国家”理论的提出,特别是酋邦模式的发现,是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成就,而根据这一理论和模式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演进划分时期或阶段不失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路径的一种新视角、新观点。不过,这一理论模式仅仅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史前社会所做的概括和说明,而是否符合史前社会的实际,还有待于考古学的检验。因此,他提出:必须加强考古学的研究,实现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才能真正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为加强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加强考古遗迹中的聚落遗址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社会形态的大量信息。他指出,考古发现表明:不同时期的聚落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而通过对不同聚落形态特征的研究可以发现其演进的轨迹,划分其演进的阶段,建立其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据此,他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历程可以概括为:社会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形态——开始分化和分层了的原始宗邑聚落形态——已形成文明的城邑国家形态;而最后一阶段即城邑国家文明形成于夏王朝之前的前王朝时期,相当于考古学所称的龙山时代和古史传说中的颛顼、尧、舜、禹时代。这属于早期城邑国家产生和形成的时期,其特点是:家族一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同层同构,宗族组织结构中的主支与分支同政治权力上的隶属关系相一致,至西周则表现为“君权与宗权的合一”。因此,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属于“维新式起源”的路径。④应该说,通过考古研究,从原始聚落形态演变的角度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提出“三阶段”或“三形态”说,是他的独到见解。
三是“部落国家”说。何兹全主张此说。其要点:(1)由部落到国家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划出一个“早期国家”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2)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部落到国家的转化时期,称为“早期国家时期”,就是说,在国家形成之前,中国历史曾经有过“早期国家”阶段;(3)中国的早期国家是在部落不平等结合的基础上,在部落对部落的征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称之为“部落国家”,它属于国家形成的初期或萌芽期;(4)中国的早期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城邦国家”,它是以城为主体加上近郊组成的政治组织体,城邦居民(称“国人”)有管理城邦事务的权利。不过,与西方古代的城邦国家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而是有着上下的统属关系,实行“国”、“野”的耦国制度,领土观念模糊;春秋时期属于由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时期,虽然东西方都有过“城邦国家”的历史,只是在城邦的独立程度和居民参与管理的权力大小上有所不同而已;(5)部落转化为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地区组织代替了氏族组织;单纯的氏族酋长权力转化为王权;出现了为王权服务的群僚及其政治机构、兵及其军事组织以及为维护王权统治的牢狱等,用上述标志来衡量,西周春秋时期正处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即由部落组织向国家转变的时期。⑤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何兹全关于中国国家起源的路径简称为“部落国家”的路径,而这种“部落国家”是在征服基础上建立的,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部落联盟。因此,“部落国家”说又可以称为“部落联盟”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论是相一致的。不过,将中国的“部落国家”视为“城邦国家”,并同西方的城邦国家进行比较,指出其独特性,则是他在早期国家理论方面的创见。
历史分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从“早期国家”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新亮点;那么,从历史分期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则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在课题研究方面的新视角。这是新时期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新进展的又一重要表现。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指介于原始公社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之间的奴隶制社会;所说的发展道路是指由原始公社制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和由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路径或实现形式。因此,新时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的探讨,既同中国文明起源即国家起源的路径有关,也同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即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有关,更同中国历史分期即原始公社制与奴隶制、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有关。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分期说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观。以新时期修订再版的两部中国通史著作为例。⑥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主张夏代中期奴隶社会说、春秋过渡时期说和战国封建说。与此历史分期说相应,其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观可以表述如下。
一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是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到地域性的部落联盟的过渡时期;从夏启到少康重建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确立时期。
二是,中国奴隶制国家是在私有制出现的前提下,通过部落战争性质的改变实现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的。
三是,商周奴隶制社会的特点:(1)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是其经济基础,井田制是其实现形式,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是其耕作制度,奴隶形似农奴,贡税是奴隶主贵族榨取奴隶劳动的剥削形式,实则是一种利用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控制奴隶的更省事而有效的办法;(2)阶级构成保留着氏族制的残余,如奴隶主贵族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大家族长转化而来的,奴隶或由战俘,或由平民转化而来,或由征服转化而来的“种族奴隶”,因而保留着更多的氏族遗制;(3)宗法制与等级分封制相结合,实行家国一体、“宗子维城”的政治体制。
四是,春秋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为这种转化创造了物质基础,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成为可能。实现上述转化的路径有三:(1)通过各国内部新旧势力即“公室”与“私室”的斗争加速了新的社会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形成过程;⑦(2)通过各国的变法剥夺了旧奴隶主贵族的经济、政治特权,实现了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方式的改变,确立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生产的发展;(3)通过兼并战争实现封建国家的统一。⑧这样,由奴隶制国家起源开始,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演变,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性社会改革,至秦朝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终于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主张夏代奴隶社会说、西周封建领主制说、春秋战国过渡时期说、秦汉封建地主制说。与此历史分期说相应,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观可以表述如下。
一是,夏朝是通过王位世袭制的确立而实现由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
二是,商朝奴隶制国家:对内,依靠宗法关系统治其族众,实行“七十而助”的带封建性的力役地租剥削;对外,通过分封邦伯、委派侯甸控制地方和边陲,实行内外服制的统治,因而具有封建、宗法和分封等特点。
三是,西周封建领主制既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初期阶段,也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必经阶段。
四是,西周封建领主制是按宗法关系实行土地层层分封的土地等级所有制,井田制是其实现形式,劳动地租是其剥削方式。
五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这种转变是通过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的合法性实现的。⑨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在经历了三次转变之后,即:由部落联盟通过王位世袭制的路径一变而为奴隶制国家,又通过宗法分封的路径二变而为封建领主制,再通过制度性社会改革的路径三变而为封建地主制,才最终走完了自己的路程。
如果说,新时期修订再版的中国通史著作是在原来的历史分期说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进行新的探索;那么,新时期的中国通史新著则是在综合原来历史分期说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发现而提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的新说。其中,最具新意的代表作应首推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主张夏代过渡阶段说、商周早期奴隶社会说、战国过渡时期说、秦朝统一封建说。与此历史分期说相应,该书提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新说。其要点如下。
一是,夏代不是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而是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商汤灭夏后才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二是,中国国家形成的路径不同于希腊、罗马,而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已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产生的;夏禹传子制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而只是反映父系家长制的形成和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开始向君主世袭制转化。
三是,商周奴隶制属于早期奴隶制,其特点是:(1)在公社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进入国家阶段;(2)国家的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具有明显的从公有到私有的过渡性质;(3)过渡性的公社所有制决定了商周奴隶制的发展模式是早期奴隶制,它表现为:公社组织尚存,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社农民,而不是奴隶。
四是,针对西周封建说以生产者主要是公社农民而非奴隶而反对西周奴隶社会说的观点,提出判定西周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的标准:既要看奴隶的数量多少,更要看奴隶制的产生、发展对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和奴隶制的剥削是否占主导地位。
五是,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其转变的路径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古代公社的解体,土地所有制由公有向私有的转化,公社农民的分化,或转化为小土地所有者,或变成丧失土地的佃农,贵族和其他土地占有者转化为新的地主土地所有者。⑩
六是,秦朝的统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标志着奴隶制的终结和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终确立。(11)
从上述要点来看,最具新意的不仅在于该书提出商周奴隶制的早期性,也不仅在于它为这一早期性所做的说明,而且还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判定商周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的标准,从而使该书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观既不同于西周封建说,也有别于战国封建说。
新时期,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方面的力作是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12)名曰:“中国古代社会”,就是旨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渊源流变的过程,因此,堪称是一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专著。从历史分期来看,该书认为夏、商、周是中国古代由原始奔向文明的三大族群体,同处在由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西周春秋时期是部落到国家的转化时期,即早期国家时期;战国秦汉是交换经济占优势,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即古代社会时期;汉魏之际,是中国“封建”开始时期。与此历史分期相对应,该书提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新说,其要点有二。
一是,周灭商后,商周两族的关系是不平等的部落关系,但决不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通过征服,商周两族所建立的国家是正由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的早期国家,可以称之为“部落国家”。(13)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形成是经由“部落国家”阶段转化而来的。
二是,战国秦汉的中国古代社会是“私家主体社会”,它是沿着城市商业交换、经济发展、土地兼并、农民破产流亡为奴隶这条线发展的,这是私家经济、私家社会,而不是国家经济、皇权经济的社会;而由古代社会走向中世纪社会则是沿着自由民和奴隶的依附化、城市经济的衰落、自然经济的盛行这一条线实现的,这是私家主体社会的变化,国家经济只是跟着走。(14)其中,城市经济的兴衰是贯串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条主线。这是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所做的新概括。
值得指出的是,与建国初期的魏晋封建说相比,作者的汉魏之际封建说,从理论到实证都不乏新意,而最大的新意则莫过于不再用“奴隶社会”而改用“私家主体社会”重新为中国古代社会“正名”。之所以作此改变,据作者说,是因为“奴隶社会”一词不足以说清楚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构成的复杂性。他认为就阶级形态而言,中国古代社会既有军功贵族、豪富家族,又有既依靠豪强又具独立人格的宾客,还有庞大的奴隶群和自由民,而并非只有奴隶主和奴隶。其中,豪富家族、宾客、自由民、佃农和奴隶又是战国秦汉的社会主体。因此,即使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能否就称为奴隶社会,作者表示怀疑。一句话,作者认为“奴隶社会”这个名词不科学,最好是“束之高阁”,(15)弃而不用,而提出一个新名词或新概念,叫做“私家主体社会”。
如所周知,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奴隶制社会的问题,历来就存在着争论,迄今仍未止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问题是:学术问题上的仁智之见应有助于认清历史现象,把握历史本质。我们对于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功力是十分敬服的。但是,对于他放弃“奴隶社会”而改用“私家主体社会”,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经作者这么一改,无助于人们认清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反而模糊了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究其原因,问题就出在“私家主体社会”这一提法上。因为作者用“私家主体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势必模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奴隶主与奴隶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这是判定该社会性质的根本依据。如果我们的理解没有错,作者所说的“私家主体社会”实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即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16):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三种社会形态。那么,“私家主体社会”究竟属于哪个时期、哪种奴役形式呢?可见,用“私家主体社会”取代“奴隶社会”来为中国古代社会“正名”,对于我们的研究不是深化了,而是泛化了、模糊化了,因而无助于人们认清中国古代社会的真正本质。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
重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新亮点
资本主义萌芽是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问题时提出来的,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一是,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由原始积累所引起的“劳动者的奴役状态”的改变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而强制地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从而变成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更是“首要的因素”。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正是从这种“分离”开始的。
二是,强调“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改变的社会史意义,指出:“这种奴役状态”在形式上的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开始,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正是以这一转化为起点的。
三是,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过程的长期性。根据马克思对于西欧历史的研究,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其间经历了两个世纪(14—15)。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经历着“不同的阶段”。就是说,它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道路。(17)
新时期,我国学术界重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就是根据马克思的上述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展开的。(18)如果说,1980年代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重点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程度的评价;那么,新时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重点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道路的探讨。这是新时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新视点。
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定性、定位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始状态,即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雇佣剥削关系的最初形态。它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具有延续性、导向性、不可逆转性。持这种看法的学者都主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19)
主张明清说的学者还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道路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首先是从富裕农民的雇工经营开始的,始于明中叶。至清代前期,在地主经济中又开始产生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它们表明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20)有学者进而指出:从“农民经济”中演化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旧的影响少些,发展也快些,是“革命的道路”;从“地主经济”中演化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旧的影响更多些,发展也缓慢些,是“保守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在明清时期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21)有学者更指出:农民经济中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着两条发展道路,即:由佃农雇工向富农雇工经营转化和自耕农雇工向富农雇工经营转化的道路;前者是“保守”的道路,后者是“革新”的道路。不仅如此,在“地主经济”中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存在着两条发展道路,即:由传统的租佃地主向经营地主的局部转化和由富农向经营地主转化的道路;前者是“保守的道路”,后者是“革新的道路”。(22)
必须指出,在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尽管对其具体评价不尽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其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地主制经济为核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严重束缚”和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政权的“残酷统治”。具体地说:一是,“佃农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占有权”,自耕农赋税繁重,“经营土地因雇工盈利过低”而转向土地出租,从而“使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断地再生”;二是,封建国家“积极维护封建租佃制和封建雇佣制,防止和压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23)还有学者分析说:由于土地买卖和地权转移非常频繁,因此导致原始富农和经营地主因地位“不稳”而“产生不易发展更难”。(24)
总之,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因素,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实质则是一致的,即属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最初形态。尽管由于中国封建制的特点,这种转化过程极其缓慢,但是,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那么,按其自然历史进程是一定会逐步走向近代,实现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的。应该说,这是新时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道路问题讨论的社会史意义之所在。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隐忧
回顾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走过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或是用“早期国家”理论重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还是从历史分期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都无不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联系起来,着力探求这一变迁过程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实现形式,而这正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构成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与主要线索,因而成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令人不安的隐忧,这就是:出现了与上述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学术倾向或学术思潮,我们称之为历史研究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这是一种把社会形态排除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不再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史学思潮。如果说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变迁过程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实现形式,那么历史研究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则反其道而行之,它不再把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不再把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看作是有规律可循的过程,因而,也不再把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看作是社会形态变迁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显然,这是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背道而驰的。
如所周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人类历史进程的社会发展学说。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这一学说,唯物史观才成为被人类社会历史所证实了的科学真理。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正是社会形态的变迁使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呈现出阶段性来,而促使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源则在于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性,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历史分期法就成为马克思这一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新时期,历史研究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所竭力非难的正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历史分期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史坛兴起的这股非社会形态化思潮就是以证伪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证伪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竭力将五种社会形态说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进行切割,试图证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斯大林按照自己的观点套改马克思思想的产物;二是,竭力将五种社会形态说与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切割,试图证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马克思根据经验历史所做的归纳,而是马克思根据逻辑必然性所做的演绎,因此,是一种缺乏历史实证的“理论假说”;三是,竭力将五种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进行切割,或者更确切地说,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同中国历史进行切割,否定中国历史同上述社会形态的联系,试图以此证明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超越”社会形态而另辟蹊径,走非社会形态化的道路。对此,我曾有专文予以回应,(25)此不赘述。
进入21世纪以来,事态的发展已经由单纯的“证伪”转向直接攻击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最典型的莫过于假“实事求是”之名,行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之实的唯物史观否定论。此论的要点有三:一曰“因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导致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变更替的例子,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几乎一个也不存在”;二曰“一味强调由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人的主观想象”;三曰造成上述问题长期“纠缠不休”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否“实事求是”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所在。
从上述要点来看,唯物史观否定论犯了三个错误。
一是,犯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理论错误。
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革命的因素,它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原动力,因而也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内在根源。这是由生产力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生产力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就是说,它是人类世代累积起来的“实践能力”或“应用能力”。(26)因此,后一世代的生产力必然高于前一世代的生产力。这就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必然呈现出不断由低一级向更高一级上升运动的过程。正是生产力这一不断发展的上升运动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形态的变迁必然是由低一级向高一级依次递进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向,是由生产力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因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唯物史观否定论者所说的什么“人的主观想象”。至于他们始而否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本质属性,继而否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事实,终而否定人类社会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则是他们犯了上述理论错误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
二是,犯了曲解欧洲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历史事实的错误。
在唯物史观否定论者看来,欧洲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理由是:其时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远逊于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一句话,欧洲的封建制不如它之前的奴隶制进步。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新鲜,而是老调重弹。早在法国革命前夕,西方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是这么说的。他们普遍认为,欧洲中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黑暗时期”,是人类文明的“中断”,是历史的“倒退”。当时,唯物史观尚未被发现,因而也就不能苛求这些历史学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中去解释欧洲这段历史,承认欧洲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进步性。问题是: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人口称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历史,实则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于不顾,而径直按照自己的某种需要任意曲解历史。这是最不“实事求是的态度”。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首先,在评价欧洲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时,必须从这样的基本事实出发: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用恩格斯的话说:它“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或者说,“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从而造成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商业、手工业和艺术衰落,人口减少,都市衰落,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是当时奴隶制束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封建制之代替奴隶制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于是,一种“唯一有利的形式”——小规模经营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出现了”。田庄被分成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隶农”去耕种,他们就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这说明在罗马帝国后期已经出现了后来称之为封建制的新因素。恩格斯特别强调:这种封建制的新因素,包括“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27)这就是说,当时出现的封建制新因素是完全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因而也必然是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唯一有利的形式”。同样,日耳曼人在征服罗马帝国后所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他们的军事组织由于“遇到”罗马帝国内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28)因此,它同样是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可见,在评价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时,首先必须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而唯物史观否定论者,则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其次,在评价欧洲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时,必须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切忌机械、片面地看问题。如所周知,生产力既包括物的因素,又包括人的因素,而后者更具决定性的意义。从物的因素来看,欧洲封建社会生产力较之奴隶社会进步,其最重要的标志是新的生产工具手推磨的应用。马克思曾以“手推磨”和“蒸汽磨”的应用分别作为欧洲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物化标志,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是“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29)这说明“手推磨”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新生产力”,因而必然较奴隶社会生产力进步。更重要的,还应该看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即劳动者的实践能力及其人身解放程度。恩格斯说:中世纪农奴制这种奴役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这说明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较之奴隶制社会形态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方面又前进了一步,而不是像唯物史观否定论者所说的“远逊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
在讨论这一时期欧洲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时,固然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罗马帝国的衰落和蛮族的征服以及连续不断的战争对当时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二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小规模经营”所形成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对于分工发展的影响和生产力提高的制约。但是,这两个因素只能作为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何以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理由,而不能作为欧洲封建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的证据;恰恰相反,正因为欧洲封建制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需要,所以,最终才有可能得到恢复和发展。恩格斯在论述欧洲这段历史时指出:中世纪以来的400年间,欧洲社会“毕竟是继续前进了”。他称这一时期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沉沦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像“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曾经是古典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则成了“新的世代”“新发展的起点”。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行的分化和改组”。(30)可见,欧洲封建制之代替奴隶制是“新的世代”“新的发展的起点”,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终点,更不是历史的倒退。至于这些源自欧洲封建社会的“新文明”的“重大成果”更非“远逊于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文明成果。事实表明:欧洲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进步性,是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反映和表现。这是生产力不断发展使然。同样,奴隶制之代替原始公社制,资本主义之代替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之代替资本主义也应作如是观。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已经证明或正在证明的“客观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只有无视这一“客观事实”的曲解,才是名符其实的“人的主观想象”。
三是,犯了历史观的错误。
根据以上分析,唯物史观否定论者的错误,无论是理论层面或是历史层面,其源盖自历史观的错误。所以,尽管他们也说了不少关于“实事求是”的好话,甚至视其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所在。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只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问题,而不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上述两者的“根本分歧”问题。实际上,这不是论述的角度问题,而是对唯物史观本体论的态度问题。唯物史观本体论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从他们否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本质属性,否定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看,显然是与唯物史观的上述根本原则相违背的,因而是错误的。历史观的错误必然导致他们对于“实事求是”方法论在理解和运用上的错误。上述对于欧洲历史事实的曲解就是明证。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而奢谈“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实则是将一元的唯物史观二元化。其结果必然是南辕而北辙,适得其反。
据说,历史喜欢捉弄人:明明是从这个房间走进去,却偏偏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从新时期中国史坛所出现的这股非社会形态化思潮的走势来看,特别是从近年来的发展势头来看,重提历史研究“走错房间”的“殷鉴”并非“杞人”之“忧”。因此,我认为这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隐忧,似不为过。
注释:
①参加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修订者有:吴荣曾、田余庆、吴宗国、邓广铭、许大龄、林华国等。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③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69、474页。
④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9、11页。
⑤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0—512、29、91、93—95、83页。
⑥新时期修订再版的两部中国通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之所以没有包括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新时期续编后,全书改名《中国通史》),是因为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只限于唐代以前的相关历史,而范著《简编》唐五代以前部分已于1965年修订出版,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故不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除第1册外,其余各册都在新时期修订出版。考虑到所讨论问题的历史连续性,故将第1册放在新时期与其他相关内容一并论述。
⑦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29、140、134—136、246、173、263—264、352页。
⑧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15、109—110页。
⑨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2、36—39、67—72页。
⑩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9、227、229、204—205、167—171、454—465页。
(1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第173—174页。
(12)该书于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何兹全文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新版。
(13)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520—521、29页。
(14)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序言》,第2—3页。
(15)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271页。
(1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6页。
(17)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0—823页。
(18)建国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54年由《红楼梦》的讨论而引发的对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持续至60年代初;第二次开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持续到80年代末。
(19)详见李文治:《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张寿彭:《“两汉资本主义萌芽”说质疑》,《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5年第5期等。
(20)李文治:《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21)魏金玉:《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2)罗仑:《关于清代山东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道路问题》,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84页。
(23)李文治:《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24)吴量恺:《试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清史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5)详见拙文:《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历史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3期;《从历史研究现状看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在当今所面临的挑战》,《云梦学刊》2004年第3期。
(26)《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
(2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9—150、15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29)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页。
(3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155—156页。
标签:中国历史论文; 中国通史论文;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文; 历史学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古代社会论文; 中国史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