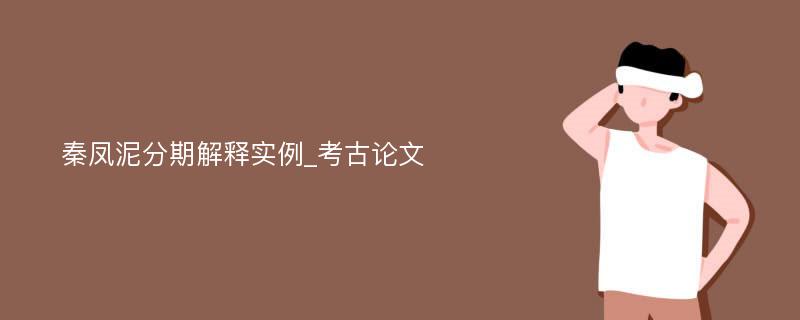
秦封泥分期释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封泥在关中的出土,最早约到清末。但由于当时封泥研究刚刚起步,于是见诸著录的秦封泥往往被认为是汉物,只有极少品种被明确为秦。上世纪90年代后期,西安相家巷地区盗掘出土大量封泥,而在流散中被路东之先生收购并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者,周晓陆先生即定其时代为秦①。而同时出土的流散封泥,后分散收藏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②、澳门珍秦斋③及日本等地,并陆续公布。以此为契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该地进行了发掘,收获颇丰。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亦在此进行了清理,并公布了相关发现④。
对于西安相家巷出土封泥时代的认识,在学界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周晓陆、路东之、庞睿在最初公布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封泥时提出,它们“大致在秦统一直到二世时”⑤,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则相对宽泛,认为“今天我们说秦印、秦封泥,应理解为年代可上溯下延,以不远于秦代为近是”⑥。而张懋镕先生则专门对其时代做出分析,认为这批封泥“下限在秦二世,秦朝灭亡之前,至于上限,我们认为在战国晚期,大约不会早到吕不韦执政时期”⑦,此说之后基本上被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所认可,“目前所谓‘秦封泥’的上限可以达到战国晚期秦国遗物,大约难以早到吕不韦执政的时期,而其下限,可以达到秦二世时期;超过两千枚封泥的确切时代,大多在秦始皇统一这一段时间的左右”⑧。
而在大多数学者认可其为秦封泥时,学界也曾出现不同的意见。如李陵先生不同意其为秦之遗物,认为它们“上限起自惠帝即位的公元前195年,下限止于文帝二年即公元前178年,前后共18年”,是一批上下限都非常明确的汉代早期遗物⑨。对此,王辉先生与我都分别著文对其加以反驳辨正⑩,史党社、田静先生也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补充(11)。此后,就极少有学者再认为此批封泥为汉物(12)。
在研究相家巷出土秦封泥之初,因公布的封泥均属流散物,因此对其时代的考证,只能以封泥内容参照文献和有关出土遗物开展。而在刚发现秦封泥时,受商贾欺瞒,甚至连确切出土地点也难以确定——李学勤先生指出,这类似于甲骨文发现初期的情况(13)。但很快,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发掘明确了秦封泥的出土地。不过,由于此次出土封泥的数量、品种及出土信息未能及时公布,因此随后学者的研究也还只能基于流散封泥。而正因这些封泥缺失了出土地层,学者就难以根据出土情况开展考古分期,只有如张懋镕、孙慰祖等少数学者,从封泥内容及字体风格方面,较粗略地指出封泥存在早晚差异。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发掘资料的公布,上述遗憾大为改观。这次发掘,不仅从地层上证明相家巷封泥“应属战国晚期或秦代”,不会晚到汉,只能是战国秦和统一秦的遗物,而且还出土了以往未发现的“酆玺”等封泥,使相家巷封泥中存在战国遗物的认识得以落实,进一步解决了秦封泥发现以来其所属年代的争议,也免去了学者心头有关真假的疑问。此外,随着湖南里耶在出土大量秦代简牍的同时也发现与西安相家巷所出封泥风格一致的“酉阳丞印”等封泥,西安相家巷所出封泥就不仅有了直接的地层依据,且更有湖南的出土品为证,时代为秦已不容置疑。
目前,关于西安相家巷所出秦封泥时代的认识,无论是李学勤先生,还是张懋镕等先生,基本上提的都是一个较宽泛的时间范围。而在这个时间范围内,至少包含战国秦、统一后秦始皇秦、秦二世秦等三段。当然,按李学勤先生意见,三段外还当有汉初,组成四段(随着有关发掘资料的公布,秦封泥中有汉初的可能性正逐渐被排除)。而若考虑到统一秦仅十余年时间,将统一秦再细分为秦始皇秦和秦二世秦,在考古学上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4)。因此相家巷秦封泥的时代,也就只能粗略地分为战国秦与统一秦两段。不过虽有如此划分,但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除马骥先生曾有专论外(15),基本上多为零言片语,对相家巷封泥中的哪类封泥该属哪个时段,并没有学者做过专门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根据文献及睡虎地、里耶秦代简牍等出土资料,对已公布的相家巷秦封泥中的一些品种进行初步分段(16),不当处请方家正之。
一、“玺”类封泥
目前在考古发掘和流散的秦封泥中,带“玺”字的封泥大体有六种,为“酆玺”、“厩玺”、“请玺”、“寺工丞玺”、“衙丞之玺”、“客事之玺”(17)。其中,“酆玺”中“酆”为地名,刘庆柱、李毓芳先生认为其“当为西周丰京故地的‘丰’”,与“衙丞之玺”中的“衙”一样,都是具体地名(18)。而“寺工丞玺”中的“寺工”与“厩玺”中的“厩”均为秦职官,屡见于秦铜器、陶器铭文,在秦都是一些地位较低的职官。“请玺”中的“请”,马骥先生指出原有“请乡之印”封泥,“请”为乡名(19)。
传世文献对“玺”、“印”二字演变有较多记载。如东汉蔡邕《独断》:“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春秋左氏传》曰:‘鲁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称玺者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纽,唯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类似内容还见卫宏《汉官仪》。从文献看,汉人认为“玺”字在秦统一前有较广使用,到统一后则仅天子方用“玺”,“印”则不受其限。
传世文献之外,云梦秦简中也有类似内容(20)。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规定:“亡久书、符券、公玺、衡羸(累),已坐以论,后自得所亡,论当除不当?不当”。《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也载:“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钱,亦封印之”。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的时代,学者已指出其抄写下限不超过《编年纪》截止的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反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秦统一前的秦国制度(21)。由于秦在统一后曾对旧制有大规模改定,因此睡虎地秦简所反映的基本都是改定前的情况,但也有一些统一后改定的内容。如秦简《法律答问》中出现“公玺”,而《金布律》中就不用“玺”,而是“以丞印印”。整理小组指出,其中“公玺”相当于后世“官印”,说明一般秦官府用印确实在统一前被称为“玺”,但从“以丞印印”可知,至迟秦统一前已大体不用“玺”来称呼官印了。
因此从传世文献和秦代简牍看,含“玺”字封泥的时代,大体应在秦统一之前。也就是说,“玺”类封泥基本都应是战国秦封泥。秦封泥中“酆”、“请”等县、乡机构用“玺”的情况,正与《独断》载“玺”成为天子专用印称谓始于秦始皇统一的记载相符。
二、“泰”、“大”类封泥
秦封泥中有31种“泰”、“大”类封泥的内容可对读,其中有“泰医丞印”、“泰医左府”、“泰医右府”、“大医”、“大医丞印”等5种,“泰行”、“大行”等2种,“泰仓”、“泰仓丞印”、“大仓丞印”等3种,“泰内”、“泰内丞印”、“大内”、“大内丞印”等4种,“泰官”、“泰官丞印”、“泰官库印”、“大官”、“大官丞印”、“大官食室”、“大官飤室”、“大官左中”、“大官幹丞”等9种,“泰匠”、“泰匠丞印”、“大匠”、“大匠丞印”等4种,“泰史”、“大史”等2种,“康泰后寝”、“康太后寝”等2种。除此之外,还有“泰厩丞印”、“泰宰”、“泰卜”、“泰山司空”、“泰上寝印”等5种,“大陆”、“大府丞印”、“蜀大府丞”、“大田丞印”、“大尉府襄”、“大尉之印”、“大原大府”、“大原守印”等8种单独出现的“泰”、“大”类封泥。
对于上述封泥中“泰”、“大”二字,目前多数学者仅讲“泰某”亦作“大某”、“大某”亦通“泰某”,或“泰,太者,大也”等等(22),少数学者则注意到它们应存在时代差异。如黄留珠先生曾在秦封泥发现之初即对此有所探讨(23)。他在分析“泰行”时提出,其“存在或为秦物或为汉物两种可能。如系前者,其时间当在战国末至秦统一初之间,如是后者,则应在西汉初改典客为大行令之后。当然,这里也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即完全否定‘泰行’封泥为秦代之物”。周晓陆等先生认为“至迟到秦统一,秦行人就改为泰行”(24)。孙慰祖先生从“西汉印中,已基本不再用‘泰’,仅南越尉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官印仍因秦制……可反证‘太’字做‘泰’字本是秦的旧体”,但未指出二字孰早孰晚(25)。刘庆柱、李毓芳先生也指出相家巷所出秦封泥中“‘泰官’封泥占绝大多数,‘大官’封泥甚少”,而“汉代封泥多为‘大官’,‘泰官’甚少”(26),从“泰官”、“大官”数量与时代变化的角度,间接提出“泰”早于“大”的认识。可以说,在“泰”、“大”类封泥的时代上,以往研究大体认为先“泰”后“大”。王伟先生更提出,“写作‘泰’者是统一之前的写法”(27)。但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可能并不成立,或者说问题要远远复杂于此。
首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六年)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在二十六年统一后,不仅制度多有改变,而且还进行了许多“正名”的举措。如将“王”改“皇帝”、改“命”为“制”、改“令”为“诏”、独天子可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到二十七年,则“更名河曰‘德水’……命民曰‘黔首’,同天下书”(28)。到三十一年还“更命腊曰‘嘉平’”(《史记·六国年表》)。在这场大规模名号更易中,“泰”被大臣重点提了出来。虽后来秦始皇自号“皇帝”,未用“泰皇”,但尊庄襄王时用“泰”,则表明其对“泰”字的肯定(从下引里耶木牍看,今传本《史记》中“太上皇”当为“泰上皇”)。
其次,据里耶古城J1第8层出土的455号木牍,“毋敢曰王父,曰泰父”,“庄王为泰上皇”(29),均用“泰”而非“大”。里耶J1出土简牍的时代,张春龙、龙京沙先生已指出“为秦始皇(王政)二十五年至二世胡亥二年,8-455号木牍书写的时间自当在此年限之中”。而该木牍均为“秦始皇称帝后改制的诸多事物名称的改变”情况,现残存56种之多的更名之举。其制作“背景也极明确,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其议帝号’的具体整治措施之一种,其内容为诏令无疑,而不是当时某些人的个人设想之记录”。这样借该枚木牍,学界开始在《史记》之外,较全面地见识了秦统一后更名改号的规模。胡平生先生已指出,秦始皇统一后,旧称谓更改为新称谓的数量远多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30)。故而从木牍改名易号用“泰”而非“太”或“大”的情况看,在秦始皇统一之后的更名,应是“泰”而非“大”。
第三,在基本上为秦统一之前的睡虎地秦简中,也有类似使用。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内史课县,大仓课都官及受服者”,“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讎食者籍。仓”。《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都官输大内”,“县、大内皆听其官致,以律稟衣”。《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大官、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课殿,赀啬夫一盾”。《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其大厩、中厩、宫厩马牛也,以其筋、革、角及其贾(价)钱效,其人诣其官”。
由于睡虎地秦简基本为秦统一之前,因此简文中职官用“大”非“泰”的写法表明,统一前应是“大”而非“泰”。
第四,岳麓秦简0706号简: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三川、颍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0194、0383号简:……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颍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31)。
岳麓秦简中的“泰原”,即前述相家巷封泥中的“大原”。由于岳麓秦简的《日志》包含了“秦始皇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的月份干支”,而整体上各简的“形制和文字风格多不一致”,“书写风格多达8种之多”,并不能保证出于一墓,其中纪年早晚均有(32),因此上述几枚简牍的时代就尚有争议。陈伟先生认为它们是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灭楚后,边境往东推进时的反映(33)。王伟先生则根据“岳麓秦简0083、0163、1219号简文中的‘廿五年’”,认为相关郡名是在“秦统一之前”;并认为0383简中的“绾”,应与“同类简文多次出现的‘南郡假守贾报州陵守绾、丞越’……是同一个人,即州陵县的临时县令”(34)。但我认为,从0706号等简所涉内容多达数郡,反映的是对全国范围内“戍者”加以安排的情况看,似应非州陵一县假令所能持,其论恐有不当。据里耶J1出土的8-455号木牍中关于“边塞曰故塞,毋塞者曰故徼”的更名规定,从岳麓秦简0383号简中出现“故徼”分析,这几枚岳麓秦简大体应是记秦统一后事,“泰原”是秦统一后才有的名称。
第五,时代为秦统一后的周家台秦简《日书》中,有“人皆祠泰父,我独祠先农”语(35),与前述里耶古城J1第8层出土455号木牍中“毋敢曰王父,曰泰父”内容一致,再次反映出秦统一后“泰”字的使用。
因此综上分析可知,据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资料,秦统一后秦政府在采取书同文等一系列措施过程中,将原在战国秦时使用的“大”改为“泰”。据此前述“大”类封泥就基本应为战国秦物,“泰”类封泥则为统一之后所留。而如学者已多次提及的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数量较多“泰官”封泥的情况,虽可理解为南越国制度的相对滞后,但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秦统一后相关制度在南越地区的保留——礼失于朝而求诸野。当然,从很多文献看,汉代的很多官名从“泰”变回到“大”。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泰官”封泥说明,在汉政府中央职官名称已恢复用“大”时,南越国仍保持着秦统一后用“泰”的传统。
虽然我们至今还无法证明汉初什么时候将“泰”回改为“大”,但至少在秦封泥中,“大”类封泥应是秦统一前物,“泰”类封泥则明显要到统一之后(36)。
三、“灋丘丞印”、“废丘丞印”、“废丘”
除前述“大”、“泰”类可以对照的内容外,在秦封泥中还有一些品种也可以对读。如“灋丘丞印”、“废丘丞印”和“废丘”3种封泥。学者已指出,“灋”是古文“法”字,而“灋丘”就是“废丘”。这类封泥的相对早晚,通过文献可基本确定。《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槐里”条:“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史记·樊哙列传》:“下郿、槐里、柳中,灌废丘最”。《史记·高祖本纪》:“走废丘”、“引兵围雍王废丘”。秦亡前写法为“废丘”,“灋丘丞印”早于“废丘丞印”。《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有“灋丘”:“告灋丘主,士五(伍)咸阳才(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鋈其足……灋丘以传,为报,敢告主”。故宫博物院藏“灋丘左尉”铜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三年大将弩机”刻“灋丘”二字,弩机时代考证为公元前233年(37)。“灋丘”时代早于“废丘”。“灋丘丞印”的时间大体应早到秦始皇统一前,较“废丘丞印”要早,但究竟“废丘”是秦统一后写法,还是统一前已开始,目前资料尚不能确定。
四、“上寖”、“泰上寖”
相家巷出土有“上寖”、“泰上寖印”等两种封泥。“泰上寖印”据前引《史记》和里耶秦代木牍,“泰上”指秦始皇去世之父庄襄王,则“寖”指庄襄王陵寝,此封泥应是秦在统一后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后的产物。“泰上寖印”为统一秦的秦封泥。
而“上寖”,目前分歧较大。史党社、田静先生认为,“上寖”是设立于秦始皇生前负责管理秦始皇陵寝的专设机构,其上限不早于信宫修建即公元前220年,下限不晚于始皇死即前210年(38),周晓陆、路东之先生认为,“上寖”是咸阳附近的一处寝宫(39)。王辉先生认为“‘上寝’即‘尚寝’,其职责是服侍皇帝、后之寝卧”(40)。概言之,其分歧在于“上”是秦始皇还是泛指,“寖”是寝殿还是陵寝。对此我认为,据蔡邕《独断》:“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之),但言上,不敢泄渎言尊号,尊(尊)(王)之意也”。可见“上”是对尚在世帝王的尊称。因此“上寖”中的“上”应是一位在世的秦帝王。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竘社。生共公。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文献中有“高寝”、“太寝”、“受寝”等内容,因此“上寖”封泥中的“寖”,就当如周晓路等先生提出的,是指生人居住的寝殿,非指陵墓中寝。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秦始皇陵园出土“丽山食官”陶文及下引“丽山食官”封泥看,秦始皇陵有专称——“丽山”,“上寖”应不会是秦始皇陵寝。
从“上寖”封泥和“泰上寖印”封泥中“上”、“寖”二字风格基本一致看,“上寖”应与“泰上寖印”一样,都是秦统一后遗物。因当时“上”为始皇,“上寖”封泥则应是负责始皇寝职官的印章所抑。也就是说,“上寖”是秦统一后为秦始皇服务的机构所留。当然,据此也可知“泰上寖左田”这枚传世秦印的时代,也应是秦始皇统一之后。
五、“丽山食官”、“丽邑丞印”
相家巷出土有“丽山食官”和“丽邑丞印”两种封泥。从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秦始皇陵园不断有“丽山食官”等内容的陶文、瓷文发现,学者目前已一致认为“丽山”应是秦始皇陵专称,故“丽山食官”当指丽山寖园的食官,而“丽邑”是在丽山秦始皇陵园附近设置的陵邑。王辉先生指出,它们都是秦二世时所设立的祭祀始皇陵的职官,“丽邑丞印”封泥是典型的秦二世时期封泥,“对出土封泥的断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1)。
六、秦封泥分期验证
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上文对57种秦封泥进行了大致的时代划分,将其确定到战国秦、统一后秦始皇秦、秦二世秦三段之中。虽然这些封泥种类在已发现800余种秦封泥中仅是少数(42),但还是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开展秦封泥分期工作的可行。当然,上述分期是否合适,还需出土地层的检验。
据已发表资料,发掘出土秦封泥的地层分早晚两期,T2③、T3③为早期地层,TG1为晚期地层。对照前文揭示的具有早期特征秦封泥种类,其大部分发现于早期地层之中,而具有晚期特征的秦封泥则基本上都出自晚期地层。如“灋丘丞印”(2000CH相1T3③:11)发现于早期地层,“废丘丞印”(2000CH相1TG1:8、65)出土于晚期地层。“大内丞印”(2000CH相1T2③:11)、“大匠丞印”(2000CH相1T2③:36)、“大官丞印”、“大官□□”、“大官丞□”(2000CH相1T2③:14、82、47和2000CH相1T3③:4)、“大仓丞印”(2000CH相1T2③:40、49)出土于早期地层,“泰匠丞印”(2000CH相1TG1:21、68、78)、“泰仓”(2000CH相1TG1:53)发现于晚期地层。“丰玺”(2000CH相1T2③:32、76、130)、“寺工丞玺”(2000CH相1T2③:133)均出于早期地层。因此前文通过文献考察得出的结果,基本与发掘出土秦封泥的地层埋藏情况吻合。
当然,据发掘资料,在早期地层出土的封泥中也出现个别上面论证中指出具有晚期特征的封泥。如“废丘丞印”(2000CH相1T3③:44)出土于早期地层。这种情况,首先可能是因该职官变化要早于前文揭示的更改官名时间推断,而我们也并不能确定“灋丘”与“废丘”的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其次则可能与发掘中对早晚交接带的划分有一定关系,即不排除工作中将个别晚期地层和早期地层交接带遗物归入早期地层的可能。此外,具有前揭早期文字特征的封泥也有出土于晚期地层的情况,如“大□官□”(2000CH相1TG1:84),而这对秦封泥分期推断影响不大。因为一是晚期地层可出现早期遗物,二是职官变化肯定远复杂于残存至今少数文献所反映出的情况。
封泥作为文件的附属物,在被揭取后它就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历来封泥发现的情况看,秦汉时期封泥往往于一地点集中废弃或埋弃。发现它们地层的早晚,大体即能反映出它们使用时间的早晚。但由于目前公布的大部分秦封泥均为盗掘出土,早已丧失原生地层,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发掘中获得的秦封泥地层关系,就成为可资使用断代的唯一依据。当然,在汉城队发掘之外,还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同地发掘,这些资料虽尚未公布,但期望今后它们的发表,不仅能增加秦封泥的种类和数量,更能提供一些用来推进秦封泥分期研究的地层关系。
虽然上文开展了秦封泥的分期探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即是现可分期封泥的全部。据有关资料,其实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如从里耶古城J1第8层445号木牍内容看,有“郡邦尉曰郡尉”、“邦司马曰郡司马”、“毋曰邦门,曰都门”等更名内容。而在已公布的秦封泥中,“邦”、“郡”、“都”封泥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庞大,因而结合文献资料对它们开展分期的条件也已具备。此外由于本文分期的秦封泥种类和数量都已较多,故据分期结果对它们进行图像学分析的条件也大体具备——先从中找到每时段封泥的特点,再据这些共同点对其他未开展分期的秦封泥进行初步分期,在不断修改和调整中趋于细化。在开展封泥分期后,过去很多据现有封泥时代得出的认识,就有了更确切的时间范围,有关认识也自可进一步修改。同时在对秦封泥分期后,对有关制度——秦郡县、职官等相应会有一些新的判断。而这些工作限于篇幅,只能今后另文开展。
《秦封泥集》曾据所收秦封泥字体,指出其中不仅有许多以往不见的古异体字,也有如“中厩”、“重泉”、“西盐”、“麋圈”等“表现了早期小篆的气息,反映了更早传统的孑遗”的品种。而“中厩”的“中”,“御府”的“御”,“居室”的“居”,“西共”、“西盐”、“西成”的“西”,“邓丞”的“邓”,“寺从”的“从”都有两种写法,“印”、“雍”更有三种字形,“这种现象对认识‘书同文’过程中的波动,对总结汉字的艺术化处理,都有一定的意义”。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秦封泥中同字字体的差异也应与不同品种秦封泥的时代变化有关,是不同时段的产物,字体不同既是秦封泥的发展结果,也是开展秦封泥进一步分期的重要依据。
①周晓陆、路东之:《空前的收获,重大的课题——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秦封泥综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②a.倪志俊:《空前的考古发现,丰富的瑰宝收藏》,《书法报》1997年4月9日。
b.傅嘉仪、罗小红:《汉长安城新出土秦封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封泥初探》,《收藏》1997年第6期。
c.王辉:《秦印封泥考释(五十则)》,见《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
③孙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④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b.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⑤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⑥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⑦张懋镕:《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和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⑧周晓路、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⑨李陵:《汉长安城出土印泥的断代与用途》,《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9日第3版。
⑩a.王辉:《也谈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断代》,《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7日第3版。
b.刘瑞:《也谈汉长安城出土封泥的断代与用途》,《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3期。
(11)史党社、田静:《新发现秦封泥丛考》,见《秦文化论丛》(六),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12)白于蓝在一篇文章中,认为相关封泥为汉代遗物。见白于蓝:《释包山楚简中的“巷”字》,《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
(13)李学勤:《秦封泥集》序,三秦出版社,2000年。
(14)张懋镕先生就曾指出“这批封泥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有可能早到战国晚期,但这一类数量很少。第二类数量很大,无论从字体、书体、笔划的纤细程度来分析,风格非常接近,显然是一个时期的文物,无法再细分出早晚来”。而马骥先生也指出,“由于秦国和秦代一脉相承,而秦代又国祚短促,时仅15年即告覆亡,要想从数量众多的秦式封泥中把统一前后划分开来的确不易”。见马骥:《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7日第7版。
(15)马骥:《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7日第7版。
(16)本文封泥品种除另行指出外,均引自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西泠印社,2010年。
(17)《新出封泥汇编》0134号封泥释读为“邦尉之玺”。据拓片,该封泥残破较甚,“之玺”二字无存,故此处暂不从引。
(18)同④b。
(19)同(15)。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指出“此处一般官印称玺,是秦统一前的制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
(22)任隆:《秦封泥官印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
(23)黄留珠:《秦封泥窥管》,《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24)同⑤。
(25)孙慰祖:《封泥的断代与辨伪》,见《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26)同④b。
(27)王伟:《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郡名称补正》,《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
(28)此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于始皇二十六年,《史记·六国年表》记于二十七年,应以年表为正。
(29)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见《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下同,不再出注。
(30)胡平生:《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性质刍议》,见《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已公布的岳麓秦简内容,表明里耶J1秦简8-445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有法律条文对其加以细化。如里耶木牍中有“诸官(名)为秦,尽更”,规定在官吏的人名中若有“秦”字都要修改。而岳麓秦简2026则有令曰:“黔首、徒隸名为秦者,更名之。敢有有弗更,貲二甲”,则明确规定百姓、刑徒等名中有“秦”的都要变更,否则将有处罚。
(31)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2)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33)陈伟:《“江湖”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
(34)同(27)。
(35)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墓葬时代为秦二世元年。
(36)秦和汉初陶文中有大量的“大匠”及“大”类内容。秦“大匠”及“大”类内容陶文的发现地点,有秦咸阳宫、秦始皇陵附近遗址和林光宫、阿房宫等遗址。秦始皇陵的建设时间从秦始皇即位已经开始,所以出现“大匠”类陶文并不奇怪。阿房宫的建设时间在秦统一以后,但目前在阿房宫遗址区发现的“大匠”类陶文多为采集,而阿房宫遗址区分布有很多早期秦宫建筑,所以在科学发掘品公布以前,“大匠”类陶文反映的“大匠”职官应是早期书法。据文献记载,秦林光宫为秦二世修建,不过秦林光宫与秦甘泉宫是同位于一地,目前在秦林光宫发现的“大匠”类陶文也是采集所得,不能证明“大匠”时代为晚。至于汉初“大匠”陶文,是不同朝代的产物,可能有另外原因。当然不排除秦统一后中央已更官名,但实际生产中工匠仍使用旧“大匠”陶戳的可能。
(37)吴振峰、师小群:《三年大将吏弩机考》,《文物》2006年第4期。王琳认为“灋丘”是人名(见王琳:《有关〈三年大将吏弩机考〉的灋丘问题》,《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陈家宁对此加以反驳(见陈家宁:《也谈“三年大将吏弩机”的灋丘问题》,《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吴振峰对此也有辩证(见吴振峰:《“灋丘”即“废丘”辩证》,《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
(38)田静、史党社:《新发现秦封泥中的“上寝”及“南宫”“北宫”问题》,《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
(39)同⑧。
(40)王辉、程学华:《秦文字集证》,艺文印书馆,1999年。
(41)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
(42)王伟先生统计现在秦封泥发现有888种。其中残破封泥57种,单字封泥11种,其他封泥820种。杨广泰先生最新统计为434种,见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西泠印社,2010年。
标签:考古论文; 秦始皇论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文; 地层划分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文物论文; 汉朝论文; 战国论文; 秦简论文; 独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