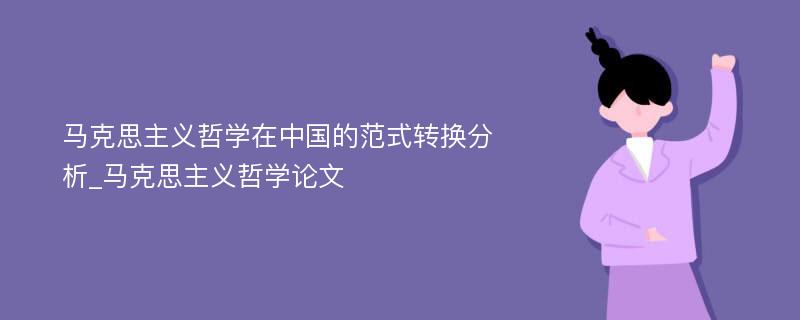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001-07
在上个世纪临近结束之际,中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了一阵回顾与展望的持续性热潮。这一热潮主要内容是要对几十年的哲学研究作一回顾、反思,并试图通过反思,总结经验,以更好地规划新世纪的哲学研究方向。大概从1995年开始,各种以“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题目为名的研讨会便接连召开,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在此期间,各种以“世纪之交”为名目发表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更是有数百篇之多。一直到了2006年,仍有人以“世纪之交”为题撰文。这一热潮并非单纯是对于世纪之交这一时间节点的某种情怀,而更是包含着人们对于哲学研究方式转变的期待。换言之,人们认为,世纪之交并非单纯新旧世纪之交替,同时也是不同的哲学研究方式之交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不仅寻求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进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为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论证,而这就涉及到了哲学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尽管由于受知识储备及时间局促等条件限制,这些讨论尚欠深入,但无论如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仍不失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作一番考察和评论亦有重要的意义。
一、哲学范式转换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
中国哲学界对研究范式或思维范式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步提出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在世纪之交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第三个阶段则是在近一时期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新的反思。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哲学界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借来了“范式”这一概念,并将之用于对思维方式及其转换的描述。这一时期哲学界虽然进行过对于研究范式问题的论说,但一般而言并不是关于整个哲学思维方式的。例如,于文军在1989年撰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突破与进展当然也首先要取决于新研究范式的确立”,而此处所说的“新的研究范式的主要内涵是从主体的实践角度,探讨历史主体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超越问题”。[1]此外,人们也在中西哲学比较、不同哲学家思想方式比较的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如姜澄清的《〈易〉的思维范式与东方审美思维》一文便是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的,而译文《康德之后的两种思维范式——谢林与费希特的对立》(泽迈克著),则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2]
第二个阶段始于1998年。这一年,国内哲学界正式提出研究范式转换问题的。最早论述这一问题的,据笔者考察,应该是王书明、耿明友、陶志刚等三人发表于1998年的《困惑中的进步——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的当代转型》一文。在该文中,他们明确提出了以下论点:“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困惑中开始了思维转型,即经历了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范式,再向人学范式的转换。”[3]在这一年,高清海、徐长福二人也发表了《力求哲学范式的及早转换——对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主张》一文,提出了“哲学范式转换是指哲学的思维方式、观念系统、理论格局、社会功能的总体性变迁”,而“哲学范式转换在其内在方面的含义是从‘物’转向‘人’,在其外在方面的含义是从‘一’转向‘多’,并且二者不可分割”。[4]随后,在1999年,王南湜发表了《启蒙及其超越》、《论哲学思维的三种范式》,高飞乐发表了《百年历程:哲学的价值论转向》,[5][6]对哲学范式转换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间,还有一批相关论文问世,深化了这一讨论,主要有:衣俊卿的《论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的走向》,徐长福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邹诗鹏的《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刘怀玉的《论马克思的现代哲学范式革命》,仰海峰的《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7][8]
第三个阶段集中于2008年。在这一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又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关于这一问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一批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有:孙正聿的《对作为“范式”的哲学教科书的检讨与反思》、《伟大的实践与实践的哲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汪信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郭湛的《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孙利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意义——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李成旺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与马克思哲学的革命》,胡梅叶的《从实践唯物主义到生存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演变的回顾与反思》,何中华的《论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重建和变革》,张再林的《“殷鉴不远”:当代中国的哲学建设必须直面由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理论转型》等。[9][10][11][12]在这些文章中,人们对思维范式转换问题又从新的理论立场作了审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域。
二、“范式”与“范式转换”概念使用的分析
虽然国内学界所使用来描述哲学研究方式变化的“范式”一语都源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且这20多年来有这么多的学者撰文讨论哲学研究范式以及范式转换,但“范式”这一概念却没有一个为人们所共同肯定的明确定义,人们往往是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这一概念。为了使下面的论述具有比较确定的含义,我们需要对学界使用“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略加辨析。
粗略地梳理一下20多年来国内学界对“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的使用,大致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类是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意义上使用的。如王书明等所说的“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范式,再向人学范式的转换”,[3]高飞乐所说的“从本体论哲学范式到认识论哲学范式再到价值论哲学范式的变革”,[6]徐长福所说的从“物”的哲学范式向“人”的哲学范式转换,[8]凌新所说的“由哲学范式向科学范式的转变”,[13]衣俊卿所说的“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另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14]冯平所说的“看世界的哲学”与“改造世界的哲学”,[15]孙正聿所说的“由朴素实在论思维方式向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转换”,[9]汪信砚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1]何中华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知识论向本体论的过渡,一是由本体论向存在论的过渡”,[12]以及笔者所说的范式转换,所论及的“范式”一语大体上都是指“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第二类是在研究进路或侧重点意义上使用的。如金民卿所说的“重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种,即实践唯物主义解读、实践人道主义解读、人学解读、文本解读、文化解读”,[16]王素瑛所说的“文本的解释性对话与时代的问题式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的对话范式”,[17]袁凌新所说的“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8]张华所说的“研究范式上由体系研究向问题研究转变”,[19]韩庆祥所说的“文本解读”、“对话比较”、“中国化取向”等三种创新范式,[20]吴元梁所说的“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已经出现的研究范式分为问题研究范式、文本研究和解释范式、比较与对话范式”[21]等,所说的“范式”大致上都是在研究路径或侧重点一类意义上使用的。第三类是在笼统的研究风格之类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的。如贺善侃所说的“现代哲学研究范式……在研究方向上,要强化面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倡导对话型研究方式;在研究视野上,要确立先导性研究目标”,[22]张定鑫所说的“提倡个性化研究范式”,[23]便是在一种比较笼统的研究风格之类意义上使用的。第四类是在以重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使用的,如吴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生态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生态范式必然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视阈,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4]
在第一类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者,人数较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学者提到“范式”概念时,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的研究者人数也不少。相比较而言,在第三、四种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的研究者就只有很少人了。
三、“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使用的合法性问题
事实上,可能是由于“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使用上的多义化甚至随意化,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虑,并进而质疑这一组概念使用的合法性。这使得我们也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作一些简单的辨析。
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卜祥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辨误》一文中提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国内哲学界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的情况归纳为三类:“其一,在一般的但也是空泛的意义上把‘范式’理解为‘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其二,在比较通俗易懂的意义上把‘范式’理解为特定的世界观”;“其三,在比较稳妥安全的意义上把‘范式’理解为特定的方法论,即库恩所说的‘技术’因素。”对这三类使用情况,他逐一进行了质疑。[25]
笔者以为,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卜祥记所说的“范式”概念使用上的宽泛化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且如此宽泛的使用易使这一概念失去确定性,因而对之进行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人们的宽泛使用而否定继续使用这一概念的合法性。而且,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责怪中国学者错用了这一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使用上的含混性,库恩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范式”一词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含义就多达21种,[26](P77)且其后期又对“范式”概念做了某种修改或再解释。[27](P79-83)既然库恩自己对“范式”概念的使用就存在着极大的含混性,后来的研究者在借用这一概念时也就很难以一种清晰的方式使用了。况且,笔者以为,尽管国内学界在这一概念的使用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含混性,但总体上仍有某种确定性,即大部分学者都是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意义的“范式”及“范式转换”概念的确能够比较好地描述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抛弃这一概念,而是尽可能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使用。在本文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范式”概念限定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意义上,而不采用其他意义上的使用方式。
四、哲学思维范式转换的表述问题
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限定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意义上,那么,不难看出,在这一以上使用“范式转换”的论者,无论是认为这一转换是“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范式,再向人学范式的转换”,“从本体论哲学范式到认识论哲学范式再到价值论哲学范式的变革”,从“物”的哲学范式向“人”的哲学范式转换,从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的转换,从“看世界的哲学”向“改造世界的哲学”的转换,还是“由朴素实在论思维方式向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转换”等等,所欲说明的问题都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半个世纪的形态演变。关于这一形态演变,各位论者所指内容大致相同,但在具体如何表述这一演变过程时,则在阶段划分和名称上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先将这一形态演变作一简单的直观描述,然后再进一步讨论如何表述问题。
论者们一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种存在形态主要存在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当以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其典型代表。这一哲学的最突出特征是对人的能动性或主体性的抹杀,而表现方式则是将人类历史或社会生活自然化,也就是说,表现为抹平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区别,把历史观化归为自然观之推广或扩展。这种自然化的典范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那里,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而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作为自然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论者们也大都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来,哲学体系的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哲学研究也的确发生了变化。但一些论者把这一时期只视作为一个过渡性阶段,另一些论者则将之描述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并认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认识论的解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研究成了80年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另一则是这一阶段研究问题的方式都是以认识论框架为典范的,即是在主客体对立的框架中进行思考。而在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变化问题上,论者们的意见则似乎比较一致,即大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但如何表述这种范式,则名目繁多,诸如人学范式、人类学范式、价值论范式、生存论范式、文化哲学范式、实践哲学范式等等。
一般而言,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演变描述为上述三个时期的变化过程,是能为大多数论者所接受的,不同主张之间的差异则在于名称和诸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关于阶段划分上的不同主要在于,一些论者将之分为三个阶段,另一些论者则将之简单地分为两个阶段,而其中的不同又主要在于如何处理第二阶段。划分为三阶段者,又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将第二阶段与另两个阶段并列,一种是将第二阶段视为一个过渡性阶段,另一种则是进而又将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归并为一个与第三节段并列的更大的阶段。因此,就许多论者将第二阶段视为过渡性阶段或将之与第一阶段合并为一个更大阶段而言,两阶段论与三阶段论之间似乎也没有实质性差别。就此而言,总体上的两阶段划分或许是一个更易为大家接受的划分方式,因为它也包含了进一步划分的空间。
关于各阶段的名称,虽然论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案,但名称似乎也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从各位论者用来标示所主张转向的哲学范式的词语的类似性上,就可以看出来。诸如“人学”、“价值论哲学”、“‘人’的哲学”、“实践哲学”、“文化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实践论思维方式”等,所指向的大致上是相同的哲学研究方式:既不是从一个设定的客观的本体(精神的或物质的)出发,亦不是从主体自身的确定性出发,去解决哲学问题,而是从人的存在出发,从人的生活和实践出发,去理解和解决哲学问题。既然实质相同,用何种名称表述,就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了。当然,笔者认为,尽管各种表述都有其合理性,但用从理论哲学范式到实践哲学范式来表述这一转变过程要更好一些。因为当马克思批评以往的哲学家都只是解释世界,而要求将改变世界视为根本之时,他是将实践活动放在了首位,而将理论活动视为从属于实践活动的,这就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与理论哲学不同的实践哲学传统。因此,将马克思哲学视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哲学,而将它所批评的传统哲学归结为理论哲学,当能更好地表达马克思本人哲学革命的实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转换的实质。
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之问题
如果我们用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变来表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那么,不言而喻,这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根本性转换。在西方哲学史上,如果说是柏拉图开创了形而上学即理论哲学范式,而马克思则从根本上开始了对这一范式的反拨的话,那么这一转换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完成的;而在中国,则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转换过程被压缩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之中。如此急速的观念变迁,不可避免地是极其粗线条的。这种急速的粗线条转变的结果,便是会留下许多问题需要人们去逐步消化。这些问题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的:一是总体上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思维范式转型的理解问题给出清晰而系统的规定,二是如何在实践哲学范式的视阈中,重构一系列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避免地要给予某种解答的重要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前面描述的范式转换说能够成立,那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之深入发展的趋向或理论空间。
(一)哲学范式转换带来的总体性问题
哲学范式转换所带来的问题首先是总体上的问题,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规定实践哲学思维范式,二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性。
关于如何规定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对诸种实践哲学的含义作了一些辨析,认为在作为第一哲学和思维范式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与其他现代哲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28]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包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能够用实践哲学来涵括现代哲学,或者说,用转向实践哲学来表达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变。但是,由于实践哲学一语的含混性以及人们使用中的多义性,学界似乎至今还未达成一种对于哲学范式转型如何规定的共识。有不少论者在谈及实践哲学时,似乎往往不是在本文所理解的意义上,而是对之作一种比较随意的理解。于是乎,许多超越实践哲学范式的主张便被不断地提了出来。例如,已有人提出一种“后实践哲学”的主张。尽管这种声音在哲学界尚不响亮,但在美学界,一种“后实践美学”的主张却似乎要势头大得多。这里并不是说人们此外不能再提出“转向”问题,而是说,人们应该静下来对所使用的概念作一些澄清,尽量能够在共同的含义上使用这些基本概念,否则,只是自话自说,恐怕就很难推进思想的深化。
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性。虽然笔者曾对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作了一些辨析,但这一工作毕竟是十分简单的。如果我们肯定哲学从马克思以来发生了一种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换,且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的话,那么,实践哲学便不是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是马克思哲学的别名,而是一种共名,从而在同为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如何区别马克思哲学和其他实践哲学便成为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不少论者指出,实践哲学有着一个极为广泛的谱系。倪梁康说实践哲学包括“黑格尔以后的现代哲学”,哈贝马斯说实践哲学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布达佩斯学派、萨特、梅洛-庞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以及批判理论,也包括美国实用主义,伯恩斯坦说它甚至包括像克尔凯郭尔这样的哲学家的思想。[29][30](P72)[31](P123)面对如此庞大的哲学家群,如何将马克思哲学从中区分出来,显然是一项极为复杂、繁难的工作。但这一工作又是极其必要的。如果说人们往往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将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区分开来,那么,在实践哲学范式中,这种简单的方法已不存在。例如,在以往的哲学范式中,人们或者可以一方面用“唯物主义的”将马克思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用“辩证的”将马克思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区别开来。在后来,人们则多用“实践的”一语将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各种哲学区别开来。但在实践哲学范式中,这些简单的区分方式不再有效,因而我们必须通过具体的研究寻找其间的实质性区别。
(二)实践哲学视阈中的诸哲学问题
思维范式的转换是哲学思想中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对所处理的诸问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哲学中的诸问题而言,思维范式犹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2](P24)下面择其要者略举几例。
关于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也必然导致哲学基本问题的变化。黑格尔认为,“近代哲学的原则并不是纯朴的思维,而是面对着思维与自然的对立”,“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而近代哲学的“全部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把握住最高度的和解,也就是说,把握住最抽象的两极之间的和解”。[33](P6、7)恩格斯也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认为,虽然这一问题“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34](P223、224)这也就是说,古代哲学,依汪子嵩、朱德生等人之见,之所以表现为一般与个别事物之关系问题,[35]是由于其自我意识尚未觉醒,尽管一般之物只能是思维的产物,但却被当成了与个别事物一样的存在者。因此,古代哲学基本问题与近代哲学基本问题之差异只在于自我意识觉醒与否,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其实只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一种未自觉的表现形式而已。无疑,哲学基本问题的这种变化是与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内在相关的。古代哲学的思维范式决定了其基本问题只能是一般与个别之关系问题,而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则决定了其基本问题为思维与存在之关系问题。但无论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都属于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因而哲学基本问题具有内在的类似性。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是截然相反的哲学进路,一旦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为实践哲学,则亦必然导致基本问题的重大转换。事实上,在理论哲学之中,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其基本问题实质上都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二元关系。而在实践哲学之中,如果我们把理论与实践理解为人的两种基本活动方式的话,则理论哲学中的二元性关系转变为了理论、实践与实在之间的三元性关系。在这种三元性关系中,“实在”的含义大致上接近于二元关系中“存在”的含义,表示一种与思维不同的东西;而“理论”则比二元关系中的“思维”更少一些抽象性,大致上意指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其间多出来的一元是“实践”,其含义为人的一切实际性活动。如何解决这种三元性关系,就构成了实践哲学必须持续探讨的问题。
此外还有实践哲学中唯物主义的意蕴、辩证法问题、真理问题等等。如果实践哲学范式中哲学基本问题发生了相应的转换,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性关系转变成了一种理论、实践与实在的三元性关系,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含义也必然要重新界定。这一转变,同样也必然会导致辩证法、真理等问题内涵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