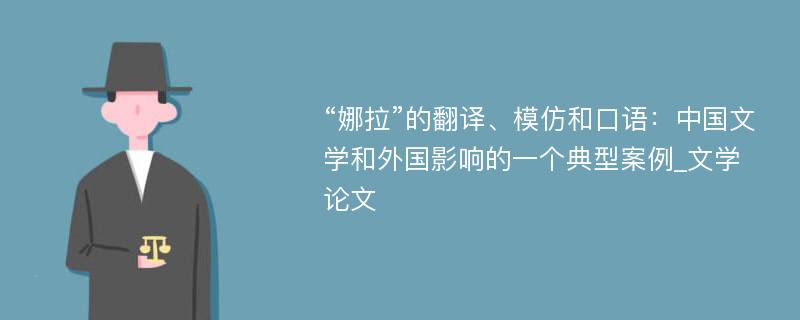
被译介、被模仿、被言说的“娜拉”———个中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典型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典型论文,娜拉论文,被译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如沈雁冰所言,“易卜生在中国是经过一次大吹大擂的介 绍的”。[1]自1907年鲁迅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将他和拜伦、雪莱等 一起称为“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的“精神界之战士”开始,1914年陆镜若在 《俳优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之剧》中又将其称为“莎翁之劲敌”、“剧界革 命之健将”,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1921年潘家洵 的译作编为《易卜生集》开始陆续出版,1928年3月20日《大公报·文学》发表了《易 卜生诞生百周年纪念》的长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易卜生作品的社会意义、艺术价值及 其局限性。“娜拉”就是在新文化先驱们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被损害民族文学 ”的热潮中,在易卜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就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新的人中没有一 个不狂热地喜欢他,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论他”的热潮中[2],飘洋过海来到了中 国。如果做时下颇为流行的关键词研究,那么在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无论是 做为剧作之名、人物形象,还是做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象征意义的指代,“娜拉”一 词都有着无法忽视的地位。因此,跟随着“娜拉”在现代中国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 理出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文学的某些关系。
一
据统计,从1918年至1948年,《娜拉》(也被译为《玩偶之家》、《傀儡之家》)先后 就有陈嘏、罗家伦和胡适、潘家洵、欧阳予倩、沈佩秋、芳信、翟一我、沈子复、胡伯 恩等九种译本(由于资料所限,暂时还不知道这些译本分别是从日文还是原文翻译过来 的),并多次被搬上舞台,如春柳社于1914年的首演,五四期间上海、北京等地的演出 ,1935年上海左翼剧社盛况空前的演出则蔓延全国,该年因此被称为“娜拉年”。随着 译作和舞台演出的大量出现,在新文学的创作中,也出现了众多被文学史和文学研究者 称之为——模仿或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娜拉式或有着娜拉影子的作品和人物。那么,此时 出现在译作和舞台上、出现在新文学的作品中的“娜拉”是怎样的形象呢?
完整地看潘家洵译的《玩偶之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易卜生文集 及单行本中大都采用了这个译本),在第三幕之前,娜拉还是一个把苦恼留给自己、把 快乐带给身边人,甘心做丈夫可爱、听话的“小鸟儿”、“小松鼠儿”,每天和孩子们 “玩玩闹闹”的活泼开朗的女性,为了给丈夫治病而借钱,为了丈夫的面子而隐瞒一切 ,甚至为了丈夫的前途而准备牺牲自己,这些都是建立在对丈夫的爱并相信丈夫也“爱 ”自己的基础上。而当真相大白,丈夫并没有如自己期望的挺身而出,反将罪责、怒骂 一股脑推给她时,她才明白自己过去是父亲的“玩偶女儿”、现在则是丈夫的“玩偶老 婆”,终于说出那句“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的名言而离家出走。相信在当时众多的译作和舞台演出中,都保留了娜拉这一人物形象 的生动、丰满,否则不会有那么强大、深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然,这也与新文化先 驱们的大力倡导分不开。
胡适不仅是“易卜生主义”的鼓吹者,因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3期上的《 终身大事》(最初由英文写成,发表时译成中文),又被称为模仿《玩偶之家》创作的第 一人。《终身大事》中的女主角田亚梅为了追求自由恋爱,给父母留下了“孩儿的终身 大事孩儿应自己决断”的纸条,便“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出走了。洪深在《中国新文学 大系·戏剧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中曾谈到“田亚梅好比是中国的 ‘娜拉’”,田亚梅之所以被看作中国的娜拉,或者说她与原作中的娜拉相同的地方, 在于为了婚姻自由而离家出走,不同的是一个离开的是丈夫的家、打算回到“从前的老 家去”,一个离开的是父母的家、可能会走进陈先生的家。胡适的剧作虽然尚显幼稚, 但却提出了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并为中国的娜拉们(文学作品中的、现实生活中 的)保留或勾勒出了一个基本的性格特征——为了个性独立而勇于反抗(父权、夫权或不 合理的社会),和行动特征——离家(父亲的家或丈夫的家)出走的姿态。可以说此后作 为人物形象、社会现象,或文学研究中所命名的“娜拉”,她所指代的含义都蕴涵了这 样的性格和行动特征,并逐渐成为现当代中国一个约定俗成的词语。
依此来看现代文学的创作,撇开那些随着《终身大事》蜂拥而出、故事情节颇为雷同 的“娜拉剧”不谈,在许多被文学史奉为经典的作家作品中,如鲁迅《伤逝》中说出“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 性》中被注入个性主义灵魂的历史人物卓文君、王昭君、聂嫈,茅盾《虹》中“将来 的事,将来再说;现在有路,现在先走”的“我行我素”的梅女士,曹禺《北京人》中 有着传统女性美德却终于觉醒出走的愫方。在这些生于不同年代和家庭、性格迥异的女 性身上,也都程度不等地闪烁着上面所总结的中国娜拉的性格或行动特征,并且在《伤 逝》和《虹》中都还提到女主人公对易卜生作品的阅读和评论,如梅女士起初对娜拉很 不以为然,很是欣赏为了家庭而牺牲爱情、与钱结婚的林丹太太,但最终她还是师法娜 拉而离家出走。
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的几部作品都出自男作家之手,然而对娜拉的阅读与评论,以 及可以用“娜拉”来命名的女性并不仅限于文学作品中。如先于五四运动十几年(1904 年)就离家出走、东渡日本留学的秋瑾女士,还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被 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写作的娜拉”的第一批现代女作家,是她们第一次那么集中地、 公开地、大胆地向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不再仅仅被男作家所言说,也不必像古代 的女性写作者“借固定的表达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思”、“借古人来抒个人的情怀”、 用“公共性掩盖着个人性”。[3]也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是行为方式还是精神气质,娜 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五四’这一代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现代女作家都是中 国的‘娜拉’。”[4](P16)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确有许多女作家经历过甚至不止一 次地经历过娜拉式的反抗与出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就是成名于30年代的萧红了, 她从父亲的家出走之后,又曾经三次从丈夫的家中出走,而她所追求的仍然是个性的独 立与人格的平等。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等启蒙者所看重的、也是许多女作家所身体力行 的毅然离家出走的反叛姿态,在她们的创作中却很少正面描写甚至避而不谈(散文除外) ,那么这些被称为“中国的娜拉”的她们更看重的是什么,所谓的“毅然出走”是否如 娜拉的形象一样被抽象化和单纯化了?
二
“娜拉走后怎样”这句经典的设问,是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文艺会上的讲演,也是研究者认为鲁迅发展并超越易卜生之所在:他在中国社会现实问 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指出走后的娜拉可能面临的两条路——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从而得出妇女只有获得了与男子相等的经济权和社会势力才 能真正得解放的结论,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青年指出了一条需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的道路。鲁迅在随后创作的《伤逝》,也被众多研究者认为是形象地展示了经济基础对 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决定作用,也是对一味乐观于娜拉潇洒出走者的当头棒喝。
沿着鲁迅“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论断,在现代中国及现代文学中并不难发现对它 们的形象阐释,包括子君离开父亲家、进入情人或丈夫家的出走方式。如《倪焕之》中 的金佩璋,曾是女子师范里成绩优异、有着很强自立意识的新女性,她摆脱门第观念和 家人的反对与倪焕之结合,但现实生活的琐碎很快使他们有关幸福家庭的梦想幻灭了; 另如40年代以“南玲北梅”并称的梅娘的水族系列《蚌》、《鱼》、《蟹》等作品中的 女主人公,仍然在封建大家庭内部的倾轧中,在两个家门之间徘徊犹豫、出出进进。在 许多作品中,女主人公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对改变命运的希望,大都维系在男性的身上 ,一旦失去男性的“爱”,除了回去与堕落(当然还包括死亡)似乎就无路可走,是不彻 底的独立意识,是谋生能力的缺乏,还是不相等的“经济权和社会势力”?这就如同子 君的死,子君从父亲的家中出走后最终又回到了父亲的家中,将她推向死路的,是最终 厌弃了她的曾作为她的启蒙者与爱人的涓生,是经济压力,是那个封建势力强大的黑暗 社会,是她在寻到感情的归宿后丧失了曾经追求的个性独立,是所谓个性主义与人道主 义无法调和的矛盾,还是这一切的合力?这是个颇有代表性的、耐人深思却难以定论的 问题,尽管它只反映了出走后娜拉的命运之一种。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 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作为历史上反抗压迫的社会 革命运动的‘酵素’(马克思语)而附属于社会革命运动之中。”[5](P20)也许正是由于 这一特征,现代中国社会及文学作品中的娜拉,在两个家门间出出进进之后,有的便走 向了广阔的社会洪流。如前面提到的秋瑾女士、《虹》中的梅女士,和在倪焕之死后突 然醒悟、决定去完成丈夫未竟事业的金佩璋。郭沫若在为纪念秋瑾而写的一系列文章中 曾谈到:“我认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 活的独立,在社会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 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就是那答案的内容。”[6](P2 20)在社会革命的风风雨雨中,梅女士们也许会像秋瑾一样献出生命,也许会动摇、迷 失甚至如《腐蚀》中的赵惠明一样堕落,但她们还是推动了社会解放洪流的前进,尽管 有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在宏大叙事中再次丧失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和话语,但比之于子君 的死、对男性依附之不可靠,她们所指出的走后娜拉的另一种命运也许有着更为光明的 未来。
张爱玲在一篇名为《走!走到楼上去!》的文章中,也谈到了娜拉的出走:“中国人从 《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 印象。”但是,“走到哪儿去呢?……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 们就会下来的。”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因为“做花瓶”、“做太太”、“做梦”、“ 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抄书”、“收集古钱”等都是上楼。[7](P75)虽然张爱玲 也很公允地说“不能一概而论”,但她用如此轻松、调侃的语调来谈论曾被启蒙者们十 分认真、严肃地思考、探讨过的事情,这其中除了思想意识、人生态度的不同,还包含 着一个时代的因素,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另一种思考。当“一般中国青年”已经从娜拉那 里学会了反叛与出走,当出走已经成为事实,现实生活的困境使她们再无余暇来温习或 标榜那有着转折意义的一瞬。就张爱玲自己而言,也曾有过惊险的出走经历,既16岁那 年在监禁中逃出了父亲那个阴沉、没落的家,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居住在现代公寓中的 名作家,而与封建旧家庭决裂的她的母亲和姑姑,也都是那个时代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与生活品位的职业女性。
然而她并未将自己的特立独行和谋生的能力,给予她笔下不得不离家出走的女性,如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因无法忍受丈夫的虐待而离婚回家,又因兄嫂的冷嘲热讽难 以在家久住,便决定在范柳原身上赌一把。和张爱玲同时的女作家苏青在自传体小说《 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中,则分别写了女主人公怀青难以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而 凄凉离家,和成为职业女性的怀青对当初离婚的后悔、以及想重建婚姻的梦的破碎(想 回也回不去了)。在这里,尽管白流苏和怀青所面对的问题(丈夫的负心、金钱的压力) 、所做出的选择(通过离婚而获得自由),与许多现实及文学作品中娜拉的出走很相似, 但是,她们点点滴滴寻找的只是平凡而切实的归宿,她们或许也曾有过对自尊、自立的 憧憬,但却没有丝毫慷慨激昂的“理想”和“追求”,以及五四式的挣扎、控诉和企望 。也许是启蒙者所“塑造”的并被我们所认同的娜拉的形象,是和反叛、进步、革命等 字眼分不开的,因此这时再用娜拉来称呼她们似乎显得十分牵强,但也许正是她们代表 了现代中国占多数的走后娜拉们的世俗命运。
前面已经涉及到,在原作中的娜拉和中国娜拉们从丈夫家出走的原因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对男性的失望。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谈到“娜拉要怎样才不走”,他举了 易卜生的另一部剧作《海的夫人》(也译为《海上夫人》),女主人公因从丈夫那里得到 了自己选择的自由(是否随昔日的爱人而去),便决定不走了,因此鲁迅认为“娜拉倘也 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同样,也可以假设白流苏、怀青等能够得到丈 夫的爱与尊重,或者可以进一步假设根本不存在不合理的社会与男权意识。但这假设毕 竟是虚妄的,从这预约的“黄金世界”里回看,现代文学中令娜拉们失望的男性形象基 本上有两种,一种形象比较单一,无论是包办婚姻还是自由结合,他们在婚姻中都扮演 着没有责任感、败家、虐待妻子或另寻新欢的角色,如上面提到的张爱玲、苏青的作品 和梅娘的《鱼》。另一种形象相对比较复杂,主要在于时代的变迁给他们所带来的变化 ,前面在追问子君的死时,曾提到作为她的启蒙者的涓生的责任,但是在鲁迅笔下、在 五四时期,涓生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忏悔,是可以理解并同情的。那么到了40年代师陀 的笔下,在写到这作为老师的“启蒙者”时,已充满了调侃与讽刺,如《马兰》中带着 马兰逃走的乔式夫,是一个翻译马克思著作的革命者(有研究者称之为“书卷革命者” 或“伪革命者”),他占有了马兰却并不爱她,自然得到了充满生命活力的马兰的背弃 ;另如《果园城记·三个小人物》中带着胡风英私奔又遗弃了她的那位“英雄”,即“ 我们在上海、北平常常看见许多这种自命不凡的大作家”之一,借给女学生看叶灵凤和 张资平的小说,在老家有老婆并按月从老家要钱。涓生与他们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他 之所以能得到理解与同情在于他的真实,无论是对子君由爱到无爱,还是对在自由、广 阔天空翱翔的向往;当然也不能否定乔式夫等人作为艺术或生活的真实性,也许在五四 那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新生事物中的投机者或负面因素尚未产生,也许是人们还无暇顾 及,但他们却一直关系着娜拉的出走及走后的命运。
在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曾提出被称为“中国的娜拉”的现代女作家更关注什么的问 题,之所以延宕到现在才回答,是想借着上面的论述来说明,她们是用自身的经历回答 了“走后怎样”这句把文学与现实问题纠结在一起的经典设问,她们写作时所关注的也 大都是走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无论是微妙的生命体悟、爱与美的哲思,还是高门 巨族与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民族、国家等社会大问题,还是个人的内心独白。 刘纳的《颠踬窄路行——世纪初:女性的处境与写作》中有这样一句话:“与出走到别 处的娜拉相比,来到写作领地的娜拉是最为幸运的。”也许她们与文学作品中的娜拉一 样有过心灵的痛苦挣扎与迷茫,有过缺衣少食的窘迫困境,有过职业女性谋生与谋爱的 艰辛,但她们之中毕竟有着冰心式的幸福家庭、丁玲式的走向革命与大众、张爱玲式的 特立独行,即使她们比作品中的娜拉有过更为难堪与难捱的悲惨经历,但就做人的尊严 和文章的千古事业而言,她们还是不枉此生的。这也许就是幸运之所在。
三
有研究者指出,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介绍迷入了歧途,即人们对他的思想的关注远远 超过对他的艺术的关注,因而只抓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进而言之,这也是当时译介 外国文学的整体特点,五四时期小说和话剧创作的幼稚朴拙便与此有关。但是,当时的 启蒙者对此也并不讳言,就像他们并不讳言自己曾受到过外来的影响,如胡适在《新文 学运动》中道“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 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仿佛就是对20世纪末期的研究者的诘难的提前 答复。这里便涉及到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接受的问题。
鲁迅的“拿来主义”应该代表了新文化运动者的基本态度,否则不会有后来所谓的“ 西方几百年的思潮、流派在短短十数年内就上演了一番”的评价(新时期后又重复了一 次)。但如鲁迅所言这“拿来”是有选择性的,五四时期对“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偏重 即是一例,同时也就意味着“拿来”有着很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但不同时期根据不同 的实际需要而特别提倡某些方面,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一直会被存而不用,何况当一思 潮或一作家的作品被译介过来以后,它所造成的影响或者说它的被借鉴和接受,是不可 控制也不可预测的,正如爱德华·赛义德在分析“旅行理论”最后一个阶段时所讲的, “已经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 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8](P28)这从上面对娜拉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演变过 程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所以,从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包括易卜生在内的 外来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或者说新文学对他们的接纳或吸收,还是存在着社会思想和文 学创作两个层面的,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创作中的侧重有所不同。
诚然,不是所有的外来思想都可以在本土落地生根,纪德在一次名为《文学上的影响 》的演讲中曾就此有过精彩的论述,如“影响因相似而起作用”、“影响不创造任何东 西,它只是唤醒”。[9](P347)《娜拉》一剧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中国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首先就是因为她吻合了新文化先驱们对吃人的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礼教的揭露、批判 ,以及对人的发现,对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疾声呼吁的时代精神,使得娜 拉的那句名言和离家出走,成为黑暗铁屋中的一道闪电,如袁振英在《易卜生传》中所 言:“当娜拉之宣布独立,脱离此玩偶之家庭;开女界广大之生机;为革命之天使,为 社会之警钟。”[10]这样,启蒙者从中寻到或发现了可以作为榜样的形象——大胆追求 人格平等、个性独立的叛逆者,而虽被唤醒却不知何去何从的青年人则看到了一丝可行 的光亮和鼓舞的力量。由此也可以明白,何以启蒙者们如此看重娜拉的出走,何以胡适 的《终身大事》虽幼稚却得到普遍的认同,因为正如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 ·导言》中所言:“在封建势力仍然强盛的中国,是没有女子敢做娜拉的,但正说明了 这出戏的意义。”
正因为娜拉被译介到中国的伊始,就与思想启蒙、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密切关联,一 个原本是易卜生“问题剧”中的文学形象也就必然会被赋予或承担更多的社会内容,如 作为对封建父权、夫权意识的控诉与反抗,作为人的觉醒、个性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等; 一个原本生动丰富的女性形象也就无可避免地被抽象成了一个指代明确的词语或“套话 ”,如前面曾从胡适的《终身大事》中总结出的中国的娜拉们所拥有的“勇于反抗”的 性格特征和“离家出走”的行动特征。而启蒙者们随后在对“娜拉走后怎样”的答案的 寻求中,又将妇女解放、个性主义思想同社会的总解放统一起来,使现实生活与文学作 品中的一些中国娜拉,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个人反抗而最终走向革命和社会大众。但是, 这其间也有前面曾论述的走向凡俗的个人生活的“娜拉”,本文一面因她们能从不合理 婚姻中挣脱出来、去寻找个人幸福,而将她们视为另一种类型的中国娜拉,一面又因她 们与启蒙者所倡导的革命、反抗等高大形象相距甚远,而觉得用娜拉称之有些不合适。 之所以有此两难,还是和新文化先驱们对娜拉所进行的启蒙话语的解读相关,而“启蒙 ”和“救亡”一直被众多文学史家视为现代文学的主流话语,只是理论、思想乃至人物 形象总是要回应着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环境,时空距离不仅使我们在另一个世纪有 了更多的言说空间和方式,如前所述,在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在师陀、张爱玲等作 家的笔下,就已经有了对娜拉、对与娜拉的出走相关的人事的另一种思考。
但新的思考并不能替代原有的思考,新的解读也并不意味着对过去解读的否定,就像 前面所讲的,五四运动时代的启蒙者从不讳言他们有着明确的目的性,鲁迅甚至用“急 于事功”来评价,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启蒙者对娜拉以及易卜生存在着“误读”的话 ,那么也是有意为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许正是这“急于事功”,才使得那么多青 年人能够从昏昏沉睡中醒来、出走,而那些出走到写作领域的,则开始了自己的言说。 而且所谓新的解读,就像纪德谈到文学影响上的“相似”与“唤醒”,或许是易卜生等 外来影响唤醒了启蒙者的个性主义,或许是启蒙者从他们那里发现了相似的主张,同样 ,可以说是娜拉教会了中国青年一种反抗的方式,也可以如前所述是启蒙者从娜拉的身 上发现了他们所要寻找的一个可以作为榜样的形象,便借用过来作为一个化身、一种寄 托,尽管在娜拉译介到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了秋瑾女士的离家出走并投身革命。之后, 有研究者在启蒙者对娜拉界说的基础上,在文学作品及现实生活中界说着被娜拉唤醒或 与娜拉相似的女性;有研究者又在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解构或质疑着启蒙者和主流文 学的界说,如前面曾提到有女性主义者认为那些走向革命和大众的娜拉(作品中的、写 作中的),在宏大叙事中再次丧失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和话语,而出现在男性作家笔下的 娜拉无论是死亡、堕落还是投身革命,也再次成为被代言者而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等等 。而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为自己的理论、主张所寻找的一种言说方式,只是这其中有 主流话语的煌煌巨言,有来自边缘话语的切切私言,也有新潮话语的惊世骇言。
无论是作为文学形象、社会现象还是一个有所指代的词语,“娜拉”之所以能引起如 此多的言说与思考,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对外来的思潮、文学经历了初期的认 同、启发或模仿后,要么因水土不宜而逐渐枯萎,要么会在新的水土的滋养下而日渐成 熟、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时,这新的作品或许还有着过去的影子,或许已面目全非 ,甚至如博尔赫斯所言,这新的作品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并赋予外来的思潮 和文学以新的意味。[11]在包括20世纪在内的中外文学的关系中,应该并不乏这样的情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