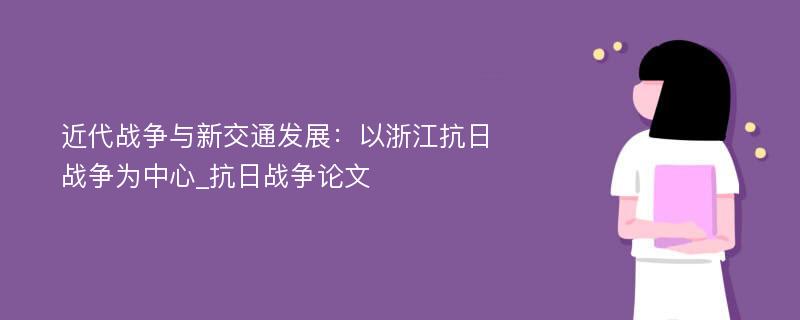
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发展:以浙江抗日战争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浙江论文,近代论文,战争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兵贵神速、先发制人,车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交通及其速度就是军事斗争取得胜利之保障。早在1870年代,李鸿章出于防务之考虑,提出架设电报、修筑铁路,“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① 民国初建,汤寿潜说:“铁道之用,以速统一,固军防。”② 无疑,在列强环伺、狼烟烽起的近代,战争对新式交通的建设与发展影响至巨。那么,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建设间的关系如何?战争是如何对交通造成致命破坏的?其破坏程度如何?新式交通作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其破坏之后续影响如何?本文以浙江抗日战争与新式交通为中心,进行初步分析。
十年成就: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建设高峰
(一)首屈一指:主要成就及其地位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推进交通建设。如国民党“五大”报告,发展交通“以适应国计民生之需要……必须全国上下全力以赴之”。③ 在内忧外患之下,在十年经济建设的高歌声中,在主政者以“筑路为今日唯一要政”思想主导下④,1927-1937年浙江新式交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其中,轮船航运发展最快。民初十年,新式航运业发展到了高峰,“把小轮船航线推广到当时按自然条件能够通航小轮船的几乎所有河流和港道”。⑤ 水乡浙江进入以轮船为特征的“船老大”时代。国民政府时期,以“航政为交通要政之一,”但“因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内河航权,丧失殆尽”。⑥ 这一时期主要以拓展各大水系航运潜能、增加联运为主,是民国初年以来轮运高峰的持续。在铁路建设方面。到抗战前全国铁路达1.3万千米,浙江有浙赣、苏嘉、江南、杭甬铁路及钱塘江桥建成,浙江铁路建设进入第二个高峰时期,浙赣线“完全以本国资本人才建筑,并自通车以来,一切管理设施,多能就客商便利方面着想。旅行该路者,每有后来居上之感觉,使社会人士对停滞已久之铁道企业,为之信念一新。”⑦ 公路建设始于1920年代,国民政府成立后,公路开始纳入国家建设规划。1936年6月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11.73万千米,浙江近3700千米,其中1934年完成1600千米,这是浙江公路建设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为民国之顶峰。⑧ 公路网基本完成,“此后已由工程重心时期而转入业务重心时期”。⑨
浙江交通建设在全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铁路来说,沪杭甬线是1900年代中国民营铁路发展的样板,主持者汤寿潜堪称民营铁路之父;浙赣线是1930年代省营铁路的样板,张静江极力倡议、积极融资并最后建成了一条“几十年前的人所认为不必要或者是不可能的”、从浙江内地通向南方的陆地交通线⑩,被称为“中国新铁路之父”。(11) 业界评说:“以我国物质文明之落后,建设经费之难筹,杭江铁路之工程计划似足为从事建设者之他山片石,而各省之闻风兴起次第修筑。”(12) 浙赣线是1930年代中国筑成的线路最长、最重要的铁路。1935年6月底,铁道部统计全国共有铁路10247千米,其中浙江637千米,其他如江苏1159千米、安徽489千米、广东598千米、江西213千米、福建仅28千米,浙江为长江以南地区之冠。(13)
浙江公路是全国的典范,好评如潮。“近十稔以来,言省道兴筑,浙江实为各省先进”。(14)“近年浙江之得为国人所称赞者以此,而浙江当局之夸示于人者亦以此”。(15)“察全国各省公路之建筑,与浙江省公路建设比较,浙江省公路建筑之成绩,当首屈一指”。(16)“有人还说是中国的模范省”。(17) 据《申报年鉴》,1935年浙江与周边苏(7670千米)皖(6907)赣(10260)闽(6924)4个省份相比,总长最短(4676),但已通车有路面者与总长之比却最高达到67%,达3136千米,仅次于江西(3999),几近苏(1280)皖(962)闽(1301)三省之总和。(18)
(二)三轮驱动: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
推动浙江交通建设的原因主要是面临的经济建设、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
从经济建设来说。经济发展推动交通进步,浙江省第一家长途汽车公司杭余公司在其《章程》中规定:“承筑省道,通行汽车,以便利客商运输货物为宗旨。”(19)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认为宁杭公路,“就商业而言,因有兴筑之必要,就政治军事言,尤非兴筑不可”。(20) 杭江铁路是“为谋浙东启发富源,振兴实业,灌输文化起见,爰有建筑铁路之议”。(21)
就政治斗争而言。大革命后共产党从城市走向山村,在江西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艰难之路。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提出“交通剿匪”。熊式辉说:“交通为剿匪必要之工具,主张应多筑公路及铁路,以利军事之进行。”(22) 浙江因毗邻江西,交通建设也被披上了浓重的政治斗争之色彩。杭江铁路是(杭州—玉山)因发展地方经济而建,南京认为有利于江西“剿匪”,从而推动其后期建设。
尤其是军事斗争的需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警觉到铁路不只是“实业之母”,应列于当务之急的“国防的经济建设”之中,积极“利用外资建造新路”。(23) 一二八事变以后,把连通大后方作为基本方针之一,并把“一切交通事业,除商业化外,尤应注意于军事化。”(24) 华北事变后,我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长后制订“五年铁道计划”,以适应国防之需。作为国防前线,浙江交通建设尤显重要,苏嘉、浙赣、江南三线,“成长于战乱之秋,非仅足以振兴实业,提高文化水准已也,对于救国救民,贡献尤多”。(25) 尤苏嘉铁路,因“淞沪停战协定”规定日军永久停驻淞沪闸北、江湾等地,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和经上海调动中转。建成后苏嘉间铁路缩短行程110千米、旅行时间缩短2小时,但它主要是为了避开上海另辟一条从南京直下杭州的战略通道、“增强国防而设”的军事运输线。(26)
公路建设也是一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浙江沿海作为上海的南翼,政府积极防备。1932年9月24日,蒋介石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宁波各要塞至后方交通各道路,有否切实进行……限于今冬明春农暇时完成”;27日又电令“乍浦澉浦交通道路,亦请照新定防御方案道路图,着手积极进行。”(27) 次年4月18日,蒋又致电曾养甫,询问义东嵊、丽云龙、鄞穿、昱徽、建淳徽五路,“无论如何,应提前筑成。如经费不足,准由中央设法垫借五万元”。6月14日,又致电鲁、曾,指示屯溪至兰溪、奉化至宁海“建筑费准由军委会每月共津贴洋叁万元,限期完成”。(28) 积极疏通从沿海前线到大后方的交通线路。
其实,大敌当前,交通线路的建造与否、走向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战争,一切服从抵抗侵略之需。战时交通部长张嘉璈说:“抗战固以交通为命脉,而交通的维系,更以抗战的前途为依归。”(29) 可不是吗,国之不存,枉论建设!
(三)大规模建设:以防守和撤退为目的
如果说苏嘉铁路是南下绕越上海的军事运输线,那么浙赣铁路、江南铁路就是为了战略后撤之需赶建完成的,它们与长江水道一起构成国民政府后撤的主要通道。
杭江铁路设计之时,“所研究,则全限于经济、商务与社会之利益”。(30) 中央政府和银行对其“不无怀疑之处”,认为“杭兰一段对于国防及经济价值,甚为有限”。(31) 但当通车至金兰时,参谋本部认为“铁道事业之发展,与国防上交通运输关系至为深切”,对杭江铁路进行调查。(32) 杭玉全线建成通车后,政府认为“于国防具有极大价值……杭州直达广州,接通香港,浙赣湘粤打成一片,一旦中日有事,长江封锁,东南各省仍可脉络贯通”。(33) 1933年2月2日,铁道部决定提前修建浙赣铁路。(34)
浙赣线在抗战中发挥巨大作用。从1937年7月7日至12月23日,所有华北各路段及京沪铁路机车车辆以及重要器材物资,由此疏运至西南;难民似潮水般地涌去后方,两广军队籍此东开赴援。仅炸钱塘江桥前一日有机车300多辆,客货车2000多辆过江。(35) 后张嘉璈略带自豪地说:“浙赣路所收获之价值,实千百倍于所投之建筑资金。若作者就职之始,稍稍迟迴,则是否能得此莫大之收获,未敢必矣。”(36)
其后,浙赣线虽随战争形势节节阻断,尚能逐段运输,与后方保持联系。至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全国铁路大多残破,惟一完整的为湄池至株洲的浙赣铁路;到1942年,皖浙闽赣数省仍连成一片,因其交通运输得以维持。外洋物资经海口或透过沦陷区经浙赣线输送到后方。从1938年7月至1939年3月,仍每日开行金华至株洲,直至桂林列车。从1937年7月到1942年底,浙赣铁路运输人数为346万人次、其中作战人员226万人次,作战部队2068列,军粮、被服、枪支弹药、器械等近47.5万吨。(37) 行政院高度评价“其对战时经济,更有重大贡献”。(38)
江南铁路原为沟通华中与华东之陆上联系,但为应对战争,线路设计经历三变。1932年4月,张静江联络李石曾等,依孙中山东方大港的计划,组建江南铁路公司,修筑乍(浦)芜(湖)铁路,蒋介石也加入为股东。(39) 华北事变后,铁道部加紧修建东南铁路,因京沪路濒海,另选京衢线作南京西向之运输线;“嗣以此路离海边太近,且沿线无甚出产”,改定京赣铁路。(40) 抗战全面爆发,该路成为撤退的运兵铁路。1937年11月8日,全部拆除。该路从1936年5月开筑,“费时一年有半,耗资3800万元,不特不见其完成,且由建设而转为破坏,伤哉”。(41)
八年摧残:新式交通的噩梦
(一)争保弃破:轮番上演的翻手戏
交通作为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军队的生命线。在空间上表现为对战争物质流的控制,瘫痪敌方交通,阻断其兵力移动、火力转移和物资输送,也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战略内容和迅速结束战争之捷径。敌对双方围绕交通线,防与攻、运与阻、修与破,展开异常激烈的“保交”、“破交”作战,并成为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
“日本军阀南侵之初,即以破坏或封锁我铁路交通为鹄的”。(42) 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就开始对我后方尤其是交通设施进行重点轰炸。此后,凭其空中优势,以轰炸作为对我进行纵深打击和军事进攻的前奏。在从八一三事变起的两个多月中,京沪铁路遭敌机轰炸达264次,沪杭铁路达128次,“当沪战剧烈之际,被敌机炸伤京沪路机车69辆,客货车96辆。沪杭甬路机车28辆,客货车207辆”。(43) 沿线各站“几于无日不炸,愈炸愈烈”。(44) 为切断我唯一后撤退路,对正在紧张施工中的钱塘江桥进行轮番轰炸。1939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企图割断浙赣铁路,以切断皖浙我军联络线。(45) 3月17日,攻占南昌,浙赣铁路被拦腰截断。1941年,浙赣铁路东段“沿线轨道及建筑物被炸损害共计有五十二次之多”。(46)
任何交通设施、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均是中性的。为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要千方百计地修筑与保护它,一旦落入敌手,又将成为打击我方之利器。《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说,为己“务尽万般手段,尽量利用所有机关,而增大其输送能力”,为“不资敌用计,应预有破坏之准备,其破坏之程度,则按国军尔后之企图,而决定之”。(47) 抢运与破坏成为撤退中的主要工作内容。
1937年11月6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为阻止敌人进攻,我拆除上海松江48千米路轨;12月,日军增兵嘉兴,图犯杭州,沪杭线所存机车车辆材料一律移至浙赣线。为封锁钱塘江,12月23日下午5时,我主动炸毁钱塘江桥;杭州沦陷后,我将江边至诸暨64千米路线、桥涵彻底破坏。(48) 但因撤退无序,除抢运出机车车辆和物资以外,对京沪、沪杭、苏嘉路均未彻底破坏,反为日军利用,迅速推进。为吸取教训,黄绍竑令浙东实行焦土抗战,1937年底将甬曹段、曹萧段全部拆除,因曹娥江桥尚未竣工,将东段车辆拉至丈亭站附近焚毁,将机车拆卸沉于江中。(49) 次年2月又令“拆毁曹甬段铁路及观曹段等公路之路基”。(50) 如杭徽公路破路历时三年,“凡已经破坏之公路,其填土部分路基高广在二公尺以内者,应一律化路为田,其在一公尺以上者听便”。(51) 临安仅1938年1-8月份动用民工20万人次;日军在临安的侵扰,也限于化龙以东,限制了敌人的机动能力,减轻了皖南、赣东大后方的压力。
为扩大侵略和有效进行殖民统治,日军急于修复交通线路。沪杭线于1938年1月修复通车,浙赣线杭州至金华段也于1943年1月修复通车。1940年5月9日,陆军中将兵团长土桥一次在浙江治安委员会会议上训示“通过爱路村保证铁路的安全,维修、开通和确保主要公路、水路和通信线路。”其特殊需要维修、保养和开通的主要公路有杭州-湖州、塘栖-武康等8条线路,水路有杭州-湖州、菱湖-新市等9条线路。(52) 在岱山,“当时日兵为更好控制东沙,打击游击队,就修建马路,通行汽车……阿拉当地的顺口溜了:‘吃吃六谷糊,做做汽车路,性命还在司令部’”。(53)
在敌后,抗日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破交斗争。“沪杭公路上敌军交通线均被我军破坏”。“我冲越钱塘江北之游击队……旬日以来,拆毁沪杭铁路廿余段,沪杭线已不能通车。”(54) 武汉沦陷后,军事委员会“拟修正作战计划草案”指出:“我军转进时,应将各公路、铁路按所规定之破坏交通计划,彻底破坏之。”在1939年《夏季作战计划》又令第三战区“积极破坏京沪杭交通”。(55) 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谭震林说:“(只有)控制长江,控制京沪、沪杭、苏嘉三条铁路,才能迫敌(日军)于死地。”(56) 1944年8月3日,毛泽东等致华中局:“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57) 据华中铁道公司(下称华铁)《公司营业年报》资料,仅1941年度敌后抗日武装对沪杭线和苏嘉线实施的列车出轨、炸毁桥梁、妨碍通车等各类袭击事件分别是34起和11起,估计损失分别为24.1万元与7.3万元。(58) 在浙北,原有可通车公路841千米,因游击队的破坏和侵略者只用不养,实际通车里程仅283千米,占可通车线路的1/3。
(二)独立战场:沿铁路线展开的三大战役
七七事变后,我奋起抗日,铁路沿线首先变为战场,全盘铁路计划发生根本变动。面对敌人的纵深攻击,交通线成为首先打击的目标并呈现独立战场之趋势。浙江战场围绕交通线展开,1937年的沪杭线战役、1941年的宁绍战役、1942年的浙赣战役,夺取或者毁坏交通线成了战争的基本目标。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并宣布:“兹以外侮紧迫,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各市、县及鄞县、镇海等处,着自即日起宣告戒严。”(59) 10月底,淞沪会战进入僵持状态,日军转而大规模增兵,11月5日在杭州湾北岸强行登陆,一路直扑沪郊,一路“顷注全力于公铁路正面,以期突破一点,进逼嘉善”。(60) 作为淞沪会战的延续,嘉善阻击战激战七昼夜,在沪杭线上咬住敌人,为我军转移赢得时间。12月初,张发奎部频繁破坏交通线,阻止敌军之进攻。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主力沿津浦线北犯的同时,为完成对沪宁杭三角的占领,其第10军沿公路铁路南犯。24日晨,杭州沦陷。浙江战局出现隔江对峙局面。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但原先相对平静的钱塘江南岸地区,发生了宁绍战役和浙赣战役,这是浙江两次规模最大的正面战场战役,也是抗战中期正面战场的重要会战。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浙东沿海的镇海、石浦、海门、瑞安实施登陆,发动宁绍战役。日军仅用二周时间,占领了杭甬线曹甬段两侧、杭州湾以南整个宁绍地区。从1942年5月15日至同年6月底止,日本为防止盟国空军利用浙赣铁路沿线的机场进攻日本本土,企图打通浙赣线,占领或破坏铁路沿线的中国机场,并掠夺武义、义乌、东阳等地的萤石矿,在浙赣发动所谓的“铁道作战”。8月,日军基本撤退。在东西夹击下,浙赣铁路两端均无出路,所有机车、客货车、机厂等无法撤退,除自行对其破坏,日军攫取重铁轨6.4万条、轻铁轨2万条、机车6辆、其他车辆39辆。这些器材除了为运输萤石用于修复浙赣铁路之外,大部分被掠往东北,浙赣铁路毁损殆尽。(61)
(三)残酷榨取:侵略者的掠夺式经营
日在华交通政策经历了一个以军事攻防为主到经济掠夺为主的过程。“在军事行动的初期,日本在沦陷区的交通适施,多侧重于军事的意义,还没有顾及其他……军事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的交通政策即迅速转而侧重于经济的掠取”。(62)“敌人战略,首在夺取铁路线,以谋军事运输之便利,次为夺取资源,以达以战养战之目的”。(63)
日军在侵占浙江期间,也修复或新筑过一些道路。如为盗运武义萤矿修筑了金华至武义铁路支线、修复金华至杭州段铁路,新筑了海宁长安线、长安硖石线、金华诸暨线等公路。(64) 至1944年,修复公路杭笕、杭六等24条公路,约500千米;增筑了余杭仇(山)石(濑)、余(杭)仇、余石路26千米,海宁杭县硖(石临)平路50千米。(65) 对当地的交通起到了一定改善作用,如苏嘉铁路修复通车后,因商品短缺,这里成了单帮客之首选捷径,1942年的铁路客货运量大幅上升并达到最高峰。
但这种改善,在服从日伪军事之需为其侵华输送军队和军需之外,为更有效地掠夺中国财物。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浙江的民用物资、战略资源,从上海走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日本;其后,则通过华北、东北、朝鲜运送到日本。日军还期待浙赣线能成为其航空工业不可缺少的“萤石直通运输”线,估计在其盘踞武义的3年中,每天用工1500-1600人,每天约开采氟石110万斤。(66)
在沦陷区,对交通进行军事接管、垄断经营。日军在华东侵占之交通线,始由“华中军铁道部”负责修复整理,1939年4月28日汪伪政府与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签约,创设中支铁道株式会社,即华铁,“担当以华中一般运输为目的之铁道之建设及经营,并依于主要路线之汽车运输事业之经营。公司以外不另承认此项事业”。(67) 统制经营华中铁路,包括前述沪杭、苏嘉、江南和京沪铁路等,还垄断华东地区的长途汽车运输。(68) 其实华铁是直接听命于华中振兴公司,并在日军管制之下。其在浙设杭州汽车区1个,萧山、绍兴2个办事处,配备客车29辆、货车13辆,经营全长626千米的杭州-湖州、萧山-宁波、嘉兴-苏州等19条线路。(69)
市内交通方面,早在我军从苏南浙北撤退后,日军即以“中兴公司”的名义经营公共汽车业,1938年3月,设立但马佑治公司经营杭州的汽车运输业务,开行1路迎紫路(今解放路)至拱宸桥、2路迎紫路至灵隐两路市内公交线。1938年11月5日,但马佑治在上海成立华中都市公共汽车公司(下称华都),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设营业所,在无锡、镇江设立办事处,统制经营华东主要城市的市内公交。杭州运营线路除上述1、2路外,增开3路迎紫路至南星桥、4路城站至圣塘路日本特务机关门前两路公共汽车。
八一三事变后,江南水上交通一度停顿,后以日资日清汽船公司为主体,组织江浙轮船公司,作为内河航运之统制机关。1938年7月28日,在该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内河轮船公司,经营华东地区内河航路之客货运输、船舶贷借、仓库及码头等业务。为垄断华东地区陆上运输,1941年又成立华中陆运公司。1938年12月16日,创立中华航空公司,强化统制占领的华东地区的航空事业。(70)
这样,这些殖民侵略机构控制了华东地区所有的新式交通事业。(71) 除了垄断经营之外,还享有种种霸王特权,不交养路费,不交营业税,只顾组织运营,不问设施建设。如华中都市公共汽车公司,一直不交专营费,汪伪铁道部公路署交涉无果,上报汪伪行政院也无功而返,因其享有免税特权。(72) 而华铁也是“特殊法人”,其“特典”规定,“对于公司之财产所得及营业,公司之契约登记及登录,并公司事业必要之物件之租税及其他一切公课之免除”、“对于事业有关之土地及其他物件与权利之征收之免除”。(73) 中华航空公司除了独占航空事业、国有机场独占使用权之外,享有“对于航空事业必需品之关税及其他一切公课之免除”。(74)
这些侵略机构对华东地区进行无耻掠夺。华都共有车辆205辆,仅1939年盈利373558元;1941年4-9月,在杭州只投入营运客车11辆,日均行驶806千米,载客1385人次,日均收入高达416.29元。中华轮船公司1940年度盈余111578元。上海内河轮船公司1940年度纯益高达20万元。华铁1941年3月份营收6130110日元。(75) 1943年度实际维持的行车线路455千米,营收97346日元,行车里程482484千米。(76)
1942年7月华铁、振兴、中华轮船公司、上海内河轮船公司等联合成立华中运输公司,专营蚌埠以南华中日占区的货运业务,资本总额800万日元,其中中国人的股金仅1000元,仅占0.125%。在杭州、嘉兴、金华等开设支店。其杭州支店拥有运货汽车28辆,马车30辆,双轮手推车35辆人,汽轮2艘,拖船数只,独揽转运业务,仅成立的1942年上半年就获取纯利185000元,下半年高达363000元。(77) 通过行业垄断,榨取高额利润。
从运输结构来看,只重货运发展,对人民生活所需之客运却弃之不顾。据华铁1939年10月《事业计划说明书》记载,沪杭线1939年与1934年相比,日均旅客人数从10053人下降到155人,日均发货吨数从1829吨下降到797吨,分别只是原来的1.5%和43%。另据该公司1941年《公司营业年报》记载,1939、1940、1941年3年中,军用货车与运输用货车总数之比率从10.4%、11.4%上升为13.4%,而民用车辆则从18.7%、16.4%下降到14.3%。(78)
卅年恢复:被透支和截断的交通现代化
(一)另类促进:对社会财富透支式的破坏
前述浙江新式交通建设之成就与地位表现为一种量之累积,而质之变化则表现为战争对交通现代化之促进作用。
其一,抗日战争也把浙江的新式交通建设推上了一个高峰。交通运输保障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一个结合点,“平时要如战时之紧张,以预备一切,战时才能如平时之安定,而战胜一切”。(79) 但浙江新式交通的建设,开始是以发展经济作为第一需要来进行的。如有军事目的也仅仅作为一个应急的预案,一种将来可能出现的假设。随着战争乌云的迫近,这种假设也就变成现实。
同时,抗日战争也把浙江交通现代化水平推倒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战争促进了交通发展。一是技术水平。如双层公铁两用的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当时的中国甚至是世界上均已达到先进水平,是中国二十世纪桥梁的帜树。1934年11月11日,曾养甫在大桥开工典中说:“预定自开工日起,再有一年半之时间,即可完成。”(80) 1935年4月6日正式动工,1937年9月26日才正式通车。钱塘江为流沙河段,古称“无底”,水深沙厚,变化莫测,水流汹涌,冲刷力强,工程挑战大;加以经费少,工期紧。在茅以升(1896-1989)主持下,采用气压法沉箱掘泥打桩,在流沙不定的钱塘江上筑起9座桥墩,为大桥主体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大桥炸断后,日本人一直无法正常修复。
二是管理水平。“吾浙公路素负模范之称……至于建筑之完善,管理之周详,尤为他省人士所称道”。(81)“浙江省内公路交通吧……除了极少数偏僻县区以外,几乎都有公路线通过或到达,通车的情形都相当良好”。(82) 如制度保障,仅《浙江省建设月刊》第7卷第3期(1933年9月)上就刊登《浙江省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及长途汽车公司管理规则》、《修正浙江省管理汽车暂行章程条文》等6个管理法规。1930年代浙江公路管理上均达到了意想不到的高度,成为全国的样板,国联专家进行专门考察。浙江省公路局局长、总工程师陈体诚(1894-1942),把浙江公路建设推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1930年10月,陈体诚等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道路会议,会上将浙江公路建设资料进行散发,深得好评;翻译美国公路桥梁设计和路面施工规范、公路投资和收费的规章制度等,编写考察报告。提出“先求其通,后求其畅”之议,修通大量由平原深入山区的公路,在山区悬崖峭壁地段,首先采用“半山洞”设计。培养出一大批技术人才,散布全国各地,人称“浙江是我国公路的摇篮”。(83) 同样,铁路建设也取得骄人成绩。如修建杭江铁路,经费严重匮乏,工程专家们精打细算,“固本简末”,终于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节约措施,以实现适合于当时社会需求的运输能力。其建造费用每千米37000元,仅为国内同期的120000元的1/3;建筑平均工期为两天1千米,开创我国铁路建筑工期的新记录。(84) 负责本路修筑的杜镇远,是继詹天佑后的又一位铁路专家。
这种进步与发展是中国政府与人民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造成的结果,是在政府优先发展的策略下展开的。晚清至民国时期,“国中生产事业规模之宏大,当莫国营铁道若矣。今日之国营铁道,论里数则有一万余公里,论经过之区域则有十九行省,论资产则约有九万万元”。(85)《中国实业志》中说:“浙江建设事业,其发达较早者,厥惟公路。”(86) 交通建设及其成就是近代浙江投资最大、成绩最大、水平最高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战争大背景下,政府集中力量发展交通,尤其是经济不发达,作为政府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有效地集中了仅有的社会资源着力发展新式交通。
1931年浙江省财政概算为2119万元,1932年浙江省收支预算为2800余万元,后经缩减预算,1933年浙江省收支已均为2100余万元。(87) 整个1930年代,仅浙江铁路的建筑费用如下:苏嘉铁路为280万元,浙赣铁路杭玉段近1700万元(其中包括300万元后续的道路加固费用),完成沪杭甬铁路(其中钱塘江桥532万元)为1880万元(88),合计3860万元,这是1929年浙江全省财政收入2940万元的1.31倍,是当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841万元的4.59倍(89),是1937年度浙江省财政预算3023万元的1.27倍。(90) 1937年全国交通建设投资占各项建设投资的34%(91),浙江远在此之上。交通建设是当时投资比例最大、建设成就最高的建设项目。无疑,这种投资与促进是以对社会资源、财富的严重透支为代价的。据统计,1936年全国新筑公路里程19449千米,经费为2287276元;而1937年新筑公路里程仅1594千米,经费却高达12522496元。(92) 其原因是建设的半途而废,战争中交通线路、交通设施与交通工具惨遭无情破坏,并趋衰败。
(二)一场浩劫:直接的与间接的损失
抗战期间,浙江交通遭受重创。如铁路,沪杭线沦陷,钱塘江新建大桥轰然炸断;杭甬铁路萧百段尚未正式通车,惨遭拆卸。长兴煤矿轻便铁路,1938年破坏停用。(93)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湘桂作战,拆除苏嘉线,移修岳州与株洲间铁道。浙赣铁路屡兴屡废,抗战胜利时仅存杭州至诸暨、江山至上饶两段线路。
同样,浙江公路也破坏严重。“迨抗战军兴,吾浙地濒沪海,敌寇首先侵扰,全省公路破坏殆尽,损失之巨,亦较他省为甚”。(94) 战前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3716千米,但战争期间破坏里程(不包括重复破坏者)为2424.44千米,加上沦陷的841千米,共计3265千米。(95) 浙江公路的4/5公路毁于抗日战争。如杭徽公路,黄绍竑说:“那时奉令破坏了……这条公路在这矛盾的心里之下就破坏了去,也可以说这是浙江公路大破坏的开始。”(96)
另外,战争破坏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实物的,还有正常营业的中断、投资的无法回收、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等。如杭徽公路于1937年11月15日停止营业,1938年实施破坏,直到1947年4月21日全线修复,停业长达9年5个月。据《杭徽公司民国廿五年10-12月份营业统计》,以日平均收入700元计,近十年中,损失营业收入达250万元(以战前币值计)。(97) 另据统计,抗战期间交通部门因公受伤者为1657人,死亡为4211人。(98) 如浙江公路的奠基人陈体诚1942年4月就在昆明殉职。又如交通的空前破坏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困难,“战时的行路,可以当作故事来讲,许多离奇的遭遇,信不信由你:‘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这并不算是奇事”。(99) 交通要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致命打击,如海门,“在抗战以前轮帆栉比,商业甚盛。今则受敌舰、敌机之炮击、轰炸,市面凋零不堪”。(100)
就日本侵华战争给浙江造成的破坏与损失,专家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101) 就浙江交通而言,可分二块。一是战后铁道部的统计。就已报铁道部者,计损失时之币值为1237260397932元(1945年9月币值为426650946290696元)。其中,国营铁路为846300169412元、公营及民营为10925980230元。(102) 浙赣、沪杭甬、苏嘉三线的直、间接损失,以1945年9月币值计,共为42774024万元,约4300亿元。当然,以上三线共计约1400千米,其中在浙江境内约660千米,加上钱塘江大桥,浙省损失应该略高一些,可定为2300亿元。(103) 二是,其他交通损失。据1945年底浙省政府统计室资料,抗战时期公路水路遭受的实物损失:公路2770千米,县道20830千米,汽车523辆,手车9913辆,船38246只,汽船60只。据1945年底现值估计,手车19826万元、船238476万元,汽车、汽油、修理机械等134800万元,公路581285万元、县道214300万元,合计1188687万元。(104) 因铁路之间接损失为直接损失的6.7倍,公路、轮运投资较铁路为少,见效更快,则间接损失更大,如设为10倍,则损失为:直接1188687+间接1188687×10=13075557万元,约1300亿元。
日本侵华战争给浙江交通事业带来的损失,水公铁三项合计达3600亿元。
(三)阻断与延误:战争破坏的一个时间评估
从战争后续影响来说,战争对新式交通的破坏是致命的。
首先,以战前的平均建设速度来看。有人估计修到战前的水平约15年才能恢复。(105)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扩大内战抢修津浦铁路,于1946年拆除江南铁路,1948年再度辅轨营业,但已无往日的繁华景象。浙赣铁路1946年开始逐段修复,1948年12月才全线修复通车。1948年3月底,浙江省公路有路面的通车路线为2268千米。(106) 到1949年4月人民政权接管之前为止,全省通车营业里程只恢复到2371千米,且其中1512千米只是勉强可以通车的,仅及抗战爆发前的40%。(107) 到1957年,全省公路里程达到4962千米,才从量上超过了抗战以前,全省82个县中有75个可通汽车,不通车的为嘉善、桐乡、崇德、德清、嵊泗、象山和泰顺7县。其实,这些县抗战之前或多或少都是有公路(或在建中),至此也仅为简单修通,其恢复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其次,按实际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来看,约需半个世纪。如果以恢复与发展之间划出一条时间界线的话,可以认为这个时间点约为35年,也就是直到1980年前后,浙江的交通才开始摆脱战争带来的历史重负,起步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而这距离日本侵入浙江,已近半个世纪。可以说1980年代初,浙江交通建设的总体水平基本上停留在抗战前夕1930年代的水平线上。笔者曾于1986年5月,对杭嘉湖市镇进行过实地调查,一些街区还保留着为日军火烧的残迹。从铁路建设来说,萧甬线从1953年开始重建到1959年才正式通车;杭宣段要到1994年才正式建成,至今湖嘉铁路还在规划之中,苏嘉铁路依然是水月镜花,东方大港计划不复存在。直到1990年代浙江铁路复线和金温铁路建设,才发展成为20世纪浙江铁路建设的第三个驼峰。其中沪杭线复线是1993年建成;浙赣铁路复线于1994年12月全线建成通车,其运输能力提高69%。第二座公铁平行的钱塘江大桥于1993年建成通车,成为浙赣、沪杭甬铁路复线之枢纽。公路以前述1957年未通车的嘉善县为例,1936年11月10日杭枫公路从清泰门到枫泾通车营业,(108) 次年上半年沪杭全线通车,是320国道今天上海到云南昆明畹町的一部分。1937年4月,善西(塘)、焦善公路建成通车,全县公路总里程为38.6千米,抗战期间破坏殆尽。杭枫公路就此废弃,连路肩多被垦殖,33年之后的1970年6月20日才修复通车,1987年换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善西公路要到1971年修复通车。在桐乡,杭枫公路境内有约30千米,1959年修复通车,并且是县内唯一之公路,其它如石门1982年、屠甸1983年、乌镇1984年,才通公路。嘉善、桐乡是浙江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公路交通的欠发达,与该地水运发达密切相关,但主要是战争破坏的后遗症,代表性地反映了战争对浙江交通发展带来的影响。
无疑,日本蓄意发动的侵华战争打断了浙江新式交通建设,并使之延误约半个世纪。
注释:
①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鸿章全集》第2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31页。
②汤寿潜:《〈浙江铁道史〉题辞》,政协萧山文史委《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印,第507页。
③秦孝仪主编《抗日战争前国家建设史料:交通建设》(《革命文献》第7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10页。
④曾养甫:《浙省建设当前之两大任务》,《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9期(1932年3月)。
⑤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
⑥秦孝仪主编《抗日战争前国家建设史料:交通建设》,第278页。
⑦《中央日报》1936年1月15日。
⑧徐望法主编《浙江公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45、238页。
⑨《浙公路网大体已告完成》,《大公报》1935年11月28日。
⑩阮毅成:《浙东西二十五县》,《阮毅成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217页。
(11)周贤颂:《中国新铁路之父:张静江先生》,国民党党史会编《张静江先生文集》,1982年版,第372页。
(12)“曾养甫序”,杭江铁路工程局《杭江铁路工程纪略》,1933年版,第1-2页。
(13)申报年鉴社《(第四次)申报年鉴》,1936年版,交通编N第3页。
(14)“程振钧题词”,浙江省道萧绍段《浙江省道萧绍段三月刊》第1期,1928年版。
(15)洪瑞涛:《铁路与公路》,交通杂志社1935年版,第253页。
(16)黄霭如:《浙江省公路建设之研究》,《浙江省建设月刊》第4卷第6、7期(1931年1月)。
(17)曾养甫:《公路建设同人之努力方针》,《浙江省建设月刊》第7卷第8期(1934年2月)。
(18)申报年鉴社《(第四次)申报年鉴》,交通编N第14-16页。
(19)陈惠民:《承筑杭余省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创办概况》,1924年编印,规程第1页。
(20)刘荫棠主编《江苏公路交通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133页。
(21)杭江铁路工程局《本厅所属建设机关工作概况》,《浙江省建设月刊》第4卷第11期(1931年5月)。
(22)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62页。
(23)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737页。
(24)秦孝仪主编《抗日战争前国家建设史料:交通建设》,第281页。
(25)浙赣铁路局《浙赣铁路统计年报》(民国三十五年),第1页。
(26)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杨湘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39页。
(2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292、293页。
(28)“总统府机要档案”,浙江省档案馆《浙江民国史料辑要》上册,2002年印,第619、622页。
(29)张公权:《抗战与交通》,国民政府交通部《抗战与交通》第1期(1938年3月15日)。
(30)“踏勘杭江铁路线报告”(1929年5月16日),浙江省档案馆L085-002-3177。
(31)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37页。
(32)“浙江省政府训令秘字第4934号”(1932年5月4日),浙江省档案馆L085-002-3177。
(33)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54页。
(34)《铁道部筹划先筑浙赣铁道》,《申报》1933年2月3日。
(35)茅以升:《钱塘江建桥与炸桥的回忆》,方吾权《杭州抗战纪实》,1995年印,第186-187页。
(36)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55页。
(37)据金士宣《铁路与抗战及建设》(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7-39页统计。
(38)行政院新闻局《浙赣铁路》,第6-7页。
(39)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769页。
(40)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802页。
(41)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143页。
(42)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页。
(43)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第176页。
(44)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141、143页。
(45)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4页。
(46)《浙赣铁路局三十年度工作报告》,浙江省档案馆L086-1-990(1),第24页。
(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48)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143-144页。
(49)史理斋:《甬曹段铁路沿革》,浙江省政协文史委《浙江文史大典》,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03页。
(50)“浙江省政府秘机字第冬号代电文一件”(1938年3月2日),浙江省档案馆L085-002-3177。
(51)“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令”(1939年7月27日),转引自王国林《东南抗战前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52)浙江省档案馆《日军侵略浙江实录》,第139-141页。
(53)袁成毅、丁贤勇主编《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54)《浙西我军向乍浦挺进》、《沿沪杭线》、《京沪沪杭线游击队活跃》,《申报》(汉口)1938年4月16日、(香港)4月19日、(汉口)6月24日。
(5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70页。
(56)无锡市委党史委《平原水乡任驰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57)浙江省档案馆《浙西抗日根据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2页。
(58)〔日〕浅田乔二等:《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袁愈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59)《中央日报》1937年8月14日。
(60)浙江省档案馆《日军侵略浙江实录》,第5页。
(61)〔日〕浅田乔二等:《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第371、385页。
(62)郑伯彬:《日本侵占区之经济》,资源委员会1945年版,第224-225页。
(63)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225页。
(64)郑伯彬:《日本侵占区之经济》,第236页。
(65)章颐年总编《浙江省政概况》,浙江省政府(汪伪)1944年版,第137-139页。
(66)浙江省档案馆《日军侵略浙江实录》,第587页。
(67)陶希圣:《长江下游的日本经济独占组织(各种经济密约及密件)》,1940年印行,第12页。
(68)陶希圣:《长江下游的日本经济独占组织》,第30页。
(69)浙江省公路交通史编委会《浙江省公路运输发展史》,1985年印,第115页。
(70)上海市档案馆《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298-302页。
(71)日伪还成立民船公会,将民船强制性地改组为“日本掠夺物资的运输工具”。见〔日〕浅田乔二等《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第370页。
(72)徐望法主编《浙江公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页。
(73)陶希圣:《长江下游的日本经济独占组织》,第18-19页。
(74)上海市档案馆《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第301页。
(75)上海市档案馆《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第298-302页。
(76)张涤铭主编《浙江公路运输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131页。
(77)浙江省公路交通史编委会《浙江省公路运输发展史》,第112页。
(78)〔日〕浅田乔二等:《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第47、352、361页。
(79)张公权:《蒋委员长之五年铁道计划》,《铁道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16日)。
(80)钱塘江桥工程处《钱塘江桥开工纪念刊》(1934年11月11日),第6页。
(81)钱豫格:《复员以来之浙江公路》,《浙江经济》第3卷第5期(1947年11月30日)。
(82)《如何整理浙江公路交通》,《浙江经济》第1卷第5期(1946年11月30日)。
(83)徐望法主编《浙江公路史》第1册,第238页。
(84)“刘贻燕祝辞”,杭江铁路工程局《杭江铁路月刊》(全线通车纪念号),1933年12月28日版。
(85)麦健曾、朱祖英:《全国铁道管理制度》,交通大学研究所北平分所1936年版,第9页。
(86)实业部国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十编交通,1933年版,第20页。
(87)《浙省召开财政会议》、《浙省二十一年度新预算》、《浙省缩减预算》,《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1号(1932年1月)、第4卷第14号(1932年7月)、第5卷第4号(1933年2月)。
(88)新编《杭州铁路分局志》,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年,第139、103页;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57页。
(89)其中国税2000余万元、关税约156万元、省税784万元(见上海《时报》1929年4月2日)。浙江铁路建设,除浙江财政拨款、银行借款外,苏嘉路由中央拨款,钱塘江桥铁道部与浙江省承担各半。
(90)曹必宏主编《中华民国实录·资料统计》(第5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4页。
(91)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杨志信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1939-1944年,分别占65、80、72、73、65、73%。
(92)曹必宏主编《中华民国实录·资料统计》(第5卷上),第5301页。
(93)张雨才:《中国铁道建设史略(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94)钱豫格:《复员以来之浙江公路》,《浙江经济》第3卷第5期(1947年11月30日)。
(95)徐望法主编《浙江公路史》第1册,第145、155页。
(96)黄绍竑:《五十回忆》(中)重来浙江,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32页。
(97)浙江省公路交通史编委会《浙江省公路交通史运输篇下册资料长编》,1983年油印本,第四章第24页。
(98)俞飞鹏:《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京沪区铁路管理局会计处1946年印,第109页。
(99)曹聚仁:《万里行记》,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页。
(100)《台属各县军事政治经济调查报告》(1940年9月27日),浙江省档案馆,L069-001-0003。
(101)详见袁成毅《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2)俞飞鹏:《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第124页。
(103)俞飞鹏:《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第125页。折合现值为1945年9月份之币值。
(104)《八年抗战浙江省遭受的损失》,浙江省档案馆《日军侵略浙江实录》,第803页。
(105)徐望法主编《浙江公路史》第1册,第150页。解放战争中,交通设施又经战火之破坏。
(106)路局统计室《浙江公路统计》创刊号(1948年3月31日),油印本第1页。
(107)徐望法主编《浙江公路史》第1册,234页。
(108)《杭善路设站营业》,《申报》1936年10月25日。
